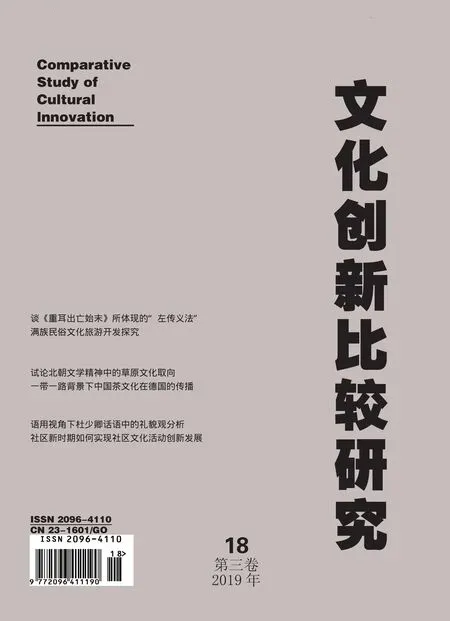论巴金小说《家》中的女性形象
钟祥瑞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
巴金先生在《家》中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里,既有鸣凤、婉儿、喜儿等身份低微的丫头,又有瑞珏、梅芬、淑贞等受旧礼教束缚的旧式小姐,她们备受社会制度的压迫,以不同程度的悲剧收场;也有紧随时代潮流,积极参与社会改革运动,以琴与许倩如为代表的新式女性,她们在社会思想接受方面有落后与进步的差别,但在两性关系极不平等的男权社会下都无法获得女性的价值认可以及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1 备受封建压迫的旧女性
在高公馆这个封建大家庭内生活着一系列受旧社会思想体制影响与控制的旧式女性,卑微的丫头们在最高统治者高老太爷的控制之下没有一点话语权,无尽的忍耐,默默接受一切安排;尊贵的小姐们看似光鲜亮丽,却在旧社会对女子的道德规范下逐渐失去自我。巴金在《家》的代序中写道:“我代那许多做了不必要的牺牲品的女人叫出了一声:‘冤枉’!”这些女性虽然各自遭受的苦难不尽相同,人生走向不同,但都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选择习惯性顺从、无奈地妥协,都成为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1.1 等级制迫害下的女奴:鸣凤、婉儿、喜儿
鸣凤、婉儿、喜儿同为高公馆的丫头,地位最卑微,受压迫程度最高。喜儿被嫁给太太选定的丈夫,又回到公馆继续做工,提起丈夫如何对她不好,常常独自流泪。婉儿代替鸣凤嫁给冯老太爷做妾,其妻常发脾气拿她出气。而鸣凤相比其他两位更幸运的是获得三少爷觉慧的真心,曾短暂地享受过普通人的爱情,但她也无法摆脱作为这个封建大家族的女奴的共同命运——无法选择自己的归宿。
鸣凤在高公馆待了七年,常常挨骂,在觉慧帮她折梅花时也嘱咐他不要让太太知道,她无时无刻不在惧怕这个家庭里的权威力量。她常在夜晚流泪,思考自己的未来,也曾幻想自己出生于富贵人家,备受父母的疼爱,享受家庭的温暖,但她知道“世间的一切都是由一个万能的无所不知的神明安排好了的,自己到这个地步,也是命中注定的罢。这便是她的简单的信仰,而且别人告诉她的也正是如此。”她深信命运却害怕重蹈喜儿的覆辙,只求保持生活的原样,尽管要承受太太无尽的责骂,但就这样一直留在主人身边做事已是一个奴隶最好的归宿。在被安排嫁给冯老太爷做妾时,她曾在心里坚定地反抗,然后不断哀求太太,最后选择投河以捍卫自己的尊严。
1.2 旧道德束缚下的小姐:梅芬、瑞珏、淑贞
梅芬与瑞珏的婚姻践行的是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家庭准则,女子在婚姻上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因为家人间偶然发生的矛盾,梅芬没能嫁给理想的伴侣觉新,之后的丈夫也是家里人安排的,爱情与婚姻上的打击使她一直活在痛苦与回忆中,经常自哀,感叹一切都是命,最后带着遗憾死去。除此之外,淑贞也是在封建压迫下成长的旧式小姐。从小被缠足,畸形的小脚曾被母亲作为引以为傲的标志,不但遭受身体上的痛苦,也并未迎来期待中的赞扬目光而是哥哥姐姐的嘲笑。“现在她刚上了十三岁,还是这样轻的年纪,她就做了牺牲品了。”裹脚的陋习也是旧礼教对女性的束缚,为了符合旧社会的“审美”标准,淑贞一类的少女从小便遭受着身体上的痛苦,无法自由行走意味着无法追求自己的幸福。
2 走向思想解放的新女性
小说中人物所生活的是一个新旧文化相接的历史转折时期,不少思想解放运动已经兴起,只是在四川成都这个相对闭塞的地区,敢于走向抗争的人并不多。但琴与许倩如则是为数不多的新派人物,时代的新女性。她们都积极地关注学生运动,念女子学校,读《新青年》等刊物,在旧社会最后的黑暗时期里勇敢呐喊,让人看到女性个人的光芒。但由于家庭环境不同,琴在做决定时往往考虑到母亲的感受,不如许倩如的大胆果敢与思想解放的彻底。于是,一个仍在旧社会中挣扎,一个则完全迈入新的时代。
2.1 徘徊于新旧社会的反思者:琴
相对身份卑微的鸣凤,琴有更多的人身自由,她也是大家庭的小姐,她的母亲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成为她的支柱。她能上女师,还决定考外师,期待男女同校,即使知道有困难也决定试一试,我知道任何改革的成功,都需要不少的牺牲作代价。现在就让我作一样牺牲品罢。
同为富家小姐,她不像梅芬与瑞珏那样用“贤妻良母”定义自己的社会角色,有更高的人生追求。她和那些接受五四新思想的男性青年一样关注时代的发展,与致力于社会革命运动的觉民觉慧志同道合,她更有可能实现女性对命运的抗争。但相对于家庭结构松散的许倩如来说,琴受到更多的约束,亲戚众多而不得不考虑母亲的处境。在试探了母亲的态度后,逐渐打消了剪发的念头,羡慕倩如的大胆,时常陷入矛盾之中。“我的确是一个没有勇气的女子。我自己造了一个希望,我下了决心要不顾一切地向这个希望走去。可是一旦逼近这个希望时,我却有点胆怯了。顾虑也多起来了。我不敢毅然前进了。”因此,即使是新女性也有犹豫无奈的一面,旧制度与旧思想限制着大多数人前进的脚步,很难彻底摆脱精神桎梏,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2.2 致力于女性革命的反抗者:许倩如
许倩如是琴在女校非常要好的同学,也是琴在人生追求方面学习的榜样。由于父亲是同盟会的会员,在思想上比较开明,而母亲又早逝,作为家中独女的许倩如没有受到过多的家庭约束,独立自主,行动果敢。她是女校第一个剪发的女学生,丝毫不惧社会的异样眼光,激励班上的女同学勇敢迈出第一步,积极加入剪发的行列。面对琴的犹豫,她劝其不要做无谓的牺牲,“跟着时代走的人终于会得到酬报。可悲的是做一个落伍者而抱恨终身”,要为全体女性的幸福冲锋陷阵,勇敢战斗。对于许倩如本身而言,她已经走在同时期所有女性的最前面,承载着中国女性争取自由解放的希望。在《家》中,作者虽对她着墨不多,但她的存在却让这个封建大家族成为旧时代最后的回声,预示新时代的到来。
然而,社会并没有给予女性自身解放更多的支持,即便是思想解放运动,依然以男性为主力。在这个时代里,女性的反抗依然会迎来异样的眼光,传统的男权文化与礼教精神仍禁锢着普通大众。许倩如虽比琴更加义无反顾,但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获得社会的认可,也终将被时代所淹没。
3 女性形象塑造的时代意义
从《家》中旧女性的悲剧命运与新女性的解放运动来看,无论是饱受封建压迫的旧女性,还是走向思想解放的新女性,她们都没能真正摆脱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她们所生活的社会以男性为中心,旧社会长期赋予男性最高的话语权而忽视女性的存在,她们相对于男性来说总是被轻视的那一方。
3.1 打破旧社会的男性中心论
“在传统文化的视野下,女性一直被看做男性的附庸”,旧式女性被作为物品交换,依附于男性存在。从鸣凤等丫头的命运中可以看到女性在旧社会中曾被作为物品交换,她们被高老太爷一一送给他人,哪个老爷看上了就绑上花轿,从而实现男性之间的利益交换。鸣凤死了,婉儿还得替嫁,女性被看做物品,女性仅仅为满足男性的需要而存在。
其次,鸣凤与觉慧的爱情悲剧除了社会身份的差距还有男尊女卑的潜在观念。从觉慧的角度看,“他不能够单单为着那一对眼睛就放弃一切”,他虽然喜欢鸣凤但明确表示不会为了她而放弃自己的志向,在鸣凤最后的挣扎中求助于他时却忙于外面的事业,没有机会听她说出真相。“男人梦想自己就是一个施予者,解放者和救世主时,仍渴望女人服从。”
男性将女性视作其附属品,希望对方依靠自己,满足私有的主观愿望。当女性将男性视为唯一的依靠时,男性却不能给予其同样的心理位置。他们之间的对话总是不对等的,而只有想办法改变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女性才能寻求自我的存在价值。
3.2 重塑新时代的女性价值观
男性将女性定义为自身的附属品,女性自身也在默默接受这样的定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把女性牢牢地固定在贤妻良母的位置上,使其失去自我,动弹不得,处于一种集体失语的状态,无精神意义上的自我、独立,女性成了服从者和奉献者的代名词。”
梅芬虽是寡妇但也可以寻找自己的幸福,却一直沉浸在对觉新的回忆里,又怕影响他现在的家庭生活而极度痛苦;瑞珏原本能画画赚钱,在嫁给觉新后就努力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不再关注自我。旧式女性的爱情观以男性为中心,生活重心在家庭,这都忽视对自身价值的关注,也自然而然地承认了女性从属于男性、男尊女卑这一思想观念。
而琴首先对此进行反思:“难道女人只是男人的玩物吗”,她无法接受女性在旧社会里一味地做出牺牲,她希望自己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她哭着说:“我不走那条路,我要走新的路”。女性首先应学会自救,重新审视自我,找到自身的优势,只有发现自身的社会价值,才能获得与男性同等的社会身份,再用其重新被社会所认可。
3.3 呼吁全社会给予女性解放运动以支持
社会原本限制女子上学,后来在集体的反抗中制度有所放宽,但不能破除女禁,女性在读书方面无法享受与男性同等的条件。对于女子剪发,社会给予各种鄙夷的眼光与侮辱的言论,用传统的审美来打击女性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对于觉民觉慧来说,琴虽抱有很大的反抗热情与坚定的决心,很多时候也会陷入矛盾与迷茫之中,产生自我怀疑,在一些行动面前有所退缩。而许素如面对社会的眼光毫不在乎,个人的思想解放意识十分彻底,但单凭她一人的力量,女性仍然无法获得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自身的价值无法被认可。因此,只有社会给予女性解放运动足够的条件,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的身份能真正得到认可,才有可能实现自我的存在。
旧社会给予男性最高的话语权,男性用社会赋予的权利去诠释女性的存在价值,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爱情婚姻,女性都自然而然地成为男性的附庸,男尊女卑成为社会的普遍准则,人人奉行遵从;更成为女性的精神桎梏,逐渐失去自我。要改变旧社会的女性悲剧,社会思想观念需要革新,女性首先自救,主动打破传统的男性中心,社会承认女性的身份、解放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