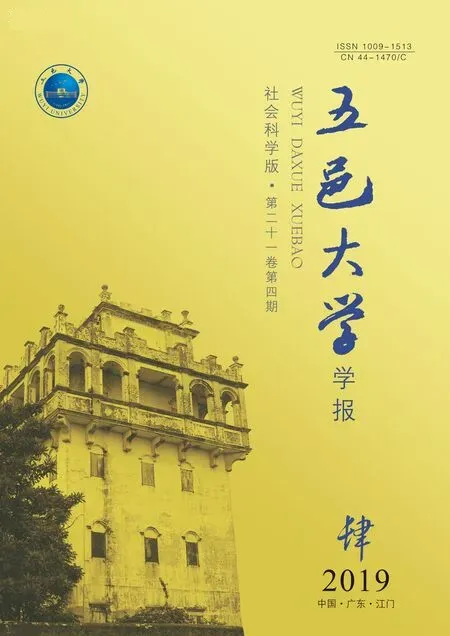布迪厄社会理论视角下唐廷枢翻译活动探析①
李小英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外国语学院,广东 珠海,519087)
一、前言及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
近年来译史研究已经成了翻译研究的一大热点,并且呈现了跨学科态势。除了史学,国内外学者还将翻译史研究跟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结合起来,把翻译活动放在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去考量,探讨翻译与社会、文化、历史、宗教之间的关系,其中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最为热门,因为翻译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交际行为与活动,[1]2产生并作用于社会。然而,从目前已有文献来看,不管是翻译史方面的研究还是社会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大都集中在文化性译者及其译作,而对事务性译者和口译员的研究比较少。此外,探讨翻译行为对个人影响的研究则更为少见。而本文的研究对象唐廷枢(又名唐亚区,唐景星),在成为买办和民族资本家之前,曾在香港殖民政府和上海海关担任过长达十年的翻译,主要承担巡理厅和江海关的口笔译工作,属于孔慧怡所说的“事务性译者”, 相比于今天口译人员令人艳羡的薪水和光鲜的职业形象,“能见度低,名字不传于世”。[2]若不是因为唐廷枢在经济史上的重要贡献,他或将不为世人所知。然而一个人在人生不同阶段所参与的社会实践活动是相互联系的,通常前面参与的活动会为后来的活动积累资本和惯习。因此在研究个体时,应该考察其“社会轨迹”[3]276,即个体社会化的历史过程[4]12。目前对唐廷枢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如汪敬虞[5]、刘广京[6]、胡海建[7]等人的研究,而对他这段翻译历史的关注研究甚少,本文拟在这方面做些补充。
场域、惯习、资本是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中最核心的概念,也是最主要的分析工具。 布迪厄所称的场域指的是“具有自己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3]162;[4]6。惯习指的是人在成长、家庭教育、学校学习、工作、交际等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学习、内化以及强化他们所认识的社会规律而产生的一套“定势系统”[8],每个人倾向于根据自己的思维方式而采取某些有规律可循的行为。资本是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工具。不同的场域要求的资本不同,每个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本也不一样,因而在场域中所处的地位也不同。布迪厄认为资本表现为四种基本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
二、唐廷枢参与翻译活动时所处的场域
翻译的跨领域性决定了翻译活动不可能只发生在翻译场域,它还同时发生在其他场域之中,与相关场域的规则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所以,我们要考察翻译场域中的规则,就常常需要观察它与其他相关场域的关系和互动。[4]10
在唐廷枢先后任职的巡理厅和江海关这两大场域中,具有分配资本和决定社会结构能力、在权利场域中处于支配地位的都是英国殖民者。1841年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英军首领义律宣布所有在港华人都是大英帝国的子民,接受英国地方法官的控制,在高等法院成立以前(1844年),该法官对所有扰乱香港社会治安和违反法律的行为具有审判权和处罚权。唐廷枢所任职的机构就是集司法和警察大权于一身的巡理厅。[9]5-6因此,该地方法院就是英国政府维护其在香港殖民统治的主要机构。
江海关表面上是清政府管辖下的一个重要机构,但从1854年7月起就落入了外国殖民者之手,清政府虽然名义上保留有对总税务司的任免权,但人事任免权、行政事务管理权等均操纵在外国人手中,总税务司和主要骨干都是洋人,直至1929年以后才陆续有华人晋升为税务司。[10]因此,江海关虽为中国政府机构,维护的却是西方殖民者的利益,是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掠夺财富的工具。在该权利场域,处于支配地位的不再是清政府,而是外国殖民者。处在该场域的唐廷枢,利益得不到保护,虽然能力超群,除了薪酬比其他华人译员高些之外,仍然受到西方殖民者的排挤,职业发展受限。
三、唐廷枢进入翻译场域的资本和惯习
场域最大的特点就是竞争,[11]而争斗总是围绕着权利的界限、场域的进入权、参与权,以及资本的数量限制等问题。由于清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导致《南京条约》的签订,再加上后来的《天津条约》,使得中国在与西方的博弈中败下阵来,丧失了在香港的统治权和江海关的管辖权,因而在这些场域活动的华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在竞争中也处于劣势。在巡理厅和江海关,占支配地位、拥有绝对话语权的都是英国殖民者。那么唐廷枢是如何获得巡理厅和江海关翻译场域的进入和参与权的呢?这得追溯到他曾接受的六年西式教育,也正是这六年的西式教育为其积攒了进入上述场域的资本和惯习。
首先,他在马礼逊学校积累了一定的跨文化惯习①和社会交往惯习。通过与布朗夫妇的交往,他形成了西方人和中国人是平等和睦、没有排斥欺凌的跨文化惯习,这为他后来接受殖民机构中的职位奠定了情感基础。此外,通过西方上层社会人士的到访,他看到了西方人社会交往的礼节,而通过两位汉语老师教导及诵读经典,唐廷枢懂得了中国社会的礼节,熟谙中国文人的交往之道,这对他后来与中国官员交往奠定了基础。[12]
其次,唐廷枢在马礼逊学校积累了非常过硬的文化资本以及良好的社会资本,具体表现如下:
1.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包括身体化文化资本、客观化文化资本和制度化文化资本。不同的场域要求的资本不一样。在现代社会,要进入翻译场域,参与者除需具有优秀的双语能力,即身体化文化资本外,还要有各种证书等制度化文化资本。但在当时各种证书比较少,主要靠的是双语交际能力。唐廷枢所从事的笔译当然是英汉语之间的转换,但口译主要是粤语和英语之间的转换。唐廷枢生长在广东香山,粤语是其自幼说的语言,自然不在话下。而在马礼逊学校,布朗采取的是半天汉语、半天英语的教学模式。上午由传统中国教员教读四书五经等经典书目,下午按照当时英美国家小学的课程设置,用英语教授阅读、写作、算术、历史、地理、科学等科目。正因为如此,唐廷枢的英汉语能力得到了中西方人士的一致好评,“唐景星的英文写得非常漂亮”,“这个人的英语是这样地精通(怡和洋行经理机昔)”“说起英语来就像一个英国人(琼记洋行费伦)”“唐廷枢熟悉中外语言文字(李鸿章)”。[5]157-158
2.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指某个个体或是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识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不管这种资源是实际存在的还是虚有其表的”[13]。陈雅晴认为早期华人港府译员的招募很可能不是通过固定、系统的考选,而相对依赖社会网络。[14]275例如唐廷植进入上海英国领事馆及巡理厅都是由于布朗的推荐,容闳进入香港高等法院做译员也是因为其旧友、《德臣报》主笔肖锐德(Andrew Shortrede)的引荐[15]21。虽然没有看到唐廷枢进入巡理厅的引荐人,但以其在马礼逊学校的受教育经历以及优秀表现,不难想到是有人推荐。因此从马礼逊学校积攒的社会资本是唐廷枢进入殖民机构的重要因素。
四、唐廷枢从翻译场域获得的资本和惯习
(一)经济资本
在香港殖民政府中的华人译员虽只属于初级公务员,但拥有政府行政人员的身份,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上都和大部分华人所属的劳工群体有着迥然的差异。[14]294-295虽然译员内部的薪资有所差异,但总体而言比普通杂务工人高出一个档次,甚至比文员、买办和学校教师都要高。华人译员有着非常不错的经济基础,能保证个人的安逸生活,如果管理有度应该足以拥有一定的积蓄。不少华人在担任政府译员时都有投资经历。唐廷枢也不例外,他在去上海江海关之前已投资香港的两家当铺并且都是盈利的,年利率在25%~45%。[5]3
去了江海关后,唐廷枢的待遇应该比在香港殖民政府时更高。虽然没有看到其本人在江海关的薪酬记录,但从与容闳的对比可以知晓。容闳在高等法院做译员时的报酬是每月75港币,[15]211856年在上海海关任翻译时的报酬是每月75两银子,“这比在高等法院做翻译时高一点”[15]22。唐廷枢于1851年接替胞兄唐廷植担任香港巡理厅临时中文文员暨译员,年薪100镑,1855年后涨至150镑,按照一镑相当于4.8港币算,[14]271月薪只有60港币,比容闳的还低。这也许也是他离开巡理厅去江海关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唐廷枢做翻译时期确实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本,这也是后来他得以进入商业场域做买办和资本家的前提。
(二)象征资本
象征资本是一种权力形式。自古以来,语言和权利都密不可分。在香港殖民政府和江海关工作的华人译员在无形中拥有了亲近权力阶层的便利和优势。作为华人中少有的掌握殖民者语言的人士,香港殖民政府和江海关中的华人译员,虽不处在支配地位,但在不会英文的普通人眼中“带有官家权利的色彩”,因而具有了象征资本。如果真正掌握权利的人士无法对翻译进行充分有效的监管,有些华人译员就利用语言优势,在中西社会交流的空隙间借机发挥自身的影响力,攫取利益。[14]2961857年,唐廷枢帮助理检察官查理士审黄墨洲的账本,也被指隐瞒了其中的证据[16]445,究竟是为金钱所动摇,还是因为那些嫌犯是华人,不得而知。
(三)信息资本
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中没有提到信息资本一说,但是处在信息时代的我们非常清楚信息对于做成一件事情有多重要。在此,我们把信息资本定义为任何因获悉时间不同或是否获悉而产生不同结果的消息,比如供求信息等。掌握信息的一方完全可以通过转让信息获得经济利益,或是自己捷足先登,夺取先机。虽然当时还未进入信息时代,但是19世纪60年代初期,唐廷枢得知美国因为南北战争爆发,棉花紧缺,进而促使他开了“修华号”棉花行,为怡和洋行购入大量的棉花,因此而得到怡和洋行经理机昔的赏识。[6]164具体唐廷枢是通过什么渠道获知这一消息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鉴于他当时在江海关任职,便于了解中国商品的进出口贸易情况,尤其是国际市场紧缺的货物。更何况唐廷枢早就具有关注商业领域的惯习,其叔叔就曾是一个买办,其同乡也有不少买办,最著名的有徐润、郑观应,以及怡和洋行的林钦。不难推断他也会关注当时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以及买办的动向。因此翻译活动也为唐廷枢积攒了信息资本。
(四)社会资本
1844年香港高等法院设立后,引进了西方法律制度,这些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体现出优越性,如人们利用香港法院很容易实现他们的商业利益,所以在港经商的华人为了自身商业利益,往往倾向于利用港英政府控制下的法院进行诉讼。[17]虽然唐廷枢只是巡理厅译员,但由于当时华人译员的职责划分很不明确。巡理厅的译员经常承担高等法院的翻译任务,或直接被派去做高等法院的译员。虽然香港政府蓝皮书中没有记载,但有关唐廷枢的生平史料中,多处都有他在1856-1857年间代理香港大审院华人正翻译的记载。[18];[5]158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因为他的被殖民者身份,殖民政府虽让他做高等法院的翻译工作,但却没给其相应的职位和薪酬。
因此,不管是在香港殖民政府还是在江海关做翻译时,唐廷枢都有机会接触到当时众多的中国商人和洋行经理和买办,因而为其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资本。
(五)文化资本
前面已经提到,各场域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翻译活动的跨文化、跨领域特性使得译员可以涉猎非常丰富的知识。据容闳称,他去高等法院做译员的主要目的其实是学习法律。[15]40唐廷枢做翻译时主要涉及政治场域、法律场域、商业场域(协助巡理厅及高等法院审理商业案件)以及贸易场域(江海关的职责包括对进出口商品征收关税和海务)。[19]处在法庭翻译场域中的唐廷枢,首先可以学到很多西方法律知识,尤其是商法。其次,通过在江海关工作,唐廷枢熟悉并掌握了大量海关法例、国际海关规章制度。事实证明这些知识在其后来的事业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1873年朱其昂购买的“拉普蒂克”轮船从英国抵达上海。唐廷枢和史柏丁到船上查看,看遍了船只的各个部分,发现该船所列的90a级与实际不符,便拒绝接受这艘船只,被对方制造厂家告上了法庭。唐廷枢勇敢出庭作证。他凭借深厚的船舶知识和法律知识胜诉,拒绝接受这艘船。[20]此外在其后来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和两次齐价合同中也都展示了他从翻译生涯中积累的这些专业知识与能力。
五、唐廷枢翻译生涯的瓶颈
虽然唐廷枢在殖民政府做翻译期间表现出了卓越的翻译能力和道德品质,如首席检察官在为其在黄墨洲一案中辩护时说:“唐亚区(Tong Aku)是在我担任首席检察官的两年半里所知的所有欧洲和华人译员中最优秀的译员,甚至包括高和尔先生在内。至于他的信念和可信度,我认为绝不次于任何人”[16]43。 然而当时香港华人的被殖民身份依然十分突出,港英政府对华人的警惕和排斥从未消失。华人译者在薪酬待遇、地位和职业发展空间方面和欧洲人士存在较大差距。虽然华人译员的等级和薪酬有差异,“但是他们的晋升仅限于译员圈内部的等级变化而已,并不能跳出这一处理日常事务为主的初级公务员群体。而欧洲译员往往可以快速跃至管理层,成为殖民政府官员”[14]279。
在江海关的情况也是如此。虽为清廷下属机构,其人事和行政权完全掌控在外籍总税务司之手。李泰国对容闳的答复就是最好的说明,不管个人能力和才干、道德品质有多优秀,只要是华人就无此希望。[15]22
究其原因,还是在于资本。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总被烙上最初获得状态的烙印,如人的口音、饮食习惯、生活起居等,无论怎样竭力掩饰,个体行动者都无法彻底抹去最初的社会身份。[21]唐廷枢虽然接受多年西方教育,但无论怎样也改变不了他的华人身份。“(一名华人)可能是英国子民,但不论在穿着、思想,还是在习惯上都不是英国人。他们仍然臣服于满清统治者,而且只有极少一部分人信仰基督教,他们还赞成纳妾和蓄婢”[14]310。《香港日报》上的这段文字充分代表了当时英国殖民者对华人的看法。因此,虽然语言这种身体化文化资本帮助唐廷枢进入了殖民机构中的翻译场域,但其身份资本决定了他在该场域得不到更好的发展。
六、结 语
从1851到1861年,唐廷枢从事了整整十年的翻译活动。但他这十年的翻译生涯并没有得到多少学者的关注,原因之一在于唐廷枢在其他领域的成就远大于此;原因之二应该是翻译历来社会地位都不太高,古时候在中国还有“舌人”之称,尤其他这十年的翻译生涯从事的都是事务性翻译,不像文化性译者会有译作留下来,对社会的影响更大。但是纵观唐廷枢的一生以及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其早期翻译活动对他后来所取得的成就意义重大。一方面,进入那些重要部门做翻译让他积攒了大量的资本和惯习;另一方面,其翻译职业发展的瓶颈也恰好造就了其后来的发展。试想,倘若唐廷枢在巡理厅或江海关的翻译职业发展顺利,例如进了最高法院或是成为了一名税务司,那么他后来在洋务运动中所作出的那一番成就和贡献将不复存在。不仅其个人的历史要完全改写,连整个洋务运动的历史都要改写了,因为有人说过“洋务运动可以没有李鸿章,但不能没有唐廷枢。”正如陈雅晴所言,“对于能力优秀的双语人才,长期从事译员一职难以一展所长,甚至可以说是屈就”[14]310。因此对于唐廷枢这样一个商业奇才,如果真的埋没在了殖民机构当中,那对中国近代社会无疑将是巨大损失。
注释:
①作为一名双语或多语使用者,在接触本国文化和异国文化时会培养起一种“跨文化惯习”(例如译者对两种文化和语言的态度、偏见等), 进而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潜意识决策。参见Meylaerts R. Translators and (Their) Norms .In:A. Pym et al. eds.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Investigations in Homage to Gideon Tour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B. V., 2008. p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