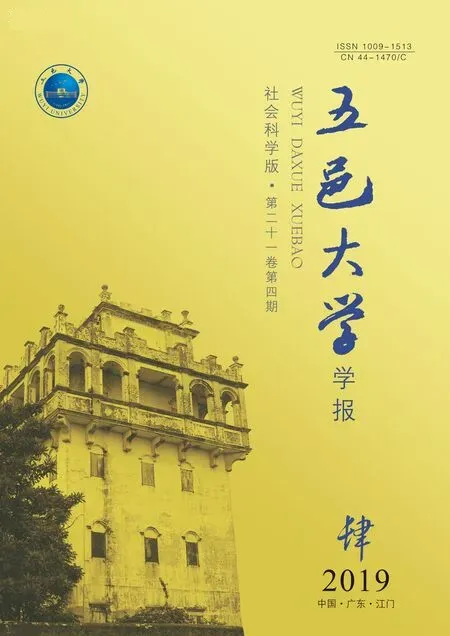论明代“粤人扬粤”①
陈利娟
(广东金融学院 财经与新媒体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1)
秦朝时,南海郡龙川县(今广东龙川县)令赵佗曾建南越国,割据自立为“南越武王”;宋朝时设广南东路,简称广东路,由此出现“广东”一名;元设广东道;明设广东省。由于其辖区在汉初时,属于南粤之地,故简称“粤”。“粤人”主要指广东人;“粤地”主要指以广东为中心的岭南。“粤人扬粤”是明代郭棐在其《粤大记》序中提出的:“谨按:昔云阳氏肇都沙丘,始轩辕分野,厥维荆扬,吾广介焉,是为扬粤。”[1]1意指其身为粤人,写《粤大记》的目的是“扬粤”。从其编纂体例和笔法看,主要是有意识地宣扬粤地人物、地理、民俗等文化现象,使粤地文明得到他地、他人的认可。“粤人扬粤”古已有之,直到明代,才真正实现了对广东文化的有效建构和积极传播。
一
明代以前,粤籍人士对以广东为中心的岭南的传扬已经出现,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传扬异域风土人情和表达眷恋故土之情。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合浦人姚文式做的《交州记》,以魏晋主客问答体,书写他人对南海和赵佗郡所的疑问以及作者的回答。其对南海和番禺的介绍,为他乡人了解岭南提供了线索。张九龄乃曲江(今韶关)人,初唐名相,其政治作为与文学才华一时为人称颂,被后世岭南民众称为岭南形象的最佳代言人。其对岭南书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赞颂岭南风光美好,有归家之感,如诗作《与王六履震广州津亭晓望》:“明发临前渚,寒来净远空。水纹天上碧,日气海边红。景物纷为异,人情赖此同。乘槎自有适,非欲破长风。”[2]373另一方面叹家园远遥,仕宦飘零,如诗作《初秋忆金均两弟》:“江渚秋风至,他乡离别心。孤云愁自远,一叶感何深。忧喜尝同域,飞鸣忽异林。青山西北望,堪作白头吟。”[2]398写出了中国古代在外为官、不能回乡者的普遍心声。其后中唐龙川人韦昌明作《越井记》,讲述了赵佗开掘越井和家族如何产生的大致经过,对于研究唐代粤东循州的开发以及韦氏家族的来源等,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和价值。[3]北宋曲江(今韶关)人余靖对粤地的传扬主要在书写当地名胜古迹美景,如《武溪集》卷五《韶亭记》:“贤人君子,乐夫佳山秀水者,盖将寓闲旷之目,托高远之思,涤荡烦绁,开纳和粹,故远则攀萝拂云以跻乎杳冥,近则筑土饬材以寄乎观望。惟韶山,去州治八十里,自元精胚胎阳结阴流,不知炉锤者谁独秀?兹境在昔,虞舜南狩苍梧,《九韶》之乐奏于石上,山之得名起于是矣。……”[4]南宋末年番禺人李昴英在介绍家乡时,以自豪的口吻写道:“吾州全盛时,巨舶衘尾笼江,望之如蜃楼屭赑,殊蛮穷岛之珍,浪运风督,凑于步豪贾四方至,各以其土所宜贸易。民以饶侈,每岁赋额足以周兵额而羡,故用益而储实。”[5]311写出了家乡经济繁荣的景象,并提出富庶的物产和便利的水运交通是经济繁荣的原因,是国家税赋缴纳充足的基础,为王朝军队提供了物质支持。
另一种对粤地的传扬是帮助当地建立学派或大力传扬本土杰出人士。南宋增城人崔与之,其对粤文化的传扬,主要是开创了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学术流派:“菊坡学派”,带领岭南人学习儒术,遵行法度礼节,为朝廷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本土人才。元人王义山云:“五羊之广,则为象犀珠玉之广,史书礼乐之风未敦也。姑以近世言,丞相菊坡由上庠取科第,广之士自是而相励以学。”[6]崔与之的弟子李昴英为纠正中原人鄙视广东“钟物不钟人”的偏见,申明广东文化的繁荣:“惟广素号富饶,年来浸不逮昔,而文风彪然。”南宋始兴县主簿张庚则以张九龄为典范,论述当地人在礼仪文化方面对先贤圣人的学习与追慕,突出了岭南人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努力。[5]313、312
这些文字和事迹对纠正对岭南的偏颇印象起到了一定积极效果,皴淡了中原人士对岭南的异物感和他者感,但因所述内容多为物质资源和个别名人风范,且多记载于文人文集,并不具有推广性,反而因片面地强调物产富足、地貌独特,引发了中原人士对其人物不够出色的审视。宋代杨万里就在《张余二公合祠记》中云:“人物,粤产古不多见,见必竒杰也。故张文献公一出,而曲江名天下。至本朝余襄公继之,两公相望,揭日月引星辰,粤产亦盛矣哉。盖自唐武德放于今五百有余载,粤产二人而止尔则亦希矣。”[7]这段话虽肯定了粤地人杰地灵,也写出了这些人物之所以格外出色的原因:稀少。物以稀为贵,反复书写、歌颂单个对象的行为背后,隐现群体落后的现实。因此“扬粤”的效果并不明显。
二
“粤”及“粤人”直到明代才真正为天下所认识、接纳和认可。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序中说:“广东居天下之南……天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其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8]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广东经济在此时高度发展,带动了政治、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的发展之外,更与“粤人”主动有意识地“扬粤”分不开。
明代“粤人扬粤”的独特策略,首先与一些粤籍史学家专注书写本土地方通志和辖区方志有关。相对于前代粤籍人士的零星记载和专项宣传,明代文人在传播和宣传本土文化时,态度更严肃,视野更宽广,以正风俗、宣教化为目的,收集和撰写了广东本土的地理风物和民风民俗著作,致力于广东文献的研究和整理。广东方志起源于风物志,主要书写岭南风土物产。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杨孚有《交州异物志》,《唐书·艺文志》记载王范撰《交广二州记》。其后宋王靖撰《广东会要》,已具方志之雏形。
通志始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戴璟的成稿《广东通志初稿》(40卷)。作为现存最早的广东通志,其设置地理、风俗卷各门类,展现了先秦至嘉靖初年广东的风土人情。由于戴璟非粤籍,是以广东巡抚身份主编此书,且缺少助手,时间仓促,修志时间不超过8个月,这本通志总体质量不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是书乃璟于嘉靖乙未以临代之时两月而成,未免涉于潦草,其门类亦多未当。”[5]尽管如此,其开创的通志体例以及基础文献的整理,仍给后来的修史者很大启发。嘉靖三十六年,黄佐继修《广东通志》。由于黄佐是广东香山人,对故土山河怀有浓厚感情,修撰家乡史志寄托抱负甚深。他招寻一些得意弟子,如欧大任、黎民表、梁有誉等,分章列目,研修撰写,并查漏补缺,严察细访,历时4年,终撰成书70卷。《广东通志》分图经、事纪、表、志等几大类,主要内容是志,有民物志、政事志、礼乐志、艺文志、外志等,包括名宦、流寓、人物、烈女,以时代先后为序。这本书的史学价值很高。清代著名史学家阮元在黄佐编纂的《广东通志》序中称该书:“为泰泉弟子所分撰者,体例渊雅”[9]。至万历二十九年,郭棐再纂通志。南海人郭棐尤其注重其家乡广东的方志事业,历二十余年,为广东修志三本:《粤大记》(32卷)和《岭海名胜志》两部专志——乃是为《广东通志》做的资料准备,《广东通志》72卷。郭本《广东通志》体例更加完备。全书分藩省志和郡县志两部分,涉及舆图、分野、沿革、气候、事纪、……外志(仙释、寺观二门)各个方面。不同于志家只褒不贬的惯例,他的书中还设“罪放”、“贪酷”二门,以示讥贬,颇得史家遗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较他志体例为协”,清学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补逸》亦云,“为从来地志所未有”“皆可取法”[10]。
除了通志,粤籍历史学家还以别的方式为本土人物风物立传。明朝前期香山人黄瑜,开始以笔记形式记载洪武至成化年间事。《双槐岁钞》是其历时四十年写就的一本类似断代史的笔记。今人虽把它归为明代笔记小说一类,作者本人实际是把它当作严肃历史来写的。作者说:“言今必稽诸古,言天必征诸人,言变必揆诸常,言事必归诸理,此予著述之志也。”[11]97他想和太史公司马迁一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参天地之理。此书有十万字、十卷长编,涉及岭南人物与风物的,几乎每卷都有记载。篇目有:《何左丞赏罚》(卷一)、《朝云集句》(卷一)、《史孝子》(卷三)、《周宪使》(卷三)、《陈情愿化》(卷四)、《场屋知人》(卷五)、《盅吐活鱼》(卷五)、《冤梦入魂》(卷五)、《祷神弭寇》(卷六)、《井妖致殒》(卷六)、《薛尚书论礼乐》(卷六)、《黄寇始末》(卷七)、《名公诗谶》(卷八)、《狱囚冤报》(卷八)、《夜见前身》(卷八)、《咏竹言志》(卷九)、《庄定山》(卷九)、《道具体用》(卷九)、《奖贤文》(卷九)、《何孝子》(卷十)、《丘文庄公言行》(卷十)。记事记物篇有:《春王正月辩》(卷一)、《邑俊升郡学》(卷二)、《外任改京秩》(卷四)、《易储诏》(卷五)、《寿星塘》(卷七)、《莲峰卿云》(卷七)、《登科梦兆》(卷七)、《彭蠡缆精》(卷七)、《鹊桥仙》(卷八)、《龙洲魁讖》(卷九)、《谪仙亭》(卷十)、《筹边翊治策》(卷十)、《刘王疑冢》(卷十)、《进士教职长史》(卷十)、《保举神童》(卷十)等。这些篇目多为人物传记,宣扬粤籍官民的高尚品质,其中《何左丞赏罚》中的主角何真被高祖皇帝封为“东莞伯”,《周宪使》一再借永乐帝之口宣称南海人周新为“广东好人”。黄瑜之孙黄佐在祖父的影响下,立意为本土文化建设努力,除了70卷本的《广东通志》外,还写下了《广州府志》60卷,《广西通志》60卷,《广州人物传》、《罗浮山志》各若干卷。流传后世的一些伟大人物,如洪武时期被封为“东莞伯”的东莞人何真、永乐时期被称为“冷面寒铁公”的南海人周新、被呼为“大声秀才”的番禺人陈谔……都借他的笔墨留下光辉灿烂的一笔。郭棐在《粤大记》和《岭海名物志》中亦对岭南人物和风物进行了撰述和描绘。《粤大记》分五类:事纪类,科第类,宦绩类,献征类,政事类。全书以人物为主,辅以记事;以历史为主,辅以地理;以叙述为主,辅以评论。全书资料丰富,仅介绍广东人物,达574人,与广东有关人物传记421人。《岭海名物志》记录了广东名胜20处,内容相当详实细致。
一系列质量上乘、规模宏大的地方通志和其他体例方志的出现,一方面体现出广东文化教育发展迅速,能够培养与中原优秀人才比肩的高质量人才,拥有过硬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改变了中原文化圈对岭南文化和文明的偏见。明代以前大部分的外乡人都将广东视若危途,如北宋初范旻说:“岭外十州,风土甚恶,县镇津口,税赋失额。”[12]以为广东这样的蛮荒野蛮之地,不仅地理环境恶劣,人文精神更是低下粗鄙。但经过明代粤籍史学家的书写宣扬后,粤地“钟物不钟人”的印象不再成为主流。明代学者姚涞在读过黄佐的《广州人物传》说:“太史黄子才伯(佐)惧先正之久而湮也,乃为传以表之,凡二十有四卷,余得而阅之,知黄子之精于史也。综之群典以辑其逸,参之故实以定其讹,鉴前史之得失以辨其微,……事核以审矣。”[13]认为以黄佐为中心的本土史学家修养和书写态度完全不输任何其他大家。这些创作态度严肃、学术含量很高的著作改变了异地外乡对广东的偏见,使得他们不再以为广东是蛮夷偏远之地、粗鄙之乡,广东亦如其他省区一样是在儒家文化教化熏陶下的地方,其发展是遵循儒家正统的人道和天道观念,秉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俭持家、春耕秋收、顺应天时、生儿育女的生活方式,以三纲五常、父慈子孝等伦理观念约束要求自己,创造文明。正统史书的大量出现,凸显了粤地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文明程度的高妙。
其次,明代的“粤人扬粤”,格外突出粤籍人士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文化教养。人是社会发展和文明提高的最重要因素。粤籍史学家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从彭森为周新做传《冷面寒铁公传》,到黄瑜《双槐岁钞》的《何左丞赏罚》《周宪使》《高瑶》《丘文庄公言行》,黄佐《广东通史》中的《张九龄》《丘濬》《霍韬》《陈谔》《李质》,郭棐《粤大记》《广东通志》中的《陈献章》《周志新》《湛若水》“南海五先生”等,都特别突出粤籍人物的美好道德修养和人格修养。如明朝永乐年间的周新,其“广东好人”的称呼最早出自其同乡彭森为之所作《冷面寒铁公传》中,后同乡黄瑜将之进一步发扬光大。他在《双槐岁抄》卷三《周宪使》一文中,先是记载了周新在各地任按察使时杰出的办案能力和关辉事迹,最后写其因不畏权势拘捕朝廷红人纪纲手下,遭锦衣卫纪纲诬陷。在纪纲构陷下,“上(永乐帝)命官校逮新。既至,抗声陈其罪,且曰:‘按察司行事,与在内都察院同,陛下所诏也。臣奉诏擒奸恶耳。’上怒,命僇之。临刑,大呼曰:‘生为直臣,死当作直鬼。’上寻悟其冤,顾侍臣曰:‘新,何许人?’对曰:‘广东。’叹曰:‘广东有此好人。’称枉者再。后纪纲坐罪伏洙,其事益白。同里彭参政森作传,谓上尝见有衣红立日中者,问为谁。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刚直,命为城隍。’言已不见。天颜怃然。”[11]158后来者粤籍黄佐、郭棐都继承了彭森的说法,以 “广东好人”来书写其政绩与人品,甚至以天帝将其封为浙江城隍之神的传说当作史实,彰显了周新忠贞为国、刚直不屈的伟岸人格。由于多次书写,导致直臣屈杀的现象成为中国人对神灵的一种寄托和期望:冤死的忠臣死后会成为神灵。龚自珍在《夜读番禺集,书其尾》中说:“奇士不可杀,杀之成天神。奇文不可读,读之伤天民。”[14]虽然其本意是悼念明末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屈大均,但其思路隐现的是对忠贞之人被屈杀致死的愤懑。
“粤人”对本土人物道德水平和人格品质的赞扬,改变了他乡人对粤人的负面评判。辜鸿铭曾说,要估价一个文明,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是否修建另外很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制造出漂亮舒适的家具、精制适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而在于它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人,男人和女人。“一种文明所生产的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正好显示出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也即显示出该文明的灵魂。”[15]人是国家、地区整体素质最直观显现的综合体,好人,而不是名人,更能集中具体展现当地的教育水平和文明程度。黄佐深明此理,他在早年撰写的《广州人物传》中,就书写和赞扬了大量的广州人物,后在《广东通志》中又增加更多贤人嘉士,用了几乎20卷为人物立传,几占全书三分之一,共辑入1818 人,以“名宦”“流寓”“人物”“列女”四类分列,其中“名宦”922人,“流寓”152人,“人物”591人,“列女”147人,基本上涵括了嘉靖中期以前历代广东先贤在政治、经济、文教、军事、气节等方面的业绩。张九龄、丘濬、陈献章、周新、陈谔等粤籍官民彰显了岭南人民的美好精神和思想高度,成为了岭南一代士人的杰出代表,增强了广东人对本土文化的归属感和自信心。
再次,明代的“粤人扬粤”始终将粤文化与中原文化连接在一起,并不强调粤文化教育的独特性与另类性。粤人在宣扬自己的文化特色和风物名俗时,是附于中原儒家文化大的传统流脉下的,是依据儒家的道德伦理和制度管理为基础的。黄佐在《广东通志》凡例第一条明确写到:“通志犹列国之史,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此修志之大要也。’”[11]1体现“民物志先风俗”的传统结构安排,与司马迁《史记》所开创的体例并无太多差别,明显体现儒家“以民为先”的政治理念。其甄选人物,无论是忠臣周新,平民史孝子,亦或是学术大师陈献章,都体现了儒家提倡的君子人格。郭棐在《粤大记》中说:“予(郭棐)尝综究粤事,周武王十一年定为蛮杨, 此则我粤入中国之始;……显王三十五年,楚子熊商伐越,……此则百粤肇迹之始;……秦始皇三十三年,以赵佗为龙川令,此又百粤列郡邑、置守令所由始也。迄汉唐以来,郁然焕然称奥区矣、非武王、周公开创于前,孰臻兹哉!……揆厥原本,讵容泯沫哉!”[1]10强调粤地民俗地理是在周朝所创立的文教武功的基础上发展的,是汉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分支。他们所宣扬的人物与事迹必须符合儒家文化正统,符合黄瑜在《双槐岁钞》序言中所说:“凡圣神功德必书,崇大本也;人文典礼必书,急大务也;天地祥眚必书,期大化也;经史异同必书,决大疑也;懿行美政必书,昭大节也;异端奇术必书,正大经也。”[11]97凡是有益于政教德化、裨补人心、鉴真历史的内容,他们都收纳、录写于书中。正是看到了中原与粤地的紧密影响,明末清初粤人屈大均才在《广东文选·自序》中说:“嗟夫!广东者,吾之乡也。不能述吾之乡,不可以述天下。文在于吾之乡,斯在于天下矣!惟能述而后能有文,文之存亡在述者之明,而不徒在作者之圣。吾所以为父母之邦尽心者,惟此一书。”[16]
结 语
经过两百多年的文化建设与文化传播,至明末,广东经济持续增长,学术、科举、教育、家族文化传承、书院开办等方面都有显著提高。明代人才辈出。据不完全考证,有明一代广东被察举618人,进士874人,举人6437人,凡7929人。超过历代广东上述人才总和。①因此屈大均说:“明兴,才贤大起。”[17]另外地方志撰写蔚然成风。据《广东省志·总序》统计,广东(包括海南)志书,宋代可考者有101种,元代14种,明代224种,清代441种。[18]广东刻书业在明代也有较大发展,官刻、私刻都比较兴盛,其中私刻很多以刊刻本土著述著作为主,如琼山丘濬刻《武溪集》、《张子寿文集》(张九龄)、《广东通志初稿》等,唐胄刻《白玉蟾海琼摘稿》、《武溪集》、《宋丞相崔清献公全录》等,香山黄佐刻《双槐岁钞》、《泰泉集》诸书,增城湛若水刻《甘泉湛子古诗选》、《甘泉先生两都风咏》等。学术呈现历史上最繁盛的面貌:“广东文化虽然源远流长,自汉以来,各学术门类也有其代表人物,但到底根基浅薄,在理论体系、框架结构、内容特色和风格上未能卓然独立、问鼎中原,还谈不上形成学派。但到明代,广东已进入社会经济较快发展阶段,文教兴盛,人才辈出,地域文化特色日益显露,在继承历史积累基础上,新的学术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应运而生,标志着一种学术流派开始在广东出现,并以崭新姿态和装束,活跃在中国学术舞台。其代表就是陈献章及其创立的‘江门学派’。”[19]明代南海伦以谅在霍韬《渭厓文集序》中也认为 “钟物不钟人”的提法应当成为历史了:“昔韩昌黎送廖道士,叹岭南瑰荦奇伟之气不钟于人而钟于物,一或有之,又出于异端方外之徒灵炳之所发洩而钟焉者也。使昌黎遇之(霍韬),必不为黄冠而兴叹矣”[20]。
明代“粤人扬粤”不仅提升了本土民众对广东的归属感,也改变了以中原文化圈为中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岭南的看法:不再是野蛮粗鄙之地。粤地民众的自尊心提升,拥有了文化自信,继而对儒家正统的伦理观和制度更加亲近,更自觉地提升文明程度,成为明代在各方面比较领先的省区。
注释
① 据道光《广东通志·选举表》卷六七(同治三年1864)重刻本、《明清进士提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至道光二年(1876)年间的数字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