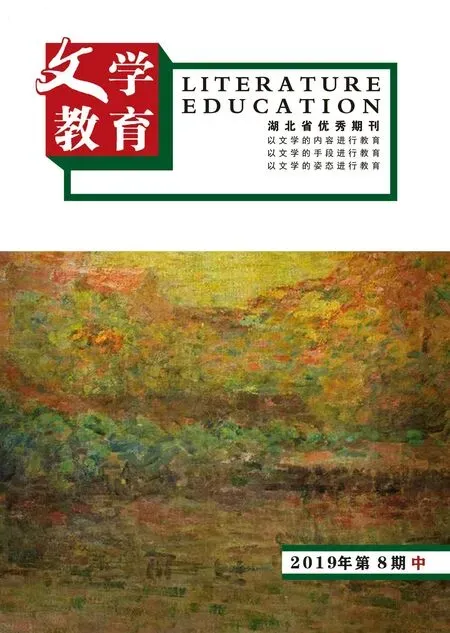《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的“语言”问题探析
陈 桑
《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是海德格尔一份就谈论人道主义的回信。然而海德格尔通篇并不是大谈特谈他的人道主义观,而是要重新讨论什么是关于才是“人道主义”?什么是和人性的?而在谈论人道主义之前,海德格尔奠基性的探讨了思与语言的问题。
一.人对语言之沉沦
海德格尔十分强调语言对于存在彰显的地位,称语言乃是“存在之家”。然而他却揭示了人们遗忘了语言之原初归属关系的指示,语言之真谛在“常人”之中隐而不显。这里的“常人”德语(das Man)更多是指代表一种支配个人的公众状态的人,它既抽象又具体。在中文中也可理解为大家、大众。个体的人为了逃避自由的责任将自己的选择权交予大众,把及自己沉浸在一种公众话语中,受自然语言支配,而在这样的境遇下人被派生关联所掩盖脱离了与存在的本质关联,这也被其称之为“语言之荒疏”。而海德格尔正在借助“常人”这个概念指出人们因为语言之荒疏面对着一种危险,甚至这种危险是人们目前仍然没发现的。他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如此提到:“语言之为语言究竟向来是以何种存在方式存在的?到处而且迅速地蔓延着的语言之荒疏(verördung der Sprache)不仅消耗着一切语言用法中的美学的和道德的责任,而且这种语言之荒疏根本上来自一种对人之本质的戕害……在今天,这样一种语言用法甚至毋宁是说明了我们还根本看不见而且不能看见这种危险,因为我们还从来没有注意过这种危险……在现代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统治之下,语言几乎不可遏止地脱落于它的要素了,语言还对我们拒不给出它的本质,即:它是存在之真理的家。语言倒是委身于我们的单纯意愿和推动而成为对存在者的统治工具了。”①在这里海德格尔就强调语言降格成为了我们用来统治存在者的工具,沦为了一种技术性的用途。
他同时认为形而上学也不过语言工具性使用的一种体现。殊不知在海德格尔的意义下,真正的存在之真理就是“自行自送,显隐一体”的。即存在不断的显现又不断的遮蔽,而不管是什么样的形而上学总是要把存在对象化,总是强调其显现光明的一面,却忽略了存在自行遁隐的阴暗面。海德格尔引入“绽出”(ekstatisch)这一概念,也可以翻译为绽入,实际上这个词在德语中即有出又有入的意思。海氏正是要用这个词来区别于形而上学中常使用的实存(existentia)和本质(essentiae)。这两个词总是强调光明显现的一面,凸显存在者显示存有,而“绽出”(ekstatisch)则是既要进入显现之存有,又要走出去回到阴暗中,就像出入光暗的两个场域,而不限于预设存在者的前提。所以,绽出正是对应着显示与遮蔽的一体性,同时一定把存在去对象化,存在必定是域化性的。绽出的途径就是要通过在与存在打交道中转入存在,在这个域中存在既显现又隐匿。海德格尔在的一段就明确指出:“实际上,在‘环境’(Umgebung)一词中,集中着生-物的全部谜团。语言在其本质中并非一个有机体的表现,亦不是一个生物的表达。所以,语言也绝不能从符号特性方面得到合乎本质的思考,也许甚至不能根据含义特性得到合乎本质的思考。语言乃是存在本身的橙明着-遮蔽着的到达。”所以,反过来说正是这种主体形而上学下的使用,使得语言脱离了它的要素。海德格尔曾很形象的做过鱼与水的比喻。人不可能通过考察离开水的鱼儿确定其生存周期,因为鱼儿已经脱离其生存之要素。同理,语言亦是如此。我们不能脱离语言之要素来使用语言。
二.语言自身之矛盾
故而海德格尔要重新唤起人们对于语言真正含义的重视。那就是要进入让语言重新与存在关联,按照海德格尔话讲就是再度回归到存在之近处。他的具体论述是这样展开的:“然而,如若人还要再度进入存在之近处,他就必须首先学会在无名中生存 (im Namenlosen zu existieren).他必须以相同方式既认识到公众状态之诱惑,又认识到私人领域之无力。人在说话之前,必须先让自己重新接受存在的招呼;这时人就有一种危险:他在这种呼声之下鲜有可说或者罕有可说。只有这样,词语才能重获它的本质的宝贵,而人才能重获适合于在存在之真理中居住的寓所。”②他重点提到了“无名中生存”,一旦人开始言说他就极其容易受到集体无意识的支配,实际上并不是自己在言说而是在传达一种集体意识。即使作为个人只是尽力去对这种公众事物集体意识的否定,他仍然脱离不了集体意识的支配。因为这种看似自由的私人话语却要依赖公众事物而得以成立。海德格尔很锐利的看出了这一点,他如此提到:“于是,‘私人生存’就违背本己的意愿而证实了它为公众状态所奴役的情况。”③所以,私人领域是多么无力。因此海德格尔认为首先是不说或者无话可说,达到一种无名的生存——这里的不可说要区别逻辑实证主义的不可说,逻辑实证主义的不可说还是停留在论证与逻辑函项的推理说明,把所有存在问题掷入另外一种人工语言中去,将符合这一人工语言(也就是逻辑)可表达得称之为可说之物,将其不可表达的称之为不可说。实际上,这仍然只是形而上学的老把戏——对象化了存在之本质,在逻辑实证主义中把存在变成关联项。然后不可对象化为关联项的东西便不可说。海德格尔是如此提到:“语言倒是委身于我们的单纯意愿和推动而成为对存在者的统治工具了。存在者本身显现为因果网络中的现实事物。我们在计算和交易之际与作为现实事物的存在者相遭遇,但也科学地与之相遭遇,在用种种说明和论证进行哲学活动之际与之相遇。甚至那种声称某物不可说明的保证,也属于这类说明和论证。以这样一些陈说,我们便自以为立身于神秘(Geheimnis)面前了。仿佛这已经是如此确定,以至于存在之真理完全可以归结为各种原因和说明之根据,或者——那是同一回事——可以归结为真理的不可把握性。”④海德格尔的无话可说远不是在这人工语言意义下的不可说,人工语言仍然是一种工具化的受人支配的语言。最后,这就引出了一个矛盾问题或者说是“危险”,海德格尔极力要人们告别派生关联回归本源关联当中去,即与存在一道。但此时人们又无话可说是否会使得语言自我消解呢?无话可说的语言还能称其为语言吗?一种极力要求语言回归自身本质要素的诉求最后致使语言自我取消的结果是否显示着海德格尔理论的矛盾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三.语言暗示着存在
早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开头,海德格尔就放出了这样的洞见:“思想完成存在与人之本质的关联。思想并不制造和产生这种关联。思想仅仅把这种关联当作存在必须交付给它自身的东西向存在呈献出来。这种呈献就在于:存在在思想中达乎语言。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思想者和作诗者乃是这个寓所的看护者。只要这些看护者通过他们的道说把存在之敞开状态(Offenheit des Seins)带向语言并且保持在语言中,则他们的看护就是对存在之敞开状态的完成。”⑤可以看到海德格尔强调存在在思想中达乎语言,语言便是存在之要素。思想则是要通过人用语言将存在之本身呈献出来。故而我们可以理解为,与其说人通过语言将存在呈献,毋宁说存在是在借助人道说自己。人总认为语言是自己的工具,实际上在海德尔格看来人是语言的工具,是存在的这一种本源性在征用人来呈献自己。因而当人将语言当作自身的附属用来技术性的述说存在者时,已然陷入了这样一种危险即海德格尔所提到的一种语言之荒疏。正在在这样的情形下,海德格尔才呼吁要回到存在之近处,人要参与到对存在的参赞工作中去。而哲学与诗正是这种征用工作的具体表现,这也是为何海德格尔强调思想者和作诗者是这个语言寓所的看护者。人与语言主次关系的不同就使得语言具有两种身份。当人在利用语言时,是语言流于存在者之中扮演着一种日常语言或者说自然语言的角色,这是海德格尔要批判的。而当语言(存在的征召)在利用人时,语言便超越了存在者达成了与存在的本源关联,而这就是艺术、美学与诗的领域。这时候思想者和作诗者便有了发言权。所以,海德格尔要语言回归本质要素使其无话可说是要其就存在者方面无话可说,并非语言自身无话可说,语言仍然可以去道说。这种道说就是就是去言说关于存在与人最本源的关联,以及达乎审美与艺术的象征领域。
与此同时,当人进入本质关联,并非抛弃派生关联(存在者)而是重新确认派生关联,更热切的去生存这就是前文提到的绽出之生存(Ek-sistenz)。在澄明着-遮蔽着的两种状态下出入,而这时语言直接的对象化的规定诉说,而是象征着的去感应存在之征召。所以关于语言的言说他是有一个平衡点,那就将语言诉诸于诗和艺术,诉诸于审美来暗示着存在的真理。虽然这表面上看仍然是一种语言的言说,但是是带有关于存在之关切的言说,也就是道说。张柯教授也这样提到:“语言之本质如是被揭示为“同一性与差异性”之根据,根据在自身同一中差异化即在显示中自行隐匿,此即道说(sage):以暗示的方式进行的显示。从而,语言之本质转化为本质之语言。”⑥用语言的道说暗示者人与存在的本源联系。这就有点类似老子的《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之言。但老聃仍然洋洋洒洒写成了道德经五千言,把不可说之道道说了一遍。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关于语言学说天然的就与道家哲学有着微妙的共性,那么后期的海德格尔沉迷于道德经研究也就不足为奇了。
注 释
①[德]马丁·海德格尔 著,孙周兴译.路标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72-373.
②③④⑤[德]马丁·海德格尔 著,孙周兴 译.路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73-374、371、373、366.
⑥张柯.论后期海德格尔的“语言本质”思想[J].江西社会科学,2008,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