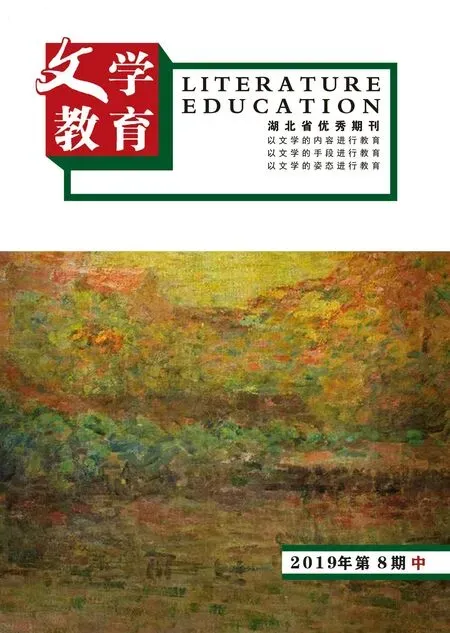论韩少功寻根小说中的意象世界
杨兴龙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坛出现了“文化寻根”思潮。一些作家开始关注本民族传统的历史、命运,大量运用象征性、隐喻性手法创作小说作品,“寻根文学”作家群体非常看重意象的塑造与运用。韩少功是八十年代“文化寻根”文学活动中的代表性作家,特别在乡野文化题材方面,他堪称一位旗帜性的人物。1985年,他发表了后来被批评界认为是“寻根文学”纲领性文论的《文学的“根”》一文,他在文中提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根不深,则叶难茂。”①
《爸爸爸》作为韩少功寻根小说的代表作,其情节充满离奇色彩,在细节方面运用了大量充满冲突的意象。笔者看来,无论是人物还是物体,在“象”方面,都具备许多丑陋、离奇、令人嫌恶的表征特点,而其背后的“意”又富于隐喻性,指向韩少功对深层次的文化内涵的思考。
一.《爸爸爸》中疯癫、蒙昧的人物形象
在韩少功的寻根小说中,大多数人物已经并非单纯的形象,他们已经被作者当做一种意象来对待。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携带了很多非正常的符号化特征,是对原始社会下人性与社会群性的抽象,是韩少功试图表达的思想的隐喻,具有很强的象征意味。韩少功塑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些带有疯癫因子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都具有深刻的文化指向,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其著作《疯颠与文明》中说,“疯颠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颠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颠的历史。”②福柯在这里表明了他的观点:疯颠会成为疯颠源,是因为正统文化的历史文明对其的压迫、排斥、迫害,在理性文明定义下的疯颠指向一切非理性的情感、行为,非理性从而成为区分疯颠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在韩少功的作品中塑造了许多类似于巫师、神婆这样的具有疯颠性质而又不失神秘色彩的这一类人物,《爸爸爸》中的丙崽,他的心理、动作、言语都是正常人无法理解的,他除了具有生理上的缺陷外,他的行为也很怪异,这在现代文明社会科学理念之下是不能相容的。
《爸爸爸》中,主角丙崽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莫过于他仅仅会说的两句话:“爸爸爸”与“x妈妈”。乍看之下,似乎很令人费解,但这确实是韩少功塑造出的丙崽所能具备的全部思维模式。其中的象征意味是相当明确的。在巫楚文化的原始社会中,人类的认知范围有限,父亲、母亲与性行为是为数不多的普遍认知对象。徐睿在《宗教对性别角色的塑造》中讨论到中国原始宗教时,提出:“……男女两性被推到了两级,并分别被盖上了神圣和世俗的印章。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认为,原始宗教环境下的概念普遍具有不同方面的意义,居于崇高的、神圣的一极的是男性及其象征物,与他们相对的当然是不洁的、危险的女性一极。”③可见,作为原始社会的一个象征和缩影,韩少功笔下的丙崽其实是在用这两个词进行最简单的价值判断:碰见需要讨好的,令人高兴的,营造正面情绪的事物,一律喊“爸爸爸”。而与之相反,则喊“x妈妈”。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看似仅仅是丙崽这个痴呆怪物的想法,但其实这背后深层影射的是寨民们的思维模式:对待丙崽,要么当作一个可以随意杀掉的祭品,主宰他的生杀大权,要么当成跟刑天祖先神一样的大仙,心甘情愿地为他做奴仆;期间态度变化完全就是无缝衔接。对待鸡尾寨的人,则必须欲杀之而后快,因此才会出现“打冤家”这么一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行为,最终让全寨的命运陷入无法挽回的后果。通常而言,社会越处在原始阶段,人类所触碰的事物就越少,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也就更有普遍性。但是,从现代理性立场来看,这种粗暴的、未开化的思维方式,也明显是许多现代社会的积弊所在。
韩少功在小说中还塑造了一些带有封建烙印的蒙昧型人物意象,在他们身上可以毫不费力的找到传统文化中所存在的糟粕,如:愚昧、固执、保守等。在《爸爸爸》中,寨中给众人服毒的仲裁缝,与众多心甘情愿接受服毒而亡命运的寨民,他们是蒙昧时代民间保守主义的主流人群的代表。仲裁缝是寨里为数极少的文化人,他知道三国时诸葛亮的贤名,但又堪称迂腐,还把鸡头寨的存亡安危跟卧龙先生联系在一块;他又恪守封建教条,不与女性和小孩来往,妻子一去世,他就进入了永远不苟言笑、茕茕独立的生活状态。他一直抱着古代社会歧视女性的态度,特别是与丙崽的母亲尤其不睦。
笔者发现小说中塑造的蒙昧型人物意象具有一种原始思维逻辑的特点,即“原逻辑思维”。法国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列维·布留尔曾提出:“可以把原始人的思维叫做原逻辑的思维。”④而他们把握事物之间的关系靠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严谨的逻辑推理,而是通过类似天马行空的想象,把现代人看来毫无关联的事物相关联,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体现为“互渗律”的形式,正如布留尔所说:“首先对人和物的神秘力量和属性感兴趣的原始人的思维,是以互渗律的形式来想象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它对逻辑思维所不能容忍的矛盾毫不关心。”⑤
这种原始人的思维模式,在韩少功的小说中有多处直接体现,例如,在写到鸡尾寨的景象时,作者提到了蒙昧的村民把生殖器与水井、大樟树关联在一起,因为他们之间外型相似。文中提到,“有一年寨子里一连几胎都生的女崽,还生了个什么葡萄胎,弄得空气十分紧张。查究了一段,有人说鸡头寨的一个什么后生路过这里时,曾上树摸鸟蛋,弄断了一根枝桠。”⑥因此,蒙昧的寨民把村子连续生女孩的原因归咎于一件偶然事件。
二.《爸爸爸》中丑恶、陌生的物体意象
所谓意象,是赋予自然或非自然事物象征内涵。在韩少功的小说中,荒诞、污秽、超自然的物体描写此起彼伏,占据了文章很大一部分篇幅,总体来说,《爸爸爸》中秽物的陈列、怪力乱神的显灵,都有着较为明显的目的:通过不断地恶意想象来塑造、连结众多丑恶的物象,营造一种与传统寻根文学截然不同的氛围,对此前多数乡野寻根文学形成一种叛逆。
在《爸爸爸》中,诸多物象本身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感官冲击力:人尸体和猪肉混合煮成的“枪头肉”,老鼠尸体化成的灰烬,各种各样的异形、畸变的人类躯体,等等。小说中“鸡头寨”最后的结局在笔者看来具有很强的象征意味:青年男女在凤凰的带领下迁徙。这隐喻了现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与面临的困境,正如鲁枢元、王春煜所论:“鸡头寨人的生活被凝滞了,被扭曲了,后路是悬崖峭壁,是丙崽式的‘原始浑朴’;前程,是烈火熊熊,是仁宝式的‘现代文明’。鸡头寨人往何处去?是逃往更幽深的山林或是迁入更发达的城邦,如何才能逃出被封闭凝滞被异化扭曲的困厄,这恐怕不只是鸡头寨人面临的问题,同样也是每一个有良知的现代人所面临的问题。”⑦
小说《爸爸爸》中这种完全反传统的意象群构建,大量的使用丑陋、龌龊、令人恶心的意象,给传统审美观念带来了挑战,可以说在当时中国文坛是独树一帜的。说起来,这些恐怖、丑恶的物象不仅仅是出自联想而已,在传统文化中,这些事物本身就具有文化象征性。作者在这以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进行陌生化处理,这种新奇的笔法的确给全文定下了“陌生化”的基调。
对于这种“陌生化”意象的运用,蓝天提出,“但《爸爸爸》却一改故辙;……而又不希望它(《爸爸爸》)的读者驻留于‘陌生化’的形式中,而是企图借助这种手段,臻至重新认识我们民族传统的每种思想维度、每一段历史与现实”。⑧可见,这绝不是纯粹的猎奇:这些丑恶的群像是对传统文化一次无情的揭露,让整部作品的立意变得更加深邃,更加富有多元化的哲学意识。
三.结语
对于韩少功的作品,评论界一向存在多种解读的路径。鲁枢元认为韩少功自己也陷入了矛盾,他在一番欣喜之后试图寻求的文化之根,结果却满是愚昧与野蛮,看不到一点孕育着历史进步的希望;旷新年则认为韩少功仅仅是有目的地进行一些警示与反诘,对于文化寻根思考的结果,他仍然是持开放性态度的。
每一种解读,都是作品问世至今三十多年内,文学批评界多元化发展的结果,从认识论上看都有其合理性。但无论何种解读,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如同社会学家所揭示的,传统文化根植于古代社会,而古代人的思维具有明显的互渗性、象征性,在原始社会人类的行为中,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现代意义上的高尚与丑恶,各种各样的道德往往是混杂在一块的,高尚与丑恶是交织而难以分离。现在看来,韩少功所塑造的疯癫、蒙昧人物形象以及众多丑恶的反传统意象具有一种生命的原始张力。看似荒诞,实则承载着生生不息的原始生命力。韩少功的“文化寻根”在一定程度上是没有达到预期成果的,他探寻到的传统文化的内核,正如他笔下的意象世界一样,有极其不堪的一面,但在另一种意义上,韩少功也明确地揭示了文化寻根具有超乎大多数人想象的艰险与复杂,这无疑是在文学思想上非常有深度的一次创作探索。
注 释
①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②[法]米歇尔·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疯颠与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93-201页.
③徐睿:《宗教对性别角色的塑造》,P53-55,四川大学,2004硕士论文.
④[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1页.
⑤[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8页.
⑥韩少功:《爸爸爸》,《韩少功自选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⑦鲁枢元、王春煜:《论韩少功小说的精神性所在》,《文学评论》1994年第6期.
⑧蓝天:《〈爸爸爸〉给象征性小说带来什么?》,《南充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