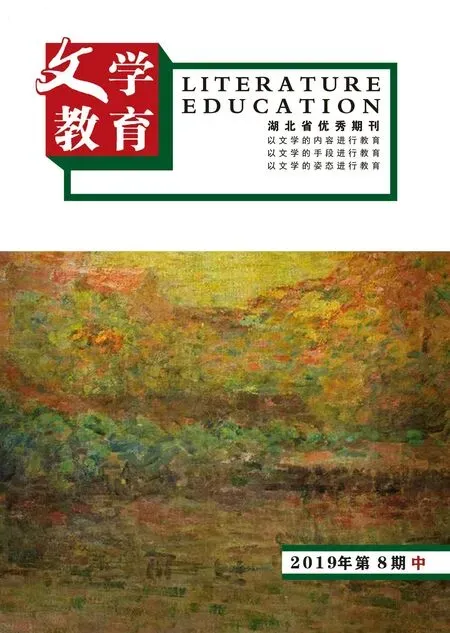“80后”作家乡土小说的魔幻现实主义叙事
常鹏飞
一
20世纪8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1]同中国当代文学发生了碰撞,而作为一个来自拉丁美洲的文学流派,其不仅造就了八十年代“马尔克斯热”,滋润了一大批中国作家的创作实践,而且给当代文学此后的发展亦带来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如90年代以来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张炜的《九月寓言》等小说,都体现了对魔幻现实主义使用上的自觉与探求。新世纪以来,则出现了莫言的《生死疲劳》、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余华的《第七天》等继续进行着自我探索与实践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
早期“80后”作家的创作大多肇始于城市当中,着力于青春题材的书写,充满着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倾向,他们不再相信任何坚固的现实或崇高的理想,仿佛“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所以,他们的创作往往沉溺于此时此刻、束缚在自我的世界当中,很难承载所谓的意义或者价值,即使有想象的飞驰,如郭敬明的《幻城》《爵迹》等,也大多流于虚无缥缈的空想,拘泥于故作沧桑的姿态下对华丽空洞的语言的堆砌。至于那些盛行于网络的玄幻、仙侠、灵异类小说,则彻底脱离了社会现实,并卸去了对其应有的思考与探索,沦为仅供消遣的类型化文学。
书写乡土的“80后”作家,则大多本就来自具有丰富地域文化气息的乡村。如黔西北野马冲的曹永、边地云南的甫跃辉、宁夏西海固的马金莲、四川郫筒镇的颜歌、海南澄迈的林森、湖南隆回的郑小驴、粤东陆丰的陈再见、广东潮州的陈崇正、湖北万家乡的宋小词等,他们在民间文化充盈的乡村中成长,风情民俗、传统仪式、神怪传说、传奇故事、气候地貌、宗教信仰等成为他们回望乡土时的构成性因素。可以说,和如今高度同质化的城市社会相比,“乡土”本身就是充满“魔幻”气息的“化外之地”。除此之外,“80后”一代面临的不只是失去统一理想的“无名”时代,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们遭遇的外部环境与价值观念想比前代人也更加丰富与多元。如此,他们对待各种理论、作品时,就少了许多先入为主的成见,多了份兼容并包的达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目前“80后”作家的主体意识尚未完全形成,所以,在写作资源的选取和写作路径的构建时,就会多了份随意性,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自觉。不过,可以确信的是,他们面对纷繁的写作资源和创作技法时,自身经验是随之敞开的。因而,“80后”作家在选取带有“魔幻”气息的“乡土”为书写对象时,创作手法中也往往有意或无意的带有了“魔幻”的色彩。
二
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谈及贵州作家蹇先艾的《水葬》一文时,就曾说过其“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2]出生于黔西北野马冲的曹永,向我们展现的即是贵州乌蒙山腹地的恶劣环境、苦焦生活与残酷人生。《捕蛇师》中的老獾是个精通捕蛇之术的农民,因祖上掌握招蛇术遭受报应,后来立下了此术只能为救人所用的家规。可没想到的是,老獾考上大学的儿子因没找到工作又干不了农活,竟然偷学招蛇术赚取利益,结果中蛇毒而亡。小说以“招蛇术”开始,亦以“招蛇术”收尾,“招蛇术”既是小说的线索,又是小说到达高潮的引子。随着老獾在儿子坟前,完成了最后一次“招蛇术”的仪式,小说也戛然而止。小说中的“招蛇术”,是民间乡土文化的一种象征,其“最重要的是捕蛇师在施行招蛇术中所体现的乡村神秘文化的符号意义和仪式感”,[3]而在“符号意义和仪式感”的背后,实际上指向的是现实乡村中的世道人心。捕蛇术既是象征神秘文化的乡村秘术,又是与外在世界相对的自足稳定的乡土产物,老獾之子“多福”象征的则是经受过城市浸染的“出走者”。然而当面对违禁抓蛇的“返乡者”多福时,老獾发出了“多福以前没这么狠毒,怎么读几年书回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4]的无奈和感慨。此时,稳固的乡土文化与民间伦理被撕开了一道裂缝,透过裂缝,我们可以看到乡土正在被现代文明侵犯与浸染的现实。小说结尾,“招蛇术”的断绝中暗含的亦是乡村中的“老獾们”发出的绝望的嘶喊。曹永借助富有魔幻气息的招蛇术来呈现变动中的乡村现实与世道人心,而在“招蛇术”的咒语声中,俨然亦是一曲凭吊乡土的沉痛挽歌。
三
甫跃辉在小说集《鱼王》的自序里说,“城市坚硬的现实长不出神话故事,也长不出鬼怪传说。”[5]其中的“鱼王”“鹰王”“豺”正是三组与乡村相关联的传奇故事。和他的“海漂”系列小说不同,甫跃辉在乡村安置的是具有神性的动物的传奇故事,而非象征城市的“巨象”或者被豢养在笼子里的“饲鼠”。“象征型艺术的目标是精神从它本身得到对它适合的表现形象”,[6《]鱼王》中的只剩下骨架的“鱼王”、消失的“鹰王”和从未露面的“豺”,构成了人与动物、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互文关系,它们与其说是作为神性存在的实体,不如说是作家欲以呈现的符号。就像小说中辈辈相传的“鱼王”在村民的哄抢之中得到“祛魅”,最终成为一具“史前动物般洁白、匀称的骨架”,[“7]鱼王”神性的“祛魅”过程也变为村民们人性的沦陷过程。回归天空的鹰王,则见证了村民的贪婪与庸常,以及无处不在的豺所带来的神秘性与恐惧感,可以说,小说集中每个故事的终结仿佛都昭示着另一种开始。还有《玻璃山》中灵异又带着温馨的人鬼友谊、《红马》中爷爷身骑红马遭遇的奇异事件等等,甫跃辉讲述的这些带有魔幻色彩的乡土故事,大多基于边地云南的民间文化与乡间流传的传奇见闻。但归根结底,甫跃辉不过是意图透过种种神秘传奇去观看天地万物,就像他引述鲁迅先生的话一样,“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8]
四
陈崇正是“80后”乡土作家中探索意识较强的一个,他的小说大多结构在虚构的“半步村”之上,“它其实就是取一个谐音‘半不存’,意指乡村伦理和文化脉搏半生不死的状态。”[9]围绕着这个虚虚实实的文学地理世界,陈崇正不断糅和进各种叙事元素与创作技法,在一个个亦真亦幻的故事中,把小说指向荒诞的乡土现实与沦陷的世道人心。陈崇正曾说,《黑镜分身术》是可以当作长篇来读的,这大概源于小说中的五个故事都发生在“半步村”中,并以互相嵌套的方式发生交互与撕扯。小说中的“分身术”作为一种异能存在,能把人分为不同年龄段的数个个体,以获得时间与空间的延展,进而达到突破时空束缚的目的。陈崇正“试图凭借荒诞而梦幻的‘分身叙事’在半步村的已知时空里置换或分出多重时空,通过摆脱历史与消解现实的方法救赎由小说背景所命定的罪罚,在另一时空里推演半步村的未来。”[10]然而,不管作家在“半步村”之上萦绕了多少神秘诡异的气息与荒诞不经的故事,以及在创造技法上如何杂糅与多变,但究其根本,魔幻的滑行最终到达的要是现实的彼岸,只有沉重处升华的轻逸才是有根之物,而陈崇正显然对小说如何“飞天入水”[11]了熟于心。
五
除此之外,西海固作家马金莲小说中富有宗教气息的死亡叙事亦带有穆斯林文化中特有的魔幻色彩。死亡,在马金莲的小说中是司空见惯的存在。“回族认为,死不是生的彻底结束,而是人生的复命归真,是一个人的必然归宿。”[12]这种“两世并重”的人生观念,使得回族人民对待死亡具备了更为达观的自觉意识。而在伊斯兰宗教文化的浸染下,丧葬仪式自然就富有相对的异质性,如通过“送埋体”、“散海底耶”、请阿訇念“苏热”等仪式,传达生于死之间的联系与沟通。“死亡是洁净的、崇高的。”[13]《长河》中,通过对伊哈、素福叶、母亲、穆萨爷爷死亡仪式的描写,在充满神秘性的死亡仪式里,把生与死的哲学也汇入到时间的长河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魔幻现实主义在不同作家的创作中呈现出具有异质性的样貌,而“80后”作家在书写乡土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采用,往往缺少了前代作家对意识形态与传统观念的反拨意识,他们更加注重的是把其作为表现乡土的象征对象与创作方法。换而言之,“80后”乡土小说作家是把魔幻现实主义提升到独立的审美体系来看待与使用的,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魔幻现实主义最终应指向现实,回归到此时此地,而非偏向滥用技法、随意杂糅的拼贴式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