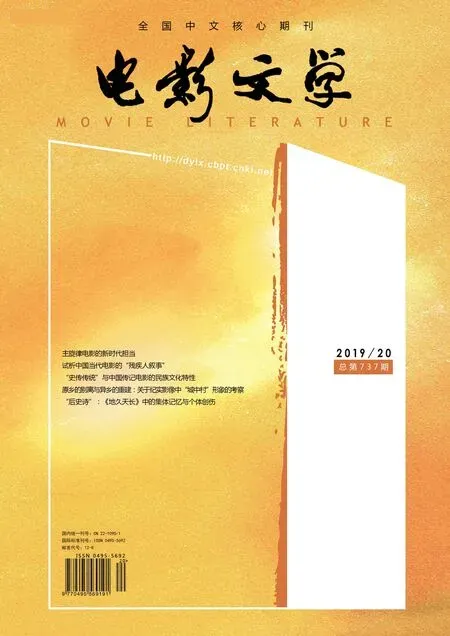试析中国当代电影的“残疾人叙事”
刘 堃 梁钟一鹤
(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
一、引 言
正如电影《我不是药神》里的台词所说,“谁家能不遇上个病人呢”。疾病是每个人都可能面对的生存境况,“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1)[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5.,苏珊·桑塔格的这段话,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容易被人忽略的是,疾病还存在一种极端情况——残疾。被打上“残疾”标签的人即便脱离了疾病对人体健康的威胁,却在肢体、精神、智力或感官层面留下了不可逆转的长期损伤,同时也被永远禁锢在“疾病王国”的领土。在大众的认知里,残疾天然地与“非正常”画上等号,残疾人已经被逐出正常人的领域而成为异质性的“他者”。
现代文明社会的共识,是尊重残疾人的人权,对这一“失能/限能群体”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与帮助。一个社会的残疾观,也是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1949年以后,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创(1949—1965)、停顿(1966—1976)和重建(1977年至今)三个阶段(2)奚从清.残疾人社会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148.,从1981年起,《人民日报》数次刊登了来自山东莘县的瘫痪女青年张海迪的事迹,1983年共青团中央授予张海迪“优秀共青团员”称号,一时间身残志坚、自学成才的张海迪成为当代青年人的榜样,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在张海迪式的“榜样力量”的建构中,文学、影视等媒介形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80年代大众传媒曾为人们树立了一系列英雄楷模,其中残疾人占有相当的比例”(3)文娟.残疾题材电影的特质与发展[J].电影创作,2001(03).,在电影作品中,有残疾劳模李云慷慨相助见义勇为青年、倾其所有为其寻找目击证人的故事(《关于爱的故事》,1997);有一聋一盲两个少女相互扶持、凭借顽强意志刻苦读书取得优异成绩的故事(《不能没有你》,1998)等。主人公身体的残疾令其内心的坚强显得尤为可贵,电影叙事的逻辑是对健全人的勉励鞭策——残疾人尚能如此,健全人更应不甘落后。这种“正能量”的精神基调对应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号召,“身残志坚”成为社会大众对残疾人群体的期待,但其中的问题是,“身残”与“志坚”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逻辑联系呢?如果电影作品暗示了这一点,是否会造成社会大众对于残疾人的高期待并使残疾人产生心理压力呢?与此同时,在民间通俗曲艺作品中,仍然存在着对残疾人的模仿与嘲讽的现象(4)韩秋月.负面的背后——对赵本山小品中负面因子产生的文化因素分析[J].名作欣赏,2013(33).。这种看上去二元对立的残疾人观,要么是仰视,期待某种身残志坚的英雄人物;要么是俯视,缺乏应有的尊重,实际上其背后的逻辑是统一的,即没有把残疾人当作正常人来看待,没有平等意识。
其背后的原因,既与宗教意识缺失、人权意识淡漠的国民性有关,与国家政策的过于宏观有关(5)我国虽然有残疾人保护法,但只是总体方向的规定,在入学、就业、招工包括公共设施等方面,没有像欧美国家那种细节操作上的规定和要求,更没有对歧视者、违反者严厉的惩罚措施。,也与文学艺术作品缺乏对残疾人的深入理解和成功塑造有关。2000年之后,残疾人题材电影在艺术表现层面有所突破,关于残疾人的塑造也更加丰富。不过此类电影更多将视点聚焦于残疾人的家庭及家人,旨在呈现残疾人家庭的艰辛以及亲情的坚毅与强大,例如2000年的孙周导演作品《漂亮妈妈》和2010年薛晓路导演作品《海洋天堂》。这些作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流文艺对“身残志坚”的片面强调,但仍没有走出“煽情”的艺术套路。这类作品情感基调的延续,显示出电影创作者对残疾人作为认“人”的认知维度并未产生本质性的突破。
2014年,娄烨执导的电影《推拿》问世,引起业界关注和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残疾人题材电影的真正突破。此后,当代电影对于残疾人的表现和叙事有了不同于前的内容和质素。有鉴于此,文本尝试以近五年来有关残疾人的电影叙事文本为研究对象,分析这类作品的叙事特点、认知价值以及审美意蕴,从而总结出这类作品在建构残疾人形象时所达到的社会学思考与文化贡献。
二、残疾人的情感叙事与“健全”诉求
2014年,由娄烨指导的电影《推拿》斩获第51届台北金马影展最佳剧情片奖、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杰出艺术成就奖银熊奖、第9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电影奖和第15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电影奖,其同名原著作品——由毕飞宇创作的小说《推拿》也曾于2011年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可以说,无论原著还是电影改编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业内的关注及认可。
《推拿》描述的盲人群像是中国当代影视作品中较为少见的艺术形象,电影以沙宗琪推拿中心为叙事空间,讲述了发生在盲人推拿师之间的爱恨纠葛,突破了此前残疾人题材影视作品对于残疾人的刻板化塑造,呈现出一个更为日常、更为现实的盲人世界。
作为一部展现盲人生活的电影,《推拿》并非以塑造某个体形象为目的,而主要是通过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来呈现一组盲人群像。其中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描写,既包括残疾人之间的交往,也包括残疾人与健全人的接触。爱情是影片在讲述残疾人之间的交往时侧重表现的一方面,其中既有两相情愿的爱恋,如王大夫与小孔,金嫣与泰来的爱情;也有苦恋无果的单相思,例如小马对小孔的情愫,沙复明对都红的追求。影片中爱情关系的多样性,旨在建构复杂的感情纠葛,以此凸显盲人群体内心生活的敏感与丰富。
王大夫与小孔的爱情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小孔的父母对她的爱情寄予功利性的期望,不愿女儿与一个“全盲”结合。由于无法得到家庭的认可,小孔只得用谎言与“私奔”维系亲情与爱情的平衡。而王大夫这里,家庭负担使得他与小孔的婚姻迟迟不能提上日程,他的内心对于瞒着父母与自己“私奔”到南京的小孔抱有愧疚,却又无法舍弃作为家中长子的责任。此外,两人的爱情也遭遇了第三者介入的危机——小马对小孔萌生情愫。这令小马背负了道义上的压力,也令互为同事的三人陷入无声的尴尬。其后,伴随着都红对小马的示好、沙复明对都红的追求等情节的出现,王大夫与小孔的爱恋最终演变为“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承受着来自内在与外界的双重压力,显示出盲人作为一个情感主体的复杂性。
其他角色的爱情同样充满曲折,比如金嫣。她并非全盲,而是一个逐渐丧失视力的人,她渴望在拥有视力的时候获得一份“看得见”的爱情,所以在与不善言辞的泰和相处的过程中,她必须做那个“主动出击”的人。再比如沙复明,他与都红的感情在单恋的阶段戛然而止。与其他人相比,他的感情经历更为曲折暗淡,和健全人相亲,他因残疾人身份而备受歧视;关怀照顾都红,却被视为“怜悯”。尽管他十分渴望爱情,但自始至终都未能如愿,只能孤独地背诵着海子的诗,想象着抽象的“美”和“爱情”。
在盲人的世界里,他们与正常人一样,有着正常的情感诉求,也同样存在着相互爱恋、暗恋、单恋等常人爱情的表现形式。但是,在盲人与健全人接触时,健全人由于集体无意识中的偏见,不能理解他们的正常诉求,往往导致双方情感上的隔膜。在电影中集中表现为两个事件:一是“三轮车事件”,二是“羊肉事件”,这两个事件都发声在推拿中心的健全人——前台高唯、杜莉和厨师金大妈之间。高唯常常用中心公用的三轮车搭载都红,招致杜莉的不满;金大妈偏爱杜莉,打饭时将超量的羊肉装在杜莉的盒饭里,这又引起高唯的不满。三位健全人在推拿中心都拥有一定的权力,却存有私心,假公济私,他们之间的恩怨也波及了盲人群体,破坏了原本和谐共处的气氛。
除此之外,电影还表现了健全人对盲人出于善意的伤害。都红的美貌招致许多客人的赞美和惋惜,在健全人的认知里这是一种鼓励与认可,然而都红愤怒地说,“我觉得那就像个笑话”。视觉概念的美在她的世界里没有意义,甚至变成了一种嘲讽、责备。又比如小马,在影片中两次被健全人称呼为“瞎子”:一次是他与小蛮在洗头房被警察抓走时小蛮向警察喊道“别抓他,他是瞎子”;另一次是小马为小蛮出头与人打架时劝架的人喊道“别打了,他是个瞎子”。在与健全人的接触中,小马变成了一类特殊的人——瞎子。在当时的语境下,它的含义不是眼睛看不见的人,而是“弱者”;而健全人的逻辑也不是同情弱者,而是站在居高临下的位置上不愿与弱者计较,实际上是一种根底上的轻蔑。“《推拿》让我们看到,歧视和伤害,有时恰恰是以慈善和关爱的面目出现的。”(6)王彬彬.论《推拿》[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02).泰勒在《自我的根源》一书中曾指出,“一个人不能基于他自身而是自我。只有在与某些对话者的关系中,我才是自我”(7)[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50.。电影《推拿》通过描写盲人与盲人、盲人与健全人之间的情感、恩怨、距离、纠葛,呈现了一个血肉饱满的盲人世界,同时也揭示出盲人与健全人之间的隔膜,深刻揭示出他们的生存困境。
三、残疾人的精神困境及其表现主义呈现
2018年末上映的喜剧电影《无名之辈》同样涉及残疾人叙事。与《推拿》类似,《无名之辈》也是一部力图呈现特定人群群像的电影,只不过电影将叙事引向了光怪陆离的底层社会。正如导演饶晓志所言:“‘无名之辈’这四个字才是主题,才是我创作的出发点,哪怕只是小人物或平凡人,他也有尊严,有孤独,有爱情,还有底层的浪漫。”(8)饶晓志,陈晓云,李卉.《无名之辈》:一种逆袭的可能[J].电影艺术,2019(01):73-78.在电影有关“底层”的想象中,这个小人物的世界包括一事无成的穷保安马先勇、来自乡村的“笨贼”胡广生和李海根、夜总会里的按摩小姐真真,以及高位截瘫的残疾姑娘马嘉祺。他们的人生因不同的境遇或文化身份而沦陷底层,却拥有着身份标签无法限定的内心世界。
其中,残疾姑娘马嘉祺是电影所塑造的一个颇为出彩的人物。这个人物以及“不请自来的笨贼与试图自杀的残疾姑娘”的故事创意,来自导演饶晓志此前的话剧作品《蠢蛋》《你好,疯子!》,或者说,《无名之辈》是这两部荒诞舞台剧的电影化改编。如果电影在表现马先勇的边缘身份时聚焦于他求而不得的“警察”身份(体制内),胡广生的边缘性在于来自乡村的他无法适应城市生活的话,那么马嘉祺的边缘性则建立在她特定的状态——残疾之上。这意味着,在通常的观念中,“残疾”与其他弱势群体一样具有某种“标签化”的意味,而影片的展开则是对这种“标签”的质疑与反思。
较为特别的是,马嘉祺与胡广生的对手戏是一种话剧式的呈现,关于残疾人生存境遇的表达也更偏于哲理层面。相比其他残疾人题材电影更热衷于表现残疾人的人生价值、道德品质或社会境遇,《无名之辈》通过马嘉祺对于死亡的执念来探讨残疾人的心灵困境。在影片中,马嘉祺的残疾身份并未与社会生活产生直接的关联,而是在密闭空间(家)中,通过与闯入者(胡广生)的“对话”展开了关于生与死的抉择。由于高位截瘫,马嘉祺的“躯壳”被死死地困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之内,她生活无法自理,无法保护自己,求生不得,求死无门。在日复一日的绝望中,她变得乖戾、暴躁,甚至歇斯底里。无论是嘲弄威胁其生命安危的蠢匪,还是怒骂性骚扰的变态邻居,马嘉祺都将其狠劲呈现得淋漓尽致。电影关于这种性格的呈现一方面呼应残疾身份对她人格的影响;另一方面这是她表达内心世界的途径。从这个角度而言,马嘉祺的塑造中融入了一定的表现主义色彩,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对她内心挣扎的表达探究其内心的困扰。
在与歹徒斗智斗勇的过程中,马嘉祺的脆弱也悄然流露。情绪彻底爆发从马嘉祺在两个陌生男人面前失禁开始,那一刻她的言语变得没有底气,透露出焦虑、恐惧与无助。高位截瘫令她失去的不仅是行动的自由,还有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无论她如何威胁、辱骂李海根(大头)让他远离自己,后者始终不为所动。混乱中,胡广生(眼镜)用毛毯遮住马嘉祺的头部,她唯一可为自我支配的身体部位也终于被剥夺了自由。这个行为是不由分说的怜悯,又冷酷似太平间里的死亡宣告。这时电影将镜头闪回到了当年导致她瘫痪的车祸。对于马嘉祺而言,她作为人的尊严在车祸的那一刻就已经“死”了,尊严的丧失比死亡更可怕,更令人绝望而难以忍受。最终,冷静下来的马嘉祺诚恳地请求死亡:“你们帮我一下嘛,我求你们了……你们就当是做好事,可不可以吗?”此时,人物内心的绝望情绪到达了顶峰。
在中国,人们回避死亡。“这不仅表现为自古缺少对死亡的哲学的、科学的研究,不仅表现为日常生活中死亡从来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话题,还表现为对死和与死相关的事物的多种语言回避。”(9)郭于华.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7.然而在马嘉祺这里,死亡成为渴望,甚至是超越生的希望。作为一个后天残疾人,除了身体的不便,马嘉祺和《推拿》中的小马一样还要承受飞来横祸后的心理落差,所以他们都想到了死亡。如果说小马的自杀行为是出于对没有光明的未来失去期望与信心,马嘉祺渴望死亡则有更为复杂的因素:一方面她要忍耐高位截瘫带来的失去一切自理能力的结果,这意味着她未来的生活方方面面都需要他人的协助,她的私人空间在无限缩小;另一方面,她要承受不能自理更不能自立的心理压力,以及无从言说的憋闷情绪,残疾在限制她的行动空间的同时也限制了她的人际空间,她日常生活中的人际接触只剩下会嫌弃她脏、臭的保姆,图谋不轨的猥琐邻居和心存愧疚而无法破除二人间心灵隔膜的哥哥。因此,在面临生理心理双重困境的马嘉祺这里,求死的心情变得合情合理。
电影关于马嘉祺求死心理的刻画实际上是对残疾人内心世界的深度解读,残忍却蕴含着某种艺术真实。不过,随着电影情节的推进,马嘉祺的内心活动从单纯的厌世情绪变得更为微妙,更为复杂。表面看来,家中闯入两个贼,是刚被保姆抛弃的马嘉祺又一次倒霉遭遇,但她所面对的并非凶恶的江洋大盗,而是心地善良、简单纯朴的“蠢贼”。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们非但没有给马嘉祺造成伤害,反而为她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生气。一方是失去自由的“残废”,另一方则是被生活所迫铤而走险、把犯罪变成了笑话的“乡下人”,两组人物在一次次争吵和调侃中萌生了某种意义的“理解”。特别是导演有意地将胡广生看到电视上的自己被恶搞后的崩溃,与马嘉祺失禁后的歇斯底里镜头安排在一起,目的便在于在强烈的戏剧冲突下让人物之间实现共情。当自我的尊严在对方面前失落,他们便能真正地体会到尊严之于彼此的重要。彼时,二人逾越了健全人与残疾人在精神层面的鸿沟,明白了囿于轮椅的马嘉祺和在城市、农村的夹缝中生存的胡广生不过都是芸芸众生中的无名之辈,尊严是他们最后的底线和所有。一如电影同名主题曲掷地有声的歌词——“粉身也不下跪,卑微的骄傲的我的同类”。这个同类,指的是尊严的受损,身体健全的胡广生,在尊严上与马嘉祺一样,都是残缺的。
整部电影最具有浪漫色彩的片段莫过于胡广生为满足马嘉祺的遗愿,在天台为其拍照的场景。在那段描述中,马嘉祺通过照相定格了完整而美好的身体,还原了作为人的尊严,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封闭空间的打破,因为此时的她已经不再是蜗居在家中的“残废”,而是一个在天台上望风景,和萍水相逢的友人聊人生的马嘉祺。所以,马嘉祺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她阴错阳差地遇到胡广生,由此获得了一个知己,一个真正理解她的人。在此之前不仅她的身躯被局限在轮椅里,她的心灵也因为无妄之灾而变得脆弱、偏执,无法走出精神的牢笼。电影《彩蛋》中她冰释前嫌搬去和哥哥马先勇一起居住,并改换成电动轮椅常去探视胡广生,意味着她终于主动尝试着走出封闭空间,开始接纳与外界的接触,标志着她对于心理障碍的突围。
《无名之辈》通过对马嘉祺心理和生活变化过程的描写,深刻地呈现了一个重度残疾人的内心世界,那里有歇斯底里的困兽挣扎,也有心如死灰的痛苦绝望;有捍卫尊严的坚硬,也有与人心灵相通的柔情。就这样,一个立体的、鲜活的灵魂冲破了那失去知觉的肉体,建立了一个精神世界的自我。“无名之辈”也终于鼓足勇气喊出了自己的名字,呼应着那句经典的台词“你叫胡广生?我叫马嘉祺”。此时,胡广生已经不需要那个用谎言编制的名字“眼镜”来自欺欺人,马嘉祺也不用绝望地自嘲为“残废”。通过姓名的重新命名,两个人不再是被剥夺了尊严的“无名之辈”,而是堂堂正正的人。
四、残疾人社会化途径的呈现与反思
如果说《推拿》侧重于描写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无名之辈》着力于展示人内心世界的困扰与挣扎,《宝贝儿》则致力于表现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的矛盾。也正因此,不同于《推拿》基调中散发着平淡的温馨,也不同于《无名之辈》泪水中透露出欢笑与感动,《宝贝儿》是在严肃地讲述残疾人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问题。电影由两条故事线交错构成:一条讲述缺陷弃婴江萌由于年满十八岁,在福利院合约的约束下即将与无依无靠的养母分离;另一条讲述江萌在医院做护工时偶遇与自己患有同样病症——无肛症的婴儿,在发觉婴儿父亲有对其放弃治疗的意图后,毅然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婴儿。
表面来看,江萌遭遇的最大危机是由于以不合法的方式拯救病婴从而可能面临诱拐儿童罪的制裁,而实际上她遭遇的困难远不止于此。首先是身体上的“隐性残疾”,由于做过心脏手术,她不能承担过于劳累的工作。找工作时,江萌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检查过了,我是健康的”,即便如此,用人单位仍对其存有顾虑而不愿雇用,中介也会毫不留情地指出“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在求职时遇到瓶颈,健全人也会有同样的遭遇,他们会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而被拒绝,例如学历低,再如技能不足。然而江萌被拒绝的首要理由是身体健康,对其残疾人身份的歧视显而易见。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导向的电影,《宝贝儿》将叙事重点聚焦在残疾人的社会生活这一角度,江萌始终在努力摆脱残疾人的标签,无论是反复强调“我是健康的”,还是拒绝福利院的各种帮助,抑或是不愿意办理残疾证。于她而言,或许正是因为残疾而被亲生父母抛弃带来的创伤令她如此抗拒残疾的标签。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认同残疾身份可能并不会给江萌带来便利,与之相反,江萌再也无法证明自己的健康。社会对残疾人群体是同情的却不是宽容的,所以体检合格的江萌依然会被“担心身体带来麻烦”。江萌的聋哑人朋友也表示:“我有残疾证,单位仍然不要,残疾证没用。”2007年国务院发布的《残疾人就业条例》第一章第四条明确指出“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然而歧视的标准为何、若自感遭遇歧视后该如何维权等问题都未有详细规定。这也使得这一规则缺少威慑力与执行力。在挽救病婴的过程中江萌多次向小孩的父亲徐先生说道“你的小孩是可以治好的”,但就像她自己的亲身经历一样,身体的病症可以治好,但“患病”(或言残疾)的烙印会始终伴随余生。江萌对拯救一个非亲非故的病婴的执着,可以理解为同病相怜的情感羁绊,也可以认为是对社会的发问——残疾人有没有活下去的权利?残疾人能不能像健全人一样活着?在电影里,残疾是一道无形的围栏。一旦被划入残疾的范围,便成了社会的“他者”,再也无法享受普通人的人生。
《宝贝儿》中也有关于爱情的叙述,江萌的聋哑人朋友小军对她抱有好感,多次向她表达想要两个人一起过日子的想法。可是在传达这个想法的时候,小军的出发点不是爱,而是两个人一起生活可以“省一半的钱”。同样,江萌拒绝小军的理由也不是情,而是她不能生育,二人由于残疾亦无法达到领养小孩的标准,这将导致未来二人老无所依,而被送往养老院度过晚年。可就像江萌说的:“有家谁去养老院啊?”社会的规则在无声地排斥着残疾人群体,令他们丧失拥有一个普通家庭的权利。在《推拿》款款讲述着残疾人也需要爱情,也能够拥有爱情的时候,《宝贝儿》尖锐地指出了残疾人在面对爱情时的尴尬处境,他们不得不将功利性的目的作为任何抉择的首选,爱情就在各种压力下变得暗淡无光。
江萌面临的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由于年满十八岁,福利院与其寄养家庭签署的合约生效,江萌必须离开寄养家庭回到福利院,否则便不能得到相应的福利补贴。其养母既无后代又是丧偶状态,同时经济状况堪忧(低保户),因此必须被送往养老院度过余生。若江萌能够继续留在寄养家庭赡养养母,既顺遂母女二人心意,养母亦老有所养不必被送往养老院,然而在规则面前这种设想无法实现。电影揭示了现行的福利院孤儿寄养政策的缺陷。寄养制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待领养的孤儿数量与有领养意愿和能力的家庭数量相差悬殊。况且弃婴被遗弃的主要原因是疾病或残疾,这更降低了他们被领养家庭接纳的可能。在这种条件下,寄养制度诞生了。寄养关系在更大程度上像是雇佣关系。政府出钱,寄养家庭代养弃婴,成年以后脱离寄养家庭,不产生任何经济纠纷。在领养家庭“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这一制度是无奈下的最优选择。但也正因如此,寄养家庭的孩子失去了拥有“家”的权利。无论他们与寄养家庭的感情多么深厚,“家”在法律层面都与他们无半点瓜葛。
对于江萌来说,她的世界不存在沙宗琪推拿中心那样可以寄身的乌托邦,也没有一个“胡广生”为她编制美好的未来图景,她所面临的是作为一个身有残疾的成年人必须面对的社会现实:她必须就业,自食其力,但频频遭遇就业歧视,在与寄养家庭的关系上深陷情感、伦理与法律的悖论与痛苦,甚至无法建立一段基于情感的爱情。《宝贝儿》以残疾人江萌个人的生活遭遇,客观地呈现出当今社会残疾人得到的社会保障以及仍然面临的种种问题,从而为观众理解残疾人的生存境遇提供了一个现实视角。
五、残疾人叙事的多样性与互文性
三部电影在表现残疾人的生活境遇和内心感受时采用了三种不同的方式。《推拿》通过对情感故事的描写,展示出残疾人情感生活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一般性是指与健全人相似,都拥有追求爱情的权利,拥有相似的情欲、深情和温柔,体现了人性的共同性。比如小马对于嫂子难以遏制的肉体欲望,金嫣对爱情的执着以及王大夫和小孔的相依相伴。同时他们的情感经历也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仔细审视这种特殊性会发现,根本原因往往并非与其生理的残疾有关,而根植于社会环境和文化偏见,比如沙复明相亲时能够用自己的洋溢才华和细腻的情感感染女方,却无法满足丈母娘择婿的标准;同样,王大夫和小孔真心相爱,却因家庭的阻力只能选择“私奔”这种模式。
相比之下,《无名之辈》并没有那么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叙事线索,电影主要是以模拟舞台剧的形式呈现残疾人的内心挣扎,具有一定的表现主义色彩。影片通过描写马嘉祺内心活动的变迁,呈现出残疾人内心的丰富性,其中既有因肢体残疾而导致的失落与绝望,也有因遭遇爱情后萌生的欣喜和期待。
与前两部作品侧重于关注残疾人的情感生活和内心活动不同,《宝贝儿》关于残疾人生活和心理的呈现主要建立在人与社会的碰撞之中。在电影中,主人公江萌身上交错着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呈现对于探讨当前社会保障体系的功能与局限具有一定的价值。比如江萌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受益者,因寄养制度而得以接受教育、获得亲情,同时也因法不容情而面临与养母分离的残酷事实。再如残疾人证明既是保证残疾人在社会中得到保障的福利,同时也可能成为他们融入社会的阻碍。从这个角度而言,《宝贝儿》在表现了残疾人享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也对这种体系展开了追问与反思。
尽管三部影片以不同的艺术手法和不同关注点来反映残疾人的生活面貌,但三部作品却存在一个明显的互文性,那就是关于残疾人尊严的表达。
毕飞宇在《〈推拿〉的一点题外话》(10)毕飞宇.《推拿》的一点题外话[J].当代作家评论,2009(02).中提到,他儿时生活的苏北乡村存在大量的残疾人,残疾人在与健全人相处过程中的自我作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让他在之后的日子里意识到“尊严的问题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在中国,它几乎是一个社会问题”(11)同上。。所以,在创作《推拿》时,毕飞宇有意识地将关于“尊严”的思考与认知融入作品之中。在改编的过程中,娄烨将尊严意识重点呈现在都红和王大夫两人身上。都红的手受伤后,沙宗琪推拿中心的众人为她筹集了善款,沙复明也替她安排好了“后路”,然而这些举动无疑都刺痛了都红的自尊心,正如原著中所说的,都红“不能答应自己变成一只人见人怜的可怜虫。她只想活着。她不想感激”(12)毕飞宇.推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266.。所以她不能允许自己成为被可怜、被救济的对象,而终日活在感激的负担中,更不能接受沙复明对她的爱意演变成两人的“交易”,于是都红从推拿中心毅然“出走”。同样,王大夫将尊严视若珍宝,尊严是他生活的支撑,是他生存的证明。就像他说的,“讨饭,我也会。但我不能。我们也有一张脸,我们要这张脸,我们还爱这张脸,我们得拿自己当人”。所以在家中以自残逼退了讨债的人后,他哭着向父母说“对不起,我不是这样的”。表面来看,王大夫受伤的是躯体,但本质上真正刺痛他的是他放弃了自己的尊严。
在《无名之辈》中,尊严这一话题是情节推进的重要因素。因为尊严,马嘉祺置身生与死的抉择,也因为尊严,马嘉祺和胡广生跨越了残疾人与健全人的鸿沟,彼此惺惺相惜,互相扶持。这部电影所要表达的核心主题就是小人物也有自己的尊严。对于肢体存在残疾的马嘉祺,尊严更是其安身立命的底线,是其还能够活下去的“救命稻草”。可以说,马嘉祺的泼辣、暴戾以及歇斯底里无一不是对自己尊严的誓死捍卫。
相较于前两部电影,《宝贝儿》中的尊严一题较为隐晦,但同时亦不失深刻。江萌反复强调“我是健康的”,倔强地与残疾身份划清界限的内在原因与尊严相关。社会生活缺乏对残疾人群体的理解与尊重,导致偏见与歧视无法消除,残疾人难以获得作为独立人格应有的尊严与价值。《宝贝儿》所反映的正是如此:“残疾人群体的特殊性不仅表现在其生理性弱势上,还表现为由生理性弱势而带来的社会性弱势。”(13)葛忠明,臧渝梨.中国残疾人研究:第一辑[A].林聚任,李秀杰.社会分层视野下的中国残疾人群[C].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53.残疾不仅是残疾人自身所面临的客观事实,更是残疾人在社会化进程中被赋予的“标签”。
由此可以看出,关于尊严的叙事是近年来残疾人题材电影中具有互文意义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残疾人形象正逐渐摆脱曾经作品中的符号属性,比如身残志坚的励志楷模,而逐渐成为有血有肉的道德与情感主体。
六、结 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推拿》《无名之辈》《宝贝儿》为研究对象,分别从人与他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三个方面分析了这三部电影在残疾人叙事上的特点和价值以及它们存有的差异性和互文性。《推拿》通过对残疾人生活和欲望的描写,还原了残疾人丰富的情感世界;《无名之辈》用表现主义的手法探索了残疾人的心灵困境;《宝贝儿》则试图以客观视角呈现残疾人在社会中的遭遇,以此反思当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三部作品在残疾人叙事中虽各有侧重却共同指向了残疾人的尊严问题和内心世界,从而改变了此前中国电影中残疾人形象的“他者”属性。本文通过探究这些作品在叙事方面的“内转”试图说明近年来中国电影关于残疾人的描写更倾向于表现其复杂的情感诉求和心灵世界,是对残疾人群体作为人的本体身份的认同。
在古今中外的艺术创作中,残疾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存在。无论是以自身的残缺衬托艺术的完美,还是赋予残疾以邪恶的隐喻;无论是将残疾作为一种道德捆绑的筹码建构意识形态,还是用某种缺陷刺激人类的情感体验,残疾人形象总是以“他者”的身份存在于文学艺术的想象之中,承担某种特定的功能,其生存境遇和内心体验的丰富性则因此被遮蔽。从这个意义来看,本文所列举的三部电影作品,尝试改变影片的叙事视角,力求还原真实、丰富的残疾人艺术形象,努力挖掘残疾人的内心世界和主体维度,其艺术进展与社会价值都值得我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