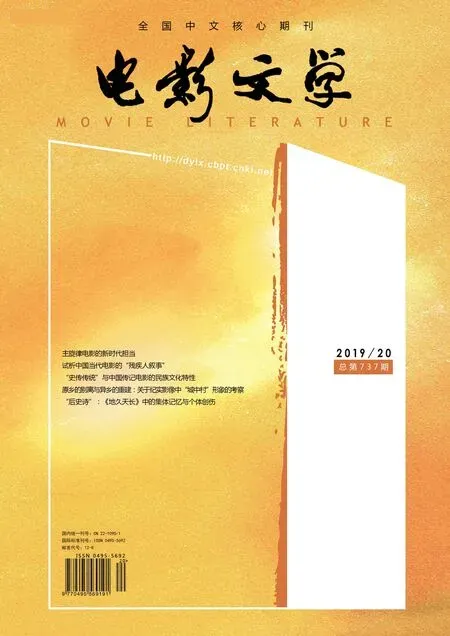现代性视野下青春影像的文化主题研究
张爱坤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一、青春与青春问题
日常语用习惯下,与“青春”一词经常混用的是“青春期”和“青少年”,相比“青春”一词的感性化特征,“青春期”和“青少年”具备更明晰的指涉对象和更为理性的现实依据,前者指代社会个体生命历程的一个特定阶段,后者指代社会群体当中的一个特定类别,由此可见,“青春”“青春期”和“青少年”这三个经常混用、替换的词汇实际上指向、含涉着不同的对象,它们相互交织、各有侧重,共同表征了一个庞大又复杂的群体。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青春”一词的含糊也预示着“青春问题”的复杂性,就个体来讲,“青春期”是每个人生命当中必定经历的阶段,青春问题之于个体带有某种必然性;就整个社会来讲,“青少年”群体的出现具有代际性,每个时期总会有每个时期的“青少年”,也就会存在每个时期的“青春问题”。也就是说,“青春问题”之于整个社会带有继生性,是每个时期每个社会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然而,之于漫长的人类社会,“青春”这一概念及其表征的生命阶段并非“与生俱来”,至少在人类文明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内,“青春”并不存在——彼时的人类生存环境恶劣,人类的寿命无法保障,大多数人死于二三十岁之间,在如此短暂的生命中,区分年龄段的意义不大。[1]更何况,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类的力量全部用于与自然力的抗争之中,当代社会面临的青少年问题在那时尚未突显,也即是说:人类文明早期,非但不存在当今世界复杂的青少年问题,甚至根本不存在青少年和青春的概念。作为当今世界面临的难题,“青春”问题的突显大抵肇始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频繁爆发的局部战争将无数鲜活的青春生命化为齑粉,青春生命的损毁成为人类文明困境的某种暗示和征兆。同时,青少年群体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和文化力量开始频繁登上世界舞台,他们立志于创造全新的文化格局,又频繁破坏现存的社会秩序。在这一进一退之间,青春能量演化为改造世界的主要力量,并在20世纪60年代时抵达顶峰。
在斯梅尔瑟看来,当今世界遭遇的青少年问题归根结底在于现代性和全球化对生命个体成长的挑战——“经济的变化,包括贫穷和富裕,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变化;家庭的变化,以文化、传统或地域为基础的宗族关系或血缘关系逐渐缩减为由父母和直系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制度的变化,包括作为社会设置之一的学校,在很大程度上把儿童和青年群体与社会分离开来”。[2]之于整个人类,现代性和全球化更像是席卷世界的浪潮,社会个体被裹挟其中,无从规避、无法豁免,在遭受现代性冲刷的人群中,青春个体又具有某种特殊性:一方面,青春个体处于生理和心理上的特殊阶段,心理上的困惑与迷茫被身体上的微妙变化放大,转化为青春阶段必须面临和经受的生命历练;另一方面,个人资本积累的客观规律又决定了青春阶段的社会个体并没有可以借用的物质资源,加之经济、家庭、制度的三重变化,所有这些共同导致了当代青少年在面对现代性冲刷时成为整个社会最脆弱、最特殊的群体,甚至可以说,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历程中,青少年群体从未面临如此巨大的裂变。
随着“青少年”和“青春”问题的突显,20世纪中期以来,如何教育、规训和引导青少年就成了世界范围亟待解决的难题。按照杜威的说法:“既然特定时代的青少年在稍后的时日中将组成那个时代的社会,那么,后者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在早一时期给予青少年行为的指导。”[3]也即是说,“青少年”和“青春”问题不仅是代际和群体问题,更是关乎民族、国家甚至全人类命运的核心议题。在这种情势下,艺术文本该如何以符号化和美学化的方式对青春问题加以呈现、问诊和纾解就成为文艺作品义不容辞的文化责任和美学义务。
二、偏倚的青春镜像
无论何时,审美文化与社会现实之间总是存在互相表里的关系,当今世界面临的青春问题同样被电影艺术所关注,并衍生出青春影像的三大类型:第一类聚焦于青春生命的恋爱经历,通过男女主人公相识、相恋、相知、相许的过程完成叙事,比较典型的如《歌舞青春》系列、《我的少女时代》《四月物语》等。此类文本中,青春生命被装裱为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是“希望”“梦想”“浪漫”“热情”“美好”等诸多正面、积极和肯定性价值的载体。然而,凡是经历过青春阶段的人们都应该明了,青春经验并不美好——“在所谓‘青春’是‘人生最美好的季节’这个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观念中,包含着某种令人质疑的成分,那就是一种自我欺骗的味道”。[4]之于过来人,站在成人角度远望,青春生命的困惑、迷茫、彷徨或许珍贵,但之于青春的当事人,正在经历的青春因为没有可以比对的生命经历而变得如此艰难,青春生命的小小困顿或许就是不可逾越的坎坷,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类文本表面上展现的是正在发生的青春故事,但影片“远望”式的符号编排已然在无形中置换了青春的呈现角度,青春的“神性”被刻意放大,失却了以青春视角呈现青春体验的可能。
第二类有关青春的影像聚焦于青春生命的成长经历,较之第一类,这类文本在类型学上更具有典型意义,甚至有人以“成长片”为之命名——“故事中心有关一位或几位青少年突然面临的、将改变其生活的经历、考验和磨难。曾经是天真、幼稚或发育期前的青少年人物现在由于这一经历而长大了、变得更懂事了”。[5]在叙述上,此类文本侧重于主人公(往往是十几岁的少年)“成长”中遭逢的变数,在情节编排上,主人公遭遇的事件成为节点,通过节点前后主人公人生态度的转变达到叙事价值的翻转,以此完成对传统伦理价值(亲情、友情)的诠释,比较典型的如《纸月亮》《伴我同行》《回到未来》《中央车站》《亲情永在》等。应该说,这一类型的青春文本直接秉承了“成长教育小说”的叙述策略和主题思想,情节编排上的节点成为青少年由“叛逆”走向“顺从”的动因,在与成人和解的过程中,青少年的“成长”本身也就是对成人世界和成人价值的归顺。这样来看,这类文本表现的与其说是青少年的“回归”,不如说是成人世界对自我价值体系的再次确认,青少年的僭越与离心运动虽然与生俱来,但最终不会破坏现存世界,也不会裂解成人中心的价值体系,在精巧的情节安排下,成人世界想象性地完成了对叛逆青春的驯服与教化,并再次强化了成人价值体系的高度权威。
最后一类有关青春的影像聚焦于青春阶段的“残酷”,此类文本将青春生命的痛苦与煎熬作为叙述中心,重点展现青春生命的躁动与挣扎,这一类型中,青春充满苦难,青春激情或因无处宣泄转化为毁灭他人、毁灭自身的不安定因素,或因缺乏理性引导转化为自我放逐的诱因,于是,电影文本也就成为个体化青春“炼狱”的美学化表征。如《感官世界》《踏空的青春》《死亡诗社》《大象》等,国内导演同样不乏对此类题材的关注,比较典型的是“第六代”电影人的早期创作,如《小武》《青红》《冬春的日子》《北京杂种》等。与上文提到的第一类青春影像相比,这一类文本中的青春不再澄澈与飞扬,相反,青春是如此多灾多难,如果说第一类青春影像着力渲染了青春的“美好”,那么这一类文本则刻意放大青春的“苦难”,并且将青春的“苦难”呈现为宿命般的存在,青春生命在“激情”中遭遇“苦难”,青少年演变为成人世界的威胁,在破坏成人世界的过程中,青春生命既无力建构全新世界,又无力拯救自身,在二者的裂隙处,青春生命最终走向损毁。
通观上述,青春影像在对青春生命予以呈现的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走向了某种偏倚,从根本上说,这种叙述的偏倚来自影像实践过程中创作者高度的成人化视角和当下社会现实中绝对的成人中心主义,青春影像或放大青春的“美好”,或夸大青春的“苦难”,实际上,之于绝大多数青春当事人,切身体悟到的青春体验与影像世界中的青春呈现往往大相径庭,作为由稚嫩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青春”既特殊又普通,说其特殊,是因为青春阶段确实面临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变化,青少年面临的苦闷与迷茫的概率确实高于儿童和成年人,能否理性、积极地应对这种变化往往决定了生命个体一生的走向;说其普通,是因为之于生命个体的一生,青春阶段和其他生命阶段从本质上并无相异之处,青春阶段面临的“成长”是每个人一生的议题,因为“成长”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诚然,电影艺术天生附带了“造梦”功能,但与“造梦”功能同等重要的,是电影艺术的“纪实”功能,这里的“纪实”不应该单单理解为纪录片的电影形态,更应理解为一种平视青春、平视人生的叙述出发点。基于此,本文在纷繁复杂的影像世界找寻到一系列平视青春、直面青春的影像文本,并梳理出青春影像的系列文化主题层面,借此管窥青春生命的切身性体验和本质性困顿。
三、现代性视野下青春影像的文化主题
(一)欲望主题
如果概括青春阶段的“关键词”,处于首要位置的当属“欲望”,之于当事者,青春阶段遭受的苦闷与困顿最根本的几乎全部来自青春期的“欲望”。青春期是“男女生殖器官发育成熟的时期”[6],荷尔蒙分泌的变化不仅会促进身体发育和第二性征的出现,更会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影响其情绪变化。这种生理和心理的变化极大提高了青少年的欲望需求,他们迫切需要抓取一些可供使用的物质、精神材料来自证“成熟”,可是现代社会高度体制化的制度与规则又决定了这一阶段的青少年并没有富余的资本可供支配,他们是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无产者”,身处其中,青少年只能无奈地面对欲望与现实的分裂。
在美学转化的过程中,青春影像敏锐地捕获到了青春欲望最根本的主题:爱(性)的欲望。归根到底,青春影像处理的不过是人与人、身体与身体之间的审美关系,而在所有身体关系当中,性关系无疑是其中最基础、最本质的关系。所以,福克斯在《情色艺术史》中直言不讳地说:“爱欲充满了,或者形成了男女之间的全部关系。不同性别的两个正常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一般地说,都可能具有爱欲的依据。”[7]推及青春影像,电影文本无论选择直白的还是隐晦的表意方式,只要触及不同性别的亲密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归根到底都能被解读出爱欲的意味。更何况,在对欲望进行展现上,电影艺术有着其他艺术门类不具有的媒介优势,因为电影的声光语言可以将“欲望”直观化、视觉化——“人们很难达到灵与肉的完美满足,却能在电影中驰骋性的幻想——七情六欲必须在心理或肉体上与一个伙伴或周围的环境联系起来才不至于紊乱”。[8]在影像中的青春世界,青少年爱的欲望往往被处理为直接的性冲动,实际上,这种处理策略也正好服膺了青春阶段生理成熟、心理未成熟的身体基础——青少年有了体验“性”之愉悦的生理基础,却没有处理“性”之复杂性的心理配置,在欲望与现实断裂的外部环境下,青少年还必须面对生理和心理的再次断裂。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中,懵懂少年雷纳多与美丽少妇玛莲娜相遇,从此,雷纳多陷入对玛莲娜狂热的爱恋与追逐当中。在美学策略上,电影将主人公无法压抑的欲望冲动转化为直观的镜头语言。少年雷纳多一无所有,唯一可以支配的物质资本就是一辆自行车,于是,这辆自行车就成为主人公唯一可以借用的欲望工具,主人公骑着它穿行于大街小巷,摇晃颠簸的自行车成为主人公躁动内心的隐喻,声声入耳的链条声音与嘎嘎作响的床板声构成了某种互文,雷纳多追随、跟踪、偷内衣、写情书,沉溺于白天黑夜虚幻的欲望世界中不能自拔,甚至在欲望觉醒之后,主人公对玛莲娜的窥探与审视也完全情色化、肉欲化——特写镜头对玛莲娜的丝袜、胸部进行了反复强调。终于,雷纳多所患上的“欲望”之病被父亲发现,父亲将儿子带到了妓院……然而对比整部电影铺张宣扬式的虚幻性欲描写,妓院中现实层面的性爱场景却被导演处理得极为模糊和简略,实际上,这正隐含了这部电影对于青春欲望的总体评判——欲望之美与欲望之魅就在于其虚幻性本质,而欲望的现实化就是对青春生命一次根本性的“祛魅”过程。正如美艳的玛莲娜最终还是被俗世中人击垮,雷纳多作为见证者,目睹了曾经不可触及的玛莲娜被人拖到街头、遭人殴打、剪去头发……欲望对象被现实毁坏了,雷纳多的欲望之火也随之熄灭了。
《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成人世界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终止了马小军们的正常学校教育,也将成年人从马小军们的世界中排除,而大院里的青少年因为都是未成年人,所以也没有参与“革命”的权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小军与大院里的青少年整日游荡、无所事事,马小军唯一的爱好就是开锁,趁着白天大部分人家中没人的时候,马小军打开一扇又一扇的大门,他的快乐也仅仅停留在用自己的钥匙打开别人家锁的瞬间,顶多偷吃顿饺子,再无逾越半步,直到无意间溜进了米兰的房间,看到了米兰那张泳装照片……实际上,马小军爱好“开锁”的细节设置充满了被解读的空间,“钥匙”与“锁”更是一组蕴意丰富的意象符码。在没有看到米兰的照片之前,马小军打开过无数家的门锁,直到打开米兰的房间,马小军的青春欲望才因异性的闯入而被唤醒。从那以后,马小军对米兰展开了疯狂的追逐,可是米兰只把他当作小孩,她更喜欢和刘忆苦说说笑笑。相比马小军,刘忆苦更为成熟,这种成熟既包括身体的发育,还包括“打起架来手特黑”,更体现在刘忆苦当过兵,直接参与过成人世界的活动。之于马小军们,刘忆苦是浓烈男性荷尔蒙和成人权威的集合体,刘忆苦的这些特质最终也成为他统领这个群体的权力资本,并且,这些权力资本是未成年的马小军们无论如何都无法触逆的。然而马小军的青春欲望已被唤醒,他既无法容忍刘忆苦对米兰的独占,也无法容忍米兰对自己俯视的态度。于是,他爬上高高的烟囱,纵身跳下,在想象中挑战了刘忆苦的成人权威,虽然自己弄得灰头土脸;他扑向米兰,希望借此证明自己的男性荷尔蒙,然而这场粗暴与笨拙的征服实践最终以闹剧一般的失败收场。在影片的情节策略下,无论是马小军的灰头土脸还是“强暴”未遂都证明了青春欲望根本上的无法实践,青春当事人无力缝合欲望与现实的裂隙。作为青春故事的结尾,马小军最终被友情和爱情所放逐——“从此我和米兰彻底掰了,大家也把我孤立起来”,他漂泊在泳池上,正如自己漂浮游移的欲望和幻想,戛然之间,青春结束了……
(二)流浪主题
之于青春个体,青春包含着多重含义,如果说青春在本质上意味着人生的转型,那么这种转型不仅包括精神层面,还包括物质层面——青春个体要依靠过去习得的生存技能在现代社会立足、谋生,以此满足自身和家庭的物质需求,于是,能否适应现代社会的制度、规则,能否在现代社会找寻到一个收获物质回报的职业位置就成为每一个青春个体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可是现代社会具有高度规则化、制度化、体制化的特征,它建构了一套严密的社会法则和职业标尺,并以此筛选和剔除冗余个体。无疑,这样的框架设定会对社会个体造成巨大的冲击,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刚刚步入社会的青春个体。一方面,青春群体的自我意识极强,自主性、个人性的锋芒初盛,甫一进入社会,未经打磨的个人棱角势必难与社会法则相融合,可是制度和规则在本质上具有刚性的特征,二者相遇,处于被动一端的必定是青春个体——要么调整自身,要么另寻他处。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个人的财富积累总是需要占有一定的资源——物质材料、人脉交际、技术经验、知识储备等都是物质财富提升的前提,而上述这些资源的储备势必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对于青春群体来说,尽快寻觅和占有资源是生存发展的必需。然而时间不可逾越,青春个体只能不断游移,以求用自身的空间成本来置换时间成本——机动性越强,生存发展的空间越大。如此一来,现代社会体制下青春个体的游移与流浪就具有了某种必然性。
《风柜来的人》中,主人公阿清和同伴们出生在一个宁静的小村庄——风柜,高中毕业之后,阿清和同伴们没有工作,等待征兵,在等待的过程中,他们百无聊赖,四处游荡;他们打架、斗殴、赌博,青春生命因为没有目的而被荒废。病弱的父亲、琐碎的家事、闭塞的村庄都是阿清挥之不去的负担,也是他们迫切需要逃离风柜的原因。在一次意外之后,阿清三人决定离开风柜,去往高雄。初到高雄,这里的一切都令人心驰神往,但他们很快发现,高雄并不是想象中的天堂,他们终究是“风柜来的人”,看似已逃离,但“风柜”早已成为刻印在他们身体上的印记,挥之不去,擦拭不掉,“美好”的城市并没有留给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他们是城市的过客。一个颇有意味的段落是三人相约看电影,可是到了三楼才发现那里空空如也。这时候三人来到未完工的墙面处,透过墙壁的缺口远望高雄,那里高楼林立、绿树成荫,可是这座陌生的城市终究是异己化的空间,他们无权拥有;真正属于他们的,不过是当下所处的、被高雄遗弃的断壁残垣,以及曾经迫切希望逃离的、远方的风柜。在这部电影中,青春个体的流浪将“风柜”和“高雄”两个空间串联起来,在两个空间的二元对立中,青春并没有留下浓墨重彩的故事,只有无意义的游荡,青春是如此难耐,却又如此漫长。
《世界》同样是一个关于异乡人的故事,舞蹈演员赵小桃是小城的“文艺青年”,无时无刻不在憧憬着外面的世界,于是她走出小城,来到都市。然而赵小桃切身体悟到的都市与曾经的想象大相径庭,这里没有风花雪月,有的只是生存的卑微,舞者的身份并没有带给她万人敬仰的场面,“文艺”的舞蹈只是她维系温饱的工具,她身着各式服装,混杂于表演的人群,倒映在光怪陆离的世界景观当中。她穿行于“巴黎”“印度”“曼哈顿”,可是这些终究只是缩微的景观,并不是想象当中真实的“世界”,她终究只是游荡于城市光晕暗影处的流浪者。在纷繁复杂的影像世界,表现异乡人、展示城市底层的文本并不少见,相比之下,《世界》的精妙之处在于导演寻获到的特殊故事空间——世界公园,这里是缩微的“世界”、是“世界”的景观,它嵌藏在现代都市,是现代人想象世界的工具。如果说现代都市是文化上标准的“景观社会”,那么世界公园就是景观当中的景观,之于赵小桃,告别家乡来到都市的初衷是感受一下外面的世界,却坠入这个“景观中的景观”,现代都市不仅容不下她,甚至剥夺了她切身感受一下真实都市的权利。在这个层面上,《世界》不仅展现了底层青年的生存困境,更为这种展现涂上了一层极其晦暗的底色。
(三)死亡主题
无论“欲望”抑或“流浪”,青春影像都以特异性的文化主题上演着青春个体的处身性体验,而在所有文化主题中,“死亡”具有尤其的特殊性:无论古今中外,人类总是希冀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摆脱和超越死亡,但囿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时至今日,人们尚且不能彻底征服死亡,科学只能帮助人们有限地推延死亡,无论主观意愿如何,死亡终究会如期到来——“一切存在都建筑在沙滩上,死亡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确定”。[9]对于每个人来说,死亡不可体验,可又是必然的体验,也因为此,死亡得以成为人类文明历史中最玄妙的未知世界——“死亡如同毫无复归之出发,毫无已知条件的问题,纯粹的问号”。[10]在这样的现实前提下,人们只能在艺术的想象世界中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死亡排演,希望借由艺术文本的符号编排在美学层面让世人熟悉死亡、认知死亡、征服死亡。在普泛性认知中,青春阶段总是充满活力与生机,青春的宝贵之处恰在于青春生命的未定型,因其未定型,所以蕴藏着无数可能。对于社会个体来说,青春阶段的磨砺、煎熬皆可视为否定性力量,而在所有的否定性力量中,最大、最强烈的否定无疑是死亡,因为它终止了青春生命,从根本上遏止了青春的诸多可能。从这个角度看,“死于青春”的影像故事正是将青春个体最美好的年华和生命最彻底的否定缝合在一起,以损毁的影像主体表达青春生命极限性的创伤体验,在青春生命的消融、腐蚀和淹没中,完成特殊的价值输出和伦理传递。
正如电影的片名一样,《青春残酷物语》将“残酷”作为青春故事的主题加以阐述,主人公真琴和阿清是恋人关系,这二人之间的爱情沉重又压抑,他们的生命似乎没有意义,恋爱非但不能带给他们精神上的欢愉,反而成为苦难的来源。两人也曾不甘于命运,也曾试图抵抗,但这种抵抗既没有原因,也没有结果,同两人没有意义的愤怒一样,两人的抵抗同样失去了意义。他们一无所有,有的只是年轻的肉体和生命,之于两人,身体不仅是欢愉的唯一来源,更是抵抗现存秩序的唯一工具,他们放纵、享乐,挥霍和透支着青春生命。终于,生命之火熄灭了,正如两人早已死去的理想。作为日本电影“新浪潮”的领军人物,大岛渚将镜头对准了社会风浪当中的年轻个体,并再次承担了“残酷青春”的代言人角色,总体来看,《青春残酷物语》浸透了悲观主义色彩,青春生命的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本质获得充分展现,在节制、紧凑的影像策略下,导演既哀叹于青春生命的陨落,又借由真琴和阿清之死间接传递出历史反思和社会批判的意识。
青春影像对于死亡主题的展现是多元化的,除了《青春残酷物语》这般直接展现肉身死亡的文本之外,还有大量文本聚焦于青春生命的象征性死亡。《孔雀》聚焦于一个五口之家,姐姐执拗刚烈,哥哥老实憨厚,弟弟忧郁敏感,在那座北方小城,姐弟三人谱写了三种不同的青春故事。姐姐一生活在梦想之中,为了成为伞兵,她甚至不惜献上自己年轻的身体,然而梦想终究没有实现,正如自行车后面拖拽的巨大降落伞被追赶而来的母亲扑在地上,她成为流水线上一名普通的女工,嫁人、生子,甚至那个蓝天下英俊帅气的伞兵也变成了路边自行车上大口吃包子的中年男子,姐姐心中最后留存的一点希望也破灭了。在菜摊上,她挑拣着西红柿失声痛哭,理想破灭殆尽,青春死去了。弟弟内向敏感,像家中无声无息的影子,他没有姐姐的刚烈执拗,也不能像哥哥一样承受父母的关爱,他无声无息地生活着、长大着。可偏偏是这个无声无息的“影子”触犯了父亲的底线,他被赶出了家门。再回来时,他带着一个离婚的女人和女人前夫的孩子,而且失去了一个手指。没人知道他在外这些年经历了什么,正如没人关心他的长大。他在家中年龄最小,却最先失去人生追求,他带孩子、买菜、做饭,混迹于老人群体……他正当年轻却在心态上老去——青春没有展开已经结束。和姐姐弟弟相比,哥哥身患残疾,但恰恰是这个身有残疾的人水到渠成地完成了青春的过渡。在父母的安排下,他与一个乡下的跛脚姑娘相亲,虽然相亲过程中发生了小小的冲突,但婚后两人勤勤恳恳,日子过得辛苦却踏实。与执拗的姐姐和敏感的弟弟相比,哥哥的青春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他大智若愚地完成了生命阶段的转换。实际上,哥哥对于青春的处置策略并非消极地逆来顺受,而是一种直面现实、坦诚真切的人生智慧——青春不必刻意,日常化亦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生命体验。
四、结 语
在爱因汉姆看来,电影艺术中“即便是最简单的视觉过程也不等于机械地摄录外在世界,而是根据简单、规则和平衡等对感觉器官起着支配作用的原则,创造性地组织感官材料”。[11]如果说偏倚的青春影像昭示着青春生命的极端化体验,属于审美世界通过符号现实收录、转化实存现实的文本策略,那么青春影像最终必须将美学转化过的符号现实投射回社会现实当中。从这个角度理解,上述青春影像就显得益发珍贵,因为他们在青春的“神性”与“魔性”之外开启了第三种青春面貌,青春摆脱了“异常”和“刻意”,开始以生活本来的样貌得到呈现和书写,并以生命本真的状态化解和引导了青春困顿,借此能够达到疗愈社会、救赎个体的文化功能。抑或,这种平视人生的叙述视角不仅是青春影像面临的美学症结,更是当下电影艺术在奇观化、视觉化道路上越走越远之时一个亟待开启的全新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