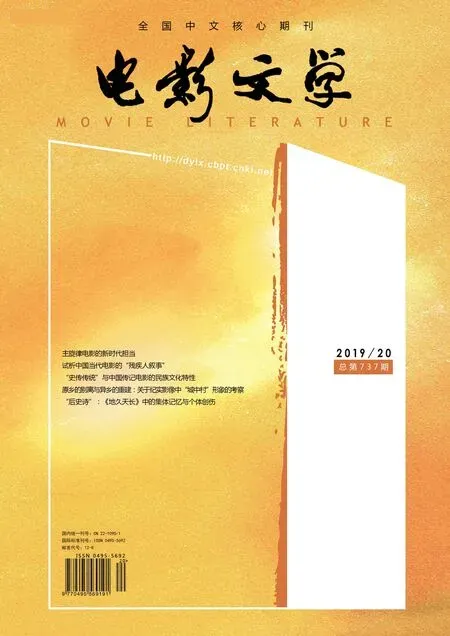浅析电影中“看镜头”的间离性及其艺术效果
滕宜娴
(西北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在戏剧里提出过“第四堵墙”的概念,即演员和观众同处于一个空间,为了不让剧情受到影响,演员要将观众视作无物,不能进行目光上的交流,也不能对观众的任何反馈做出反应,影响自己代入角色的情绪。“第四堵墙”像是一面单面玻璃,观众能看见演员,演员却看不见观众。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传统戏剧,使观看者能够融入剧情而产生情感共鸣,但德国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对传统的戏剧理论进行了创新,提出了“间离理论”,他批判了“亚里士多德”式戏剧的共鸣,认为传统的戏剧会剥夺观众的主观思考能力,应当提醒观众避免陷入艺术的幻觉之中。这种旁观者视觉机制的变革是戏剧的一次成功的探索,也是审美的一次尝试。在《等待老左》中,美国剧作家克利福德·奥德茨大胆地突破了传统戏剧的表现方式,剧中角色克莱顿在散布谣言,阻碍工人罢工时,他的弟弟在观众席揭露他的工贼身份,随后克莱顿不得不退出舞台,而他的退场路线是在观众席两旁的过道上。奥德茨使演员可以在观众席上表演,甚至可以直接面对观众发问,演员的表演区不再仅仅局限于舞台,而是包括观众席在内的整个剧场。在《等待老左》落幕时,常常有观众高呼“罢工”!克利福德·奥德茨虽然打破了“第四堵墙”造成了“间离效果”,却带给了观众更深层次的共鸣和认同,不仅引导了观众情绪,还使观众更能被故事内容所感染。
早期电影深受戏剧影响,梅里爱时期的电影,就是对舞台的银幕呈现,经过多年摸索才打破了原来戏剧式电影的模式,但戏剧的表演方式,仍然对电影产生影响。戏剧里观众和演员同处于一个现实空间,而在电影中有一条分界线,它将银幕的内外分成两个空间: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观众无法与演员产生任何物理性的交流。电影中演员的直视镜头的表现方式与戏剧里打破“第四堵墙”相似,都会影响到观众对人物角色的共鸣。因此,电影出现了一个禁忌,演员不能看向摄影机。电影银幕内的虚拟空间是由现实空间和各种镜头共同建构的,观众利用摄影机所在的位置产生进入虚拟空间的想象力,以旁观者的角度进行叙事,禁止演员看向镜头会使观众产生对虚拟空间迷幻的真实感。从空间上看,观众的位置与镜头位置一致,景随镜动,我们可以出现在任何场景,熟知每一个细节,从旁观者的视角对故事进行描述,这种致幻式的表演方式和运镜方式,会使观众逐渐融入银幕内的虚拟空间。比如当影片中的人物遭遇预料不及的突发车祸时,观众会对此意外做出下意识的身体反应,观众利用自己的想象力淡化了银幕内外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分界线。如果演员看向镜头,不仅会暴露摄像机的位置,也会使观众产生对剧情和演员的疏离感,并且强调这不是现实,只是演戏。但随着各种综艺、直播、真人秀的普及,这种演员直视镜头的“看镜头”也逐渐被观众接受,而结合不同的影片,“看镜头”所产生的效果也不再仅仅是“间离性”。以下便以“看镜头”如何作用于观众、人物角色及电影氛围进行浅析。
一、他者“面孔”的力量
电影作为第七种艺术,也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商品正在迅速发展,电影人将自己的思想以影像的形式呈现给观众,消费者从中获得心理和情感上的体验,因此作为消费体验者的观众常被认为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大部分叙事电影都是由遵循观众和叙事者习惯原则的视点镜头构成,根据观众的观影经验进行镜头的拍摄与组接,使叙述者的画面意思可以被理解,但“看镜头”是一种例外,它可能与上下镜头没有叙事或者视线上的联系。这种只表现“看”没有呼应的孤立镜头会使观众用自己的情感去理解电影。
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之一的马丁·海德格尔发现了存在对于存在者的优先地位,而法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发现了“他者”对存在者的压迫,并且超越了存在,他认为“自我与他人的伦理关联既先于自我与他人的存在关系,也先于自我与对象的存在关系”。[1]伦理学先哲学成为我与他者之间的联系,在列维纳斯看来面孔是绝对他者的面孔,是伦理可能性的条件,它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也不是表象的显现, 而是无限性的自我揭示。在我与他人“面对面”时就建立了一种伦理关系,并且他者的面孔与我形成一种“非暴力的关系”,没有言语,却时刻强调着我的责任和等待着我的回应。
法国著名导演弗朗科依斯·特吕弗的《四百击》,是部具有特吕弗个人特色的半自传体作品,他用朴实无华的情感使观众重新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引发了当时社会对孩子内心世界和教育方式的讨论与关注。影片最后有一个长达一分二十秒的经典长镜头,安托万在一场球赛中从少管所逃离,一路不停地奔跑到海边,回过身来直视镜头,他那时的面孔如蒙娜丽莎的微笑一般,意味深长让人捉摸不透。作为艺术创作,这样余味无穷的结尾将带给观众比起言传更为深刻的印象。此时安托万的面孔所展现出来的情感要更丰富于语言,他面对着观众,“他者以一种原初的、不可还原的关系呈现在我的面前”。[2]此刻他的迷茫似乎与观众有着某种关系,仿佛理解他的表情与内心情感变成了观众的责任。
美国导演亚历山大·佩恩指导的黑色喜剧《校园风云》中,吉米阻碍翠西赢得校园选举的事情曝光。在校长质问之后,吉米、翠西、保罗等人的面孔相继出现在银幕上,他们直视镜头没有说话,此时的面孔是人物角色内在心理的浓缩与外在显现,观众可以从面孔中解读出他们的情绪,比起通过台词或者演员的肢体表演,“看镜头”的使用使观众不再处于被动地位,而是主动调动观众结合自身经验以及情感对由影像呈现的信息进行解读。
二、偷窥者身份的转变
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电影院放映的《火车进站》,火车直冲观众而来的影像,在当时不仅给观众造成了恐慌而且让他们感受到了电影艺术的魅力。电影容纳了绘画、文学、舞蹈、戏剧等多种艺术,但又与依赖文字的文学、依赖颜料的绘画或者依赖舞台的戏剧不同,它结合了现代科技和各种传统艺术,成为有着自身独特性的艺术综合体,电影银幕所呈现的活动画面变成了我们理解世界的途径之一,并且从银幕上观看他人生活的方式还满足了人们的窥视欲。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好奇心和窥视欲本就是一种性本能,而电影就是“偷窥的产物”。电影院为偷窥创造了条件,明亮的银幕就像黑暗空间里透出微光的洞孔,它为每一个身为偷窥者的观众提供了一个可以窥视到他人生活的场所。电影作为艺术,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它是人们真实生活的缩影。电影中的复杂现象、人物形象等都为观众提供了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的参考标准,在心理学上“人的生活由于拥有了秘密而不可思议地扩大了”,因此秘密也就成为个人的精神财产。正是因为秘密是排他的,是被隐蔽的,因此暴露秘密才有吸引力、有价值,才会使人想知道。一方面是当事人的不懈努力加以隐藏、坚守,另一方面是追根刨底的欲望,双方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是秘密的魅力越大,秘密的暴露也就越有吸引力。由于秘密是被坚守的,揭发秘密的行为就成了一种挑战,保密与揭秘双方必然构成尖锐的对立。人们很难摆脱探究秘密的诱惑,但是又不愿为此与他人针尖对麦芒,无奈之下只能寻找一种折中的路线。这就是人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有窥视癖的原因。当然为了达到窥视的目的,窥视者需要承受内心巨大的压力,在实际行动过程中也会有许多困难与不便。欲窥不能,则更易成癖”。[3]电影创作者常利用人们的这种本能,使观众通过摄影机“窥视”到他人的生活,满足了自身的好奇感和偷窥欲,并且不会受到道德的谴责。
电影不仅满足了受众的窥视欲,而且给了大众可以接触到他人秘密的途径,带给观众一种以上帝视角俯视他人的优越感。但是如果演员望向镜头,就相当于看向了银幕前的观众,这无疑暴露了摄影机的位置,同时也让偷窥者无处遁形。观众从电影剧情中脱离出来,从情感催眠中清醒,明白自己“局外人”的身份,这种打破传统的后现代叙事手法,在美国上映的爱情喜剧片《安妮·霍尔》中多次使用。导演伍迪·艾伦让由本人扮演的男主角艾尔维可以回到自己的童年时光与老师争辩,也可以脱离剧情看向镜头与观众喋喋不休,这种无视“第四堵墙”的表现方式使观众既陌生又新奇。比如影片中艾尔维与安妮在排队时,身后的一位教授一直在卖弄自己的学问,忍受不了的艾尔维看向观众,开始了他的吐槽,而身后的教授也因此不满,与艾尔维一同直面镜头进行反驳,这种“看镜头”的方式让观众从偷窥者变成了片中评判对错的裁决者。
而在中国魔幻题材电影《画皮2》中,当雀儿向小唯表示自己感觉到了疼痛时,小唯的扮演者周迅通过“看镜头”的方式向她发出了七连问。根据剧情,小唯的质问对象应该是雀儿,但在此处导演采用了演员直视镜头的“看镜头”,让小唯面对的不再仅仅是雀儿,而是银幕前的观众。使原本作为偷窥者的观众也猛然间清醒,并从剧情中抽离,思考发问者的提问。这种“看镜头”的呈现方式产生了对原本剧情的间离感,却带给了观众新鲜且有趣的观影体验。
三、观众内心情绪的感染
“看镜头”从成为叙事性电影的禁忌而鲜有使用,到如今已取得某种程度的合法性,无论对人物角色的塑造还是对观众情绪的感染都有着独特的影响。在《安妮·霍尔》中,影片开头就是主人公艾尔维用一段“看镜头”的方式进行的自我独白,同样的独白方式在曹保平导演的《狗十三》中也有使用。如果将艾尔维和《狗十三》中的李玩进行对比,就能发现“看镜头”对于李玩和艾尔维这种“不起眼但内心情感丰富的人”的适用性。原本“看镜头的目光可以投向一个人物,投向摄影机透镜,投向观众,或者……根本没有目标”。[4]但在这样的叙述式独白中,他们的目光望向镜头,之后没有与之相承接的画面,只有观众在这种袒露心声的自语式“看镜头”中,成为他们心事的倾听者。作为看似唯一的听众,观众自然而然会加强对叙述者和他所述内容的关注。
在精神分析学中银幕与观众之间存在镜像性,剧中的画面、故事情节和人物情绪都会无意识地影响到自身的观点和情感,而观众自身也将投射到剧情之中。电影理论家巴拉兹·贝拉认为电影与文字和音乐的不同在于拥有“可见性”,“从电影的内容与形式上看,由于电影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它必须服从于现象论美学,因此只能从外部来描写主观活动的客观效果,或直接用象征的方式来暗示隐藏的内心活动和最微妙的心理状态”。[5]所以他将电影称作“可见的人类”,通过电影画面不仅可以展现人物的行为活动,也可以表现人物的内心情绪,而观众的内心世界也会因此受到感染。在电影《黄金时代》中,因其独特的叙事手法和另类的影像表达效果,在上映后引发了热议。影片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叙事视点相结合的方法,讲述了主人公萧红的人生。这种用主人公直视镜头的自述和其余人物的他述来使故事的时间和空间进行改变的方法,不仅掩饰了剧情的断裂感,而且使他们的叙述也对剧情有着推动作用。“看镜头”这种叙述方式,虽然使画面的呈现显得单一,但因为这种方式使观众仿佛成为唯一的倾听者,所以讲述者语气中所蕴含的情绪更能被观众所注意到,画面中人物的面孔和话语里所蕴含的情绪也更能精确地感受到。影片中他们讲述着自己所了解到的事情原委和他们印象中的萧红,这些叙述者仿佛也成为观众,一边跟随着故事的发展,一边讲述着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作为和观众一道的观影人,叙述者也好像同行的朋友一样被观众所接纳。因此在他们直视镜头向观众描述的那一刻起,他们的语气、情绪和面部表情也影响到了观众,为观众在观看之后的剧情前就奠定了情绪基础。例如影片中蒋锡金在讲述过程中谈到与萧红的最后一次见面时,言语里有着哽咽,他的伤心与难过的情绪或多或少影响到了观众,这种铺垫下来的情绪使观众在观看之后的影片情节时,更能激发出对萧红命运的同情与无奈。
电影叙事中插入人物直视镜头讲述自我所了解的事情原委的方式,在由巴特·雷顿执导的纪录片《冒充者》里也有使用,影片中的骗子以“看镜头”的方式讲述了他冒充一名16岁得克萨斯小男孩的经历,观众作为骗子的倾听者,因为他的讲述而受到感染,在之后的剧情发展中更能感受到骗子的惊慌、惊喜等情绪。导演用“看镜头”的方式不仅让观众了解和感受到了骗子的性格特点及当时的心情,也用这种方式让人们更加接近了故事中的谎言——人们往往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而不在乎真相。
在由弗兰克·达拉邦特执导的《肖申克的救赎》中,在主角安迪出逃以后,监狱长发现了藏在海报后的隧道,导演将监狱长安排在隧道口,镜头安置在隧道内,监狱长震惊地看向镜头,就相当于看向安迪用来逃脱的深不见底的隧道,通过“看镜头”观众仿佛化身为不在现场的安迪,站在隧道一端嘲笑着另一端道貌岸然的监狱长,此时此刻即使没有安迪的画面,观众的主观情绪也因为监狱长“看镜头”时难以置信的表情,更能感受到安迪在自我救赎和戏耍监狱长之后的喜悦之情。
四、电影气氛的营造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人们越来越依赖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而凭借虚拟的电子信息与他人进行交流沟通也成为常态。如今,有着百年历史的电影仍在不断创新与发展,出现了带有网络元素的新形式电影并不断满足着观众的猎奇心理。2018年以《网络迷踪》《解除好友》为代表的桌面电影获得了不错的口碑。同年一部没有大牌明星的韩国电影《昆池岩》,让低迷十年的亚洲恐怖片回春。这类“伪纪录片”式的电影采用如今年轻人最熟悉的数字网络和直播等方式来构建整个故事情节,而且这类电影多以恐怖、惊悚、悬疑为主,但它们不同于通过利用恐怖造型带来视觉冲击的传统恐怖片,而采用对氛围的渲染来刺激观众感官。
桌面电影多反映的是在互联网时代下的现代人面对虚拟世界时,内心深处所产生的恐惧。这些焦虑与恐惧使桌面电影可以营造出悬疑、恐怖的气氛。因为桌面电影视角的有限,所以它带有益智游戏的特点,需要通过搜索、解密来发现真相。《网络迷踪》中父亲大卫发现女儿玛戈失踪,他利用网络从杂乱无章的信息里,寻找女儿的踪迹,而观众也跟随着父亲的破译过程发现女儿隐藏的秘密。法国后现代主义主要代表人之一的吉尔·路易·勒内·德勒兹提出过“大脑即银幕”,即电脑屏幕上展现的就是影片人物的大脑世界,是“幻觉的现实”[6]。观众所看到的就是人物的思考历程。观众积极跟随父亲的思路,了解女儿压抑的本我和父女之间的隔阂,逐渐感受到人物的焦虑,而父亲在寻找女儿下落时与各色人物的视频通话更是加强了观众对角色情绪的体验感和沉浸感。由于桌面电影的镜头多为面部特写,使整部电影的叙事非常依赖演员的面部微表情。在《网络迷踪》中,女警官与父亲视频通话时,父亲认为他可以为寻找女儿出一份力,而女警官认为他因为个人情绪的原因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禁止他参与搜寻任务。两人“看镜头”的视频通话呈现在银幕上,这种人们熟悉的聊天方式,使观众产生出影像参与的错觉,父亲直视镜头歇斯底里的怒吼仿佛是对着观众自己,观众不仅可以感受到父亲的焦虑和愤怒,而且成为这种情绪的承受者,导演通过“看镜头”这种方式让观众可以更加深刻地体会和感受到一个父亲的内心波动,从而更能浸入影片所营造的氛围之中。
如今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新型的网络活动,因其低门槛和方便快捷的直播方式,给了大众展现自我的平台,所具有的移动性和泛娱乐性也使受众变得广泛。作为与时代一同发展的电影,以直播形式呈现的影片也应运而生。于是《昆池岩》这部因时代而生的,带有当下流行元素的恐怖片,勾起了观众的好奇心理。《昆池岩》开始部分是探险队的组织者以“看镜头”的方式,向观众说明了他将要组织一支队伍去昆池岩精神病院直播,这种类似现场直播式的阐述与之前放映的新闻和视频记录等,给观众营造出了一种真实感。电影采用线上线下的切换来进行叙事,线上是探险队员为观众进行直播秀,线下则是队长为了提高观看人数获取利益而与另外几个队员之间的预谋和策划,可随着一个个蓄意制造的恐怖事件逐渐脱离控制,剧情的发展也变得扑朔迷离,电影中镜头的衔接也开始变得混乱,就像希区柯克的电影中常用“主客观镜头无预兆切换,无交代性视点”[7]来营造一部恐怖电影的惊悚氛围。而且影片中在精神病院里直播的探险队员用“看镜头”的方式来描述自己的遭遇与心境,使观众不得不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直播者的每一个微表情和细微的动作。这种通过“看镜头”讲述自身所处环境和心情的方式,正是人们所熟悉的网络直播。网络直播所拥有的即时性和信息传输的零时距,使观众产生对电影中的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时间同步的错觉,对虚拟空间的界限开始模糊,到了剧情发展后期即使是开了上帝视角的观众也与进入精神病院的探险队一样,无法对有着临场性的直播进行预测。这种失控带来的恐惧更是激起了观众的沉浸感。正如希区柯克所认为的“把观众直接拉进那情境之中,而不是让他们从外部从一定距离来观望”[8]更能加剧恐怖氛围。
五、“反缝合”人物角色的塑造
“缝合”最初是由法国的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提出,用作无意识主体结构与捕捉无意识欲望。而电影中的“缝合是描述观众与电影之间的存在关系,即观众需要在电影中寻找一个自我的替代者,将自己的经验缝合进去来弥补自己不在场的缺失”。[9]为了把观众缝合进电影叙述的世界,电影创作者都会在叙事视点、叙事形式、人物塑造上避免打破“第四堵墙”。“当代电影理论的焦点之一是影片中看与被看的视觉结构关系。看与被看被视为构成电影话语陈述与接受的基本方式,经典电影叙事的秘密之一正在于它以叙境中的人物间的对视来遮蔽摄影机的存在,法国理论家让-皮埃尔-欧达尔将其称为电影的‘缝合体系’。电影缝合体系正是通过对切镜头结构成功地隐藏起叙事的痕迹,从而诱导观众对情境中的视点认同。”[10]因此在一部叙事的电影中,每个镜头的衔接,每一个人物的塑造都必须有着逻辑性,如果衔接唐突、人物出戏,无疑会对故事叙事的合理性产生影响,对演员与所扮演角色的统一性和观众的代入感构成冲击。通常电影中塑造的人物形象都基于银幕内的虚拟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无论角色是大公无私的英雄还是十恶不赦的反派,他们只处于所在影片构建出的想象世界,而处于现实空间中的观众只是他们行为处事的见证人。影片中塑造的人物与观众不同,他们只有自身所处的影片或者一个系列影片构建出的世界观,对于另外影片构建的世界就不得而知了,他们无法获知另一个世界中的人物,更不可能影响到他们。
由漫威打造的“非传统”英雄电影《死侍》无论在电影叙事还是人物塑造上都打破了传统电影的常规。主人公死侍与传统的超级英雄不同,他玩世不恭并且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他的这种精神不仅影响了人物的塑造,甚至影响到了传统电影的拍摄规则。死侍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活跃在光影世界的电影角色,作为打破“第四堵墙”的清醒者,死侍经常看向镜头,面向观众喊话,调侃其他的超级英雄,通过这种方式观众更加清楚地了解到死侍的性格特点,改变了以往观众对超级英雄的符号化、脸谱化的印象,塑造出了一个“话唠”、爱财的英雄,相比强调正义和大爱的其他英雄,死侍显得更真实和平凡。在影片中“看镜头”的使用不仅使观众从缝合的虚拟空间里抽离出来,造成间离感,而且这类打破“第四堵墙”的人物角色,还会让观众产生自身所处世界的被入侵感。死侍在影片中除了调侃金刚狼、X战警等观众熟知的英雄外,甚至在割腕逃脱时,也用“看镜头”的方式与观众谈论2010年在美国上映的电影《127小时》,死侍所拥有的世界观已不再局限于自己所处的电影构建出的世界,他像是一个突破了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人物,他身处银幕内却站在与观众相同的高度,正是这种入侵感让很多观众认为死侍是漫威宇宙最厉害的角色,甚至可以进入现实空间杀死如同上帝一般的创作者。
六、结 语
使用“看镜头”的影片,虽然通过演员直视镜头的方式,暴露了摄像机的位置,强调了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不同,造成了感知逻辑的破坏,但结合不同的影片类型、人物角色和剧情,却可以发挥其独特性。百年来电影经过不断的创新与突破,使“看镜头”所带有的价值和艺术效果,不再只是布莱希特所提出的让观众客观看待电影的间离感,而是可以成为引导、感染观众的观影情绪,塑造人物角色和营造电影氛围的手段之一,而随着电影创作理念的进步与更新,“看镜头”更为多样化的使用方式和所呈现出的艺术效果也将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