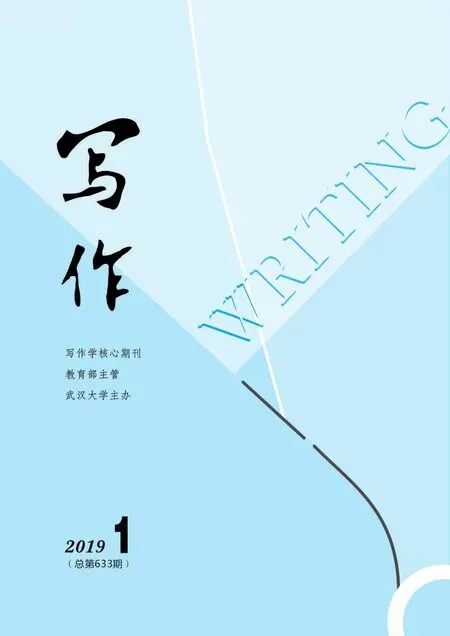“失控”的反讽:《在医院中》与丁玲的自我超克
田 淼
丁玲《在医院中》是分为2期创作的。小说于1941年春开始动笔①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0页。,经过数月创作后发生写作困难而停滞,终于在1941年11月15日,因编辑催稿很急,丁玲便用了一下午努力继续,“塞上”了一个结尾,以《在医院中时》初刊名发表在《谷雨》杂志上。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1942年6月10日,燎荧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对《在医院中时》的批评文章②如王增如所说,燎荧的这篇文章在《解放日报》的版面处理十分耐人寻味,即放在了和批判王实味《野百合花》同样的版面位置(第四版头条)。虽然丁玲和王实味被当成不同的错误来处理,但这样的版面位置对于丁玲来说,并不是好消息。。此后,丁玲写了一篇对《在医院中》的检讨和声明,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发表,检讨本身也处于草稿状态。这份草稿于2006年在李向东、王增如整理陈明旧物时发现,整理后刊载于2007年《书城》杂志第11期上③这份检讨题为《关于〈在医院中〉》,附加“草稿”,为的是突出其作为不完整文本的特征。。1942年8月转载于《战地文艺》时,改题为《在医院中》。
在“草稿”中,丁玲对创作过程进行了不无痛苦的反思。如果将这份检讨纳入解读视野,那么,不论从哪种角度来看,《在医院中》都将是一个具有高度症候性的文本。吴福辉在分析丁玲的检讨草稿时,将小说创作的失败比喻为“如同目的是要写《杜晚香》,却写成个《牛棚小品》”④吴福辉:《透过解说与检讨的表层——丁玲〈关于《在医院中》〉的阅读札记》,《汉语言文学研究》2011年第2期。,挪用李国华的术语,小说表现出一种“反叙述”,即创作结果违背作者本意的形式症候⑤参见李国华:《反叙述:论赵树理小说的形式与政治》,《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如此看来,《在医院中》作为一个失控的文本,象征着丁玲创作主体的某些危机。本文将由此出发,探究丁玲1941年的心境问题。
一、反讽叙事格局的“失控”
罗吉·福勒在《现代西方文艺批评术语》为“反讽”下的定义:“(反讽)是一种用来传达与文字表面意义迥然不同(而且通常相反)的内在含义的说话方式。”⑥罗吉·福勒主编:《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袁德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在笔者看来,如果要对反讽叙事进行一个粗略的区分,那么它大概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叙事者对所叙述对象的反讽,在文本层面,主要表现为在文本局部存在着反讽的语调,如《北望园的春天》中叙事者对杨村农等人暧昧的微讽。
第二种是隐含作者对叙事者/视点人物进行的反讽,这种反讽叙事往往贯穿于文本之中,即隐含作者通过种种暗示,使读者不再保有对叙事者/视点人物的完全信任,转而对叙事者的叙述进行反思。隐含作者可以通过多种手段颠覆这种信任,比如可以通过叙事视角的限制,让读者对事情的真相产生怀疑;也可以通过种种暗示,在道德意义上对叙事者/视点人物的权威进行颠覆;或者直接推翻叙事者/视点人物所叙述出来的故事。
一般意义上来说,上文所提到的两种反讽叙事有可能会处于一个相互生成的状态。一方面,叙事者/视点人物对所叙述对象的反讽,很容易导向自身,颠覆掉读者对于叙事者/视点人物的信任;另外一方面,当反讽导向叙事者/视点人物自身后,阐释者带着“反讽叙事”的眼光看待叙事者/视点人物的叙述,又很容易把叙事者/视点人物的叙述阐释为反讽叙事。如果借用吴晓东的说法,我们可以把叙事者/视点人物的权威颠覆后产生的叙事格局称为“反讽叙事格局”①吴晓东:《战时文化语境与20世纪40年代小说的反讽模式——以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为中心》,《文艺研究》2017年第7期。。由于叙事者/视点人物的信任是天然的,所以,如果要产生这种“反讽叙事格局”,一般来说都需要隐含作者进行精心的叙事控制,在文本的不同层面向读者反复暗示叙事者的不可靠性,从而促使反讽叙事格局的生成。
不难发现,丁玲在《在医院中》中,似乎也有一个架构“反讽叙事格局”的意愿,即在陆萍这一视点人物的基础上,架构出一个反讽叙事格局。陆萍作为一个视点人物的权威,是被作者取消掉的。但是,丁玲的架构方式却显得有些与众不同:隐含作者与其说是通过暗示使反讽转向视点人物本身,不如说是一种“明示”,即在文章一开头,便对视点人物进行了比较明显的反讽,从而试图取消掉视点人物的“天然权威性”:
“那天,正是这时候,一个穿灰色棉军服的年轻女子,跟在一个披一件羊皮大衣的汉子后面,从沟底的路上走下来。这女子的身段很灵巧,穿着男子的衣服,就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似的。她有意的做出一副高兴的神气,睁着两颗圆的黑的小眼,欣喜地探照荒凉的四周。”②丁玲:《在医院中》,《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235、238页。
我们很容易就捕获“有意”这一信息:这意味着,这个年轻女子似乎并不那么“欣喜”。很快,文章的发展就证实了我们的结论:
“她不敢把太愉快的理想安置的太多,却也不敢把生活想得太坏,失望和颓丧都是她所怕的,所以不管遇着怎样的环境,她都好好的替它做一个宽容的恰当的解释。仅仅在这一下午,她就总是这么一副恍恍惚惚,却又装得很定心的样子。”③丁玲:《在医院中》,《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235、238页。
这里是全知叙事者对女子心理的描绘。这告诉了我们年轻女子的心态:“不管遇着怎样的环境,她都好好的替它做一个宽容的恰当的解释”,这意味着,“年轻女子”在心底里其实很不喜欢这里,而只是出于某种原因不得不来,所以才只能给予自己一些自我安慰,而这种自我安慰显然是不彻底且不足够。这就似乎要暗示读者,“年轻女子”的视点经过了某种轻微的扭曲,她对于环境周围的判断需要经过我们的怀疑、判断和反思。因为,无论她再怎么试图安慰自己,她终究不喜欢这里,所以,很有可能在她的视角下,周围的环境可能会比事实上更“阴暗”些。如果说在前文中还是以全知叙事者为主要视点,那么接下来,获得“陆萍”命名的“年轻女子”便正式成了主要的视点人物,也给了读者验证上文所述判断的契机,开始不断地通过“回味”陆萍的判断来试图阐释出一种“反讽叙事”。
陆萍遇到的第一个主要人物是张医生的老婆。在她的眼里,她虽然美丽,“可是她仿佛没有感情,既不温柔,也不凶暴,既不显得聪明,又不显得愚蠢”,在“反讽叙事格局”的期待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句话的反讽意味。“她向那些粗人学的很好,不过即使她这末骂着的时候,也看不出她有多大的憎恨,或是显得猥亵”①丁玲:《在医院中》,《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252页。,这句话显得更加暧昧不明,甚至带有微微的嘲讽意味。接下来,她对其他人的嘲讽就显得越发“明目张胆”,从暧昧的“反讽”变成了比较强烈的“讽刺”。比如林莎,“她的脸有很多的变化,有时像一朵微笑的花,有时像深夜的寒星。她的步法非常停当,用很慢的调子说话,这种沉重又显得柔媚,又显得傲慢”。王医生的太太,“她总用白种女人看有色人种的眼光来看一切,像一个受惩的仙子下凡世,又显得慈悲,又显得委屈”②丁玲:《在医院中》,《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252页。。在这里,一些嘲讽甚至可以用精彩来形容,甚至让一些读者也联想到身边类似的角色。
也正是在这时,作者/我们不知不觉中已经开始认同并同情陆萍的判断,而把开头的明确信号,即隐含作者企图在陆萍这个视点人物上,构建出一个“反讽叙事格局”的意图忘却了。在一系列“精彩”的嘲讽之后,接下来,陆萍被摆放到了一个“先觉者”的位置,她似乎成了医院的“改革者”,而周围面对着重重的阻力。她倡导科学、卫生、合理的工作环境,全身心投入工作,但周围的一切环境似乎都不尽如人意。不仅如此,在她将自己全部投入工作时,旁边的人不仅不帮忙,反而都在“围着看她”。到这里,作者/我们已经很难不对陆萍产生同情乃至共情。开头叙事者所企图构建的“反讽叙事格局”,更是早就被忘得一干二净了。
直到手术之后,作者似乎才猛然醒悟,开头还有一个“反讽叙事格局”的意图存在,像是要弥补似的,增添上了这样的语句:“她寻仇似的四处寻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责一切,她每天苦苦寻思,如何能攻倒别人,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边的。”③丁玲:《在医院中》,《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252页。作者似乎试图拉开自己和陆萍的距离,从而挽回“反讽叙事格局”,但是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如上所述,隐含作者曾经有一个鲜明的建立“反讽叙事格局”的意图,但是不幸的是,这一格局最终并未完成,导致失控,从而存留有高度的症候性特征。但是,如果仅就文本来看,我们无法解读这一症候性的由来。此时,结合文本外部的材料来看,就显得必要了。
二、“成长”设想:作者、人物、原型、隐含读者的多重镜像关系
《关于〈在医院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丁玲的创作动机与人物的生成过程。陆萍的“模特”是丁玲在1939年拐茆医院住院时所结识的助产士俞武一。在丁玲看来,“这个女孩子有很大的热情和克己精神,但缺乏理智,好发议论,感情脆弱,容易感伤,并不使人欢喜”。结果,因为“我的落拓和她的纤细,以及我们的年龄和彼此要求”都不尽相同,在丁玲离开医院后,二人便“淡漠而且不自然起来了”④丁玲:《关于〈在医院中〉》,《书城》2007期年第11期。。
不过,这个女孩依旧给丁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丁玲遇到了很多和她类似的女孩子,“她们都富有理想,缺少客观精神,所以容易失望”。丁玲“喜欢她们的朝气,然而却讨厌她们那种脆弱”,“这样的人物同我接触多了之后,使我想写一篇小说,来说服与鼓励她们。我要写一个肯定的女性,这个女性是坚强的,是战斗的,是理智的,是有用的,能够迈过荆棘,而在艰苦中生长和发光。这个欲念发生之后,很自然的那个被冷淡了却生活在我脑子中有二年之久的女主人公便活过来了”①丁玲:《关于〈在医院中〉》),《书城》2007年第11期。。
在这里,丁玲的写作动机是很特别的,也就是说,作品的“原型”和“隐含读者”其实是同一类人物。而且,丁玲是要写出一个“成长”的过程:“她对生活是严肃而正视的。她不能连有一点点小资〔产阶〕级的幻想都没有,或是幽闲的有时又是热烈的情愫,但她却应该有坚定的信心和方向,而且有思想,有批判自己的勇气。经过许多内心的斗争,直到很健康的站立着。”②丁玲:《关于〈在医院中〉》),《书城》2007年第11期。在这个意义上,《在医院中》实际上也是一种革命实践,即丁玲试图通过文学写作使一个人物“成长”,来达到鼓励现实中革命青年“成长”的目的。因此,她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即写一个有优点、又有缺点的人物,并且采取了“反讽”作为“成长”书写的手段。对丁玲来说,“反讽”恰恰是对这类可塑青年最好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成长”的意义上,丁玲很可能是不自觉地以自我为“范本”,这种“范本”的姿态显得颇为复杂。一方面,丁玲和这些女孩子们通信中,表现出一种革命先辈的姿态:“要求她们有吃苦如饴的决心,要求她们有下地狱的勇气,要求她们百折不挠,死而无悔。”③丁玲:《关于〈在医院中〉》),《书城》2007年第11期。另一方面,丁玲也能够意识到,自己并非一个完全理想的范本,只是在某种意义上暂时充当,她自己也需要不断地学习:“我有很多缺点,我一点什么都不能帮助你,可是你常常在我一起,你应该比别人强一点才成。忍受苦难,自强不息,我不能永远同一个软弱的多感的动物相好。”④丁玲:《关于〈在医院中〉》),《书城》2007年第11期。所以,这个革命实践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丁玲要求革命后辈与自己一起成长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在医院中》是丁玲一种自我超克的尝试,因为她明白自己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健康的站立着”,要写出一个“很健康的站立着”的人物,无疑要通过超克自我来实现。
在这里,作家丁玲、人物陆萍、人物原型、隐含读者,在“成长小说”的设想下,形成了一种多重交错的镜像关系。“成长”前、“成长”后、预想完成的陆萍、实际完成的陆萍,各种人物之间存在的关系十分复杂,很难用言语表述清楚。笔者做了这样一个草图,作家、原型、人物、或许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存在的:

图1 《在医院中》人物的多重镜像关系
在这里,纵轴代表着某种“思想高度”,越往上越代表人的“思想觉悟”越“高”。可以看出,《在医院中》对于丁玲来说,本身就是一个颇为艰难的写作尝试,因为这样一个“成长”的预设架构,很有可能跨越了丁玲自身成长经验的限度,丁玲因为自身的成长经历,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和宽容这些革命后辈,她希望革命后辈达到的高度,实际上是当时的她也达不到的。
丁玲说过,这篇小说的失败,主要不在陆萍这个人物,而在“环境”:“有一种气氛,这个使人不愉快的气氛贯穿到全篇,它是相当的幽暗相当的繁琐而恼人”,因此,“小说创作了一半,我停止了。我已经意识到我的女主人公,那个我所肯定的人物走了样,这个人物是我所熟悉的,但不是我理想的,而我却把她作为一个理想的人物给了她太多的同情。我很自然的做了,却又不愿意”①丁玲:《关于〈在医院中〉》,《书城》2007年第11期。。丁玲意识到,自己多次想要修改人物而不得的原因在于,如果要修改陆萍这个人物,必须要把作品中的“环境”全部修改了才可能——而“环境”代表着丁玲对当时延安的真正看法,也就是1941年丁玲的“思想高度”。这是她所不愿改,也无法改的。
上文提到过,丁玲在这个“成长”设想中,是不自觉地以自我为“范本”。但是,由于自身高度,理想中“成长”后的陆萍无法生成,反而“生长”出另一个人物,即最终实际完成的陆萍——一个部分地实现了成长的人物。同时,在这样的写作过程中,丁玲也隐约意识到,按照自己之前设定的成长逻辑,不一定能真正到理想的高度。如果在写作前,她还对这种自我超克能否成功抱着模糊的希望,那么写作停滞也就意味着这个模糊希望的彻底破灭。
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她还不能彻底认识到这一点,甚至只是隐约地意识到有某种“不对”,但具体怎么“不对”,如何解决,都没有答案。在反复修改而不可得后,困惑的丁玲只好先搁置这篇文章,也同时搁置心中隐隐出现的不安,“把那些原稿纸都请到我的箱子里睡觉,不再思索它们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就能理解“反讽叙事格局”建立和失控的原因:丁玲尝试建立“反讽叙事格局”,既是对后辈的友爱的警醒,也是自我超克尝试的某种表征——毕竟只有拉开自己与人物的距离,才能把自我“往上托举”,从而实现自我的超克。“反讽叙事格局”的失控,也意味着自我超克的受挫,按照丁玲固有的成长经验,她只能写出一个部分成长的陆萍。隐含作者丁玲失去了对“反讽叙事格局”的控制,从而形成“失控的反讽”,体现了丁玲自身的某种主体困境。
三、“全知叙事”与丁玲的态度
此外,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在医院中》的反讽叙事并非一个“反讽叙事格局”所能概括。正如琳达·哈琴所说:“在没有被诠释为反讽之前,反讽就不成其为反讽。”②转引自吴晓东:《战时文化语境与20世纪40年代小说的反讽模式——以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为中心》,《文艺研究》2017年第7期。“反讽”既是文本中固有的内容,也是被阐释的结果。一般意义上来说,“反讽叙事格局”会采取严格的内视角,因为这样,叙事者权威会相对更容易颠覆。换言之,一个全知叙事者的权威,是很难颠覆的。
在内视角下,“反讽叙事格局”,往往会带来一种“阐释循环”:在叙事者/视点人物对所叙述对象进行反讽时,如果稍稍显得失度,便很容易显得不够“厚道”,而引起阐释者对叙事者的质疑,这就形成了“反讽叙事格局”;而在“反讽叙事格局”生成后,阐释者又会带着对叙事者/视点人物“怀疑”的眼镜重新审视文本,又会发现更多“反讽”的情节。二者会不断地循环、衍生、相互印证,由此带来一种循环关系。这是因为,叙事者/视点人物的天然信任一旦失去便再难生成,文本的阐释会在怀疑叙事者的基本面上展开,在对叙事者/视点人物“可信可不信”时,阐释者往往倾向于“不信”。这种“阐释循环”有好有坏:一方面,会让我们加强对文本的细读能力,反复地琢磨叙事者的叙述,从而读出更多的文本内涵;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过分地不信任叙事者/视点人物,乃至缺少对叙事者/视点人物必要的同情。
但是,《在医院中》却不完全符合这种“阐释循环”。因而,当我们尝试解读《在医院中》的反讽叙事时,便会觉得尤为困难。这是因为,不同于惯常的内视角,《在医院中》在采取全知叙事视角的同时,又安排了一个主要的视点人物陆萍,文章实际上存在着叙事者和视点人物的“双视点”。这样,在两个视点的互相映照下,文章内部的反讽结构和层次便显得丰富起来:不仅存在着全知叙事者对视点人物陆萍的反讽、视点人物陆萍对所见对象的反讽,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全知叙事者对叙事对象的直接反讽。不得不说,全知视角所带来的多重反讽层次,本身会增加写作困难,既然要建构一个“反讽叙事格局”,那么采取严格的内视角会更加简便。但是,丁玲一开始就采取了全知视角,但是后来因为写作的困难,不得不增加了一个主要视点人物,最终形成了“全知叙事+视点人物”的模式。那么,丁玲所坚持使用的全知视角,是否存在着一些更为丰富的意味呢?
“他们在有的时候显得很笨,有时却很聪明。他们会使用军队里最粗野的骂人术语,当勤务员犯了错误的时候;他们也会很微妙的送一点鸡,鸡蛋,南瓜子给秘书长,或者主任。这并不要紧,因为只由于他的群众工作好,不会有什么嫌疑的。”①丁玲:《在医院中》,《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237-251、251页。
刚见到李科长的陆萍,很显然是不知道李科长的这些故事的,这些是全知叙事者的叙述,同时也是对李科长的反讽。换句话说,这直接关涉到隐含作者丁玲的态度,而和陆萍无关。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丁玲对于这种现象皮里阳秋的态度。与其说是丁玲在“抨击解放区的官僚化现象”,不如说丁玲内心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她对于这种现象,一方面很难接受,一方面又因为这些干部确实“群众工作好”,所以这种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无伤大雅、可以容忍的。
“其实她的意见已经被大家承认是好的,也绝不是完全行不通,不过太新奇了,对于已成为惯例的生活就太显得太不平凡。但反对她的主要理由便是没有人力和物力。而她呢,她不管……”②丁玲:《在医院中》,《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237-251、251页。
丁玲在这里显然比陆萍深刻很多:她敏锐地体悟到,人力物力的缺乏是主要原因,但同时也遮蔽了一个更隐微的原因,即吴舒洁所谓的“革命的庸常化”③吴舒洁:《“公家人”与革命的庸常化——从丁玲的〈夜〉谈起》,《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4期。问题。革命群众高涨的感情和精神,在战争中缺钱少物、敌我混杂的形势下,在日常繁文缛节的动作中被不断消磨,生命的活力不断消失,人仿佛丧失了感情:“在她的床的对面,多睡一个人或少睡一个人或更换一个人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可以引起波动的。”④丁玲:《在医院中》,《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237-251、251页。
对于这种庸常化的现象,比陆萍承担过更多工作杂务的丁玲,自然也体会得更深。也正因此,她才对俞武一式的人物抱着复杂的态度:既欣赏她的热情,又深切地意识到,如果她不能够让自己坚强一些,这种热情一定会被消耗掉。但另一方面,对于年轻人勃勃的革命浪漫热诚,“神经变得粗了很多”的丁玲,或许也有几分复杂的心绪,对这种看起来无可避免的现象充满了矛盾和感慨。
回到《在医院中》最有力的一句提问:“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⑤丁玲:《在医院中》,《丁玲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237-251、251页。除了“几十块钱”之外,更关键的问题是“爱”,陆萍不满的原因不只是医院物质条件的落后,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同事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空气中遍布着怀疑、刻薄与流言蜚语。比如,陆萍只有在和郑鹏、黎涯在一起时,才能畅所欲言而不必担心被告发。
值得一提的是,《在医院中》本身是分两期创作的,《关于〈在医院中〉》与《在医院中时》第一期的创作相距已有一年多时间。《在医院中时》和《关于〈在医院中〉》,以及同期文本序列的复杂层次关系,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1941年6月,有可能是《在医院中时》第一期创作截止之后,丁玲完成了《夜》。在1941年的9、10月完成了《战斗是享受》、《我们需要杂文》,于1941年11月进行了《在医院中时》的第二期创作。1942年上半年,丁玲完成了《三八节有感》、《风雨中忆萧红》,之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座谈会后,完成了《关于立场问题我见》、《文艺界对于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等重要文本的写作,之后才写了《关于〈在医院中〉》。所以,经历两期创作的《在医院中时》,不仅可以、而且应当作为一个敞开文本来看待:《夜》《战斗是享受》《我们需要杂文》,作为重要的互文本,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同期创作,更是部分的内在于《在医院中时》之中的文本。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再看《风雨中忆萧红》中,便会觉得意味深长:“像这样的能无妨嫌、拘束、不需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啊!”①丁玲:《风雨中忆萧红》,《丁玲全集》第5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结合《丁玲传》,我们便可以发现,陆萍、郑鹏、黎涯之间毫无嫌隙的关系,也有着当年的丁玲、萧军、萧红的影子。
在丁玲的《战斗是享受》一文中,开头一半篇幅以上,并未出现任何“战斗”的字眼,而是用激烈的笔触描写一场烈雨。直到文章快结束,读者才意识到,文章不是写与敌人战斗,而是“与水搏斗”,在与冰冷的水搏斗中,释放出生命的能量:“只想冒着冷雨冲出去,在从山上流下来的黄色瀑布里迎着水流往上走,让那些无知的水来冲激着自己”;“人像在原始时代,抵抗着洪水,而顺着头发和面孔流下去的凉水却多使人抖擞,击打而来的劲风,多使人感到存在,感到傲岸啊!”②丁玲:《战斗是享受》,《丁玲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3页
在笔者看来,这也是丁玲心境的某种隐喻:丁玲的战斗方式,不是针对具体的外在对象,而是一种抽象的自我内心的搏斗,是在同“冰冷的水”战斗的同时,“才会感到生活的意义,生命的存在”,“才会感到青春在生命内燃烧,才会感到光明和愉快”③丁玲:《战斗是享受》,《丁玲全集》第7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3页。对于丁玲来说,反讽不仅仅是一种对现实丑恶讥刺的方式,更是作家主体在战时文化语境的笼罩下,在自我内心的剧烈斗争中,生命能量的一种强烈又曲折的展现。丁玲一直尝试努力克服自己,提升自己的修养,把这种“内心的剧烈的斗争”,抽象化成一种没有明确对象的战斗,并通过“战斗”的激情来超克自己内心的矛盾,将自己在这种冷凄的环境中压抑的能量抒发出来。这也就是全知视角的丰富意味:因为只有通过全知视角,这种能量才能被更强烈地抒发出来。
余论:革命伦理、革命律令与丁玲的逻辑
黄子平在论及《我们需要杂文》时说:“‘杂文’不仅意味着一种写作方式,而且意味着那一代知识者对他们所理解的‘五四精神’的坚持和传承。”④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页。和《我们需要杂文》同时期创作的《在医院中》,其中出现的种种讽刺,或许正如黄子平所说的,是对文学“针砭时弊”功能的坚持。但是,问题在于,丁玲的创作本意是“创造一个肯定的人物”,“她应该有坚定的信心和方向,而且有思想,有批判自己的勇气。经过许多内心的斗争,直到很健康的站立着”,如果《在医院中》单纯只有“针砭时弊”的一重“病的隐喻”,那这个创作动机和结尾的“人在艰苦中生长”便无从理解。黄子平也正是在“驱邪仪式”的意义上理解这一点的,这无疑有简化问题的嫌疑。
那么,如何理解文章的结尾,也关涉到如何理解丁玲自身:“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融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生长。”燎荧在文章中认为,“新的荆棘”便指的是客观存在的恶劣环境,但在笔者来,毋宁说是小说中所说的“剧烈的自我斗争”。这也是当时的丁玲所能给出的结论。事实上,在写作之前,丁玲便已经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自我调节方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了自我反思的意识,否则也无法解释《在医院中》的写作动机和写作信心。
那么,这种调节的方式究竟是什么呢?李国华认为是一种“革命伦理”,是道德修养层面的党员的自我要求,而且认为这是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供的某种实践方式:“刘少奇 1939年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感慨有些共产党员受到剥削者的恶浊社会的影响,‘身上带有污泥’,因此需要加强修养。根据《在医院中》的共产党员陆萍的表现,也许不妨推定,丁玲的个人经验和观察与刘少奇的意见一拍即合,她就是根据刘少奇对中国共产党队伍的观察来预先设定标准共产党员的内涵的。”
这种“革命伦理”,表现为一种道德上的、由内而外的自我的要求,一种“修养”、“锻炼”式的改造,“所谓‘不消溶’,是指在庸常和凡俗中永葆革命青春,所谓‘艰苦’,是指庸常和凡俗的日常生活,而‘人’的‘有用’和‘生长’,是指‘最好的党员’的能够反抗和抵制‘恶浊’的影响。”①李国华:《文学生产性如何可能?——丁玲〈在医院中〉释读》,《人文杂志》2014年第6期。
在笔者看来,李国华的这对概念,正好可以解释丁玲在这次主体超克尝试的“成功—失败”过程:“革命伦理”的自我修养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主体与环境的矛盾关系。这也正是当时丁玲进行自我调节的方式。
但是,丁玲在开始写作前并未意识到,这种“内启蒙”式的调节的力度是有限的,并不足以支撑一个“杜晚香”式理想人物的完成,因为这种调节方式是一种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而并非将自己进行一次“脱胎换骨”式的转变。或许,丁玲也从这次写作失败,意识到了“革命内启蒙”道路的不足,从而开始积极投入延安整风运动中,在革命律令的要求下进行革命实践,以期改造自身。正如贺桂梅所说:“这种紧张的‘自我战斗’,其结果并不是其中的‘一元’克服了‘另一元’,而是‘二元’之间不断地互相转化,进而形成一个动态的、朝向外部开放,并通过包容外部而形成更阔大自我的辩证过程。”②贺桂梅:《丁玲主体辩证法的生成:以瞿秋白、王剑虹书写为线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5期。这里包含了三个基本要素,即作家的革命现实实践、主体人格的塑造及其文学创作形式,三者处于辩证的相互塑造过程中。对《在医院中》写作困境的反思,或许是丁玲“主体辩证法”生成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