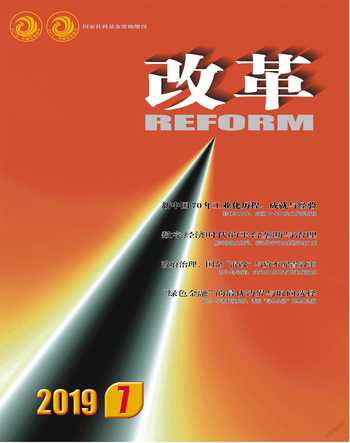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平台垄断及其治理策略
熊鸿儒
内容提要:近年来,针对数字平台寡头的反垄断争议不断。我国一大批数字平台企业快速崛起,在大幅改善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新的治理挑战。平台垄断问题引发的监管难题较为突出,传统的反垄断分析标准、执法方式及监管体系亟待完善。为顺应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的发展规律,最大限度地激励创新,并有效保护消费者,应坚持包容审慎、开放透明、灵活有序的监管原则,多措并举完善反垄断规制体系,提升监管能力。
关键词: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监管体系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19)07-0052-10
我国已是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技术投资与应用大国。近年来,凭借技术进步、业态创新和消費升级,一大批数字平台企业快速崛起,渗透到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域。新兴的数字平台在大幅改善经济运行效率、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监管难题。在我国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尚未夯实、竞争执法仍处于初期阶段的背景下,妥善处理好鼓励平台经济创新发展与合理规制垄断行为之间关系的挑战较大。针对这类新型的复杂经济现象,有必要认清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垄断问题的缘起,结合我国平台经济发展实际及时梳理发展中遇到的各类新问题,明确必要的监管原则,加快构建包容审慎、公正高效的监管体系。
一、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垄断问题缘起
所谓“平台垄断”,是指平台经济中常见的“赢家通吃”现象可能演化为少数垄断平台长期维持“通吃赢家”地位,对良性市场竞争和消费者福利造成损害。垄断是引发市场失灵的关键原因之一。如果确实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市场失灵,就需要依靠恰当的公共政策(主要是竞争政策)约束市场势力,维护市场竞争,改善社会福利[1]。
(一)针对“数字寡头”的反垄断争议不断
各国针对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反垄断监管由来已久,只是近些年关注度明显提升,社会争议也越来越大。早在20世纪末,美国司法部就针对微软公司的视窗操作系统非法捆绑搭售案进行调查;之后,谷歌公司旗下搜索引擎及安卓移动操作系统等平台自2010年起接连受到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欧盟委员会的反垄断调查。类似地,亚马逊、eBay、Facebook、优步(Uber)等数字平台企业都曾经或正在接受不同国家的反垄断调查。各国对这些平台企业开展反垄断调查,并不仅是因为其在各自细分市场拥有的支配地位或市场势力,而主要是相关的各类垄断行为。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不合理的屏蔽、歧视或劫持行为(包括限制交易);可能扼杀未来竞争或阻碍市场进入的先发兼并行为以及垄断势力的跨界传导;尚不明确的滥用用户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实施不合理歧视或达成垄断协议等。不过,是否以及如何对这些“数字平台寡头”进行适当且有效的监管,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2]。
一是主张尽量不干预的“自由派”。有人基于数字市场的动态竞争和创新激励的重要性,担心过度或不适当的干预会破坏竞争而非保护竞争,还可能对创新产生抑制作用。他们认为,执法机构不应对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进行干预,因为对动态市场的任何政府干预都将损害消费者利益,同时任何市场力量在动态竞争面前都不过是过眼云烟,反垄断规制的收益十分有限[3]。一些专家担心,在高度动态的数字市场,打击垄断与维护创新激励机制往往难以两全。
二是主张积极干预的“规制派”。他们认为,在某些情形下,数字市场急需开展竞争执法,以保护促进创新的竞争结构、及时制止阻碍动态竞争过程的反竞争行为或排他性行为。如欧盟委员会发布专门报告指出,虽然在数字市场上取得市场支配地位并不意味着必然违法,但竞争法规则应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悬于“数字寡头”上,时刻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4]。伴随数字技术扩散加速,平台利用数据、算法等新竞争要素的行为可能“侵蚀”传统竞争机制。如超出监管能力范畴的共谋将屡见不鲜,价格歧视的表现形式愈发具有迷惑性,算法驱动的垄断组织滥用个人信息等,甚至可能成为影响政治生态的强大工具[5]。一些专家呼吁:为修补市场缺陷、促进消费者福利,主动干预在所难免。当然,选择合适的时机和有效的方式,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过去那些依据传统经济构建的反垄断规则在数字平台市场中不一定总是适用的[6]。
(二)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垄断不同于传统的市场垄断,规制思路需要创新
数字化时代的平台垄断与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市场垄断有较大差别,所带来的垄断效应也不同于传统的市场垄断、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监管部门应在准确把握数字化时代平台经济发展、平台竞争规律的基础上,客观认识平台垄断的实质及影响。
一方面,平台垄断现象有其特殊性。“平台”作为数字时代最重要、应用最广的经济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多个领域的产业组织方式。互联网平台大多是双边或多边市场,具有匹配供需双方的市场属性。平台的规模扩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济运行效率——这与传统意义上的垄断有很大差别,因为后者往往是对特定产品或服务供给、需求乃至于交易价格的排他性控制,对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产生损害。不同平台的竞争主要围绕注意力或用户开展争夺,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运营规模,双边市场下的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会创造相应的进入壁垒,容易导致“一家独大”的市场格局。不过,考虑到数字时代新技术、新模式的快速迭代和高水平投资特点,成功的平台企业所获得的市场力量往往又是短暂而脆弱的,进入壁垒并没有传统市场中那么持久而稳固。只要数字技术及其扩散没有停止,在位的“数字寡头们”就需要继续通过创新来维持地位。否则,新一轮的创新浪潮往往又会诞生一批新的“巨头”。这种动态、持续的市场竞争是数字市场竞争的常态。可见,数字时代平台企业的垄断地位形成并不一定意味着市场失灵,相反在很大程度上能与市场竞争相互促进和转化,有助于资源配置效率改善。
另一方面,平台垄断现象确实带来了许多新的风险,特别是对竞争执法的新挑战。数字市场的动态性要求在位的平台巨头必须不断革新,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巨头的“可疑行为”:通过利用既有的市场力量传导至新的市场以扩张垄断地位;兼并潜在的竞争对手以获得新技术、新模式的“优先购买权”;过度采集用户信息、交易数据或无正当理由地降低互操作性以实现“用户锁定”和“完全价格歧视”;等等。当然,这些行为并不必然具有反竞争性,如企业间兼并可能是优势互补的结果,被大企业收购的前景也是新创企业进行自我创新的主要动力之一。但不可否认,实际情况经常是:即便新的竞争者拥有更好的产品、模式或更雄厚的资金实力,想要打破既有的竞争格局也是很难的;用户在享受大平台带来的便利时对所支付的“代价”(如牺牲个人隐私)往往并不知情。因此,竞争执法机构必须密切关注数字市场上的竞争动态,对可能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保持足够的警惕和有效的规制,确保市场的可进入性、可竞争性和消费者利益,同时避免保护主义思维或防止规制俘获。确保监管的有效性和灵活性,始终是促进市场健康繁荣的保障。
二、我国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状况与竞争治理问题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一大批新兴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速崛起,深刻地改变着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在网络效应彰显、线上线下加速融合的背景下,一些数字平台的规模不断扩张,对于高效连接市场、资源与用户,塑造全球化、多样化、数字化生态体系产生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一系列治理难题也在涌现。一些在传统经济中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在平台经济领域有了被进一步放大的风险。平台经济治理的复杂性对政府监管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
(一)数字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创新活力迸发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态势可谓日新月异,在很多领域甚至具有全球领先优势。从数字经济规模来看,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据中国信息化百人会2018年度数字经济报告,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2.6万亿元。从数字经济发展质量来看,我国是新兴经济体中上升势头迅猛和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之一,已成为全球领先的数字技术投资与应用大国;市场体量庞大,能够推动数字商业模式迅速投入商用,本土市场拥有大量热衷数字科技的年轻消费者;业务遍及全球的中国互联网三巨头“BAT”正在布局多行业、多元化的数字生态系统,深入触及消费者生活的各个方面[7]。
作为重要的新型产业组织形态,平台经济活力迸发,已成为促进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力量。近年来,我国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平台经济涵盖了电子商务、分享经济、社交媒体等多种应用和服务形式。众多生产者和消费者依托一大批互联网平台形成了多个网络生态系统,实现了产品设计、创意、生产、交换、分配、使用和服务的网络化。随着区块链、人工智能、5G、VR/AR的发展和集成应用,平台经济正在催生更多的新商业生态。数字平台企业通过推动产业融合与业态颠覆,已成为加快新动能成长的重要载体。以独角兽企业为例,从公开发布的各类评选榜单来看,2018年排名前20位的我国本土独角兽企业几乎都是数字平台企业。
我国数字平台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基本实现了从落后到领先的跨越式发展。依托巨大的市场规模优势,我国本土数字平台的成长速度和规模惊人。以网络零售、移动支付、网约车为代表,国内平台企业已经成为各自行业的主导者,相较于国际同行而言在体量上占据较大优势。相应地,我国数字平台企业的创新发展也成为全球网络空间力量竞争的重要载体。2013~2015年,全球互联网企业市值前30位排名中,我国企业占据的席位从7个增加到12个,而美国则从18个下降到15个。
国内外激烈的市场竞争还使得多数互联网平台不断增加创新投入,提升了产业发展的动态效率。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2018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投入合计490亿元,增速达19%,占全行业业务收入的比重达5.12%,远超全国平均水平。阿里巴巴、百度、腾讯等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研发强度分别高达10.6%、14.4%、7.8%,规模均超过百亿元。这些企业通过大幅增加研发投入,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前沿领域探索和开发新技术、新市场,创新行为更加积极,对推动行业发展、参与全球竞争具有重要作用。
(二)平台垄断与竞争治理问题开始出现
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涉及平臺竞争与垄断方面的治理问题也日益增多,如2013年的“中国互联网反垄断第一案”,平台企业频繁合并,电商平台“二选一”,平台纵向一体化、平台间不兼容或相互“屏蔽”,“大数据杀熟”,用户数据泄露以及算法滥用,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平台企业的经济特性、竞争特性密切相关。一些问题在传统平台企业上也曾发生过,但进入数字时代,问题变得更复杂、更隐蔽,影响范围也更广,使得一些传统的法律法规、治理方式及监管手段难以适应。在一些数字市场或“互联网+”产业领域快速集中后,如何确保富有活力、良性健康的竞争,激发更多的创新和更好保护消费者利益,成为政府和社会关切的焦点。归结起来,至少涉及以下四类:
一是数字平台的市场力量认定尚无规范方法或成熟经验,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判定也没有公认标准。一方面,平台厂商的市场力量与传统厂商具有明显差别,依赖市场份额、利润率等传统工具往往存在较大偏差。比如,已成为“中国互联网反垄断第一案”并产生最终判决的“3Q大战”,即腾讯公司即时通讯软件QQ平台与奇虎360公司的杀毒软件之间涉及“滥用支配地位排挤竞争”的官司。此类案例在相关市场界定、滥用支配地位行为认定以及竞争损害分析等方面都曾存在较大争议。近些年,在共享出行、“外卖”等领域多个地区的不正当竞争以及涉嫌垄断经营现象也遇到了类似的难题。另一方面,对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判定也没有普适标准。对一些大型电商平台而言,与用户签订具有“二选一”特性的排他性协议时,尽管不少专家认为违反了《反垄断法》规定的自由交易原则,同时可能削弱平台间竞争,但对消费者和商家的损害或实质影响难以事前评估。对市场支配地位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认定的合理性和准确性亟待加强。
二是不同数字平台企业间的合并现象频发,反竞争效应显现,引发限制竞争和打压创新的担忧。近些年,我国互联网多个细分市场上纷纷由“群雄逐鹿”走向领军企业“合并同类项”,市场集中度不断提升,“一家独大”或“寡头垄断”格局有所强化。由于平台企业打通线上线下融合的诉求,纵向一体化趋势也逐步显现。在互联网领域,不断激增的合并现象主要是为了扩大规模经济和获取网络效应的红利。其影响除了形成一些竞争力强的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细分领域的市场竞争,相关市场支配地位被滥用的可能性加剧。在数字经济中,不排除新合并企业基于其大数据优势,定向实施反竞争性歧视行为的可能,如强制实施搭售、抄袭商业模式、向上下游延伸垄断优势等。这不仅会打击小微企业创新的积极性,而且会损害上下游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三是各类新型垄断行为不断涌现,传统经验可能不再适用,准确识别困难加大。互联网行业的一些新业态、新模式颠覆了传统商业规则,往往难以通过传统行业规制经验或常用工具直接预判其行为的后果。一方面,若忽略其发展特殊性,容易“一刀切”地“管死”。另一方面,若放任其野蛮生长,则可能导致竞争秩序混乱,损害消费者利益,更不利于创新。以数字平台厂商的个性化定价或价格歧视行为为例,依托大数据的价格歧视有其特殊性:在平台经济中个性化服务本质上将市场特别是买方市场分成了一个个独立个体,截断了消费者的搜寻行为,使之可能在某种惯性下无选择地购买服务,网络效应容易引发“一家独大”,供需两侧可能同时失去竞争性,而平台成为唯一的“知情者”,当这个“知情者”对每一种商品向特定用户进行拍卖时,一般意义上的市场可能不存在[8]。此外,诸如恶意不兼容、广告屏蔽、流量劫持、静默下载、深度链接等一系列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广受关注,相关案例反复出现冲击着公平竞争秩序。
四是不断扩张的“数字寡头”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力加速抬升,任何潜在的垄断行为或治理不当都可能产生难以预测的后果。大多数数字市场上日益集中的竞争格局正引发越来越多的讨论。如数字平台巨头积累和控制着海量用户数据,使其具有锁定消费者或商家、强化市场支配地位的力量,或对用户分类管理,并利用计算机算法实施歧视性定价,甚至影响经济安全和网络安全。特别地,数据资源已是数字平台企业的核心资产,但大数据的使用行为引发的关于数据产权归属、数据隐私侵权、数据拒绝分享、数据驱动型的经营者集中以及数据滥用问题等,都对监管提出了较大挑战。监管部门也很难判断反垄断执法的范围和最佳时机,甚至识别企业何时会垄断市场也不容易。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所面临的反垄断执法难题与欧美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多数挑战是类似的。诸如,相关市场界定困难、市场支配地位认定难,传统分析框架及评估工具可能不完全适用,识别反竞争行为难度大、争议多,执法过程复杂度高,必要的执法能力欠缺,等等。
(三)现行监管体系和执法方式亟待改善
第一,一些政府干预不合理,迫切需要纠正、规范。一些地方在新经济领域设置不合理和歧视性的市场准入条件,就是最典型的表现之一。以网约车领域为例,多地准入门槛限制使网约车行业陷入普遍违法的窘境。截至2018年7月,全国已有210个城市出台网约车监管细则。从各地的准入条件看,不但运营企业需在各个城市注册子公司,司机需满足户籍等限制,而且车辆需转为营运车辆、车证办理有数量限制,还有轴距、排量、车龄、车价等方面的不合理要求。不科学的准入门槛不利于市场新主体进入,不利于解决“一家独大”问题。由于网约车平台间竞争具有寡头化、动态化、跨界性以及大数据驱动等新特征,过高的准入门槛反而增加了少数寡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损害消费者权益的风险。2016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主要是为了进一步规范政府有关行为,防止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逐步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作为覆盖所有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行业和领域的重要举措,数字经济、平台经济领域各层级的政策措施都要对照审查标准进行公平竞争审查,评估对市场竞争的影响,防止排除、限制竞争。但现实中,因落实不够导致的一系列监管乱象也时有发生。准入门槛不合理、地方保护主义等一系列不合理的行政干预,反而可能会加剧数字经济领域的垄断风险。
第二,现行监管方式亟待调整,临时性集中执法、选择性执法或“一刀切”执法问题突出。现有的监管是以事前许可或备案为主、事中事后为辅的方式,面对海量商家涌入、跨界创新的常态化以及普遍的多平台经营等现象,事前监管不仅疲于应对,而且效果有限。现实中,一旦某个或某类平台企业出问题了,经媒体大肆炒作,行政主管部门就不得不出手干预,但其手段多为以约谈方式暂时压制负面舆论的扩散。以多家外卖平台出现的“补贴大战”以及“二选一”纠纷为例,当时涉案地方的工商部门联合公安、物价、食药监、商务等部门,对涉事平台开展行政指导,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如不得利用高额补贴抢占市场份额、不得实施“二选一”行为等。事后不仅引发不少争议,执法效果上也引发质疑,相关问题至今仍然频发。类似的问题在互联网金融、出行领域也较为常见。一些行政干预手段缺乏充分的法律支撑,“运动式”执法的色彩较为浓厚。
第三,监管效率不高,救济措施跟不上。现有的监管手段多是事后处罚,特别是严重依赖行政处罚的被动模式,不仅对涉事主体的惩戒效果不佳,而且难以有效理顺市场的自我进化机制。仅靠监管部门现有的力量和手段,在应对市场不规范行为的大量涌现上,容易导致监管低效,甚至直接影响主管部门的地位和威信。当前,我国在大数据治理、跨平台信用体系、网络精准监测等监管手段创新上还处于探索阶段。司法保护或救济措施的及时性、有效性往往不足,不能适应数字时代竞争司法救济的需求。企业即使最终在诉讼中胜诉,也可能陷于“赢了官司,输了市场”的窘境。从司法判例来看,赔偿力度不足、临时救济措施滞后等是当事人反映最为强烈的问题。
第四,对现有管理体制的挑战显现,特别是竞争执法机构与行业主管部门的协调配合问题突出。现有的体制架构大多是条块化和属地化的,各部门条块分割的监管体制造成“政出多门”,部门之间协调不够,甚至存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政策、标准要求等相抵触的现象。互联网平台上商家的经营活动往往是跨领域、跨地区的,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的监管力量根本无法应对,传统垂直监管模式已不能满足“互联网+”跨界融合发展的需要。在线上线下加速融合的趋势下,线下业务不断向线上扩展,原有的线下监管问题通过“互联网+”进一步放大,新业态如何界定,线上和线下管理部门如何划分职责和实现协同,都是新的监管难题。此外,竞争法与部门法之间的立法、执法协调也是长期困扰我国竞争执法的难题。
三、数字经济发展中反垄断规制的原则
平台垄断问题有其特殊性、复杂性,反垄断规制思路需要创新。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带来资源配置和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政府的传统监管模式面临较大冲击。当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与原有产业利益格局交织时,监管者往往难以确保政策和监管方式的弹性和有效性,由此导致生产关系调整(特别是监管体系的调整)明显滞后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因此,对这样一个新兴且存有不少争议的问题,明确一些基本的规制原则十分必要。
(一)坚持包容审慎,适度监管
監管部门首先必须客观认识平台的“大”,慎用反垄断法。数字时代快速变化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要求决策者和监管者深刻理解数字市场竞争动态、平台运作方式及其与传统经济的差异。要充分认识到:反垄断法“反”的不是垄断地位,而是损害公平竞争的垄断行为;反垄断法保护的是市场竞争,而非单纯地保护竞争者。在看待一些领域少数平台企业“一家独大”现象或评估相关案件时,应保持包容审慎的态度,特别要警惕仓促干预或过度执法对市场自然竞争“优胜劣汰”机制和创新激励机制的破坏。在面对一些数字平台涉嫌垄断但对动态竞争及消费者福利有利的行为时,即便这些利益难以被具体量化,执法者也应考虑采取“监管谦逊”的理念,即“冷却这些市场上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是所有监管者或竞争执法者应该做的最后一件事”[9]。若不同规则难以取舍,则优先选择对于各方主体利益有最大容忍度和包容度的规则,既保障创新利益和提供创新动力,又尽量减少对合理经营行为和商业模式的损害,避免对健康市场竞争机制造成扭曲。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监管机构对数字经济中平台企业已经存在的反竞争行为视而不见,而是恰恰相反。竞争政策及反垄断执法始终是弥补数字经济领域市场失灵、有效阻止平台企业反竞争行为的重要工具。必须看到数字平台的扩张并不会创造一个“新经济天堂”,毕竟存在不少负外部性和潜在危害。实际上,目前为止还很难找到完全不受政府干预或执法规制的任何发达市场。竞争执法机构的工作就是保证具有垄断地位或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不违反竞争规则,同时寻租者不能阻碍新平台的创新。政策制定者和执法者也应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掌握更全面的数字市场动态信息,并帮助消费者和所有平台用户获得更准确的信息,避免类似传统经济中那些网络效应较强的领域容易出现的“规制俘获”或可能的“监管套利”。
(二)坚持开放透明,协作监管
针对平台企业,包括竞争政策在内的监管政策都应处理好平台自身治理和政府或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这依赖于开放、透明的规则体系。必须认识到,在数字经济领域,过去业界推崇的“平台中立”原则并不客观。原因在于:技术(使用)很难中立,平台也难以以中立为目标,同时多数平台更难以成为反垄断法上的“关键必要设施”。有效监管拥有双重身份的平台,绝不能依赖于其难以实现的“中立性”,而应考虑“数据驱动的透明性和问责制的开放创新”原则[10]。建立和实施关于事后透明性的规定,可有力补充甚至代替传统以建立事前准入规则为主的监管方式,降低政策干预的成本和惰性,并鼓励创新。相应地,主管部门要重视数字平台的自我规范,考虑到动态竞争激烈的数字市场中平台的自我规范动力,特别是解决平台内竞争或其他负外部性问题,从而实现政府规制与平台治理有机结合。
(三)坚持灵活有序,高效监管
数字市场的竞争高度复杂、动态性强,很多破坏性创新基于数字平台巨大的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往往发展迅速。竞争执法机构也应当反应迅速,在不降低调查质量的基础上提高调查过程的效率,做到“灵活有序、趋利避害”。对此,GSMA的建议值得我国借鉴[11]:一是确定需马上启动的案件,若证据不支持进一步调查,应尽早结案;二是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加强信息收集,避免对企业增加额外负担;三是确保决策小组多采用外部技术或行业专家;四是尽量在执法初期促成和解,或让当事方作出承诺;五是制定严格时间表并严格执行。总之,执法部门需要审慎对待、及时响应,既要平衡速度和效果,又要平衡正当程序和失误风险。
四、数字经济发展中平台垄断的治理策略
针对数字时代的平台垄断治理,尽管现行反垄断法及其基本分析框架仍然是适用的,但必须深入考量一些新的因素(如网络效应、数据行为及算法治理等),并在具体竞争评估和执法实践中灵活适用。
(一)创新反垄断的分析工具和执法思路
第一,及时吸收新的经济理论,强化经济分析。针对数字时代的反垄断难题,应避免采取不适用的传统思路对数字市场运作方式、平台竞争发展动态预判后果,对传统经济或实体市场中没有先例的行为产生误判。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新特点增加了反垄断分析的复杂性,执法者既要善于运用广为接受的经济理论,又要对新的经济理论保持开放。此外,产学研、执法机构及法官应共同探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中的公共政策问题,鼓励跨领域、跨学科的沟通对话。针对数字经济领域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如算法合谋或数据滥用,更要加强经济学家、法学家及行业专家的交流与合作。
第二,围绕垄断地位认定、垄断行为取证、垄断规制工具等重点问题探索新的分析方法或实现方式。首先,在反垄断分析中,要弱化相对静态的市场结构及市场力量分析,更关注市场的进入壁垒变化或市场的可竞争性程度。即使有必要在特定的竞争评估中予以探讨,也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判断。其次,一些传统工具可能不再适用于数字平台企业。如传统的SSNIP测试方法应用到双边市场界定,惯用市场份额、HHI指数以及成本加成状况等定量指标来识别市场支配地位等。适当少用结构性指标和成本加成指标,更侧重对潜在竞争状况的分析,重视动态效率的抗辩机制。再次,加强对双边或多边平台的网络效应、价格结构、使用限制、平台差异化、用户多归属等特性的分析,建立相适应的标准工具。最后,尽可能减少对行为“本身违法”的预判,更多地采用“合理原则”,在分析行为的影响之后,再决定是否进行法律干预。
第三,结合数字平台竞争的新挑战,不断创新执法思路。数字经济呈现明显的数据、算法驱动型特征,在对涉嫌违法行为反竞争效果的认定过程中,数据、算法的权重应逐步提高。如数据资源已成为数字平台间竞争的核心关切:新进入者难以在短期内掌握足够多的数据,很难开展有效的市场竞争;垄断平台也可能利用大数据优势对用户实施分类管理,以及所谓的“一类价格歧视”,甚至可能滥用数据中的隐私信息,影响国家安全。德国联邦卡特尔局自2016年3月起启动对Facebook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调查,2019年2月作出正式裁决,核心就是将具有支配地位的平台经营者违法收集、合并、使用用户数据视为滥用行为,构成反垄断法上的“交易条件滥用”——这被不少业内专家认为极具创新性(将数据保护与垄断地位滥用结合)[12]。类似地,美国、法国、英国等多国监管机构均因Facebook的数据使用问题相继开展了严格的安全审查或反垄断调查。反垄断分析必须对数据的经济特性、数据使用的权利保护及数据竞争等开展深入分析,努力将大数据利用中的潜在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第四,重視行为影响和效果评估,更多采取“合理原则”,不作“有罪推定”。研究表明,直接通过判定市场结构实施反垄断的做法已经不大合适,对数字平台企业涉嫌垄断行为的规制将越来越依靠更加复杂的经济分析手段,特别是基于“行为-绩效”的实证分析。对于任何市场行为的竞争效果评估,都应回归市场现实与经济理性,把行为置于具体竞争环境下和具体市场当中进行考察,准确识别行为对竞争的影响,着重分析其对市场竞争机制是否造成损害。就数字经济、平台经济领域而言,在考察行为对竞争的综合效果时,应注意将创新和动态竞争纳入分析过程,避免机械适用传统垄断行为分析方法。同时,在对涉嫌违法行为的反竞争效果认定过程中,还需要在分析方法上把握好“反事实比对”的思路,个案中做好“若无测试”。数字经济环境下企业特定行为的竞争效果复杂,应将涉嫌违法行为影响下的市场竞争状况与假定涉嫌违法行为未发生时的市场竞争状况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判断涉嫌违法行为是否严重排除竞争或限制了竞争效果。
(二)分类对待、精准施策,关注潜在危害大的行为,增强反垄断法的威慑力
第一,对数字平台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类型的数字平台实行差别化监管,精准施策。若忽略数字平台的不同类型、不同功能属性、不同的行业领域以及发展阶段,就容易导致竞争评估发生严重误判。一方面,分析搜索引擎、社交网络、电商平台、移动支付和其他交易模式时,应对不同功能或类型的平台各个方面进行逐一详细分析。就网络零售、社交网络等不少行业领域而言,即便暂时的竞争有限,也不能确定这种情况属于临时的还是持久的;同时在高市场集中度情况下,行业创新的动力依然很强,那这种情况也是有效率的;这就将要求相应的行政干预应当克制,竞争执法应该主要针对那些反竞争效果已相对明确的市场行为。另一方面,针对同样的市场行为,对不同地位、不同发展阶段的数字平台应区别对待。如同样是补贴行为,对于在位的垄断平台而言可能是反竞争的,对新进入者可能是有利于竞争的。类似地,国内外不少竞争执法官员也认识到:一些反竞争行为在平台小的时候可能影响不大,但平台规模大了以后就要及时予以规制。此外,大型平台在推动经济社会的资源重组方面影响较大,对那些具有一定市场支配地位、公共品属性强的平台应加大关注力度。
第二,重点关注一些潜在危害大的反竞争行为,同时要有效区分反竞争行为和合理竞争行为。从不同类型平台来看,就搜索引擎平台而言,特别是那些水平搜索平台,竞争规制的重点应该是是否存在滥用或篡改排序权相关算法导致不合理的差别待遇。就社交网络平台而言,过度收集和使用用户数据近些年成为竞争关注焦点。就电商平台而言,关注重点应是买方力量的合理使用,搭售、捆绑及纵向限制问题,也应及时考虑近些年引发普遍担忧、隐蔽性极高的新型垄断协议——算法合谋等。另一方面,如果单就行为本身而言,从国内外实践看,数字经济领域的垄断行为主要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应重点加以对待。特别要警惕一些超大型数字平台将某个市场中已有的市场支配地位直接“传导”到其他相邻市场中,破坏相邻市场的良性竞争秩序或带来明显的用户锁定,实现所谓的“跨界垄断”。拥有数据与流量巨大优势的超大型平台,通过搭售、捆绑、排他性交易等行为,很容易将在某单一市场的支配地位,传导至其他市场,开展多领域生态布局。随着数据深度挖掘技术逐步成熟,平台传导行为更加多元化、隐蔽化与便利化。如欧盟委员会针对超大型数字平台采取同一主体多案并行的调查方案,通过多次重罚阻止超大型平台垄断力量的传导。总的来说,监管部门应对带来明显限制竞争、打压新进入者或侵犯用户利益的行为予以重点关注,对一些典型案件要及时查处,加大其违法成本,增强反垄断法的威慑力。当然,对一些争议较大的复杂问题,不宜预设结论,而应在具体分析中逐一分析,不作“有罪推定”,更多地将创新因素作为分析重点。
(三)针对数字经济的前沿问题加强立法或修法调研,加快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在反垄断相关配套立法、出台释法指南或今后必要修法时,应充分体现数字时代特征,使之更加适应现实发展需要。我国《反垄断法》已实施十年多,对许多新问题还需要在配套性规章、相关指南、规范性文件中加以针对性说明。总体来看,应进一步运用竞争政策,协调反垄断法多元的立法宗旨,确定反垄断法的实施边界、实施标准,约束新型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同时保护好企业创新的动力。具体来说,一是依托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和反垄断局,尽快发布并修订数字平台企业竞争中的垄断行为评估指南,研究《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中的适用性,明确反垄断执法标准等,使相关规制有法可依,从根本上避免“监管真空”。要加快推进与现有法律法规冲突的法条“修改废释”工作。二是在互联网信息服务、电子商务、交通运输新业态等典型领域,加快出台与现行竞争法、行业规章相配套的实施细则。针对当前垄断行为高发、社会高度关切的热点问题,要尽快研究制定专门性、可操作的市场行为规范或执法指南。三是统筹推动纵向与横向规章的体系化,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各部委行政法规体系化,明确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特别要强化竞争法与网络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专利法、价格法、电子商务法以及相关部门规章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四是加强市场发展监测研究,健全非正式規则体系。重视互联网平台治理应当适用的网络社会规范、自律公约、商业惯例、诚实信用原则等非正式规则,并赋予其约束力。
(四)提升反垄断机构层级,夯实反垄断执法能力建设
为进一步强化竞争政策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关键基础性地位,建议在新组建的国家反垄断局基础上,提升其决策层级和竞争执法的强制性。同时,考虑到当前反垄断执法资源、技术和人才队伍的紧迫挑战,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反垄断机构的编制数量,增加财政性经费支持力度。数字经济领域竞争执法面对的是具有强大势力、行为错综复杂的平台主体,加上社会关注度高,因而对办案人员的专业化水平要求很高。执法人员不仅要有深厚的法律知识,而且需要具备深厚的经济理论功底。相较于国外竞争执法机构,我国现有机构专业人才不足、执法资源有限等问题还较为突出。为加快提升我国新经济领域反垄断规制能力,应加大人才培养、人才引进力度和职业培训规划,在有条件的大学设置相应学科,夯实创新型执法人才的培养基础。同时,要充分利用社会化、第三方专业机构或智库的力量,不断拓展人才队伍和网络。与此同时,反垄断机构要持续加强专业能力建设,特别在监管技术升级、执法工具改进、外部专家队伍建设等方面予以充分重视。
(五)促进与国外主要反垄断司法辖区之间的合作
数字市场往往是跨地区、跨国家开展竞争,这就会产生管辖权问题以及执法协调问题。为此,处理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问题需要不同司法辖区反垄断执法机构之间的相互协作、配合。近些年,我国竞争执法机构在国际合作与协调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与不少国家的竞争执法部门签署了一系列执法合作协议。考虑到数字市场的特殊性和高度复杂性,建议反垄断局进一步考虑与美国、欧盟等重要反垄断司法辖区针对数字经济领域签署专门的执法合作双边协议[13]。同时,要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相适应,用国际视野和标准审视反垄断规制的效果,不断增强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提升数字平台综合监管的国际化水平。
参考文献
[1]冯然.竞争约束、运行范式与网络平台寡头垄断治理[J].改革,2017(5):106-113.
[2]OECD. The digital economy[R]. DAF/COMP 2012(22)(2012-12-07)[2013-02-07]. http://www.oecd.org/daf/competition/.
[3]DAVID S E.在線平台的动态竞争[M]//比较·第九十八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269-303.
[4]Directorate-General for internal policies of the Union (European Parliament). challenges for competition policy in a digitalized economy[R].(2015-07-15)[2015-08-16].https://publications.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592ad7c1-73bf-4061-8ad7-d3df7603a02e.
[5]阿里尔·扎拉奇,莫里斯·E.斯图克.算法的陷阱:超级平台、算法垄断与场景欺骗[M].余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6]KOREN W-E.多边平台的经济学分析及反垄断启示[J].竞争政策研究,2016(2):31-35.
[7]华强森,成政珉,王玮,等.中国数字经济如何引领全球新趋势[J].科技中国,2017(11):53-66.
[8]曲创,刘重阳.互联网平台经济的中国模式[J].财经问题研究,2018(9):10-14.
[9]丹尼尔·奥康纳.理解在线平台竞争:若干常见的误区[M]//时建中,张艳华.互联网产业的反垄断法与经济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132-165.
[10]GROSSMAN N.Regulation, the internet way: A Data-First model for establishing trust, safety and security-regulation reform for the 21st century city[R].(2015-04-01)[2015-04-08].https://datasmart.ash.harvard.edu/news/article/white-paper-regulation-the-internet-way-660.
[11]GSMA.Resetting competition policy Frameworks for the digital ecosystem[R]. (2016-10-01)[2016-11-15]. https://www.gsma.com/latinamerica/resources/ceg.
[12]宋迎,周万里.德国《竞争政策:数字市场的挑战》调研报告介评[M]//韩伟.数字市场竞争政策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54-95.
[13]张嫚.论数字产业对传统反垄断理论与实践的启示[J].经济评论,2002(4):103-106.
Abstract: The dispute of anti-monopoly against the digital platform oligarch has been constantly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rise of a large number of digital platforms in China has greatly improved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social welfare, but also brought many new challenges of public governance. Regulatory problems caused by platform monopoly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while the traditional antitrust analysis standard as well as the way of law enforcement and supervision system needed to be reformed. It is critical to comply with the development law of digital economy and platform economy, maximize innovation and effectively protect consumers. Thus,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inclusive, prudent, open, transparent, flexible and orderly regulation, together with taking multipl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anti-monopoly regulatory system and enhancing the regulatory capacity.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platform economy; anti-monopoly; regulation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