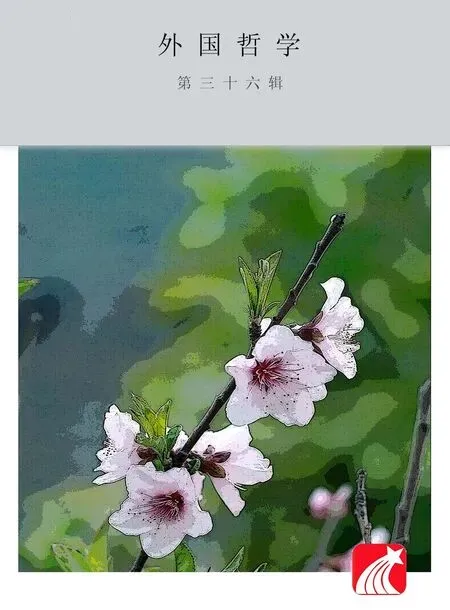哲学中的对话
——与戴卡琳教授商榷
何狄穆(Tim Heysse) 著
张楠、张尧程** 译
在《欧洲大学中的“中国哲学”:三种面向的“无”托邦》一文中,戴卡琳教授批评欧洲大学在制度上对于中国及其他“非西方”地区系统性地排挤。在文中,她以鲁汶大学的历史学系和哲学学院(我本人很荣幸地就在这所学院中工作)为例,来佐证她的发现。我的能力大概并不足以回应戴卡琳所提出的诸多重要问题。我正好处于Schwitzgebel 所说的“恶性循环”当中—既对非西方哲学一无所知,又缺乏相应的语言能力。因此,关于非西方文献的讨论,我确实无法从哲学专业的角度加以评析。然而,在戴卡琳教授的文章中我还是找到了可以回应的部分。戴卡琳在她文章的结尾提出了若干建议;这些建议牵涉到更大的议题,其中包括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因此,除了简要回应一些鲁汶大学哲学院在学制设置上的细节问题,我在本文中主要想质疑戴卡琳在哲学、政治关系上抱持的观点①这并不意味戴卡琳教授在媒体上试图揭露此问题时所遭遇的封锁就是对的。参见戴卡琳教授在她《欧洲大学中的“中国哲学”:三种面向的“无”托邦》文中1.2“未成为讨论对象的研究场所‘欧洲’”部分以及该文第16 条尾注(见本书第81 页注释①)所提到的。,并试着将讨论引向一个用来支持中国哲学或其他非西方哲学的可能更有道理的论述。
戴卡琳教授在她文章中所不满的是,以地区、语言为导向的“非西方”研究,以及人文、社科领域的学科专业之间存在着一道藩篱,欧洲大学学制在这两者之间设下了一条太深的鸿沟。为了刻画这个学制上的藩篱,她举鲁汶大学历史学系的现况为例。确实,那些研究非西方文献的学者,会因为学术体制的划分而在学科领域的夹缝之间生存不易(特别是在寻求研究资助、出版著作以及在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时候)。不过,戴卡琳的主要关切点还是在教育方面。在现有学制下,那些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或历史感兴趣的学生,大可以在欠缺中文能力的情况下(例如进入历史系学习),或欠缺相应研究方法的情形下(例如进入汉语系学习),依然完成学业。
我无法断定这样的藩篱是否真实存在,虽然我也没有什么理由去支持这份质疑。不过,我认为,对于以三年为期的本科学制而言,要求学生去掌握那些研读非西方文献时所需的语言能力和背景知识,实在是有些强人所难。毕竟,鲁汶大学在各领域都设有所谓的“衔接学程”①例如,可以参见http://www.kuleuven.be/toekomstigestudenten/publicaties/.html (2016年11月26日访问)。;获有中文学士或日文学士等学位的学生可借此直接就读政治科学的硕士学位课,而不用另外取得相关的学士学位。或例如在哲学系,已经有其他学士学位的学生亦可以再花一年的时间取得哲学学士学位。
戴卡琳教授主要关切的是例如鲁汶大学哲学院这样的哲学院系的现况。她在此一问题上深刻又锐利的评论确实无可辩驳。虽然鲁汶大学的哲学学院开设了非西方哲学方面的选修课程,但是这里的学生确实亦可在不研习这些课程的情况下顺利毕业。而这里的硕士生虽然也可以选择非西方哲学的题目来撰写毕业论文,但她们很大程度上就只能仰赖自己,因为鲁汶大学缺乏相应的师资,来指导这类论文的写作。
然而,哲学院也正开始朝着戴卡琳教授建议的方向有所改进。有鉴于研究非西方哲学的人员仅占教研人员委任总数的一小部分,例如将1/10 聘雇一名教授的经费用在阿拉伯哲学研究上,我院开始修正一些可能有误导性的措辞。例如我们在院系网站上将自己营销成一个“全面性”的哲学学系,涵盖“哲学研究中的各类领域”。这一点被戴卡琳精心挑出并被批评为名不副实。虽然我们原先想表达的仅仅只是学生可以在鲁汶大学哲学院内同时学习到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但是这样的表述确实有可能误导读者,仿佛我们学院把非西方的思想都排除在“哲学”的定义之外。所以,我院在2016年的“教学目标要点”中明确承认我院提供的教学内容仅限于西方哲学,同时并不否认非西方哲学的存在和重要性。①参见https://www.kuleuven.be/onderwijs/cobra/portaal/2015/nl/visies/facultaire- onderwijsvisie-enbeleidsplan-hoger.pdf (2016年11月26日访问)。
对于非西方哲学的支持者们而言,这些措辞上的改变显得太微不足道,来得又太迟。在他们看来,我在第一段中所坦承的对非西方思想及语言的无知,恰恰反映了哲学院中教研人员的典型情况。就事实而论,他们是对的。但是,我对此还有两点补充。首先,我绝不认为那些我不知道的事物就不值得去了解。例如,我很希望能够对戴卡琳教授在她文中列举的那一长串中国哲学家有进一步的了解(“下列先贤或著作在哲学院一律无人问津:他们之中包括孔子、墨子、孟子……”)—诚然,我们不应该在定义“哲学”一词时,把这些人排除在外。其次,我希望自己能知道的东西不计其数,但我们不可能了解一切事物。每一个从事哲学、历史学或其他人文学科研究的人都应该会坦承自己某方面的无知:或者是对那些值得了解的材料一无所知,或者是没有时间读遍那些值得研究的书籍或画作;如是种种,不一而足。因此,我对于非西方哲学及其语言的无知虽是难辞其咎,却也是不可避免。
然而,对于戴卡琳教授而言,哲学系的情况却是在另一个意义上难辞其咎:非西方哲学在欧洲大学哲学院系中遭受到的悲惨境遇起于不公正的排挤和不理性的抵制。在发觉理性论辩“纯属徒劳”之后,在我看来,戴卡琳不再期望能在这个议题上进行理性讨论。这一点在她文章的发展上也看得出来。在她文章的开端部分(1.1 节),戴卡琳列举出支持中国哲学的七种论述。而到了文章结尾,她的要求只剩下政治方面的论述—多元价值的维护、对于“他者”的尊重,以及中国与印度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哲学性或思辨性的论述都被弃之不顾。因此,在她结尾部分的建言中,戴卡琳呼吁政治性的干预,希望透过政治力量的介入来促使哲学学院“接纳非西方思想”。
透过呼吁政治干预并将讨论停留在政治层面上,戴卡琳教授凸显了一个常被哲学家忽略的张力,这个张力恰恰体现在组成我院名称的两个字眼之上:“学院”和“哲学”。①学院的全名译为“哲学高等研究院”,它在原先作为该学院教学语言的法语中被称作“Institut Supérieur de”。作为一个教育机构,鲁汶哲学学院是公民教育系统的一环,而这个教育系统是公共于全体公民的。这意味着,用以维持该系统运作的资金几乎都来自弗兰德斯地区政府税收。因此,无论是哲学学院自身,还是其所提供的教育,都不可避免带有政治考虑。此外,考虑到弗兰德斯当地的政府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这个政府有权强制推行一些经民意一致通过的政治举措。戴卡琳教授的一些建议,包括强制我院雇佣特定员工或开设某些课程,就属于此列。
作为一个认同民主价值的公民以及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中的公职人员,我必须接受哲学学院在大的原则上应配合政府政策。但同时,作为一个有幸获取教职的哲学学者,我又不得不反对政治力量过分介入哲学研究。虽然政府大部分的政治作为在哲学上都饶富趣味,但哲学议题或哲学文献的重要性却不该由国家政策单方面决定。作为一个哲学家,我深信并捍卫哲学的独立性。
不过,我们应该谨慎一点,不要用那种传统的论调来看待独立性的概念。传统的论调认为哲学之所以独立于政治权力,乃是由于哲学只为普遍的理性发声。在戴卡琳教授看来,持有这种观点的正是她的一些反对者;这些人声称自己“拥有开放的心灵”,从事着“不分地域”的研究工作“并致力于突破局限”。戴卡琳正确地对如下一点做出质疑:既然这些人把哲学理解为一个追求普遍知识的事业,那么他们又有什么理由把非西方哲学从哲学领域中排除出去?
这种老掉牙的论调并不是我所理解的哲学。我认为,哲学的历史实际上并不全然是一个理性而开放的过程:它部分地受“操作学术体制而闭门自守”影响,也受到那些决定众人研究走向的“主流的学科典范、福柯所谓的‘真理政权’(regime of truth)以及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谓的‘象征暴力’(symbolic violence)”影响。此外,这一过程中也有民族中心主义的一面。尽管哲学总是试图与掌控国家与公共讨论的人保持一定距离,并时不时地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西方哲学毕竟是欧洲历史的一部分,其中当然也包括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我无意为上面描绘的哲学形象进行辩护,但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哲学唯有在某种形式的独立性之上才能够获得价值。这种独立性正是米歇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所阐述的对话的独立性①参见Michael Oakeshott, “The Study of ‘Politics’ in a University: An Essay in ppropriateness”和“The Voice of Poetry in the Conversation of Mankind”, in Michael Oakeshott,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new and expanded edition,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91。。根据奥克肖特的观点,对话是多种声音的交汇之处;在其中,不同的声音与话语“相互承认”。②Michael Oakeshott, “The Voice of Poetry in the Conversation of Mankind”, in Michael Oakeshott,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new and expanded edition, p.198.诚然,奥克肖特认为人类文明中的对话是由一些反映人类活动的基本话语所组成:这些基本的话语类型包括社会实践、科学、诗歌及历史。但我认为组成人类对话的话语类型不止以上四项。人类文明中的对话也不止一种模式,不同模式的对话不间断地在各个地方同时发生。如此一来,“对话”一词除了可以用来描述人类文明的整体历史,同时也可以描绘那些整体历史底下更为具体的个别历史,例如艺术史、文学史或哲学史,甚至是某个特定地区的哲学史。一旦“不同话语的特殊之处”失去了它的多样性,这样的对话恐怕都将不复存在。哲学作为一种对话,也必须包含各种不同的声音才得以成立(戴卡琳教授所刻画的“典型西方”“部分西方”“非西方”之间的不同也是其中一种多元性)。
而在一场对话之中,每一个参与者也都有他“适合发声的时机”。曾经在上一场对话中成功的(例如妙语如珠地转变话题、鞭辟入里的分析或雷厉风行的批评),在下一场对话中或许不再有同样的效果。在对话中,一个特殊的话语之所以“有道理”,正是因为这个话语应时而发,并开启了特定的对话方向。①Michael Oakeshott, “The Voice of Poetry in the Conversation of Mankind”, in Michael Oakeshott,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new and expanded edition, p.198.时机的适切与否,便构成了“对话的规范性”;一时适当的表述,以后可能不再适当。然而,此一规范性亦尊重不同的声音。这种规范性“不要求也不认为一种声音会吞没另一种声音”;它也不认为在对话中只能有单一的目标(例如发现真理、证明某一结论等)或单一的标准:
不存在主持人,亦没有仲裁者,更没有谁会去把关你发言的资格。每位参与者的价值皆由他们具体的表现而定。只要能在思绪的湍水中一同流动,任何话语都能够被接受。各类声音不分贵贱,高低无别。②Ibid.
为了理解哲学在政治之外的独立性,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对话的规范性。首先,奥克肖特虽然说各类声音无贵贱之分,都有发言的资格,但这并不意味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到对话之中。大多数的对话都是由“特定圈子内的成员”所进行(例如,太太们在茶会上对话时,负责倒茶的男仆并不能参与其中)。再者,一个对话的成功与否只取决于对话中的内在因素。它的成功仰赖于那些在对话中能够引起他人兴趣并进而获得接受的修辞性力量。正是言语所能唤起的他人的兴趣,使得对话的发生得以可能,进而左右对话的走向。对话的规范性与修辞的作用紧密相关,它其实是一种与兴趣相关的规范性。
正是这个与兴趣相关的规范性确保了对话得以独立于权力之外。无论多么大的政治权力,也无法贸然介入对话之中,在它身上强加话题,甚或决定对话的走向。权力能做到的只不过是中断对话或带来尴尬的沉默。当然,把哲学的发展史视作一场对话,并不是要否认哲学的政治性,以及它在闭门自守、制度性排斥以及其他权力机制下所受到的影响。这个观点所要强调的是:一个主题唯有通过成功引起哲学家们的兴趣才能真正参与到哲学对话之中。话题、想法或论述也只有当它们在哲学中找到听众时才能真正开启与他人的对话。这个缓慢的过程有时需要一两个世代的时间,其中也不乏对异己观点的排斥和打压。即使在理想的情况中每个人都能参与到对话,也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够谈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或是把对话引导到他们喜欢的方向。因此,基于政治现实或社会伦理的考虑,我们固然可以动用政治权力强迫一个哲学院系接纳中国哲学。但是这样的强加却依然无法让中国哲学凭借自身真正地进入到哲学当前的对话之中。
坚持哲学作为一种对话的独立性,并不必然地与戴卡琳教授的建议产生冲突:雇用非西方研究的专家,以及开设非西方哲学方面的必修课不必然会威胁到哲学的独立性。因此让人惊异的是,像她对中国哲学这么了解的专家,竟会在论证中有这么明显的疏失;除了政治层面的论述之外,戴卡琳甚少展开哲学层面的论述。她在哲学层面所提到的论述只是宽泛地提到非西方思想与文献有其毋庸置疑的价值,与陌生思想(“他者”)的接触十分有益,有助于我们发现自身文化中所固有的预设并促使我们反思自己。①研习非西方哲学,是获得这类反思的最好方式吗?一门严苛的形式逻辑课程肯定可以迫使哲学系新生“脱离舒适圈”。我们不应该不假思索地认为只有在接触异域思想的时候才能对自己原先的信念产生怀疑和反思。
支持非西方哲学的一方需要产出更具体的论述来激起哲学家们对它们的兴趣。我们现在确实也已经有了这样的论述。以最近的两项研究为例,Richard Kim 展示了当代道德心理学是如何与当下的早期儒学研究相互影响的。②Richard Kim, “Early Confucianism and Contemporary Moral Psychology”, Philosophy Compass, 11(9),2016, p.474.Polycarp Ikuenobe 则透过非洲思想的视角,提出了一个更加强调社群共同体与责任而非个人权利的“尊严”概念。①Polycarp A.Ikuenobe, “The Communal Basis for Moral Dignity: An African Perspective”, Philosophical Papers, 45(3), 2016.另可参见David B.Wong,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Status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U.S.Graduate Programs”, APA Newsletter on Asian and Asian-American Philosophers and Philosophies,15(2), 2016, pp.9-10。
诚然,对当今的哲学家而言,有很多话题是他们不太明白该如何去讨论的。然而,只要能够推动原地踏步已久的对话再一次前行,不仅新颖的观点、概念、见解和论述可以获得讨论的空间,甚至那些旧的观点、概念、见解和论述也不会再被轻易忽视。但为了促成这一结果,这些新旧观点需要在哲学界捕获自己的听众,将对话再一次地引导至新方向。一旦达成了这一点,并且非西方思想也能够证明它确实保有能丰富哲学对话的可能,那么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想要去学习非西方思想,以及研究这些思想所需的语言技巧和专业知识。这个时候,哲学教授们个人的研究兴趣便已是无足轻重。这个时候,学院一定会添加关于非西方思想的课程,但这并不是政治力量的介入所致,乃是因为哲学的对话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