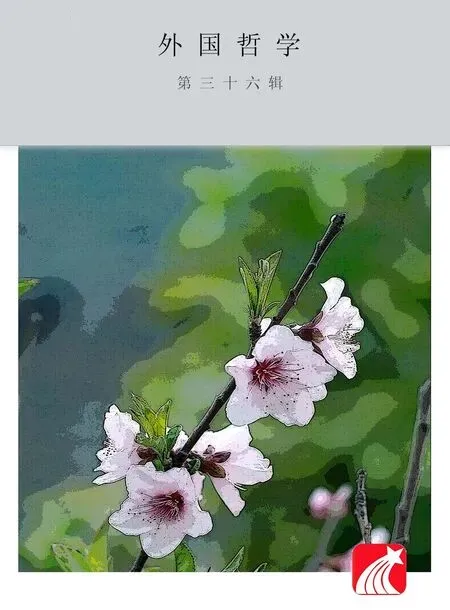洪谦先生及其学术思想*
赵星宇
一、人生轨迹
洪谦先生,祖籍安徽歙县,1909年生于一个徽商世家。由于幼年丧母、父亲新娶,他随叔父前往福建省福州市生活,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时代。据其长子洪元颐先生讲述,洪谦先生在早年接受的是传统的私塾教育,但启蒙老师是位学贯中西的开明先生,能够同时传授四书五经与西洋文化,深刻影响了他此后的外语学习和留学生涯。在这位老师的指导下,少年洪谦便在当时著名的学术杂志《学衡》上发表文章,获得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的赞誉。1922年,他被推荐到日本,跟随儒学学者宇野哲人学习王阳明哲学,可惜年纪尚幼,身体抱恙,他于1923年放弃了学业。回国之后,他来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接受了新式思想的启发,在康有为、梁启超的鼓励下于1927年再次启程,赴德国耶拿大学留学。
青年洪谦先后转学至柏林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学习数学、物理等理科方面的课程。在一次讨论中,他发表了关于王阳明哲学思想的演讲,吸引了维也纳学派核心人物石里克的注意。自此之后,他有机会参与到维也纳小组的讨论,有幸成为其中唯一一位中国学者,以及分析哲学早期发展的亲历者。在石里克的指导下,洪谦于1934年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问题》,并得到著名量子物理学家海森堡的审阅和肯定。但遗憾的是,当时欧洲局势动荡,石里克遭到学生枪杀,洪谦不得不在石里克女儿的帮助下匆匆前往苏联。在那里,却遭遇了当时正在进行的肃反和戒严,历经波折才辗转回国。
国内形势同样紧张,他先受聘于清华大学,后在战乱中随西南联大前往重庆、贵州和昆明等地,流离之际看到了祖国的满目疮痍。据洪元颐先生回忆,他父亲曾提到他在天津遭到了侵略者的殴打,在重庆经历了长时间的空袭。尽管少年时曾游历日本,但自此对这一民族失去了好感。有幸的是,他在战乱中结识了从事分析化学的科学家何玉贞女士,二人在贵阳医学院院长的主持下结为连理。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应维也纳学派成员魏斯曼的邀请,前往牛津大学新学院任教。在这段时间里,家人曾试图前往英国,却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扣押。1947年,他才终于回到祖国与亲人团聚。
洪谦先生为人耿直严肃,在政治上并不敏感。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曾任职于外交部对外文化协会,不久便由于不了解形势、言辞直率被调离,随后赴燕京大学哲学系担任负责人,又在院系调整中来到北京大学哲学系。20世纪50年代起,他着力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些外国哲学评述结合起来。例如他在《康德的星云假说的哲学意义—读〈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的一些理解》中,介绍康德如何从自然历史发展的角度为科学的宇宙起源论奠定基础,又巧妙解释了这一理论蕴含了哪些朴素的唯物论、发展观以及辩证法要素。
1957年,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不要害怕唯心主义》与《应该重视西方哲学史研究》,强调研究西方思想的重要意义,呼吁不要重中轻外。但是,正是这两篇不失偏颇文章,导致了洪谦先生此后学术生涯的沉寂。由于反潮流的敏感内容,他受到了较为集中的批判,曾为此离家出走并寻短见。20世纪60年代,他遭到了来自外交部工作人员的审查和殴打,所幸受到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隆基先生的保护与告诫才免于受进一步冲击。因为一生在辗转颠簸中求学、任教,不参加任何学术、政治上的斗争,也不是任何党派的成员,洪谦先生被人称为“流荡的教授”。
由于时代所限,他回国后的大部分工作限于编译,以及对西方哲学史与维也纳学派思想的介绍与阐发。一系列西方哲学著作在他的主持、组织和参与下翻译完成,其中包括《逻辑经验主义》《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包括:《古希腊罗马哲学》《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等。1980年以后,洪谦先生也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如《论“确证”》《关于逻辑经验主义的几个基本问题》,以及《评石里克的〈哲学诸问题及其相互关联〉》。但是,其中观点多是已有思想的阐发与综述,许多创见被埋没在了时代的洪流里。
有幸的是,改革开放后,他有机会再次发挥自身所长,积极投身到国际学术交流中。1980年至 1984年间,年过七旬的洪谦先生三次访问维也纳大学与牛津大学,出席第五届国际维特根斯坦讨论会,以及石里克与纽拉特哲学讨论会,发表会议论文Wittgenstein und Schlick;1986年访问东京大学,发表演讲《关于逻辑经验主义》;1988年访问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了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会议。他将一些经历写在《欧洲哲学见闻》中,向国内学界介绍了当时国际上哲学发展的新趋势。
在洪谦先生的描述中,此时的他对欧洲已完全陌生,维也纳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现象学、存在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思想占据。而他所熟悉的逻辑经验主义传统,结合了新的逻辑学和科学成果,在格拉茨大学形成了一个新的分析哲学学派。关于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则是当时的热点,但令他惊讶的是,曾经没有被分析哲学足够重视的伦理学成了重点讨论的对象。伦理学的应用范围和可能性得到了新的评估,义务、责任这些传统议题获得了新的定义,决策论、行动论和道义逻辑被创立和发展出来。
在生命最后几年的岁月中,洪谦先生仍不忘悉心培养下一代学子。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他借助自己的国际声望与影响力,于1987年参与创办了中英暑期哲学学院,担任名誉院长至1992年去世。截至2018年,该学院已举办22 届,国内新一代从事外国哲学研究的青年学者都曾受益于此。
二、洪谦先生与维也纳学派
1.洪谦先生与石里克
在学术方面对洪谦先生影响最大的人物,无疑是他的老师石里克。在洪谦先生长子洪元颐的回忆中,他的父亲常常提起恩师的帮助和教诲,他不仅在学术和语言学习上对青年洪谦进行辅导,还让他作为其代表出席一些重要的学术活动,甚至在洪谦先生患胃病期间邀请他到瑞士家中休养一年。毕业后,青年洪谦留在维也纳大学担任助教,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在这段时期里,他在石里克的引荐下结识了一些学术界名士,同时受到了维也纳学派中流行的左派思潮的影响。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学者的持续关注,洪谦先生才得以在回国后的历次运动中保全下来。
可惜的是,石里克对他的培养于1936年戛然而止,尽管石里克并不是犹太人,却死于一个有精神问题的纳粹学生之手。回国之后,洪谦先生撰写了数篇关于石里克的文章,如《石里克与现代经验论》《维特根斯坦与石里克》等。在他最先出版的著作《维也纳学派哲学》中,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石里克的认识论,甚至是较少被人关注的人生哲学。1989年,80 岁高龄的他还撰写了《评石里克的〈哲学诸问题及其相互关联〉》,发表于英国学术期刊Ratio上。
在认识论方面,洪谦先生对石里克《普通认识论》一书的第一、二版进行了详细比较,指出了石里克在“批判实在论”时期与“逻辑经验论”时期的连贯性。他介绍,在石里克看来哲学就是对认识论问题的解决,分析科学命题,探讨其中概念的逻辑意义。传统形而上学中的许多困难都来自于哲学家没有清楚区分直观的对象与知识的对象,前者在于体验内容,而后者在于构造形式。立足于直观的知识观念是问题重重的,例如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与关于空间的说明,马赫等人通过“感觉的复合”为科学实在进行证实等。有人认为,石里克的真理符合论谈及的是思想与客体的符合,但洪谦先生澄清道,实际上这是判断与事实的一致。他举例,命题“光是由加速波的微粒形成的”就是一个难以与事实相符合的判断,因为波动说与微粒说根本属于两套理论系统。
在人生哲学方面,石里克的思想被洪谦先生总结为一种“乐观论”,最核心的概念在于“游艺”(das Spiel,或译为:游戏)。这一想法虽脱胎于席勒,但石里克对它别有一番论述,即:人生中的空虚和悖谬,大多来自目的的达成或不可达成;游艺之所以可贵,之所以能够体现人生意义,在于它是一种能够将行动的手段、价值及其目的结合在一起的特殊活动。在游艺中,人类对目的的执着得以弱化或消解,而与之相呼应的状态是哲学家们汲汲以求的至美(艺术之美从纯粹对象的状态里解脱出来)、至乐(人的“青春化”)与至善(善行出自自发的状态,而非迎合外在的目标)。它们并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具有某种“天赋的”价值,而仅仅在于,其内容本身就能够充实人类的精神生活,使他们“乐趣的感觉”得到满足。
也许正是继承了石里克这样的乐观理念,洪谦先生才得以在流离的一生中葆有对生命和学术的热诚,并相信对知识的追求并不在于它能够作为维持生存的工具,而在于“一切科学文化的进展,都是人类精神游艺的结果:科学家竭其终生之力从事探索宇宙之谜而不以所得为念者,就是这个游艺的人生观的表现,就是这个游艺的人生观对于人类的贡献:人类整个文化的进展与前途,都是靠这个人生哲学而产生的”①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载韩林合编:《洪谦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 页。。可以看到,对知识的探求也可以被当成一种自由的“游艺”,科学探究与哲学工作本身就是对至真境界的追求。
一些观点认为,作为学生的洪谦先生毫无反驳地接纳着石里克的全部思想,但实际上,他认真思考过后者思想中的漏洞,可惜没有机会得到展开。这些思考源自石里克与维也纳学派其他成员的一些分歧。他记述道,石里克对学派中一些“相对主义”的观点有所不满,他试图为科学系统找到坚实可靠的基础,并主张科学系统要建立在确证的基础上(因为确证提供的陈述能够反映人们对事态的领悟)。卡尔纳普、纽拉特所支持的真理融贯论没能得到石里克的认可,后者认为融贯论是向约定论的倒退,背离了经验论的主张。
洪谦先生为此提供过一个谦逊而简单的反驳,并指出自己的困惑,即:尽管石里克一再强调唯我论与感觉经验论的诸多问题,但他坚持的真理符合论可能最终会面临与前两种理论相同的问题。那些融贯论者将记录句(protocol sentences)作为科学的基本陈述,是有所述说的,但石里克只对何为“确证”有所述说,终其一生也没有言明何为“确证的陈述”,就将之视为科学系统的基本陈述。而且,“石里克关于确证的见解似乎同他关于‘认识’和‘体验’的理论以及他的形式和内容学说不能相容。因为不存在直接的知识这一类东西,而且所有有意义的陈述有可能全都是假的”①洪谦:《论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74 页。。
2.洪谦先生与卡尔纳普
卡尔纳普也是令洪谦先生毕生难忘的师长之一,他们都曾就读于耶拿大学,并在数学物理实验室工作。卡尔纳普曾在1928年起教授青年洪谦数理逻辑,并组织了关于罗素《数学哲学导论》和弗雷格《算术基础》的讨论(在当时,弗雷格还不是一位受人关注的哲学家)。洪谦先生认为,虽然维特根斯坦对维也纳学派的影响颇深,但卡尔纳普的思想资源实际上来自于塔尔斯基。例如,反对维特根斯坦早期关于神秘的观点,以及句子的意义只能通过句子自身“显示”出来的看法。他主张,语言既能阐明逻辑结构,也能反映实在意义,还能够根据元语言构造纯形式的陈述理论。塔尔斯基的真理观强化了卡尔纳普构造形式化语言的信心,并促使他将研究的重心从逻辑句法转向了语义学研究。
与洪谦先生和石里克主张的真理符合论不同,卡尔纳普秉持的是真理融贯论,即:对真系统的选择可以在摹状句法的范围内实现,而不依靠任何内部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卡尔纳普的物理主义批判》中,洪谦先生还批评了他的“方法的唯物论”不够彻底,以及物理主义中包含了反唯物论的观点等。这些批判既有完成政治任务的意味,也是他们观点上真正的分歧。但与洪谦先生志趣相投的是,卡尔纳普在定居美国后也开始了概率方面的研究,不仅批判了赖欣巴哈、米塞斯的“相对频率论”(theory of relative frequency),也批判了维特根斯坦、魏斯曼的“逻辑值域论”(theory of logical range),并区分了统计概率与逻辑概率。
洪谦先生还认同卡尔纳普的一些政治观点,这是由于他们同维也纳学派的大多数成员一样都是社会主义者,也受到了来自石里克与罗素自由观的影响。由于局势动荡和对纳粹的憎恶,卡尔纳普于1935年从布拉格离开前往美国,洪谦先生也在不久后离开欧洲。此后,二人保持着书信往来,卡尔纳普甚至将自己的每一本著作都寄给他。在写给洪谦的信中他提到,自己厌恶越战,反对独裁专制和种族歧视,还参加了一次营救黑人哲学家的活动。他认为,哲学家不应受政治目的的左右,否则对事物的观察就难以采取客观中立的立场。卡尔纳普还提出了一种“科学的人道主义”政治观,即:终有一天“人类摆脱了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正确而合理地创造美好的社会”①洪谦:《论逻辑经验主义》,第227 页。。这一理想在洪谦先生看来有些乐观而天真,但又十分认可他的理想与初衷。
不过遗憾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禁止与国外通信,1978年他才从费格尔那里再次获得卡尔纳普的消息,得知的却是他已于1970年逝世。在与哈勒的访谈中他还谈到,他们的熟识其实是通过后来成为卡尔纳普妻子的斯托格女士,她曾在语言和专业上给予青年洪谦巨大帮助。但同样令人遗憾的是,斯托格女士已于洛杉矶自杀,洪谦先生无从了解此事的真假,也难以确认她自杀的真正动机,只能时常以感激而悲伤的心情怀念她。
3.洪谦先生与艾耶尔
艾耶尔也曾在哲学家赖尔的介绍下赴维也纳大学进修,与洪谦先生结识。不过他于1932年左右就返回英国任教,未能坚持参与小组的讨论,因此他们的互动更多是学术上的交流。在由Lewis Edwin Hahn 编纂的“在世哲学家丛书”第21 卷中,分别收录了洪谦先生的评论《艾耶尔和维也纳学派》,以及艾耶尔对他的回应《答洪谦》。
洪谦先生认为,在《语言、真理和逻辑》一书中,艾耶尔虽然论述逻辑实证论,但结合了剑桥分析学派的观点。这导致的结果是,尽管他从维也纳小组中吸取了许多思想资源,观点却大相径庭。例如,艾耶尔不接受卡尔纳普的“确认代替证实”而提出了两类证实原则(当且仅当经验确定命题为真的“强证实原则”和只要求观察与决定命题真假相关的“弱证实原则”,并强调没有命题能够在强的意义上被证实),以及反对石里克将功利主义作为伦理学哲学的基础,主张价值的情感理论。在评论中,洪谦指出了艾耶尔的一些问题,例如:艾耶尔认为石里克的科学观退回到了马赫的观点,但在重申关于感觉经验的观点时,他自己也退到了马赫的要素学说与罗素的构造论。另外,艾耶尔在后期提出道德事实的特殊性,但未能给出一个充分的论证。
艾耶尔在给洪谦的回应中对自己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补充。首先,他认为石里克关于“证实的可能性”的表述有一个严重缺陷,即它能否分别对应说话者、听话者和观察者。如果能够对应,则必须接受种种限制。维也纳学派的证实原则更多是来自维特根斯坦的精神,而非其文本。维特根斯坦没有表明《逻辑哲学论》中的“对象”概念是在感觉材料的意义上可观察的,也不会容纳卡尔纳普和自己所主张的弱证实原则。其次,艾耶尔指出洪谦先生不应把中立一元论的立场—外部世界是感觉材料的逻辑构造—的观点归诸于他,因为他已经得出了现象主义站不住脚的结论。尽管自己忠实于感觉材料理论,但并不像大部分感觉材料论者主张的那样以“私人性”实体作为出发点,而且他强调经验的私人性并不妨碍经验的可交流性,“公共”和“私人”的区分其实是一种浅薄的处理。
不过艾耶尔认为,洪谦和自己在以下几个观点上达成了共识:第一,拒绝真理融贯论。洪谦先生肯定艾耶尔关于真理符合论的论证,同意在关于哲学陈述换位为形式结点的过程中,把陈述解释作“语义陈述”,而非卡尔纳普所假定的“句法陈述”。第二,没有物理陈述能够在逻辑上等价于心理陈述。不过艾耶尔对此进一步的想法是,精神状态和脑状态并没有超出因果依赖以外的关系,因为称二者同一但两个类型又非一一对应,这是难以理解的。
1989年艾耶尔去世,洪谦先生撰文悼念。他十分肯定英国哲学家斯特劳森的评价,即艾耶尔是一位“反偶像论者”。洪谦先生认为艾耶尔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从来没有全盘接受某个学派的观点,无论是石里克、卡尔纳普,还是他的老师赖尔,更没有像许多研究者那样神化维特根斯坦,而是对他们的著作进行批判的考察。这一点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做到,一生继承并笃信石里克的思想,少有反驳。更令洪谦先生尊敬的是,艾耶尔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是积极的:他终生致力于对自由事业的促进,在濒危之际仍笔耕不辍,撰文赞扬法国大革命中的民主精神。
三、洪谦先生的理论贡献
1.关于因果律与量子物理学的新见解
从博士阶段起,洪谦先生就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即:海森堡所描述的“不确定关系”能否重构人们关于因果律的理解?1929年雨果·伯格曼提出了对物理学中非决定论观点的反对意见,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讨论。洪谦先生的博士毕业论文《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问题》对此进行了回应,他认为通过决定论或非决定论为自然规律奠定基础是不可能的。回国之后,他继续对量子物理学中“因果律失效”的哲学意义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与之相关的其他议题,如自由意志与时间哲学等。
洪谦先生认为,自己关于因果原则的主张类似于休谟的观点,即因果律并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它的存在只具有实践意义,不能作为任何理论的预设。因果原则也不是一种自然规律,而是一种表达方式,用以刻画自然界中存在的规律。只有自然规则存在,因果陈述的内容才得以成立,因果性才能够表述某种现实。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根据自然规则来了解因果律,但不能断定因果的必然性,或认可因果律能够支配一切。对因果律的传统定义都过分突出了它的形式标准,但真正要重视的是,因果律与实际命题的联系,以及因果命题是否有实际的内容。它的实际的标准在于“预说的言中”(das Eintreffen der Voraussagen),即“所推论的能否有经验的证实,所预说的能否有事实的相符”①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载韩林合编:《洪谦选集》,第58 页。。但是,因果律却不要求“最后的证实”,因为人类最后的观察结果很有可能指出其为假。
对因果律的迷信—通过确定某个事件的开始条件和领域条件,其他事件就能够由此推论而来—植根于古典物理学当中。不过,20世纪初的量子物理学挑战了这一看法,科学家们发现以上两个条件可能无法同时被确定。“海森堡的‘测不准理论’认为物理体系所包含的不准确性,实际上就是质点的位置与速度在同时的精确度量中的不相容性……质点的位置的精确程度愈甚,则它的速度的不精确性愈增。假如我们对于质点的位置与速度欲同时准确地确定,则结果其中之一—位置或速度—都无法确定了。”②同上书,第61 页。面对量子力学,传统的因果原则是失效的,因为关于事件的条件难以确定,对未来的预说难以言中。但是,新康德主义者雨果·伯格曼认为,这一失效对哲学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作为科学知识的先验前提,因果律根本不能被经验推翻,因果律的可能性就是一切知识的可能性。
但在洪谦先生看来,康德所划定的这一前提已失去了意义。如果认定因果律仅为先验前提,那么它就是缺乏实际内容的同语反复命题;一个缺乏实际内容的同语反复命题,当然不能被经验推翻。可是,现代物理学已经指明因果律的失效,而且其真伪性是能够为经验所支配的,它不再是先验的前提,也不是空洞无内容的同语反复。因果律的失效是一个科学事实,它说明的是这样一件事:精确预言的不可能,并没有一个普遍有效的公式能够仅仅根据之前的事件对未来进行说明或推论。康德与新康德主义者的一些主张,很难在现代科学的语境下立足,除了因果律作为一切知识条件的设定,他关于欧几里得几何与空间的看法也随着非欧几何和相对论的发展成为无法成立的了。
洪谦先生关于这一问题的总结性评述是:“因果律既不是一种合乎逻辑意义的命题,既无最后的证实可能性,自然我们对它,亦无法加以绝对的肯定或否定。同时我们对于因果律原则在理论上生活上的信仰,亦无须因之而根本动摇,因为谁也无法否认:在科学之再进展中,因果律之为自然的基本形式之为科学理论的基础,又将恢复它的理论上与实际上的应用性,又将恢复它过去对于学术文化的价值与光荣了。”①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载韩林合编:《洪谦选集》,第66 页。也就是说,尽管因果律失效的现象被发现,并消除了物理学与哲学上关于因果律的迷信,但这影响不到人类的日常生活。他一直以来都秉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科学理论的建构不应受独立于经验的前提的限制,任何结构都有着成为现实的可能。量子力学的成就之一在于让人们意识到,应根据自然规律本身确定科学原理应用的界限,而非仅仅去遵循那些先验的神话。
关于因果律,洪谦先生还有一些其他的见解。首先,他认为自然界中没有因果规律和概率规律之分,而只存在关于它们的两种分布。不过后者不表达任何规律和自然知识,它只涉及偶然性,在没有偶然性的地方才有规律可谈。物理学中的统计规律也不是概率规律,而是部分地描述秩序、部分地描述偶然的“局部”规律。随着物理学的发展,有些人主张由于因果律的失效,现代物理学应以概率规律为基础。但洪谦先生的看法是,人们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概率的意义在现实中与在计算中的区别,或事实的概率与逻辑的概率的区别。在前一种情况中,人们通过观察枚举出的数量总是有限的,而在后一种情况中,数是无限的。海森堡的不确定关系,导向的并不是物理系统中观察的精确界限的存在,而是预言的可能性界限的存在。米塞斯试图用极限概念来对概率进行定义,赖欣巴哈论证因果陈述都有着概率的形式,这两种看法皆无法成立,洪谦先生甚至用“不能带来任何现实的认识”①洪谦:《论逻辑经验主义》,第36 页。对之加以批评。他认为,“规律”这一概念指明的就是严格的秩序,科学家拷问的就是自然界是否存在秩序。如果有一种“概率规律”,那它就是对规律的否定或无秩序的秩序,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被认为是科学规律。
其次,有一些学者认为因果律的失效给了自由意志问题以思辨的机会,这在洪谦先生看来则是将两个不相关的议题联系到一起。前者是指事件不为法则所支配,关照的是科学中的非决定现象,后者则是一个伦理学议题,涉及自愿与否的心理与行为。只有在误解决定论与宿命论关系的时候,才会有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相冲突的问题。另外,洪谦先生还留下了一个理论上的难点:因果秩序与时间秩序。有人主张,只有凭借前者才能对客观时间进行确定,后者由前者规定;也有人主张,一切规律都要在时间中展开,前者由后者规定。一般的因果律表明,未来的事件由过去决定;目的论则认为,过去的规定皆取决于未来。洪谦先生的观点是,从过去导向未来还是从未来导向过去,二者在逻辑上并无差别,没有哪一项有着优先地位。在玻尔的原子模型中,辐射频率既取决于初始条件,又取决于终结状态。自然中发生的这些事件,并不是先天的就具有因果论与目的论之分,很难通过它们对时间进行定义。有些人认为,或许可以通过“熵”来对时间的正向和反向进行描述,但他对此抱有怀疑,认为“熵规律”只能刻画概然性的不可逆,它不一定是严格有效的自然规律。
2.介绍逻辑实证论
回到祖国之后,洪谦先生致力于向学界介绍现代哲学的新趋势,并于1944年出版了作品《维也纳学派哲学》。该书不仅收录了他对逻辑实证主义观点的介绍,还有对现代自然哲学中几个基本问题的回应,例如不可知论、科学世界观以及非欧几何学与康德哲学等。对于当时的中国学界来说,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前沿性著作。它虽然篇幅不长,但像地图一般清晰展示了西方世界在20世纪初科学与逻辑学方面的进展,以及在此激励下哲学展现出的新图景。1949年,洪谦先生则在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上发表了一篇介绍逻辑经验主义的文章。
在传统的讨论中,哲学家倾向于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归咎于人类有限的认识能力;但随着现代逻辑的发展,人们开始注意到一些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隐藏着逻辑缺陷—它们不能被“有意义地”表达,进而得到或真或假的判断。但是,对于这些从原则上就无法被说明的问题,哲学家为什么未能保持沉默并孜孜以求呢?洪谦先生给出的回应是:首先,他们没能意识到这些问题中的语言陷阱以及逻辑漏洞;其次,他们往往怀有这样一种企图,即,让主客体在知识上达到统一,却没有意识到形式构造与直观性体验的区别。
像叔本华、柏格森这类哲学家,试图将认识的世界(die Welt der Erkenntnis)与体验的世界(die Welt des Erlebnis)加以统一地认识,却忽略了二者的差异:“好似想将不能认识的加以认识,不能体验的加以体验,于是乎就产生所谓形而上学。”略加反思就会发现,主体与客体的一致无论作为前提还是目标,都无法加诸“知识”之上。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譬如我们欲认识水之为水,则必须将我们与水视为一致。但是我们知道,假使我们假定与水合而为一,也无法知道水的本质,不仅与水合而为一不能认识水之为水,就是我们化身为水也还是无法知道。”①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载韩林合编:《洪谦选集》,第23 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主客观通达的追求毫无价值,诗歌、艺术乃至神学都可以以体验世界为目的。人们通过把握情绪,施加想象,也能够“使得心神如入其境”。
一些传统的形而上学论题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是失效的,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它的范畴应该被重新定义。受到维也纳学派的影响,洪谦先生主张这样一些观点:首先,哲学不是科学,而是一种活动,它不属于任何一种知识体系。其次,哲学的意义在于对实际知识或真理的逻辑意义进行说明,分析它们的基本概念。他以爱因斯坦提供的一个概念为例,在科学家进行试验之前,必须先对“两个事物能够在不同地点同时发生”的意义,以及它的证实方法有所说明。相比于科学,哲学家要关注的不是亲自寻找证据对命题加以验证,而是前一步工作—澄清概念与命题意义。面对一些尚不能回答的问题,哲学家要对其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探讨这些问题是仅仅需要等待证据的出现,还是源于语言上的误用。
洪谦先生还指出,逻辑实证论不同于传统的实证论,却替后者承担了不少责难。例如,逻辑实证论中的“证实”方法并非就事实而言,而是从原则上探讨命题在何种条件下为真。另外,传统的实证论认为,“实在”是一种感觉的复合,人们不能根据抽象的科学概念来认识它们;但在逻辑实证论看来,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关于实在“命题”的逻辑意义和说明它们为真或为假的证实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逻辑实证论不强求用事实来进行证实,但命题要对事实有所主张和表达。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哲学中那些超出实际现象甚至表达范围的“实在”(例如康德意义上的“物自身”),就属于空洞的、似是而非的命题了。
需要强调的是,不同于传统实证论对哲学的否定,逻辑实证论认为哲学不可以被取消。哲学的工作就在于研究真理的意义,辨别真问题与似是而非的问题,限制语言的误用。长久以来的一个误解是,认为逻辑实证论否定形而上学。但洪谦先生试图说明的是,他们否定的仅仅是形而上学作为实际知识的可能。这就是说,虽然像灵魂不朽、宇宙大全这些主题在哲学中不再必要,但关于它们的讨论可以回应人类的情感诉求。他引述过魏斯曼的一段话对此进行澄清:“假如我们视形而上学之知识体系如科学之为知识体系一样,那就错了。可是假如我们视其为一种生活的基本感情,一种如何了解人生、体验生活的基本感情,其形而上学不但不能否定,而且我们原则上就应当敬仰和维护它了。”①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载韩林合编:《洪谦选集》,第40 页。也就是说,逻辑实证论只是在特定意义上否定了传统哲学、形而上学,却在另一重意义上真正捍卫了它们。
3.对《新理学》中形而上学的批评
冯友兰先生于1939年出版了作品《新理学》,在谈及哲学方法时他借用了维也纳学派的一些主张,以彰显传统形而上学的困难,并确立自己“真正的形而上学”之成功。但是,其中一些理解在洪谦先生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在《论〈新理学〉的哲学方法》一文中,他称冯友兰先生的观点为“俱无一厝”的形而上学。洪谦先生对该理论的批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冯友兰提出的某些命题虽然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中那些“似是而非”的命题,但是属于“重复叙述的命题”(tautologische Aussage),即同语反复。如果按照早期分析哲学对语言的处理,那些传统形而上学命题属于无事实根据的“胡说”(sinnlos);冯友兰的命题虽然能够永不失其真,但属于无所说的“空话”(sinnleer)。其次,维也纳学派的“反形而上学”并不是对形而上学的“取消”,而是指明形而上学真正的活动范围—虽然作为一种实际的知识体系值得怀疑,但它在人生哲学上的积极意义并没有被否定。传统的形而上学命题如上帝存在、意志自由等,虽然不符合人们对知识系统或真系统的要求,但有着伦理学、美学以及丰富的情感意蕴;冯友兰提供的命题,如“山是山不是非山,必因有山之所以为山,水是水不是非水,必因有水之所以为水”等,则既不符合实际知识系统的要求,也不能提供文化、感情上的慰藉。
以上评述引发的争论延续至今。一些学者沿着洪谦的思路,继续指出冯友兰论述中的问题,例如他的形而上学命题并非真正的分析命题①参见黎汉基:《冯友兰与洪谦—有关新理学方法问题的讨论》,台湾哲学学会2000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以及他的“同天境界”论证无法成立②参见韩林合:《洪谦对冯友兰新理学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及其展开》,《哲学分析》2010年第4 期。等。另一些学者则指出,虽然站在西方哲学的立场来看洪谦的批评有理有据,但冯友兰所做的尝试是宝贵的,隐藏在背后是中西哲学的不同旨趣,以及科学的实证主义传统与人文主义的对立。例如:
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虽然不重视逻辑的分析, 但是却特别注重人生哲学中的人生境界理论。冯友兰完全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他的哲学工作的路向就是要给传统哲学的人生境界奠定一个现代性的哲学理论或方法论的基础。在这样做的时候, 他思考的重点毫无疑问的是传统的人生境界说,而从西方借鉴来的逻辑分析方法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工具。①胡军:《重建还是拒斥形而上学—从洪谦和冯友兰关于形而上学的论争谈起》,《东岳论丛》2002年第1 期。
以及:
在他看来,科学是为学,哲学是为道,为学是求一种知识,为道是求一种境界。人要达到最高境界,需要对于人生有最后的觉解。形上学所能给予人的,就是这种觉解。而这是科学所不能达到的。②李维武:《冯友兰新理学与维也纳学派》,《现代哲学》1990年第4 期。
通过后一类表述我们会发现,洪谦先生的评论并没有得到充分理解。这些辩护往往隐藏着一个预设,即: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分析、科学实证,却轻视了对人生境界、对人生最后觉解的追求。但正如洪谦一再强调的是,维也纳学派并没有将人生哲学剔除,他们的工作就是在为其划界。对它们的处理虽然曾是传统形而上学的重要工作,但也可以交由文学、艺术甚至宗教来发展。冯友兰的“形而上学”虽然不同于传统,但其最终指向也没有超出这一范畴。更严重的是,这类表述埋下了一个更大的隐患,即中西哲学的对立。如果试图认真地探讨“人生境界”并彰显它在中国哲学中的特殊地位,首先要说明的是哪些问题属于人生境界问题,它如何界定,它的哲学基础是否成立,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它与西方哲学讨论的人生哲学、伦理学和美学问题有所不同,又在何种意义上只属于纯粹哲学的范畴,不能交由文学、艺术来探讨。如果不能对以上问题加以说明,那么该类辩护只不过是在重复一个刻板印象,却规避了洪谦先生质疑的真正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