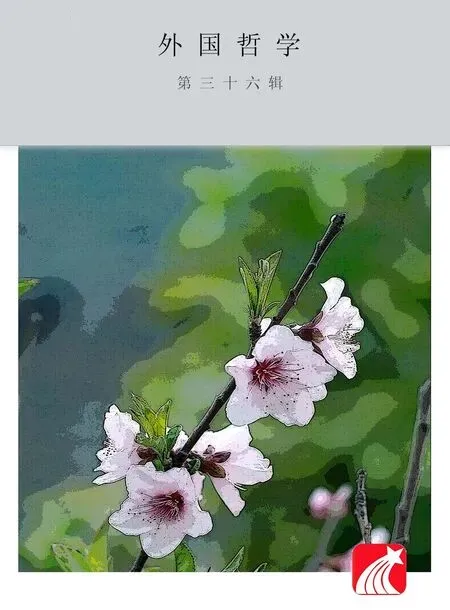严师之教
陈启伟
欧阳修有云:“古之学者必严其师。”此所谓“严”,非指学生当敬重师长,维护师长的尊严,而是说一个人要学而有成,必须有严以教之、能严格要求学生的老师,必须有严以治学、其严谨学风堪为楷模的老师。我们北大之所以能在学术上长盛不衰,之所以代代都有优秀乃至杰出的学者出来,我以为极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教育上有一个“严”的传统。我们的教师是以严字教书育人,以严字造就后学的“严师”。
我生也有幸,从读大学和研究生到留校教书,几十年间一直生活在北大,对严师之教乃亲身经历,体会至深。在北大我曾受业于其门下的先生自然不止一人,我从他们那里都学了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在我的学术道路上对我要求最严因而也教育最大、影响最深的,却莫过于我做研究生时的导师洪谦先生。现就记忆所及,对我师从洪先生时所受先生严教的情况略作追述,也作为对先生的一点纪念吧。
洪谦先生是驰誉国际哲坛的著名哲学家,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学派之一“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我在1952年考入北大哲学系,很长时间里虽久仰其大名,却无缘得识,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像他这样的“资产阶级”教授是不许登台授课的。只是到了我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即1955年秋天,由于我选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批判休谟的不可知论”,系里请洪先生做我的论文指导教师,我才有机会去拜见了他。
我发现洪先生待人很平和,也许是初次见面吧,他对我很客气。他似乎不善言谈,而且说话也很谨慎,除了谈毕业论文的写作并指定几本必读书外,几乎没有什么题外之言。但是,有几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至今难忘。洪先生说:“你这个论文题目只有一半,只有‘休谟哲学’这一半,我可以做些指导,至于‘批判’这一半,你恐怕要自己多思考。‘批判’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我学马克思主义大概还不如你们同学学得多。苏格拉底说得好,‘我知我为无知’(我后来知道,这是洪谦先生非常喜欢的一句格言)。我不能以自己无知的东西去指导别人。”但是,他接着说:“不论你怎样去批判休谟,你首先要认真地读休谟的书,弄清楚休谟自己究竟是怎么说的,这是学术研究最起码的要求。”
其实,这个“最起码的要求”也就是一年之后我做他的研究生时他还屡屡以之教我的治学第一要义,用他的话说就是:研究一个哲学家,首先就要“沉下心”读他的书,反复地读,“钻到”他的书里去,真正把握他的思想,不要事先有个批判的框子,把人家的思想“切割了往里塞”。对洪先生的这个教导,我在1956年11月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读书应浸沉于书中,深知其当然、其所以然之故。慎勿先存成见。为批判而寻章摘句,必不能沉下心读书也。”
我是1956年夏在北大哲学系本科毕业后被推荐给洪先生做研究生的,研究方向还是休谟哲学。我们这届研究生是春季始业,即到1957年2月才正式开学,但洪先生在1956年秋季就安排我开始学习了。过去大学毕业论文的写作、修改和定稿虽然都得到洪先生的悉心指导,但那时同他见面求教的机会并不多,现在做了研究生,则整个学习生活都是按洪先生拟订的计划进行的。按照他的规定,我每隔两周去见他一次,向他汇报学习的进度和情况,提出问题和讨论,而事实上经常是他听了汇报之后首先提出问题要我回答,即使我向他提问请教,他也要我先谈谈自己的看法,然后才予以点拨,而且往往只是略作提示,还要我自己去再读再思考,自己求得详尽的解答。这样,我很快就感觉到,在洪先生门下执弟子礼,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每次去见他都仿佛去参加一次考试,丝毫不敢马虎。
这样的学习安排大约持续了一年半的光景,即从1956年秋到1957年冬。1958年“双反”运动之后,由于洪先生长期卧病,他就没有再这样指导我的学习了。但是这一年半是我在研究生学习时期读书最多、最刻苦,收获也最大的一段时间。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洪先生以他的严教在学风(包括治学方法和学术品德)上对我的培植和锻造。这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洪先生反复对我说,做学问首先是要打好基础,好比盖房子,地基不牢,盖不了高楼大厦。又说,知识基础要像铁板钉钉一样打得扎扎实实。他甚至用手指着头说:“就是要把基础的东西牢牢地钉在脑子里。”我们那届研究生学制是4年,为了打好基础,洪先生要我用一年半的时间读西方哲学史。他说,你研究休谟也好,研究别的哲学家也好,都必须有深厚的哲学史的功底。有人讲维也纳学派目中无史,不重视哲学史,洪先生说:“其实石里克(维也纳学派领袖,洪先生的博士导师)有很深的哲学史的修养,我在他指导下学习时,哲学史是必读的。”他告诉我,他指定我读的两本书(策勒[Zeller]的《希腊哲学史大纲》和法尔肯贝格[Falckenberg]的《近代哲学史》)就是当年石里克要他读的。此外,洪先生还要我全读或选读了许多西方哲学的古典名著。他总是讲一定要读哲学家自己的书,一定要读原著,这是“基础的基础”。有的著作,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他还特地请对希腊哲学研究有素的方书春先生做过几次辅导,为我解答疑难问题。
二、洪先生特别强调做学问要细。首先,读书要细。一字一句都要弄得一清二楚,不能半生不熟,囫囵吞枣。我双周去向他汇报学习情况时,他常常在我读的策勒或法尔肯贝格的书上找出一段话来要我讲解并逐字逐句当场口译出来(我当时读的是这两书的英文本)。对每个词的含义和句中各词间的语法关系,他都注意得很仔细,稍有舛差,立刻纠正,并且不惮其烦地对我说,读书也好,翻译也好,都要非常细心,要一字不苟。有的翻译就是因为一字看错或没弄清楚句子的上下关联语法关系,结果大错特错,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其次,研究问题、思考问题要细。细,就是要勤于分析,善于分析;不要粗枝大叶,浅尝辄止;不要大而化之地高谈阔论。有一次我刚读完了培根的《新工具》去见洪先生,他要我谈谈对培根哲学的理解,我没有就《新工具》一书的内容具体地阐述培根的思想,而是笼统地大谈一通他的唯物主义经验论、辩证法因素,如此等等。不料洪先生不耐烦地打断我说:“你有没有仔细地读《新工具》?培根在《新工具》里讲的东西你没做一点分析,却空谈什么唯物论、辩证法!”然后他要我回去写一篇“仔细分析”培根归纳法的读书报告。这是我在学习上唯一的一次遭到洪先生的训斥—由于学问没有做细而遭到的训斥。
三、洪先生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探索的精神。他屡次对我说,无论读谁的书,都要自己动脑子思考,形成自己的见解,不要读了什么就信什么,不要人云亦云。1957年底我在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时产生了一个疑问。康德在“导论”第一节开头说:“毫无疑问,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但是他不承认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起源的,因为知识的成立还有赖于某些先天的,即不是来自经验的形式(先天的感性形式和先天的范畴),正因此故,没有人因为康德承认一切知识始于经验而说他是唯物论。然而这样一来就同我们的哲学教本里流行的一个说法,即“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发生矛盾了。我问洪先生怎么理解,他说很抱歉他还没有注意过哲学教本里这个流行的说法,不过他认为我的思考是对的,并且补充说,柏拉图也不否认认识开始于经验,他认为只有经过感觉的诱导才能使灵魂去回忆它本来固有的对理念的知识。但也没有人说柏拉图是唯物论嘛。像这样鼓励和赞许我对哲学问题做独立思考的例子,我还能记起一些。我觉得我在洪先生的培育下在学术上锻造出来的这种独立的精神,是他留给我的一份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洪先生总是教导我要非常严肃、认真、审慎地对待写作。他经常要我写读书报告,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大约写了大大小小一二十篇报告,有些报告(如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洛克、巴克莱)写得相当长,也很下了一些工夫。但是洪先生不主张轻易发表文章,一再告诫我不要“为发表热所驱,汲汲于敷衍成文”。写一篇文章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翔实的资料、深入的思考,这就是中国古人说的,要“厚积而薄发”。根据洪先生的教导,我在日记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学有根柢始发为文章。内蕴丰厚而外现宏阔伟大—这是一切学问家所经历的途径。”很惭愧,我并没有成为这样的学问家。但是我一直切记洪先生的教导,治学著文,从不敢空谈妄议。
洪先生很不喜欢当时苏联哲学界的文风,他们写的东西冗长而烦琐,除了引经据典,就是一大堆不加论证的断语,简直不知其何所据而云然。20世纪50年代在北大哲学系讲学的一位苏联专家的《西方哲学史讲稿》,就是这种文风的一部代表作。从我的研究生学习之始,洪先生就对我说:“这个书不必参考了,书里没有什么资料,论述也不说理。”而且要我记住,写文章切不可这样写。他尤其厌恶有些人写文章无凭无据,妄下论断。
例如,50年代末国内翻译出版的《保卫哲学》一书上有苏联哲学家阿历山大洛夫写的一篇“序”,竟说维也纳学派卡尔那普等人的逻辑分析方法是“秉承英美反动统治集团的意旨”制造出来的。我见到洪先生时给他念了这段话,他觉得很滑稽,想不明白他们的“阶级分析”怎么会“分析”出这样荒谬的结论来。他也不能容忍那种不顾事实、信口开河的文章,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寄给他境外刊物上发表的一篇讲分析哲学的文章,他要我拿去看看,说这篇文章“开口便错”。原来文章劈头第一句话就说:“分析哲学起自19世纪后半期的逻辑实证论。”洪先生说:“分析哲学既不起于逻辑实证论,逻辑实证论更非出现于19世纪后半期,连基本的历史事实都弄错了,这种文章怎么立得住!”他认为,诸如此类的作品都是学风不正的表现,都是学术上的“败行”。
洪谦先生离开我们近30年了。但是每一忆及,当年亲受先生严教的情景犹历历在目。回顾自己几十年来走过的学术道路,先生的教诲始终谨遵,未敢或忘,这也许差可告慰于先生在天之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