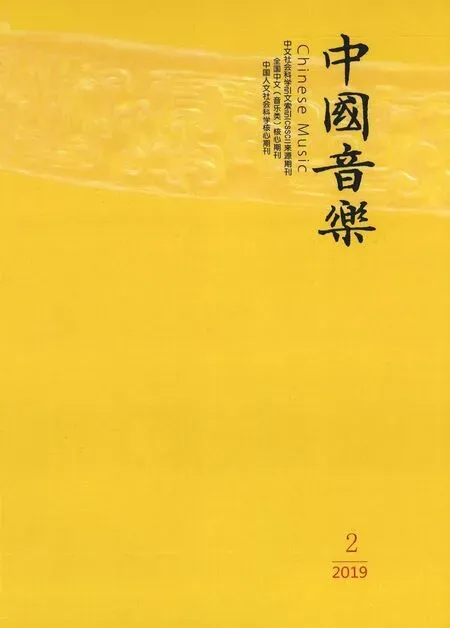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及其音乐文化建构
○
锡伯族原为东北地区世居族群①沈阳锡伯族家庙《太平寺碑记》译文中写道:“历史明载世传之锡伯部族,原居海拉尔东南扎费托罗河一带”,扎费托罗河即今绰尔河,位于今嫩江流域。参见赵展:《锡伯族源考》,《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3期,第100-101页。,后受清政府派遣,锡伯族官兵携家眷(共计4030人)于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西迁至新疆伊犁屯垦戍边。②乾隆二十四二年(1757年)、二十四年(1759年)清政府先后平定阿睦尔撒纳和大小和卓叛乱后,伊犁地区防务空虚,为巩固边防,清政府调遣东北地区锡伯族官兵携其家眷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到新疆伊犁屯垦戍边。参见吴元丰、赵志强:《锡伯族西迁概述》,《民族研究》,1981年,第2期,第22-29页。自此,形成锡伯族横跨一万余里跨域分隔的格局。锡伯族音乐文化也随着锡伯族的西迁被分置于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并在历史的变迁中形成不同的传承样态,其中西北地区锡伯族将锡伯族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了下来,而作为锡伯族文化原生地的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则呈现文化式微的样态。
1954年国家民族识别工作确认了锡伯族的民族身份③我国民族识别工作分为四个阶段,其中1949-1954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确立了38个少数民族,其中包括锡伯族。参见辛华:《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四川统一战线》,2006年,第6期,第23页。.,在东北地区锡伯族与周边其他民族相比较的过程中,发现锡伯族传统民族文化遗失严重,民族文化特性不够鲜明,在这一背景下,东北地区锡伯族即开始建构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性的音乐文化,从而更能标识其独特的民族身份。而锡伯族音乐文化的建构首先需要确立其音乐文化建构的根基与来源,即选择什么样的文化作为文化建构的根基文化,课题组在对东北地区锡伯族聚居区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东北地区锡伯族不同文化主体所选择的根基音乐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概而言之有两类:第一类是由文化精英群体所选择的将西北地区锡伯族通过跨域反哺④根据尹爱青在《锡伯族音乐与舞蹈跨域反哺研究》一文中的界定,跨域反哺是指同族异域文化传承主体将所传承的文化由传承地传播至该文化的原生地,并对原生地母体音乐、舞蹈文化具有一定文化重建价值与意义的文化现象。参见尹爱青、刘江峡、刘畅:《锡伯族音乐与舞蹈跨域反哺研究》,《中国音乐》,2017年,第4期,第50页。过程传播到东北地区的锡伯族传统音乐文化作为自身的根基文化;第二类是由东北地区锡伯族群众所选择的将聚居所在地的地域音乐文化作为建构锡伯族音乐文化的根基文化。不同文化主体所选根基文化的差异反映出东北地区锡伯族对锡伯族自身音乐文化认同的差异。本文即是在这一文化背景的基础上探究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的差异,以及这一认同差异对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建构所带来的影响。
一、东北地区锡伯族的音乐文化认同
(一)对锡伯族反哺音乐文化的认同
文化认同,即“人们对所属民族共同体文化的自我意识和肯定性体认,即个体对自己所属民族文化的接受和内化”。⑤鲁全信、颜俊儒:《文化自觉:推进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与传承的有效路径》,《贵州民族研究》,2015年,第5期,第2页。如果将文化认同问题的分析引入时间维度,还可以发现一个人并没有一个固定身份,“‘我是谁’至少可以划分为‘我过去是谁’‘我现在是谁’和‘我将来是谁’。当人们采取本质主义的态度来理解人时,就会以‘过去是谁’来理解一个人,因为本质被假定为一贯如此。”⑥赵汀阳:《认同与文化自身认同》,《哲学研究》,2003年,第7期,第16-22页。反映在民族音乐文化认同上,即是用一种固定不变的本质主义方式去把握民族音乐文化的固有特征,这种本质主义的方式以一种确定的、稳定的、超越历史时代的永久的音乐文化特性作为民族音乐文化的核心特征,并以此作为族群文化与周边其他民族文化的文化边界。
课题组在东北地区锡伯族聚居区调研过程中发现,东北地区部分锡伯族认为西北地区锡伯族所传承的锡伯族传统音乐文化蕴含着锡伯族音乐的固有特征,所以应将西北地区锡伯族所传承的锡伯族音乐文化作为标识东北地区锡伯族文化身份的民族音乐文化,因此,对近年来西北地区锡伯族通过跨域反哺过程传播至东北地区的锡伯族传统音乐文化具有较高的认同。秉持这一认同观念的多为对锡伯族民族音乐文化变迁过程有着较为清晰理解与认识的文化精英群体,这一群体具有较为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对本民族的音乐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有着充分的认识。自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锡伯族部分官兵携其家眷西迁至新疆伊犁屯垦戍边之后,限于当时社会交通方式,两域锡伯族陷入了空间隔绝状态,两域锡伯族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传承着锡伯族音乐文化,经过186年的文化变迁,直至20世纪中叶两域锡伯族才得以建立联系,在此之后两域锡伯族即开展了相互考察,⑦参见沈阳市民委民族志编纂办公室:《沈阳锡伯族志》,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329页。根据辽宁省民族志锡伯族卷编委成员那启明整理的纪实资料,自20世纪中叶两域锡伯族即已开展了相互考察,考察活动多是锡伯族知识分子等文化精英所组织的,较少有锡伯族群众参与,如1951年7月,西北地区锡伯族学者托永寿、何文清等多次到东北调查访问、寻根问祖,1959年5月至9月,西北地区锡伯族学者吉庆、肖夫赴东北对锡伯族进行社会历史调查,1981年东北地区锡伯族学者韩启昆到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进行调查,1997年沈阳兴隆台锡伯族镇党委书记傅永林等到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考察……⑧参见那启明:《心连心手足情——新疆—东北锡伯族交往纪实》,(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14f6ce0 101o3kj.html),2013年11月22日。。通过两域锡伯族的考察活动,东北地区锡伯族得以认识到两域锡伯族在锡伯族音乐文化传承上的“文化时差”,西北地区锡伯族所在的察布查尔等聚居区在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环境下传承了丰富的锡伯族传统音乐文化,而东北地区锡伯族因受辛亥革命等历史事件的影响,锡伯族传统音乐文化遗失严重。通过对西北地区锡伯族的考察以及对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传承中断的现实考虑,东北地区锡伯族文化精英群体认为西北地区锡伯族所传承的锡伯族传统音乐文化才是标识锡伯族民族文化身份的根文化,这一发现成为东北地区锡伯族反哺音乐文化及其文化认同得以确立的内在根据。而近年来,西北地区锡伯族音乐跨域反哺过程则为东北地区锡伯族的反哺音乐文化认同奠定了条件。20世纪80年代末,两域锡伯族联谊会的成立,标志着由锡伯族文化精英群体所构成的锡伯族民族文化组织的形成,推动了两域锡伯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文化互动,锡伯族音乐跨域反哺正是在这一条件下逐渐实现的。锡伯族联谊会成立之后,每年都会在锡伯族民族重大节日之际组织锡伯族联谊活动⑨参见尹爱青、刘江峡、刘畅:《锡伯族音乐与舞蹈跨域反哺研究》,《中国音乐》,2017年,第4期,第50页。,开展锡伯族祭祖仪式以及西迁纪念活动。一般在仪式活动开展之际,西北地区锡伯族联谊会即会组织安排锡伯族民间艺人到东北地区表演锡伯族歌舞。锡伯族传统音乐通过这一跨域反哺过程得以为东北地区锡伯族所认识与了解。课题组在访谈过程中了解到:锡伯族认为锡伯族音乐文化的根在西北地区(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东北地区的锡伯族音乐文化不是地道的锡伯族音乐文化,东北地区锡伯族应将西北地区锡伯族所传承的锡伯族传统音乐文化作为本民族的音乐文化。
锡伯族传统音乐对东北地区锡伯族来讲,是锡伯族民族音乐文化起源与发展的反映,对西北地区锡伯族反哺传播而来的锡伯族传统音乐文化的认同,能够使传统音乐文化遗失的东北地区锡伯族认识到其自身音乐文化的历史独特性,东北地区锡伯族认同西北地区锡伯族传承下来的锡伯族传统音乐文化,并选择将其作为文化构建的根基文化是锡伯族音乐文化传承中断后的一种再续,这一再续较为关注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发展的历史性定位,将东北地区锡伯族现今音乐文化发展的起点置于锡伯族音乐文化传承与变迁的时空之中进行反思与定位,最终选择将锡伯族音乐文化建构的起点回归至本民族固有的音乐文化传统之中。
(二)对东北地域音乐文化的认同
对东北地域音乐文化认同即是东北地区锡伯族将其所在地的地域音乐文化作为标识自身民族身份的音乐文化,持这一认同观念的多为东北地区锡伯族当地的群众,其对文化的认识属于无意识的“自在”认识,并以经验、习俗、习惯等自在因素的合理性确证其存在方式的合理性,音乐文化实践经验所内涵的时空有限性决定了其对音乐文化的认识具有一定的时空限度,难以在音乐文化实践经验中获得对锡伯族文化变迁过程的整体认知,在缺乏对锡伯族历史客观准确认知的情况下,认为东北地区锡伯族当前所拥有的音乐文化即是本民族的音乐文化,并将东北地区锡伯族当前音乐文化与周边他者音乐文化的差异性作为民族音乐文化的边界。
东北地区锡伯族对所在地地域音乐文化认同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成因,课题组在东北锡伯族聚居区调查期间了解到,东北地区锡伯族所传承的音乐文化多是在不同历史时期随着人口迁徙从关内传播至关外后逐渐形成的地域音乐文化。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清政府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招募汉族群众到东北地区屯垦,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部分汉族群众陆续迁至东北地区,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的汉族音乐文化亦随着这一时期的移民屯垦而传播至东北地区,这一时期东北地区锡伯族在保存其民族自身音乐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随着移民的迁徙而传播至东北地区的汉族音乐文化。后来,“直至清末辛亥革命时期,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等革命口号的号召下,各地掀起了反封建统治的革命运动,作为统治阶级的八旗官兵也成为了革命的对象。”⑩尹爱青、刘江峡:《东北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变迁:阶段、成因及其影响》,《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32页。,在这一反封建统治运动过程中“各地旗人害怕报复,纷纷改姓换装,隐瞒自己的旗籍出身”[11]陈静:《“驱逐鞑虏”后的京旗满族形象建构》,2011年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第8页。,由于锡伯族于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即已纳入满族八旗[12]锡伯族原属于蒙古八旗,后由于全国驻防兵源紧缺,加之东北防务的需要,清政府于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将锡伯族编入满族八旗。参见吴克尧:《锡伯族编入满洲八旗简述》,《黑龙江民族丛刊》,1987年,第2期,第69-70页。,生活习俗与满族八旗相近,在革命爆发之际亦随着满族八旗官兵改汉姓、换汉装,形成八旗旗人去民族性的现象,根据1911年《申报》所载“排满之议起,学生之旗籍者,纷纷冠以汉姓;世家之有协领等匾额者,急为卸下,他若妇女改装、男子改姓者,尤不一而足”[13]《申报》(1911年2月29日),载赵毅、王景泽:《“革命排满”与八旗社会》,《东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第2页。。锡伯族传统音乐文化的隐藏以及所在地地域音乐文化的彰显,成为旗人避免在排满运动中受到迫害的重要方式。表现在文化认同上即是标识旗人民族身份的音乐文化的消解,地域汉族音乐文化成为东北地区锡伯族新的身份标识,这也标志着东北地区锡伯族地域音乐文化认同的初步确立。
自辛亥革命为始直至20世纪中叶,东北地区锡伯族逐渐融入至东北汉族文化群体中。随着时代的更迭,锡伯族传统音乐相关的历史记忆也逐渐随着代际更替而遗失。在访谈过程中,发现被访锡伯族群众中有97%的锡伯族群众对现今锡伯族音乐文化的源起以及发展变迁过程缺乏了解,不知道锡伯族传统音乐的原始样态以及变迁过程。在缺乏锡伯族历史文化记忆的背景下,东北地区锡伯族将东北地区的地域音乐文化作为锡伯族自身的民族音乐文化。在对东北锡伯族村落调查时发现沈阳新民村锡伯族群众认为唱秧歌是锡伯族的音乐文化,大孤家子村、岳士村等锡伯族村民认为“灯官秧歌”等是锡伯族的音乐文化,唱秧歌、“灯官秧歌”原本为清初随着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的汉族移民迁徙而传播至东北地区的音乐文化,现已成为东北地区锡伯族标识自身文化身份的音乐文化。
二、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的建构
东北地区锡伯族的音乐文化认同是一种观念上的认识,选择所认同的音乐文化并与锡伯族民族文化身份建立一定的文化联系,则是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从观念认识向音乐文化实践转化的过程,东北地区锡伯族对民族音乐文化认同的差异,直接决定了东北地区锡伯族在认同基础上建构锡伯族音乐文化的差异。锡伯族音乐文化建构是对“我将来是谁”这一问题的思考探索。东北地区锡伯族在确立民族文化认同之后,即需要通过不断“发掘”有助于增强自身身份认同的文化事项来确证自己族群的文化身份。不同的文化认同需要通过不同的音乐文化来建构自身的合理性,应选择“怎样的民族音乐”成为民族音乐文化建构的首要问题。
(一)基于反哺音乐文化的锡伯族音乐文化建构
东北地区锡伯族的文化建构是东北地区锡伯族构筑新的族群边界的过程,基于锡伯族跨域反哺音乐文化的建构路径,即认为西北地区锡伯族传承下来的传统音乐文化蕴含着锡伯族音乐文化的固有本质特征,因此东北地区锡伯族应将西北地区锡伯族传承下来的锡伯族音乐文化作为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建构的根基文化,并以此作为东北地区锡伯族确证其文化身份的符号,从而构筑起东北地区锡伯族与周边其他民族之间的文化边界。这一基于西北地区锡伯族传承下来的音乐文化建构新的锡伯族音乐文化的过程,亦是东北地区锡伯族所遗失的音乐文化恢复的过程,在恢复的过程中较为关注锡伯族民族文化的原貌,其中越古老的锡伯族音乐越能反映锡伯族的独特性。
将锡伯族反哺音乐文化作为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建构的根基文化,其包括对东北地区锡伯族对民族身份及民族文化的历史性定位。从某种意义来讲,基于反哺音乐文化的建构路径较为关注锡伯族音乐文化的历史连续性,西北地区锡伯族传承下来的锡伯族活态传统音乐文化,让东北地区锡伯族了解到锡伯族文化的传统面貌,了解到蕴含在传统音乐文化中的民族独特性,这一传统民族音乐文化正是东北地区锡伯族所遗失的民族自我,因此,基于跨域反哺的音乐文化建构即是通过跨域反哺传播而来的锡伯族传统音乐文化重塑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的主体性,并将其作为东北地区锡伯族表达民族特性的文化载体。
在确立了锡伯族音乐文化建构的根基文化之后,即需要根据这一根基文化重塑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的独特性,以此构筑锡伯族民族文化的边界。根据东北地区锡伯族基于锡伯族反哺音乐文化建构锡伯族音乐文化方式的不同,可将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的建构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为文化归根阶段,即东北地区锡伯族所遗失的传统音乐文化归根至东北地区,多是选择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锡伯族音乐文化归根至东北地区,并将归根的音乐文化作为东北地区锡伯族的音乐文化,解决东北地区锡伯族缺乏民族独特性文化的问题;其二是在归根的锡伯族音乐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再创编,使其更适宜东北地区锡伯族的生存现状,这一阶段主要解决的是反哺的锡伯族如何在东北地区文化语境生存的问题。
文化归根阶段的锡伯族音乐文化建构,主要依靠西北地区锡伯族民间艺人将其所传承的锡伯族传统音乐文化传播至东北地区,进而凸显锡伯族的民族特色。由于反哺锡伯族音乐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受制于人的跨地域流动,而西北地区锡伯族多是在民族重大节日之际到东北地区参加活动,所以这一阶段的文化建构具有间歇性。在民族节庆之际邀请作为锡伯族传统音乐文化持有者的西北地区锡伯族到东北地区表演音乐、舞蹈节目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传播形式。例如:1983年,兴隆台锡伯族镇镇长在兴隆台镇更名为“兴隆台锡伯族镇”之际,即邀请新疆察布察尔锡伯族文工队参加兴隆台锡伯族乡成立大会并表演节目[14]参见沈阳市民委民族志编纂办公室:《沈阳锡伯族志》,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329页。,兴隆台锡伯族镇希望能以文工团所表演的独具民族特色的锡伯族音乐作为兴隆台镇更名为“兴隆台锡伯族镇”存在合理性的文化根据,凸显锡伯族文化身份的独特性。20世纪70、80年代东北地区锡伯族聚居区逐渐兴起锡伯族祭祖、西迁纪念活动,每年的西迁纪念活动都有新疆地区锡伯族同胞表演的锡伯族歌舞。通过西北地区锡伯族的反哺传播过程,西北地区锡伯族所传承的锡伯族传统音乐文化得以传播至东北地区,其中锡伯族民歌《雅其娜》即是一首较为典型的通过锡伯族跨域反哺过程归根于锡伯族原生地的民歌,这一民歌为原生于东北地区的锡伯族民歌[15]参见韩育民、佘吐肯:《锡伯族捕鱼歌、狩猎歌与有关民歌的比较研究》,《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24-26页。,并随着锡伯族的西迁传播至西北地区,后随着锡伯族到东北地区的跨域反哺而再回到东北地区锡伯族母体文化语境,从而形成锡伯族音乐文化的跨越时间空间的归根。
谱例1 锡伯族民歌《雅其娜》[16] 谱例《雅琪娜》为沈阳兴隆台锡伯族学校锡伯族教师阿吉·肖昌赠予课题组的锡伯族校本教材《锡伯语速成读本》所收录谱例。参见锡伯语速成读本编委会:《锡伯语速成读本》,沈阳: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18页。

第二阶段是在归根音乐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与第一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的音乐文化活动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从对音乐文化“持有者”的关注,转变为对音乐文化“本体”的关注。从单纯的聘请或邀请西北地区的锡伯族艺人到东北地区演出,转变为对归根的锡伯族音乐文化进行改编,使其能更好地适应东北地区锡伯族文化语境。
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2000年,兴隆台锡伯族镇镇长傅永林邀请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阿吉·肖昌与伊文兰夫妇到东北地区教授锡伯族语言、音乐、舞蹈等课程,寄希望解决人的流动性带来的反哺音乐文化在东北地区存在的间歇性问题,从而让反哺的锡伯族音乐文化在东北地区得以再生。与此同时,东北地区锡伯族在接受西北地区锡伯族反哺音乐文化的过程中,通过将反哺的锡伯族音乐文化进行一定形式的改编,使其更符合东北地区的文化背景。而在建构的过程中,尤为注重对锡伯族较具独特性的文化元素的挖掘与凸显,锡伯族历史上的西迁、民族信仰“喜利妈妈”等逐渐抽离成为标示民族独特性的文化符号,并成为锡伯族反哺音乐、舞蹈中的主要主题,并在东北地区锡伯族聚居区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强化锡伯族的民族性。例如:锡伯族西迁节活动期间锡伯族同胞所表演的歌舞《锡伯印记》《喜利妈妈的传说》《锡伯人》《西迁之歌》等,都是将反哺音乐文化改编为易于被东北地区锡伯族所接受的音乐文化,并以此来凸显锡伯族的民族文化独特性。
(二)基于东北地域音乐文化的锡伯族音乐文化建构
基于东北地域音乐文化的音乐文化建构,即是将现有东北地域音乐文化作为锡伯族音乐文化建构的根基文化进而凸显锡伯族民族音乐文化的过程,他者理论则为这一建构过程的解释提供了一定的合理性。他者理论认为“自我”的存在必须建立在对于“他者”的想像的基础之上,通过“自我”和“他者”对立的预设,为“自我”同质性提供合法化说明[17]参见王琼:《民族主义的话语形式与民族认同的重构》,《世界民族》,2005年,第1期,第1-8页。。在他者影响下的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建构,偏重于借用东北地域音乐文化形式来表现锡伯族文化,并通过将地域音乐文化民族化,以此来凸显锡伯族的民族特性。这一文化建构较为关注文化的空间性存在,是在锡伯族音乐文化空间性定位基础上所做的选择,即与同时期周边其他村落音乐文化的横向比较,而缺乏对音乐文化的历时性关注。
辛亥革命之后,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由本民族音乐文化认同逐渐转向东北地域音乐文化认同,东北地区锡伯族逐渐融入至周边汉族文化圈之中,音乐文化也逐渐与汉族音乐文化相趋同。后直至20世纪中叶,随着国家民族普查工作的开展,锡伯族确立了自身的民族身份。民族身份确立之后,需要有与其身份相符的具有民族独特性的音乐文化来标识其民族身份的独特性,这一时期的东北地区锡伯族即开始寻求建构锡伯族本民族独特的音乐文化。
基于东北地域音乐文化的锡伯族音乐文化建构过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地域音乐文化与族群文化身份关系的建构;其二是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独特性的凸显与呈现,其中地域音乐文化与族群文化身份的建构主要是确立了灯官秧歌、唱秧歌等地域音乐的锡伯族归属,灯官秧歌、唱秧歌原本为东北地区普遍传承的地域音乐文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灯官秧歌与唱秧歌从原本地域性普遍存在的音乐文化逐渐转变为一种局部或个别村落的文化传承,即文化传承空间范围从普遍性的“传承面”转变为局部性的“传承点”,而各个传承点之间缺乏一定的文化联系,传承点所传承的音乐文化经过一定时间段的代际传承之后,其所传承的音乐文化事项逐渐与传承主体的文化身份产生一定的耦合,即对所传承音乐文化的文化归属的认定。锡伯族灯官秧歌、唱秧歌即是通过这一过程逐渐演化为锡伯族的民族音乐文化。灯官秧歌、唱秧歌等在东北地域传承式微之后,沈阳兴隆台锡伯族镇新民村、沈北大孤家子村、岳士村分别将唱秧歌、灯官秧歌传承了下来,后沈阳市在进行文化普查的过程中,发现唱秧歌、灯官秧歌等为锡伯族村落所独有而周边其他村落都没有的音乐文化,而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传承者以及当时的普查者都对这一文化的具体归属难以有较为准确的判定,即在缺乏历史考证的情况下,以传承者的锡伯族身份作为这一音乐文化归属于锡伯族音乐文化的根据,传承者的民族身份则赋予了这一文化的民族性以合理性。至此,灯官秧歌、唱秧歌等原本为地域性普遍流传的音乐文化逐渐转变为东北锡伯族的标识其民族身份的音乐文化,唱秧歌更名为“锡伯族唱秧歌”,灯官秧歌更名为“锡伯族灯官秧歌”,其中“锡伯族灯官秧歌”于2011年被认定为沈阳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8]辽宁省人民政府:《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辽宁省人民政府公报》,2011年,第17期,第2-39页。、“锡伯族唱秧歌”被认定为沈北新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9]此处的区级是指由沈阳市沈北新区,为沈北新区所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政府对其文化归属的认定为东北地区锡伯族民族音乐文化的建构提供了政府层面的支撑。东北地域音乐文化与锡伯族民族身份之间建立了正式联系。
唱秧歌、灯官秧歌等原本为东北地区普遍流传的音乐文化,唱秧歌是秧歌柳子(秧歌帽)又叫秧歌帽或拜年调[20]参见李来璋:《鉴名录》,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2001年,第191-192页。,根据锡伯族唱秧歌传承人关义介绍,旧时的唱秧歌一般是秧歌队到锡伯族村里各家各户拜年。秧歌队每到一户,负责唱秧歌的民间艺人就要即兴编创唱词向该户的家人表达祝福,演唱所用的曲调一般都是固定曲调,如《正月里来正月正》《太平调》《小拜年》等,曲调多为羽调式,一般为4个乐句,每句结尾基本上都落在羽音,前三句唱毕加入锣鼓,唱词多为表达祝福(如谱例2所示)。锡伯族唱秧歌与现今陕北等地的“沿门子”相类似。
谱例2 锡伯族唱秧歌调 [21] 2015年6月5日课题组在沈阳市兴隆台锡伯族镇新民村锡伯族唱秧歌传承人关义家采访,因调研期间为农忙季节,无演出活动,关义即兴编创唱词不够完整,笔者后根据镇政府工作人员所提供的关义演唱视频资料整理记谱。演唱人:关义,男,沈阳市兴隆台锡伯族镇新民村人,根据关义提供的由沈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颁发的证书显示,关义于2013年6月获批为锡伯族唱秧歌传承人。
关 义演唱
刘江峡记谱


锡伯族灯官秧歌以其一定的情节以及角色扮演成为灯官秧歌区别于东北大秧歌的重要标志。锡伯族灯官秧歌至少需7人参加表演,即“灯官”“太太”“丫鬟”和四个“轿夫”。灯官秧歌伴奏曲调主要是东北秧歌的曲牌,如【句句双】【满堂红】【大姑娘美】等,在音乐旋律上与周边其他地区的秧歌类音乐相同。锡伯族灯官秧歌与辽宁葫芦岛市建昌县现今流传的灯会秧歌、山西的灯官社火等的表演形式相类似,“非锡伯族所特有”[22]关意宁:《重塑、反哺的传统——基于口述资料的沈北锡伯族音乐舞蹈历史与现状研究》,《交响》,2017年,第3期,第40页。。

图1 锡伯族传承人魏云星等在表演锡伯族灯官秧歌(刘江峡拍摄)[23] 该照片拍摄时间为2014年5月16日(阴历四月十八)锡伯族西迁节,拍摄地点为沈北新区锡伯族文化广场。
在确立了灯官秧歌等地域音乐文化的民族性归属之后,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独特性的凸显与呈现成为东北地区锡伯族确立民族音乐文化之后的重要音乐文化实践,东北地区“锡伯族唱秧歌”“灯官秧歌”等音乐文化独特性的确立主要是通过与锡伯族生活范围圈内的周边其他村落音乐文化的横向比较而确立的,如锡伯族群众谈到“唱秧歌就我们村有,附近十里八村都没有”,“附近其他村的秧歌都是扭的,我们屯的秧歌是带唱的”时,该访谈资料中的“十里八村”“附近其他村”等表述所反映出来的即是将其音乐文化放置于一定的空间中进行横向对比,进而确立自身音乐文化独特性之所在,这一方式缺乏历史性的定位。法国结构主义者拉康·雅克(Jaques Lacan)在他的镜像理论中深刻分析了主体对自身认识的过程,他指出:“个体对自身的认识是由他人的目光之镜,社会的语言之镜来间接实现的。”[24]转引自郭粒粒:《他者身份认同与自我建构》,《文学界(理论版)》,2011年,第11期,第106页。任何“自我”的形成都伴随着一个幽灵般的他者,主体根本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相反,他受到无意识他者的左右。在拉康看来,自我要想确立自己的身份,必须要征得“他者”的承认。他者视角更关注当下文化,其更关注的是对“现在是谁”这一问题的追问,并为当下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寻找文化依据。东北地区锡伯族的现有锡伯族音乐文化即是在他者影响下形成的,其是由东北地区的地域音乐文化逐渐民族化而形成的,在与周边其他民族所共有的地域文化基础上通过“文化特性的凸显”[25]参见陈茂荣:《“民族认同”的源与流及其认同变迁》,《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第6期,第36-42页。强化锡伯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差异,并根据其有别于他者的特性作为锡伯族音乐文化民族性的文化边界。
三、结 语
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的历时性定位与空间性定位的差异直接导致了锡伯族音乐文化建构时所选择的根基文化的不同。比较而言,锡伯族文化精英群体倡导基于反哺音乐文化建构锡伯族音乐文化,而东北地区的锡伯族群众则更多地选择基于地域音乐文化的文化建构。其中对反哺音乐文化的强调反映了文化精英群体对锡伯族音乐文化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继承性的强调,其对“未来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则是建立在对“过去是谁”这一问题的分析基础上所做出的应然的文化取向,通过知晓传统而提出本民族应然的建构取向,并实现两域锡伯族音乐文化的共通。而对地域音乐文化的强调反映了东北地区锡伯族群众对文化发展现实性的考量,锡伯族群众对“未来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则是在对“我现在是谁”这一问题的基础上所作出的现实性的文化取向,考虑更多的是现实的可行性,文化建构的条件。
两种文化认同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的二重结构,并形成一定的文化认同张力,这种认同张力主要表现在群体内部不同主体对传统与现代音乐文化的选择上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可以实现统一融合,代表锡伯族传统文化的反哺音乐文化与锡伯族现代音乐文化应能实现文化认同的一致性。但这一认同的一致性需要传统与现代之间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其现有文化应是从传统文化中逐步演化而来,虽然形态等方面有一些改变,但其内在本质是一致的。而当前锡伯族音乐文化认同的二重结构的产生与存在,是由于东北地区锡伯族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对其传统音乐文化的历史继承性缺失而导致的,现有音乐文化与锡伯族传统文化之间缺乏内在的统一性。课题组在调查过程中所发现的锡伯族反哺音乐文化在东北地区文化归根过程中的“落地难”困境,也与东北地区锡伯族现有音乐文化与反哺音乐文化之间缺乏内在统一性有关。虽然反哺音乐文化在东北地区已经得到文化精英群体的认同与接受,但其在东北地区锡伯族群众中却一直存在“落地难”的困境,反哺音乐文化一直难以实现真正的“归根”。
锡伯族音乐文化建构的过程是两域锡伯族确认其共有文化的过程,东北地区锡伯族现存的两种音乐文化认同观念的并存,是寻求新的共有音乐文化的阶段性产物,认同的差异正是寻求新的共有文化的必经阶段。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建构该走向何方?反哺的音乐文化如何在这一文化认同的二重结构背景下融入至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生活中?如何让反哺的音乐文化成为东北地区锡伯族音乐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这些问题的解决成为关系到两种文化认同观念是否能够走向融合抑或走向统一的关键。这是笔者期冀在今后的研究中持续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