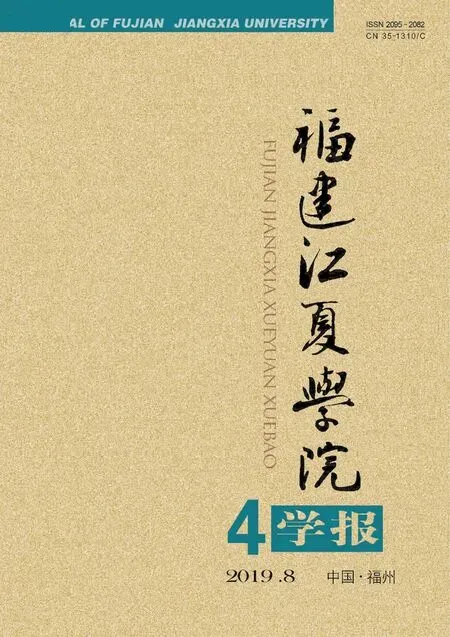论郑颐寿先生对辞章学理论的突出贡献
陈庆华
(福建江夏学院设计与创意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辞章学就是“大修辞学”或“广义修辞学”[1],它是以“话语艺术形式”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汉语辞章学是研究、总结汉语言话语艺术规律和方法的学科。它起源于先秦时期,具有几千年的历史,有关的理论研究散见于诗话、词话、文评、史论等史料之中。早期的汉语辞章学多以“辞”“语”“言”“文”等相称,这些名称与“情”“意”“理”“质”“心”等概念,形成“形式”与“内容”的对应关系。“辞章”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洪范·疏》的“言者,道其语有辞章也”[2]。此句中的“辞章”偏重于“文采”之意。通观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文评、史论等史料,未见关于汉语辞章学的明确定义。有别于古代汉语辞章学,现代汉语辞章学是为应对现代汉语的言语艺术之规律而产生的。诚如顾正彪先生在《汉语辞章学论集》的序中所说:“目前语文教材中的语文知识,大部分是从西方引进的。比如语法、语汇、语音、修辞等等,无不如此。它们同我们的汉语文有很大距离,甚至格格不入。正因为如此,这些知识教起来和学起来都相当吃力,而且对提高听说读写能力帮助不大。”[3]1在此背景下,1961年吕叔湘、张志公两位先生首倡“辞章学”(即现代汉语辞章学),用以搭建语言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培养听说读写能力的实际运用之间的桥梁。但此后由于诸多原因,辞章学的研究陷于停滞,直至1986年郑颐寿先生推出第一部辞章学专著——《辞章学概论》,才得以构建起相对成型的学科和理论体系。再而后经过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辞章学才形成更为科学和完善的理论体系。纵观现代汉语辞章学的发展历程,郑颐寿先生的贡献不容忽视,由于他的开拓和力耕之功,终使辞章学蔚为大观,成为汉语语言学花圃中的一株光彩夺目的新葩。他也因此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当代辞章学的奠基人”[4]89,并被学界誉为“最有成绩”“用力最勤、成果最大、认识最到位”[5]104的“四最”学者和中国现代辞章学研究的“领军学者”[6]4。
从20世纪80年代郑先生发表与“辞章学”有关的专论和著作开始,先后有十几部介绍修辞学的史书,多部反映国内外辞章学成就的高品位、学术性辞典对郑氏的学术成果给予正面肯定,诸多书、刊、报等论著与媒体也给予高度评价。根据这些评价媒介的不同特点和影响大小,笔者将其归为四类:第一类是反映全国性、世界性辞章学研究水平的专门辞典,如《修辞学词典》《汉语语法修辞词典》《世界新学科总览》《(世界)新潮文艺知识手册》《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家辞典》(韩国庆州大学赵诚焕著)等。这些辞典多以综述方式提及郑氏的贡献,介绍了郑氏在辞章学方面的研究特色和地位。第二类是反映修辞学科发展状况的史书通论,如《中国小学史》《中国现代修辞学史》《汉语修辞学史》《当代中国修辞学》《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中国修辞学通史(当代卷)》《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二十世纪中国修辞学》等。这些修辞史书或专章或独篇详细介绍了郑氏在修辞学、辞章学领域的创新和突破。第三类是当代的一些知名学者,如张寿康、张静、王德春、王希杰、陈光磊、黎运汉、濮侃、张德明、宗廷虎、陈满铭等所发表的专题文章和书评。他们都对郑颐寿先生的学术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赞誉。第四类是国内外的一些知名刊物和报纸对郑氏所发表的评介文章。如我国的《瞭望》《东南学刊》《读书》《修辞学习》《光明日报》《福建日报》《山西日报》《江苏日报》《明报》《国文天地》《中文》《修辞论丛》等,菲律宾的《世界日报》等,这些报刊从不同角度对郑氏的学术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由此可见,郑氏的研究成果是显著与突出的,因而得到广泛关注和充分肯定。根据上述评价和郑先生的生前谈话,本文将郑先生对辞章学理论的突出贡献总结如下。
一、创建根本性、宏观性的理论框架——“四元六维结构”理论
“四元六维结构”理论,又称“四六结构”理论。“四元”即宇宙元、表达元、话语元、接受元,“六维”即以这“四元”所构成的六对双向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这一理论是郑颐寿先生在借鉴古今中外相关学科的基础上,融汇有关文论而提出的根本性理论框架。它被用于统率辞章学的诸多中观、微观的理论,是郑颐寿先生对辞章学理论研究的极大突破和创新。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以后辞章学研究刚刚步入正途,其时虽有部分学人对辞章学的性质规律有所触及,但总体上还不成体系,尤其在理论的建构上还处于拓荒的状态,加之辞章学研究中遭遇到的系列难题和某些学者对理论不切实际的过分追求,导致整个辞章学的发展陷于被“边缘化”的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郑颐寿先生勇担大任,自觉挑起匡扶的使命。他在充分吸收和消化中华传统哲学思想和文艺理论的基础上,率先于1986年在其出版的《辞章学概论》中,第一次提出了“四六结构”的理论。其后,郑氏又借鉴语义三角形理论、信息的传播与反馈理论,将之前的理论体系作了进一步修改,并收入其专著《文艺修辞学·导论》(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进入21世纪,郑先生在对辞章学宏观、中观、微观的诸多理论问题和言语规律与方法的具体分析和实践过程中,不断改进和完善该理论,形成了以“四六结构”为统率的最新理论成果——《辞章学发凡》(海峡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这一理论的诞生与完善,是辞章学研究领域的大事件,它拓宽了辞章学研究的视野,开阔了研究的思路,有效地解决了辞章学研究中的“定位”“定义”“性质层次”“三辞三成关系”“体意先后”“辞章信息”“辞章表达(生成)”“辞章鉴识(解读)”“辞章双向互动”“辞章作用效果”“四元世界”等领域的系列难题,实现了辞章学研究的突破性发展,“为汉语语言学这座大厦树起了一根粗壮坚实的顶梁之柱”[6]4,成为我国汉语辞章学发展的“第一座里程碑”[6]3标志。
郑氏的“四六结构”理论呈现出独有的先进性和创新性,他对辞章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或与某些专家的理论不谋而合,或略为领先,或更加完美。著名语言学家王德春曾撰文说:“我一贯主张修辞学要突破以辞格为中心的框架,研究以语境为基础,以言语规律为重点的现代修辞学,不仅研究语言体系的修辞手段和方法,更要研究言语活动、言语机制和话语等方面的修辞现象。这与郑颐寿先生的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6]7著名修辞学专家宗廷虎先生在郑氏专著《辞章学发凡》的《序》中评价道:郑颐寿用来阐释辞章学之诸多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的“四元六维结构”比美国康奈尔大学阿布拉姆斯教授以作品为中心的“四要素三维三角”的批评结构图示“有很大的发展”,也比斯坦福大学刘若愚教授的“四要素四维圆形”的文论结构“图示更为完善”。[6]9需要注意的是,郑颐寿先生第一次提出“四六结构”,见于1986年出版的《辞章学概论》一书,而彼时由于国门尚开不久,有关美国学者阿布拉姆斯“四要素三维三角”的批评结构的论著《镜与灯》还没有引入中国,直至1989年12月该书才由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等引介进来。由此可见,在对文艺规律的探索与总结上,我国学者并不输于西方学者,甚至我们更为领先和完美,在这方面郑颐寿先生是杰出的代表。
二、确立辞章活动的最高原则是“诚”“美”兼论
“诚”与“美”是中国几千年来有关文艺规律的重要认识,它对中国学术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尤其是修辞学和辞章学。所谓“诚”,即修辞运用和辞章活动中要做到“修辞立其诚”。“修辞立其诚”出自《周易·乾》:“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7]长期以来,“修辞立其诚”被诸多修辞学家,包括顶尖级的修辞学家定为运用“修辞”的基本原则,甚至是唯一原则。但在郑颐寿先生看来,“这原则仅是对内容方面的要求,还未论及对‘修辞艺术’的要求。”[8]88郑先生从“修辞”语意的古今差异入手,认为“《易经》之‘修辞’与当代作为一个概念的‘修辞’不能划等号”,“修辞立其诚”中的“修辞”“是‘运用辞章’的意思”[8]88。对于“诚”的解释,郑氏在耙梳中国古代的相关论述后,认为“诚”,不仅有词汇义,而且还有“文化义”,即儒家所说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和道家所说的“真者,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戚人”。它“是合乎自然规律、合乎伦理道德、合乎上述要求的说写者的精诚的思想感情、能收到‘感人’效果的品德。我国古代哲人,讲修辞,讲风格,讲辞章的运用,都重视伦理道德”[8]88。郑氏将“修辞立其诚”这句话置于原来的历史语境,指出《周易·乾》中的“‘忠信’‘立诚’是针对‘进德修业’这特定‘内容’提出的要求”,而“‘辞章’讲的是‘艺术形式’,但它以‘有效、高效地表达、承载并借以适切、深入地理解话语信息’为前提,为其限制语。‘信息’(资讯)就是话语‘内容’”,而“辞章(含修辞)都是通过特定的形式表达或理解其所承载的内容。因此它既有对内容方面的要求‘诚’,还有对‘形式’方面的‘美’”。[8]89那么,辞章的“美”是什么呢?郑氏同样在《周易》中探微索隐,他认为,“《周易·贲》卦就是中国的第一篇论美的专文。”[8]89“贲”在《易序》中的解释为“贲者,饰也”,即今日所谓的文饰、修饰、装饰等意思。考其字源本义,上部为“卉”,指的是鲜美的草,下部为“贝”,指的是五彩缤纷的贝壳,两物结合,就是表示“美”的意思。而“美”的内涵亦包含“饰”“文”之意。这一发现给辞章这一“艺术形式”的要求以很大的启发。郑颐寿进而指出,“《周易》贲卦,在我国文化史上首次提出‘外饰’美的论题,它所讲的美,是要为内容服务的,也就是要达到‘文附质’的目的;也就是不使‘文灭质’。‘文质彬彬’应该是其本义。这道理通用于修辞——‘辞章的运用’。”[8]89由此,郑先生提出应该将“情诚辞贲”“情信辞巧”视为辞章学的“圭臬”。其中,“情诚”——“修辞立其诚”是就内容方面提出的要求,“辞贲”——“辞欲贲”是就形式方面提出的要求,两者结合,才是“修辞”——“运用辞章”的总原则,郑先生把它提炼抽象为“诚美律”。
郑颐寿对辞章活动原则的补充和完善,加深了人们对辞章运用中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的认识,“为辞章学的社会化、群众化解决了重大的理论问题。”[6]10对此,台湾知名学者陈满铭评价说:“郑颐寿教授对《汉语辞章学》这一新学科,不但兼顾宏观与微观来研究,也将理论与实际应用作了高度之结合,尤其从中提炼出‘四六结构’与‘诚美律’,将‘真’‘善’‘美’融为一体来统括《汉语辞章学》’,其贡献与影响是极大的。”[9]陈先生还在其专著《当代辞章创作及研究评析——以成惕轩、罗门与王希杰、郑颐寿、曾祥芹、赵山林等大师为对象》中对郑先生的“诚美律”理论进行了专章介绍,并强调“由此更足以见出郑颐寿辞章‘诚美律’说之重大成就以及它对辞章学不可磨灭的贡献”[10]。
三、首次提出“常格”“变格”“畸格”的语格理论
常格就是合乎常规的言语,即遵守文字学、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的一般规律,能够按照字面理解的言语现象。变格就是超出常规的言语,即突破文字学、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逻辑学、心理学的常规,不能按照字面来理解的言语现象。畸格则是违反了常格与变格及其运用原则的言语,它不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所谓“语格”指的是运用语言的规律、方法的品格。“常格”“变格”“畸格”是“语格”的三种形态。这一理论首见于1986年出版的《辞章学概论》,它是郑颐寿先生在吸取陈望道先生“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又受启于张弓先生关于“是不是仍保持词语的本义、常义,是不是不发生转义”“表层结构是不是突破结构常规”等的理论基础上,从中华五千年以来“常”与“变”的哲学关系中,参考古今中外语言学家、文艺评论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的理论,尤其是孔子、孟子、刘勰、吴乔、陈永康、郑板桥、叶圣陶、秦牧、亚里士多德、达芬奇、康德、洛儿伽等的相关论述,而提出来的新概念、新理论。在郑先生看来,“常格”“变格”“畸格”(其中“常格”与“变格”合称为“健格”)反映了言语活动的内在规律,属于“四六结构”中“话语元”的规律,因此将其命名为辞律的“内律”。它们之间的关系可用数学的坐标进行表示,即“健格”是“零点以上”的,“畸格”是“零点以下”的,“常格”是“规范的”,“变格”是“正向的偏离”,“畸格”是“反向的偏离”。他认为,“消除畸格,使之成为常格,这是辞章修养的起码要求”[11]223“由畸格到常格,这是一种进步;由畸格到变格,则是一种飞跃。这后一种改动,真是化腐朽为神奇”[11]225。
郑先生的这一理论建构起辞章学内部微观层面的科学体系,解决了文学界与语言学界长期存在的关于语言规范问题的争论,大大推进了辞章学的发展。为此,宗廷虎先生在其主编的《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下卷)》中指出:“文学界与语言学界关于文学语言规范问题的争论,大都表现为对变格与畸格关系的认识偏差。郑颐寿从辩证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指出‘变’与‘畸’转化的临界的‘度’,是有积极意义的。……使其研究更具说服力。”[12]
郑氏提出的“常格”“变格”“畸格”的理论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中国人文科学总干事庞朴先生于2004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浅说一分为三》中的“常”“变”“畸”的提法相对应。庞先生指出:“一切事物,都有常态,有变态,有正态,有畸形。人类认识亦复如此。”[13]107这一见解从哲学上印证了郑先生理论上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使其成为郑先生“常格”“变格”“畸格”理论的最好注脚。
四、发现辞章学原创性理论的制导性“秘诀”——“中华密码”
所谓“中华密码”,即从《易经》和《老子》这两部中华元典中概括出来的“○一二四多”和“○一二三多”,及其反向排列(即“多四二一○”和“多三二一○”)所构成的密码,并用这些密码来诠释和推衍事物变化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又被概述为“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分为多”及其反向(“合二为一”“合三为一”“合多为一”)。它是郑颐寿先生在研究辞章学及其分支学科的过程中,在考究儒道哲学的基础上,参照和验证于西方哲学,从中提炼出来的中国古代哲学精要,是郑氏研究中国古代辞章学及其分支学科形成原创性理论的“秘诀”。
在郑氏看来,哲学是科学的科学,任何时代的学人在从事学术研究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哲学思潮的制导和影响。古代并没有马克思主义,但我国早有自己朴素的辩证法,郑氏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从事源自于先秦之辞章学及其分支学科研究时,常常探本溯源,关注中华元典对先人们的学术影响。他发现来自《易经》和《老子》两部元典的哲理智慧,广大精微,包罗万象,充满着孕育新生事物的生命能量,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郑先生认为,“古代汉语辞章学是言语艺术的国学,它的哲学密码之一‘○一二四多’来源于先秦‘群经之首’的《易经》。《易经》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14]20他又指出,《老子》第42章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是又一个‘密码’,可用‘○一二三多’来表示”[14]22。上述的“密码”及其反向被郑颐寿先生合称为“中华密码”,它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中“阴阳磨”“阴阳争”“阴阳和”“阴阳合”等多元的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成为古人推衍事物发展变化的重要理论根据。
郑先生从《易经》和《老子》这两部中华元典中提炼出来的“中华密码”,与台湾著名学者陈满铭先生提出的“○一二多”及其反向“多二一○”所构成的章法学理论基础——“阴阳双螺旋互动系统”十分相似,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就其相似性而言,两者的理论基础都源自于《易经》和《老子》,都强调事物中存在着的“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一分为多”与“合多为一”的特性,即“对立”的“两体”(对立体)和“统一”的“一体”(统一体)。就其不同点而言,前者除了关注到上述特性外,还注意到阴阳交融与渗透过程中产生的“中间体”或“融合体”现象,亦即“一分为三”。郑先生以太极图为例,指出“正是‘阳’的一方发展到最壮大之际,开始了‘阴’的生成;又正是‘阴’的一方发展到最壮大之际,开始了‘阳’的复生”“‘阴阳’转变的过程,都有其中间融合的阶段。此图揭示了矛盾转变的规律,可用来说明万事万物,由始生到极盛,或由极盛到衰亡,整个消长、变化的过程,都是三分的”。[14]25郑先生还以“山之主脉与支脉,河之主流与支流,树干、树枝与树梢;树枝与树叶,花萼与花瓣”[14]23的关系为证,指出它们中存在着的“对生、三生、多生”[14]23的可能,强调“一分为三”所具有的普遍性。郑先生的上述认识在庞朴先生的《浅说一分为三》中得到充分印证。庞朴先生认为,“一分为三的事实,则是客观的无处不在的”“世界本来便是三分的”[13]2,他将“一分为三”视为“东方密码”。有别于庞朴的“东方密码”和陈满铭的“螺旋结构”,郑颐寿的“中华密码”不仅关注“一分为二”与“一分为多”及其反向(“合二为一”与“合多为一”),而且关注“一分为三”及其反向(“合三为一”),其密码中的“○一二四多”特别标出“四”与“一二”相配,以突出其不断地“一分为二”的这一辩证法的特性,而“○一二三多”则特别标出“三”和“多”,以突出其“一分为三”和“一分为多”的特性。因此,就其理论体系而言,更为全面和客观。
郑先生运用以上“密码”体系探寻作为言语艺术国学的辞章学理论和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在辞体分类方面,在先生之前,学界通行着“实用体”“艺术体”的观念,郑先生根据“一分为三”的密码,提出在上述“两体”之外,还存在“融合体”的现象。这一观点在当时可谓独具慧眼,令人耳目一新。又如,先生在对媒体的分类过程中,在以往“口语”和“书语”的基础上,提出存在“电语”的新类,这一观点也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和采纳。再如,在研究、总结语格三组九对的对立统一的变化规律与方法中,提出了建立语格辞章学及其下位的三门学科:规范辞章学、常格辞章学、变格辞章学的观点。这些都是郑先生在实践中灵活运用“一分为三”密码,创建新学科、新体系的几则例证。事实上,郑先生对“中华密码”的运用呈现出行稳致远的常态,他的理论体系随处可见由“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分为多”及其反向(“合二为一”“合三为一”“合多为一”)而描绘的理论图谱,并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丰筋多力的特性。
除了以上贡献外,郑先生还创造性地提出“体素”“格素”等术语,用于概括语体风格的类型,这些术语后来也被学界普遍采纳,成为辞章学理论的重要范畴。郑先生在辞章学领域的系列创新与突破,受到同行专家的热切关注和一致好评。早在20世纪90年代,由林道周和张学惠主编的《福建社会科学研究概览(1949—1989)》就指出:“修辞学是十年来现代汉语研究中进步最快的领域。从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看,最有成绩的是郑颐寿。”[15]21世纪初,高万云先生在台湾《中文》刊物发表《郑颐寿的辞章修辞学研究》,强调在扩大修辞学研究的范围方面,“后来,陈望道、吕叔湘、张志公、宗廷虎、倪宝元、王希杰等学者,都对修辞学的范围有着相似的认识,而用力最勤、成果最大、认识最到位的应该是郑颐寿。”[5]104这些评价成为郑先生获誉“四最”学者的赞誉之源。郑先生在辞章学领域的突出贡献还得到社科界的高度肯定,他也因此多次获得福建省社会科学奖项,其中,两次获得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第七届获奖论著为《辞章学发凡》,第八届获奖论著为《辞章体裁风格学》),三次获得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获奖作品有《比较修辞》《文艺修辞学·导论》《言语修养》)。有鉴于此,中国修辞学会会长、著名语言学家张静先生称许其为中国现代辞章学研究的“领军学者”。[6]4
综上所述,郑颐寿先生对辞章学的贡献是极为重大和突出的。在汉语辞章学的发展历史上,他为“学科的奠基与建设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他出版了重要专著、论文,为辞章学学科系统化奠定了理论基础”。[16]正因如此,他也被视为“国内外公认的中国当代辞章学的奠基人”[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