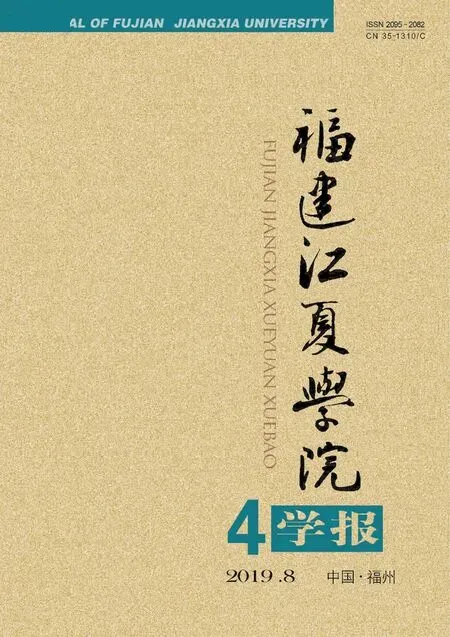人的认知与客观世界
——论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她的埋在土中的小狗》
关冰冰,杨炳菁
(1.浙江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浙江杭州,310023;2.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北京,100089)
一、前言
《她的埋在土中的小狗》(以下简称《小狗》)是收录在村上春树短篇小说集《去中国的小船》中的作品。从叙述结构看,《小狗》中明显存在着“我”和“她”以及“我”和恋人这两个故事。而且在和“她”分开后,“我”开始给恋人打电话,因此,两个故事之间应存在某种关联。然而,有关《小狗》的早期研究却将其看作表现“精神创伤”以及创伤治疗的故事,认为该作品是把“对话疗法伪装成小说”[1]45,是“分析疗法教科书式的病症研究”[1]48。由于所谓的“精神创伤”及治疗都出现在“我”与“她”的故事中,因此早期研究存在忽视“我”与恋人之间故事的问题。
2000年以后,出现酒井英行、山根由美惠、津久井秀一等人对《小狗》的研究。酒井英行认为,“她”就是“我”的分身,对“她”的治疗导致“我”和恋人(即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改变。山根由美惠在指出“精神创伤”仅仅是推动小说情节向前发展的道具后说道:“在《小狗》这一作品中,存在藉由他者关系改变自身的文本结构。”[2]277津久井秀一认为,治疗只是“‘我’与‘她’对话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偶然结果”[4]53。在治疗过程中,“发挥途径作用的是‘我’所特有的、‘无法表达的部分’(即‘空虚’与‘孤独’)”[4]54,而“我”与恋人之间的故事表明“我”试图冲破“虚无”与“孤独”,回归现实。
与早期研究相比,上述三人的研究具有以下特征:首先,虽然“精神创伤”及治疗依旧是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但不论是山根由美惠的“推动情节发展的道具”,还是津久井秀一的“偶然结果”,都表明在研究者看来其对小说的重要性在逐步减弱;其次,以上三人都承认小说中存在两个故事,而这两个故事的关系是“我”在与“她”接触后要改变“我”与恋人之间的现状。
正如前文所言,由于“精神创伤”及治疗存在于“我”和“她”的故事中,因此,当研究者仅聚焦于“我”和“她”的故事时,其重要性便会被放大。相反,当“我”和恋人的故事受到关注,其重要性必然会被弱化。由于上述三人所要处理的是小说中两个故事存在何种关系,因此弱化对“精神创伤”的关注是自然而然的事。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三者都认为两个故事的关系是“我”在与“她”接触后要改变“我”与恋人之间的现状,但在回答具体改变了什么这一问题上,三者却显示出不同。
酒井英行所说的“我”与恋人(外部世界)的关系意味着“我”与恋人(外部世界)处于不可分的状况中,“我”给恋人打电话是因为不满意自己与恋人所处的状态,因此给恋人打电话是手段,改变与恋人的关系是目的。而山根由美惠的“藉由他者关系改变自身”与此不同,改变自身是目的,因为要改变自身所以有了给恋人打电话这一行为。二者的根本区别是:酒井英行说的是“我”要修正与他人的关系,山根由美惠说的是“我”要修正自身。津久井秀一与山根由美惠一致,只是他把“我”需要修正的内容赋予了“虚无”“孤独”等具体内涵。
判定《小狗》究竟是一部要修正与他人关系的小说,还是一部修正自身的小说非常重要,因为这决定了《小狗》的主题。笔者认为,上述三者之所以出现不同结论,是因为他们都在试图解释“我”与“她”分手后给恋人打电话意味着什么,也就是将焦点都集中在了故事的结局。但故事的结局往往是由开端决定的,而上述三人恰恰忽视了这一点。事实上,“我”和“她”在度假旅馆偶遇前没有任何关系。在偶遇后,“我”对其产生关注,然后才有后面的交往,以致最后影响到“我”和恋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一开始的关注,就不可能有后面的事情。因此,探明“我”对其产生关注的原因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回答“我”给恋人打电话是为了修正与他人的关系还是为了修正自身这一问题的基础,也是揭示小说主题的关键。
二、“我”对“她”关注的起因
由于“我”在与“她”偶遇前并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在偶遇后也不存在第三方推动要素,所以二人要想发生故事,必定是其中一方引起了另一方的关注。阅读小说可以知道,是“我”先开始关注“她”,但“我”究竟是在何时真正开始关注“她”呢?
“我”首次遇到“她”是在度假旅馆的餐厅里,“当我用咖啡壶往杯里倒第二杯咖啡时,一个年轻女子走进餐厅。”[5]127小说随后描写了“她”的服饰、进餐厅时的表情以及点餐的过程,但这些并未引起“我”对“她”的特别兴趣,因为在服饰描写后“我”只是和男侍应生一样“舒了口气”[5]127,而之所以如此则在于“因了她的出现,宾馆餐厅终于开始像宾馆餐厅了”[5]127。将“我”与男侍应生们的感觉等同起来,说明此时“我”对“她”并未感到什么特殊,造成上述效果恐怕仅仅因为“她”是一位年轻女子。在“她”“打量餐厅,一时间显出困惑”[5]127后,“我”也立刻认为“情有可原。虽说是度假宾馆的下雨的星期五,但早餐席上只有一个客人无论如何也过于冷清”[5]127。而对她点餐时那种“似乎习惯于对别人颐指气使的说法”[5]127,“我”也马上评判到“那种说法的确是有的”[5]127。这说明,“我”对“她”的上述举止、态度都作出了至少“我”认为合理的解释,所以,此时的“她”并未让“我”感到有什么特别。让“我”觉得特别的是点餐之后。
点完菜,她臂肘拄在桌上,手托下巴,和我一样看雨。由于我和她相对而坐,我得以隔着咖啡壶把手有意无意地观察她。她诚然在看雨,但我不大清楚她是否真的看雨。似乎在看雨的彼侧或雨的此侧。三天时间我始终看雨,对雨的看法已相当成熟,分得出真正看雨和不真正看雨的人。[5]127
这段内容含有诸多重要信息。第一,“三天时间我始终看雨,对雨的看法已经相当成熟”,说明前三天“我”并非仅仅是把“雨”作为一种风景来看待,看雨的同时“我”进行了深刻地思考。而“对雨的看法已经相当成熟”,表明“我”对自己看法颇具信心。第二,“分得出真正看雨和不真正看雨的人”表明,“我”依据自己的心得能把看雨之人分成“真”和“假”两部分。第三,“我不太清楚她是否真的看雨”,说明在“我”自认为比较得意的“看雨”这一领域却无法对“她”作出准确的判断。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原文中,“真”这个词是以着重号的方式加以强调的。此标记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我”对“她”看雨方式无从判断的状态。换句话说,至少在此阶段,“她”对“我”来讲是不可解的。第四,从“似乎在看雨的彼侧或雨的此侧”中可以发现,“我”将雨分为“彼侧”和“此侧”。这里暂且不论“彼侧”和“此侧”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二者毫无疑问有着本质性区别。因为在小说中,“雨把灰濛濛的天空和暗沉沉的大海的界抹得一干二净”[5]126,连平时可见的绿岛也无从寻觅。也就是说,单从这一描写便可以发现,雨的“此侧”只有灰濛濛的天空和暗沉沉的大海,但“彼侧”则会有小小的绿岛。
虽然从以上信息无法窥探“我”对雨看法的实质性内容,但从上面分析中可以发现,“我”对“她”开始真正产生关注并非是其衣着、进餐厅后的表情以及点餐过程,而是“她”看雨的方式。相比之前“她”的那些态度、举止,“我”无法对其看雨的方式给予解释,而这也正是“我”对“她”产生关注的开始。
正是由于“她”看雨的方式让“我”不解,因此,在那之后“我”开始对其展开全面观察,而小说也在这之后分别描写了“她”的头发、耳朵、习惯性动作、个子、相貌等。总体来讲,“我”对“她”“感觉也不特别坏。衣着格调到位,举止也够脱俗”[5]128。但“她全然没有下雨的星期五独自在度假宾馆里吃早餐的年轻女子很容易挥发的那种特有氛围。她普普通通地喝咖啡,普普通通地往面包卷上抹黄油,普普通通地把熏肉炒蛋夹到口中”[5]128。“衣着格调到位,举止也脱俗”表明“我”对“她”抱有好感。然而,通过其后的描写可以发现,这种好感并非来自异性的吸引,因为“她”的所有动作都让“我”觉得“普普通通”。事实上,“我”之所以对“她”加以观察是为了弄清“她”看雨的方式而非其他。然而,“她”的一切是那么普通,这就使得“我”无法单纯根据外貌、举止解释其看雨的方式。既然如此,“我”要想寻求答案便只能去探求“她”的内心世界,而这就是故事开始的契机。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明白,“我”之所以对“她”产生关注,是由于“她”在“我”自认为得意的领域显示出不可解性。此种不可解便是“我”对“她”产生关注的根本原因。如果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这应属于“我”的认知需要。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其代表作《动机与人格》中将人的基本需要划分为不同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和基本的认知需要。[6]15-28其中,认知需要是“获取知识,使宇宙系统化”的过程,也是“自我实现的表达方式”[6]26。“我”已经看了三天雨,且自认为对雨的看法相当成熟,然而“我”却无法判断“她”是否真的在看雨,这说明由于“她”的出现使“我”无法完成对外部世界已经形成的系统化,由此便产生新的认知需要。换言之,这种对“她”的关注以及希望探究其内心世界的欲望来自“我”的认知需要,某种意义上也是“我”“自我实现的一个表达方式”。
判明“我”对“她”产生关注的根本原因,来自于“我”的认知需要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我”之所以关注“她”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并非“她”的问题,那么由此一来,“她”所具有的“精神创伤”便不再是该小说所主要反映的问题。此外,所谓“我”自己的问题指的也并不是“我”与他人的关系,“我”与他人的关系是马斯洛需求层次中的归属需要。尽管这也是人的基本需要,但却不是小说所重点描写的“我”和“她”产生故事的契机。因此,从这一角度讲,《小狗》所反映的并不是“我”对自己人际关系的修正,而是通过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探求来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
三、“我”对“她”关注的实质
“我”对“她”关注是因为“我”无法判断“她”是否真的看雨,是在看雨的彼侧还是此侧。然而,“她”看雨的方式何以如此令“我”介怀,以致产生认知需要?要想弄清这一问题必须阐明雨之于“我”的重要性。
从小说的叙述看,与“她”偶遇前基本是以对雨的描写为主。因此,单纯从逻辑上讲,如果“我”关注“她”具有某种必然性的话,那么,雨应该在其中起到某种作用。而且“我”在度假旅馆共停留四天,第五天离开,而前三天都是在看雨。单纯从时间的角度来讲,看雨占据了大部分时间,花这么长时间在屋子里看雨,那么,雨对“我”来讲也应具有某种特殊意义。
窗外仍在下雨,已连下三天了。单调的、无个性的、不屈不挠的雨。
雨几乎是与我到达这里同时下起的。翌日早上睁开眼睛时雨还在下,晚上睡觉时也下,如此反复了三天,一次也没停止。不,也许不然,也许实际上停过几次。即使停过,那也是在我睡着时或移开眼睛时停的。在我往外看时雨总是下个不停,每次睁眼醒来都在下。
雨这东西有时候纯属个人体验。就是说,在意识以雨为中心旋转的同时,雨也以意识味中心旋转——说法固然十分模棱两可,但作为体验是有的。而这时我的脑袋便乱作一团,因为我不知道此时我们看的是哪一侧的雨,但如此说法实在过于个人化,说到底,雨只是雨罢了。[5]125
上面是小说的第一节,从时间上讲正是“我”到旅馆后的前三天。这一节由三段话组成,前两段似乎是在描写窗外正在下的具体的雨,而第三段则完全脱离具体的雨,描写一般意义上的雨对“我”所产生的作用。也就是说,第三段是在写“我”对雨的看法。不过,其实在前两段里,有关窗外正在下的雨的描写也很少。松本隆曾对小说前两段中“雨”字后面的助词「は」和「が」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助词的使用看,叙述者是“一边眺望着不停歇的雨,一边沉溺于对过去的回想,最终又提及现实世界的雨”[7]105。具体来讲就是两段文字“由客观描写现实世界的「雨が」作为第一句和最后一句,中间则是表示观念世界的、带有主观性的「雨は」”[7]105。通过松本隆的结论可以明白,在小说的前两段中,除了第一句和最后一句是在描写“我”眼前所见的客观上正下着的雨以外,其它句子中的雨都属于“我”的主观部分,是通过雨对过去所进行的回想。在这种情况下加上第三段文字便可以知道,小说第一小节的重点并非是对窗外下着的雨进行客观描写,而是表达了“我”对雨的看法。
那么,“我”对雨究竟有怎样的看法?通过考察上述引用可以发现,“我”首先提出了一个关于“雨”是否停过的命题。事实上,只要稍作调查便可以准确知道三天中雨是否停过。然而,“我”的兴趣却并非在于客观上雨是否停过,“我”所要表达的是:对于“我”来讲,也就是在“我”的认识上,这三天中“雨从未停过”(此处用了「は」)。但雨或许停过,因为“我”有睡觉和没看雨的时候。在此种情况下,让“我”头脑混乱的问题便出现了,即究竟是“我”的认识是现实,还是作为客观事实而下着的雨是现实?“我”没看到雨停过,那结论自然是雨一直在下;与此相对,雨或许在客观上停过,但由于“我”睡觉或者做其它事情而没有看到。那么,究竟哪一方对“我”来讲是可称为现实呢?
很明显,这里涉及客观世界以及人对其进行认识的问题。客观世界在那里,人要对它加以认识。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当然有一个过程,即所谓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认知过程是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观察,“亦即人脑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形式反映客观对象的性质及对象间关系的过程。”[8]人类认识世界是从感觉和知觉开始的,人们感知事物时以注意为前提,并从众多信息中将有用的信息筛检过滤,储存到记忆系统,继而形成表象和概念。这个过程用小说中的情况来说就是,窗外下着雨,“我”对其进行感知,并将相关信息筛检过滤储存在记忆系统,最终得出雨一直在下的结论。
一般情况下,人们当然会认为自己通过认知过程得出的结论是客观的,反映现实的,并用得出的结论指导自身的行为。但该过程或许存在问题,因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有时会有缺陷。例如,由于“下雨”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它或许一直下,或许下了停,停了下,而且“我”虽然三天都在看雨,但却并不是24小时一直看雨,这或许就会导致雨一直在下的结论与客观世界中雨的真实状态发生偏差。虽然此种偏差是否真的存在并不清楚,但从逻辑上讲肯定存在着完全客观的雨和“我”所认知的雨。客观世界的雨不经过“我”的认识便无法形成“三天一直在下”的结论(概念),但“我”所得出的结论或许会存在偏差。因此,“我”便会有不明白雨的一方是现实的,还是“我”这一方是现实的感觉。而客观世界的雨和“我”所认知的雨之间的关系用小说原文来表达就是:以雨为中心意识在回转的同时以意识为中心雨在回转。这里的第一个“雨”代表了客观世界的雨,而第二个“雨”代表了“我”所认知的“雨”。它反映了一个由意识为中转站,客观世界的雨变为“我”所认知的雨的过程。
上述内容应该是“我”在看雨的三天里所思考的问题。简单来讲可以概括为:虽然我们对客观世界会产生认知,但此种认知很难做到与处于动态的客观世界的真实状态相吻合。那么,究竟哪一方对我们来讲是现实的呢?论述到此便可以回答为何不知“她”是否真的看雨,看雨的彼侧还是此侧能够引起“我”的关注。首先,雨是“我”思考客观世界和人类认知之间处于何种关系的对象。在入住度假旅馆的头三天,“我”通过对雨的观察和思考得出“以雨为中心意识在回转的同时以意识为中心雨在回转”的结论。其次,当把“我”对雨的思考与小说中有关雨中景物的描写相结合后就会发现,所谓雨的此侧虽是“灰蒙蒙的天空和暗沉沉的大海”,但却代表了人所认知的客观世界;而雨的彼侧,既是指因下雨而无从寻觅的“小小绿岛”,也代表了真实存在的客观世界。因此,“她”是否真的看雨,到底是在看雨的彼侧还是此侧,便与“我”看雨时的思考具有了相似性。也就是说,“我”在看了三天雨之后,得出“以雨为中心意识在回转的同时以意识为中心雨在回转”的结论。该结论虽然反映出人的认知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差异,但却没有解决客观世界和人的认知究竟哪一方具有现实性的问题。而从看雨的方式上,“我”觉察到“她”或许和“我”一样不知将何种客观世界作为现实,由此便产生对其进行了解的必然。因为了解“她”或许可以解决“我”自己所抱有的问题。
四、“我”对“她”关注的结果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知道,“我”虽然通过看雨思考了问题,并获得了成熟的看法,但此种成熟仅限于人的认知与客观世界存在差异这一点上,用小说中的表达便是雨的此侧和彼侧的差异。然而雨的此侧和彼侧,也就是人的认知和客观世界究竟哪一方才更具现实性,却是“我”依然抱有的问题。那么,“她”的经历是否给了“我”最终答案?
从一般意义上讲,较之人的认知,客观世界毫无疑问更具现实性。然而,这里却存在着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那就是对于人来讲,客观世界只有通过人的认知才能成立。因此,探讨人的认知和客观世界何者更具现实性的问题,其本质是一个应如何面对自己认知的问题。那么,“她”是如何面对自己的认知呢?
在小说中,“她”觉得自己手上一直残存着挖小狗坟墓时所留下的气味,且多少“给人以固执己见之感”[5]128。此种状态不但表明“她”是以自己的认知作为客观世界本身,且更是用该认知作为自己日常行为的某种指导。在挖小狗坟墓时,或许的确有某种气味残存在“她”手上,且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但当“我”嗅“她”的手时却发现,“她”手上“只有香皂味儿”[5]161。显然,“她”的认知与客观世界的真实状态存在决定性差异。然而,“她”却执着于自己的认知,且以此种带有差异的认知指导行为,这或许正是此前先行研究之所以将目光聚焦于“她”是否属于“精神创伤”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在小说中“她”不但曾经意识到自己认知方面可能出现了问题,且有机会避免该问题。在回忆当年这段经历时,“她”讲道:“当时最让我意外的,是自己一点都不害怕。(中略)什么也没有,什么感情也没有,简直就像去信箱取回报纸。”[5]159“她”所感到的“意外”清晰地表明,“她”当时便已意识到自己的认知出现某种问题。而当“她”拔装有小狗的箱盖钉子时,曾有电话打进来,且铃声持续了二十次。这二十声电话铃被认为是“来自于‘外面的世界’、某一个能够感觉其真实存在的他者的呼唤。是一种把想重新回到‘与小狗的世界’的她带回‘外面的世界’的呼唤”[3]40。那么,如果“她”在意识到问题后选择去接电话,或许应该就能避免其认知所发生的问题,“她”可能也会和今天的样子有所不同。
人的认知与客观世界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不仅停留在认知层面上,更会给予行动极大的影响;当意识到认知存在问题时,通过某种契机或努力很可能避免问题。以上两点可以说是“我”从“她”的经历中所获得的启发。或许正是因为此种启发,在与“她”分手后,“我”开始给恋人打电话。显然,这一行为意味着“我”要通过努力改变自己。而“我”之所以要改变自己,其原因当然在于现在的“我”其实与挖院土时的“她”极为相似,也正处于认知存在问题的阶段。
小说中,“我”来的这家旅馆是一家老式度假宾馆。这里的一切“都让我喜欢”[5]129,但“再过几年——也许不出十年——这一切必然灰飞烟灭”[5]129。虽然“改建日期显然迫在眉睫”[5]129,但我却希望“改建日期多少推后”[5]129。“我”对这家就要被改建的度假旅馆的情感,某种意义上就像“她”虽也知道应该走向外面的世界,但却依旧喜欢与小狗一起封闭在自我的世界。此外,“我”来度假旅馆前刚与恋人吵完,二人正处于分手的边缘。虽然提出分手的是恋人,但原因却应该在“我”。因为“我”对所有恋人都不是一种“爱”,而仅仅是“钟意”。在此种情况下,“我”虽然“想到同她分手另找新女孩”[5]149,但却“一阵心烦”,因为“一切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5]149。事实上,即便“我”不嫌麻烦另找新的女朋友,但最终结局也依旧不会改变。因为在这个恋人之前,“我”已经有多个女友,这从“我屡次领着女友来这家宾馆。若干个女友”[5]129的表达中可见一斑。这说明,虽然“我”想回到与现在恋人的状态,但却存在问题,而这是与“她”想要回到与小狗的世界时发现存在问题是一致的。
“我让铃响了二十五遍,然后放回听筒。夜风摇曳着窗边薄薄的纱窗,涛声也传来了。我再次拿起听筒,重新拨动号码,慢慢地拨。”[5]161-162二十五遍这个数字明显与“她”所经历的二十遍电话铃相呼应。如果二十遍铃声没能使“她”重回现实世界,那么,比这更多的二十五遍铃声或许就能让“我”摆脱与恋人间所存在的问题。如果不行,那就继续拨打,恋人不接电话也无妨。虽说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我”的此种行为正是在确认自我认知存在很大问题后寻求改变的一个方式。
五、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小狗》是一部要进行自我修正的故事。具体来讲,就是表现人所认知的现实世界究竟与纯粹客观的现实世界处于何种关系,以及如何处理人的认知与客观世界间所存在的偏差的问题。《小狗》中的两个故事具有不同的作用。与恋人的故事给“我”带来了问题,促使“我”思考,与“她”的故事让“我”明白了问题的实质,并着手解决。虽然小说最后仅仅写到“我”给恋人不停地打电话这一试图改变的行为,而没有提及最终结果,但它却给人极大启示,那就是当意识到问题的实质后,要去努力改变自身。
人的认知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可以说自村上春树文学开始便是其重要的表现内容。1979年,《且听风吟》出版,小说的第一章被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视为“可以用作讨论他后期创作的参照”[9]。在这一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要努力认识的对象和实际认识的对象之间,总是横陈着一道深渊,无论用怎样长的尺都无法完全测出其深度。我这里所能够书写出来的,不过是一览表而已。”[10]5“但我还是这样想:如若进展顺利,或许在几年或十几年之后可以发现解脱了的自己。到那时,大象将会重返平原,而我将用更为美妙的语言描述这个世界。”[10]27年后的1986年,当《小狗》发表时,努力认识的对象和实际认识的对象间的那道深渊似乎依旧横陈在村上的面前。然而,与《且听风吟》不同的是,在《小狗》中可以真切地看到“我”为试图跨越而作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