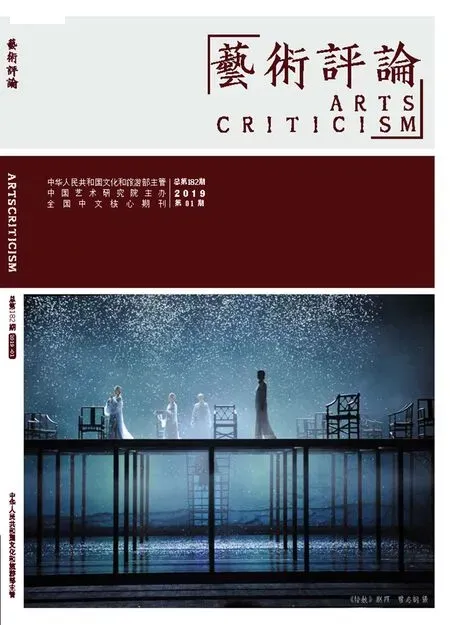“艺乘”十年
——陶身体剧场的质朴身体·剧场
慕 羽
演出延迟了一会儿,约莫有8分钟,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的观众还是比较安静的,像是都准备好了,共赴一次身心合一的约会。即将上演的是“陶身体剧场十周年纪念演出”。这是一支仪式感十足的团队。从起舞到谢幕,静谧肃穆的气场一以贯之,不显露任何情绪、情感,律动已经沉入了舞者们的细胞、器官、组织、系统。虽然一直以强大的理性能量驱动身体,但首演当日的演后谈上,陶身体剧场的三位创始人——陶冶、段妮、王好都动情了,这一刻很微妙,让我感到纯粹生命的美好!舞者和观众之间仿佛产生了某种电磁场,随时间的变化而相互作用着,从演出伊始到演后交谈。
这些年,跟随陶身体剧场的起舞逻辑,抑或是生命涌动的现场,我都能感受到他们是在用身体认知世界,这种体验让我想到波兰剧场大师格洛托夫斯基(Jerzy Grotowski)留给人类的精神遗产——“艺乘”的理念。十年间,陶身体剧场所有的作品本质上没有区别,重点在于身体的修炼。套用一句格洛托夫斯基的话来说:“舞蹈不是目的,舞蹈只是条道路。”
低调的舞者 高调地起舞
2018年,对中国现代舞而言,迎来建团十周年纪念的陶身体剧场已经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代言”了,最大的变化便是国内文化艺术和舞蹈界对其认知度的提升。这与五年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墙内开花墙外香”是当时我对他们的一个印象。2011年我刚从纽约访学回来,恰好闻到了这股独特幽香。
那年,他们登陆了2011年的纽约“秋季舞蹈节”——纽约的一项品牌文化盛事。该舞蹈节的选拔像一个大筛子,专门邀请过去一年间在全美各地最受欢迎的团体和作品齐聚一堂。可想而知,陶身体剧场2010年在美国舞蹈节的首次亮相就让他们脱颖而出了。没想到,这个在中国曾经极为低调、甚至边缘的现代舞小团队,刚登上国际舞台就如此高调。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算得上中国最具国际性的年轻一代舞蹈人了。
不同于文化外交式的礼节性交流演出,专业的国际表演艺术舞台有着十分苛刻的艺术标准。作为当代艺术维度的现代舞,始终强调的便是一种先锋的、开拓的、实验的精神。其实,他们之所以能如此高调地起舞,根本上源自于他们一直是低调的舞者。陶冶成立陶身体剧场后,首要的事情便是让自己的心“安静”和“简单”下来。尽管开初,这个过程颇为艰难、拮据、枯燥,然而年轻的陶冶却沉浸其中,这一专注,就是十年。
五年前,我明显感受到了一个变化正在发生,或许正源自于陶身体剧场参加第二届“北京国际芭蕾舞暨编舞比赛”开幕式的演出,这让他们登上了国内最重要的主流文艺平台——国家大剧院。我当时认为,这次“‘迟到’的亮相可算一个中国现代舞生态悄然变化的文化事件”。换句话讲,“体制外创作”的动向正在不断地明确起来,自由创作的声音也越来越变得洪亮。舞蹈的先锋地位也留给了部分“体制外创作者”,在推进非媚俗、非学院派、非主流精英的路途中,担当着独立艺术家的身份。
不少中国现代舞作品受到世界各国现代舞权威人士的赞誉,似乎由于他们的作品散发着现代精神和东方民族的特殊魅力。所以会有人说,林怀民之所以成功是源自于他“中西古今的交融”,而陶身体剧场的成功,则是因为它“投其所好”,实际上西方对陶冶的作用远没有“生活在中国”对他的影响大。其实,如果将“中西古今”或是“西化”作为某种创作策略,恐怕“云门”和“陶身体”都不会获得真正的、持续的成功。
不过,相比于国际性,陶身体剧场的“本土意义”或许更为重要。世界很大,舞团十年间穿梭于多个国际著名平台,他们却没有一刻忘掉过这块孕育了他们的地方!在中国,“现在舞”多么重要!他们的初心一直都在。从对“身份动因”的质疑,到对“身体如何动”的笃定,再到“身体还能如何动”的坚持……其实,他们一直都在以挑战身体的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在中国的语境诞生,陶身体剧场的存在和坚守本身就是一种生命意义。
身体·时间·空间的交汇
十周年纪念演出的设计,并不让人意外,却让人颇为感念。毕竟,十年的时间和空间在此时此刻的交汇叠加,颇为微妙。《重3》是创团起点,而最新作品《9》则代表舞团的第一个十年节点,同时又有回到“原点”的寓意。让人不禁思绪翻飞,经过《2》的默契《4》的爆发《5》的绵延《6》的隐藏《7》的揭示《8》的回归,才会有《9》的释放……这是一支“和而不同”的9人舞,并非群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划圆路径,却又舞出了“和声”,像是对时间与空间的致敬,犹如在不同轨道上的行星,某一时刻的相遇,既是偶然,更是必然。对观众而言,你看谁?是看整体,还是局部,其实和每个人当下的选择相关。
身体好比时间,剧场就是空间。对人类而言,不可或缺的不是舞蹈,也非剧场,而是我们切实拥有的时间,以及可由空间转换的时间。无论何处,只要是你我相遇的地方,舞蹈的一瞬或许能让时间停留,甚至常驻心间。
音乐和舞蹈也是这样的关系。在陶身体剧场的诸多舞作中,音乐和舞蹈相得益彰,却又各自独立,舞蹈不会跟随音乐逻辑去走,因为自然舞动本身就是节律。身体就像是一个小宇宙,陶冶被其中一种严谨的宇宙秩序规则所吸引着。其实,《重3》不是陶冶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却是陶身体剧场重要的奠基之作,由此陶冶开始践行他的身体探寻理念。“限制”成为他的命题,也是他通往自由的必经之道。《重3》的三支舞——“zhong”“chong”和“棍舞”相互独立,却又彼此关联。成名前的陶冶非但不会认为“重复”的生活奔波很枯燥,反而让他珍惜脚下的每一步体验,就这样,“直立行走”这个人类最基本的运动方式,就成了他们颇有隐喻性的身体语言起点。

《重 3》(Chong) 范西 摄

《重3》(Zhong) 范西 摄
“行走”根本上就是一个重心改变、转换的过程。既然专注行走,在“zhong”中,陶冶就给头部、上肢和脊柱设了限,当晚,黄丽和鄢煜霖两位舞者很专注肃穆地在“行走”着,去掉了跳跃的冷暖对比色调,素色的服装更纯粹了些;鼓声阵阵,但两位舞者依循的实际上是自己的节奏,随着运动速度的加快,动作幅度也在不断增大,前后左右、交错对称……他们沿着十年前陶冶和王好的路径稳稳地行走着。看上去并不需要多么高超的技巧,但就是这份的控制力也是十分耗费体力和精力的,前排的观众眼见着从那微倾扭转摆动的身体上甩出了汗水。虽说尚难以企及创始人强大的能量场,但他们眼帘低垂,双臂架在腰间,让关节至下而上一节一节地发力,从而改变身体重心,维持身体动态平衡的这份专注力,十分吸引人。这不像是一种表演或扮演状态,他们是在和自己的身体对话。幸运的是,这种本真的“非表演状态”一直贯穿着整场演出,俨然获得了陶冶的真传。
“chong”是另一段双人舞,身体间是否接触、如何接触是这段双人舞颇有意思的看点。宽大的长袍遮蔽了两人互牵的手,却阻断不了两人的联系。除了偶然间的旋转,任凭脚底生花,两人的手就是相互拉拽着,一直保持着双手的触点。让人感觉他们以心灵的眼睛彼此关照,这是一种身体的凝视。这段舞蹈灵气逼人,被年轻的明达和国桓硕诠释得竟然有一种“不倒翁般”的萌态。
“棍舞”更是整场演出最具标志性的一个作品,这原本就是陶冶为段妮量身定做的一支独舞,那根棍子代表着他们的“自立”。舞枪弄棒算得上段妮的“童子功”,那是70后一代舞者的必备技能之一。有意思的是,段妮舞起扫帚来,也是自然天成。于是,陶冶针对段妮的身体特点,专门为她设计了这样一支渗透了中国传统戏曲元素的当代舞作。从2009年舞至2015年,“棍舞”见证了段妮的身体巅峰状态,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让她一度陷入绝望,难道这支舞就此“消失”了吗?直到一位年轻舞者张俏俏的出现。空荡荡的舞台上,一束光洒在一位娇小身躯的女舞者头顶,只见她单手或双手交替舞棍,还伴随着原地旋转,在高低、左右、前后空间中切割出无数个平圆、立圆、八字圆,刚柔并济地重复着、重复着。你会去数她转了多少个圈,或是舞了多少次棍吗?其实知道具体的数字没有多少意义,可是她的每一圈、每一次旋转却又是如此真切,这就是生命意义的显现,就像我们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
段妮的个人成长仿佛被投射到了张俏俏身上,这不是一种普通的教学,而是她向张俏俏的完全开放与接纳。由于张俏俏的新生与段妮的重生,“棍舞”获得了共生的契机。看到张俏俏舞出这一幕,我突然想到极简主义作曲大师斯蒂夫·莱奇曾说:“我感到最值得的事,是年轻音乐家想要演奏我的音乐,而且观众想要听。在这样的情况下,音乐会活下来;反之,音乐就死了。”而与《重3》相伴相生的音乐恰巧就是斯蒂夫·莱奇的手笔。是的,好的舞蹈也须得被跳,才能延续真正的生命,否则就只能进入博物馆了,即便是当代作品。
“艺乘”十年的陶身体剧场
中国的舞台上有太多的舞蹈“节目”,而缺少作品。陶身体剧场如此频繁地、秩序地回归身体本身,理由其实很质朴。陶身体剧场把身体看成时间,将舞蹈看成一种修行,但他们不是“苦行僧”,他们珍视自己的身体,只是累并快乐着。《重3》之“重”(zhong/chong)很能代表陶冶的艺术观。一个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生命中的一切大小事宜,有的事情看似轻松、简单、平凡,却常常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是生命重量之“重”,陶身体剧场却能以舞蹈的方式去消化。一天天、一年年、一个数字作品接着又一个数字作品,最难能可贵的是还能保有出发时的“初心”,这是“重复”却不雷同的艺术专注力。陶冶的确做到了——通过“重复”去达到某种极致,即他所追求的“真善美”——最真实、最质朴、最自然。或许,正是因为对“数位序列”这个艺术命题独特的、持续的、沉静的、缓慢的、渐进的关注,这份“专注力”才使陶身体剧场在国内外脱颖而出。如此下功夫,这在当今世界的年轻编舞家群体中是不多见的。当然,对其的赞誉和质疑也集中于此。
身体不只是一个舞者的工具,舞者也不仅是一份职业,而是“艺乘”。让我没有想到的是,陶身体剧场如今的舞者中,还有几位并非舞蹈中专科班出身,他们大学阶段才开始专业学习舞蹈,这的确是近年中国舞蹈生态的一个改变。身体是一个隐喻,帮助你更清晰地看清生活。如果说,现代主义舞蹈强调对身体的主观表现的话,后现代主义舞蹈更是一种基于人类共有身体的“探讨”,同时囊括了身体所关联的环境,它专注于提出问题的原点,以及不断追问的过程,而不是真正找到一个答案。当然,“现代”与“后现代”本就是对立统一的。陶冶浸润在当代艺术的世界语境中,的确受到了“极简主义”音乐或艺术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一种独一无二的舞动方式,也呈现出“跨文化”的色彩。
陶冶是一位极富创造力的天才编导,他的杰出并不止于创造了一系列数字作品,以及代表宇宙规则无始无终的“圆运动系统”,也包括他彻底颠覆了一种既有的舞蹈创作的方式,甚至拒绝灵感的到来。不用猜,《9》之后,你也应该会想到他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
五年前,陶冶十分笃定地告诉我,他的下一部作品是《5》。五年后,他说,数字序列的委约编舞已经到《12》了。但同时,他也表示会继续为段妮编舞,而且不会用一以贯之的数位的方式来对待她。“未来”已来。如今,人类的身体意识正在历经千年未有的变革。在我的心中,猛然升腾起若干未知与好奇。然而,珍视人类身心的宁静和自在,以及彼此的联系,这依然是一种永恒的身体观,舞蹈也只是一种途径而已。
注释:
[1] 参考钟明德.接着格洛托夫斯基说下去——格氏的“艺乘”及其在我们文化中的可能发展[J].戏剧艺术,2002 (2):27-36.
[2] 慕羽.陶身体剧场“数位系列”:隐匿身份 突出身体[J].艺术评论,2013 (9) :72-75.
[3] 汪雅婷.斯蒂夫·莱奇:好音乐永远反映时代[J].PAR表演艺术,2011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