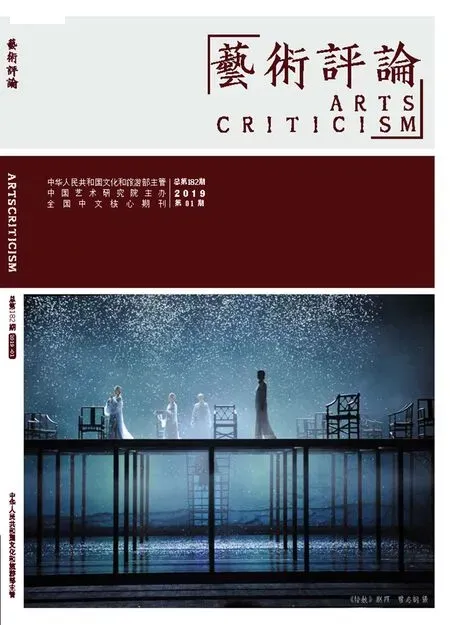从《审判》到《特赦》
——话剧《特赦》的创作经历
徐 瑛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案,十年前就是我选择的创作题材之一,最初想写成电影,走的是情节剧的思路,因种种原因,计划被搁置了,但心中并没有放下,相关资料的收集与研读,一直没有停。我之所以对这个题材感兴趣,首先源于我骨子里对极致人物的一种偏爱,其次是它属于静止的历史,与我保持有一段距离,相对于发生在眼前的事,我可以看得比较清。对写作来说,静止的历史具备一个优势,即你可以拥有更多的从不同角度观察与思考这个故事的资料,借此让你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进而找到它与我们的关联。找到题材与我们的关联是极为重要的,就施剑翘刺杀孙传芳这个题材来说,找不到它与我们的关联,写出来就是一个传奇剧,找到了,就是一个有现实意义的现代戏。古今中外所有优秀的历史剧,在我看来都是可以发生在当下的故事,所以我一直主张,历史剧要当现代戏去写,现代戏要当历史剧去写,惟其如此,作品出来才可望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不至于将来清盘时被当作垃圾扔掉。
于欢案的发生引发了全民的热议,也激发了我写作《特赦》一剧的激情。这两起刺杀命案,有许多的相似之处,情与法的较量,权与钱的博弈,司法独立审判与大众同情对司法审判的道德绑架,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宛如历史在重演,我的创作思路也因之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戏的主角,由施剑翘而变成了法律,这是最初选择《审判》作为剧名的原因。

《特赦》剧照 曹志钢摄
剧本创作的时间很短,完成初稿仅用了五天的时间,可以说是一气呵成。之所以能够这么顺利,首先要感谢民国时期的报人对庭审过程的详实记录,剧本中法庭上控辩双方精彩的唇枪舌战,许多台词都来自庭审的实录。法庭外的戏是我编的,但也不是凭空杜撰。虽然参与该案审判的法官和律师们的生平事迹留下来的记录很少,男一号孙家震能查到的资料,更是只有“孙传芳长子,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这么十几个字,然而他们面对该案的观点和立场,却是可以通过当年媒体的报道得见一斑。比如二审时证人没有到庭,报纸发表的文章即披露了民间关于孙家花钱收买了检察官的传闻。另外戏中戏的设置,也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只是当年演出的剧本没有留下来,具体内容已不可考,其立场却可以通过《侠女复仇记》这一剧名得以想见。至于大众同情在该案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民国政府最后对施剑翘颁发特赦令这一事实就已足够说明,借助报童的叫卖和戏中戏对此加以渲染,便可将舆情干扰司法审判的情况呈现出来,对编剧来说,这只是选择一种表现手段而已。
对施剑翘的遭遇,我是怀抱同情的。对孙传芳的长子孙家震,我同样也是怀抱同情的,在我眼里,他就是十年前的施剑翘。但同情不能替代法律,所以施剑翘的律师为她出庭,争的是有罪的减刑而不是无罪的辩护。一切立足于法律的框架内,这是民国时期的法官和律师的共同追求,这一态度深刻地影响了我的剧本创作。我希望能够客观而又艺术地呈现这个故事,首先必须收敛我的同情心与倾向性,把我的思考隐藏在人物的命运中,给这个题材一个更大一点的格局。
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只是有想写的冲动,根本没想过有没有机会搬上舞台的事情,更没想到会被国家话剧院看中。剧本写完后,有如释重负之感,因为总算完成了一个写作计划,了却了一桩心愿。心愿了了,也就搁下去忙别的事了,直到有一天国家话剧院其时在位的副院长罗大军在电话里跟我提起两年前的约稿,隔一日李伯男导演在电话里跟我说起十几年前许下的要合作一个戏的承诺,这才打开电脑,把剧本同时发给了他二位。

《特赦》剧照 曹志钢摄
伯男在收到剧本的当天就给我回话了,说喜欢,想排,说故事发生在天津,跟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合作合适,他负责与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联系。
罗大军的回复则晚了好多天,说剧本在剧院传阅了,大家都觉得写得不错,国家话剧院有排演的意向,在等周予援院长拍板定夺。
我担心落下一个一稿多投的嫌疑,赶紧把这个情况告诉伯男,他说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已回复他,说他们要排别的戏,演员没有档期,婉拒了。我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拒绝他人与被他人拒绝,总是被拒绝让人来得轻松。
此后又过了多日,李伯男通知我,周予援院长约我俩去国家话剧院谈一谈合作的具体事项,至此,《特赦》的排演算是落到了实处。
与周予援院长的交谈非常愉快,有一见如故之感,最快心的事,是我和李伯男可以在他的办公室里抽烟。我们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讨论了主创团队的搭建和排演日程的安排,期间,戈大力副院长也参与了进来,与我探讨剧本的修改。是时,剧名仍叫《审判》。
我一直以为《审判》作为剧名更为准确贴切,不仅因为施剑翘案经历了初审、二审、终审直到最后国民政府颁发特赦令这样一个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法庭外存在于大众心中的道德法庭始终都在参与,对法院的审判进行审判。与此同时,孙传芳未经审判残杀俘虏与施剑翘状告无门只能法外实施报仇的举动,以及孙传芳之子孙家震在最后一刻放弃射杀施剑翘完成复仇的念头,甚至包括施剑翘剧终时遁入空门自省在内,均与审判二字有着紧密的关系。法庭审判,道德审判,良心审判,多层的审判,是施剑翘案的核心内容。所以最终剧名改为《特赦》,内心纠结了许久。除了上面说的那些原因,还因为审判是过程,特赦是结果,看戏看的是过程,先把结果说出来,好比让人猜谜语,一开始就把谜底给漏了,没有了丝毫的悬念,有点让人泄气。
这事跟戈大力和李伯男反复讨论了很多次,最后他俩在我给的一堆剧名中挑了《特赦》,两票对一票,我相信他俩的经验、觉悟与鉴赏力,也就不再坚持。戏演出后,郭文景说《特赦》这个剧名好,是从另一个角度的理解。郭大师善解人意,于我是一种宽慰,让我实在地释怀了许多。
《特赦》一剧能够搬上舞台,要感谢的人很多,没有周予援院长和国家话剧院的担当,真不知这个戏何时才能见天日。此外数位专家在剧本论证会上对这个戏的力挺和对剧本修改提出的一些建设性意见,也让我心存感激。
参与该剧创作的主创,都是非常优秀的艺术家,他们为《特赦》一剧贡献了各自的才华,这才有了这个戏现在的面貌。
回首《特赦》的创作经历,此时此刻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施剑翘被特赦后面对记者提问时的感言:感恩,唯有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