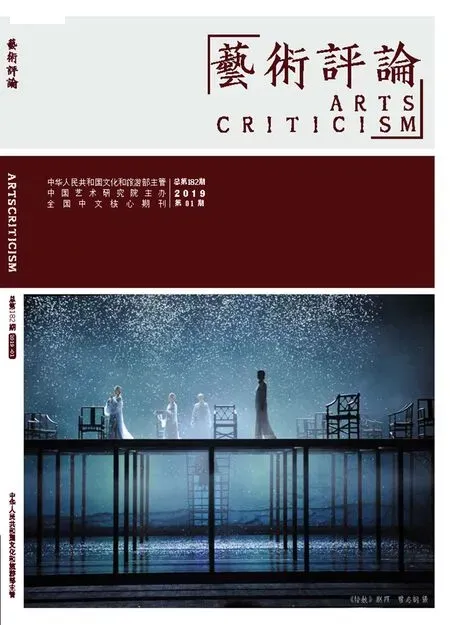《特赦》:关于公平正义的终极追问
刘金妮
1935年11月13日,下野军阀孙传芳在天津居士林诵经时,被前来替父报仇的施剑翘当场枪杀。事发后,施剑翘经法院多次审判,最终被国民政府下令特赦。
2018年12月4日,中国国家话剧院根据“施剑翘枪杀孙传芳案”庭审过程创排的话剧《特赦》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大剧场首演,该剧直面“情与法”的两难命题,深入探讨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该如何实现”的宏大主题,其事件本身自带的强烈戏剧性和创作者在编导、舞美、表演等方面独特的艺术处理手段,让这部作品充满了直击人心的力量。
谁是主角?
《特赦》一剧,以民国女子施剑翘的故事为蓝本。她的父亲施从滨在战争中被孙传芳俘虏,枭首示众,她出于孝情,发誓报仇,先后寄希望于堂兄和丈夫,对二人幻想破灭后,她携子离开夫家,隐姓更名,历尽艰辛,终于亲自完成了复仇计划。
从古至今,施剑翘这样刚烈如火、情深似海的奇女子最惹人遐思,她十年蛰伏筹备、一朝手刃仇雠的非凡经历也最容易入书入戏,令人为她喝一声彩,叹几口气,掬一捧泪。话剧《特赦》中,一身深色旗袍的施剑翘虽然充满了清冷、峭拔、刚烈甚至决绝的特殊魅力,但显然她并没有被当作真正的主角来塑造。也就是说,创作者从一开始就拒绝把这个故事讲成一个寻常的民间传奇。无论从戏份上,还是人物的丰富立体程度上,双方的主要辩护律师——余棨昌和孙观坼似乎更具有主角气质,庭审过程中,他们表现出的专业素养令人肃然起敬,庭审之外的戏,则将他们的人格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孙观坼是一个刚直不阿的理想主义者,对法治有着坚定信仰。当“施剑翘案”的公众舆论大大不利于孙家时,孙传芳的儿子孙家震打算动用金钱贿赂法官,利用权力打通上层关系给法院施压,都被孙观坼严词拒绝。在他看来,“法官一身正气八风不动,律师引经据典立足法理,这是我想看到的一道风景”,任何案件都必须在法律框架内作出公正裁决,不受其他各方势力的影响,这才是律师的尊严感和成就感的来源。为了坚持理想,他甚至中途拒绝出席庭审,绝不肯让不正当的手段污染他内心最美好的风景。
余棨昌是一位充满人文关怀、洞悉人性幽微的智者,他对施剑翘案有着自己的判断。作为律师,他一直致力于给她减刑,却从来没有做过无罪辩护,因为在他看来,施剑翘杀人本身是犯罪行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他作为一个专业律师的基本判断。因此,当南京政府下达了特赦令时,他却感到了由衷的悲哀,“法律代表了公平的上帝在人类社会的最高意志,在一个法治的国度,政府是没有权利干涉法律的审判的,否则法律将形同虚设,进而成为政府践踏民权、任意侵犯大众利益的工具”。
两位德高望重的大律师在法庭上针锋相对,在私下里却彼此敬重,因为他们都将法律作为最高信仰,所追求的都是不受干扰的纯粹法理和司法公正。然而,国民政府颁发的特赦令让两位律师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失望的喟叹:“施剑翘被特赦,于她个人是幸事,于国家和社会则可能是灾难。”意外的结局,使两位光彩夺目的人物无法最终完成其主角弧光的闭合,他们的行为并非导出故事结局的直接动力,从这一点上看,他们虽然是剧中极重要的人,却也不能成为主角。
《特赦》中的所有人物,不论是立足法理的精英律师团,还是看重伦理的芸芸众生,不论是结成世仇的施、孙两家人,还是出面定音的政府官员,都只是牵引事态发展的一股力量,多股力量的考量、博弈、影响和制衡,才有了这个令人深思的故事结局。归根结底,《特赦》舞台上的真正主角并不是某一个人,而应该是:法律、舆情和权力!
谁在发声?

《特赦》剧照 曹志钢摄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案”是当时名噪一时的社会公共事件,案件的每一次进展与转折,都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几乎承包了1935年末到1936年最大的头条热点。除了审理此案的法官、律师之外,公众人物、新闻媒体、普通百姓都在这件事上持有观点,并热烈地通过各种方式广泛播扬,以至于最后国民政府出面作出最后的裁决。《特赦》还原了当时社会对于此案方方面面的态度,这些舆论与态度,汇聚成一股合力,对案件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小觑的影响。
舞台设计成由金属廊柱支撑起来的立体双层结构,后方一架楼梯供演员上下,空间流转极度灵活,场景自由切换,一会儿是法庭,一会儿是监狱,一会儿是戏台,一会儿是回忆中的虚拟时空,各种各样的人物在上面穿梭往来,持各自观点激烈论战,微妙地拨动着观众内心的天平。值得一提的是,《特赦》并没有预设“主角光环”,将话语权倾斜向有利于施剑翘的一方,而是对于社会各个领域的声音都给予了充分关注,旨在真实展现处于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态度,以及他们出于各自利益和立场进行的发声。
三场庭审是本剧的重场戏,也是精华所在。民国法制社会建立之初,法律的权威性和大众的法制观念还未完全确立。事件的源头就是一场法外暴力的发生,孙传芳杀俘的不合法,成为法庭上被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关于施剑翘“孝义复仇,其情可悯”问题的争论则是现代法律规则和传统民间认知的一次正面冲突;法官将审判结果由十年改为七年,又究竟根据什么在校准……舞台上一个个问题的抛出,让观众的大脑也在随之飞速运转:如果法律无法保障公民的尊严和安全,那么公民还应该向谁求助?如果阳光无法普照所有的黑暗角落,“私权”的行使是否具有合理性?如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奋起反抗,他是否应该被当作恶徒来对待?如果“杀人偿命”是铁律,那么为什么有人要接受惩罚,有人却可以逃脱制裁?如果法律罔顾人的尊严和权利,无法实现真正正义,那么公民是否还要遵守这样的法律……“情与法”的乱麻,在双方律师逻辑严密又充满激情的慷慨陈词之下,被慢慢地剥离、理清。艰涩繁复的法律名词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不仅不枯燥,反而具有了一种诗意。这诗意来自律师们将“司法独立”当作一种信仰的坚守,来自他们不为金钱、权力、舆论所干扰的纯粹,来自他们追求一个更好、更公正的世界的情怀!

《特赦》剧照 曹志钢摄
两段“戏中戏”是创作者巧妙而独特的设计,虽然跳脱在故事主情节之外,却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大众视角。当时,上海天蟾舞台热衷于把时事编成戏文上演,大受追捧,施剑翘案就是其中之一。该戏被命名为《侠女复仇记》,其情绪倾向性非常鲜明。扮演施剑翘的京剧名伶追捧者甚众,相当于现在“大V”级别的公众人物,他的文化程度应该不高,无法理解孙观坼、余棨昌等人关于法理的论述,然而行走于江湖、混迹于市井的人们自有他们所认同的一套价值体系:来源于几千年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情义和孝道。施剑翘为报父仇,舍身刺虎,完全符合百姓对于“孝女”“侠女”的想象,他们将她本人与升华过的戏中人相对位,在情感上对她百分百认同和支持。京剧名伶演出现场签署联名状,要求释放施剑翘,下面看客群情激奋,振臂高呼。戏剧化情境中,人的情绪最容易受到感染,可以想见这种不需要判断、只需要从众便能占据道德高地、获得情感满足的选择,必定是社会领域最大多数人的态度,他们的发声也必然以排山倒海之势,对庭审产生压力和影响。除此之外,剧中有个报童共六次出场,在案件的每一个重大节点上,他都会出来喊一段“号外”。还有一群专门追踪此案的记者,向施剑翘直接提出观众想知道的问题,他们都是社会声音的一部分,间接对案件进行着法庭之外的“媒介审判”。
政治干预在剧中出现的时间很晚,发声内容也很简短,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张特赦令,抹杀了之前一切激烈的辩护和严肃的审判,为结局带来一丝荒诞之感。
谁持正义?
公平与正义,在任何时代都是灼灼闪光、令人向往的境界,每一个人都渴望得到公平的对待,渴望社会中充满正义的力量。
道德和法律,是人们追求公平与正义过程中的重大发明,二者大多数时候互相补充,但也有时会矛盾相悖。当“情”与“法”发生对立的时候,行为动机的正义性便成为了天平倾斜的关键砝码。
施剑翘杀人后,选择了主动伏法,并提前立好遗嘱,说明她深知自己的行为并非绝对正义,必然要接受制裁。然而,相对于孙传芳不经审判处决人犯并暴尸以后法律的缺席,她无奈之下的暴力反击又有一定的正义性。“若先父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公然践踏人的尊严,我才与他不共戴天!”施剑翘关于父亲“受辱”的描述在剧中多次出现,孙传芳“缺乏程序正义而杀人”,是创作者寻找到的支撑她“复仇正义性”的关键心理动因。
施剑翘在洋洋千言的《告国人书》中,将父亲描摹为一个高风亮节、爱民如子的长官,这也许是女儿眼中父亲的光环,也可能是为了占据正义高地进行的宣传。《特赦》的创作者却并没有被这一立场主导,而是翻开了更深一层的历史真相:“施从滨军队纪律极坏危害地方,其率领的白俄雇佣军洗劫村庄残杀平民,违反了《陆海空军刑法》第34条”——这是原告辩护律师孙观坼在法庭上的陈词,虽然并不能成为孙传芳随意杀害俘虏的有力辩护,但是也渗透出一个重要信息:“春秋无义战”。军阀混战是为了争夺利益,本身并不存在谁更正义,倘若说孙传芳杀死施从滨不合法,那么很可能因为施从滨的白俄部队犯下滥杀抢劫的罪行在先,早已激起民愤,不得人心,这才引来孙传芳的轻率对待。
有观点认为,孙传芳虽然曾经是个暴虐的军阀,但早已下野隐居,手无寸铁,远离征伐,潜心修佛,不应受到枪击横死。关于这一点,《特赦》也微妙地点出了孙传芳虽处江湖之远,却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尴尬处境。孙传芳的儿子孙家震有一段台词:“家父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日军华北方面最高司令长官冈村宁次是家父留学日本军校时的师友,他多次亲自登门拜访家父,请家父出任华北政府主席,都遭到了家父的断然拒绝。家父皈依佛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想当汉奸。”虽然是为孙传芳正名之语,却多少透出欲盖弥彰之意。当时日本策划华北五省独立,政局风雨飘摇,特务机关四处散发“拥孙倒蒋”的传单,蒋介石派人暗杀政敌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孙传芳为避锋芒,皈依礼佛,但是民众并未因此就转变了对他的看法,也没忘记他当年志得意满之时“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的“大言”。从施剑翘案一边倒的社会舆论上看,民众对“放下屠刀”的军阀仍旧没有丝毫好感。
《特赦》的出色之处在于,创作者没有将社会简化成黑白两面,没有把一个绵延了十年之久、前因后果极其复杂的事件戏剧化地处理为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而是向真相层层发问,孜孜探求。从字里行间无数有据可考的细节中可以看出,创作者在极力克服主观立场带来的偏颇,力求通过还原每一个细节和真相,让观众在抽丝剥茧的探索中去理解“公平正义”的真正含义。
谁主沉浮?
“施剑翘案”其实非常明确,杀死孙传芳的勃朗宁手枪、剩余的三发子弹、被告本人供认不讳的供词,都是可以直接定案的确凿证据。然而,当最高法院作出七年监禁的最终判决的时候,国民政府却发出一纸特赦令。看似舆论干预了判决,事实委屈了规则,民意大获全胜,政府被迫妥协,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特赦》中,余棨昌律师在获悉施剑翘被特赦时,有一段颇含深意的台词,揭开了案情背后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之一角:“蒋介石一直想在中国实行法西斯统治,但是国民党的合法性却一直让人怀疑,如果施剑翘被特赦,国民党就成了案件的最终裁决者,其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威性便自然地会被树立起来。”
创作者没有止步于皆大欢喜的结局,而是触及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探讨“特赦”这个结果的真实原因。彼时国难方殷,人心危浅,各个势力争权夺势,孙传芳的死亡,无疑为蒋介石除去了一个政治对手。施剑翘的复仇动机又属于私人恩怨,与蒋毫无干系。这一类以“报仇”为名的暗杀在当时曾经很盛行,如军阀张宗昌、北京政府前总理张绍曾、皖系名将徐树铮等人都是死于这种“仇杀”,杀人者不光为世人喝彩,也能博取法律网开一面。施剑翘虽然在法庭上坚持是自己一人所为,也很难说在她所不知道的领域,是否有人在为她暗中提供方便。冯玉祥出于与施剑翘父辈的情义,出面斡旋营救成功,并非他在蒋介石面前有多大的话语权,而是施剑翘的行为符合国民政府的利益,国民政府发令特赦,既给了冯玉祥面子,也博得了民众好感,可谓顺水推舟,这个特赦的结果,从一开始就早已注定。
结尾处,获得特赦的施剑翘并没有在精神上得到解脱,而是面临着如何安放沉重的良心、如何背负人命继续生活下去的难题。她在《金刚经》的吟诵声中,缓缓穿行于漫天飞雪,寻觅着未了的答案……有人评论说,孙家震冲天放空的那一枪,才是对施剑翘真正的特赦,那是一个人主动选择终结了冤冤相报式的诅咒,用人心之“不忍”下达的特赦令,笔者亦深以为然。波澜起伏、震惊全国的大案,历尽浮沉,落点回归到人性本身,《特赦》这部剧所达到的深度,在于超越了社会认知领域对复杂人性的审判,表达了真正的特赦应来源于人对自身狭隘的克制和对光明的追求。
《特赦》这部民国题材的作品带给人们一种疏离的思考,虽然“施剑翘案”已经隔着历史的烟尘离我们遥遥远去,但剧中的情景和人物、观念和困惑却仍旧如此熟悉。中国国家话剧院选择了将《特赦》这样一个题材的作品搬上舞台,也正是考虑到,当下许多社会事件和犯罪案件依然需要执法者妥善处理好法制中的道德伦理问题,依然或多或少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最后的裁定不仅仅关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命运,更关乎一个已迈入现代文明、正在实现法治的国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