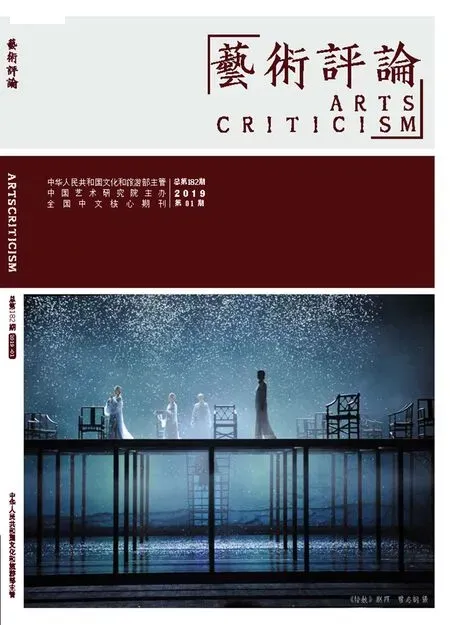禅宗思想对文人画创作审美之影响
杨江波
[内容提要] 禅宗是把印度禅本土化的宗教,它的“空性”理念深刻影响到中国文化,文人画家有“追道”思维,因此常常在作品中展现禅的审美理念。在画史上凸显禅境的著名文人画家和画僧层出不穷,也因此形成了文人画禅意审美特征。禅宗思想清净空灵的呈现对于文人画“逸品”审美的生成和笔墨涵义的成熟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上古未有文字的时代,先民籍图画来传情示意。后来民智日繁,图画中分科愈细,文化上愈加丰富,中西、古今审美各不同。总体来看,皆是人类后天所习,从先天而言,皆是禅宗直指所悟,本性是“赤裸裸,净洒洒”的,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中国文人画以洁白宣纸为底,展示无限空间,在空白所展示的虚空里,有水墨氤氲所化成的境相。一个高明的水墨画家,必然重视空白的运用,在虚实结合中试图营造一个圆满的生命场。说是营造,不如说是自然流露,因无心故,所造皆自然。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曰:
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
著名学者田青说:
与世界上其他所有的宗教、教派、哲学、主义比起来,禅宗是最有诗意的思想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可以称其为“艺术的哲学”。对于以理性思维、逻辑思维为主的哲学家来讲,这一点也许不那么重要,但是,对于重感情、重形式、重趣味的艺术家来讲,这一点却不是可有可无的。
中国审美理想的创构,由于禅宗思想的渗透和影响,使这种理想境界更加空灵玄远。在创作方法上舍弃繁琐的形似描写,更加重视气韵、传神,而鉴赏或表现气韵,不可不借助于直觉与妙悟。在审美观照方面,把直觉顿悟直接运用于艺术——审美活动中,从而产生“静照”“妙悟”等审美概念。受禅宗思想的影响,中国艺术所追求的审美意象更加虚化,更加空灵化。
一、佛教禅宗与文人和文化史的关系紧密
西方哲学讲逻辑的严密性,中国禅宗却认为一切语言文字都是片面性的,它宛如“指月之指”,因此主张“不立文字”,重感悟。不被语言、思维所局限其实也是中国文化本有的传统,比如老庄美学里的“得意忘言”“言不尽意”,但是毕竟他们还没有完全脱离语言,而禅宗则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所谓“无立锥之地”。它甚至在非逻辑化的问答中来打破执着,表达既要脱离语言的理性束缚又要传达某种意蕴,这使得中国文字模糊多义性的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它充分利用了言与意的矛盾,在矛盾与模糊性中表达得耐人寻味,这一点深深影响到了中国画的深层审美。关于这一特点,我们在八大山人的作品里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他的诗与画好似彼此不关联,但总能让人有所感悟。当然,禅是灵活的,若把公案当作概念化的公式来运用则南辕北辙不会悟道。西方文化讲两元辩证对立,而禅宗和道家文化却赞美大自然的无目的性,其美学“物我一如”,主客观浑然一体。在一张画里,画者“无立锥之地”,只是一片荒寒宁寂,在大自然云卷云舒、花开花落的无目的性里来彰显生命的真谛。

禅宗对儒家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宋明新儒学借鉴得以升华,被称为“儒禅”,其“入世”的“平天下”理念的人格完成在“人人皆为尧舜”。关于心性,禅宗的“明心见性”此时被新儒家转化为“养心存性”。冯友兰先生说:
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自传入后,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宗教、哲学、艺术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佛教禅宗与文人和文化史的紧密关系使得文人画的禅意审美特征很凸显,影响既广,便不能一一列述。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只能依据画史在此略说其意,以供佐证。
南北朝时,为宣扬佛教,故佛画大兴。寺庙亦成为画家研习外来艺术和壁画创作的地方,在此情况下,画家中不能画佛画者也为罕有。南朝宗炳追随慧远法师参加白莲社,慧远法师在庐山创立的东林寺被尊为净土宗祖庭。宗炳曾作《明佛论》《画山水序》等文章,他深受佛法影响提出“澄怀观道”“畅神”等创作理念。唐代王维应神会禅师所嘱为禅宗六祖慧能禅师所作的《能禅师碑》,从碑文内容中可以看出王维对慧能思想的深入把握,而王维则被视为文人画的始祖。关于禅宗公案也是颇有一段因缘,六祖慧能的四十年传教生涯并无著述,一万多字的《六祖坛经》只是由别人记录整理而成。成熟时期的禅宗以心印心,不立文字,如云门文偃禅师说法时反对别人记录,但晚唐时期战乱频繁,人民疾苦,寺院也大多荒废。这时禅宗因为隐居深山加上地域文化的差异,逐渐兴起并分为五宗七家,所谓五宗七家大同小异,但在指引方法上各有特点。黄檗希运和临济义玄提倡“机锋”,用“棒喝”的方式使其学人醒悟,这种“禅行”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公案的运用迫使人的理性走投无路,当相对之心“能所双亡”时便可彻见自性,这被称为“垂直切断”。
后来在宋代,禅匠将文字和禅结合起来,最主要的形式是“以诗证禅”。这是禅宗“不离文字”的工具化使用,即是所谓“句中有眼”。宋代兴起文字禅并所谓“句中有眼”,这是大量文人参与到禅宗后的公案学必然趋向。这时大量绘画作品也以“画里有眼”为追慕,可以说禅宗在唐宋时期的艺术创作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禅意作品或者禅宗题材的作品俯拾皆是。
宋代社会政治提倡儒学,宋代文人在接受南宗禅的时候更多体现的是三教融合,苏轼作有《南华长老题名记》一文,结尾一句点明主旨说:“乃为论儒释不谋而同者,以为记。”李公麟在紫柏大师门下精研佛典,明代僧人海观在《题李次公佛菩萨法像后》跋曰:
居士之写画,不留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其智与百工通作佛菩萨像,皆以意造,而与佛合,佛菩萨摄之。

二、文人画的禅意特征
以上略举,所列画家皆是美术史中赫赫有名之人物,其作品和创作审美都足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但是问题在于是否一个著名的禅画家能和一个高层次禅修者完全划上等号呢?其实也不必然,佛学大师圣严法师认为:
许多出家人以书法、绘画、诗歌闻名,但除了少数例外,在中国佛教史上都没有显著的地位,因为他们不是杰出的修行者。
禅最重要是打破自我,“缘起性空”的理论是其要旨,换句话说,只要自我存在,就很难谈得上是深层次的禅法。而画家艺术创作是要抒发自我的情感,即所谓借物抒情。在“心手两忘”的专注情况下,画家也会有一定禅的体悟,“艺术家是有可能达到所谓艺术家的开悟的境界的,这是一种统一心,这时艺术家与艺术合二为一,但这个经验根据的依然是‘有’,而不是‘空’。我们可以把艺术家的证悟当成较浅层次的禅的成就,但那和见到自性是不同的”。净慧法师也说:
以禅的眼光来看,得到思想空灵的人,禅文化上可能有成就,但是生活是否潇洒、生命是否自在,那就不一定。
虽然著名的禅意画家未必一定都是禅修境界很高明的修持者,但很显然,禅宗所倡导的无我、无执、空灵的审美意蕴已深深影响到文人画创作者,他们以此为向往和追求,在画史中聚沙成塔,积点成线,最终形成了璀璨的文人画演变史。
从中国绘画史来看,中国绘画因为文人的参与而形成了独特的文人画。文人思想的审美又较多地受到了庄禅思想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文人画的核心是禅。由此可以看出研究文人画禅意审美的重要性。
对世俗超越后带给文人画家的是内心的静寂,“画为心迹”,于是受禅宗影响的文人画家也自然将其审美体现在作品里,若总结文人画的禅意特征,可以列出以下几点:
(一)寂照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义理后体认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

《水墨写生图》卷(局部),南宋,法常作,纸本,水墨,纵47.3cm,横814.1cm
佛学《心经》是整个大乘显宗义理的浓缩,而一部《心经》又可精炼为一个“照”字。“寂照”的美学境界是佛法大乘般若宗所带来的,日本受中国禅宗的影响亦有枯寂之美学。“寂”非无生命之枯境,而是直探生命本源后的生命的灵动。画家以“寂照”之心理体会万物之美,则万物皆寂而灵动。
(二)返约单纯
历史上不受佛教影响的大诗人有陶渊明、杜工部、韩退之、欧阳修、辛弃疾、李太白,其中陶、李近乎道而不完全,杜、辛近乎儒也不完全,但他们共同一点是开合变化复杂,是壮美而非禅意“返约单纯”之优美,王维等则呈现优美而非壮美。壮美则气吞山河,气势在外,优美则含蓄蕴藉,脱巾独步,神气内敛。
一个“返”字最能凸显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是“心性文化”,所谓“圣人转心不转境”,认为外境乃内心之映射,于是修养身心,返朴归真是人生第一要务。禅法启发刺激了儒学探究心性的那一部分,理学和心学相继而起。绘画的审美之心由驰骛外境而敛心觉照,逐渐进入了“见山还是山”的审美第三境,单纯朴素之境是繁华落尽后的审美领悟。
(三)不可说
文人画“诗画一律”的特点非常明确,在这之前其实也经历了一个辩论的过程,最终苏轼一首“诗画本一律,天真与清新”的诗句确定了文人画的这个特点。“诗画一律”指的是它们的“不可说”之境是相通的,禅宗的悟境非理性逻辑思维所能描述,是需要行者参悟体验的。学者顾随先生认为:
艺术创作时,景是为了诗人情感服务的。也就是说借景抒情,化情入景。情来源于心,胸襟的开阔与伟大必然流露出相应境界的作品。中国古人深明此理,甚至超越了伟大与渺小的二元对立,直接从生命本体的源头去探索,于是“法尔如是”的本来面目逐渐走进了人们的审美视野。艺术作品与禅宗在“不可说”这一点上相携手。东汉、魏、六朝人多信禅,诗人不在佛教禅宗之内者,数人。其中之大诗人,首推陶渊明。陶不受外来思想影响。人皆赏其冲淡,而陶之精神实不在冲淡,自冲淡学陶者多貌似而神非。
(四)心无旁骛
“心无旁骛”类似心理上的专注又不尽然。专注是一种创作时心理集中的精神状态,道家也有“解衣盘礴”这一典故,而禅宗则以“空性”为要旨,由坐禅之专注而明悟心性。因此,心无旁骛既是指创作时心无杂念的心理状态又是指内心清净不为名利所牵绊的“无所住”修为境界,有此修为才能创作态度真诚自然,作品意境天真散淡,若此,文人画逸品境界则不得不至。
(五)游戏三昧
“游戏”是一种状态,“三昧”是一种境界。画家忘怀得失兴来泼墨,在解放心灵的状态中获得自由的创造力,这是本心灵感的自然流露,也是一种诗性的“兴”,它的美学关键词是“自在”“无碍”和“超脱”。创作主体精神自由了,创造力才能充盈而丰沛。
三、禅境与画境
关于文人画“意境”论,聂振斌认为:
意境范畴形成的历史过程是漫长的,上可追溯到先秦的儒道思想,中经魏晋玄学时代和南北朝时期儒道释的渗透融合,直到艺术繁荣昌盛的唐宋时代,禅宗僧徒与文人士大夫过从密切,以文会友,禅宗思想向人文世俗渗透,从而已成为诗书画创作的重要思想源泉。唐代诗人王昌龄首先在诗词批评领域提出“意境”概念。释皎然和司空图等人,极大地丰富了意境的内涵,并指出意境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及司空图所说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严羽所说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等语。经过宋元明清的充实、发展、扩拓,意境成为诗文、绘画批评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
王建疆也认为与道家的美学框架相比,禅宗的“空灵”是意境的灵魂。但其实禅并不排斥儒家,禅宗的空观是“空有不二”,也造成了中国画艺术的独特的意境审美。
禅宗求真的理念深刻影响着文人画家的创作,艺术创作如何才能真挚呢?铃木大拙认为“无意识”是关键,他说:
科学家谋杀,艺术家重创。后者知道由分解是不能达到实体的。因此他用画布画笔与颜料,来试图从他的无意识中创造出来。当这个无意识真挚而诚实地将自己同宇宙无意识相认同,艺术家的创作便是真挚的。他真真实实地创造了某种东西,他的作品不是任何东西的抄袭,它是因自己而存在的,他画一朵花,而设若这朵花是从他的无意识中开放出来,他就是一朵新的花,而不是一个自然物的模仿。
禅宗的特点是反理性逻辑,智识在禅宗视域里是一种困境,因此禅师运用种种方法来突破这种困境,参话头、棒喝都是其对机方便运用的手段,目的是打破无明执着的“黑漆桶”而豁开生命的真相。因此,禅宗在文人画史发展困境时产生过几次大的影响。一次是促使“逸品”的出现,另一次是“南北宗论”。
综上所述,禅宗思想对于文人画史影响极大,受禅宗思想影响的文人士大夫和以禅修为要务的禅画僧人皆把禅境融入画境,这对文人画“逸品”的生成影响极大,也促使文人画“笔墨”概念演化的进一步成熟。
注释:
[1][2]俞剑华编.中国古代画论类编[M].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论·论画六法.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33,71.
[3][12]聂振斌.中国艺术精神的现代转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98,218.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221.
[5]《东坡全集》卷三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7册,第525页。
[6]海观.题李次公佛菩萨法像后.《林樾集》卷二.兰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99册,23页.
[7][8]圣严法师.禅的智慧[M].单德兴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85,190.
[9]净慧法师.生活禅钥[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271.
[10]宗白华.艺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89.
[11]顾随.顾随随笔[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69.
[13]〔日〕铃木大拙.禅与心理分析[M].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