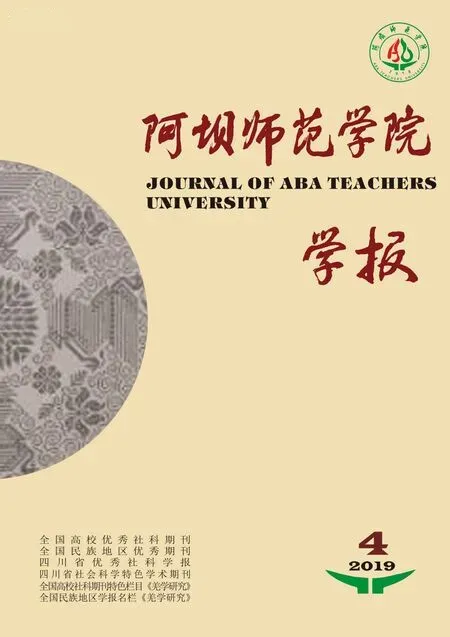重估“道统”:儒学之当代使命
孙旭鹏 ,赵文丹
儒学复兴已经成为近几年的热门话题,然而儒学如何复兴,以及儒学实现在何种意义上的复兴,却是莫衷一是,众说纷纭。既然谈到了儒学“复兴”,那么其潜台词必然是儒学曾经“衰落”过,或者至少是在某一时期内“衰落”过。尤其是近代以来,儒学面临的危机尤甚。因此我们就不禁要思考,在当前儒学发展中我们是否仍然需要儒学之“道统”,如果需要的话,是采取一种固守的态度,还是采取一种发展更新的态度,这都是我们今天重估儒学“道统”的意义所在,更是儒学的当代使命所在。经过考察发现,传统儒学的“道统”夹杂着一些偏颇的观念,我们只有对其加以清除,才能使儒学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来与其他文化对话,并且只有在这种文化对话中,儒学才能够顺应时代不断完善自身,从而承担其应有的使命。其实,儒家的“天下”观念就天然包含有一种普世关切之情怀,如果说儒学在当代仍然需要坚守一种“道统”的话,“天下”观念就应该是这一“道统”的内核,从而改变以往“道统”观念纠结于门户之争、观点之争的狭隘性,也就是说,只要是对天下民生有益的学说,都应该与儒家以“天下”为关切的“道统”不相违背。在当代,我们只有从儒家的“天下”观念出发,才有可能克服儒学传统“道统”观念之偏颇,以泽及“天下”的胸怀为社会的发展以及正确处理国际关系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一、传统“道统”之偏颇
儒家“道统”是在当时佛教思想盛行的文化背景下对自身文化的一种自觉认同,其在一定程度上坚守了儒学一以贯之的“道”,从而有利于儒学的源远流长。韩愈面对当时佛教风头正盛,甚至压过了儒学的局面,从儒者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儒学本身也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道”,韩愈在其《原道》中阐发了这个“道”的传承:尧——舜——禹——汤——周公——孔子——孟子,其后,宋代的朱熹更为明确地将“道”与“统”合在一起,从而确立起了儒家的“道统”。彭永捷先生认为:“对儒家道统说进行哲学的分析,可以把儒家的道统归结为三个方面:认同意识、正统意识、弘道意识。”[1]很显然,认同意识与弘道意识有利于儒学的传播和发展,而正统意识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偏颇之处,其主要问题在于,在儒学思想的不同思想流派中,以何种标准来确立所谓的“正统”?在确立了某一思想倾向为儒学之正统之后,很显然是阻碍了其他思想倾向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这从根本上也不利于儒学的全面健康发展,容易导致一种固守教条的僵化的儒学形态。
那么,在传统的“道统”观念中,究竟认为什么才是儒学所应该一以贯之的呢?也就是说传统儒学家们认为从尧开始到孟子一直传承的什么,韩愈曾以“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来阐发儒家之道,也即是说“仁义”之道便是儒学所一直坚持的“道统”。那么“仁义”的根基又在哪里呢?或者说儒者为什么认为“仁义”是可能的呢?很自然地,他们将“仁义”的根基指向了“性善”,也就是认为只有建立在“性善”的基础上,“仁义”才成为可能,这从程、朱对荀子“性恶”的评价中可以看出端倪,程颐曰:“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2]262朱熹则曰:“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3]3254由此可见,程、朱认为“性善”为“道统”之本。于是,在“性善——仁义”的思想模式下,孟子自然被看作了儒学道统的重要传承者,因为孟子主“性善”,致“仁政”,孟子讲:“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英国汉学家葛瑞汉这样评价孟子的人性善的本质:“道德倾向(moral inclinations)与身体的成长发育一样属于自然。它们自发地形成,而不必后天的习行,人们可以滋养、伤害它或使之枯竭,如果养护得当它们会生长,但不能外力强迫。”[4]148也就是说,孟子认为“性善”是人所本有的,其实现完全依赖于自然生长而不假外求。其实,我们知道在孔子那里对人性的看法并非如此,孔子如此讲:“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并没有认为人性天然具备一种“善端”,只是说“性相近”,也就是人生下来的本性都是差不多的,至于这差不多的成分是“善”还是“恶”,孔子并没有进一步探讨,而是马上转向了“习相远”,也就是认为后天的学习和教化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后天的“习”使原本相近的人性产生了诸多差异。或者可以这样认为,孔子没有纠结于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而是更关注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表现,应该说,这是较为客观的,因为人性并不是脱离现实行为而孤立存在的,否则极容易使人性陷入一种“虚无缥缈”之境,显然,孟子强调人性本具“善端”,确实背离了孔子将人性置于现实中加以考量的轨道,而宋儒们却偏颇地认为主“性善”的孟子才是孔子思想的真正传承者,并且进一步将“性善”作为了儒学“正统”的主要标志。
以“性善”为正统的“道统”观显然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其将致力的重心转向了内在的心性修养,也就是过多地强调了“内圣”,而相对忽视了“外王”。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在先前儒家那里“内圣”与“外王”并不是割裂的,而宋明理学尤其是后期的“心学”则有流于空谈心性之嫌。在先秦儒家中对由内圣而外王做出最重要理论贡献的当属荀子,而宋儒们竟然仅仅因为荀子的一句“性恶”便将其排除在了“正统”之外,从而造成儒学对现实社会的关切程度大大削弱。“道统”观念这种以“性善”为正统,以“性恶”为歧出的做法,不仅对学术思想的发展是不公平的,就是对社会的长足进步也是危害极大的。首先,从学术发展层面来看,“道统”拒斥主张“性恶”的荀子思想,从而造成了之后学术界长久以来对荀子思想的忽视,使对荀子思想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对孟子的研究,这无疑是学术研究的一种重大损失。因为,宋儒们只因荀子主张“性恶”就对荀子思想进行全面否定的做法无疑是以偏概全的,更何况荀子主张“性恶”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化解现实之恶,实现一种“正理平治”的社会,这与孔孟思想的最终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徐克谦先生认为:“荀子为什么会得出‘人性恶’的论断?原因也许是复杂而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跟他所处的战国末年的社会现实有关。”[5]6也就是说,荀子“性恶”是面对变化了的时代对儒学所做出的自觉调整,而并不是对儒学的背离,盲目地将荀子排斥在儒家正统之外,无疑不利于儒学的发展。其次,传统的“道统”观念不仅不利于学术的发展,从更深层次看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我们知道,孟子主要继承发展了孔子“仁”的概念,走的是一条由“仁心”到“仁政”的道路,因此其更注重内在“心”的修养工夫,认为如果每一个人具有了“仁心”自然就会产生“仁政”,这种理想固然美好,然而现实政治却充满着复杂性,“仁心”充满着不确定性很难被运用于社会治理之中,这从当时孟子游说各诸侯国宣扬其“仁政”学说却并不被采纳就可见一斑,质言之,孟子的“仁政”学说操作性太差。而传统“道统”确立了孟子在儒学中的传承地位之后,大大强化了儒学对于“心”的修养工夫的重视,最终导致了陆王心学空谈心性之流弊,从而造成对社会现实的关切越来越弱,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正如美国汉学家狄百瑞所认为:“在儒学首要或者特别关注的众多话题中,必须把治国术和领袖品质,学术和学校,家庭和人际关系,礼仪和宗教包括进来。”[6]4很显然,将焦点关注于个体内心修养的“道统”儒学,在某种程度上有意无意地疏远了这些现实关切,造成了与现实社会的脱节。
二、以“天下”为统
我们既然看到了儒学传统“道统”观念的偏颇之处,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就是儒学究竟应以什么为“统”?其实也就是应该以什么为判断儒学的终极标准,显然宋儒们以“性善”或者“性恶”来判断儒学是否正统的做法是片面的。儒学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学派,其从一开始就关注于“外王”之道,“内圣”只是实现“外王”的途径,而“外王”才是最终目的。而所谓“外王”的对象无疑是儒家所讲的“天下”,孔子多次提到“天下”的概念,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处为其回答颜渊问“仁”:“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孟子更是多次提到“天下”,他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荀子提到“天下”的次数更多众多,他讲:“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故操弥约而事弥大。”(《荀子·不苟》)由此可见,儒学从一开始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尽管不同儒者在具体问题上存在着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的观点,然而都有最终的一致目标,显然我们就有理由讲,儒学应该以“天下”为统,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关注于儒学的终极指向,而不应该纠缠于其中具体观点的争议,“天下”是儒学的终极关切。“儒家文化对问题的思考不以认识客观事物为最终目的, 而是要达到一种天、地、人相互统一和谐的整体状态”[7],确实如此,儒家将其视野范围内的所有人类都纳入了“天下”这个概念,其社会治理理念也并不是针对某一个诸侯国而设定的,而是面向全体的。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的“天下”观念包含着一种强烈的社会关切,这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济世”品格,应该是其最为生动的精神内涵。《论语·微子》中有言:“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也就是说,“君子”通过做官来参于社会治理是一种不可推卸的义务,即使其政治主张不为人所理解和接受,也要竭尽全力地去做,可以讲这是作为“君子”的终极目标,“君子”不仅仅体现在内在之“德”的层面,更主要的是其对“天下”也即社会治理的关切。在孔子看来,现实中的每一个人都要“为政”,而且也都能够“为政”:“‘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只要能够去积极主动地构建良好的社会关系,也算是一种“为政”,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孔子不管讲“仁”还是讲“礼”,都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从“天下”的角度来讲的,此即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仁”与“礼”绝不应该脱离对“天下”的关切而沦为个体内心的一种神秘体验。到了“孟子”这里,其依然存在着浓烈的“天下”情怀:“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然而,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地方是,尽管孟子也强调“兼善天下”,然而这种“善天下”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达”,而如果“穷”的话则只能做到“独善其身”,这显然与孔子的明知“道之不行”也要“行其义”有了较大的差别。而正是这些差别后来被无限放大,造成了之后尤其是宋明以来儒学家们对“独善”的过分强调,有意无意间弱化了“兼善天下”的现实关切,将“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打成两截,这其实从孟子将二者进行对举开始就有了这种萌芽,最终导致过分注重“内圣”无法实现“外王”的结局。
其实,在先秦儒学的发展进程中,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已经发觉了孟子过分注重“内圣”而忽视“外王”的这一偏向,并批评孟子的“性善”为“张而不可施行”之学说。荀子讲:“今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岂不过甚矣哉!”(《荀子·性恶》)何为“张而不可施行”?也即无法对现实社会起到任何作用,如此何以谈“外王”,何以谈“平天下”?从根本上,荀子并没有否认孟子具有“平天下”的愿望,而只是否定了孟子这套以“性善”为根基去“平天下”的方式,认为“性善”说根本对现实社会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也就是说,荀子认为孟子由“仁心”到“仁政”的路线是行不通的,治理“天下”必须依靠外在之“礼义”:“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荀子·王制》)荀子认为外在的“礼义”才是“治之始”,而非孟子讲的“仁心”,“荀子正是以‘礼’为核心, 通过‘化性起伪’的方式, 使现实的道德世界得以挺立”[8],荀子的“礼义”具有鲜明的后天经验性品格,其直接指向对“天下”的现实关切。荀子认为只有通过“圣人制礼”的路径,才能够实现“天下”的良治:“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荀子·荣辱》)荀子的“制礼义”明显具有一种外在社会制度设计的色彩,强调对社会的现实功用,实现一种“群居和一”的社会。
由此可见,尽管在先秦儒家最为重要的三位代表人物孔、孟、荀那里,他们的思想不尽一致,然而其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平天下”。传统“道统”观念过于纠结他们尤其是孟子与荀子之间在具体观念的纷争上,比如将“性善”与“性恶”截然对立起来看,殊不知,在孟子与荀子那里,不管是“性善”还是“性恶”都只是一种方式与手段,这种方式与手段的最终目的是相同的,那就是“天下”。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儒学如果确实存在一个“道统”的话,那么这个“道统”应该是“天下”观念,也就是对现实社会的关切,一种强烈的“济世”品格才是儒学的应有之义。
三、“天下”与当代使命
既然对“天下”的关切才应该为儒学所坚守的“道统”,那么儒学的当代使命无疑就是面向现今之“天下”,也就是处理当下时代中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况且,在当今时代中,不仅我们自身社会发展需要解决很多难题,而且如何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也需要我们更加积极地应对。儒家的“天下”观念无疑可以带给我们诸多的有益启示,当前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多元文化并存并相互交锋,可以讲这是人类历史中文化交流最为频繁与活跃的时期。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一方面,儒学作为我们本土文明自然应该以包罗“天下”的胸怀,积极地与其他文化展开交流对话,不断完善发展自身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儒家的“天下”观念从一开始就具有超越某一固定国界的视野,其视能够接触到的所有人类生活的地区为“天下”,因此儒家的“天下”具有一种国际视野,其理应在当前国际关系的处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儒学的当代使命其实也就集中体现在这两点:以“天下”的胸怀实现一种现代转化以及为国际关系的处理贡献自己的力量。
首先,我们来谈儒学应该以“天下”的胸怀实现一种现代转化。在当前国际地区交流日益频繁,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背景下,世界仿佛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各种文化思潮之间不断地发生着交流碰撞,作为我们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自然也参与其中,从而具有了鲜明的时代色彩。任何以盲目自大的态度拒斥儒学与其他文化思想进行交流对话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是逆文化潮流而动的行为。其实当前很多学者已基本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儒学应该积极借鉴其他文化有益的成分来完善发展自身,从而完成儒学的现代转化,分歧主要在于在多大程度上吸取其他文化的成分以及应该吸取哪些不同文化。或许,我们从儒家的“天下”观念出发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儒学对其他文化的吸收应坚持有利于“天下”的标准,这里的“天下”便是指我们当前的社会建设,凡是有利于我们社会发展的其他文化的因子,儒学都应该积极借鉴并予以吸收,顽固地死守儒家思想某些不合时代的教条或者不加辨别地照搬外来的某种思想,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是我们应该加以摒弃的。刘述先先生认为:“今日世界讯息流通迅速,由中西比较的观点来理解和开拓自己的传统,恐怕是一条必由的道路。”[9]106确实如此,儒学面对流派纷呈的西方文化的涌入,必须积极参与到中西比较的对话之中,只有如此才能完成儒学的现代转化,适应当下社会的发展潮流,积极改变儒学自身体系中不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部分,并大力发掘其适应当下社会的积极因素。总之,儒学只有以关切“天下”的胸怀,积极吸收借鉴一切对社会发展有利的因素,才有可能在时代变化发展中不断展现出其新的生机与活力。
其次,既然儒学的“天下”观念在生成之初便是超越国界,面向其所能接触的人类全体的,那么,在国际交流与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儒学同样能够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发挥出其应有的现代价值。正如孔子所讲:“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如果将孔子讲的“礼”置于“天下”这一视域之下,那么这个“礼”便是各国之间所能普遍接受的一些国际规则,当然前提是这些国家规则必须通过各国之间的平等协商来达成,而不能通过暴力或者强权单方面制定所谓的国际规则。当前世界越发处在一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之中,既有不同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的冲突,也有各种政治因素与经济利益的交织,稍不留意就会引发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激励冲突与对抗。因此,我们需要寻求一种国际社会所能达成一致的道德底线,这种道德底线可以保证彼此之间相互尊重互不伤害。其实也只有建立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互惠合作才有可能实现。那么,这种国家之间应该遵循的“道德底线”究竟如何寻求呢?其实儒学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借鉴,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孔子认为要做到“在邦无怨”,也就是处理好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自己不想要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各国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都存在着较大差异,有时我们很难达成对“要”做什么的共识,但是我们可以退一步,在我们“不要”做什么上达成一致,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认为:“因为真正对话的实现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对话的最低要求就是通过互相沟通减少矛盾冲突,这是不可或缺的机制。”[10]256需要注意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很容易被进一步发挥为“己所欲,施于人”,显然,“己所欲,施于人” 就隐含着“强权”的因子,自己认为好的,就认定对别人也会是好的,这违背了儒学的初衷。事实上,儒家的“推己及人”应该在一种“弱”标准上加以应用,而不应在“强”标准上加以发挥,儒家思想的“推己及人”在中国文化中也曾被“强”标准所发挥,从而造成了“一言堂”“君主专制”等不良后果。总之,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我们正确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一种“道德底线”,如果自己的国家不想要战争与贫穷,那么也不要去造成别国的战争与贫穷,从而使各国之间能更为包容地对待彼此间的差异。
四、结语
在当前多元文化交织碰撞的时代背景下,儒家思想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对自身进行一种重新思考与定位,那就是儒家应该坚守什么的问题。传统的“道统”观念是千余年来儒家一直所传承与坚守的,因此,如果要回答在当前儒家应该坚守什么的问题,我们就必须对其传统的“道统”观念进行一种重估。我们通过考查发现,儒家传统的“道统”观念存在着明显的偏颇之处,其固守个别教条的同时,明显阻碍了儒学的进步与发展,对儒学近代以来的式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重估儒学“道统”的过程,也就是一个重新思索儒学“道统”的过程,我们认为儒学的“天下”观念更适应当下时代的发展要求,儒学只有以关切“天下”之胸怀积极与其他文化进行对话,才有可能实现其现代转化,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并有可能对当前国际关系的处理提供有益的借鉴。重估儒学“道统”的目的,从根本上是为儒学赋予崭新的时代内涵,唯如此,儒学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才能够承担其应有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