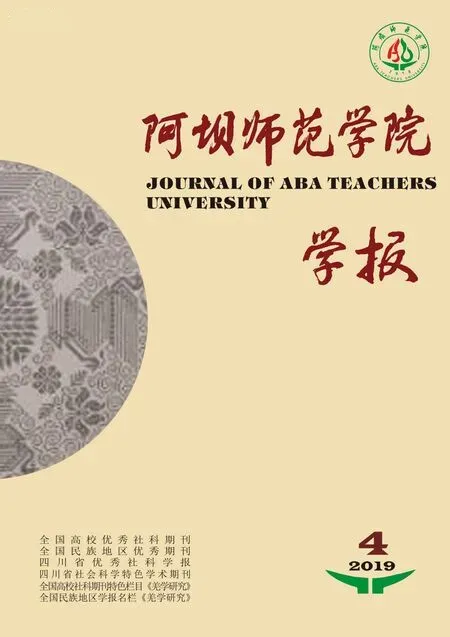古羌江源文明再认识
——华夏文明多元发祥的重要一脉
王永安
学界谈及华夏文明的起源地话题时,惯常说法是“关中渭水流域”或“中原大地”[1],此种见解有其历史依据。与此同时,我们更强调华夏文明的多元起源,否则,何以成就兼具整体性与多样性的中华文明、中国文化?岷江上游古称“江源”,《水经注·江水》云:“岷山,即渎山也,水曰渎水矣;又谓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导也。”[2]1035在古人眼里,江(长江)、河(黄河)、淮(淮河)、济(济水),为天下之大脉,尤以江为著,故列为首。而岷江长久被视为长江正源,所以岷江上游谓之江源之地,也即“大禹故里、西蜀羌乡”。诚如谭继和指出:“这个区域是华夏文明满天星斗起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发祥地。”[3]2
一、上古族群互动:古羌江源文明与华夏文明始源共生
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陇蜀和中原地区出现了一些较大的部落与邦国。他们为了生存时而联盟,时而发生战争。著名的炎帝部落、黄帝部落、蚩尤部落等族群,就是在战争与和平之间进行着族群互动、文化互融的史前“文明对话”。黄帝则是融合了包括炎帝部落等而逐渐壮大的族群联盟[4]。考炎黄族群根源,据《国语·晋语四》所言:“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5]385又如彭邦本论及:“从黄帝与炎帝均为早期西部的羌人支系,且同出一源,则二者所居,当依例相近。”[6]137黄帝与炎帝,皆为华夏人文初祖,既然炎黄同根,华夏文明初萌于炎羌文明之论或亦成立。
上古时期战争是族群互动的一种形式,而在经济、文化、日常生活上的来往更是族群互动的主要形式。例如,跨区域、跨族群间通婚联姻是很值得关注的。据《史记·五帝本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取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7]5西陵即为蚕陵,乃今日茂县之叠溪也。邓少琴指出,叠溪之叠字,乃嫘祖二字合文之省[8]28。结合地方语言,本研究注意到,羌语“祖”字之音乃指“水”,指溪指河,而“嫘”字蜀中语言读如“垒”或luó。这种羌语与汉语地方语言合文组词,意思是十分明确的,即嫘祖之名其实也是地名(叠溪)的称呼。除黄帝与西羌江源之地结下姻亲关系外,其子昌意也娶蜀山氏女为妻,其曾孙崇伯鲧纳汶山广柔女修已为妻,其玄孙姒禹又纳汶山涂山氏女为妻[9]。黄帝及其直系后裔如此密集地与西蜀羌方建立姻亲关系,是值得研究的历史事件,从中可以窥知两个问题。其一,黄帝部落集团选择与西羌之女为妻,其实是中原与西蜀两个区域、炎黄联盟与古羌族群两个政治集团、华夏文明与江源西羌文明两大文明的联姻。其二,古往今来求偶结婚要双方“看得起”。正如《诗经》所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10]2那么,黄帝氏族数代求偶于西羌之女,说明他们“看得起”西羌之女。从“人缘”上来讲,前有炎黄部落的联盟,已为羌夏互联创立了基础,以至于当黄帝部落与西陵、西羌交通联姻时,相互的隔膜、障碍就变得很小了。从地缘上来讲,也即从地理方位和交通上来看,黄帝所居的“姬水”和“嫘祖”为代表的西陵之女,实际上是渭河流域和岷江流域之间的联姻相通,是中原文明与古羌江源文明的互联互通,更是华夏文明的滥觞。
二、“禹生石纽”:古羌禹迹腹心区域的文化标杆
对于大禹的具体出生地,历来见解纷纭,总体上亦有较为趋同一致的说法,即是“禹生石纽”“禹兴西羌”之论。诸如西汉扬雄《蜀王本记》中写道:“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畔。”[11]380又如东汉赵晔在《吴越春秋》中载:“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12]101再如东汉末谯周在《蜀王纪》中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13]537上述文献记载大多出自蜀人记载,也相当于是史实传说的“当地人”的记录,获取纪实性的素材来源比较便捷,也有一定的可信度。
不过,“西羌”是一个宏观区域,特别是古汶山郡广柔县,因历经数百年之变迁,其治所也常处于流变状态。就龙门山地区的汶川、北川、理县、茂县乃至于都江堰、什邡等地都属于此区域,并且有关县份都有“石纽”和“刳儿坪”等丰富的禹迹传说[14]。大禹生地在哪个“石纽”“刳儿坪”,不好明确下来。宋代有人把“石纽”限定于两地,即汶川与北川,将汶川的“石纽”称为“古石纽”,将北川之“石纽”称为“今石纽”。这样的认定,将分歧的区域相对划小了。但是,问题在于,人的出生只有一次,出生地也应该只有一个。大禹生于古石纽还是今石纽?汶川、北川为此各持已见,直到今天分歧仍然存在。
2004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峡考古队在重庆市云阳县旧县坪发掘出东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此碑距今已有1800余年,是东汉朐忍的后任县令雍陟对前任景云县令所立的“碑”。碑文记叙了景云县令的家世以及他化政如神、深得民爱等情形。碑文旨在颂扬景云县令的政功、政德,属“政绩碑”。但是在行文之中谈到了“大禹”“汶川”等内容。例如在谈到景云的家世先祖时,言景氏先祖源自高阳颛顼夏后氏系,与大禹一起治水行天下,因功分封于楚地,后辗转定居蜀地。大约在夏朝少康中兴时,其先人伯况带着一些族人省访故里、聚会汶川,述怀禹迹,祭祀大禹。访问汶川期间,他们在车上屋内设立大禹祭台、神位,敬香膜拜大禹:“先人伯况,匪志慷慨,述禹石纽,汶川之会。帏屋甲帐,龟车留遰。又如在颂扬景云人品高尚,政绩卓著时写道:“惟汶降神,梃斯君兮。”[15]
景云碑的发现纯属偶然,如果不修三峡工程,此碑将永埋于地下。因为偶得,就少了“刻意”“造假”之嫌。再说碑文内容本在颂功赞美,却旁及“述禹石纽”“惟汶降神”的记述,这不仅印证了扬雄等人“禹生石纽”之论,还进一步限定性地、排他性地表述为“禹生汶川石纽”。如此明确表述,让千百年来禹生何地的“公案”基本上有了结论。这个淹埋于地下近两千年的文物所提供的“证据”,其可信度不言而喻。
毋庸置疑,大禹的成长地应该是有很多处的,至少包括汶川在内的岷江上游、北川在内的湔江流域乃至毗连的古羌冉駹之地。大禹之所以在成长中留下了许多“禹迹”,可能是因为当时古羌人游牧兼农业、狩猎的生计方式,以及随父治水,居所流动性较大所致。需要注意的是,禹生汶川的历史真实性、相关禹迹的关联性以及“惟汶降神”的独特性是不可忽视的。
首先,汶川地处古羌江源文明的腹心地带。羌语之“岷汶”,有“天方”的意思。同时,在古人认知概念里,岷山之“岷”、汶水之“汶”的本义即有迷蒙、神秘、混沌之意,也有仙方神居、高山仰止的意思。大禹,名曰“文命”,与“汶岷”相谐。此与古羌人在取名时托命山水万物之风俗极为吻合。有其地,即有其人。人杰地灵,地灵人杰,此之谓也。
其次,汶川的众多禹迹中,尤以“三山”同列一地名扬天下。这就是石纽山,涂禹山和天赦山。三山都是圣地,都受到当地人的保护。“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中,不敢追,云畏禹神。”[16]190就目前而言,在我有限的见闻里,大概只有汶川才有“天赦山”。天赦山大概是大禹时代祭天祭神的天然祭坛,这完全符合古羌人在野外山颠设坛敬神的习俗。虽然没有文献记载大禹曾在这里主持祭祀的盛况,但可以肯定人们在这里敬祀神禹,保护圣地当属无疑。天赦山是古代祭祀神坛,若此论成立,那么,大禹降生汶川亦当是顺理成章之事。同理,其他地方没有“天赦山”,亦属正常,更加证实“唯汶降神”实非虚传。
再次,景云碑所提示的相关信息可知,景云先祖伯况在夏代少康时来祭祀大禹。伯况就是伯杼,他系少康之子,乃夏代第七代君王。他卒众“汶川之会”来祭拜大禹,这既是夏后氏系认宗追远的家族之祭,也是代表夏王朝的“国家祭祀”。伯杼的大禹之祭影响引导了汶川民间祭祀,尤其绵虒乡人直到今天都有拜大禹的习俗。据当地一些老人讲,每年的二月二、六月六、九月九,都是朝拜圣禹的神期日子。当地民谣曰:“禹王庙、圣母祠,朝拜香火很是旺;飞沙关、高店子,烂稀饭都卖得好价钱!”汶川祭祀大禹,“官祭”历史那厚重,“民祭”信众虔诚,敬禹的民间文化氛围浓重,这是历史铸就的宗教习为,是禹生汶川所形成的特定的禹羌地标性文化之反映。
三、“禹兴西羌”:古羌江源文明对华夏文明的贡献
古人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本人却对大禹赞佩的五体投地。他说:“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无疑,大禹是继三皇五帝,成就华夏文明的人文初祖。对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探寻他的出生地、成长地,探寻他的发迹、兴起的人生背景,其实也是对华夏文明的一种寻根求源的途径。
司马迁“禹兴于西羌”的说法,不仅将大禹的出生地、成长地做了概括性的表述,而且把大禹兴起以及走向成功的基础因素归结于“西羌”的人文环境。换句话说,了解西羌、研究西羌,即是理解大禹与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路径。由此,无论汶川、北川县,还是理县、茂县都是圣人的故乡,都是江源古羌文明的摇篮,都是伟大的华夏文明的发祥地。
(一)古羌原始宗教对“禹兴西羌”的影响
岷山在古代称为昆仑山,这里万山簇拥,高峰接天。在古人眼里,这里离天最近,是神仙的“居所”、上天的“阶梯”。从对大山的崇敬转而对石的崇敬是十分自然的。古代文献中多有“禹生石纽”,禹居“禹穴”的记载,这与“西羌拜石”“夏社崇石”极有关系。因为石头撞击后可以生成火,继而带来光明、安全、熟食,所以,对石崇拜与火崇拜是一致的。羌族的白石崇拜虽有多种说法,其中对火神的崇拜可能是根基性的因素[17]。火可以生成青烟,上达苍穹,而天神“莫达伯”(羌语发音)正是古羌人心中最大的神,所以羌人最初实行火葬。其目的是投入天神的怀抱,这也是敬天所生发的丧葬习俗。
在上古西羌地域里,每一个人都无不打上“神”的烙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他也不例外。他自小濡染于西羌之地,无不体现着西羌的人文特点。仅以他的姓氏名字来分析,也可窥其一斑:禹,姒姓。“姒”可能是古羌语读音,“姒”与“释”的羌语音近并含义相同。“释”即是“释比”(也是“姒比”)。羌语“比”指“老人”或“父亲”,而“释”就是“知道”“智慧”,能通天意、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姒比”是古羌人的祭师,是与神灵沟通的智者。上古时,姒姓者可能是掌管着祭祀,在部落氏族中属于贵族当权者;再说,“禹”在释比经文中称为“耶格西”或“耶嘎西”,比如汶山寨禹王宫所敬之神即称耶嘎西。“格西”是“能干”“厉害”的意思,而“耶嘎”是指展翅而飞的大鸟。“耶格西”或“耶嘎西”就是指能搏击风云、翱翔天宇的神鸟。今汶川飞沙关、羊店附近有个“大邑坪”的地方,也有人说是“大禹坪”。“大邑”之“邑”,可能与“耶格西”之名有关,可能是神鸟起降的圣地。所以,从大禹之名姓可以看出古羌人对天的崇拜,或者说在古羌人的名姓里都充满了神的辉光。
古时,人们普遍认为昆仑山周围有海、有龙,岷江被视为“江源”,而岷山被视为华夏山川之“龙头”。《史记·天官书》云:“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因此古羌人向有崇龙拜龙之习。直到今天,每个寨子都有龙王庙或叫“王爷庙”。许多庙子虽曰为庙,其实就是一个山包、土坛,这与古羌人有神无庙无偶像古今一致。其实,在大禹时代。可以说是个“造神”的时代,他的母亲含神珠而孕,早就是一个神话的开端。至于因为治水,就意含“管水”“控水”,意含呼风唤雨、风调雨顺,于是,大禹就成了“龙”。于是,龙的传说、龙的神恩在“西王国”逐渐衍化为崇拜龙的宗教习俗。时至今日,大禹的诞辰“六月六”又称为龙的生日。羌地有谚:“六月六、晒龙衣,打湿龙衣要晒七七四十九天。”龙衣就是龙的衣服,就是大禹的衣服。
从上述可知,在大禹时代,每一个人的眼界里无不闪现着神灵的光辉。每一个人既是神灵的崇拜者,也是神灵的“创造者”。大禹就是山川万物的崇拜者,也是被人们拥戴神话的人物。夏氏掌管了国之神器后,更是建立了新的神灵世界。这便是“禹兴西羌”的宗教文化背景。随着大禹治水的足迹遍布九州,随着大禹治水团队与其他族群的互动交往,古羌文化得到了传播,各种文明有了接触与融合。此后,中国的神仙崇拜、龙崇拜、道教文化等都在如此背景下孕育,逐渐成熟,终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二)大禹治水与文明传播路径
2000—2006年,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及阿坝州文管所、茂县羌族博物馆组织了联会考古队,先后五次对营盘山遗址进行了发掘研究。营盘山遗址的年代距今约为4600—5300年。在遗址中发现了植物种子近8000粒,以粟(2350粒)、黍(2161粒)、藜属(2405粒)和狗尾草(548粒)为大宗[18]1-16。此考古结果可以说明,早在四、五千年前,岷江上游一带已有大量的人类活动遗迹;大量植物种子的遗存,证明这里已经出现了早期农业,并且可以证明当初这个区域水草丰茂,气候比现今湿润。
我们知道,岷江上游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系中国南北地质的断裂带,是地震多发区。据地质专家考证,这里约在两万年前曾多次发生过极端灾变,形成过一系列古堰塞湖(当地称为“海子”)。公元前四、五千年,这里因为地震、洪灾一度变成了汪洋泽国[19]。对此,羌族的创世纪神话中就有《黄水潮天》的故事。其中讲到当初洪水泛滥时,浊浪齐天,水面上飘浮着无数人和动物的尸体以及烂草枯木,大地上仅剩下了两兄妹。在天神“莫塔伯”的保佑下,兄妹繁衍了人间[20]5-6。现今羌族男子穿的形如船的“潮鞋”,女子所穿纹如水波的“云云鞋”,就是为了纪念水灾而留存的民族集体记忆之表征。
以上所述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岷江上游区域自古以来自然灾害频发,尤其是地震、洪灾给先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可以断定,大禹生活时代,洪灾所波及的危害范围很广大,或如当时人们所认知的“全天下”;二是在大禹时代的岷江上游及其周边地区,已经有了早期粟作,洪灾对农业等生业的破坏,让先民们民不聊生。抗洪救灾成为黎民百姓最迫切的心愿和呼声。大禹正好诞生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他生于西羌,身临其境,深知民间疾苦。在舜帝时,他临危受命,担当起了治水救灾的大任。
当然,并非所有文明的起源与传播必须以灾难为条件,但是在历史的必然与偶然中,有时的确是因为灾难降临引发了人们战胜灾难的斗志,故而转危为安,变祸为福。大禹治水就是始终贯穿战胜水患,多难兴邦的过程,更是古羌文明得到了一次划时代意义的传播过程。
首先,大禹治水团队是传播古羌文化的先行者。大禹治水无疑是宏大的社会工程,大禹作为领袖,其组织、指挥、协调等作用是无可否认的。除却神话色彩,个人的作用总是有限的,民众和团队的作用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根据《景云碑》提供的史料信息,地处水患重灾区的西羌民众都踊跃参加了大禹治水工程。而且许多人始终与大禹一道走南闯北,亹亹穆穆,最终疏通了九河,治理了九州,封功于会稽。他们的许多后裔还继续为国“攘境蕃卫”“镇安海内”。景云家族作为个案就是一个明证,也是颇能代表“汶山”地区先民们参加大禹治水的典型。
其次,“大禹治水”是传播古羌文明的成功尝试和历史契机。史料记载,因鲧治水不成,乃殛鲧于羽山以死。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鲧之业”何也,就是治水。后来大禹不仅治水成功,治国也很成功。被“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在古代众多典籍中,记载大禹治水的内容较多,而大禹治国的内容就很少。其实稍加分析,大禹治水和治国是同一行为的两个方面。在上古大禹时代值新石器末期,氏族、部落、“方国”“邦国”林立,各自为阵,常常为争夺土地或人口等资源杀伐战争不断。炎黄二帝“战于阪泉之野”,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等等,就是曾被司马迁记载的上古相互征战的“史实”。但是,在大禹治水的十三年间,没有战争的记录,虽然并不表明当时没有战争。但是毕竟夏王朝统摄了天下,民心归禹如形影相随,正好说明他们的治国之道是非常成功。
我们认为,大禹为首的夏王朝的成功正是在于治水得民心,民心是最好的“攻城掠地”。治水让许多松散的互不统属的部落得到联合,治水让各个族群有了利益上的相帮、互助,以及资源上的共享。治水这个伟大的社会工程必须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于是治水产生了管理,产生了集权,最终从治水的机构演变上升为国家政权。故而,治水本身就是传播文明的途径与契机。大禹作为西羌人,用来自西羌的思维、理念、文化来治水治国,更是书写华夏文明的煌煌大作。
四、结语
文明的起源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人类摆脱野蛮状态,进入秩序社会的过程。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她的形成和发展,如众山托起的巍峨,如多源共汇的江海。古代江源之地,是我国著名的禹迹圣地、西蜀羌乡。这里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发祥地。从上古族群互动中可以看到江源之地与中原之地有过十分频繁的接触、互联互通。尤以黄帝为首的氏族与西羌氏族的联姻通婚为例,充分说明上古江源之地已非一般的聚落人群,这里的自然生态、文化生态已经发展得相当充分了。也就是说她与中原文明有着“门当户对”对话“联姻”的基础, 对华夏文明走向成熟与浩大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大禹生于新石器晚期,此时的中国正是华夏文明最活跃的肇始阶段。大禹无疑是奠定华夏国家文明开创性与标志性人物。大量文献和史前传说证明大禹生于汶川石纽、兴于西羌。他的思想、言行无不打上禹里的烙印。大禹对华夏文明做出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古羌江源文明对华夏文明的贡献。
西羌,既是上古族群的一个称谓,也是上古西部区域众多族群、部落的泛称。从古西羌发脉形成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应该包括岷江上游的羌族,以及西南、西北诸地的众多民族。研究江源文明、大禹文化,不惟一方一地一人一族之辩,而是着眼于整个中华民族,着眼于华夏文明的开启与绍续。这对传承中华文化、发扬大禹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进一步增进华夏一家亲的认同感,从而进一步激发向心力和爱国热情,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目前,学界对夏商周断代史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就,但尚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例如,许多研究更多的精力投注于人们熟知的核心区域,如黄河流域的“晋南豫西”,但对西部山区关注力不高,以至成为研究的“盲点”。一些研究尽管述及江源文明,也承认西羌之地禹迹多多,但一直停留于司马迁、扬雄的文论里,停留于民间的神话传说中。我们期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文史研究有所突破,这要借助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交叉性、综合性研究,从而对江源文明、禹兴西羌等主题有更为重大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