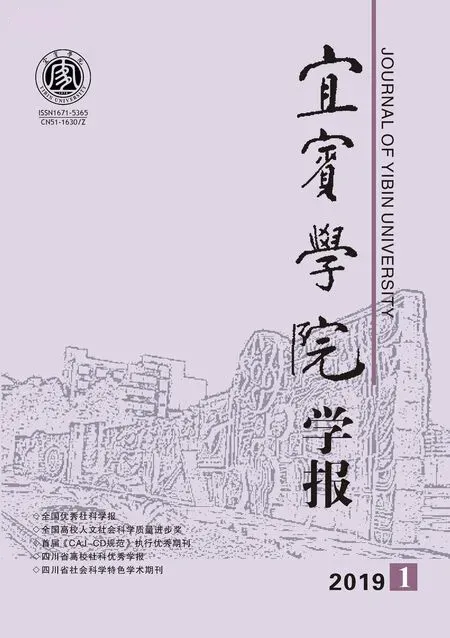地下歌者的文化建构、自我完善及表达设置
——青年边缘亚文化群体探微
沈 杨,朱 雅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扬州225009)
2018年7月14日,由爱奇艺自主摄制的音乐真人秀节目《中国新说唱》又一次让“hip-hop”①文化在社会发展圈中大爆发。同时,也让人们对于“地下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熟知。与商业主流机制不同,他们有自己的演出场所、媒体、发行渠道、受众群体、自己做演出海报、自己发布演出通知,有别于地上传统定义的演艺群体,社会将其称之为“地下XX”。“地下歌者”是社会对于从事“hip-hop”表演者的称呼。面对松垮的着装、奇异的装扮以及充斥个性化的歌词设置,hip-hop引起了当下青年群体的积极回应,更多的青年参与到其中,通过文化原创的方式有效地促进hip-hop的普及力度。但主流群体却往往会对此报以淡漠甚至拒绝的态度:“这也算是歌曲吗”“这不就是那些平常不好好学习的那类人吗”“你看看他们的奇装异服。”在现代社会发展中,青年边缘亚文化发展总是伴随着风险与自由的双重矛盾,而青年群体总是享受这样的矛盾,认为自己通过娱乐性、戏谑化的心态缓解社会给予的种种压力,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表明的“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1]4面对主流社会的质疑,为何青年群体仍然要坚持并投入?对于文化的奇特追求背后彰显了青年群体如何的现实境遇?青年群体在其中自我获取了什么以及文化发展的表达特质如何体现?本文通过对于当下流行的hip-hop的深度观察与资料透析,分析“地下团体”的本质属性、文化趋向、生活方式及表达设置。
一、 地下歌者的文化建构及反抗:仪式背后的趣缘聚合
要理解hip-hop群体所从事的行为本质内涵,首先就要从青年文化表征入手,hip-hop作为一种当下青年群体所疯狂追逐的文化表现形式,其产生、发展到风靡的过程并不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偶然体现,我国学者衣俊卿认为:“任何文化都不是简单的社会附属,在现象背后更多表现出来的是文化内在与社会实践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2]72。hip-hop的初始文化产生来自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街头,黑人青年描述自身街头生活及宣泄对于社会不公的文化武器,原本就是一种带有反主流文化倾向的亚文化形式。以Beastie Boy(布斯迪男孩)、Puff Daddy(吹牛老爹)、Eminem(埃米纳姆)、Jay-z(肖恩·科里·卡特)等全美说唱巨星逐渐将hip-hop这样的地下文化形式带到正统的公共舞台上,但是其主要的文化表征仍然具有黑人文化中的显著特点,这在歌曲名以及歌词设置上都有很充分的表现。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给hip-hop文化传入我国带来可能性,hip-hop在21世纪初逐渐在我国青年群体中广泛流传。起初,青年群体大部分通过录音带或CD了解hip-hop,“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听到快节奏的歌曲,咬字不清的旋律。我就觉得这个音乐形式就是我喜欢的,这比什么春晚上的《难忘今宵》好多了好吧,这才是我们青年人应该去听、去玩的音乐形式,你听过埃米纳姆的《rap god》么,那个真的是太棒了,听完那个后,我就开始了疯狂的追随和模仿。”②与传统音乐截然不同的节奏点以及充满个性化的言语包袱都让青年们在短时间内接受了这一项异域文化。
(一)青年亚文化建构基础:网络空间的传播认同及趣缘聚合
在主流社会的视域中,这样的演唱技术并不符合群体对于青年发展的传统要求,表演形式的不正统化,词语的成人化、污化让社会群体对于这样的演唱形式嗤之以鼻。所有的社会群体都会制定规则,并且在某些时候和某些情况下努力执行这些规则。社会规则定义了情境以及适合于这一情境的行为类型,把一些行为规划为“对的”,禁止另一些“错的”行为。[3]15以奇装异服、节奏新奇的hip-hop文化模式,在主流传统视域中始终是无法得到认同的文化形式,以hip-hop文化作为起始点常被归纳到青年负文化、青年反文化的发展方向。现实中,以边缘亚文化为主要表征的青年群体在接受hip-hop文化的同时,只能以“隔离现实”“脱离主流”的地下文化作为载体的实现自身对于hip-hop文化的最终追求。地下hip-hop群体发展有自身固有的发展模式,小众的消费团体和固定的表演形式及表演场所,始终将表演“另类”风格的演绎作为自身文化发展的座右铭。伴随着网络空间发展的不断完善,hip-hop文化的发展寻求到了全新的发展路线——虚拟的网络空间。网络空间的即时性、无差别、不确定性等特点给hip-hop文化及表演者提供了一个完全自由发展的赛博空间,如:在网络空间上传自己的说唱视频,或是通过虚拟技术虚拟电音(remix)优化自己的说唱旋律。同时,以网络直播的模式举行关于说唱的小规模比赛,多样化说唱文化融入也通过网络虚拟技术提供了可能性及实践性的平台,如在B站(BILIBILI)中up主“非桥段”的上传视频“康熙说唱王朝:部落到帝国,怒斥群臣”的点击量就达到了916.5万。久而久之,hip-hop文化的发展由地下的文化自嗨逐渐发展为当代青年彰显自身文化价值的文化自嗨。众多hip-hop歌手经由网络空间的快速传播逐渐被更多的青年网民所熟知,如:GAI、海尔兄弟、小老虎等,网络空间的生成发展可以说赋予了青年群体边缘亚文化发展的自由空间。在这里,大家可以通过简单的打招呼、加好友就可以找到与自己趣缘聚合的团体,能够形成数量可观的青年趣缘集体,青年群体的集体抵抗往往就来自这些在网络空间建立起来的爱好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对于亚文化载体有相同喜好的青年可以互相交流他们的独特见解,并且青年亚文化集体也存在等级性,那些技高一筹的人在人群中拥有更高的地位,并以此来作为牢固集体的粘合剂。
(二)青年边缘亚文化的仪式抵抗:自娱自乐到公开的独特抵抗
青年边缘亚文化的仪式抵抗的定义来自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青年亚文化的产生来自青年的街头生活,其产生根源于青年地位、权力被忽视且无法有效协助青年群体寻求解决自身在现实社会中的角色缺失下的“失权”“弱权”的实际困境。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文化撞击和发展冲击赋予青年自我探索提供了土壤,比如:阴三儿的《老师你好》、宋岳庭的《Life A Struggle》等其中包含着青年群体发展的文化缩影,主流社会的期待压力往往造成了青年发展的路径固化,整合青年文化发展的特征,青春性、多变性和挑战性的特性有别于位居社会主体的成人文化,其实际反映出了成人世界与青春世界、父辈一代与子一代之间那种永恒的矛盾和张力关系。[4]1“你也知道我父母根本不同意我去干这些,在他们看来我这个可能是不务正业的,他们就希望我天天好好学习,我看着他们都觉得烦,我就要和他们对着来,谁怕谁。”青年边缘亚文化的发展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性,主流群体发展模式的不认可及边缘文化群体发展行为独有的文化创造力和多样性都成为其主要障碍。主流群体也将青年边缘亚文化的发展视为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民间恶魔”,青年群体则始终坚持对于自身文化的独特改造,通过对于hip-hop的透视,这样的变化往往在歌曲形式及歌词设置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老师他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老师。我讨厌穿制服,我讨厌学校的制度。我讨厌训导主任的嘴脸,讨厌被束缚。很多人不屑我的态度,他们说我太cool。没有谁有权力拿他的标准衡量我。主宰是我自己,随便人家如何想,我还是我。”(歌词来自宋岳庭《Life A Struggle》③)hip-hop歌词中出现这样明显的对抗主流群体的歌词设置更多折射出来的是青年群体处在发展困境中的迫切心理,得不到周围群体的理解和认识。同时,以一个“局外人”的定位去对抗主流群体的看法及规制。“我抵抗,胸口存在的不安及惶恐,我不断听到痛苦的声音在内心怒吼。Life a struggle日子还要过。品尝喜怒哀乐之后,又是数不尽的troubles。”对抗主流社会的固有文化已然成为现代青年边缘亚文化群体的文化默契,依靠冲击文化传统的壁垒从而不断加强青年群体的文化保护墙以及文化抵抗力。
当然,终究边缘亚文化会被主流文化所同化、接受或是改造,作为一个以hip-hop文化为信仰的真玩家,他们享受来自hip-hop文化带给他们的边缘亚文化体验的刺激感以及群体认同的虚荣心和自我满足程度。即使,这样刺激的文化只能是一种美好的乌托邦寄托,但是他们依旧享受这样的一种短暂胜利带来的精神快感。在当代文化的理解中,hip-hop在青年的视域中已不仅仅是一种“underground”(地下、小众),而是通过音乐去表达青年的发展际遇和社会文化的有效形式,同时,也体现出青年边缘亚文化发展的严峻局面。
二、 仪式抵抗中的自我完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补贴
边缘文化的发展需要以独特的文化形式及新奇的文化内容才能够形成一定的抵抗力。以hip-hop的实际发展为个例,hip-hop文化能够有助于青年群体逾越文化困境,使得青年群体在文化体验中获得充分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能够通过文化内容的构建获得刺激感和愉悦感,不过往往这只是青年边缘文化体验中的一部分,青年在文化体验中往往也非常注重自我个体的有序完善。处于集体主义发展目标下青年个体总是被“有计划”地安排和固化在特定的社会位置,即丧失了自我发展的主动选择,同时,也忽略了青年本身发展的个性设置。以hip-hop歌手那吾克热(LIL-EM)的说唱曲目《水滴石穿》中这样说道:“你说这条路上谁都没有犯错,谁没有走过弯路,但我庆幸的是,我找回了自己。”寻求自我以及完善自我一贯是青年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个性体现,往往青年强调的寻求自我包括:精神世界的自我完善及现实社会的自我满足。
(一)刺激的舞台风格:制霸④舞台的征服快感
作为地下文化的一种,hip-hop文化有其独特的表演方式,也有其特有的表演文化。在表演文化中不会一直遵循传统文化中的辈分等级因素,在台下可以尊重对方、称兄道弟,到了台上就是各凭本事的疯狂互怼成为hip-hop文化中的众生相。从诞生到发展hip-hop文化就是一种可以随心所欲说出你自己想说的,尽情抱怨你在现实社会中所遇到的不公平,通过歌词diss宣泄自己心中不快事,可谓是“不吐不快”。“没有敌意,其实私下里我和这些idol我们还是挺聊得来的,人是人,作品是作品,你不行就是不行”[5]。在对于hip-hop歌手来说,制霸舞台,将对手怼得无话可说就是对于对方最大的respect(尊重)。“去参加livehouse的说唱比赛刚上场的时候挺紧张的,下面的观众盯着你,评委盯着你并找准机会diss你,但是一上场吧,下面的朋友及观众都在给我欢呼,整个舞台就是我一个人,我一个人控制着整个演出,下面还有小姐姐给我打节拍,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就是人生赢家,你知道这种感觉吗,太棒了!”将自己对于现实生活的抱怨宣泄在演出中,青年群体在同辈群体的自创空间中“刷新自我”。这样的“刷新自我”来自平常现实生活的期待重压、角色定位不准确以及青年文化发展的实际困境。“当我参加了那一次吧,虽然说我比得很烂,但是之后我也更喜欢这个东西,有什么比赛我都会去参加,在网络上上传我自己的视频,有人给我点赞,在朋友面前即兴说这么一段,感觉很棒,我喜欢。”这既是一种青年边缘文化发展的成就彰显,同时也是青年在新奇文化体验中寻求自我价值的刺激历程。
(二)符合style的风格装扮:装饰服装一件都不能少
在hip-hop的外形装扮中,松弛的外套和显眼的大金链子配合说唱文化独有的慵懒气质成为人们主观印象中的hip-hop打扮方式。而如今的hip-hop文化发展中,一方面强调内在的文化构建,让青年群体在理解hip-hop文化内在的自由因子;另一方面,注重外表的极致模仿也成为了青年自我满足中的一个关键点。“你说我进来了这个圈子,人家都那种好看的外套加一双AJ鞋,我不也得这样么?”那些知名的hip-hop歌手的包装也会成为hip-hop圈竞相模仿的热点对象。如:Kanye West与阿迪达斯合作的球鞋yeezy boost 350以及Nike公司旗下系列air Jordan 1系列都成为hip-hop青年所向往的说唱装备,与大部分亚文化群体相似,追求怪异的价值诉求、强调特殊技能实际是亚文化群体宣称自己是“社会精英人群的手段”[6]296。“现在这些装备也不便宜,一件外套差不多就要1 000-2 000左右,还有现在炒到价格爆炸的AJ1和椰子350便宜的1 000多,贵的就得5 000左右,剩下一些要和大家一样的装备也得花不少钱,大家都穿了,我不穿不就等于我不是这个圈子的,你让我穿个普通鞋去表演我还会被别人瞧不起啊。”消费主义学派认为:“消费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求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7]73“现代社会的消费往往体现的不是一种物质补充,更多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文化符号。青年群体对于文化消费往往抱着一种“跟风”的态度,人们在购买和消费商品时,着重考虑和刻意追求的不是它们的物理属性和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意义和象征价值。”[8]260符合hip-hop风格的服饰搭配在当下hip-hop发展中俨然成为群体进入的“通行证”。高额的装备价格可能会刷掉一部分爱好者,但是凭借着高额的消费门槛也更能表现出hip-hop群体的自我特殊性,以消费的门槛提高地下歌者的筛选条件,从而让进入这个圈子的人能够产生一种“万里挑一”的荣誉感。
三、 仪式抵抗中的独特形式:充满文化内核的表达设置
hip-hop文化是以说唱形式为内核的文化载体,其主要表现在通过词语韵脚设置玄关,以连续的押运、上下的对称作为语言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早期在黑人群体为了方便使用母语去表达自己的意识,简化了一部分英语单词,创造了“黑人英语”⑤。如:nigger(黑鬼)被简化成nigga,另一个motherfucker也被简化成为muthafucka。黑人文化中大胆运用字母的转移变化,通过不同的表达节奏,迎合歌曲的节奏点而去表达词语其本身的不同含义。很多的单词含义在逐渐发展之后也被好莱坞等媒体群体所接受、使用、普及。但是,作为地下黑人文化,也有其作为黑人地下风格的词语代表,如:fuck、shit、sex、drug等折射出社会负方面的词语。以黑人地下风格作为主体的hip-hop文化,在传入中国之初,其早期多数是沿袭美式黑人风格的模仿或是对于崇拜偶像的复制演唱。很多语言梗来自西方的语言传统但容易让主流意识形态对hip-hop文化产生误解,将这种外来亚文化的表现形式归类于反文化、负文化。
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入及传统语言艺术的掺入也让hip-hop的词语设置并不是单纯的词语排列,歌词设置中融入了许多排比、对称的语言形式。如:MC Hotdog的《差不多先生》以差不多作为一个排比序列:“我抽着差不多的烟,又过了差不多的一天;时间差不多的闲,我花着差不多的钱;口味要差不多的咸,做人要差不多的贱。”结合传统语言艺术中的排比形式让人们能够更好地体会hip-hop表达的韵律感及降低语言模仿的难度而增强青年群体关于hip-hop的学习或是普及。同时以韵脚相同叠加押韵的方式,也说唱歌手吸引关注和引发热度的手段,如:“感谢年轻的生命,不同的声音,像猛禽。这将增加难度,让游戏更新。传播挫折,阻止弱势群体。一半人被残酷的掠夺,强者有权活下去”(歌词来自马俊《我的梦想》)。以结尾的歌词歌词押运能够顺应节奏,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表征。
在语言设置取巧之外,hip-hop歌词的表达也在形成之初就沿袭青年群体的心之所向。以地下街头的文化表达作为hip-hop歌词设置的主要内容。hip-hop歌词设置所体现出来的是奇特的文化表达,脱离传统约束的文化程度,以“暴力”“色情”“戏虐”“诙谐”的文字内容构成的文化形式。通过歌词的表达之意嘲讽社会主流群针对青年群体及小众文化的抹杀及轻视,以一种“放荡不羁爱自由”的文化形态去保卫自身的文化地位。如:“我早就受够了,当你走投无路,回避生存面临危机,被迫变得卑鄙,生活变成恐惧。”(歌词来自艾热《受够了》)。歌词中表达对于生活困境的一种无所适从,往往这体现为一种文化发展的不理解和文化发展的孤独感。同时,歌词的表达设置也结合当下青年群体所喜爱的网络文化、二次元文化、体育文化等作为歌词生成的主要参考,如:“还不习惯讲skr,最死忠的科粉习惯不了詹姆斯穿紫色。”(歌词来自张震岳《飞太远》)。歌词反映出青年群体社会发展下的文化压力,结合当下青年所认同的文化形式也就成为hip-hop歌词设置的主要来源。
结语
边缘亚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并不是青年发展中的异端,而是社会快速发展忽视青年文化基础建设的必然结果。当下,我国的青年亚文化发展特点与西方青年发展有很大的不同,较之西方青年群体行为的暴力性、直接性,我国的青年行为多数处在对于原有传统文化形式的自我特色改造,其温和进行的仪式抵抗也给我们合理对待亚文化群体提供了诸多行之有效的策略。目前,青年边缘亚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双侧利益重叠,通过利益发展的共合体促进边缘亚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双向破壁。当前,hip-hop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味的“特立独行”,也不是一谈到说唱就是“低俗风”“滞后风”,说唱文化也可以在自由创造中具有“社会风”及“正能量”。2018年4月3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高长利指出:“自主创新的节目应该坚持以“小大正”(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为指引,解决一系列短板和顽疾”[9]。第二季的中国新说唱以hip-hop为节目基础,其中充满了众多的正能量以及慢慢的中国风。比如:那吾克热的《儿子娃娃》中的“我来自新疆,And I am made in China。”通过青年群体喜闻乐见的亚文化形式,积极融入传统优秀文化及现代发展的主流价值,通过破壁融合的文化形式拉近青年去主流群体之间的距离,一方面,让青年能够意识到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在发展过程中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能够加速主流群体针对青年边缘亚文化形式的积极认同,让边缘不再边缘。
注释:
①hip-hop是文化名词,包括饶舌(rap)、打碟(DJ)、涂鸦(Graffiti)、街舞(street dance)。hip-hop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文翻译为嘻哈,hip-hop从字面上看hip是臀部,hop是单脚跳,hip-hop则是轻扭摆臀,原先指的是雏形阶段的街舞,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我们所熟知的现代定义。
②采访者为石凯瑞(carry),陕西西安人,日常石油人兼职自由说唱歌手。
③文章中所摘录的歌词均来自网易云音乐搜索引擎。
④制霸即称霸,获得冠军之意。
⑤黑人英语:黑人英语是英语的一种变体,使用者多为身处社会下层的美国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