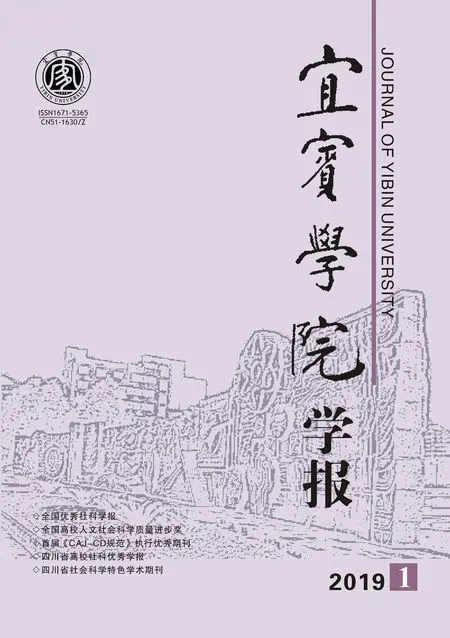洛克观念起源论中的“知觉”概念
牛桥钢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桂林541000)
洛克的观念哲学旗帜鲜明地反对天赋观念论,“在近代哲学史上第一次力图创立一个博大的认识论”[1]365,推动近代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洛克的观念起源论是其整个经验哲学的基础。在《论人类的认识》①中洛克把观念的来源分为“感觉”和“反省”,正是通过感觉,简单观念首先出现在心灵中,并被心灵的种种功能所作用,对这种作用的反省则造成了简单的反省观念,因此,天赋观念是不必要的,认识所需要的一切只是外物的刺激和心灵的能力。但是,这种观念起源论要想具有说服力,就不能停留于简单的断言层面,于是洛克便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方面,他尝试解释感觉的基本过程;另一方面,他尝试解释反省。知觉概念就出现在这些解释中,成为保证解释有效性的重要基础概念。这既意味着知觉的重要理论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必须回到洛克对感觉和反省的论述中才能准确地把握其知觉概念。为实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回到洛克对感觉的论述中来明确知觉的一般所指。
一、 知觉的一般所指
洛克在其观念起源论中对知觉、观念、感觉等概念的用法存在着许多模糊不清相互纠缠的现象,使得知觉的所指扑朔迷离。
对于感觉,洛克说:“我们的种种感官在熟悉了特殊的可感的对象以后,按照那些对象作用感官的各种方式,把事物的一些明晰的知觉的确传递入心灵。这样我们便获得那些观念,我们便有了黄、白、热、冷、软、硬、苦、甜,以及所有那些我们称之为感性的质”[2]76。从这段话里我们看到,感觉被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对象作用感官;第二阶段,感官传递“知觉”;第三阶段,心灵获得观念。在这里知觉是被感官所传递的“造成观念”的东西。
在另一些地方,洛克又否定了知觉的“被传递者”身份,他说:“我所谓种种感官传递入心灵,是指它们把在那里产生那些知觉的东西从外界对象传递入心灵”[2]76,被感官所传递者之所是被暂时搁置了,而知觉是某种“被产生者”。洛克后来在大多数地方将感官所传递的东西叫作“印象”,于是,知觉只能是“被产生者”,它属于感觉的第三阶段——心灵获得观念,那么要知道知觉的含义,我们就需要知道知觉与观念的区别,就要知道洛克“观念”概念和“知觉”概念的关系,因为观念和知觉在洛克那里无法在不与对方相关的情况下被理解,因此必须在洛克对知觉和观念两个语词的相对用法中确定知觉的基本含义。
洛克对“知觉”与“观念”的相对用法表明,他认为知觉并不是“心灵的直面对象”这个意义上的“被产生者”——这是观念的含义,他说“灵魂在开始知觉时,就开始有观念”“要问一个人什么时候开始有观念,无异于问他什么时候开始知觉;因为具有观念和具有知觉是同一回事。”[2]79可见,知觉指的应该是心灵获有观念(无论是否是确定的观念)。
这种“获有”显示,知觉被看作是对某种直接对待关系的命名,“心灵在自身中知觉到的一切,或者知觉,思想或理智的直接对象,我叫它们作观念。”[2]104至此,知觉与观念的关系就得到了基本澄清,“知觉是心灵运用我们的观念的第一种功能”[2]113,思想、记忆、考虑和理解等则是另一些人心对观念的运用,观念在这里我们只能说它是“人心所直接面对着的东西”(即观念作为人心的唯一对象)。洛克宣称,除了反观自察之外没有什么办法通过语言让人进一步理解这种直接面对。在这里我们选择“面对”一词还是选择“观察”“拥有”“看见”等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这里它们都不能超出一种比喻含义,最恰当的处理方法是,表述为:“人心→观念”(为方便起见,我们把箭头仍然表达为“面对”),这个表述不再联系到其他表述上,而是直接联系着“反观自察的体验”。因此,洛克知觉的一般意义类似于日常用语中感觉的意义,是一种主体与其内在对象的直接关系,这种对象和关系是不再容纳任何间接对象和间接描述的内在的原初状态。因此,洛克的“知觉”不是实体名词,也不是过程名词,而是“状态名词”。
需要这样的分析才能确定知觉的确切含义乃是因为洛克本人在表面上并不以严格一贯的方式使用观念和知觉概念,例如在“外界的对象给心灵提供可感的质的观念,它们是对象在我们里面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知觉”[2]77和“一个雪球具有引起我们的白、冷和圆的观念的能力,把引起我们的这些观念的各种能力看作是在雪球中,我叫它们作质;看作是我们理智中的感觉或知觉,我叫它们作观念”[2]104-105。在这两句话中,知觉很难被发现为严格的状态名词,二者实际上等义了,如果我们把这两句话中的知觉和观念两个概念互相替换,句子仍然表达同一个意思。但是无论如何,这里涉及一种面对和被面对。洛克大多数情况下用观念指称心灵面对的对象,所以,我们有理由坚持在“面对对象”的意义上使用知觉概念,在“被面对对象”的意义上使用观念概念。
根据我们的分析,感觉的过程实际上得到了这样的承认:第一阶段,对象作用感官;第二阶段,感官传达“产生知觉的东西”;第三阶段,人心面对观念(即知觉)。缺少任何一个阶段,感觉就不能发生,观念就不能叫作来源感觉的观念。知觉则被定义为“人心面对观念”,从可能性上来讲,知觉是人心面对观念的能力,从现实性上来讲,知觉是人心对观念的面对。如此,我们就确定了知觉的基本含义,它不是实在名词,也不是过程名词,而是“状态名词”,指称一种“潜能态”或“现实态”。毋庸置疑,这种状态是内在的,外在的过程如何造成内在的状态,为回答这个问题,洛克把知觉的发生问题带入了一种因果论。
二、 知觉的因果论
由本文第一部分可知,我们只能在知觉中提到“观念”概念,因此,第二阶段感官传达的“可造成知觉的东西”就不能是观念(更不能是知觉),而是另一种不同于观念的东西,洛克引入了“刺激”“印象”或“运动”这三个概念,这里的印象和运动由对象刺激感官而引起。借助这些概念洛克构造了一种关于知觉的因果论。
但至少在逻辑上我们将看到这种因果解释没能成功地解决知觉的发生问题,反而使得感觉的前两个阶段(简称前知觉)与知觉发生了语境的断裂。
首先,洛克的“印象”概念同时出现在对感觉的第二阶段和知觉阶段的描述中,当他说:“这是一些印象,由外在于心灵的外界物体在我们感官上做成”[9]。“它(感觉)是在身体某个部分引起的印象或运动,从而在理智中产生某种知觉”[2]88。这时,印象在感官中,是被传递的那“造成观念的东西”,当他说:“人类智力的第一种能力是心灵适合于接受在它身上的做成的印象,这要么由外界物体通过感官做成,要么由心灵反省其自身的运作时做成”[2]89。这时,印象经由感官或经由反省而存在于心灵中,它所占据的正是前文观念概念的位置。所以,要么印象属于感官或身体而不属于其与知觉的连接处,要么印象只是给观念的另一个名字,同样不能起到连接作用。
其次,洛克对知觉作了这样一个类比:“对观念的知觉之对于灵魂(我认为)就同运动之对于物体”[2]79,这样,知觉确实得到了一个新的意义:它是心灵的动作,当然,它是由外物所引发的动作。如果“印象”不足以传递到心灵中,运动似乎足以做到,只要知觉本身就是心灵的一种类似的运动。洛克把这种被引发的运动视为在第一性质层面上产生的,他举例说:“在一种情况下,它(太阳)能改变我的眼和手的一些不可感部分的体积、形状、组织和运动,从而在我们里面产生光和热的观念”[2]112。可是心灵是无形体的,这为洛克所承认,心灵不面对外物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即使对第一性质的观念也只是外在性质的模本,这也是设定“观念”这个概念的价值所在,它要标定出外在存在与心灵对象之间的这种质的差别。所以,如果知觉只是心灵的动作,那么它不是类似外物(包括身体)的运动或动作那样的运动或动作。于是,我们还是不知道一种外在的极其不同的运动何以扰动心灵并引发心灵的动作。另外,对于心灵的动作我们能知道的只是观念在以变化的方式向它呈现,我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在变化中的呈现。它恰恰是我们“何以产生知觉”这个问题的另一种问法,而不是回答。所以,心灵的运动和印象一样不能作为通向知觉的连接轴。
洛克在很多地方对感觉所作的因果论述都不是真正对知觉发生问题的解决,而毋宁说是一种拖延。在笛卡尔那里存在的二元问题,在他的观念论中依然潜在。
洛克没有成功地告诉我们感官所传递的“可造成知觉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于是,知觉的实现方式没有得到连贯的澄清,第二阶段与知觉之间的鸿沟把他的感觉论切割开来。在一种语境中,洛克谈论对象对感官的刺激,感官和整个身体所能接受的印象或运动,以及这些变化所可能对应的观念(这里潜伏着作出“预定和谐”假设的可能性),显然这是一种因果论断;在另一语境中,洛克谈论知觉现象,即心灵对观念的面对以及所能作出的各种处置。前者有时涉及一种原子论和一种粗糙的神经生理学设想;后者涉及多种类型的主体能力及其错综复杂的观念相关项。由于前者涉及知觉之前的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前知觉语境”,后者则更多地关注给定的观念,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觉语境”。洛克本人曾表达过自己对知觉的因果性解释是尝试性的,不影响其对人类认识现象的讨论,也不列在《论人类的认识》的议事日程中(但对于受其影响的心理学这个解释则至关重要)。可见,深入知觉语境而不固执于其知觉的因果论,才是理解洛克认识论的关键。
确实,自休谟之后,认识论中的知觉语境逐渐占据上风,休谟将观念来源问题转化为知觉来源问题,认为“洛克先生曾用‘观念’一词表示我们的全部知觉,违反了它的本义;我现在应用这个词,或者宁可说是恢复了它的本义。我所谓印象,读者请勿误会我是用以表示生动的知觉产生于心灵中的方式,我只是指知觉本身”[3]10。他通过把印象与观念同时视作知觉,使得观念的外在起源问题不再能够被讨论,我们能谈论的只是印象与观念之间的主观关系(休谟以清晰和强烈的程度划分彼此)。对于外部存在来说,我们似乎不能问它何以造成最初的知觉,而只能问从最初的知觉出发对于外部存在所形成的观念是如何可能的。
不过,休谟保留了心灵的独立地位,保留了洛克前知觉语境的刺激概念,他也谈到了感官受到刺激是一切的开始,但前知觉语境的因果性解释被搁置了。在康德的感性论中,刺激同样是被保留的概念,他认为“通过我们被对象刺激的方式获得表象的能力(感受性)叫作感性”[4]52,但刺激的方式乃至刺激者也被搁置了。可见,洛克的知觉语境具有被构造成独立的认知现象学的潜质,离开了前知觉的因果论,从知觉现象开始的独立的认识论是其观念哲学固有的内在可能性。后来的观念哲学都可以看作以不同方式对这种可能性的实现。
黑格尔说感性既是“最丰富的认识”,又是“最贫乏的真理”[5]61。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它就像我们上文所提到的知觉那种只能在体验中反观自察而不可再描述的定义:对观念(洛克意义上的观念)的直接面对。对于知觉(黑格尔意义上的知觉,是介于感性和知性之间的精神阶段)及其以后的意识来说,感性的对象是丰富的、变化的,但对于感性阶段的意识,其对象是“方生方死”的,这种意识始终处于一次次“新生”中。所以,黑格尔的感性贫乏指的是感性意识的形式贫乏,而其丰富性则指的是感性意识的质料丰富性。
由此可知,刺激概念的保留之所以在休谟与康德那里依然存在乃是由于它是对知觉现象之丰富性的一种解释,他们近乎本能地在质料层面上将主体视为绝对的先天贫乏者,而不是在形式上的贫乏者。质料贫乏的主体自然地要求一种来自别处的丰富性,如果这种丰富性也是主体所具有的,主体就成为一个自足的“单子”,那意味着经验主义的毁灭和趋向绝对内在的危险。洛克对知觉的发生进行的因果论解释显然也是为了捍卫经验哲学,但他并未停留于此,除了这种被动的知觉,在知觉语境里他进一步论述了“知觉的主动性”。
三、 知觉的主动性
在知觉的主动性中,洛克首先指的是知觉的“主动接受性”。
对于知觉的主动接受性洛克说:“无论对物体造成什么变化,如果变化不能传到心灵;无论在体表印上什么印记,如果不被内心注意,就不会有知觉”[6]22;随着“注意”概念的引入,印象成了“有待被注意者”,一种有待被注意的内在对象,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准观念”以便与作为“被感官所传递者”的印象相区别。我们称其为准观念因为它逻辑上必须在人心中,不然不能被人心所注意(因为观念是人心的唯一对象),同时,又不能已经被人心面对否则注意就是多余的概念。可是这是矛盾的说法,相当于说人心知觉而同时不知觉(因为在人心中就是被人心面对的意思)。那么准观念究竟是怎么回事?为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回到洛克对“有定和确定的观念”的论述中来。
孔狄亚克曾在其认识论著作中提出:“具有观念,而具有含糊和混乱的观念,那就等于什么观念也没有”[7]142,但洛克观念概念的意义要更加丰富,有学者认为其“观念”概念“非常类似笛卡尔的‘思想’”[2]114。可以相信,洛克相信并不是所有的观念都是有定和确定的观念,一个这样的观念必须是“看得清楚”并“知得明白”的,他说:“用那些名词(有定的或确定的),我的意思是指心灵中有某个对象,因此是确定的,亦即不过是在那里被看到和被感知到那样。如果在任何时候,它不过是心中的对象,因此是确定的,我认为它们叫作有定的或确定的观念是适当的,它不变地附着于确定的名称或音节清晰的声音,是人心相同对象的固定的标志,或有定的观点”[2]12。可见,有两种观念都是心灵的直面对象,准观念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无定的和不确定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注意才是知觉所需要的,因为注意存在的前提是“有待注意者”的存在。但准观念是很难描述的,因为它的不确定性躲避一种理解的审视,而这审视的前提恰恰是确定性。同时,必须提到一点,准观念和观念不是绝对的,“有定和确定”关涉到一种比较后得到的关系,所以洛克说“它们叫作有定的或确定的观念是适当的”。这种观念的有定化或确定化也就是知觉的有定化或确定化。因此,知觉的主动接受性就是内心的注意能力,它的作用不是使观念可能,而是使观念确定化地被给予。知觉主动接受性的这种定义则必然把知觉与反省直接联系起来,最明显的线索就是洛克对反省的描述也借助了“注意”概念。
对于反省,洛克有这样的描述:“反省一词,我理解为心灵对自身的运作及其方式所加的注意,由于这种注意理智有了这些运作的观念。”[2]77很显然,反省意指一种注意,需要这种注意,乃是因为人心在发生活动时并不总是能注意到自己的心灵活动,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注意总是需要“有待注意者”才能成为必要的概念,在这里,人心活动本身就是“有待注意者”。根据上文的同一种逻辑,我们得到结论:人心活动必然要先作为一种“准观念”被给予。伴随人心活动而起的无处不在的对心灵活动的知觉就是洛克对此种“准观念”的提示,他说:“任何人不可能在知觉时而不觉察到他确在知觉。当我们看、听、嗅、尝、感受、深思或意愿任何东西时,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样做”[2]310。洛克在这里使用的“觉察”当然是指一种知觉,这种觉察有待于被主题化,它是一种还没有把它自己的确定观念给予我们,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伴随着我们,有待我们的注意来完成其明确所予的东西。
一个画家沉迷于画作的欣赏,一个数学家沉浸于计算的时候,对心灵活动本身的知觉并非完全退场,总有一种机会,这画家和数学家会回过神来在回忆和观察、命名和思索等的帮助下开始审视在自己身上和心中刚刚发生了什么,是如何发生的,那被洛克叫作“觉察”的始终伴随着心灵活动的知觉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和一套符号系统一起达到洛克所定义的那种确定化(观念发展与符号行为之间的关系在本文中暂且不作讨论),从而这个画家和数学家就形成对自己心灵活动及其活动方式的一套认识,这就成为一种相对完成了的反省(洛克自己的认识论也是一种相对完成了的反省)。所以,作为反省实现之条件的“准观念”就是人心对自己的活动所有的那种始终存在的“知觉”,而反省作为一种注意,使它有定化和确定化,我们因此才能说出“我在看”“我在思考”之类的话,反省是此种知觉确定化的一个条件。
因为知觉主动接受性的实现意味着知觉的确定化,而反省也是知觉的一种确定化,所以,反省是一种特殊的,或者说是专属于人的“知觉主动性”。通过这两种连贯的“知觉的主动性”,洛克的知觉似乎应被理解为一种意向活动,用存在主义的话来说,乃是“我们所是的实存者借以使它自己趋向现成者的运动”[8]。
值得一提的是,洛克相信如果一个观念被称为有定的或确定的,那么“它不变地附着于确定的名称或音节清晰的声音,是人心相同对象的固定的标志,或有定的观点”[9]112,这意味着有定的或确定的观念的被给予是一个依赖语言行为的过程。
结论
分析至此,我们发现,洛克没有像莱布尼茨那样,仅仅视知觉为“充满我们的观念的灵魂的第一种功能”[2]12,而是赋予了它更多的内涵。
首先,洛克知觉的一般所指——心灵面对观念,划定了前知觉与知觉的界限,但由于因果解释的失败,未能对它们进行有效的联结;其次,知觉的主动接受性的展开是观念确然化地被给予的过程;最后,那种始终在场的对心灵活动的知觉使得反省得以展开,而反省的展开则是那种始终在场之知觉的确然化。于是,知觉就是这样一个连续的存在过程,它“如同一张其网结变得越来越清晰的网”[10]33。
可见,洛克的知觉概念在其观念起源论乃至整个观念认识论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它贯穿于洛克的“感觉论”和“反省论”之中,既维系着观念起源论内在逻辑的连贯性,又成为暴露观念起源论内在问题的一个创口。其中知觉语境与前知觉语境的断裂为贝克莱和休谟彻底的内在主义哲学提供了机会,知觉的主动性则为康德的先验哲学埋下了伏笔。
注释:
①旧译《人类理解论》,由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