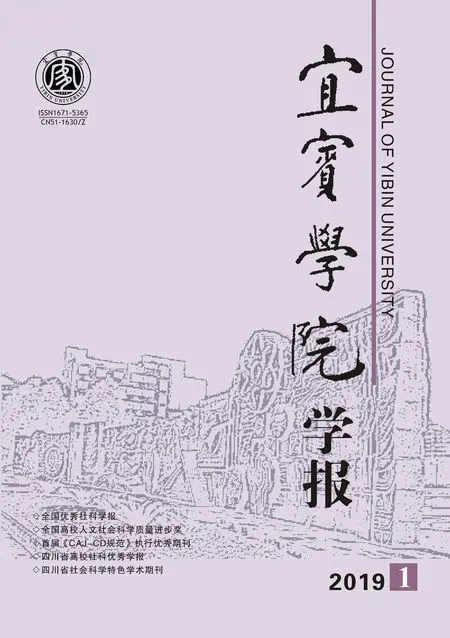公司越权对外担保的效力判断
——以实证分析为视角
林文奇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上海200050)
公司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主体,在市场经济关系中,公司难免存在筹集资金等需求,因此有为他人提供担保或者请求他人为其提供担保的可能,加上市场经济的竞争日趋激烈,公司一旦发生资金链断裂,可能会陷入停工停产甚至破产清算的危境,因此,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相比1993年《公司法》,解禁了过去公司越权对外担保的限制,并删除了原《公司法》第214条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越权对外担保直接课以“责令取消担保”之法律效果的规定,这体现在现行《公司法》第16条。但如果法定代表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公司章程之规定,未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许可,擅自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担保,第16条并没有规定违反之法律后果,第148条也仅仅规定了公司的归入权,那么该越权担保合同效力如何?①该问题在学术界与实务界争论已久,但尚未达成共识,主要原因是存在两种不同的分析进路,不同分析进路往往产生不一致的结论。一种是通过认定《公司法》第16条并不是《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或《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所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而是“管理性规定”或“非效力性规定”,并以此为依据认定越权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②;另一种是结合《公司法》第16条与《合同法》第49、50条等条款之间的关系,探究越权担保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表、表见代理,进而论证该担保合同的效力③。
一、 公司越权对外担保的实证数据分析
本文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裁判文书的收集并进行统计分析,力求揭示越权对外担保合同之效力认定的司法实践情况,并为笔者提供的对策性建议奠定基础。
通过威科先行-法律信息数据库,以“《公司法》第十六条”为搜索关键词、以“最高人民法院”限定法院级别,最后检索时间为2018年6月16日,共检索100则案例,排除最高院审查案件事实认定实为给公司本身提供担保、因起诉主体不适格被驳回起诉、实质上以其他根据作为最终裁判依据等事由,所以只有59则案例被列入本案样本数据,加上1则2011年第2期的公报案例,最终有效样本数据为60则案例。因为引用该条文判决有4878则,笔者能力有限,无法全部研读,鉴于最高院作为我国裁判文书效力的最后一道防线,且最高院裁判文书中折射的裁判思路,下级法院会适度参考,因此将最高院裁判文书作为本文的样本数据。
(一)整体数据概况。
通过统计分析发现,63.3%的样本案例集中于近三年,因此,该样本数据能够反映最高院的最新裁判思路。在援引第16条作为裁判依据的60则样本案例中,认定公司越权对外担保无效的合同比例较低,仅为16.6%,说明实务界倾向于裁定违背第16条规定的越权担保有效。
(二)裁判思路与分析进路。
通过阅读案例裁判要旨可知,最高院的裁判思路主要体现为两种分析进路,学术界也主要是采用这两种分析进路来论证越权对外担保的效力,第一种分析进路为判断第16条是“管理性规定”或“非效力性规定”以此认定担保合同效力;第二种分析进路是第16条结合《合同法》第49、50条判定,这两种分析进路占样本案例比为76.6%。
(三)越权对外担保存在不同情形。
阅读案例时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多种不一致的情形导致越权对外担保合同无效,即存在特殊越权对外担保的情形,如股东作为债权人接受公司担保、被担保人是专业担保公司等。对于特殊越权对外担保情形的效力判断规则应当区别于一般情形的判断,文末会提出相应的判断规则。
由上可知,论证越权对外担保的效力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分析进路,分析进路的不同往往会导致越权对外担保合同效力判断的不同结果。下文将具体论证该两种分析进路,并采取《公司法》第16条结合《合同法》第49、50条的分析进路,提出“在一般越权对外担保情形下,债权人接受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时负有形式审查义务”的效力判断思路。
二、 一般越权对外担保情形的效力判断
前已述及,探究公司越权对外担保的效力不管在学术界还是实务中,均存在两种分析进路。一种是通过《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来判断《公司法》第16条是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规定;另一种则是通过民法教义学分析,在越权代表(代理)情形下,结合《公司法》第16条与《合同法》第49、50条,以此判断越权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
(一)分析进路的选择
对于越权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本文认为,第一种分析进路有悖于规范意旨,该解决方案并无实益。理由如下:一方面,《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中的“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旨在保护的是公共利益[1]481,但此处危害的是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法》第16条正是基于此规定了公司对外担保的程序,以引导担保人充分考虑风险、作出科学决策[2]36-37,不难发现二者的保护对象并不一致。另一方面,从比较法看,《德国民法典》与我国《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有着类似的规定,体现于《德国民法典》第134条“法律不另有规定的,违反法律禁止的法律行为无效”。德国主流学说认为“第134条的真正意义不在于针对民法领域的规定,而是规定了民法以外的制裁措施(如刑法上的可罚性或行政法上的许可的可撤回性)的法律禁令,即适用于违反了自身规定、但未对民法上行为之效力作出规定,因此需要第134条才使得这些法律禁令成为民法上的完善法律。”[3]483由此可见,本文探讨对象属于私法领域,不应当适用第一种分析进路。第二种分析进路从私法视角以《公司法》第16条之规定究竟仅是内部控制程序抑或具有公开宣示性为出发点,结合《合同法》第49、50条之规定,能够准确认定越权对外担保合同之效力。
在德国法上,代理人与代表人都被称为Vertreter,代表人在学说上被视为机关代理人,二者除细微差别外,关于代理的规则通常适用于代表,故有关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也适用于表见代表。[4]我国主流学说认为,表见代理除构成无权代理外,还应当具备如下要件:“相对人是善意的、有代理权外观的表象、该表象是被代理人风险范围内导致的”[5][6]520-530。
有关“代理(表)权外观的表象与该表象是被代理(表)人风险范围内导致的”这两个要件,在本文讨论“越权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的情境下,是很容易满足的,因为法定代表人或者经理的身份(如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等)的本身即可说明“代表(理)权外观的表象与该表象是被代理(表)人风险范围内导致的”。司法实践中引发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认定担保权人是善意的,即善意的认定标准。换言之,关键在于认定《公司法》第16条仅是内部控制程序抑或具有公开宣示性,从而确定债权人的审查义务,从而根据债权人是否履行了审查义务来判断其善意与否。
有观点认为《公司法》第16条的立法意旨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防止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债权人利益,其实质在于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来约束交易相对人,因为必须谙熟公司法相关规范才能避免因担保公司内部管理不善导致的风险,未免过于严苛④,相对人无义务审查是否已经召开股东会,是否提交股东会决议以及股东会决议上签名是否为公司股东⑤;况且组织法上的规定无法推导出相应责任,只是影响公司关于对外担保中的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本身效力,无法推导出课以被担保人的审查义务[7]。
本文不予认可,相反,《公司法》第16条已经对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员的职权构成法定限制,赋予了被担保人一定的审查义务,以防止法定代表人或高级管理人员借助权力作出违背公司授权范围外的事情[8]108-109。其一,法律具有宣示性,推定任何人均应当知悉若要接受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应当按照公司章程规定或经过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其二,过去立法是禁止公司对外担保的,因为这对于公司而言具有重大利益,动辄可能承担担保责任,进而损害公司、公司股东、债权人的利益,需要防止法定代表人或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擅自对外提供担保,故现在尽管允许对外担保,但第16条应当是具有涉他效力的,而不仅仅在于规范公司内部本身。其三,公司法有很多内部监督与管理的规定,但有些规定是具有涉他性的,如《公司法》第37条第九项规定“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由股东会行使职权”,该规定看起来是涉及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但其意义并不仅在于此,若法定代表人仅仅依据董事会决议或者无决议与其他公司签订合并合同,不能说合并合同效力没有瑕疵,其效力应当结合《合同法》第50条判定,[4]《公司法》第16条也是此类具有涉他性的规定。当然,涉他性并不是要课以担保权人实质审查义务,而是形式审查义务,否则对担保权人过于严苛,影响交易效率。
综上,越权对外担保合同的效力应当综合《公司法》第16条与《合同法》第49、50条的规定进行判断,由于第16条具有涉他性,故应当课以担保权人形式审查义务,以认定其是否善意从而满足表见代表(理)要件,使得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
(二)担保权人审查义务:合理的形式审查
其一,审查担保公司方签订人身份:公司营业执照或授权委托书。若是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订对外担保合同,善意第三人得信赖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权限范围内可代表公司签订合同,被担保人应当要求其提供公司营业执照或采用其他途径核实其身份。若非法定代表人,应要求其提供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授予其代理公司签订担保合同”事项,并盖公章,同时尽到其它一般注意义务。因为法定代表人应当比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审查信赖程度高。[4]
其二,审查公司章程:债务人是否为被担保人股东与公司章程有无对外担保程序要求。隐名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没有体现在公司章程上,实践中也很难知悉公司的隐名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之有无,接受担保的债权人仅需查询债务人是否为公司章程中记载的股东即可⑥。若为关联担保,须查询股东会决议是否通过;如果是非关联担保,需查看公司章程是否授予法定代表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对外担保权限,若未授予,须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通过。另外,需查看公司章程对于对外担保的程序性要件,如担保数额有无上限、出席人数下限、表决权通过比例下限、通知与会天数等。
其三,审查股东会决议或者董事会决议。审查股东会决议或者董事会决议是否满足公司章程或者《公司法》规定的有关出席人数下限、表决权通过比例下限、通知与会天数等规定;决议本身是否有明显瑕疵:比如为关联股东提供担保,未回避;或者股东的印章具有明显瑕疵,以防止伪造之可能:如印章与公司章程注明的名称不一致、无有限责任字样等。
其四,审查担保合同。担保合同应当盖有担保公司的公章。有判决书认为:“担保合同已经有了法定代表人之签名,能够代表公司为债务人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有无盖章均不影响担保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⑦笔者并不予以认可。因为前述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等资料,债权人仅需负形式审查义务,因此可能存在伪造之可能,可能公司股东对法定代表人权限有限制没有将印章提供给法定代表人,此时假如资料伪造但债权人已尽形式审查义务的情形下,如果不要求担保合同上应当有被担保人的盖章,则会违背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倘若公司印章也是伪造,且债权人履行了形式审查义务,则此时债权人应予保护,公司此时须为其任人不贤负责,即担保人不能以公章是伪造为由拒绝承担担保责任。
在债权人履行形式审查义务后,即使发生越权对外合同,债权人得以依据《合同法》第49、50条结合《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6条规定,主张担保合同之法律效果归属于担保人,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
综上,债权人接受公司提供对外担保时,须按照上述要求履行合理的形式审查义务,依次审查担保公司方签订人身份、公司章程、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担保合同,方可在发生越权行为时,主张担保合同有效。最高院的裁判文书折射出了与一般越权对外担保不同的特殊情形,其适用了不同于一般情形的效力判断规则。
三、 特殊越权对外担保情形的效力判断
由上可知,在一般越权对外担保情形下,债权人须履行合理的形式审查义务,依次审查担保公司方签订人身份、公司章程、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担保合同,方可在发生越权行为时,满足有关善意之认定从而主张担保合同有效。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特殊越权对外担保的情形,其形式审查义务与善意的认定应区别于一般越权对外担保情形的效力判断。
(一)担保对象:为股东之间转让担保人股权或股份公司的董监高提供担保
公司资本维持原则是公司正常运营的重要保证方式,也是保护债权人、股东的必然要求,其中第35条与第115条即是公司法通过禁止相关行为来维护公司、债权人、股东的合法权益。
我国《公司法》第35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股东既然不得抽逃出资,当然,公司股东之间达成股权转让协议时,更不得约定由公司为该股权转让债务提供担保,否则在一方股东无法向另一方支付股权价款时,由公司履行担保责任,这无异于允许股东间变相规避抽逃出资条款。在“郭丽华、山西邦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如果公司为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提供担保,就会出现受让股权的股东不能支付股权转让款时,由公司先向转让股权的股东支付转让款,导致公司利益及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受损,形成股东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变相抽回出资的情形,有违《公司法》第35条关于不得抽逃出资的规定。⑧
此外,《公司法》还通过第115条规定了“公司不得直接或者通过子公司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借款”。“该规定是对股份公司向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借款的禁止性规定,这主要是因为股份公司股权较为分散,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难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必要监督,防止他们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通过公司或者子公司向自己提供借款转移公司资产、掏空公司等现象的发生。[2]166-167笔者认为,债权人不得接受股份公司为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金钱债务提供担保,因为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法履行债务的情形下,担保人需要履行担保责任,这无异于公司变相给董事、监事、高管提供借款,规避《公司法》第115条之适用,与“公司为股东之间移转其股权提供担保”而规避《公司法》第35条规定之适用如出一辙。
因此,公司为股东之间转让其股权提供担保是变相规避禁止股东抽逃出资规定的担保行为,其效力应当为无效。债权人接受担保时,先看担保人是否为股份有限公司,若担保人为股份有限公司,则债权人不得接受担保人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供的担保,否则,担保人拒绝追认时,该担保行为无效。若担保人为有限责任公司,则按照上述流程进行形式审查。
(二)担保公司:上市公司、以担保为业的担保公司
1.上市公司。证监会、银监会于2005年12月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在上市公司实施对外担保行为时,对担保人、被担保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均规定了严格的要求,这体现在:一是限制了公司章程对外担保行为意思自治的规定,对外担保必须经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不得授权法定代表人或其他人行使;二是公司章程必须对“对外担保事项”明确规定,不得沉默;三是被担保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必须履行审核义务,包括上市公司履行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批的程序、担保能力等事项,但该规定并未表明违反上述规定引发担保合同无效的私法效果,因此,在发生越权担保时,作为被担保人的审查义务按照本规定履行,私法效果则按照上述流程进行判定。本文不予认可最高院在“韩雪松与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的裁判观点,本案担保人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但最高院认为“《公司法》第16条属于对公司内部的程序性规定,即使在签订《借款协议书》前未经青海贤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公司授权,但韩雪松对此并不知情,《借款协议书》对青海贤成公司有约束力,青海贤成公司关于《借款协议书》中的担保条款对其不产生拘束力,其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⑨
2.以担保为业的担保公司。以担保为业的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时,债权人无须审查其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等资料,仅须审查担保合同本身即可。这是因为:其一,该担保公司以承担“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之风险而提供担保活动作为营利手段,不存在上述所说的“对外担保行为会给公司利益带来重大影响”;其二,提供担保行为是其营业活动,会十分频繁,要求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审议才可通过,会给此类公司带来极大不便,影响交易效率。反之,如果是以担保为业的公司接受担保人提供的对外担保,则需要履行一般情形下之合理审查义务,因其作为专门从事担保业务的专业机构,应当更为谙熟我国有关担保类的法律法规,从而知悉《公司法》第16条有关公司对外担保之规定。在“河北敬业担保有限公司与圣地隆房地产有限公司、兆亿贸易有限公司等追偿权纠纷”一案中,最高院认为“谢利明在代表圣帝隆房地产公司向敬业担保公司出具《反担保保证书》时未提供《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圣帝隆房地产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等相关文件,而敬业担保公司作为专门从事担保业务的专业机构,本应对谢利明是否越权尽到更为谨慎的审查义务,但其并未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因此不构成善意”。⑩因此,在涉及以担保为业的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时,须区别其身份究为债权人抑或担保人,以确定债权人不同的形式审查义务。
(三)担保方式:不动产抵押、票据保证与质押
在公司越权对外担保中,发生争议的案件集中体现于担保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其他担保方式也会有所涉及。
1.不动产抵押。在2015年公报案例“招商银行与振邦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振邦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最高院认为“且案涉抵押担保在经过行政机关审查后已办理登记,至此认为招行东港支行在接受担保人担保行为过程中的审查义务已经完成”。本文不予认可其裁判观点。在公司为债务人提供不动产抵押时,不动产抵押行政登记机关虽对提供的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进行形式审查,但此处,最高院无异于将行政机关对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的形式审查作为债权人善意判断的根据,而不论债权人是否履行形式审查义务。在担保人举证法定代表人或高级管理人员越权对外担保情况下,债权人若未履行审查义务则不属于善意第三人,进而不能依据《合同法》第49、50条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最高院的最新判决,“因《十堰市辰泓木材有限公司决议》系办理案涉抵押权登记时即向十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并存档,建行襄阳高新支行作为担保合同相对人及抵押登记的共同申请人,是否对《十堰市辰泓木材有限公司决议》内容明知,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辰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舒大成超越权限签订合同等事实,对正确认定《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及最高额抵押权设立的效力有直接影响,需要进一步审理查明。”简而言之,债权人不得以“取得不动产抵押权的登记”弥补越权担保合同善意的判断。
2.票据保证与质押。在我国,《票据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及中国人民银行《票据管理实施办法》和《支付结算办法》等有关票据的规定中,均没有规定票据表见代理规则,也没有关于认可法人对无权代理或越权代理的追认规则,如《票据法》第5条第2款规定“没有代理权而以代理人名义在票据上签章的,应当由签章人承担票据责任;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的,应当就其超越权限的部分承担票据责任”。但基于《公司法》《票据法》与《合同法》的特别私法与一般私法的关系,在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法》第16条与公司章程规定越权对外提供票据保证或票据质押时,若债权人善意须类推适用《合同法》第49、50条认定担保合同有效。[7]这是贯彻表见代表(理)保护善意相对人与交易安全的应有之义,因为这对于票据取得人而言,其根本不可能更无法律上之义务审查直接前手之前的票据代理人的代理权。基于票据行为具有要式性、文义性、无因性的基本特征,接受票据保证、票据质押的债权人除须履行一般的合理审查义务外,还应当注意到票据行为的特殊性,仍须审查票据上载明了“被代理人、代理人、代理意图”,如是,则可以构成票据代理外观。
综上,发生特殊越权对外担保行为时,形式审查义务与善意的认定区别于一般越权对外担保情形的效力判断:其一,为股东之间转让担保权人的股权提供担保或股份公司为其董监高提供担保时,债权人不得主张为善意,若担保人拒绝追认,该合同无效;其二,接受上市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必须审查是否经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通过,接受以担保为业的担保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无须审查公司章程、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其三,债权人不得以“取得不动产抵押权的登记”弥补越权担保合同的有关善意之判断,越权对外提供票据保证与质押之效力判断,债权人除须履行一般的合理审查义务外,须注意到票据行为的特殊性而审查票据上是否载明“被代理人、代理人、代理意图”。
结语
公司越权对外担保的效力判断,应当采用《公司法》第16条结合《合同法》第49、50条判断的分析进路。由于第16条具有涉他性,因此担保人须履行合理的形式审查义务,依次审查担保公司方签订人身份、公司章程、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担保合同,才能在发生越权对外担保时主张其主观上为善意,满足表见代表(理)之构成要件,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另外,发生特殊越权对外担保行为时,形式审查义务与善意的认定区别于一般越权对外担保情形的效力判断。
注释:
①本文探讨越权担保合同效力指的是担保人与被担保人之间的外部效力,内部效力根据公司章程或者法律规定判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四》)第6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或者撤销的,公司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第三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担保合同的对内效力与对外效力应当分别判断。若未作明确表示,本文探讨对象即为外部效力。
②参见李金泽《〈公司法〉有关公司对外担保新规定的质疑》载于《现代法学》2007年第1期;华德波《论〈公司法〉第16条的理解与适用——以公司担保债权人的审查义务为中心》载于《法律适用》2011年第3期;(2017)最高法民申370号;(2016)最高法民再24号。
③参见杨代雄《公司为他人担保的效力》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1期;钱玉林《公司法第16条的规范意义》载于《法学研究》2011年第61期;(2017)最高法民再209号。
④参见(2012)民提字第156号。
⑤参见(2016)最高法民申字1006号。
⑥本文将“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称为“关联担保”,此外为其他人担保为“非关联担保”。
⑦参见(2017)最高法民申2340号。
⑧参见(2017)最高法民申3671号。
⑨参见(2015)民申字第2539号。
⑩参见(2016)最高法民申2633号。
——基于《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13条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