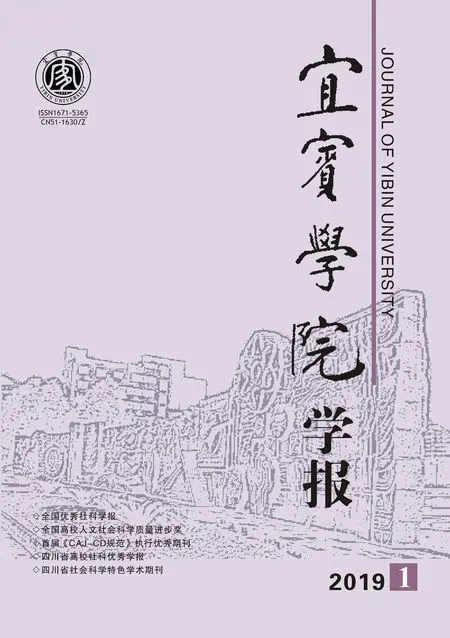本土方法论的理论渊源与转向
——基于加芬克尔本土方法论的理论检视
张建晓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起源于现象学的本土方法论为社会学的研究打开了日常生活的大门,将社会学从帕森斯及其追随者建构起来的“秩序王国”拉回到了日常生活世界之中,为深具宏观秩序的传统社会学带来了现代性日常生活的冲击,使得人们意识到另一种认识社会的方式。那么,何为本土方法论?加芬克尔在《常人方法学研究》一书中试图作出描述性的概括,他认为本土方法论的研究就是为了达致“社会成员用于产生和操纵有组织的日常事务的各种环境的种种活动,与他们用于使用这些环境变得‘可以叙述’的种种程序是一致的”[1]这样一种目的。诚如加芬克尔所言,本土社会学一改传统社会学的秩序信仰,试图以经验性的研究方式介入社会学的研究之中,将研究的注意力放到日常生活的各种最平凡的活动上,并将此类实际现象的研究纳入到规定性的研究范畴之中。[2]346对本土方法论的考察是整体性的考察,而不是“人物—理论”的切片化考察。本土社会学的生发及其过程是循着一条核心理路,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不断求索、增益的。笔者尝试在检视加芬克尔的本土社会学发展路径的基础上,抽析出本土方法论的发展的逻辑理路,并对本土方法论的现实困境作出一定回应。
一、 本土方法论的时空状况
亚历山大(Jeffery C. Alexader)认为,“理论是在特定时空对个别事物的抽象”[3]1。理论所抽象的对象是来源于特定时空域限中的个别事物,可见,一定时空是理论出产的前提性条件,也是检视理论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因素。笔者认为,时空是一个组合性的考察维度,尤其是对于理论的考察,不能仅仅注重时间或者空间的考察,而要综合时空因素立体检视理论的生发过程。
(一)社会文化:反主流文化运动
20世纪60年代,本土方法论兴起于美国,并兴盛于70年代,受到一批青年社会学家的追捧。这是由社会性的因素造就的。对于美国而言,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在现实生活中,高度发展的经济和科技带来了丰裕的物质生活,却形成了异化的人际关系,带来了“见物不见人”的认同危机。[4]在精神生活中,二战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创伤尚未愈合,新的战争(越南战争)再次上演,而在国内,种族歧视广布全社会,整个社会充斥着反叛的情绪。其中,作为新生代的大学生受此影响最大,以这些学生为首,整个美国社会兴起了反主流文化运动,以种种形式表达对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愤慨。在反主流文化运动的日渐兴盛的大趋势下,美国的人们开始反思自身与政府乃至与社会之间的关系。[5]在这种反思的催动下,人们对集体秩序的理论产生质疑,逐渐关注深刻影响日常生活的偶然性因素,开始朝着个体主义的发展方向迈进。
(二)理论对峙:反帕森斯运动
作为本土方法论的创始人加芬克尔,并不是一开始就走向了反叛帕森斯的路途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对峙则聚焦于加芬克尔的中后期思想之中。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理论界的乐观主义即将消散殆尽,传统社会学理论家们所坚持的可以凭借理性解决世俗社会中社会问题受到现实战争、思想“动乱”等的冲击,悲观主义的情绪逐渐蔓延,并影响了一批美国青年学子。在反集体主义和对个体的关注影响下,美国一大批青年学生开始炮轰“秩序王国”的创建者——帕森斯。到了60年代中期,加芬克尔为这场反帕森斯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并提出了本土方法论,受到了一大批青年学生的热烈支持。当然,这些学生比加芬克尔本人更进一步,他们不满足于借助催动本土方法论走上反集体主义的道路的观点性呈现,甚至打出了支持本土方法论就是拒绝社会学的旗号,并为了提高本土方法论的合法性,认为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中的人作为不自由的存在被框定在秩序框架之内,这是对人的自由本性的戕害。
(三)多重身份:超越而不可逾越
加芬克尔的本土方法论是存在众多的理论渊源的,包括美国社会学家米德(Mead George Herbert)的角色理论和德国哲学家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的现象学,并大量吸收了舒茨(Alfred Schutz)的现象学社会学和英国日常语言哲学的思想观点。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加芬克尔曾师从帕森斯、舒茨,他从舒茨那里继承了现象学社会学的观点,继续了舒茨对行动者(个体)的关注,并尝试用一个真正综合的方法来解决个体主义陷入的困境,他希望在现象学中创建一个社会的、超越个体的依据,从而使之摆脱偶然性和不确定性。[3]187同时,加芬克尔面对帕森斯是复杂的,一方面是恩师,另一方面是理论反叛的对象,两个身份聚焦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处理起来也是复杂的。但是,有一个判断是可以作出的,即是只可超越不可逾越。
加芬克尔创立本土方法论的过程是实现对恩师的超越的过程,不论是反叛也好,还是背离也好,他没有绕过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这座理论大厦,而是进入到里面,并在里面“参观”,也曾认可、也曾赞同、也曾批判。这从帕森斯并没有直面加芬克尔的反叛就可以看出,在某种程度上,一位理论大家还是比较乐意看到学生对自己的合理超越。基于此,加芬克尔经历了早期、中期与晚期的一次根本性的思想转向,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完成了超越。
二、 本土方法论的基本传统
理论建构的源泉一方面在于理论工作者的“筹谋”,另一方面在于理论的继承。理论的继承是通过理论要素的自上而下的传递完成的。自上而下的理论传递不是依靠观察就可以获取的,主要是通过一定领域内理论传统的继承,也即是上一个理论家传递给下一个理论家的遗产。对于本土方法论而言,其最基本的预先假设是个体主义。个体主义的发展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加芬克尔的独创,而是有着理论生发的源头。当然,在这里,对个体主义不作整体性的考据,只限定于本土方法论之中。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到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再到加芬克尔的本土方法论,这便是本土方法论的基本传统。
(一)胡塞尔现象学传统
胡塞尔被公认为现象学的开创者,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性的怀疑是他的理论的主要特色。胡塞尔的怀疑精神在其矛盾性的理论主张中得到了最大体现。在《笛卡尔的沉思》一书中,胡塞尔提出“这个客观世界,这个为我们而存在的世界,这个一直为我而且还将继续为我而存在的世界,永远为我而存在的唯一世界——这个世界,连同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从我本人这里……获得它的全部意义和存在的状况。”[6]26在这里,胡塞尔将个体与客观世界联系起来,坚持外在的客观世界的“全部意义和存在的状况”来源于人,整个世界的有序性的维持的合法性依据来源于个体。从中可以看出,个体主义是胡塞尔的基本立场,同时,又将个体与客观世界的联系起来,将个体看作是客观世界的有序联系的基础。在这里构成了一组矛盾性的存在,即个体主义的基本立场与个体是集体社会的有序模式的基础相互矛盾。其中,胡塞尔所坚持的个体主义的立场正是本土方法论的预先假设,前者为后者提供了第一个理论传统。
(二)舒茨现象学社会学传统
舒茨对胡塞尔的现象学作出了修正,将个体主义的讨论聚焦于意识与文化之中,提出了现象学社会学。他提出,从个体意识出发,联系特定的文化环境,得出只有将个体意识活动放置到一定的文化秩序的背景中才能进行讨论。舒茨写道, “我们日常经验世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存在于主观之中的文化世界……来自先天遗传的和学习获得的东西,来自传统、习惯的各种沉淀,以及他本人以前对意义的构造,这些都能被记住和再度复活,由此而建立的他生活世界的经验贮备是一个封闭的有意义的情结。”[7]134-137在这里,舒茨明确指出了,个体行动者在行动之前就已经存在对自己的行动产生影响的“有意义的情结”,也即是集体文化情结。由此可知,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将意识作为一个对象进行了讨论,将之引入到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之中,拓展了胡塞尔现象学的个体主义的讨论空间,为本土方法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方法的讨论提供了基础。
(三)加芬克尔自成传统
加芬克尔的知识传统经历过两次转折或者说是一次根本性的立场转向,形成了以个体主义为根本立场的本土方法论的知识传统。在早期思想中,加芬克尔从帕森斯那里继承了规范的秩序,坚持了对集体秩序预先假设的信仰。尤其,《“信任”作为协调稳定行动的条件的概念和实验》一文,融合了帕森斯、胡塞尔、舒茨的理论,借助游戏来说明内化规则的重要性,将规范纳入到了个体意识的分析之中。[8]加芬克尔非常清楚,“只有用内化了的规则,调节活动才能发生;只有内化文化相关联,构造的期望才得以存在,意识活动才能进行。”[3]190到了60年代,加芬克尔开始了关注偶然性因素对个体行动的影响,试图作出一些突破,不过还未越过秩序的范畴,继续把个体性的技巧与集体规范文化相联系的尝试,并提出一些具体的方法,诸如解释、文件法、社会分裂方法等。到了后期,加芬克尔抛弃了文化意义的理论,完成了根本性的转向,即极端个体主义立场转向。
在《本土方法论研究》一书中,加芬克尔表示他的研究努力“对实际的活动、实际的环境以及实际的社会学思维进行探讨”,他“承认一个人所说话的意思,不只包括承认他所说话的方法,而且包括承认他是怎样说的。”[9]29加芬克尔的本土方法论认为个体的行动是个体自发的产物,个体意识中充斥着偶然性的因素,偶然性的行动不能预先规定在一定的秩序之中,这是对人的发展与理论发展的限制。它切断了个体行动和集体秩序之间的联系,认为经验和行动(尤其是个体意识的技巧等)是它关注的对象,而所谓的秩序和由以建构的文化意义不在它关注的范围之内。由此,加芬克尔建构了以极端个体主义为基本立场的本土方法论,并为其后继者们的研究提供了本体意义上的知识传统。
三、 本土方法论的理论转向
到目前为止,对本土方法论的探讨都被打上了加芬克尔的烙印,这正印证了一个理论只可被超越而不能被逾越的预判。加芬克尔作为本土方法论的创立者,其理论主张成为本土方法论的基本立场,不管后继者们如何阐发,都绕不过加芬克尔所作出的基本判断。那么,在这里,笔者同样要返回到加芬克尔的本土方法论。加芬克尔的本土方法论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存在明显的理论差异,以本土方法论为原本,便是相对于结构功能主义的转向,主要表现在预先假设、行动性质、基本论域等方面。
(一)预先假设的转向
本土方法论与结构功能主义共同争论的焦点之一就在于预先假设的选择上,即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或者个体意识与集体秩序之争。被亚历山大称之为“成功现代性的理论”的结构功能主义建构了一套严密的社会系统理论,将复杂的社会简化为可以理论直观的系统图式,主张通过规范的、集体主义的方式描述个性化的社会现象,形成高度抽象的理论范畴。不过,这正是本土方法论所抨击的对象,本土方法论坚持个体主义的根本立场,批判结构功能主义脱离现实性的社会经验,主张将目光转向日常生活的世界,关注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以明确的方式维护了个体意识的自由空间。籍此,本土方法论完成了对结构功能主义的个体性批判,实现了朝向个体主义的理论转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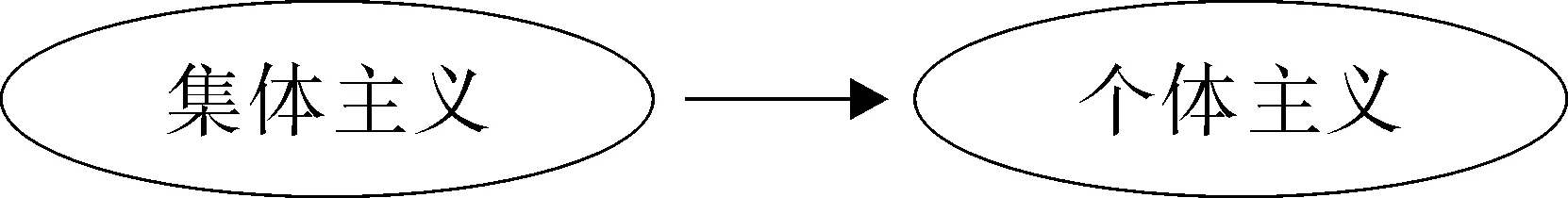
图1预先假设的转向
(二)行动性质的转向
理性和非理性是一组对立性的行动性质,而理性和非理性都存在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科学理性与日常生活态度便是之一。波洛玛(Margaret Polomar)区分了科学理性和日常生活态度,“作为稳定的行为特征的科学理性是由理论化的科学态度支配的。相反,由日常生活态度支配的行动的明显特点是缺少这种或是作为稳定的特点或是作为能得到认可的理想的理性。”[10]223在秉持科学理性的结构功能主义者看来,行动者对自己的行为、外在的客观世界有着自觉的认知,能够依据科学的原则进行秩序编织以建构社会秩序。在本土方法论者看来这是脱离了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现实,是不符合人的发展的,他们坚持日常生活态度,认为社会学的研究“不应强使人们日常行为符合科学理性的范式,而应如实反映人们习以为常的行为方式,描述我们熟悉的共同知识,并彰显我们 ‘日用而不知、习焉而不察’的那些沟通的方法,将一个至今还鲜有人提及的我们共同知识的更深沉的领域展示出来。”[2]348-349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日常生活中的技巧与方法便是本土方法论的理论目的。由此,本土方法论完成了从集体主义到个体主义乃至极端的个体主义的理论转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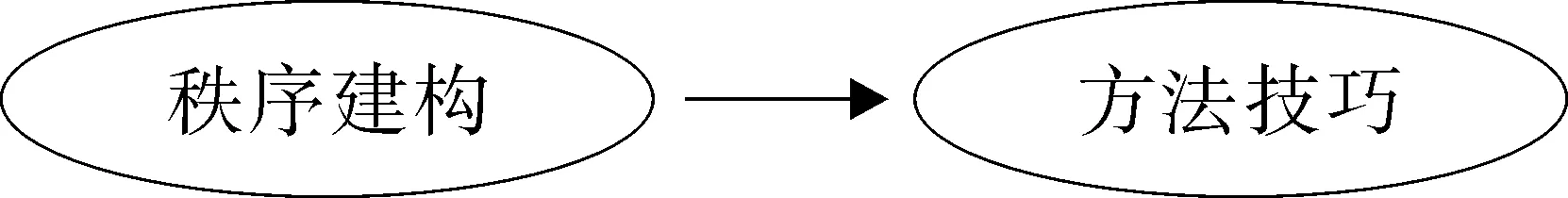
图2行动性质的转向
(三)基本论域的转向
社会秩序的建构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基本论域之一。对于结构功能主义者而言,社会秩序是外在性的、规范性的、现实性的存在,个体是通过对社会秩序所蕴生的文化价值于人有意义而内化为个体的内在价值,换言之,就是社会秩序对人与社会关系的维系有重要作用而内化为人的内在的秩序需求。结构功能主义者希望借助高度抽象的理论范畴,将现实社会筹措起来,编织进社会秩序网络之中。而本土方法论者悬置了秩序问题,转而关注如何产生“秩序感”的问题。由此,如何定义和规范不是本土方法论关注的中心问题,而他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行动者如何才会对定义、规范之类的东西取得一致的印象?通过什么方法人们可以看到、描述和证明定义和规范的存在?人们如何利用其相信定义、规律的存在这一点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现实感?”[2]347-348可见,形成秩序感的方法、技巧才是本土方法论者关注的中心问题。基于此,本土方法论者完成了基本论域的理论转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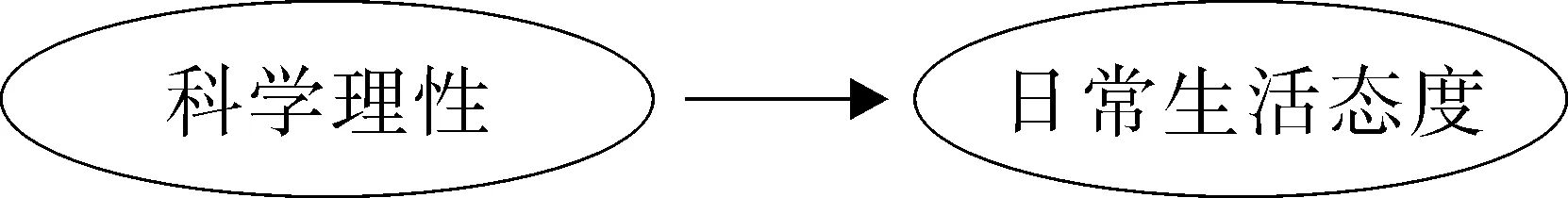
图3基本论域的转向
结语
六七十年代的绝大部分理论都是从反叛帕森斯理论起步的,本土方法论也不例外。但特别的是,本土方法论在个体主义的基础上,引进了大量的偶然性成分,企图通过个体意识的构造能力解释社会。个体倾向是加芬克尔学术生涯的底色,一开始他的个体主义还限定在承认集体规范具有独立力量的框架之内,但是经过60年代的论战之后,个体主义倾向得到了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认可之后,极端的个体主义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展,文化意义的理论、集体秩序的理论被彻底抛弃。
从时空背景、基本传统、理论转向三个维度考察了本土方法论之后,本土方法论也许可以解释当理论研究与日常生活相遭遇的时候的尴尬问题。作为学习和从事社会学专业的人,甚至是扩展到更广的理论研究中,或许都曾遇到过这样令人尴尬的情形:当针对某一群体、某种生活方式及生活历程的研究报告呈现在被研究者面前时,对方可能会用十分疑惑的神态打量这些文本。因为文本上呈现出来的“生活”与他们自己的现实生活或者与他们的自我认知是如此的不同,或是被描述得极为陌生,他们认不出这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甚至会以为研究者根本不懂得他们以及他们的生活。排除必要的研究技术问题等可能性原因,笔者认为,由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立场、视角、知识背景等差异,以理论研究的方式所展示出来的生活图景,在置身于其中的人看来,必然是“陌生的”。因而,被理解为已经不是对生活本来面目的描述的观点的提出实属正常。在本土方法论者看来,在此基础上所做的解释,尤其是“对变动不居的人的行动及社会秩序所做的解释也必然是苍白无力的”[11],或者说这种理论和方法给出的不是to be(是什么)而是ought to be(应该是什么),这在很多人那里是不能够忍受的。不过,虽然本土方法论对传统社会学的进行了种种颠覆,但其本身却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超越。根据本土方法论的思想精义,其与后现代的话语体系或者基本思想相契合,这让理论本身的悲观主义色彩愈加浓厚。而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相互交织的时代,一个充分复杂的客观社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复杂的现象、思想、文化不可避免地迷惑了一大批人,而本土方法论对方法技巧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在思想上停留于表面,在现实中使人变得更为迷惑。这对于本土方法论的理论发展而言,是一个挑战,更是一个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