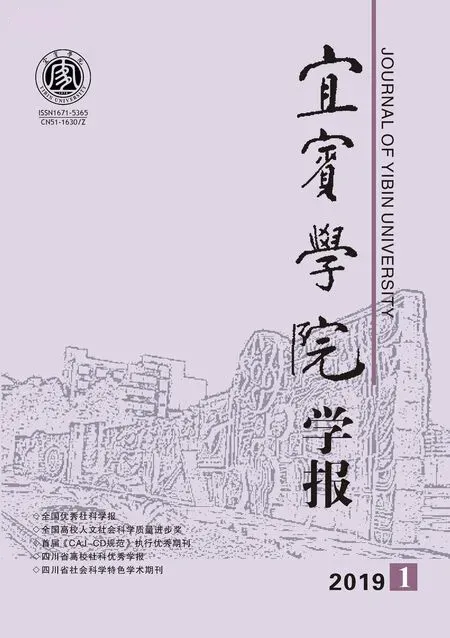论胡塞尔自然主义批判与其早期先验现象学之间的关系
黄 伟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当胡塞尔先验现象学在1911年首次公开问世时,其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对“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哲学”的批判,这种批判“像一个幽灵,钻进了成千上万个赞成者与反对者的心,它也像一次战斗的号角,一个世纪来长鸣不息”[1]59。在胡塞尔现象学的诸多概念中,“自然主义”这一术语首次明确出现在1911年《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这一“先验现象学的宣言书”之中。尽管在《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中,胡塞尔也使用过一次“自然主义”[2]323,但只是提及而已,并没有对其作出相关的说明或规定;更为重要的是,《逻辑研究》中这唯一提及到的“自然主义”一词却是在1913年第二版新增进去的内容,而此时,《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已经发表了两年。因此,胡塞尔最早、最明确地提出“自然主义”,这仍是《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的事情。
一、 “自然主义批判”的范围限定
那么,胡塞尔的“自然主义批判”思想也是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最早出现的吗?要解答这一问题,不仅需要从术语上、更需要从内涵和规定性上来理解胡塞尔的“自然主义”和“自然主义批判”,进而限定本文所要讨论的对象。“自然主义”总是与“自然态度”或“自然的态度”相关,或者说,它就是“自然态度”。而胡塞尔所说的“自然态度”主要有两种形式:“素朴的自然态度”和“自然主义态度”,而“自然主义”就是指“自然主义态度”,它是“根植于素朴的自然态度之中的”,同时也是“素朴的自然态度”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3]204,210。但本文所要讨论的“自然主义批判”并非只针对第二种“自然主义态度”即“自然主义”,同时也包括胡塞尔对“素朴的自然态度”的批判,它既涉及1911年《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的“自然主义”,同时也涉及1907年《现象学的观念》中的“自然态度”。也即是说,本文所要讨论的“自然主义”,不仅仅指“自然主义”,也泛指“自然态度”。那么,本文的这一限定有何根据呢?为什么要用较为狭义、严格的“自然主义”来泛指所有的“自然态度”呢?
对“素朴的自然态度”和“自然主义态度”的区分及其悬置,胡塞尔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以《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经验与判断》《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为标志。但在1920年之前,特别是在1907年《现象学的观念》、1911年《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和1913年《纯粹现象学通论》中,胡塞尔对这两种自然态度及其悬置基本上都是“一并处理”的,并未明确对之进行区分[3]211-212。而本文所探讨的对象——胡塞尔的自然主义批判与先验现象学之间的关系,其主要涉及的时间段是1900年至1913年,所要讨论的著作是《逻辑研究》《现象学的观念》《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和《纯粹现象学通论》,这正好是处于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早期,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胡塞尔此时乃是“一并处理”这两种自然态度及其悬置的。所以,本文所讨论的“自然主义”和“自然主义批判”就是在这种“一并处理”、未明确区分的意义上使用的,它既指对自然主义的批判,同时也指对自然态度或“素朴的自然态度”的批判。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所讨论的“自然主义”之基本内涵和规定性便是:它未经认识论的彻底反思,就直接设定了“超越的”存在,直接确信世界的自在存在,既直接将物理物的自然视为独立的客观自在,又直接将精神物(意识或观念)自然化,从而使其依赖于物理世界或属物理世界的躯体,故它仍立足于世界信仰的基地上。因此,本文所讨论的“自然主义”既指自然主义态度和素朴的自然态度,也可指胡塞尔常说的“自然态度”“自然的思维态度”“自然思维”“自然观点”“自然认识”等。故我们便能回答这一问题了:即胡塞尔“自然主义批判”思想也是在1911年《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最早出现的吗?事实并非如此,早在1907年《现象学的观念》中,胡塞尔就已经开始其“自然主义批判”了。
二、 “自然主义批判”的出现与先验现象学的诞生
在《现象学的观念》中,胡塞尔明确区分了“自然的思维态度”和“哲学的思维态度”,并将前者视为“哲学态度”的对立面。他具体分析了这一“自然态度”的基本内涵和思维过程,并指出,它就是所有自然科学的根本前提和思维基础,同时也是日常意识、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思维前提和基础。但这种“自然态度”有其根本的缺陷:“自然的精神态度尚不关心认识批判。在自然的精神态度中,我们直观地和思维地朝向实事,这些实事被给予我们,并且是自明地被给予”[4]19。而对自然态度及其缺陷的克服又必须依靠彻底的认识论批判和认识论的还原——即现象学的还原或现象学的悬置①,这种认识论批判和认识论还原便是先验现象学的任务。故胡塞尔此时就有了“自然主义批判”思想。与此同时,他在《现象学的观念》“5次讲演”中,“既清楚地阐述了现象学还原的思想,也清楚地阐述了对象在意识中构造的基本问题”[4]“编者引论”9, 所以,他“已基本完成了向超越论现象学的突破,从而成为一名超越论观念主义者”②,其先验现象学思想也就诞生了。
胡塞尔在《现象学的观念》中的“自然主义批判”思想并非是外在的批判或否定,而是进入到“自然态度”的内在性中对其进行自身否定,并揭示其思维过程和思维原理的自身矛盾,同时也是在现象学的内在性中对这种“自然态度”进行否定,这就体现在现象学的还原方法上,即必须对这一“自然态度”进行排除或搁置,现象学才能达到“纯粹的现象”和“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4]45-47。尽管《现象学的观念》的这种批判是内在性的批判或否定,但它所批判的核心是:指出“自然态度”不能进行真正的认识论批判,不能回答并解决“认识如何可能”“认识的切合性”如何可能等根本问题。它只是指明了认识论批判中的一些根本原则,但并没有从“现象学哲学”的立场来对当时科学界所盛行的“科学主义”和“心理主义”进行具体、深入的自然主义批判。而随着胡塞尔先验现象学思想的不断发展,“现象学的哲学”成为“严格科学”的内在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他的“自然主义批判”也就更为具体。
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胡塞尔从现象学的哲学高度对自然科学、尤其对实验心理学中的自然主义展开具体批判。他首先指出:所有“自然主义者”的共同点就是,“他所看到的只是自然并且首先是物理的自然”“一切存在的东西,或者本身是物理的,隶属于物理自然的统一联系,或者虽是心理因素,但却只是依赖于物理因素而发生变化的东西,至多是一种派生的‘平行的伴随性事实’。”[5]8一切自然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将意识自然化”“将观念自然化”“将所有绝对的理想和规范自然化”、甚至“将理性自然化”[5]8-10。由于这一自然主义或自然化,实证主义、实验心理学都直接设定了“物理自然的实存”并以其作为前提,它们的这种“自然素朴性”使其根本无法摆脱怀疑主义的攻击,它们自身也无法正面回答“认识的切合性是如何可能”这一根本的认识论问题。故此,它们都不具有真正的彻底性、科学的严格性和无前提的绝对性,也就无法成为严格的科学或哲学。胡塞尔认为,对认识论根本问题的回答只有依靠对意识自身的本质研究——现象学的本质研究——才有可能。在随后将近30页[5]16-45的篇幅中,他相当具体地批判了实验心理学(或精确心理学、现代心理学)中的自然主义,讨论了实验心理学与现象学的关系,并得出结论:实验心理学不是哲学,也根本不是严格的科学,它是以自然主义为基础的经验心理学,故哲学或现象学根本不需要模仿实验心理学或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无需以其为自己的出发点;恰恰相反,只有以“意识现象学”[5]18为前提,只有以一门“对意识的本质构型以及它的内在相关项”进行纯直观研究的“真正彻底的和系统的现象学”为前提和基础[5]43,实验心理学才能摆脱自然主义的思维束缚,才能成为科学。
由此可知,与《现象学的观念》相比,胡塞尔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的“自然主义批判”就更加具体和详尽;与此同时,其先验现象学思想也在1911年得到了具体的发展和充实,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1910年10月到11月的课程中……讲题为‘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它初步包括了《观念1》和甚至《观念2》的大部分内容”③。而相比于《现象学的观念》和《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纯粹现象学通论》或《观念Ⅰ》中的先验现象学思想则更为成熟、系统和具体,与此同时,胡塞尔在《观念Ⅰ》中的“自然主义批判”也变得更为成熟、深入、积极和彻底。
《观念Ⅰ》“自然主义批判”的这种成熟性和深入性,主要体现在其第二编第一章“自然态度的设定及其排除”。从第25节“自然态度的世界:我和我的周围世界”至第30节“自然态度的总设定”,胡塞尔对自然态度进行了现象学式的分析和描述,这4节其实仍然停留在“自然主义”阶段。但他在此围绕“自然态度”的系统分析是相当独特的,完全不像《现象学的观念》和《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所呈现的那样,这里既没有对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批判,也没有对自然科学和实验心理学的批判,更没有重提“认识的切合性”问题和“严格科学”的要求,而是深入到“自然态度”中并仅以其为中心,富有“同情心”地来描述经验自我的周围世界,“从自然生活中的人的角度开始思考,‘以自然的态度’去想象、去判断、去感觉、去意愿”[6]89。这种自然态度中的周围世界不仅包括自然世界,也包括“观念世界”“价值世界、善的世界和实践的世界”[6]91;这种在自然态度中生活的人不仅包括“自我”,也包括“他人”,这就涉及主体间的共同世界。故与之前比,胡塞尔在此对“自然主义”的分析是更为深入了,它深入到了自然态度所涉及的整个生活世界。
而《观念Ⅰ》“自然主义批判”的这种积极性和彻底性,则主要体现在先验主体和先验还原的思想上。在《现象学的观念》和《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胡塞尔虽然表达了“现象学的还原”这一思想,但并没有明确提出更具彻底性的“先验还原方法”④;同时,在这两部著作中,他对自然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排除自然态度上,虽然这种“排除”也是在现象学的方法内对自然态度进行否定,但由于自然态度的根深蒂固和难以根治,若没有一种能彻底克服自然主义的“新习性”并长久地在此“新习性”中生活,排除或悬置式的否定处理多少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外在性,这种单纯的否定并不能从正面积极有效地、彻底地克服自然态度。⑤但在《观念Ⅰ》中,先验还原和先验主体性的要求得到了明确表达,“新习性”就有了培育的温床和基地,一旦这种“新习性”得到养成并加以坚持,那么自然态度就能够得到彻底克服,从而被“新习性”真正地扬弃掉[7]400。
综上所述,在胡塞尔先验现象学初步形成时期,即从《现象学的观念》《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到《观念Ⅰ》的进展中,我们发现:一方面,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思想在逐渐发展,并初步走向了成熟和系统化;另一方面,与之同时发生的则是,胡塞尔的“自然主义批判”思想也变得更为具体、深入、积极和彻底。这种相互伴随的现象反映出“自然主义批判”与先验现象学之间的某种独特关系:即伴随着先验现象学的诞生,“自然主义批判”开始出现;伴随着先验现象学的发展和系统化,“自然主义批判”也进入了具体化、深入化和彻底化。
三、 “自然主义批判”要以“认识论的批判”为前提
在《逻辑研究》第一版中,胡塞尔并没有明确提出“自然态度”或“自然主义”,更没有对其进行专门阐释、批判或现象学的悬置,而是仍停留在自然态度中。[8]158,220但他还是提到了一些与“自然态度”相关的术语,比如“自然性”“自然的思维步骤”“自然的意义”“自然的思维经济过程”或“自然的思维过程”“自然的思维机构”“自然理论”“自然思维”等,⑥但这些相关术语中的“自然”一词并非指自然态度,而是指不清晰、不具有明见性的意义,与本质直观的清晰明见性相对。与《逻辑研究》第一版相反,胡塞尔在1913年第二版中却明确地提到了“自然观点”“自然的观念”“普遍自然观念”和“自然主义”等术语,⑦只是没对它们进行任何具体的解释,且它们都是胡塞尔在1913年新增进去的内容。所以,《逻辑研究》中与“自然态度”相关的这些术语,并不能表明胡塞尔在1900年至1901年的《逻辑研究》就已提出了“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批判”。众所周知,在1913年《逻辑研究》修订版问世之时,胡塞尔早已达到了先验现象学阶段,并已出版《观念Ⅰ》,而且他正是根据《观念Ⅰ》的原则来修订《逻辑研究》,以求将《逻辑研究》提升到与《观念Ⅰ》的先验现象学原则相一致的水平。[2]第一部分“编者引论”(8-11)故在1900年至1901年《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并没有明确提出“自然主义”“自然态度”或“自然主义批判”,与此同时,他也没有达到先验现象学的立场,而是仍处于“本质现象学”或“描述现象学”阶段。
结合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在1900年至1901年《逻辑研究》中,胡塞尔还没有明确提出“自然主义批判”,他也没有达到先验现象学水平;在1907年《现象学的观念》中,他首次明确地提出“自然主义批判”,与此同时,他也坚定地完成了向先验现象学的突破;在1911年《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自然主义批判”进一步具体化,与此同时,先验现象学也得到具体的发展和充实;在1913年《观念Ⅰ》中,其“自然主义批判”进一步成熟并走向深入化、彻底化,与此同时,其先验现象学思想也走向成熟和系统化。那么,在自然主义批判与先验现象学之间,除了这种相互伴随的协同一致关系之外,笔者想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相互伴随的协同一致关系究竟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胡塞尔的“自然主义批判”究竟如何才是可能的?
胡塞尔有言:“正是通过完成这些任务,认识论才有能力进行认识批判,更明确地说,有能力对所有自然科学中的自然认识进行批判。”[9]39这里所说的“自然认识”就是指在自然主义态度中的认识,由此便启发以下观点:要想对自然态度或自然认识进行彻底的认识论批判,就必须首先“完成这些任务”,而“完成这些任务”又分为两种:“消极任务”和“积极任务”。所谓的“消极任务”,即必须首先谴责、反对并揭示自然主义的思维态度所必然陷入的那种谬误,并以此来反驳怀疑主义的理论及其攻击;“积极任务”则指对认识的意义、有效性及其与认识客体的相互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也即是对认识的可能性和切合性等问题进行本质研究,这一本质研究也就是胡塞尔所说的、真正的“认识论批判”或“理论理性批判”,亦即先验现象学关于意识的本质研究。但实际上,“消极任务”的真正完成乃是以“积极任务”的完成为前提条件,因为若没有对认识的可能性和切合性问题进行彻底的本质研究,对自然主义谬误的揭露、对怀疑主义的反驳就没有扎实的根据和真理般的积极基础。
由此可知,既然“自然的思维态度”乃是以“直接设定对象或事物的自在存在”为根本前提,所以,只有对“认识与对象的自在存在”之间的这一关系进行彻底的本质研究,才能彻底有根有据地进行“自然主义批判”;也即是说,只有对“事物的自在存在”进行彻底的认识论批判,才能够对自然态度进行理性批判。而胡塞尔所说的“认识论批判”乃是其先验现象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故对“自然主义”的批判进一步要以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为前提;反过来说,倘若胡塞尔没有达到先验现象学的领域,也没有明确把握住先验现象学的基本原则,他就不可能进行认识论批判,也不可能在哲学上明确意识到“自然主义”的本质和缺陷并对其进行批判。这就从反面启示我们: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之所以没有明确的自然主义批判,这与其还没有达到先验现象学领域、还没有把握先验现象学的基本原则是有内在联系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对“自然主义”及其局限性毫无意识,这是因为:一方面,《逻辑研究》中的“本质还原”方法已经包含有对“存在设定”的某种排除、不关心或“中立化”[10]83-86,95-102;另一方面,他在里面详尽分析并批判了心理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相对主义和人类主义,而这些理论都以“自然主义”为思维前提。因此,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对“自然主义”是有某种认识的,只是这种认识还是模糊不清并缺乏彻底性,既没有展示在意识的清楚明见性上,也没有提高到哲学反思的彻底性和自觉性。
四、 先验现象学要以“自然主义的彻底批判”为出发点
综上所述,胡塞尔的“自然主义批判”与其先验现象学之间确实有内在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当还没有达到先验现象学领域时(以《逻辑研究》为代表),胡塞尔并没有明确提出“自然主义批判”;而当他初步达到了先验现象学领域(以《现象学的观念》为代表),其“自然主义批判”就清楚明确地呈现出来;当先验现象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走向具体化时(以《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为代表),其“自然主义批判”也得到发展并变得更加具体;当先验现象学走向成熟化和系统化时(以《观念Ⅰ》为代表),其“自然主义批判”也更加成熟、深入、积极和彻底。另外,上文已指出:对自然主义的批判,必须以真正彻底的认识论批判为前提,即以先验现象学为前提。那么,这两者的关系难道就只是单向的因果关系、“奠基与被奠基”的关系吗?难道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不也以“自然主义批判”为前提吗?毕竟先验现象学在进行先验还原之前,必须要实行“先验悬置”以彻底排除自然态度,而这一“先验悬置”的操作当然是在进行自然主义批判,并且是彻底的自然主义批判。这就意味着先验现象学反过来也要以“自然主义批判”为前提,但上文也已论证:“自然主义批判”要以先验现象学为其前提。那么,这两者之间难道就是彼此互为前提、彼此相互奠基的关系吗?这仿佛就陷入了“一个逻辑怪圈:悬搁的前提是必须要有超越论自我的觉醒,而超越论自我之觉醒的前提是必须先进行悬搁”[11]43。
“胡塞尔所关心的是‘现象学剩余’或纯粹的意识现象……现象学的‘面对实事本身’,就是要回溯到这种现象。为了无成见地回溯到这种现象,首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必须把习以为常的自然态度、生活兴趣、存在信念悬搁起来。只有这样,先验的纯粹意识领域才能够向我们敞开,现象才能够如其所是地向我们呈现出来。”[8]52因此,就先验现象学而言,对自然态度的彻底批判或“先验悬搁”乃是极为关键的一个环节,甚至是“首要的一个步骤”,但这个“首要的步骤”是前提吗?倘若是前提,便与先验现象学的原则相矛盾,因为先验现象学本身就是一门绝对独立、无任何前提的“第一哲学”[6]456-459。伊丽莎白·施特洛克在谈到现象学的“加括号”与先验还原之间的关系时,明确区分了“前提”与“出发点”,认为“这种加括号本身并不能构成为现象学还原之主题的前提,它最初只构成先验现象学还原的一个出发点”[8]223。正是受这一认识的启发,笔者认为:对自然态度的批判或“加括号”不能成为先验现象学的前提,而只是其“出发点”。先验现象学的这一“出发点”只能从操作方法或步骤上来讲,甚至是为了照顾普通人的自然思维习惯以便引导人们从自然态度转变到现象学的先验态度而被迫采取的“让步”,因为自然的思维态度根深蒂固,要想对这种思维习惯完全不管不顾而直接跳入先验现象学的领域,这对习惯于自然思维的人来说是相当陌生和困难的,但若从对自然态度的阐释和批判出发,则势必会有助于人们对先验现象学的理解和接受。因此,先验现象学不是以“自然主义的彻底批判”为前提,而是以之为“出发点”。
五、 胡塞尔自然主义批判的哲学启示
“自然主义”具有朴素性、自然性和非明证性,它根本没有摆脱日常经验的意识水平,因而在胡塞尔哲学中,它基本上是先验现象学的对立面,属于非真理的一方。从胡塞尔对“自然主义”的批判历程来看:即便是非真理的“自然主义”或“自然态度”,若是想要对其有彻底的、批判性的反思,也必须要以更高的、作为真理的先验现象学为前提和基础;对真理的原则和内容认识得越具体、深入和系统,对非真理的自然主义之批判也会同时变得具体、深入和彻底;反之,若是对真理根本没有明确的把握,则对自然主义的批判根本不可能展开,而只能仍旧停留在非真理的“自然主义”。
故此,精神要想彻底清除非真理的自然主义,就必须首先掌握真理的内容和原则;精神若要对非真理有清楚明确的批判意识,就必须先要对真理有清楚明确的认知。反过来,若没有首先清除自然主义的成见,精神就不可能真正进入先验现象学的真理领域;若对自然主义的排除不够彻底,则精神对先验现象学的认识必定会受到阻碍。
上述真理与非真理、先验现象学与自然主义批判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在胡塞尔的哲学史论述中也能找到相关例证。根据胡塞尔的认识,即便是笛卡尔、康德这样的大哲学家,仍没有完全摆脱“自然主义”:笛卡尔的“我思”具有“经院哲学的成见”和人类学倾向,[12]112-113“康德的先验哲学本质上也总是以存在论为取向的”,“从而落入一种绚丽多彩的人类主义中”。[13]1195-1196那么,笛卡尔和康德为什么没能彻底清除自然主义的残余呢?笔者认为,他们没能完全摆脱自然主义,这与其没能真正进入“先验现象学”领域有着重大关联。胡塞尔也明确地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即在通向先验现象学的道路上,笛卡尔和康德都还没能找到真正坚实可靠的起点,距离真正的“严格科学”或“现象学的科学系统”都还相当遥远。关于笛卡尔,胡塞尔说道:“笛卡尔的失误就在于此,而他也因此而在所有发现中最伟大的发现面前止步了,他已经以某种方式做出了这个发现,但却没有把握住它的本真意义,即先验主体性的意义,因而他没有跨过通向真正先验哲学的入口大门”[12]113。而对康德,胡塞尔有言:“但康德却构想了一门先验的科学理论……或者毋宁说,构想了那种最初的尝试——尽管十分片面并且局限于问题之中”[13]1194,“他只是在第一个先验演绎中作了一些小小的启发。康德没有进一步使他普遍假定的直观着和思维着的认识的整个肉体—心理—物理的植根过程成为先验的主题,从而落入一种绚丽多彩的人类主义中……而且自始就把先天概念、先验的能力概念、先验知觉的概念置入一种非科学的昏暗之中……而且正是由之而产生了一种意义深远的不清晰性的氛围,它蔓延在整个体系上,还从没有人能够使之成为一种纯粹的清晰性。”[13]1195-1196其实,早在1907年《现象学的观念》中,胡塞尔就已经明确洞察到了这一点:即康德没能彻底地摆脱自然主义,这与其还没能真正进入先验现象学领域有着直接关系。他说:“康德缺乏现象学的和现象学还原的概念,他不能完全摆脱心理主义和人本主义。”[4]50而所有的心理主义或人本主义都假定了在世界基地上实存着的、有物理躯体的人这一“超度”或“超越”[4]42,但这种“非法的超越”便意味着:精神仍然没有摆脱“自然主义”或“自然态度”。
注释:
①《现象学的观念》中的“认识论还原”即是现象学的还原或现象学的悬置,可参见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修订版,第398、404页。
②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08页。保罗·利科也持有同样的认识,详见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法译本译者导言”第487-488页。
③详见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89页。《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本身就蕴含着先验现象学的基本原则,它就是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公开预告”或“宣言书”,参见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译者前言”部分第5页。
④关于“现象学还原”与“先验还原”这两个概念的差异,可参见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398、404页。
⑤胡塞尔对此有明确的意识和洞见,可详见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导论”第43-44页。
⑥详见胡塞尔《逻辑研究》全两卷,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自然性”见第一卷91页,“自然的思维步骤”见第一卷92页,“自然的意义”见第一卷128页、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118页,“自然的思维经济过程”或“自然的思维过程”见第一卷199页、209页,“自然的思维机构”见第一卷199页,“自然理论”见第一卷208-209页,“自然思维”见第一卷92页、208页。
⑦详见胡塞尔《逻辑研究》全两卷,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自然观点”见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11页、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119页,“自然的观念”和“普遍自然观念”见第二卷第一部分第620-621页,“自然主义”见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23页。
——专栏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