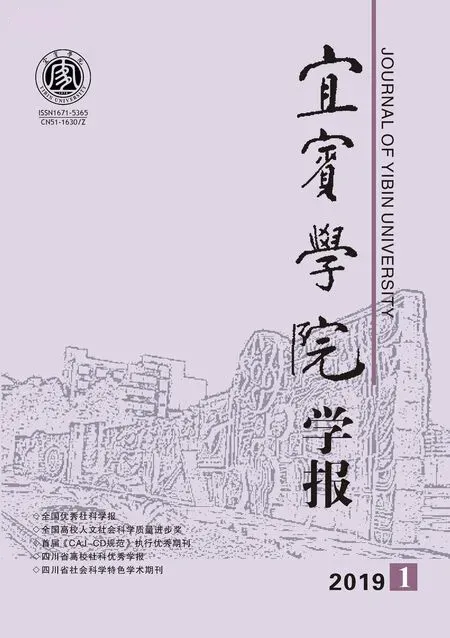从“此在”到“常人”的沉沦之路
——《存在与时间》中人的异化问题研究
王博医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上海201602)
“异化”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哲学命题,它自卢梭提出,起初用来意指一种背离人的自然天性的“社会化”状态。黑格尔为“异化”一词赋予了哲学意义,用其来表示“绝对精神”向外界的自我实现。而后,哲学家开始关注“人”的异化问题,马克思认为“工人”的劳动成果反过来对抗自身即为“异化”。自此,卢卡奇、弗洛姆、马尔库塞等后学开始从资本和技术层面寻找“人”背离其自由本质的原因。而海德格尔则从人的“存在”问题入手,另辟蹊径地探讨了“此在”向“非本真”状态异化的根源。
一、 异化的根源:畏死
海德格尔将生存在世界上的“人”称为“此在”(Dasein),其原意为“去,下落,做梦等”[1]55。与生物学的定义不同,“此在”表达的不是具体“存在者”是什么,而是人如何“存在”着,如此,海德格尔成功地将西方哲学的最基本范畴“Being”转化为了“Sein”这个“把‘同一性’这种关系绝对化为判断间的关系”[2]92-93的系词,换言之,“他把此在之存在规定为‘在世界之中存在’”[3]32,或称“在世”。海德格尔认为,人是“被抛”于世的存在,“被抛”的人为这样一种孤独无援的境地而感到恐惧。因此,“此在”不会停留在“被抛”的“本真状态”,而必然会异化为一种“非本真”的状态,海德格尔把“此在”向“非本真”状态的异化称为“沉沦”。
最初的“此在”是人的“本真状态”,它先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范畴,具有人确证自己“存在”的本体论意义,此时的人只是自身,而与任何“他人”都没有牵涉。但在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产生后,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在世界中的孤独、无助,换言之,本真的“此在”是一种“个别化”的存在,海德格尔称之为“不在家”的状态,这种孤独、无助的感觉让人无法忍受。于是,不堪重负的“此在”逃遁到与他人“共在”的日常生活中,试图驱散孤独,从而获得一种虚假的“在家”状态,在千篇一律的人群中感到安宁。然而海德格尔指出,正是这种“安宁”的假相把“此在”引向了异化,如他所说,“这种异化把此在杜绝于其本真性及其可能性之外”[4]207,从而使“此在”跌入“非本真的日常生活的无根基状态和虚无中”[4]207。自此,个别化的“此在”开启了向平均化的“常人”的沉沦之路。
在海德格尔看来,所谓“常人”并不是“人”本身,它无处不在,却又“从无其人”,它所具有的只是一种“平均化”的状态,亦即这样一种状态:它“先行描绘出了什么是可能而且容许去冒险尝试的东西,它看守着任何挤上前来的例外。任何优越状态都被不声不响地压住。一切源始的东西都在一夜之间被磨平为早已众所周知之事”[4]148。并且海德格尔强调“沉沦”的普遍性,亦即强调“它的影响在哲学传统中的支配地位”[5]127。
诚然,平均化的常人之间的“共在”能够麻痹“此在”对“被抛”的孤独处境的焦虑,但究其根源而论,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不在家状态”并非来自于“被抛”,而在于“畏死”,即有限的个体对于必然到来的死亡的“畏”。“畏”使“此在”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暂时的,他的“出生”中就预设了“死亡”,如海德格尔所说,“死亡是一种此在刚一存在就承担起来的去存在的方式……只要此在存在着,它就被抛入了这种可能性”[4]294-301。
“畏”的情绪看似没有对象,实则是对“死”的必然性和“生”的有限性的恐惧。“畏”使“此在”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人生而向死亡这一终点前进,生命的旅途只是暂时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终将结束的旅途中,对任何途中风景的执着在“死”的参照下都毫无意义,因为“死”是最本己的可能性,任何他人都无法施以援手。由此海德格尔认为,“对此岸的存在论的死亡阐释先于任何一种存在者层次上的彼岸的思辨”[6]27-28。
此时,“此在”在死亡临在时将无法继续混迹于常人之中,相反,他将被常人的“公众意见”所厌恶和遗弃,这时,“误以为如此安全地处在公众性的保护壳中的人们突然意识到了他本身的虚无性,他瞥见自己处在可怕的独在状态中”[4]227。这时,先前一切看起来有意义的追求都暴露出其虚假的本相。“世界已不能呈现任何东西,他人的共同此在也不能。”[4]227也就是说,“此在”最终将不得不独自面对先前被遮蔽的“死”,以及对死亡的“畏”,它无法逃避到常人之中,只能在“死亡”的“澄明”中感到孤立无援。因此,海德格尔告诫人们:“沉沦”的作用仅限于对当下“畏死”的“遮蔽”,而不能从根本上、永久地消除“死”的在场。
尽管如此,“此在”仍然乐此不疲地沉沦为常人,他们“不让畏死的勇气浮现”[4]292,通过讳谈死亡来掩盖死亡的可能性。然而海德格尔认为,实际上“畏死”也是勇气的体现,因为既然“此在”终其一生都无法真正摆脱死亡和“畏死”的在场,那么勇于直面这种情绪,并主动从虚假的“安全感”中抽离出来的人,就已经超越了自欺、遁世的常人。
海德格尔认为,这种“安全感”的消失是“此在”从“沉沦”中解脱的唯一途径,换言之,“畏死”不仅是“此在”沉沦的根源,其中也潜藏了摆脱沉沦的唯一可能性。因为只有在“畏死”的情绪中,“此在”才能够得以识破日常生活的虚假许诺,看到其生而为人的真正意义所在,不再为“常人”,即不再为非本真状态下的追求所累。“畏死”使人不得不去关注“死”、不得不预见到“生”的有限性和“死”的必然性,并在“死”的参照下摒弃常人无意义的追求。
因此,海德格尔认为“畏死”是一种积极正面的情绪。一方面,它是“此在”沉沦、异化的根源;而另一方面,它又是常人重新回归本真“此在”的唯一可能性。海德格尔将“畏死”喻为“这样一种呼声:它使此在能够把它自身筹划到它最本己的能在上去。它呼唤此在从非本真性中走出来,并将意识到自己是其最本真的可能性的自由的生存”[4]331。也就是说,“此在”只有接纳了死亡这一“此在”的有限性,才能摆脱沉沦,回到最本真的“存在”。
那么,“畏死”如何呼唤“此在”摆脱沉沦而回到“本真状态”呢?海德格尔认为,“(畏死)这一呼唤是一种沉默”[4]338。与常人的“共在”是一种“有声的言谈”,“此在”在这些闲谈的声响中迷失了自我,而“沉默”的力量恰恰能够消弭这些声响,使“此在”重新倾听本己内心的声音,把迷失在“闲谈”中的人“唤回到它本身的静默中去”[4]338。
二、 异化的表征:闲言、好奇、两可
如前所述,“此在”的本真状态是“沉默”,那么与此对应,“沉沦”的非本真状态就是“闲言”。
(一)异化的表现之一:闲言
“闲言”是“此在”异化的所有表征的基础,它指的是“无须先把事据为己有就懂得了一切的可能性”[4]208。 “事”即“真相”,闲言不同于“探讨”真理之处即在于它绕开来真相,顾左右而言他,以无意义的“闲言碎语”充填了本应属于真相的位置。
人们在直面事情真相的时候都会感到恐惧,而闲言就是为应对这种恐惧而生的,它并不关心事情的真相,而只去在乎是否能使话语快速传达。也就是说,闲言的根本目的就是规避人的“存在”,从而使“此在”异化为常人,其结果就是:“话语丧失了或从未获得对所谈及的存在者的首要的存在联系,所以它不是以原始的把这种存在者据为己有的方式传达,而是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的方式传达自身”[4]200。因此可以说,“此在”沉沦为常人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参与到闲言的传播中,亦即放弃了自己“个别化”的意见,屈从于常人的“平均化”思维。从此,话语不必再经过个体的深思,而变成了常人之间为了“共处”而“说说而已”的手段,其本质正是对平均化的“公众意见”的传播。
然而,闲言在使“此在”免于“领会真相”的责任的同时,也让其失去了自由,因为它有效规避了真相和意义。闲言看似滔滔不绝,实则以空洞的言语掩盖了令人恐惧的“真实”。而这种对真相的遮蔽恰恰迎合了常人躲避“畏死”情绪的诉求,正因为如此,闲言总是流传得最为广远,它较真相而言更易于上手,任何人都可以谈论事情,即使他并不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
我注视着这些貌不惊人的果实,个头比黄豆略小,紫黑色的身体因为成熟而变得有一些柔软,在这之前,它们曾是青绿色的果子,并且一直在秋天到来前都保持着坚硬。审美其实是一件特别感性的事情,就比如在我看来,那些姚黄魏紫的脂粉再美,也美不过我手里的这捧樟果,它独一无二的香气,是捅开我记忆深处那间黑屋子的钥匙。
因此海德格尔指出,闲言所开拓的“世界”只是一种“无根基的漂游无据”的状态,它使人感到“到处都在而无一处在”。因为闲言压抑了知识和真理,遮蔽了死亡必然性的真相,但无法真正消除“此在”的有限性,当“畏”的情绪袭来,一切将重新回到虚无,由闲言建筑的空中楼阁终将成为泡影。
(二)异化的表现之二:好奇
沉浸在闲言中已久的常人逐渐忘却了曾经令其生畏的真相,反而真心相信了常人“共在”世界的“美好”。这样的世界安逸但又平庸,在其中,只有易于理解的、具体的“存在者”,而没有了让“此在”惊奇而恐惧的“存在”。这时,“此在”对自身的“存在”失去了本己的感悟,而只剩下对日常世界的平庸的“好奇”。
如果说闲言是常人“说”的方式,那么好奇就是在闲言引导下“看”世界的方式。由于闲言将事物真正的意义都隐去了,好奇也就根本无法把握“存在”,它只是常人对日常生活的“贪新鹜奇,仅止为了从这一新奇跳到那一新奇上去……不是为了有所知地在真相中存在”[4]200。因此可以说,好奇只是一种对世界的“失真”的理解,它以常人为主体,以闲言“创造”的日常世界为客体。遵循二元论的认识模式,早已失去了对“存在”、对真相的感悟能力。好奇的常人终会被表象所迷惑,其作用充其量只不过为闲言提供更多的话题。
海德格尔把对“存在者”的虚假的关注称为“好奇”,为与之相区分,他又将“此在”对本真存在的感悟称为“惊奇”。海德格尔认为,惊奇追求事物的最原始的本质,是与人的存在相伴生的一种情绪,因此,也只有惊奇能够与“此在”的本真状态相沟通。而“对好奇来说,问题不在于被惊奇带入无所领会;好奇操劳于一种知,但仅此为了有所知而已”[4]200。
(三)异化的表现之三:两可
异化的“此在”沉沦在免于责任的闲言之中,闲言引发了趋之若鹜的好奇,而好奇又引发了自欺欺人的“两可”。
闲言遮蔽了世界的真相,好奇使人在真相周边游走,其最终的结果,或称常人的生存状态就是“两可”。在两可中,常人失去了对任何事物的敬畏,他们罔顾事实,用平均化的“公众意见”评价、议论一切。如海德格尔所说,“将要发生的事,还未摆在眼前但‘本来’一定要弄成的事情,人人都已经大发议论了”[4]201。在闲言和好奇熏陶下的常人是无法把握任何真相的,他们只能根据人云亦云的话语,对摆在面前的事件做出似是而非的界说。当问及其是否了解某一事件时,常人总是“知道”的,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好奇中打探消息,但常人的“知道”也仅限于“两可”,即好像是这样,又好像不是,永远无法证实或证伪。“一切看上去都似乎被真实地领会了……而其实却不是如此,或者一切看上去都不是如此而其实却是如此。”[4]201
两可是“此在”沉沦的结果,也是大多数人与他人“共在”的常态,而其危害也是显著而恶劣的。两可“让真实的创新来到公众面前之际已变得陈旧”[4]202,也就是说,它会扼杀人之为人的“本真”存在,使“此在”丧失了创新的能力和兴趣。其作用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让“此在”以为恒久的日常生活才是真实,而使“畏死”隐退到了黑暗的深渊,再也无法“陡然袭来”。如此,沉溺于闲言、好奇和两可中的常人回归本真“存在”的可能性愈发渺茫。
总的来说,海德格尔认为,常人统治下的“日常世界”是一个被扭曲和异化了的虚拟空间,但是这种“异化”对于生活在其中的“此在”来说又是不可避免的。处于闲言、好奇、两可状态的常人误以为摆脱了“被抛”的境遇而沾沾自喜,逐渐忘却了其作为“个别化”存在的“畏”,而成为作为常人的、与其他“此在”的“共在”。
三、 沉沦的救赎:向死而在
有限的“此在”无时无刻不在面对“死”的可能性,而“死”使得其它的可能性都不再可能。正因为如此,“此在”太沉沦为常人,逃遁到常人的闲言中,以好奇代替个别化的惊奇,最终陷入两可的自欺欺人状态中。
但海德格尔认为,这种“逃遁”终究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常人所“畏”之“死”是“经验的死亡”,而不是“本己的死亡”。换言之,常人的“畏死”只是害怕经验到的死亡,而不是只与自身相关、真实体验到的死亡,这是一种“存在者”的死亡,亦即“他人之死”,而不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本真的死亡”。
常人虽然也“畏死”,但却不敢正视死亡,他们的经验提醒自己生命是有限的,但这种呼声总是被遮蔽在对“永恒性”的妄想中。常人表面上承认“终有一死”,但对于自身而言却只是把自己的死亡规定在今后的“虚无缥缈某一天”。
另一方面,“公众意见”对死亡问题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因此,常人总是乐于沉浸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而对“死”这一沉重话题则讳莫如深。“此在”将“死”这一最本己的可能性异化为“他人之死”,希望通过“死亡”与“他人”的绑定消灭其与自身的关联。甚至在面对他人的死亡时,常人也会尽力规劝,使其相信自己会逃脱死亡,从而返回常人安宁的生活中来。于是,死亡成为了被日常世界遗弃的边缘问题,常人避之不及,甚至不允许任何人重拾直面死亡、畏惧死亡的勇气。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在海德格尔看来,只有在对“存在”的直接体悟中重新感受到“畏”的情绪。也就是说,异化的“此在”被救赎的可能性来自它的有限性,而“畏死”则是开启“此在”摆脱沉沦、回归“本真”存在之路的钥匙。
如海德格尔所说,“在死之前畏,就是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和不可逾越的能在‘之前’畏”[4]288。由此看来,“此在”所“畏”之“死”并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此在”时时刻刻与之共生,标识“生”的有限性,并使“此在”与他人相区分的最本己的可能性。为此,海德格尔指出,死亡“使此在可能本真地领会与选择排列在那无可逾越的可能性之前的诸种实际的可能性”[4]303。
海德格尔始终坚称:遮蔽了死亡的“此在”是不完整的存在。如他所说,只要“此在存在,它就包含有一种它将是的‘尚未’,即始终亏欠的东西”[4]279,因为其本质还未完成。只有使死亡澄明的“此在”,即言人的本质就是接受最本己的终结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只要“此在”存在着,在他之中就有某种可能性是缺失的,这种缺失的可能性就是“不再存在”,亦即“死亡”。那么使“此在”成为完整的存在的唯一方法也就是:先行到“此在”的死亡中去领会,直面死亡以及对死亡的恐惧。
诚如海德格尔所说,人归根结底都是要面对死亡的,也只有在死亡这一最本己的可能性中,“此在”才能摆脱一切世俗关系,即从常人平均化的“公众意见”中解放出来,重新成为“个别化”的存在,对只属于自己的生命之旅进行“可能性的筹划”,而不是一味地沉沦于日常生活之中。由此可以说,“此在”自身的存在方式就是“先行到死中去”,这是一种“最本己的能在”,即一种“无所关联”的可能性。“死”要求“此在”进行个别化的生存,因为它本就无所关联,只涉及自身。
然而这并不是说,“此在”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而是要倡导“此在”不再沉溺于常人的闲言中,消解自身本真的“存在”,需要反身直面自己最本己的可能性,因为只有“先行到死中去”,“此在”才能让“死”的威胁始终“敞开”, 如海德格尔所说,“它不仅不淡化这威胁,反倒必须培养这种不确定性”[4]305。威胁就从此在本身涌现出来并因此使此在作为个别的此在来在世。也就是说,正是“畏死”这种恐惧的情绪使“此在”从平均化的“共在”中抽离,重新审视自己“个别化”的“存在”。因此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畏”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它不仅仅是作为消极负面情绪而出现的,人异化的根源,更是“此在”摆脱沉沦,向死而在的关键。
从这个角度来看,海德格尔是从积极意义上看待“死亡”的。诚然,初始状态的“此在”全部处于“被抛”的孤独境地之中,但对未来的生命路径如何选择却造就了不同的人:向死而在的人向着其本真“存在”的可能性不断筹划;而异化沉沦的人则将死亡驱逐出日常世界之外,仿佛死亡永远不会临在,他们偏执地认为,只有将“死”遮蔽在“生”无法窥见的边缘,才能积极乐观地面对生命。但海德格尔却对此看法迥异,他认为“生”与“死”看似冲突,实则相辅相成,因为只有直面死亡、直面“畏死”恐惧,才能真正懂得生命的意义。正如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所说:“终有一死的人比天神更早地达乎深渊。”[7]283
对常人来说,终其一生躲避在日常生活虚假的安宁中亦未尝不可,但只有“死”是不得不亲力亲为的本己之事。如海德格尔所说,“死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在此能在中,此在在它自己的这一别具一格的可能性中保持其为脱离了常人的”[4]302。排除“公众意见”的干扰,筹划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死亡给予“此在”的启示。
海德格尔说,向死而在的人是自由的,是“为自己的死而先行着成为自由的,这就把此在从丧失在偶然地拥挤着各种可能性的情况中解放出来”[4]303。也就是说,只有在“存在”和“死亡”这两种状态下,真实的“此在”才会澄明,而在其间,能够提醒“此在”回归本真的可能性只有“畏”能够提供。在“死”之前体悟到“死”,人就能够向未来“敞开”,为自己的生命筹划各种可能性,从而成为自由的“此在”;而在“死”临在之际,一切可能性都将成为不可能,一切“能在”也将成为“定在”,这时“自由”将无从谈起。
诚然,海德格尔在面对死亡问题时并不乐观,他毫不掩饰地指出“死”是“此在”不可抗拒的必然性。为此他甚至被哲学家沃林批判为“激进反人道主义倾向……(因为)他赋予存在以至高的位置,与之相对,人类行为的自主性被极度贬低”[8]202。然而海德格尔的思想并非仅仅如此,他同时主张开发“畏死”的积极意义,即用“死”来凸显“生”的价值,使人们明白:正是因为“死”必会临在,其之前的各种可能性才弥足珍贵,从而在有限的时间内作出更多的筹划。如此,“死”就从破坏性转向了创造性,并且其创造性之强无与伦比,如海德格尔所说,只有死亡才能够“先行向此在揭露出丧失在常人自己中的情况,并把此在带到主要不依靠操劳操持而是去作为此在自己存在的可能性之前”[4]305。
结语
先行到死中去的“此在”才会从与常人的“共在”中猛醒,不再沉浸于虚假的“安宁”中,转向自己生命的诸多可能性早做筹划,在对“死”的“畏”中确证自己的“存在”,海德格尔用犀利的批判语言践行了苏格拉底的教诲: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度过,在他的思想也逐渐由严肃的理论思辨转向了“一种全新的思境,即与形而上学和作为它现实基础的在场存在状态绝缘、而与非学术的诗与艺术相依存的另一种本有之思”[9],他认为,“向死而在”这样一种近似于艺术和美学探讨的方法可以使作为常人的“此在”从沉沦“变得在家,这也就是海德格尔秘密思想构境的本然之境”[10],其所做出的努力——为可能性筹划,就是审视自己的人生,而经过审视的人生终将获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