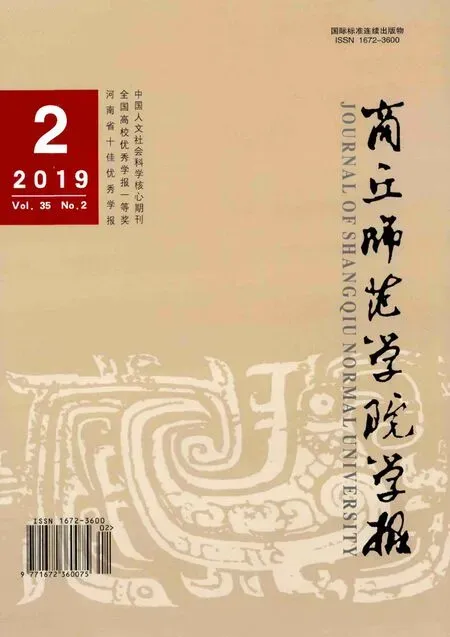足性逍遥与《庄子注》中的德性论
尚 建 飞
(内蒙古大学 哲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就其初衷而言,郭象注释《庄子》的目的并不在于还原庄子的本义,而是为了阐发其对社会人生问题的基本看法①自南北朝开始,《庄子注》是否为郭象所著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目前学术界大多认可《晋书·向秀传》的观点,认为郭象注自有独到之处,只是在向秀注的基础上“述而广之”。。在《庄子注》中,郭象不仅将“逍遥”解释成“足性逍遥”,而且依据个体天性的差异性来重新界定庄子的“无为”和“知”。如果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那么所谓的“足性逍遥”就是要实现以个体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并将顺应个体天性确定为内在价值的基本原则。与之相对应的是,《庄子注》又把个体顺应天性的品质和认知活动称为“自得”“自知”,并且据此建构起了一种能够同人伦秩序相调和的德性论。
一、足性逍遥的价值内涵
从其用法来讲,“足性”概括了郭象的“足于其性”“足于天然”表述形式,它的意思是指满足个体天性的实践活动②例如,刘笑敢就解释道:“‘各据其性分’‘物冥其极’‘足于其性’‘足于天然’‘安其性命’,用词不同,意思都是一样的,都是要达到内在之自足与满足,我们可以简称之为‘性足’或‘足性’。”见刘笑敢:《从超越逍遥到足性逍遥之转化──兼论郭象〈庄子注〉之诠释方法》,《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3期,第9页。。以“足性”来界定“逍遥”的立场表明,郭象只是接受了庄子推崇个体天性的思想,与此同时又完全放弃了后者关于人之本性的见解。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说,郭象所谓的“足性逍遥”呈现出顺从既定人伦秩序和注重个体内在感受的特征。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如何调和自然与名教,使人的天性适应君臣、父子所代表的人伦秩序是魏晋玄学的主题之一③名教包括君臣之伦(政治秩序)、父子之伦(家族秩序),其在魏晋时期的变化显得颇为繁杂。关于名教在魏晋时期的演变,详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03页。。虽然郭象没有直接将“自然”与“名教”对举,但他同样关注人的天性与人伦秩序之间的关系,并且用自己的言说方式表达了一种独特的观点:“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1]591通过解读穿牛鼻、络马首的现象,郭象认为,人对牛马的驯服、驾驭也正符合了它们的天性。依此类推,“人事”表示君主、臣子、皂隶等社会角色的划分,是与“天命”“天”,即每个个体的天性一一对应。或者说,人的天性就表现为其在人伦秩序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在郭象看来,确信自然与名教、人的天性与人伦秩序之间具有一致性,是进行价值判断的逻辑起点。例如,在赞赏其“知本”“知无心”的同时,郭象又批评庄子不懂得“心无为”与“冥物”(《庄子序》)。换句话来说,郭象认为,庄子的著述,即《庄子》之所以“虽当无用”的原因在于,将其推崇个体天性的思想游离于人伦秩序之外,从而只能演变为内心独白和文字思辨。
显而易见,调和自然与名教成为郭象探讨价值论问题的基本视域,而《庄子》仅仅是其展开理论论证的思想资源。这种立场使得郭象能够重新诠释庄子的逍遥思想:“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1]1按照郭象的观点,尽管个体天性存在着差异,然而只要找到令其感到惬意的生存方式,从事与其天性、能力和角色相一致的活动,那么每个个体都可以享有“逍遥”。从价值论角度来讲,郭象所谓的“逍遥”是以实现个体天性作为终极目的,并且通过在此过程中所获得的满足感来加以验证。更为重要的是,“逍遥”或满足于个体天性的生存方式将会对人类社会产生积极影响:“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1]9也就是说,如果大鹏、小鸟及其所象征的各色人等都能满足于自己的天性,那么他们就会因为“逍遥”而忽略彼此之间的差异,最终完全顺从既定人伦秩序的安排。
从逻辑上讲,郭象一方面把“逍遥”限定在个体天性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又凭借区分个体天性的类型来解释“逍遥”的等级分化。按照郭象的理解,个体天性在应对生存情境方面有着优劣之别,从而形成了圣人与凡人所象征的两种天性和“逍遥”。在注释《逍遥游》中与“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相对应的人格形象时,郭象指出:“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哉!又顺有待者,使不失所待,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1]20只有顺应其他事物的天性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个体才能在现实世界当中消除对待、通行无阻。此处的“与物冥而循大变”“无待而常通”,不仅证明个体拥有出类拔萃的天性,而且又会导致其他个体放任自己天性的结果。如果就其所享有的生存方式而言,那么“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遥”,即是为“至德之人”所独享的逍遥,其实质则在于兼顾自我与他人的天性,使彼此免受干涉、皆有实现自身天性的可能。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逍遥”也被称为无待的逍遥,它也是郭象专门为“至德之人”和圣人所设计的逍遥[注]当代庄学研究者认为,“无待”虽然出自《庄子》,但是只有在郭象的《庄子注》中上升为哲学范畴。关于“无待”一词的考察,详见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38~140页。对于郭象所赋予“无待”的意义,杨立华指出:“‘无待’者与‘有待’者的根本区别即在于‘无待’者能够泯除彼我的分别和界限。”见杨立华:《郭象〈庄子注〉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2页。。然而,根据上下文的语境来看,郭象所谓的“无待”应该是指,能够摆脱特定情境限制的天性及其生存方式。相比之下,为数众多的凡人处于“有待”的状态,也就是有如列子御风而行那样,必然是在特定的情境下实现其天性、获得有待的逍遥。通过澄清无待的逍遥与有待的逍遥,郭象所要力图说明的是,圣人的天性和“逍遥”使其有资格成为人类社会的统治者,而凡人的天性和“逍遥”则造就了被统治的命运。
作为诠释庄子逍遥的经典理论,郭象的“足性逍遥”无疑契合庄子推崇个体天性的思想,然而同时又背离了后者优先考虑人之本性的立场。实际上,庄子的逍遥恰恰是要破除人们对于个体天性的迷恋,其中的道理就在于这种观念遗忘了生命本身的存在价值。例如,《逍遥游》的开篇列举了诸多生物的天性:大鹏、小鸟受到空间大小的限制,朝菌、大椿的分别在于生存时间的长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个体天性的空间、时间向度决定了生物的生存方式。与其他生物有所不同,人的天性呈现出自主选择的特征:世俗君子追求荣誉,宋荣子或宋钘怀揣救世之志,列子热衷于方术奇技。庄子之所以要将上述生存方式归结为“有所待”的理由在于,它们虽然展示了个体天性的多样性,但也有可能把生命视为达成某种外在目的的手段。
正是有见于此,庄子才会针锋相对地提出“逍遥”的价值原则:“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庄子·逍遥游》)所谓“乘天地之正”的意思是指,把握住“天地”的精神,即能够以公正无私的态度来守护生命[注]释德清的观点颇有见地:“正,天地之本也,如‘各正性命’之‘正’。”见[明]释德清撰,黄曙辉点校:《庄子内篇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御六气之辩”所要说明的是,个体天性具有的情感欲望不能违背守护生命的原则[注]郭庆藩的考证表明,“六气”的其中一种含义是“六情”,分别是与北东南西上下相应的好怒恶喜乐哀等情感欲望。详见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上),中华书局,2006年,第21页。。在理论论证的层面上,“乘天地之正”的前提是人必须具备与之相应的能力,而这也关系到庄子对于人之本性的理解。简单地说,庄子认为,人之本性就体现在“心”所固有的“神”,是一种可以超越彼此是非之分别、认识天地万物之本原或“道”的直观能力[注]有关庄子之“心”“神”的用法和含义,详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338~346页。。所以,庄子的“逍遥”是在运用人之本性的前提下顺应其天性的生存方式,或者说,是以守护生命优先于放任情感欲望的原则来应对变化无穷的具体情境。
针对郭象误读“逍遥”的现象,东晋的支道林就曾指出:“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2]160郭象的“足性逍遥”必然会赞同夏桀、盗跖的暴行,并且会由于无视他人生命的意义而丧失道德价值。不过,支道林的解释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仅仅用于表示“至人之心”和“建言大道”[12]1。除此之外,当代的吴怡着重探究了郭象曲解“逍遥”的理论根源,其结论是郭象的“逍遥”“没有分清物性和人性”,从而“以自限的物性,封闭了向上的人性”[3]11。可以肯定的是,支道林的责难揭示出了“足性逍遥”的核心内涵,即是以满足个体天性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然而,在承认每个个体都有可能获得“逍遥”的过程中,“足性逍遥”又否认了人与生固有领会“道”和守护生命的本性。同支道林相比,吴怡的观点有见于“足性逍遥”与现实相妥协的特征,也就是把个体天性还原为特定的角色规定,因此个体的人生意义就被说成是顺从既定的人伦秩序。
如果概观郭象与庄子的分歧以及后世的评论,那么我们就会对“足性逍遥”的价值内涵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具体地来讲,“足性逍遥”是以个体天性与人伦秩序的统一性作为理论依据,进而将满足于个体自身的天性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并且,无待和有待两种逍遥的划分,最终使得郭象不仅消解了“逍遥”关于人之本性的预设,而且也颠覆了庄子确信每个个体生命具有同等存在价值的基本主张。
二、自得与德性的原则
在郭象的话语体系当中,“足性逍遥”得以可能的根源在于个体天性可以“自为”,它使得个体拥有保全自身和确定社会身份的能力。只要个体能够“任其自为”,即完全放任天性的自发运作,那么他将会“自得”或是因为实现其天性而感到惬意。在此基础之上,郭象既将“自得”确定为德性的原则,同时又提示出“足性逍遥”是一个放任个体天性的过程。
从理论论证的角度来看,“足性逍遥”对于每个个体都有效的前提是个体与生俱来有实现自己天性的能力。事实上,郭象恰恰认为角色定位与特殊能力是个体天性的两个基本向度:“故大鹏之能高,斥鷃之能下,椿木之能长,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为之所能也。”个体天性在形式表现为大鹏、斥鷃、椿木、朝菌等角色,而导致上述区别的根源却是彼此不同的特殊能力。例如,大鹏的垂天之翼使其翱翔于九万里高空,身形小巧的斥鷃可以在榆枋之间穿梭,大椿以三万两千岁为一年,朝菌的荣枯不过一日。此外,这些特殊能力是每个个体与生俱来的禀赋,所以也是其保全自身、适应生存情境的先决条件。但与其他物种相比较而言,人类的天性显得更为复杂:“足能行而放之,手能执而任之,听耳之所闻,视目之所见,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为其自为,恣其性内而无纤芥于分外,此无为之至易也。”[1]184手足耳目等感官知觉代表着人与生俱来保全自身、适应生存情境的能力,与此同时,理智判断可以帮助他把握住各种能力的适用范围。因此,个人如果能够放任其天性中所固有的能力,那么他的实践活动将会与自己角色身份保持一致。在这一基础上,郭象一方面把个体天性中的各种能力统称为“自为”,另一方面又对“无为”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其实质就在于个体完全放任自己与生俱来的能力。
经过郭象的注解,庄子的“无为”被看成是赞同世俗人伦秩序的理论: “无为者,非拱默之谓也。直各任其自为,则性命安矣。”[1]369首先,“无为”有别于保持静默、疏远人伦秩序的消解态度,反而是“任其自为”,即通过放任个体天性中的各种能力来确定自己的角色身份。其次,就其所产生的效果而言,“任其自为”意义上的“无为”会令个体获得自足性的生活:“无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闻也。”[1]184“无为”可以确保个体保全自身以及适应生存情境,同时也将由于实现其天性而享有幸福或逍遥。再次,遵循“无为”所成就的品质被郭象称为“自得”。在《逍遥游》的题解中,“自得”之所以成为一个核心术语的原因在于,它意味着“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1]1。也就是说,个体的“自得”表现为能够从事与其天性、能力和角色相一致的活动,而且凭借享有“逍遥”或自己的满足感来加以证实。从逻辑上讲,“自得”起始于“物任其性”,即个体要选择适合其天性的生活方式。立足于这一基础之上,“事称其能”和“各当其分”彰显出自愿性的特征,而“逍遥”或个体自身的满足感则是“自得”的标志。概括起来看,郭象所谓的“自得”就是,个体在遵循“无为”,实现其天性的过程中所成就的品质。
依据其对个体天性及其实现途径的理解,郭象不仅赋予了“无为”以新的含义,而且也将“自得”确定为德性的原则。在庄子的语境当中,“无为”本身就被确定为评判德性的尺度,但却把人的本性当作界定这一范畴的根本视域:“夫恬惔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庄子·刻意》)“恬惔寂漠”是指“心”无成见、无好恶的心理状态,“虚无”表示消解自我中心的观念[注]关于“虚”“恬惔”“漠”在《庄子》的用法和含义,详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341~344页。。它们共同展现了“心”所固有的功能,而这正是庄子对于人之本性的基本看法。紧随其后提到的“无为”则是正确运用人之本性的方式,即突破血缘亲疏、尊卑等级以及自我中心的狭隘观念,使“心”效仿“天地”和“道”的公正无私[注]成玄英曾指出:“恬惔寂漠,是凝湛之心;虚无无为,是寂用之智。天地以此法为平均之源,道德以此法为质实之本也。”见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中华书局,2006年,第538页。。换句话来讲,庄子的“无为”源自于其对于人之本性的理解,并且是以公正无私地守护生命作为德性的原则。与庄子相比,郭象不再承认“无为”与人之本性的内在关联,反而是仅仅关注个体天性以及“自为”的理论。然而,当“无为”被转化为“任其自为”之时,郭象更为看重的是与个体自身的满足感相对应的“自得”。所以,就其是“足性逍遥”所必需的品质而言,“自得”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郭象检验德性的基本原则。
在形式上,郭象的“自得”及其实践主张似乎并没有背离庄子的精神,因为他把握住了后者批判“仁义”的相对性和推崇个体天性的特征。例如,郭象赞同庄子的看法,强调仁义仅仅对个别人有效:“故多方于仁义者,虽列于五藏,然自是一家之正耳,未能与物无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1]313仁义展示出曾参、史鳅等人的天性,或者说,是他们实现各自的天性所养成的卓越品质。以此类推,所谓的“道德之正”或德性的评价尺度只能是“各正性命”,而这也恰恰证明了“自得”或实现个体天性的德性原则有其合理性。当然,郭象深信“自得”不会导致利己主义:“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于己,彼我同于自得,斯可谓善也。”[1]328也就是说,只有任凭个体满足其天性,那么他才有可能顾及其他人的需求。而且,德性的善恰恰就表现为,每个个体都可以实现自己的天性。从逻辑上讲,放任个体的天性既有可能帮助其他个体实现自己的天性,同时也有可能会阻碍其他个体实现自己的天性。所以,郭象的观点只是或然性判断,因为其前提与结论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联。
此外,从文本本身来看,虽然《庄子·骈拇》的主题是抨击“仁义”和推崇个体天性,但庄子的论证却蕴含着“不失其性命之情”与“臧于其德”两个向度。所谓“不失其性命之情”是指,不能迫使个人改变其天性,必须尊重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如果就其将“仁义”斥为“非道德之正”的理由来说,那么庄子也认为“仁义”只是出自少数人的天性,所以用“仁义”陶铸他人天性的主张并不具有普遍有效性。然而,在尊重个体差异性的背后,庄子又揭示出天性的统一性内涵,或者说,个体的“性命之情”统一于“德”。这种论证方式表明,顺应天性意思应该是以“臧于其德”统摄“不失其性命之情”,即在守护生命的前提下尊重个体差异性才是德性的根本法则。
毫无疑问,“足性逍遥”在实践活动中就体现为“自得”,而且二者共同奠基在个体天性所固有的能力或“自为”之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重新诠释“无为”及其有效性,郭象将契合个体天性的生活方式统称为“自得”,其中涉及了个体的选择、意愿以及情感体验等层面的内容。不过,无论在形式论证上有多么完善,郭象依据“自得”所构建起的德性评价尺度都有别于庄子的原有思想:颠覆了天性的统一性内涵以及守护生命的价值原则之后,个体的实践活动就有可能偏离道德的立场,或者说是以成就利己主义者作为生活的终极目的。
三、自知的实践意义
尽管“足性逍遥”和“自得”力图表明,放任个体天性的生活方式简便易行,然而人类生活的实际情况却在不断地质疑这一理论的有效性。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并不安于自己的天性,而是人们希望改变其天性的有力证明。对此,郭象给出的解释是,个体能否实现天性取决于“知”:自知其天性可以使人享有“逍遥”和“自得”,误解其天性则必然会遭遇诸多生存困境。
对于人们为何不能享有“逍遥”的原因,庄子给出的解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受到“成心”的误导,个体陷入是非、彼此之争;一是沉溺于“俗学”“俗思”,遗忘了人的本性和“道”的意义。归结起来讲,能否使其“心”摆脱个体自我中心的藩篱,运用“心”的认识功能去把握住人的本性和“道”,是人们享有“逍遥”的先决条件。在《庄子注》中,郭象接受了庄子探讨“逍遥”的理论框架,即确信人的认知与“逍遥”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至人知天机之不可易也,故捐聪明,弃知虑,魄然忘其所为而任其自动,故万物无动而不逍遥也。”[1]593所谓的“天机”是指个体天性所固有的能力,而且只有认识到“天机”的自在性,放弃任何试图改变“天机”的欲求,个体才会由于放任自己的天性而享有“逍遥”。从相反的角度来讲,如果无视其天性的限度,那么个体的“知”或认知活动将会出现“失当”“灭于冥极”[1]115,也就是在追逐享乐的过程中误解自己的天性和“逍遥”的意义。
就其相似之处而言,郭象和庄子都把能否实现“逍遥”当作评价“知”与认知活动的标准[注]陈少明在解读《齐物论》的“知”时指出,庄子评价“知”的标准“不是基于其内容的真实水平,而是基于其远离是非的程度”,“是‘善’而不是‘真’”。见陈少明:《〈齐物论〉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4~215页。但与此同时,陈先生似乎忽略了庄子的“知”与其所谓的“善”,即逍遥之间存在着必然性的关联。。但是,随着“逍遥”被转化为“足性逍遥”,《庄子注》开始致力于用个体天性来重新建构“知”与认知活动的思想体系。
首先,郭象认为,“知”是个体天性所固有的能力:“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见,心不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矣。”[1]593足、目所象征的感官知觉和“心”之“知”或理智判断能力,共同展现了个体天性的具体内涵。并且,“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1]61,即“心”之“知”主宰着感官知觉是个体天性的运行法则。需要说明的是,郭象提到的“不知”既表示个体无从知晓天性得以形成的缘由,同时又凸显出各种能力为个体与生俱来,可以自发地运作。援引郭象本人的话来讲:“今未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皆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1]61也就是说,“不知”虽然表明个体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拥有“知”和其他能力,但其肯定性的意思却体现在“自知”“自生”:个体可以自然而然地知道如何保全自身、适应生存情境。
其次,“自知”还意味着个体的“知”与认知活动有其特定的限度。郭象注意到,“自知”得以可能的前提是“不知”:“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则知出于不知矣”,“知出于不知,故以不知为宗。”[1]224从逻辑上讲,“自知”也可以被划归到“不知”的领域,因为它是以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方式为个体所拥有。或者说,个体天性所固有的“知”,使其知道如何保全自身、适应生存情境的先决条件。郭象据此推论道,“自知”并不会使个体变得无所不能,甚至不是个体生存实践活动的决定性因素:“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众,为之所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1]225。在郭象看来,天地万物的整体运作为个体生存提供了充足的条件,而“自知”仅仅关注个体自身,所以无法掌握影响个体生存的全部要素。例如,“五常”和天地万物的整体运作法则就超出了“自知”的范围,但个体生存却必然要依赖后者所提供的人伦规范和庇护。此外,“自知”还容易受到好恶之情的干扰,其中好生恶死正是最为典型的案例:“死生一也,而独说生,欲与变化相背,故未知其非惑也。”[1]103死生与梦觉相类似,二者皆为个体生存的构成性要素。并且,正如人们通常偏爱梦境那样,生或保有自身生命也被个体认为是善的事物,相反,死或丧失自身生命则被个体看成是至恶。殊不知生与死都是个体生存所必然要经历的阶段,而好生恶死、不知道平等地对待生死恰恰背离了生命变化的道理。从某种程度上说,个体天性的成因、人伦规范以及天地万物的整体运作,完全超出了“自知”的能力范围,但生死的意义和生命变化的道理却是“自知”所能把握的对象。
在揭示“自知”的本体论根基及其适用范围的同时,郭象又力图证明“知”与认知活动无须探讨天地万物的根源,而这一观点可以通过其对老庄之“道”的界定来加以把握:“知道者,知其无能也;无能也,则何能生我?”[1]588“道”并非是生成天地万物的根源和统一原理,将其等同于“无能”是为了提醒人们,天地万物都“自然而生”或自然而然的产生。所以,如果“知道”,也就是明白“道”只不过是一个理论上的预设,那么人们就不必相信彼此之间分享了某种相同的禀赋。并且,与悬搁“道”相应的是,郭象又更改了老庄关于“无”的用法:“夫庄老之所以屡称无者,何哉?明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为生也”[1]381-382。 “无”已经不再是用来形容“道”的术语,其内涵应该被确定为“无物”。具体地来讲,天地万物的产生与自身之外的事物无关,即每个个体的形成皆因其天性而使然。
从整体上来看,通过思考与“自知”相关的诸多要素,郭象明确提出“知”与认知活动的适用领域仅仅在于个体天性。一方面,“自知”会使个体明白自己的天性具有客观自在性:“苟知其极,则毫分不可相跂,天下又何所悲乎!”[1]13只要认识到个体天性的“极”,也就是承认个体与生俱来的能力有其极限,是无法选择和改变的独特禀赋,那么人们就不会因为彼此之间的差异而感到悲伤。在此基础之上,每个个体能够无条件地接受、顺从自己的天性,从而可以在实现自己天性的过程中获得满足感和享有“逍遥”。
另一方面,“自知”也将有助于理解是非争论的必然性。事实上,庄子是把执着于个体差异性的认知确定为是非纷争的渊源:“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庄子·齐物论》)如果单纯地立足于“我”或个体性的角度,那么人们就会因为彼此的差异而无法形成关于仁义、是非的统一认识。或者说,人们只能依据“我”或个体性的角度来确定仁义、是非的标准。因此,只有突破个体差异性的藩篱,人们才能从“道通为一”的层面构建起评判仁义、是非的统一尺度。虽然郭象也认为个体差异性与是非争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但他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对于郭象而言,“人自师其成心,则人各自有师矣。人各自有师,故付之而自当”[1]61。个体与生俱来的“成心”使其能够把握住实现自身天性的方式,这种立场不仅可以将是非的标准归结为个体自身,而且又否认了是非有可能用统一的尺度来加以评判。更为重要的是,郭象由此提出了是非争论本身就是无可避免的现象:“自知其所知,则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则以彼为非矣。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1]66-67“自知”应该被看成是“成心”的功用,它令个体自发地知晓自己所要达成的目标,进而导致了“自以为是”,只认可自我评判的结果。与此同时,个体的“自以为是”也产生出“以彼为非”的立场,即拒绝接受其他个体所欲求的对象。所以,作为实现天性的必要条件,“自知”必然会使个体处于是此非彼的状态。
显而易见的是,郭象确信“知”与认知活动是享有“逍遥”和“自得”的逻辑起点,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们把握住后者的实质、作出相应的选择。换个角度来讲,由于所谓的“逍遥”和“自得”共同以实现个体天性作为终极目的,而这也表示运用“知”的正确方式即是“自知”:凭借标示出“不知”的领域和悬搁关于“道”的观念,最终是将个体生存需求及其天性的客观自在性视为认知活动的对象。就其对实践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而言,“自知”明确了人类生活的核心议题:“夫无以知为而任其自知,则虽知周万物而恬然自得也。”[1]548人类生活的目的不在于认识天地万物的真相,而是应该将关注的焦点投向个体自身,也就是“自知”或明白个体的生存需求及其天性的客观自在性。并且,只有紧扣这一核心议题才能理解实践活动的意义,或者说,是在“自得”与放任个体天性的过程中享有“逍遥”。此外,奠基在“自知”之上的实践活动仅仅限定于个体自身,所以,郭象的“逍遥”和“自得”要以放弃是非争论的统一标准作为代价。
作为诠释《庄子》的经典文本,郭象的《庄子注》非常清楚庄子以及道家的实践主张,并且指出后者的弊病在于无法化解个体天性与人伦秩序之间的对峙。正是有见于此,《庄子注》首先把庄子的“逍遥”转化成“足性逍遥”,其理论依据则是承认个体天性与人伦秩序中角色定位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所以满足于个体自身的天性就意味着要完全顺从既定人伦秩序的安排。其次,立足于“足性逍遥”,郭象提出“自得”即是“道德之正”或德性的评价尺度,从而把放任个体天性的满足感当作道德实践的根本原则。当然,从逻辑上讲,理解“逍遥”和“自得”的理论内涵要以“知”与认知活动作为前提。郭象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是,个体天性所固有的“成心”使其有“知”的能力,而且运用“知”的正确方式只能是“自知”。概言之,郭象的《庄子注》所接受的仅仅是庄子推崇个体天性的主张,与此同时又遗弃了庄子关于人之本性的理论预设。因此,所谓的“足性逍遥”“自得”和“自知”,无不奠基在个体自我中心观念的基础上,其后果则是要求人们认同人伦秩序的安排和是非争论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