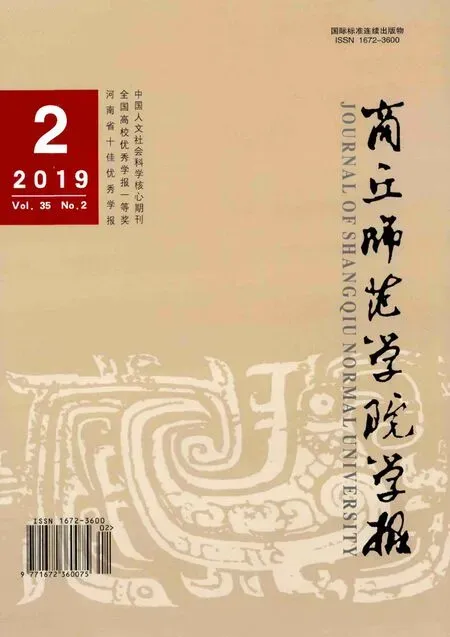《齐物论》三处释义
刘 洪 生
(商丘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此前笔者曾有几篇拙作谈及《庄子》一些字、词、句的解释问题[注]《〈庄子〉中的豫东方言与民俗》,《诸子学刊》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庄子〉疑难解读与浅释》 ,《殷都学刊》2015年第1期;《〈庄子〉中那些被误读千年的文字》,《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11期。,均是在新、旧注之外,别立异说。这里继续奉上关于《齐物论》篇几处解释的不同意见,以就教于各方家。
一、“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
首先,这节文字中的“代”,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字。“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这句话,郭象注云:“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师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谓短而舍其所谓长者也。”[1]61是将句中的“代”字,作动词“代替”解。成玄英疏云:“愚惑之类,坚执是非,何必知他理长,代己之短,唯欲斥他为短,自取其长。如此之人,处处皆有,愚痴之辈,先豫其中。”[1]61亦是将“代”字视作“代替”“替换”解。郭庆藩引郭嵩焘言:“《说文》:代,更也。今日以为是,明日以为非,而一成乎心,是非迭出而不穷,其曰知代。心以为是,则取所谓是者而是之,心以为非,则取所谓非者而非之,故曰心自取。”[1]61-62这里,郭氏叔、侄二人持论与郭象、成玄英同。但却是有问题的。
因此,又有人将“代”释作“更化”“变化”等含义。锺泰:“‘代而心自取’,即前‘日夜相代乎前’‘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之说也。”[2]35张默生:“章太炎云:岁序递迁,是名为代。默按:即前文‘日夜相代乎前’之‘代’。”[3]101崔大华:“知代,懂得变化也。”并引林希逸语:“知代,古贤者之称也。代,变化也,言其知变化之理也。”又引罗勉道语:“‘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是从‘日夜相代’‘咸其自取’来。”[4]59曹础基:“代,更,变化也。知代,懂得事物的变化。”[5]21陈鼓应注:“‘代’,指自然变化之相代。”[6]50杨柳桥则把“知代”翻译为:“懂得循环交替的道理。”[7]13
上述第二类解释,已经不再是将“代”释作表示横向的、空间关系机械转移的动词——“代替”“取代”“替换”等,而是释作了表示纵向的、时间关系抽象流动的动词——更迭、变化、交替等,是较为恰当的。
而笔者理解,此“代”字,根本上很可能就是“化”字之误。“化”是庄子学说中的一个重要哲学概念[注]与《庄子》一书内容交叉最多的《列子》中 ,“化”也是一个重要概念。《天瑞》:“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无时不生,无时不化。阴阳尔,四时尔。不生者疑独,不化者往复,其际不可终。疑独,其道不可穷……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黄帝》:“凡有貌像声色者,皆物也。物与物,何以相远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则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夫得是而穷之者焉,得为正焉?彼将处乎不深之度,而藏乎无端之纪,游乎万物之所终始。壹其性,养其气,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周穆王》:“有生之气,有形之状,尽幻也。造化之所始,阴阳之所变者,谓之生,谓之死。穷数达变,因形移易者,谓之化,谓之幻……知幻化之不异生死者,始可以学幻矣。吾与汝亦幻也。”其他早期文献,如《周易》与《老子》亦然。因此,可以说这种变化、运动的认识,是中国先民最普遍、最朴素、最基本的哲学思想。,解作“化机”“大化”。而作“代”解,是较为突兀的,而最终还是要回到“化”字的意义上。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
其一,紧接本节文字之前,“化”字反复出现:“一受其形,不化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都是在讨论万事万物存在的本体形式问题,即:一切都在变化之中,“道”即“大化”“大化如流”。正由于此,所以一切物,或一切物论,都是平等的,都是齐平的。事实上,这也正是本篇《齐物论》的主旨或理论基础。
其二,在大资料下统计,“化”更是庄周之学、之书中一个核心性的概念范畴。《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齐物论》:“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人间世》:“夫胡可以及化!犹师心者也。”“夫循耳目内通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是万物之化也。”《大宗师》:“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又况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待乎?”“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与予之尻以为轮,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物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系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乎!且方将化,恶知不化哉?方将不化,恶知已化哉?”《在宥》:“徒处无为,而物自化。”《天地》:“天地虽大,其化均也。”《秋水》:“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至乐》:“万物皆化。”《知北游》:“今彼神明至精,与彼百化。”《则阳》:“无始无终,无几无时。日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天下》篇论庄周之学时,更是说:“其应于化而解于物,其理不竭,其来不蜕。”因此,在庄子看来,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从无开始,具象之后,经历过所谓的存在阶段,又必然返回到虚无中。“这种物与物、物与人之间的无界限、无条件的自由转化,庄子称之为‘物化’。”[8]114而且,庄子认为,这种“化”的动因仿佛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主宰着,称之为“自化”,“化其万物而不知其禅之者”(《山木》),“虽有大知,不能以言读其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将为”(《则阳》)。如果进一步从价值论方面评估,庄子的这种“自化”论,一方面,明显地蕴含着对必然性和制度规范的否定和拒斥,所以也就必然导致其哲学思想中的不可知论;一方面,又和儒家伦理思想中“为仁由己”(《论语·颜渊》)的涵养自觉意识一起,共同构筑起中国传统思想中防范宗教主宰的屏障和堤坝,在现实的理性追求中,具有信仰的职能,儒、道互补,形成稳定和谐的中国传统思想,具着无穷的权变智慧。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笔者认为,今本《庄子·齐物论》中“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这句话中的“代”,本字应是“化”,是在早期的传抄中,由于写手的误写,或抄者的误识,而导致了今天的结果,进一步导致了后世层层转读拆解的隔膜。明代学者叶秉敬即在“奚必知代而自取者有之”的“知代”二字下,用粗笔标出符号“XX”[9]30,以示其疑问,不知是否就是这种理解。应该说,在中国古代的经典中,每一个汉字的使用,都隐藏着汉民族文明的密码,细细寻绎下去,背后都有深沉厚重的社会文化生活,都是先人生活经验和智慧的高度抽象化的概括,或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下,章学诚有“六经皆史”之说,并认为“善读古人之书,尤贵心知其意义”[10]300。后世可能由于时空的阻隔或知识文化背景所限,无法理解元典的“一字之妙”,这实在需要一种“同情之了解”,需要一种通透圆融的眼光和功夫。
其次,这段文字中,第二个疑点是“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中的“未”字。这句话郭象注:“今日适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明夫是非者,群品之所不能无,故至人两顺之。”成玄英疏:“吴越路遥,必须积旬方达,今朝发途,昨日何由至哉?欲明是非彼我,生自妄心。言心必也未生,是非从何而有?故先分别而后是非,先造途而后至越。”[1]62郭、成二家均将这句中的“未”字释作表示否定判断的副词“没有”“不曾”等意。但笔者认为,这种解释可能仅是就字面上的理解,忽略了相关的语境以及前后行文的连接和逻辑关系,是看似通顺而实不切题的、“鸵鸟”式的解读。
这节文字的根本大意,是从认识论角度批评人们:常常是先在一种成见或偏见左右下,去判断是非,认识真理,这就像没有出发去一个地方,而强说已经到达了一样荒唐,是“以无为有”,即使像大禹一样神明也是办不到的。
这节文字中,作者要批判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成心”[注]王闿运《庄子王氏注》:“随其成心而师之:成心已形,为我之心。”“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成心尤多也,然贤愚虽异,自是则同,故不足师矣。” 见方勇编纂《子藏·道家部·庄子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亦即本篇后文所说“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中的“小成”,《人间世》中所谓“夫胡可以及化,犹师心者也”。是说:就是因为人们先有了“成心”,或是非之心,因而遮蔽了体道、知化的眼光。对这一道理,笔者认为,本节文字是分两层阐述的:“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为第一层,陈述或描写在“成心”左右下,所出现的认识上的乱象;“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为第二层,进一步分析或论证,在“成心”左右下的认识,是不合理和不可能的。本来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可问题就出现在“未成乎心”四字上。“成乎心”就是第一句中的“成心”,这是大家一致的理解;而这里的“未”字,笔者认为应该就是发语词“夫”字之误,不应作否定副词“未”解,因为:第一,“成乎心”与“有是非”是同时发生的事情,“有是非”就是有了“成心”,故原文在其间使用了一个表示并列关系的连词“而”——“成乎心而有是非”。第二,如果作“未”解,“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那么,“有”成心而有是非,就不是“今日适越而昔至”,这就是在肯定有“成心”,显然与前文抵牾。清人屈复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的《南华通》注云:“未成乎心(此句疑有脱误,大约是不师成心)而有是非(到此方露是非二字,物论不齐,皆由于此),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只是言其以无有为有也)。是以无有为有(此句覆解上句),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11]51在屈氏看来,原文“未成乎心”中的“未”是令人费解的,因而他怀疑有脱文或错简;而且认为这几句行文是层层递进,下句“覆解上句”。第三,如果作“夫”字解,第一层第一句话是“夫随其成心而师之”,第二层第一句话是“夫成乎心而有是非”,构成了两个整齐的祈使句;两层之间,排比行文,次第深入,语意完整,通顺流畅;同时也避免了郭象注的尴尬。郭注:“今日适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这样说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可今本的原文却是:“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所以郭象的注是自说自话,是架空的、“鸵鸟”式的解释,或者郭象所依据的本子与今本不同,这里的“未”,压根就是“夫”的一笔之误。
至于王元泽将“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解释为:“心者,人之真君也;人能不丧其真君,所以谓之成心也。成心既存而自师之,则与道冥会而与神默契,不必知阴阳代谢而,然后谓之得道也。愚者不能知有真君而存之,徒务役形而求道,此其所以自惑也。故终身求之而不知也。”又将“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解释为:“圣人固其成心而无是无非,下文所谓以是非为环得其中者也。众人丧其成心,而有是有非,此之所谓今日适越而昔至也。”[12]41-42之后,更有人坚持认为,“未有成理昭然于心,而预设是非之辨,皆心所造作,非理本然也”,“非本有之心,故曰以无有为有”,“未成凝一之心妄起意见,以为若者是道,若者非道,犹未行而自夸已至”等[注]分别见:王夫之《庄子解》、徐廷槐《南华简钞》、叶玉麟《白话庄子读本》。见方勇编纂《子藏·道家部·庄子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这种认识,恐怕与该段文字的前后文语境,与整篇文章批判“成心”“固念”的思想背道而驰。这里,王氏没有办法合理解释“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这句话中的“未”字,只好曲解前文。
二、“昭文之鼓琴也,师旷之枝策也,惠子之据梧也,三子之知几乎!皆其盛者也。”
句中“几”字,郭象注:“几,尽也。夫三子者,皆欲辩非己所明以明之,故知尽虑穷,形劳神倦,或策杖假寐,或据梧而瞑。”成玄英疏:“几,尽也。昭文善能鼓琴,师旷妙知音律,惠施好谈名理。而三子之性,禀自天然,各以己能明示于世。世既不悟,己又疲怠,遂使柱策假寐,或复凭几而瞑。三子之能,咸尽于此。”[1]76林希逸亦云:“言三子之技皆精。几,尽也。言其智于此技极其尽也。”陈鼓应注:“这里向来有两种断句法:(一)三子之知几乎,皆其盛者也;郭象注:‘几,尽也。’意即这三个人的技术达到了顶点。依郭注则以‘几乎’断句。(二)三子之知,几乎皆其盛者也;武延绪说:‘几乎’二字,疑当连下句读。释德清注本与林云铭注本等正以‘几乎’二字连下文为读。若依郭注断句,则前后两句重复,故当从(二)。”[6]68
综合而论,在这一问题上,晋至宋,以郭象、成玄英、林希逸为代表的较早的注家,将“几”字释作“尽”;而明、清至今人陈鼓应等学者又将“几”字解释为“差不多、几乎是、算得上”等,且在断句上也有了新的认识。
然而,笔者认为,这些解释以及新的断句,均值得商榷。参照这几句话的前后文,以及《齐物论》全篇主题,这里的“几”,当指万物所由产生的极其微小的、原初的基本物质,或“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13]288。可释作“几微、先机、征兆、迹象”等义,又引申为事物未形成之前或事件未发生之前的雏形或趋势等。 此处的“知几”,就是“见微知著”,指得道者那种先知先觉的智慧。“三子之知几乎”,意思是说:昭文、师旷、惠子三人都是可以预知未来的明道、体道之人。依据如下:
1.《周易·系辞传下》:“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关于其中的“几”字,周振甫注:“几,预兆。”[14]264
2.贾谊《新书·审微》云:“善不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明者之感奸也蚤,其除乱谋也远。故邪不前达。”又云:“老聃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管仲曰:‘备患于未形。’上也。语曰:‘焰焰弗灭,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于微,此也。事之适乱,如地形之惑人,机渐而往,俄而东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见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缪千里也。”锺夏注云:“机渐而往,犹言由始而往。《礼记·大学》注:‘机,发动所由也。’《素问·离合真邪论》注:‘机者,动之微。’《尔雅·释诂》:‘渐,进也。’”[15]76
3.刘勰《文心雕龙·论说》:“次及宋岱、郭象,锐思于几神之区,夷甫、裴頠,交辨于有无之域;并独步当时,流声后代。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评价魏晋玄学“贵无”论与“崇有”论两家学说,一方面批评二家极端思想之弊,同时又赞扬他们的思辨高度几乎达到了佛教空观论的最高境界。这里,刘勰说郭象“锐思于几神之区”“动极神源”,无论是“几神之区”,还是“神源”,都可以注解《齐物论》“三子之知几乎”这句话。
4.苏轼《范增论》论范增“亦人杰也”,认为范增鸿门宴后,决然以告老还乡为借口,弃项羽而去,才是他真正的明智之举,不然,必遭项羽杀害。同时,苏轼又认为,作为项羽的第一谋臣、号称“亚父”的范增,落得如此下场,又是他的愚蠢——脱离楚霸王太晚,没有把握好最早、最佳之时机。他应该在项羽举事之初、杀害卿子冠军宋义时,即看出项羽迟早会抛弃并加害于他的苗头,而毅然离开。对此,苏轼论到:“(项)羽之杀卿子冠军也,是弑义帝之兆也。其弑义帝,则疑(范)增之本也。”“(范)增始劝项梁立义帝,诸侯以此服从,中道而弑,非(范)增之意也。夫岂独非其意,将必力劝不听也。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项)羽疑(范)增,必自是始矣。”于是,苏氏论定:“(范)增之去也,当于(项)羽杀卿子冠军时也。”并引证说:“‘知几其神乎’?《诗》曰:‘相彼雨雪,先集维霰。’”“相彼雨雪,先集维霰”语出《诗经·小雅·頍弁》,意思是说,雨雪在形成和降落之前,是先有云雾汇集或小冰粒的阶段。显然,《周易·系辞传下》和《诗经·小雅·頍弁》,都是先民先知先觉的智慧结晶,苏轼在征引时就是将“几”字理解为先机和征兆的。
5.在《庄子》整部书中,“几”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范畴。《至乐》篇:“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蠙之衣……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这里的“几”字,即作名词解,指原初的一种低级生命体。而其中的几个“机”字,马叙伦、胡适都认为当为“几”字,即“种有几”之“几”。崔大华《庄子歧解》:“几,微也。谓物种皆有几微生成。胡适:‘种有几’的‘几’字,当作‘几微’的‘几’字解。《易·系辞传》说:‘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正是这个‘几’字。‘几’从‘丝’,‘丝’从‘么’,本象生物胞胎之形。我以为此处的‘几’字,是指物种最初时代的种子。(《中国哲学史》)马叙伦:《寓言篇》‘万物皆种也’,是此‘种’字谓万物之种也。几者,《说文》曰:‘微也,从二么。’么,小也。从二‘么’,故为微也。是‘几’者,谓种之极微而万物之所由生者也。”[4]500正是在上述意义下,“几”又引申为事物或事件未出现、未发生前的苗头、先兆、迹象等。《应帝王》篇“列子与神巫观道于壶子”的寓言中,有“是殆见吾杜德机也”“是殆见吾善者机也”“是殆见吾衡气机也”。此寓言同样见于《列子·黄帝》篇,而三个“机”字,均作“几”[16]41,正是苗头、先兆、迹象等义,《列子·说符》篇所谓“圣人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来。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更可作为互证。
6.至今豫、鲁、苏、皖交汇地带,特别是以商丘为中心的豫东地区,方言词中仍有“虮”或“虮子”之称,指虱子的虫卵,虱子还没有完全形成的一种生命体。文献中这类的指称也很多,如《韩非子·喻老》:“甲胄生虮虱,燕雀处帷幄,而兵不归。”《淮南子·虮虱》:“牛马之气蒸,生虮虱。”曹操《蒿里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庄子·在宥》篇:“灾及草木,祸及止虫。噫,治之祸也。”其中的“祸及止虫”之“止”,即“几”,音近通假[17]。庄子这里是批评儒家的所谓“治天下”,很多都是过度的干预,必然带来严重祸患,灾难甚至会殃及维系自然界的最小、最根基的生命体。
由以上可知,经验哲学思想极其发达的中国先民,在生存意识方面也是极具抽象之思和忧患感的,因而,思考问题常常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未来意识。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几”已经作为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名词在广泛使用,“知几”更作为一个语法关系紧密的动宾词组,出现在早起文献中,不可分割断读。因此,笔者认为,将《齐物论》此处的“几”字,释作副词“尽”,或将“知几”二字断开理解,都是扞格不明、有伤文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