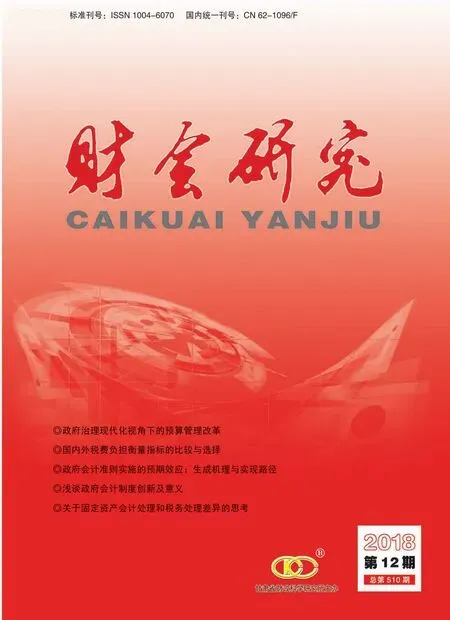关于固定资产会计处理和税务处理差异的思考
■//毛 懿 高 悦
在实务工作中,固定资产的会计和税法规定的差异使得企业需要额外注意其中的涉税“地雷”,典型如固定资产会计和税法折旧差异、融资租赁方式下固定资产的会计与税务处理差异、固定资产转变用途后的增值税进项扣除及后续折旧税前扣除等。本文以上述主要涉税风险点出发,解析相应的会计和税务处理,提出会计准则和税务规定进行协调的建议。
一、固定资产会计处理和税务处理现行差异概述
对于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和税法规定的冲突,在进行所得税申报时则要求以税法规定为准,告诫企业在运营固定资产时需要准确拿捏固定资产涉税处理规定,避免不必要的违规损失。
(一)取得环节
购置环节中,会计准则强调历史成本观,初始入账以构建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发生的一切合理、必要支出。而税务机关则强调计税基础观,不同途径取得的固定资产计税基础构成存在较大差异,虽然大多是以会计核算中的“历史成本”直接作为计税基础,但也存在某些方式下的固定资产会计入账价值和计税基础是不一样的,如融资租赁形式取得的固定资产,税法上要求以双方签订合同所约定的付款总额和承租人在签订合同时发生的直接费用作为计税基础,与会计处理上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和该资产的公允价值两者孰低者作为入账价值存在显著差异。再如存有弃置义务的固定资产会计入账价值需要考虑到将来资产弃置时发生的支出折现值,而税法上在弃置义务未确定发生时不予在固定资产基础价值中认可。
(二)持有期间
会计准则要求企业对自身拥有的所有固定资产按月计提折旧,但已提足折旧额却仍在使用的固定资产以及单独计价入账的土地除外。折旧适用方法可以是工作量法、年限平均法、年数总和法以及双倍余额递减法,折旧方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列举3类不得计算累积折旧进行税前扣除的固定资产范围来反向推导出允许税前计算折旧扣除的固定资产范围,对比会计准则和税法规定可以发现,允许税法折旧的固定资产范围显著小于会计准则规定应该计提累积折旧的固定资产范围,同时对于加速折旧方法(年数总和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在税法上有严格的适用规定,对于固定资产适用的折旧年限税法上亦有最低年限限制,而会计准则在折旧方式和折旧年限赋予财务人员更多的职业判断和选择空间。最后,企业在持有固定资产时,会计准则基础谨慎性要求企业考虑资产的减值迹象,足额提取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而税务上却并不认可企业各种提取减值准备行为。
(三)处置环节
依据会计准则规定,固定资产的处置一般通过“固定资产清理”具有中转性质的科目结束使命,应当在出售、转让、报废固定资产或者固定资产发生毁损时将处置现金流入扣除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计入当期的“处置非流动资产损益”。而企业所得税则要求企业在处置固定资产时,将“处置净收入—计税基础”后的余额纳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显然,在固定资产的处置环节,亦存在会计损益和税务损益的不同,需要企业进行准确的核算记录。
二、融资租赁方式下固定资产的会计与税务处理差异
租赁是指在双方约定的期间内,出租人将资产的使用权让与承租人并获取租金收入,而承租人以支付租金为代价取得资产的使用权的一项经济活动。企业会计准则要求租赁双方在租赁开始日根据租赁资产所有权相关的风险和报酬转移情况,区分“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进行会计处理。对于融资租赁的界定,《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规定了五项典型的判断标准,对于符合一项或多项标准的,应当认定为融资租赁,承租人需要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要求将通过租赁取得的固定资产纳入自有固定资产核算范围并在持有期间内进行折旧,固定资产的初始入账成本应该是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和该资产的公允价值两者孰低者,并将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作为长期应付款的入账价值,其差额计入未确认融资费用。
案例1,甲公司2016年12月31日通过融资租赁形式取得某固定资产用于管理活动,公允价值200万元,租赁期自2017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共计10年,每年12月31日支付年不含税租金25万元,适用增值税率17%,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193.0434万元,税法规定折旧年限为15年。为简化计算,资产折旧按年限平均法,折现率为5%。
取得固定资产时,确认固定资产180万元,长期应付款220万元,未确认融资费用40万元。
借:固定资产—融资租入资产 1,930,434
未确认融资费用 569,566
贷:长期应付款 2,500,000
自2017年1月1日开始按月计提折旧,计入当期管理费用。
借:管理费用 16086.95
贷:累积折旧 16086.95
2017年12月31日,支付租金并确认当期分摊的财务费用。
借:财务费用 96521.7
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96521.7
借:长期应付款 25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42,500
贷:银行存款 292,500
依据《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相关规定,企业购进贷款服务所产生的进项税额不得自销项税额中抵扣,比较企业通过金融机构贷款取得资金再行购买情形,通过融资租赁不止可以抵扣标的资产流通环节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更可以将租金的“利息”部分纳入增值税抵扣链条,降低税负。而根据《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是以双方所签订合同约定的租赁付款总额和承租人为签订合同所发生的直接费用作为计税基础,合同未约定租赁付款总额的,以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承租人为签订合同所发生的直接费用作为计税基础,实质上是将融资租赁资产行为等同于分期购买固定资产进行税务处理。这将导致企业按照会计准则计提的累积折旧和分摊的未确认融资费用需要进行所得税前扣除调整,而允许扣除的税前折旧应该是依据计税基础计算得到的。
因为本例固定资产折旧能够完全反映记录在损益类科目,税务调整相对便利,但实际如果固定资产累积折旧额计入制造费用,再通过产品成本流转到营业成本上,由于产品完工差异和生产销售不匹配将导致仅按年度平均累计折旧直接入税前扣除实际和企业收入不相匹配,忽视经济活动的实质换取核算的便利性有待商榷。但目前而言,会计和税法规定的差异要求企业在做好财务记账的同时,也要注意在涉税风险面前理清业务过程规范纳税申报工作。
三、固定资产转变用途时的增值税处理及后续累积折旧的争议
税法规定,原已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发生用途改变(如专用于简易计税项目、集体福利、个人消费及免征增值税项目)或发生非正常损失,应当做增值税进项转出处理,适用公式(1)。相反,当原不能抵扣且没有抵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发生用途改变使得可以按规定进行增值税进项抵扣,则在企业具备合法有效的增值税扣税凭证的前提下,可在用途改变的次月计算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适用公式(2)。

案例2,甲公司2016年5月31日取得一处房屋用作生产车间,取得时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价款1200万元,增值税额132万元,房屋使用年限为20年,折旧方式适用年限平均法,符合税法规定,2017年12月底决定改造为职工宿舍(管理人员)并于当月投入使用。
取得固定资产,不动产进项税额适用分次按比例抵扣,当月抵扣40%,待到第13个月抵扣剩余60%。
借:固定资产—房屋 10,0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528,000(132万×40%)
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792,000(132万×60%)
贷:银行存款 13,300,000
自2016年6月开始,每月计提折旧。
借:制造费用 50,000
贷:累计折旧 50,000
至2017年5月,抵扣剩余60%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792,000
贷: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 792,000
后续固定资产转变用途,做进项税额转出处理。截止2017年12月底房屋净值=1200-1200/(20×12)×18=1110万元,进项税额转出金额=1110×11%=122.1万元,此时房屋账面价值=1110+122.1=1232.1万元,固定资产剩余折旧期限为222个月。
借:固定资产 1,221,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1,221,000
但值得注意的是,固定资产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是否抵扣将导致其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发生变化,但如何在后续持有期间内计提折旧进行所得税前抵扣却未有明确的规定,存在会计和税务处理的“灰色空间”。在实务当中,主要存在两种会计处理方式:
一是参考固定资产暂估价值入账后金额变化的“未来适用法”,在新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下,重新计算每月应计提的累计折旧金额并适用于剩余折旧期间。
借:管理费用 55,500(12,321,000/222)
贷:应付职工薪酬—职工福利 55,500
借:应付职工薪酬—职工福利 55,500
贷:累计折旧 55,500
二是参考“追溯调整法”,重新计算固定资产整个持有期间每月应计提的折旧,并与前期已计提折旧比较实行“多退少补”,差异一次性计入用途改变后的首月累积折旧中。截止固定资产转变用途时已累计折旧金额=5×18=90万元,重新计算每月应计提的折旧金额=(1200+122.1)/(20×12)=5.50875万元,截止当前应有的累积折旧金额=99.1575万元,差异金额为91575元。即首月累积折旧计提数为55087.5+91575=146662.5元,后续期间每月累计折旧数仍为55087.5元。
借:管理费用 146662.5
贷:应付职工薪酬—职工福利 146662.5
借:应付职工薪酬—职工福利 146662.5
贷:累计折旧 146662.5
由于会计准则和税法规定的空白,上述两种会计处理方式均有被实务工作者采用,但本文更倾向于第一种会计处理方式,固定资产的初始入账环节无瑕疵,仅因固定资产用途改变而需要进项税额转出导致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变化属于当期新发生的事件,并不构成前期差错和会计政策的变化,无需调整原已计提的累积折旧数,而理应在后续持有期间依据新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计提折旧和税前扣除。同时,即使按照第二种会计处理方式需要调整原应计提的折旧金额,也不应将前期的累积折旧差异91575元直接附加在用途改变后的首月折旧金额上,而是应该调整相应的折旧对应科目—制造费用,但如此一来将导致需要账面调整的科目范围无限循环,陷入“可靠性”和“重要性”的矛盾之中,亦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最后,随着原使用时间的拉长,在转变固定资产用途时需要调整的累积折旧差异更大,如若于2027年5月底发生固定资产用途转变(具体情形如案例2),选择第二种会计处理方式将产生累积折旧差异33万元直接计入用途改变后的首月累积折旧金额数,严重扭曲了会计信息质量。尽管如此,若从企业税收筹划角度来看,当前选择第二种方式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税收节约。
四、结论
由于制度设计出发点的不同,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侧重会计信息决策有用观,降低财务信息生产成本,赋予了企业更多的职业判断和选择的空间,而税务规定则侧重于方便开展税务工作和保障国家税收不流失,这也导致同样固定资产的核算工作却存在会计和税务两套体系方法且二者矛盾突出。对于某些待商榷、可调和的矛盾,需要从税收立法精神出发,审视会计和税务内在关联、剖析并完善税法规定的不足。如在融资租赁取得固定资产方面,税法仅将此认可为“分期购买固定资产”,虽然便于税款的征收管理,但却使得企业实际成本与收入匹配脱离,忽视经济活动的实质换取核算的便利性广受质疑。再者,在固定资产转变用途时的因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和抵扣处理导致后续累积折旧的计算差异方面,却未有明确的会计准则规定和税务处理规则,监管盲区和利益的驱使无疑是在诱导企业采纳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节税效应的会计和税务处理方式,扭曲了会计信息的质量,同时可能导致不同税务机关之间判断标准不统一。
站在企业角度,强化纳税风险意识十分重要,固定资产涉及取得、持有、处置等环节,对于固定资产的折旧范围和方式、年限,会计准则和税法规定的差异需要财务人员界定清晰,在准则面前加强职业判断,选择符合企业现实情况的会计处理方法,而在税务规定面前更需要以政策为导向,依法依规处理好固定资产涉税风险,既要避免因偷逃税款受到税务处罚,又要充分利用税务规定的税收筹划空间节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