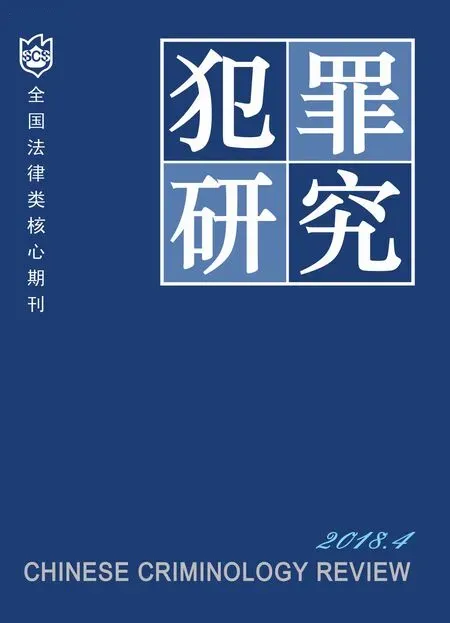暴力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以美国“街头守则”为视角
李 杨
引 言
世界上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有属于自己占主导地位和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主流文化之外还存在一定的亚文化范畴,亚文化是相对于主流文化而存在的。亚文化通常被定义为与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非大众文化。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冲突,是诱发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有着与主流文化相对立的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和特定的传播范围,有着自己的行为评判标准、规则及其禁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能简单地把亚文化等同于犯罪文化,犯罪文化是亚文化的极端形式,但亚文化与犯罪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长期生活在以亚文化为主导的社会环境中,将逐步形成对于亚文化的认同,按照亚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行事,从而引发犯罪行为。
美国学者安德森(Anderson)提出了一个关于“亚文化暴力”的当代解释。他利用在贫民区的实地研究认为,在美国的贫民区存在一个“街头守则”(The Code of the Street),即在许多经济落后的社区,暴力文化的威胁非常高,而且通常情况下,人们不能完全指望警察保护,在这种“街头”环境中,青少年无疑属于潜在的“受害者”,他们会遵守所谓的“守则”以阻止他人来伤害自己。笔者基于安德森提出的“街头守则”理论认为,家庭文化、青少年的社交文化、亦或是青少年形成的叛逆心理,这三个方面极易伴随着暴力因素,青少年潜移默化地受此影响,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一、“街头守则”的形成及其核心
“街头守则”理论源于美国“街头”暴力亚文化的环境,即便是在美国这样经济社会高度发达的国家,其贫困社区中依旧涌现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其中,没有一个问题比充斥暴力的犯罪行为更加严重,例如斗殴、抢劫、枪击等犯罪,所有这些犯罪行为都可能让无辜的居民成为受害者,且现在这种现象已经逐渐影响到更多的郊区居民和城市居民。
一般来说,在贫民区生活的居民难以支付生活费用,而且他们还面临着种族歧视、应对着毒品的猖獗,久而久之,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居民更加缺乏对未来的希望。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青少年面临着被不良文化侵袭的风险,这种亚文化环境也意味着,即使部分青少年的家庭倡导主流价值观,青少年也必须能够在面向不良的“街头”环境中把控自己,警惕自己被同化。
所谓的“街头守则”,是自发形成的一套管理人际公共行为的非正式规则,这种规则默认了人们可以用“适当的”方法去应对侵害,默认那些有侵略倾向的人通过暴力冲突的方式解决问题。数据表明,安德森讨论的以下一些因素有助于采用该守则:行为人是男性、贫困、受到父母的严格监管、成功机会受到限制、遭受歧视、暴力的受害者以及参与暴力行为——尤其是有参与暴力的同伴。①See Francis T. Cullen, Robert Agnew, Criminological Theory: Past to Present: Essential Reading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P. 143.“守则”不同于“文化”,一旦违反“守则”,就会受到惩罚。因此,对守则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御外界的侵袭。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具有主流文化导向的家庭虽然非常反对“街头守则”的价值观,但是他们还是不得不鼓励他们的孩子去熟悉这种“规则”,最重要的目的在于防止他们的孩子受到亚文化环境的侵害。
“街头守则”的核心是将“尊重”视为一种“权利”。特别是青少年,如果长期处于暴力环境中,一旦他们觉得自己得不到周围人应有的重视,“尊重”被视为几乎是一个难以获得的外在实体时,他们就会通过自己的手段去争取“尊重”,只不过他们获得“尊重”的手段往往也是通过暴力方式。通常,一个人可以通过他的外表,包括他的穿着、举止和行为方式来改变他在别人心中的形象,并且可能获得其他人一定程度的尊重。而“街头守则”实际上也是为获得“尊重”提供了一个框架,只不过在这个框架内,整个的文化环境接受崇尚暴力的价值观念,鼓励奉行暴力,惩治偏离暴力的行为。因此,一旦青少年受到暴力亚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就会认为主流文化及其带来的影响是一种异化,从而导致对正常社会无从适应。
二、家庭文化塑造青少年的人格
暴力亚文化寄居于生活的许多方面,其中家庭环境极易成为充斥暴力亚文化的重要方面。在安德森提出的“街头守则”理论中,他将家庭分为“体面家庭”(Decent Families)和“街头家庭”(Street Families)两种类型,“体面家庭”和“街头家庭”在实际意义上代表着价值取向的两极,是两个对立的概念类别,这两种不同类别的家庭对青少年人格的塑造有很大的差异。“家庭既是生活的港湾,也可以变成犯罪的温床。”②康树华、张小虎:《犯罪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6页。
(一)“体面家庭”对孩子的文化教育
一般来说,所谓的“体面家庭”更倾向于全面地接受主流价值,并将主流的价值灌输给他们的孩子。毫无疑问,“体面家庭”的经济条件比“街头家庭”更好,他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在物质基础得到满足之后,他们更重视对精神文化的追求。一方面,他们重视努力工作和自力更生,打造自己的事业;另一方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去教堂,并对他们孩子的教育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对主流社会有一定的信心,他们寄希望为他们的孩子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体面家庭”的父母在教育子女的做法上往往更严格,鼓励孩子尊重权威和行走笔直的道德线,他们对社会上的热点事件有强烈的关注,并提醒他们的孩子要学会观察和从中学习。同时,他们自己对别人保持礼貌和体贴,并且教育他们的孩子用同样的方式待人接物。概言之,“体面家庭”更多的是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并且重视孩子的教育,以求通过优良的教育完成对孩子人格的塑造。
(二)“街头家庭”对孩子的文化影响
相比之下,所谓“街头家庭”的父母往往表现出对孩子缺乏考虑,毋庸置疑,他们也非常爱自己的孩子,但其中许多父母发现很难与孩子的需求相协调。这些家庭更多的是去适应街头的“守则”,父母可能会以规范的方式积极地将他们的孩子社会化,从而令孩子在“守则”中根据自己的价值去评判他人。
在“街头家庭”的环境中,由于父母自身文化水平等各种因素的局限,一些父母容易对孩子使用言语辱骂和身体的惩罚,在惩罚之后又缺乏任何耐心的沟通和有效的解释,他们自己都没有认识到自己采用了不当的教育方式。其实,父母们之所以会打孩子,特别是如果孩子违反了他们的“行事准则”,不是因为他们讨厌孩子们,而是因为这是他们控制和教育孩子们的方式。社会上许多父母都认为男孩子必须要打,但他们难以把握使用“暴力”的边界,当造成虐待儿童的严重后果时还认为只是父母在教育孩子。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父母的行为会潜移默化的误导孩子:孩子会认为在解决任何人际关系问题时,采取富有侵略性的言语威胁或行为暴力是解决问题快速而有效手段。
更加糟糕的是,有些家庭的父母极度不负责任,放任孩子不闻不问。这些家庭的孩子,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长大,有时尝试以周围的成年人作为榜样,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打架。在亚文化的环境之中,可能充满抱怨、愤怒、言语纠纷、身体侵略,青少年观察这些行为,可能认为这些行为是正确的。青少年模仿能力强,很快学会还击那些惹怒他们的人,而且以这种“以牙还牙”的心态占据优越感。为了生存,为了保护自己,青少年们认为有必要以暴力的方式处理逆境,这时候,青少年可能已经学会了在“街头”法则中生存的第一课:生存本身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更不用说被尊重了,你必须为你在世界上的地位而战。在这样充斥暴力的环境中,青少年很容易因为暴力行为触发法律的警报线。
安德森的研究表明,事实上,绝大多数的“街头家庭”试图靠近“体面家庭”的家庭模式,但是,他们的经济资源不仅极其有限,而且他们也很容易荒废所拥有的一切,在最绝望的情况下,受挫于生活开销,甚至沉浸于酗酒、毒品的滥用,一些人由此走入自毁行为。换言之,“街头家庭”在生活的困境与压迫之下,很容易缺乏自我控制,自暴自弃。
家庭是青少年接触最早的群体关系,是青少年最重要的教育来源,影响着青少年的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和人格的塑造。“长期生活在吵闹、暴力的家庭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受此影响,传递给青少年的家庭教育是厌恶与憎恨,而不是爱与包容。”①杨宗辉主编:《当代犯罪学前言问题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4页。家庭环境如果充斥着暴力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为孩子提供反面的学习范例,即在青少年自我意识形成的敏感阶段,无视其独立的人格,强化其逆反心理,令未成年的孩子更易于寻求社会亚文化圈获得认同和自我满足。①参见卢建平:《中国犯罪治理研究报告》,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页。忽略健康积极的家庭文化氛围,父母对孩子没有正确的引导途径,孩子会形成以暴制暴的思维模式,实施暴力犯罪。
三、同辈社交浸染青少年的行为
当“体面家庭”的孩子和“街头家庭”的孩子聚在一起时,会发生一种社交洗牌,孩子们有机会去接触和体验另一种生活方式。孩子们的行为固然会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但家庭环境并不能决定孩子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青少年有自己的朋友圈,在街头的玩耍中、在学校里以及在青少年团体中,青少年相互之间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孩子们通过他们的玩耍,将他们的个人生活经验投入到一个共同的知识库中,他们会对看到的东西进行观察,并将自己的技能与他人的技能相匹配。他们也能细心察觉到其他人的言语或身体的争斗,之后他们注意比较和分享他们对事件的理解,进行不断的学习。同辈社交的相互影响可以从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寻找理论根据,即“犯罪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人的犯罪行为是在社会生活中通过实施或观察犯罪行为而学习获得的;人们是否进行犯罪行为,深受社会环境中的有关因素的制约。这一理论尤其适合于解释暴力犯罪。”②吴宗宪:《西方犯罪学》,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14页。
(一)竞争赢得“尊重”
青少年在社会交往中实际上也处在一个竞争的系统中,在这个系统中通过竞争的方式来赢得尊重。在暴力亚文化的社会环境中,保存着许多攻击性的习俗,它们包括奖励那些最好斗最敢斗的成员的内容。由于攻击行为在这里受到了强化,所以其中发生攻击行为的频率很高,并逐步演化为暴力犯罪团伙。
竞争的重要方式是夺取他人的财产,看似普通的对象可以成为远远超过其货币价值符号的价值财产,通过竞争夺取的财产可以象征着侵犯某人的能力。其一,财产不一定是有形的物品,它可以是另一个人的荣誉感、它可以是一场战斗的胜果、它可以是某种标准的强加,当一个人可以从另一个人那夺取财产,然后炫耀它时,他通过作为该财产的所有者或控制者而获得一定的尊重,但是这种所有权的宣示可能又会激起其他人的挑战。其二,对于夺取的财物,不论是利用其外在价值或是内在价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游戏由谁控制就标志着谁是当前的赢家,这种竞争游戏经常会在“街头”环境中上演。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提高自己的程度取决于他把另一个人能力的降低,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街头”环境中,一旦青少年感觉很少获得尊重,而每个人又通过竞争来获得肯定,他们的自尊感就容易受到伤害,青少年渴望这样的尊重,他们将冒着违法犯罪的风险获得和保持这种“尊重”。在“街头”环境中,很多男性青少年会相互之间组成结构松散的群体一起活动,并经常与周边地区的青少年打架斗殴,形成团伙犯罪。
(二)女性青少年犯罪增加
近些年来,在青少年犯罪中,女性青少年犯罪日益突出,引人注目。在与男性朋友的交往中,越来越多的十几岁的女孩正在模仿男孩,因为女孩和男孩的目标是相同的——获得尊重,他们试图学习男孩们惯用的方式来达到目标,包括学习男孩子的谩骂和使用暴力来解决争端。这也体现出女孩子的独立地位在逐渐加强,女孩子通过自己的行为证明他们可以像男孩子一样独当一面。
女性青少年犯罪除了数量上升外,还呈现出“男性化”的特征,一些少女开始涉足过去由男性“一统天下”的某些违法犯罪。①参见宋浩波、靳高风:《犯罪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97页。一般认为男孩子才和暴力相关,通常如果一个女孩受到攻击,她会求助于信赖的男生。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女孩完全可以自己解决问题,甚至要求他们的男性朋友教他们如何用暴力打击别人。与男孩子不同的是,女孩子之间的冲突很多是源于他人背后的非议和八卦,女孩子对个人被负面性地评价非常敏感,基于此,她们可能会报复。虽然,许多非议可能不会带来实质性的伤害,但是,这种非议会损害女孩子的名声,为了免受诽谤,防卫者通常学习她们周边的男孩子用一场暴力“战斗”来解决问题。另外,除了暴力犯罪,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受到周围男性朋友的唆使,或者是为了朋友间所谓的“义气”,卷入毒品、盗窃、敲诈勒索、诈骗等犯罪。
四、叛逆性格助长青少年的犯罪意志
在“街头”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受到“街头守则”的影响根深蒂固,他们认为“街头守则”的标准是城里唯一的游戏。在缺少主流社会重视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和主流社会产生隔阂,久而久之,他们会在一定程度上拒绝和蔑视主流社会,在处理这种蔑视和拒绝时,一些青少年会有意识地投入自己更多的精神与情感,失去和主流社会“沟通”的兴趣,自主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文化来对抗主流文化,用所谓的“反叛”来捍卫他们的“自尊”。
青少年正处于生理上的发育期和心理上的叛逆期,二者直接存在阶段性的冲突,这个时期的他们自控能力差,做事情容易冲动,不愿意被束缚。美国学者伍顿与布拉扎克在著作中认为,青少年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他们很大程度上对主流社会感到厌倦、与传统社会相隔离所致。犯罪成为刺激反叛行为的一种形式,这些青少年试图反对在他们看来几乎是死水一潭的平庸生活。他们打破约束、挑战权威、逃避制裁,所有这些使他们感到兴奋和刺激,但是,当大多数青少年以较温和的方式实施犯罪时,有一些青少年则实施较为严重的盗窃犯罪和暴力犯罪。②参见[美]罗纳德·J.博格、小马文·D.弗瑞、帕特里克亚·瑟尔斯:《犯罪学导论——犯罪、司法与社会》,刘仁文、颜九红、张晓艳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0-311页。
最可怕的是,青少年将这种叛逆心理演变为无所敬畏的生活态度,这种无所敬畏的态度会让青少年遇事缺乏理智,动辄用暴力作为解决争端的主要手段。甚至,在面对执法者时,许多“街头”出身的青少年并不在乎警察,他们认为去监狱不仅没有损失,反而可以凭借“蹲监狱”的经验来提高在“街头”的声誉,即有过蹲监狱的经验,在他们的朋友圈更容易获得“尊重”。许多面向街头的青少年更在乎来自朋友圈的“尊重”,而不是警察的手铐,这种无所敬畏的态度对加强执法有影响。
综上所述,暴力亚文化环境是影响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因素,但是,并非意味着生活在暴力亚文化环境中的所有青少年都会无差别地吸收和信奉“街头守则”特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青少年是否会吸收和信奉这些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与其在家庭教育、社会交往、性格特点等方面的差别有关,由于存在这些方面的差别,有些青少年吸收和信奉这些价值观念,有些青少年则摆脱了“街头守则”的束缚。可见,青少年犯罪很大程度上源于青少年习得性的反应,这种反应是在社会环境中被助长和整合成为的一种习惯和人格特征。
青少年犯罪类型研究一直是犯罪学中的重要议题,在有关青少年犯罪对策的研究中,研究者大都十分强调净化暴力环境的重要性,尽管这样一种新动向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但是学界对这一问题并未能及时给出有深度的解释和有效的对策建议。正如日本学者上田宽所言,“不管怎样,文化基准多元化的结果是形成了诱发犯罪和不良行为的局面,社会对此的批判变得软弱无力,对于青少年而言,丧失了帮助他们形成道德性人格的稳定机制基准,这关系到深刻的人格问题,远远超过了‘犯罪学’的范畴。”①[日]上田宽:《犯罪学》,戴波、李世阳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