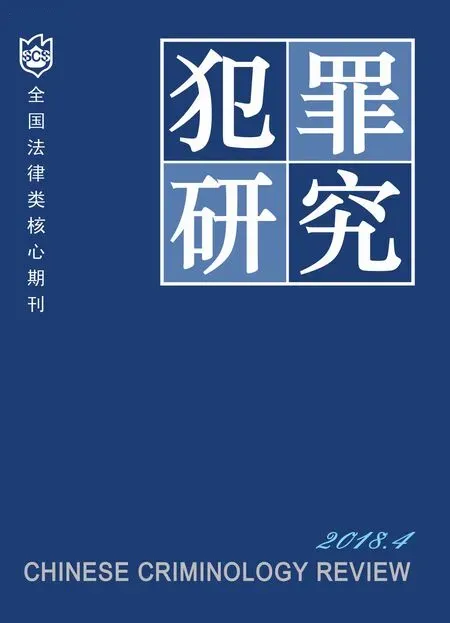“犯罪分子”称谓之弊探讨
戚兴伟
引 言
“犯罪分子”的称谓,在我国法律中的使用较频繁。我国《宪法》(第28条)和《刑事诉讼法》(第2条)各1处,《刑法》共有50余处使用“犯罪分子”称谓一词。“犯罪分子”一词在法条中泛指为已判有罪的受刑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等多重含义。在刑法典中已然出现概念的混乱不清、极易导致刑事案件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辩护等多方面陷入“有罪推定”的研判怪圈。
“犯罪分子”称谓是我国建国初期特定历史时期维护社会秩序、打击犯罪活动的需要。该称谓已不适宜当下建设法治国家的环境,应退出历史舞台。本文从侦查、审判两类司法执业立场出发,探究“犯罪分子”称谓带来的弊端,故此得出急需在刑事法典中剔除“犯罪分子”一词的迫切性。
一、“犯罪分子”称谓属政治术语
(一)“分子”一词的政治属性
所谓“分子”是指属于一定阶级、阶层、集团或具有某种特征的人: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积极分子。①《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4页。“分子”一词源于近现代社会政治生活,始于“五四”运动前后,革命战争年代为常用如:反动分子、右倾分子、机会主义分子等;建国初期的政治运动有所发展变化如: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右派分子、贪污分子、反动党团分子、破坏分子等;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使用“分子”一词“……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广泛使用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如:黑帮分子、打砸抢分子、修正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保皇分子、特务分子、臭知识分子、 动摇分子等。“分子”被当作政治标签使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的产物。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依法治国作为党的治国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但“分子”一词仍然在 1997年刑法使用“犯罪分子”“首要分子”的次数高达几十余处。公众将“分子”使用于各种书面和口头表达,如:积极分子、犯罪分子、知识分子等。
(二)“犯罪分子”是贬义的政治术语
“犯罪分子” 产生于我国特定的政治社会生活,反映了特定时期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和真实性。不论从“犯罪分子”称谓的产生的社会背景分析,还是从使用实际效果分析,都彰显出浓厚的政治色彩。“犯罪分子”不是法律术语。法律语言应准确、清晰、抽象和情感中立。准确和清晰要求词义清楚,概念内涵、外延准确,无歧义;抽象要求法律语言客观;情感中立要求法律语言不能包含褒扬、贬斥等感情色彩。“犯罪分子”称谓,缺乏准确和清晰,具有较强的政治含义并含贬义,使“犯罪分子”一词缺乏中立性。
二、“犯罪分子”一词对刑事司法实务人员的影响
(一)对刑事侦查人员在收集证据时的影响
1.《刑法》总则中“犯罪分子”一词频繁出现,政治术语出现在《刑法》条文中,打破了刑事法律条文的严谨、清晰的特征,容易使刑侦人员对刑事法条的阅读、理解、记忆中形成惯性思维,既对“犯罪分子”概念混淆不清的现状隐性的心理接受并认同。例如《刑法》第23条第1款的规定“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该条文中的“犯罪分子”跃然纸上时,侦查的方向已经确定为有罪,对无罪的证据往往被忽略甚至无视。这与刑侦人员的职业能力无关,而是被“犯罪分子”一词潜移默化的影响的结果。若此条款中的“犯罪分子”改为“行为人”,既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内容和表达更为准确,刑侦人员不仅会对“行为”展开有罪、无罪、罪轻证据的收集,也会对“人”的证据进行收集,而不是对“犯罪分子”展开调查。
2. 再以刑法第394条规定的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和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为例。对本罪中“犯罪分子”的理解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本罪中的“犯罪分子” 是指实施了犯罪行为,尚未受到追诉的犯罪嫌疑人;另一种观点认为,本罪中的“犯罪分子”,应指触犯刑法而应当或已经受到刑罚处罚的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第三种观点认为,本罪中的“犯罪分子”仅指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并进而认为本罪罪名表述欠妥。亦有有学者对刑法第417条规定的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相同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①王建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罪名表述欠妥》,载《检察日报》2003年4月2日。众所周知《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该条文并非典型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表现,但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未经人民法院定罪判刑的情况下,不能称其为犯罪人或罪犯。“犯罪分子”是亦有犯罪人或罪犯的代指,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包含在“犯罪分子”之内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②罗开卷:《“犯罪分子”称谓反对论》,载《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另一方面,刑侦人员在收集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时,要同时证明两个犯罪行为。首先要收集“毒品犯罪”的相关证据,包括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犯罪行为。其次要收集本罪中包庇的客观行为表现。笔者认为该条文中的“犯罪分子”若是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证明范围尚属正常,若“犯罪分子”仅指已经被判处刑罚的犯罪人或犯人,就会出现在追究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之前的毒品犯罪人已由人民法院判的要求。这样处理照顾到了法院判决的谨慎和审慎,但不利于打击犯罪,也有刑事司法适用僵化之嫌。
笔者认为“犯罪分子”在刑法中的出现对刑事侦查人员造成了收集证据方向的“有罪推定”,容易造成刑事侦查人员证明范围、证明要求的模糊不清现象,对后续审判工作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同时“犯罪分子”一词是刑讯逼供现象频发的因素之一,刑讯逼供不是有了“沉默权”“律师在场权”后就可剔除的司法陋习,更要从刑事立法条文的准确用语点滴入手建设刑事司法文明的大厦。
(二)对审判人员审理案件时的影响
法官作为个体不是独立于社会生活而存在。法官应当拥有对社会生活敏锐的洞察与思考;应拥有对法律条文本意的准确理解与适用;应拥有对个案研判正确与理论提升的双重职责。司法公正对刑事审判庭的法官要求更高。刑法中“犯罪分子”一词对刑事审判法官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刑法总则中近五十处使用了“犯罪分子”,容易让法官陷入一种片面的认识——“在法庭来接受审判的均是犯罪分子”。例如《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为本罪成立的主观要件,该罪的主观要件的认定实质上是对客观证据的综合认定过程,在审判实务中,对罪名的认定与量刑有一定的难度。当在案证据均不能直接证明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时,审判人员受到的刑事法律条文中“犯罪分子”会左右法官对案件证据认定起作用。法官的“先入为主”不是来自其本性,而是来自于刑法条文中“犯罪分子”的语境。我国没有陪审团制度、没有法官自由心证,当个案出现间接证据较多,无法认定时,审判人员因受到的刑事司法教育、成长背景就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犯罪分子”一词的在此时就会发挥人们意想不到的影响,这也正是通常法院较难作出无罪判决原由之一。
三、逐步削弱“犯罪分子”一词对刑事司法实务影响的思考
(一)建议将《刑法》中的“犯罪分子”称谓修改为相应的法律术语。
对《刑法》总则中抽象描述犯罪定义、犯罪形态时使用的“犯罪分子”修改为“行为人”,例如《刑法》第23条第1款“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中的“犯罪分子”修改为“行为人”;对于描述已经判决刑罚的人将“犯罪分子”的表述修改为“罪犯”,例如《刑法》第50条第2款中“……暴力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中的“犯罪分子”修改为“罪犯”;对于描述已经判决刑罚的人将“犯罪分子”的表述修改为“罪犯”,例如《刑法》分则第349条、第362条、第 417 条涉及包庇型犯罪和帮助型犯罪中包庇和帮助的“犯罪分子”修改为“犯罪的人”。①王燕飞:《刑法中的“犯罪分子”应该修改》,载《河北法学》2005年第12期。将具有政治色彩的“犯罪分子”修改为“行为人”或“犯罪的人”或“罪犯”后,将是对宪法人权保障精神的彰显,符合当下刑事司法文明的迫切需要。
(二)提高人权保障意识
《宪法》第 33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评价人权状况的指标之一为被拘禁者受到人道与尊严待遇的权利状况。“犯罪分子”这一带有侮辱性的政治标签,显然不符合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应当退出刑法法典中。将犯罪人或罪犯,甚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统称为“犯罪分子”,这种不文明的称谓包涵着对犯罪人或罪犯人格的贬损,不利于犯罪人或罪犯的人权保障。我国《监狱法》第7条关于“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的规定。无罪推定原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法治精神的重要体现,而法治精神恰恰是以保障人权为己任。①罗开卷:《“犯罪分子”称谓反对论》,载《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称为“犯罪分子”,是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权的践踏,与法治社会要求背道而驰。浙江张氏叔侄冤案中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民张高平,在法庭陈述中说出了让全场人静默的话:“你们是法官,但你们不能保证你们的子孙后代也是法官,如果这样(不改变),他们也可能有危险!”这样的警示话语足以引起我们对人权保障的深思。
四、结论
“犯罪分子”称谓系政治术语,带有人格贬损含义,已严重不符合人权保障的宪法精神。政治术语与法律术语混杂出现在刑法典中,造成刑法法律语境的丧失。法律语境的丧失改变了刑事司法一线人员的刑事思维习惯,给刑事侦查人员、刑事审判人员心理造成“先入为主”“有罪推定”的“内心确信”,这无不与“犯罪分子”一词有着密切的关系。足以说明科学严谨的法律语境的现实重要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他法律术语与“人”相统一、协调,使用“犯罪的人”或“罪犯”、“受刑人”等术语,是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和保障犯罪人或罪犯人权的应有之义。依法治国需要法治文明和人权保障,有损法治文明和践踏人权的法律规定终将被历史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