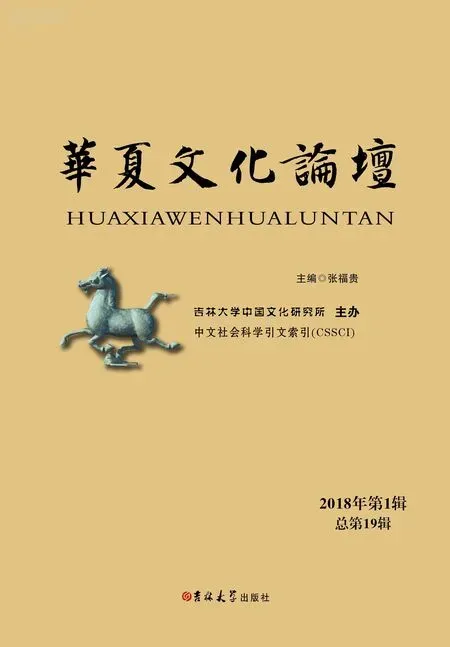进化论与中日近现代的新小说
杨文昌 苏芊芊
【内容提要】进化论对近现代中日两国小说文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小说观念的更新上。中日近现代的启蒙主义文学家都在用进化论为小说正名,并对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的特性进行了近代意义上的规约,由此,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变成了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尊贵、独立的新小说。这既是历史进化观念下对小说历史使命的重新定位,也是社会有机体论中的个性意识所带来的小说文体意识的觉醒。
进化文学观之下的文学是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认识是在历史进化观念下把文学置于时间的维度中进行考察的理论归趋,因此,历史范畴中的新与旧便自然地被移植到文学中来,于是,“新文学”观就成了中日近现代文学的首要理论问题。
“新文学”观中的“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新文学应该是独立的。文学要进化,就必须摆脱对一切外在之政治、思想的依附,从“文以载道”的旧模式中彻底解放出来,取得文学应有之位置和尊严。这也是对文学与人的关系的重新定位,是对“一般社会对于文学者身分的误认”的校正。“‘装饰品’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学者现在是站在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分子;文学作品不是消遣品了;是勾通人类感情代全人类呼吁的唯一工具,从此,世界上不同色的人种可以融化可以调和。”这方面,虽然坪内逍遥表现出了义无反顾的姿态,但因为其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所以他概括的近代小说的四大裨益中,既有可以导向启蒙的“提高人的品格”,又有指向道德说教的“劝奖惩戒”;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先觉者的态度虽然不如坪内那般决然,但因其思想精神是激进民主主义的,故而在启蒙的文学道路上并未表现出对旧势力的真正妥协。其次,新文学应该是在言文一致的语言背景下的白话文学。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言文不一致严重限制了文体的选择,文言已无法表现复杂多样的社会现实内容,已构成文学表达的桎梏。第三,新文学应该是关注现世生活的。根据进化的文学观的推理,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现世的现实生活即是文学内容的根源或表现对象,因而文学与现世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很好地表现现实生活的文学才能进化。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所以,新文学应该是“人的文学”,是以存在于群体中的个体的人为对象的,而不是为政治及伦理道德等服务的。
近现代的中日两国,通过对西方进化论的改造与吸纳并进而用于文体变革之中,不仅实现了文学语言的近代转变,同时也大大促进了两国国语的统一与定型。小说作为文体的一种,在中日两国历来是以茶余闲资甚至是奇技淫巧的面目出现的,同样是因为借重了进化论的力量,两国的小说都在各自的发展历程中实现了质的飞跃。可以说,白话文体和小说体裁的兴起,代表了两国近现代文学文体演进的突出成就,也是进化论对近现代中日两国文体演进影响最显著的方面。
进化论对近现代中日两国小说文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小说观念的更新上。这种更新,既表现在处于同一社会整体中的作者及读者的文学思想中,也表现在当时社会的文化意识中;既包含着小说文体主体性的确立过程,也包含着小说文体意义空间的近代转型。众所周知,“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但与目下小说概念的内涵、外延及所涵盖的文体意义相去甚远。真正对现代小说产生影响的言论来自历史学家班固,他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的一段话,压制了小说文体几乎两千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此文中“小说”的概念是很宽泛的,后世的“小说”概念也各有其时代性,但是,小说“浅薄”“鄙陋”的品性以及作为小道旁枝、奇技淫巧的面目还有作为底层文体的定位,无不是从班固而来。当然,班固的言论不是孤立的一己之见,它代表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两千年来的中国文学进程中,也曾出现过反对正统观念的声音,而真正具有颠覆之功的应首推严复。可以说,其与夏曾佑合作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对中国小说文体的近代转型具有规范性价值和指导性意义。从其后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到五四文学先驱发动的“文学革命”,从这些运动的理论主张,到其中逻辑论证的思维特征,都能发现严复思想的深刻印记。该文中,严、夏二人从进化论出发,对小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二人认为,书籍对于传承或者说一个民族的延续是至关重要的,而其中的记事之书“为甲”。记事类书籍之所以能发挥第一等的作用,就是因为其易传性。他们总结了记事之书易传的五大优点:第一,“书中所用之语言文字,必为此种人所行用,则其书易传。其语言文字为此族人所不行者,则其书不传。”第二,“故书传之界之大小,即以其与口说之语言相去之远近为比例。”第三,“繁法之语言易传,简法之语言难传。”第四,“言日习之事者易传,而言不习之事者不易传。”第五,“故书之言实事者不易传,而书之言虚事者易传。”二人由此得出结论,国史不易传,小说易传,所以,“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于是,小说乃至文学就成了种族延续以及社会文明进步的依托:“文章事实,万有不同,不能预拟;而本原之地,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如果说这还只是对小说与社会文明进步相始终的地位的理论论证的话,欧美以及日本的开化历史则为他们提供了有力的例证:“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所以,二人“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或译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微。”他们把小说看作优势文体,而这种“优势”又是历史进化的结果和民族进步的必要前提。二人甚至由此把小说的地位置于正史之上:“抑又闻之:有人身所作之史,有人心所构之史,而今日人心之营构,即为他日人身之所作。则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矣。若因其虚而薄之,则古之号为经史者,岂尽实哉!岂尽实哉!”从以上分析可见,这篇文章不仅涉及小说地位的问题,同时也关涉到文学内部规律问题以及对中国文学近代转型的预期。既然文学及文学实践是文明开化的必由之路,那么,在当时的民族生存困境中,文字的通用性问题,书写语言的口语化问题,文学语言的繁简即具体与概括、形象与抽象问题,文学题材的大众化问题,文学写作中的主客观关系问题,翻译与创作的问题等,都是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严、夏二人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中虽然对此没有具体的阐述与论证,但其中有关小说、文学的论断或体会,对后继者有着强烈的或明指或暗示的作用。“由《春秋》以致小说,又不可谓之非文体一进化”“使孔子生于今日,吾知其必不作《春秋》,必作一最良之小说,以鞭辟人类也。”所以,“小说,小说,诚文学界中之占最上乘者也。”“吾以为吾济今日,不欲救国也则已,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于是,“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这里,小说的地位已经远出于经史之上。由此,严、夏二人以社会有机体论为小说张目的思路已经完全清晰,小说从此也由娱乐、游戏之低俗走向思想启蒙之尊贵以致崇高。如果说此时梁启超等人的文学主张忽视了先前严、夏二人对文学主体性及内部规律的谨慎态度,从而导致文学主体性被政治使命所绑架的话,那么,五四文学先驱对“游戏文学观”及“载道文学观”的批判,则纠正了这一偏向,其主张倾向基本回转到严、夏之较为冷静、理性的思路,逐渐将新小说的发展引向既自尊又独立的方向。新文学的缔造者之中,连作为政治家的文学论者陈独秀都认识到“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所以,文学“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这也是以社会有机体论为依据的进化文学观对文学及小说作为个体存在的主体性的确认。尽管五四新文学最终还是承载了思想启蒙的社会使命,甚至还潜存着走向为政治革命服务的倾向,但文学的主体性存在确已成为五四文学意识的构成要素之一。
从现有史料来看,在日本,最早使用“小说”一词的是西周。他在介绍西洋文艺的《百学连环》一书中,分别提到了 “稗史”和“小说”,但和我们今天的看法却有很大的不同。以后则很长时间看不到“小说”一词的出现,尽管当时翻译的西方小说很多,却代之以“情史”“奇谈”“情谱”“人情话”等名称。政治小说兴盛时期,“稗史”和“小说”之名目问题渐受重视,从而出现了为小说正名的历史契机,最后终于在坪内逍遥那里有了定论。小说是日本近代文学的主流文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坪内逍遥确实堪称开日本近代文学先河的一代宗师。当然,坪内逍遥的贡献主要还在其小说理论的创设上,尤为重要的是,在他发现“小说”这一概念的同时,也发现了“小说”这一文体,“是他,最早提出了‘真’为唯一的文学理念,与封建主义的‘善’(封建主义的文学功利观)相对抗,为日本文学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成为日本小说近代转型的引路人。
由于受儒家文化及汉文学的影响,日本文学传统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尊诗文而轻小说的观念;到了近世,“文以载道”观大行其道,“道也者文之本也,文也者道之末也。末者小而本者大也。”当这种文学观借助小说的通俗性和娱乐性来实现时,就形成了日本近世“戏作”文学中的劝惩小说。从近代意义而言,这几乎是将小说文体托下了深渊。从而,深受儒学影响的明治启蒙思想家们当然要把小说列为有害的文体,拒绝用小说作为启蒙的工具。其后,虽然民权派政治小说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对江户戏作文学观构成了冲击,但此时的小说文体又被现实的功利主义宣传所左右。所以,此时的小说成了有用的文体,而不是被人尊重的文体。正如坪内逍遥所说,“我国习俗,自古以来,将小说看作是玩物,作者也满足于此,无人敢于想去改良小说,使之成为娱悦大人、学士们的艺术。”“而将小说视为妇女童蒙的玩物,这种错误的看法皆出于不承认小说为艺术。”坪内逍遥从进化论出发,向世人揭示出小说的应有地位及近代价值,彻底扭转了小说在近代日本文学中的不利地位。“Novel即地道的小说在世上出现,总是在戏剧趋于衰微的时期。”推其原因,“这是因为在文明尚浅近、蒙昧未开的社会,”“由于这个时期的人情世态都显露在外,所以刻画这类人物并不困难,”“但是随着文明气运的进展,每个人、每件事的悬殊性质已越来越少,只用所谓‘思入’这类表演方式,有许多是难以表现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戏剧逐渐让位于稗史、小说的缘故。”通过对日本小说变迁史的梳理以及同戏剧等文体的比较,他认为小说随着文明的进步,自然而然地在社会上盛行起来,并受到重视,是“优胜劣败,自然淘汰的规律所使然,时代所趋,无法抗拒的”。这是从历史进化的角度对小说的发达及其在近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的学理性论证,赋予了小说以时代的尊严。在阐述小说的裨益时,他认为小说的直接利益,“在于娱悦人们的‘文心’,那么‘文心’又是什么呢?不外就是美妙的情绪。”“更何况约翰·穆雷先生也曾说过,对人间世界的批判,乃人生一大乐事。”“有识之士读了它,其感受之深,远非读其他经书或读正史所可比拟。”这里,他把小说的目的与人类的美妙情感直接关联起来,并把小说直接的社会批评作用置于经书、正史之上;同时他还把“使人的品味趋于高尚”列为小说间接裨益的首位:“小说这种东西,它所致力的,并不是给人以官能的享乐,而是致力于投合人们风雅的嗜好,给人以娱乐。而风雅的嗜好,美妙的情感,是一种最高尚的情绪活动。如果不是文化发达,具有高的文明的民族,是绝不可能具有这种情绪的。”总之,在坪内逍遥看来,小说具有促进文明发达的妙机妙用,小说的发达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文明时代之所需,从而有力反驳了小说无用论及游戏文学观,为小说争得了在近代日本文学中应有的位置;另一方面,因为其所谓“妙机妙用”是以“真”为基础和前提的,所以,他提倡局外人式的纯客观的小说创作原则,主张如实模写,将“载道”观念拒之于文学的大门之外,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日本小说主体性的一次彻底解放。
从上面的梳理可见,中日近现代的启蒙主义文学家都在用进化论为小说正名,并对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的特性进行了近代意义上的规约,由此,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变成了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尊贵、独立的新小说。这既是历史进化观念下对小说历史使命的重新定位,也是社会有机体论中的个性意识所带来的小说文体意识的觉醒。但是,近代中日两国本土化的进化论中的“个体”观念是有差异的。加藤弘之的社会有机体论在日本影响最为深远,其中的个体观念是以“唯一利己的根本动向”为核心的。这种动向可以附着于国家或民族作为个体的存在之中,从而导致国家主义或民族霸权主义;也可以附着于个人作为个体的存在之中,从而形成近乎极端的个性意识乃至极端利己主义。当然,如果把文学视为一种个体性的存在,则很有可能对文学的独立性意识和主体性意识产生极端性的影响。从《小说神髓》尽力排除一切作者主观因素干扰的创作原则看,坪内逍遥小说理论的文学主体性意识,应当也附着了这种“唯一利己的根本动向”。而在近代中国的社会有机体论中,既强调个体的进化本位作用,同时又强调群体的进化实现功能,个体与群体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对立统一关系之中,个性意识的伸张程度是以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使命为底线的。所以,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个体观念中总能发现群体的影子,文学的主体性诉求似乎也不像近代日本文学那样强烈和执着,在作者的主观能动性与作品的客观存在之间,中国现代文学比日本近代文学更强调前者。当然,进化论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也不能说是唯一的因素,其实,从两国近代的文学史中也可以发现影响近代文学个体意识的传统因素。据叶渭渠先生的观点:“‘真实’与‘物哀’两种思潮作为日本古代文学的主潮,不仅显示了日本古代文学思想的完成,而且‘真实’文学思潮成为‘物哀’‘幽玄’‘闲寂’诸文学思潮的基底,推进了一个时代文学的发展。”日本古代文学的“真实”精神虽然主要体现于主流文学之中,但肯定会在精神层面对坪内逍遥的小说理论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在追求“真”或“客观”的技巧上,坪内逍遥更多地借助了心理学等近代科学成果。相比之下,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则更注重作者的入世态度甚至“经世致用”的目的意识,“载道”也好,“言志”也罢,其中的“载”和“言”都可能意味着作者主观对文学主体性的主动干预以致支配,这一文学传统对于由非主流文学近代化为主流文学的小说文体自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