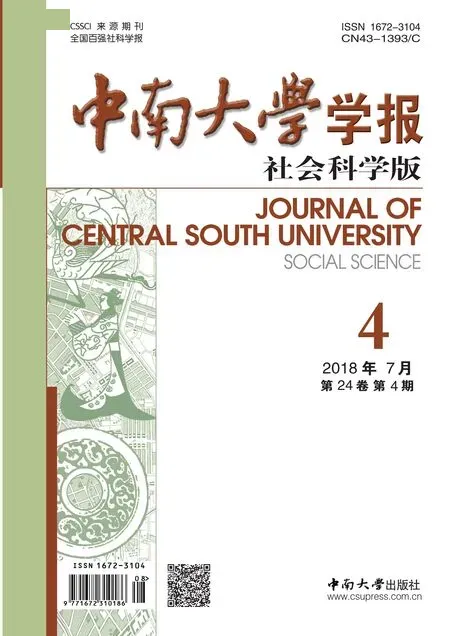清宗室戏曲创作刍论
梁帅
清宗室戏曲创作刍论
梁帅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3)
清代北京剧坛活跃着一支以宗室为创作主体的贵族作家群。清前中期岳端、永恩、敦诚、绵恺、佑善等人创作的作品有杂剧与传奇,载阔亭、溥绪等人则是晚清北京皮黄戏编剧的代表人物。八旗王公贵族府邸浓厚的观剧氛围,为宗室频频涉足戏曲创作奠定了基础。消遣排忧是宗室剧作家主要的创作动机。他们的剧作具有浓厚的宣扬教化色彩,太平之时宗室借戏曲鼓吹国运昌盛,危难之际他们则以扭转世风为目的。在创作过程中,宗室与门客故吏的合力共筑,不仅助力宗室戏曲成就的取得,也极大地提升了门客戏曲创作的水准。
清宗室剧作家;创作动机;创作主旨;创作方法
清代的皇族根据与清太祖努尔哈赤血缘关系的远近分为宗室和觉罗,宗室指努尔哈赤及其兄弟的后代,即世人所称的皇族。明末东北地区戏曲文化贫瘠,此时旗人尚未摆脱奴隶制束缚,入关以前的宗室未见有戏曲作品问世。定鼎中原之后,以宗室为主的八旗王公贵族沉醉于歌舞赏乐,孔尚任《桃花扇》作成后,“王公荐绅莫不借钞”便是最有力的证明[1]。这一时期的宗室也开始涉猎戏曲创作。长期以来贵族阶层的文学创作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演进,先秦贵族文学、西汉宫廷文学、隋唐士族文学、宋明之际士大夫官僚文学等,均在文学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清宗室的戏曲创作便是清代贵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宗室长期生活在北京,他们的剧作同样是清代北京剧坛结出的累累硕果。以往学术界鲜有关注清宗室的杂剧、传奇创作,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剧目多属文人案头之作,故而饱受学界质疑。陈芳就批评永恩的创作“不重视关目结构,只是聊以娱乐遣兴,雕琢词章”[2]。在李真瑜看来,永恩的剧作“内容没有什么新意,只是追求一种喜剧性的冲突,热热闹闹,演过之后在观众心中留不下多少印象”[3]。对于清宗室戏曲创作的动机,邱慧莹认为只要他们“对戏曲活动有兴趣,就可致力为之”,“不用担心皇室的压力或为此而影响声誉”[4]。相较之下,溥绪的皮黄戏创作也仅在一些文学史、戏曲史中偶有提及①。清宗室剧作家并未引起戏曲学人的足够重视。然而早在康熙朝,尤侗就将岳端媲美于朱有燉,“铜雀台边演陈思之妙舞,金梁桥畔唱周宪之新歌”[5]。不可否认,无论是创作水准还是对后世的影响,清宗室剧作家都不能与明初藩王剧作家相比。然而学术界也不应忽略清宗室的戏曲创作,清宗室的戏曲创作实践,理应是清代戏曲、北京剧坛乃至宫廷戏曲研究的重要对象。
清宗室创作的戏曲作品有岳端《扬州梦》传奇、永恩“漪园四种”传奇和《度兰观》杂剧、敦诚《琵琶行》传奇、绵愷《业海扁舟》杂剧、佑善《鉴花亭》杂剧等。近代以来,载阔亭、善耆、溥绪又创作了大量的皮黄剧目②。他们的生活年代自清初至民国初,无论是从作品的数量来讲,还是从题材的丰富程度来看,都远远超过明代藩王剧作家。与清宗室创作的皮黄戏剧目常被搬上舞台并广受欢迎不同,清宗室的杂剧、传奇作品多属案头之作。但是得益于宗室较高的社会地位及富裕的经济条件,一些剧目也偶有演出。如《扬州梦》作成后,岳端“遍招日下诸名流赏之。会者百余人,内有少年王生善集唐,即席诗成,结句云:‘十年一觉扬州梦,唱出君王自制词。’主人大喜,以黄金十四挺,白玉卮三,奉酒为寿曰:‘一字一金也。’生饮酒受金,即以金分给梨园十四人,曰:‘同沾君 惠’”[6]。该剧后来又在碧山堂、白云楼等处上演,上演时甚至有“真本”“演出本”的不同。庞垲《碧山堂观〈扬州梦〉新剧率赋》记:“雪宫曾许看真本,演出当场又不同。”[7]据朱襄回忆,《扬州梦》上演之际,“一时名士之在京师者,咸相与咏歌其盛”[8]。敦诚《琵琶行》传奇作成后,其兄敦敏也曾作诗记录剧目的搬演,“西园歌舞久荒凉,小部梨园作散场。漫谱新声谁识得,商音别调断人肠”,“红牙翠管写离愁,商妇琵琶湓浦秋。读罢乐章频怅帐,青衫不独湿江州”[9]。敦诚、敦敏在右翼宗学与曹雪芹相识,此后三人关系甚密。曹雪芹对《琵琶行》评价道:“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10](卷五)清宗室的杂剧、传奇创作显然在当时的北京剧坛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
一、清宗室戏曲创作的沃土:府邸浓厚的观剧氛围
旗人早在入关之前,就对汉族戏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崇德六年(1641),费英东之子索海随多尔衮攻陷锦州后,便招“降将祖大乐俳优至其帐歌舞”[11](9182)。崇德七年(1642),英亲王阿济格、扎喀纳也“歌舞作乐在伊帐内,复弦歌为戏”[12]。顺治二年(1645)五月十八日,距离清兵进驻南京城才过去三日,多铎就迫不及待地在军营中看戏。《崇祯纪闻录》记:“忻城约各勋戚唤戏十五班,进营开宴,逐出点演。……忻城手递报于王,阅之漠然;又点戏四五出,方撤席,发兵迎敌,即刻便行。”[13]定鼎中原后,为了让宗室等八旗贵族通晓汉族戏曲,顺治帝专门成立翻书房,翻译“《西厢记》、《金瓶梅》诸书,梳栉字句,咸中綮 肯”[14](397)。在顺治帝的默许甚至是推动下,观剧之风日渐盛行于宗室府邸。久而久之,这又引起了顺治帝的不满,“曾有诸王贝勒等,置酒宴会,优人演剧为乐。……朕常恐后世子孙,弃我国淳厚之风,沿习汉俗,即于慆淫”[15](702)。康熙朝宗室府邸的观剧之风愈演愈烈。《长生殿》剧成后,“圣祖览之称善,赐优人白金二十两,且向诸亲王称之”[16]。《桃花扇》一经问世,“王公荐绅莫不借钞”[1]。塞尔赫亲眼目睹宁王弘皎府邸演出时,“笙歌鼎沸间,忽见波涛滚滚而来,仙人乘槎波上,复现空中楼阁,作海屋添筹状,真奇观也”[17],盛况堪比内廷演剧。质郡王绵庆是乾隆之孙,“亲音律,其后九宫谱调,无不谙习,较之深学者,尤多别解”。绵庆之子奕绮则酷爱八角鼓,据传其演唱时,“九城哄传,各巷口报单高挂,书写‘今日某园准演绮贝勒八角鼓’”[18]。戏班是宗室府邸戏曲活动开展的重要支柱。早在康熙十八年(1679),御史任弘嘉巡视南城时便偶遇某王府伶人,“有锦衣骏马突其前,诃叱之。隶卒白曰:‘此王府优也’”[11](10170−10171)。到了乾隆朝,北京城就有了“京腔半隶王府”之说[19]。庄王府“大成班”“王府新班”是此期王府戏班的代表。质郡王绵庆也豢养有家乐。《啸亭杂录》记:“时有优童王月峰,髫龄颖俊。王每佳时令节,于漱润斋红牙檀板,使月峰侑酒而歌,王亲为之操鼓,望之如神仙中人。”[14](185)嘉庆二十四年(1819),内务府借调查内廷艺人姚兰生一案,在庆亲王永璘府内查获伶人50人,其中刘山桂、杨二保、金罩住更是昔日南府承应人员[20]。晚清奕䜣、奕譞、善耆等人府邸的王府戏班,不仅极大繁荣了府内演剧,而且对北方昆弋的发展有突出贡献。为了方便观剧,宗室府邸纷纷建戏楼(台)③。以宗室为中心的八旗王公贵族观剧活动的高涨声势,不仅使宗室长期沉浸于浓烈的戏曲文化氛围中,也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戏曲创作的积极性。
长期以来清宗室剧作家对戏曲抱有极大的热情。敦诚十五六岁时,“每归自宗宾,伯父(纳尔朴)便来召家优歌舞,使预末座”[10](卷二)。敦诚与怡亲王弘晓交往密切,而据《怡府书目》记载,弘晓府中藏有戏曲《桃花扇》《缀白裘》《度曲须知》等戏曲类书籍近30种[21]。绵恺自幼“狎比便倿,不喜正言”,他早年与南府太监张明德交好。道光七年(1827),27岁的苑长青在刚成立不久的升平署担任净脚。由于张明德“在升平署当差,不能常往复,(绵恺)起意令将太监苑长青展转引 出”[22]。事发后绵恺被夺爵,不过一年后他又恢复了亲王爵。熟料绵恺竟不知悔改,道光十八年(1838)定郡王载铨在绵恺府内查出被囚禁者76人,并意外查得在绵恺府内唱戏的升平署太监全顺和全禄。据穆彰阿调查,全顺首先在京城戏班谋生,道光十年(1830)绵愷将其“由戏班内唤至园中”。次年,其弟全禄也被绵愷召进府中,兄弟二人共同在绵恺府上唱戏。道光十二年(1832)正月,内务府总管王德恩发现全顺藏匿在王府,遂“令该王将全顺等二人放出”。然绵愷却依仗自己的势力,将他们“送至伊戚白姓家暂住”,并封给二人四品、六品顶戴,还替他们在“船板胡同代置房屋,赏给衣服、银两等物无数”[23]。事发后,绵恺再次被夺亲王爵。绵恺两次因豢养内廷伶人而获罪,可见其对戏曲的狂热。佑善是郑亲王乌尔恭阿之孙,他自幼生长的郑王府不仅建有一座戏台,乌尔恭阿还召集南府艺人在府内组织戏班,“西南隅建室三楹,曰音乐房,置上赏南府供奉张景福、陈凤鸣、朱莲生等诸人演习音乐”[24]。佑善的戏曲创作自然受到幼年在郑王府内尚戏听曲的影响。清末肃亲王善耆则“全家皆能演剧,常父子兄弟登台”[25]。善耆还与其弟善豫一道唱戏,“善耆之弟,尤工花旦。唱《翠屏山》,善耆之石秀,及其弟之潘巧云,一时无两”[26]。光绪帝逝世不久,善耆甚至“在家中以唱戏为乐,闲或粉墨登场,与诸伶杂演”④。善耆在自己所编的《战台湾》中,“自饰郑成功,文武唱做悉备,全本须演六小时。善耆精神抖擞,始终不懈,伶人多自称不如也”[27]。光绪末年溥绪在北京的茶园戏馆玩票串戏,演武生兼老生,戏名“金伴菊”,民国后他又“尽力提倡剧学,尤肯提掖伶界后进”[28]。票友出身的善耆、溥绪不仅擅长皮黄戏的演唱,而且能够编写剧目,溥绪还对京昆艺术有深入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清宗室的直接影响下,许多戏曲票房在其府邸周边成立。赏心乐事、塔院、霓裳雅韵三处票房毗邻恭王府,公余同乐紧挨庄王府。部分宗室还在府邸内自建票房,如善耆的肃王府票房、载燕宾和载阔亭的翠峰庵、载澂的赏心悦目、溥绪的“尚友社”等。这些戏曲票房不仅繁荣了宗室府邸的戏曲活动,而且票房内票友的建言献策也能提升宗室戏曲创作的水准。
值得注意的是,清宗室戏曲创作受到宫廷戏曲、北京民间剧坛的双重影响。以往学术界论及清代北京剧坛,多将其简单划分为宫廷戏曲与民间剧坛。对以宗室为中心的旗人戏曲活动的讨论,多夹杂于民间剧坛的相关论述中⑤。实际上在宫廷戏曲与民间剧坛之间,北京剧坛还有数量庞大、影响广泛的旗人戏曲活动值得关注。宫廷“凡遇元旦、万寿、上元、端阳、中秋、重阳、冬至、除夕等节”[29],宗室便会被邀请进宫庆祝,席间即有戏曲演出。除此之外,皇帝还会邀请宗室在特定时间进宫看戏。受宫廷文化和宗室身份的影响,宗室剧作家的作品往往带有明显的贵族气质。如在岳端、永恩的剧作中,经常描绘奢华、热闹的场面,极力营造恢弘气象。在他们的神仙道化剧中,得道升仙、超然度脱是永恒的主题。宗室戏曲作品的刊印十分精美。康熙四十年(1701),启贤堂《扬州梦》刻工考究、精致,严谨的规制、舒朗的字体堪比清内府刻本。岳端还聘请当时久负盛名且已80高龄的徽派版画大家鲍承勋为《扬州梦》刻印插图24幅。鲍氏早年曾为长洲钱谷绘图本《杂剧新编》刻图。《业海扁舟》有道光十七年(1837)朱墨精钞本、四色精钞本、五色精钞本。据五色精钞本原藏者齐如山介绍:“此为各王府雇人抄好进呈本,都是五色笔所抄,极工整。”[30]今人颜长珂亲自寓目该本后描述道:“分别用黄、绿、红、蓝诸色,如宫中所用剧本(安殿本)的格式。”[31]宗室剧作刊印、誊抄的讲究与严谨,绝非其他剧作家的作品所能比。不过,清宗室剧作中的贵族气息随着八旗社会的瓦解而逐渐淡化。与明代藩王成年后被分封至各地不同,清宗室长期在北京生活,他们的剧作也多有反映京师梨园的细节。如岳端在《扬州梦》第十二齣《赏灯》中,借着良辰美景,众人表演了“十番乐”。《桃花扇》第二十五齣《选优》、《长生殿》第十四齣《偷曲》均有“十番乐”的表演。在演出过程中,“鸾笙吹徹羯鼓喧,敲象板,拨凤弦,音韵悠扬绕半天。春风几阵吹不散,逢令节,与翩翩达旦浑忘 倦”[32]。王芷章认为“十番乐”在乾隆朝才由吴中地区传入北京[33]。然而结合《扬州梦》《桃花扇》《长生殿》来看,在康熙朝中叶北京民间就已有“十番乐”的演出。再如绵恺在《业海扁舟》题句中记:“霍六财官并虎张,马牛(一作郝升)唐套大头郎。”[34]绵恺举出的霍六、财官、虎张、马牛、唐套、大头郎,正是戏曲史上赫赫有名的“京腔十三绝”中的名伶。《都门纪略·词场》记:“时人贺世魁画。所绘之人,皆名擅词场:霍六、王三秃子、开泰、才宫、沙四、赵五、虎张、恒大头、卢老、李老公、陈丑子、王顺、连喜,号‘十三绝’。其服皆戏场装束,纸上传神,望之如有生气。观者络绎不绝。”[35]绵恺又在第四折《新词申警》中借一讲弹词的老者之口,生动描绘了此时北京南城盛行的“相公”。《业海扁舟》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对道光初年北京剧坛的写实描绘,其剧情对我们了解此期花雅争胜及北京梨园演剧形态的衍变有极大帮助。受到宫廷演剧及北京民间剧坛的共同影响,清宗室剧作家的作品呈现出有别于其他作家的另一番景致。
二、消遣排忧:清宗室剧作家的创作动机
消遣排忧是清宗室剧作家进行戏曲创作的主要动机,但是在清代前中期和清末,宗室排遣内心忧闷的出发点却不尽相同。岳端、永恩、敦诚是在享受太平盛世之余,借戏曲宣扬盛世;溥绪、善耆则是在国家濒临灭亡之际,以戏曲来逃避现世。
岳端出身名门,父亲岳乐是努尔哈赤七子阿巴泰之子,母亲赫舍里氏是清初辅政大臣索尼之女,家族地位十分显赫。岳端初封勤郡王,父亲去世后,他按例降为贝子。康熙三十七年(1698),岳端因“与在外汉人交往饮酒,妄恣乱行”遭削爵[15](1000)。《扬州梦》恰作于此年稍早时候。岳端与王士祯、尤侗、孔尚任等素来交善。正如王士祯所言:“生于富贵,而其胸怀潇洒乃尔。”[36]戏曲创作俨然成为他结交文人豪士、彰显自身才艺的方式,可惜的是岳端也因此而获罪。永恩素善交友,“诗酒从容,负一时文藻之誉”[37]。姚鼐《礼恭亲王家传》记其“读书、骑射、为学日益精厉,作诗、古文皆有法,高宗纯皇帝闻而喜之。……暇则以笔墨为娱,其论文以义法为要,诗以清远澹约为宗,其往来议论者谢皆人、刘大魁、徐炎、朱孝纯辈也”[38]。永恩《诚正堂稿》中有诸多题咏花草虫鱼的诗作,展现了他闲淡雅致、清静无忧的生活境况。敦诚亦“素耽山水……好宾客……尤喜访胜探奇”[10]。岳端、永恩、敦诚皆生活于康乾之际,他们的剧作没有对现实的针砭,也少见内心的忧愁苦闷。《扬州梦》取自宋代李昉《太平广记》中“杜子春三入长安”的故事。《琵琶行》描写白居易在浔阳江头偶遇琵琶女之事。《五虎记》则源自“纩衣传诗”的典故。《四友记》以元代吴昌龄《张天师断风花雪月》及《花间四友东坡梦》二剧为本事。《三世记》敷演清初流传颇广的济宁奇人邵士梅的故事,时人王士稹《池北偶谈》、蒲松龄《聊斋志异》、钮琇《觚剩》对此事均有记载。《双兔记》搬演花木兰从军的故事。《度蓝关》则演韩湘子借向韩愈祝寿之际,劝其遁入道门。这些剧作皆立足于个体形象的展露,作者没有让人物背负时代的枷锁,因而作品并不存在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倒是处处彰显着个人的浪漫主义情怀。更有甚者,道光朝的佑善甚至将戏曲创作视作游戏消遣。佑善年仅十五岁时便创作了杂剧《鉴花亭》,这在历代剧作家中实属年轻。《鉴花亭》围绕武则天与韦后的故事展开,每折选取一个故事进行演绎。然而纵观全剧,不仅故事叙述紊乱,唱词亦不押韵。诚如吴晓铃先生所言:“宫调错乱,体制混淆。”[39]
与此前的清宗室剧作家不同,清末民初善耆、溥绪的作品中流露出对大清国气数已尽的无奈,戏曲创作成为他们规避现实的良方。善耆《战台湾》里郑成功率领众人披荆斩棘,《请清兵》中吴三桂煞是可怜地哀求清兵攻打李自成部,这些人物及情节无不体现着善耆内心的英雄主义倾向。善耆在排演《战台湾》一剧时,“文武唱做悉备,全本须演六小时。善耆精神抖擞,始终不懈,伶人多自称不如也”[27]。据宪钧回忆,其父善耆演出该剧时,“还特意拍了一张剧照留 念”[40],善耆内心的自豪感不言而喻。善耆对刻画八旗子弟的威武果敢最为用心。《镇江府》一剧演清兵破郑成功一事,“尝聚缙绅子弟,票爨于邸中。梨园从无演者,剧本也不传”[41]。《请清兵》一剧尤能体现八旗军队的威不可挡,惜该剧今已不存,幸运的是剧中多尔衮宣读满文圣旨的情节保留至今。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据明国三海关总兵吴三桂奏,流贼李自成打破北京,逼君自缢,吴三桂诚意替君父报仇,是因寡不敌众,特来叩求正宫求借雄兵数万,恢复中原,殄灭流寇,与彼国君父报仇,着照吴三桂办,联洞悉明国臣子,素无信义,该总兵攒刀盟誓。剃发投诚,方准发兵,钦此[42]。
李自成倒行逆施的行径、吴三桂大军的低沉士气,与八旗百万雄师的替天行道、忠勇果敢形成鲜明对比。此份奏折一经宣读,必定引起旗人对昔日征战疆场的追忆。民国年间,该戏由萧长华教予富连成科班,演出时观众需加洋十元观看,可见颇受民众欢迎[43]。作为末代亲王,家族荣辱也始终在溥绪心头涌动。民国十九年(1930)六月,溥绪曾奏请北洋政府修缮惨遭毁坏的庄王陵[44]。溥绪的皮黄戏创作进入民国之后渐成气候,他借编剧之机尽力逃避亡国带给自己的伤痛,突显了末代亲王内心的惆怅与无助。溥绪为捧红尚小云,特意组织了一个多达千人的“尚友社”,以致“百万家财尽消沉丝竹”[45]。他在为《尚小云专集》题写的诗作中也流露出百无聊赖的心境,如“画栏斜倚听歌坐,且作优游快活人”“只愁一轲江南去,怅对青峰唤奈何”“痴心愿祝春常在,一扫人间万古愁”,等 等[46]。在溥绪的皮黄戏中,历史剧最多,汪侠公曾言其“尤喜旧古代历史诸戏,为予生平之良友。曩日与之研讨,获益实深”[47]。《婕妤当熊》讲述班婕妤解救汉元帝,《化外奇缘》演七擒孟获,《佟家坞》取材自白莲教起义,《荒山泪》的题材则来自明末高良敏被猛虎吞食之事。溥绪沉醉于对历史事件的追忆,进而逃避现实带给自己的苦闷和彷徨。在具体的情节中,溥绪对武戏的编排最为用心,且为人津津乐道。尚小云深得溥绪历史剧、武戏排演的精髓,其表演尤以武功见长。20世纪30年代王瑶卿评价四大名旦时言:“梅兰芳的‘像’,程砚秋的‘唱’,尚小云的‘棒’,荀慧生的‘浪’。”[48]尚小云的“棒”即指其武功好,他的这一艺术特征显然与编剧溥绪密切相关。
消遣的心态导致清宗室纷纷醉心于深邃奥古的音韵声律研究。岳端“聚音律家纂修”《南词定律》[49],允祉则撰有《八音乐器考》,永恩编纂的《律吕元音》更是对客居其府上的毕华珍的《律吕元音》的问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清宗室最精于音律者莫过于庄亲王允禄。乾隆四年(1738),允禄因“与允礽子弘晳往来诡秘”而被削爵[11](9049),不过他仍食亲王双俸。允禄素善音律,从乾隆六年(1741)开始,他与三泰、张照共同管理乐部。此后由乐部负责,内务府相继刊印了《律吕正义》《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太古传宗》等书。清宗室在音韵声律学方面取得的瞩目成就,不仅是宗室剧作家的兴趣所在,也是由于他们的内心情感无处排解所致。
三、宣扬教化:清宗室剧作家的创作主旨
作为皇权统治的帮手,清宗室戏曲创作的主旨便是宣扬教化。太平之时,宗室借戏曲传播世道人心,鼓吹国运昌盛;国家危难之际,宗室以劝善为己任,并将扭转世风视为目标。《扬州梦》中杜子春挥金如土且屡教不改,以至家道败落、妻子出家,夫妻二人此后屡受魔王、冥司折磨,后经太上老君度脱才得以转世。世俗的人间与圣洁的仙道形成鲜明对比,岳端借此劝说世人戒除贪念。永恩在《律吕元音》中说:“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50]他认为音乐既能够正教,又可以使人端正精神、调养心性。永恩在《五虎记》中也表露出这一倾向,他将“纩衣传诗”的故事与李世民平定王世充造反事合二为一,旨在劝诫百姓对清朝不能存有二心。允禄在《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序》中谈及此书编纂的原因时也强调:“逢此太平风月之场,况乃皇都佳丽之地,向司其事,爰成是 书。”[51]他支持清唱曲谱集《太古传宗》的付梓,也是出于“歌咏升平”[52]。基于鼓吹天下安定的目的,清宗室在戏曲、音乐理论上的复古保守思想十分严重。清宗室的戏曲创作及由其主持修纂的曲学、律学书籍,在杨荫浏先生看来甚至是“脱离物质,逃避现实,贩卖神秘主义”[53]。
清宗室借戏曲宣扬教化者,无人能与惇亲王绵恺相比。他的杂剧《业海扁舟》,以及其洋洋洒洒近万言的戏曲理论著作《灵台小补》,均是说教的典范,以至于有学者将其与晚清戏曲教化观的集大成者余治并论⑥。道光十二年(1832)问世的《灵台小补》开头便言:“余平生最恶,莫甚梨园,比诸孽海,万丈深渊,从古至今,为患久矣。”正文最后还提及:“余自幼心性,独恶此技,视若仇敌,又深悯焉。”[54]绵恺以亲身经历告诫世人远离梨园。在《灵台小补》中,他借《三国演义》《水浒传》大谈君臣伦理道德。他对三国戏、水浒戏中描写匪患、宣扬起义的情节嗤之以鼻,并认为这是当下农民起义频发的根本原因。五年后,绵恺在《业海扁舟》中又把伶人低下的社会地位、悲惨的生活遭遇,撕裂给读者和观众看。他详细刻画了伶儿、董洁等艺人血淋淋的生活遭遇,不仅是希望伶人脱离苦海,也是告诫世人勿沉溺于赏戏听曲。无独有偶,绵恺的弟弟、惠亲王绵愉也撰写过一篇与绵愷异曲同工的《演戏之事迷人》,极力批评观剧赏戏的行为。绵愉认为戏曲“以古圣人正人心,化风俗之乐,变之再三,而成此靡靡之音。又生出雄狐绥绥之事,误尽多少聪明而未已也”[55]。与岳端、永恩等人在剧作中首先树立积极的价值观,进而宣扬正统教义、归化人心不同,绵恺和绵愉将世道堕落的矛头直指观剧之风的盛行。这不仅有悖常理,也显得格局极小,给人更多的是作者意气用事之感。再结合道光帝继位以来实施的诸多禁戏举措,无论是此期的宫廷戏曲还是北京民间剧坛的发展都受到前所未有的阻碍,笔者不得不认为绵恺、绵愉此举更多的是表明对道光帝的拥护。
乱世之际的劝善教化更加鞭辟入里,它对内心的冲击也更为强烈。溥绪在国剧传习所的开班仪式上讲道:“戏之道,既能移风易俗,亦能随世风变迁。”[56]可见他对戏曲启迪民众心智以及借戏曲激发民众救国热情的期待。他在《编新剧之我见》中还强调:“鄙人以为若将历代史书,各种典故,尽编成皮黄,词句须明白坦易,使妇人孺子莫不通晓,既可补助无形教育,又可提倡中国艺术,冶理论哲学于一炉,尤易感化人也。”[57]溥绪认为皮黄戏的创作应建立在旧戏的基础之上,他尤其注意中国古典戏曲中“有益人群社会”的部分。民国二十一年(1932),他发表《预祝国剧传习所诸学员》,文中较为全面地阐释了这一理念。
大家力求进步,发扬国剧,须将戏剧中荒诞不经者删去。再将中国良好典故编排成剧,并旧本中有益人群社会者,尽皆排演。力求文武场改革,搜集旧有之牌子,久无人演者。旧戏有不合时宜处,力求改变,精益求精[58]。
溥绪不仅要求将旧有剧作中有益人群社会的剧目进行编排,还要求对不合时宜的剧目予以改编。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溥绪在剧作中极力刻画具有正义感的人物,如碧云(《峨眉剑》)、苏武(《苏武牧羊》)、石守信和桂英(《千金全德》)以及班婕妤(《婕妤当熊》)等。取材于佛经原典、描述域外风情的《摩登伽女》,更是处处彰显男女主人公的凛然正气。老拙对此剧的结尾评价道:“末场诸佛莲座说法,恶魔消灭,摩登伽女皈依正果,颇见编剧人之寓意。”[46]借戏曲宣扬世道人心、正统教化,这一直贯穿于溥绪戏曲创作的 始终。
四、合力共筑:清宗室剧作家与门客的戏曲创作互动
早在明初,曲家名伶便纷纷投奔各藩王府邸,明代藩王与曲苑名家的良性互动,不仅提升了藩王的戏曲鉴赏水平,而且有利于其门客戏曲创作的开展。无独有偶,清宗室剧作家与其门客的创作互动大致也是如此。
清宗室剧作家周围亦不缺乏长于度曲者。孔尚任自康熙二十九年(1690)抵达京师后,寓居北京长达十年,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岳端。孔尚任有诗记:“高宴南皮礼数宽,古香池馆接红兰。主人辞赋清无敌,惊得邹枚袖手看。”题下小注:“古香、红兰两主人,博学能诗,恭俭好士,有河间之风。”[59](370)岳端也曾作诗记录他与孔尚任等友人彼此唱和的情景:“火云烧日脚,驱执无义鞭。朱陆行转缓(尚任),清飚吹难遄。……盻星目已穿,睡魔频压颈(尚任)。……宝瓶蛛丝缠,草连窗翡翠(尚任)。……琱猊枕纸眠,庭楸敛夕影(尚任)。……酒攻叠块坚,银盤蜡溢泪(尚任)。”[60]孔尚任是《扬州梦》的第一批观众。他在《燕台杂兴》中写道:“压倒临川旧羽商,白云楼子碧山堂。伤春未醒朦胧眼,又看人间梦两场。”下注:“玉池生作《扬州梦传奇》,龙改庵作《琼花梦传奇》,曹于碧山堂、白云楼两处扮演,予皆见之。”[59](380)孔尚任给予该剧极高评价。朱襄、顾卓、沈方舟等人也与岳端交好,岳端“喜为西昆体,尝延朱襄、沈方舟等为上宾”[14](180),《扬州梦》的刊印便是由他们负责审理校阅。康熙三十八年(1699),降为闲散宗室的岳端邀请尤侗为该剧作序,尤侗盛赞该剧“无异霓裳羽衣”“堪续湘水之九歌”[8]。岳端以“三千里外身难到,心逐双鱼达太湖”[61]答之,视尤侗为知音。《扬州梦》从问世、刊印到传播,凝聚了岳端及其门客故交的诸多心血。曲苑名伶对宗室戏曲创作的影响,在皮黄戏编制过程中更为突出。与杂剧、传奇等古体戏曲创作不同,皮黄戏的编创往往非一人之力、一时之功,它需要剧作家、演员结合演出实际反复打磨。如清末载阔亭与兄载燕宾一道,成立了翠峰庵票房,该票房“年代为最早。而且该处所出人才为众”[62]。民国初年,溥绪也组织了“尚友社”,“据说社员多至七八百人”[63]。票友们竭力支持载阔亭、溥绪的戏曲创作。如昔日内廷供奉“砌末张”张小山,素善制作砌末,他在创作《蓝桥会》时,“做许多砌末,如龙宫,嫁妆等,当时亦甚受人欢迎者也”[64]。载阔亭便向其学习砌末设置之法,后来载氏为韩俊峰编排《普天乐》时,“自做地域砌末一份。韩君俊峰饰包拯,花脸志七之张洪(即胖官),载阔亭君之齿流鬼。每逢走局时,人皆喜看此戏之砌末”[65]。善耆编排的《请清兵》《战台湾》等剧,也并非靠一己之力完成。宣统二年(1910),徐廷璧受邀为肃王府的“复出昆弋安庆班”排演了全本《请清兵》。善耆与谭鑫培、汪桂芬、王凤卿等艺人交好。在曲家名伶的影响下,善耆的演唱水准迅速提升,以至于谭鑫培盛赞“我死后能得我传者,唯有某王爷一人而已”⑦。

宗室剧作家因自身特殊的社会地位,对剧作家、伶人有着极大的号召力。曲家们以能够在王公贵族府邸承值为荣,他们也为宗室的戏曲创作实践提供了专业化的指导。清宗室剧作家戏曲成就的取得,凝聚了其门客们的集体智慧。与此同时,宗室又对其门客故交给与了极大帮助。无论是门客故交的物质生活,还是门客故交所编剧目的印行与搬演,宗室都予以大力支持。宗室与门客戏曲创作的互动,自清初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成为清代戏曲发展的重要推手。
五、结语
清宗室剧作家的戏曲创作,经历了与清代戏曲发展大体相当的演进过程:由杂剧、传奇转向皮黄;由案头转向场上;由低潮渐入佳境。最值得瞩目的是清末以载阔亭、溥绪为代表的宗室剧作家,他们开创并率先实践了“因人设戏”的编剧理论,不仅在当时取得了极大成功,而且直接影响了之后皮黄戏编剧的发展。如果说清初宗室剧作家的传奇创作是集前贤之所长、逞一时之快慰,那么清末民初的宗室剧作家可谓是开后世之先河、树一代之典范。
以清宗室的戏曲创作为中心,再考察此期旗人的观剧与演剧活动,戏曲学界应当注意清代北京剧坛由“沙漏型”向“金字塔型”的转变。清前中期的旗人将民间戏曲带入紫禁城,民间戏曲在八旗贵族文化的熏陶下成为宫廷戏曲,两种戏曲文化逐渐形成差异。此时的北京剧坛形成“沙漏型”戏曲活动模型。受清代爵位制度和旗人生计日趋恶化的影响,虽然此后宗室等八旗贵族仍然坚守着贵族化的戏曲观演风尚,但是中下层旗人却与普通民众的戏曲活动日趋一致。自嘉庆道光年间始,北京剧坛的戏曲活动模型由“沙漏型”渐变为“金字塔型”,旗人的戏曲活动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伴随着晚清的民间戏曲被不断输送进紫禁城和王公贵族府邸,八旗贵族的传统戏曲观演风尚再次被吞噬。黄仕忠已注意到在清代演剧活动消费对象的构成中,形成了“由低到高、层次分明的金字塔式结构”[73],王公宗室是十分特殊的消费群体。而与国内学者相比,域外汉学家早已注意到北京旗人的戏曲活动。马克拉斯在《清代京剧百年史》中直言:“满洲皇室的亲贵均为戏剧的有力赞助者。”[74]近年“新清史”风靡北美汉学界,郭安瑞认为宗室虽然可以邀请演员到府中演戏,但他们到外城观剧却被视为禁忌,这反映出满族汉化过程中的焦虑[75]。戏曲创作是清宗室戏曲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以此为基点,清代北京旗人戏曲活动的内容与形态理应引起学界足够重视和深入探讨。
注释:
① 梁淑安《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钱仲联《中国文学大辞典》、关纪新《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北京艺术研究所《中国京剧史》均对溥绪及其剧作有概要性介绍。
② 关于清宗室剧作家的生平及创作剧目可参看拙作《清代旗籍剧作家杂剧、传奇作品叙录》,拟刊于《中华戏曲》第57辑。
③ 据笔者统计,郑王府、恭亲王、僧王府、那王府、醇王府、庆王府、肃王府、睿王府等八旗王公府邸均建有戏楼。
④ 此份奏折既无作者署名,未标注时间,今仅知藏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奏折复印件托北京社科院满学研究所杨原先生赠与,在此特表谢忱。
⑤ 如牛川海《乾隆时期剧场活动之研究》((台湾)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版)、邱慧莹《乾隆时期戏曲活动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2000年版)、范丽敏《清代北京戏曲演出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么书仪《晚清戏曲的变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著作,均将清代北京剧坛划分为宫廷与民间两部分。
⑥ 谢柏樑言:“真正自觉地全面理解戏剧艺术的自身特性,从而把戏剧当成阐扬风教、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的批评家,是前清道光年间金连愷和晚清集教化系统之大成的余治。”谢柏樑.中国戏曲文化学,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400.
⑦ 无名氏《梼杌近志》“肃亲王戏癖”条记:“叫天尝语人曰:‘我死后得我传者,惟某王爷一人而已。’或云即肃王也。”收入《清代野史》,巴蜀书社, 1998: 940.
[1] 孔尚任. 桃花扇·本末[M]. 康熙四十七年刻本.
[2] 陈芳. 乾隆时期北京剧坛研究[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 232.
[3] 李真瑜. 北京戏剧文化史[M]. 北京: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4: 307.
[4] 邱慧莹. 乾隆时期戏曲活动研究[M]. 台北: 文津出版社, 2000: 49.
[5] 尤侗. 扬州梦·序[M]. 康熙四十年启贤堂刻本.
[6] 查为仁. 莲坡诗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
[7] 庞恺. 丛碧山房诗: 卷五[M]. 康熙刻本.
[8] 岳端. 扬州梦[M]. 康熙四十年启贤堂刻本.
[9] 敦敏. 懋斋诗钞[M]. 清钞本.
[10] 敦诚. 四松堂集[M]. 乾隆刻本.
[11] 清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2] 王先谦. 东华录: 卷“崇德七”[M]. 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
[13] 叶绍袁. 崇祯纪闻录[M]. 台北: 大通书局, 1984: 56.
[14] 昭梿. 啸亭杂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5] 清实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6] 王应奎. 柳南随笔[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23.
[17] 塞尔赫. 晓亭诗钞: 卷三[M]. 乾隆十四年鄂洛顺刻本.
[18] 奕庚. 佳梦轩丛著[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4: 110.
[19] 李光庭. 乡言解颐[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54.
[2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永璘秘档[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 417.
[21] 允祥. 怡府书目[M]. 民国间钞本.
[22] 王先谦. 东华续录: 卷四[M]. 光绪朝刻本.
[23] 清代档案史料选编: 四[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356.
[24] 凌景埏. 全清散曲[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5: 1511.
[25] 罗瘿公. 鞠部丛谈[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8: 792.
[26] 张肖伧. 菊部丛谭[M]. 上海: 大东书局, 1926: 208.
[27] 徐凌霄. 凌霄一士随笔: 第二册[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7: 614.
[28] 吴幻荪. 吟碧馆答[J]. 戏剧月刊, 1930(12): 60−65.
[29] 内务府. 钦定宫中现行则例: 卷一[M]. 嘉庆二十五年武英殿刻本.
[30] 齐如山. 齐如山回忆录[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 196.
[31] 颜长珂. 《灵台小补》、《业海扁舟》作者金连凯考[C]//赵景深. 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 第二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173−189.
[32] 岳端. 扬州梦[M]. 康熙四十年启贤堂刻本.
[33] 王芷章. 清昇平署志略[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19.
[34] 绵恺. 业海扁舟[M]. 道光十七年精钞本.
[35] 杨静亭. 都门纪略[M]. 同治三年荣绿堂刻本.
[36] 王士祯. 香祖笔记: 卷十一[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4: 103.
[37] 孙楷第. 戏曲小说书录解题[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370.
[38] 姚鼐. 惜抱轩文后集: 卷五[M]. 《四部备要》本.
[39] 吴晓铃. 止酒停云室曲录[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4: 37.
[40] 宪钧. 善耆反对宣统退位图谋复辟[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2: 70.
[41] 傅惜华. 皮黄剧本作者草目[C]//傅惜华. 傅惜华戏曲论丛.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 367.
[42] 印丽雅. 京剧《请清兵》满语唱词译释[J]. 满语研究, 1996(1): 114−119.
[43] 唐伯弢. 富连成三十年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60.
[44] 佚名. 房山庄王陵被掘[N]. 申报, 1930−6−26(B3).
[45] 吴幻荪. 吟碧馆剧剳[J]. 戏剧月刊, 1930(12): 2.
[46] 徐汉生. 尚小云专集[M]. 北京: 京津印书局, 1935.
[47] 汪侠公. 侠公剧话——清逸编《化外奇缘》志感[N]. 立言画刊, 1944−3−1(B5).
[48] 徐城北. 尚派艺术五题[J]. 戏曲研究, 1990(33): 143−153.
[49] 许之衡. 扬州梦·跋[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4: 200.
[50] 永恩. 律吕元音: 卷二[M]. 乾隆刻本.
[51] 允禄. 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序[M]. 乾隆内府刻本.
[52] 朱珩. 太古传宗·序[M]. 乾隆十四年刻本.
[53] 杨荫浏.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1: 1012.
[54] 王利器.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356, 360.
[55] 绵愉. 爱日斋集[M]. 同治十年宝文斋刻本.
[56] 溥绪. 预祝国剧传习所诸学员(续)[N]. 国剧画报, 1932−7−8(B2).
[57] 溥绪. 编新剧之我见[N]. 国剧画报, 1932−3−25(B3).
[58] 溥绪. 预祝国剧传习所诸学员[N]. 国剧画报, 1932−7−1(B2).
[59] 孔尚任. 孔尚任诗文集: 卷四[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60] 岳端. 蓼汀集: 卷二[M]. 清钞本.
[61] 岳端. 松间草堂集[M]. 清钞本.
[62] 郑菊瘦. 四十年前北京票房[N]. 立言画刊, 1939−12−23(B4).
[63] 怡楼主人. 讲讲北平的尚友社[J]. 戏剧月刊, 1929(8): 49−52.
[64] 溥绪. 票友之艺术: 四[N]. 国剧画报, 1932−4−29(B2).
[65] 溥绪. 票友之艺术: 五[N]. 国剧画报, 1932−5−13(B2).
[66] 毛奇龄. 西河集: 卷四十七[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7] 邓之诚. 骨董三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608.
[68] 张蘩. 双叩阍·序[M]. 宁府钞本.
[69] 杨钟羲. 雪桥诗话全编: 卷七[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379.
[70] 宫敬轩. 海岳圆·题辞[M]. 清钞本.
[71] 叶廷管. 鸥陂渔话: 卷一[M]. 同治九年刻本.
[72] 舒位. 瓶水斋诗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809.
On drama creation of Qing imperial clan
LIANG Shuai
(School of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3, China)
There appeared an aristocratic group of dramatists in Beijing Theatre of the Qing Dynasty who took imperial clan as major creation entity. In early and mid Qing Dynasty, such dramatists as Yue Duan, Yong En, Dun Cheng, Mian Kai and You Shan produced Zaju and Chuanqi, while in late Qing Dynasty, Zai Kuoting and Pu Xu we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Beijing opera playwrights. From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nobility mansion of Eight Banners kings has strong atmosphere for the opera activities, which laid foundation for the frequent involvement in drama creation. From the writers’ view, recreation was the major creative motivation, and their drama had strong didactic coloring in that at peace time they made use of drama to sing praise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 but at the critical moment, they turned the tide. Hence,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on, both imperial clan and the gatekeeper made joint efforts, not only helping the imperial clan achieve opera achievement, but also improving the gatekeeper’s proficiency in drama creation.
imperial clan dramatists in the Qing Dynasty; creative motivation; creative theme; creative method
[编辑: 胡兴华]
2017−10−25;
2018−05−15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全清戏曲》整理编纂及文献研究“(11&ZD10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2批面上资助项目(2017M622326)
梁帅(1988—),男,湖南耒阳人,艺术学博士,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戏曲文献学及元明清文学,联系邮箱:616647309@qq.com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8.04.021
I207.3
A
1672-3104(2018)04−018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