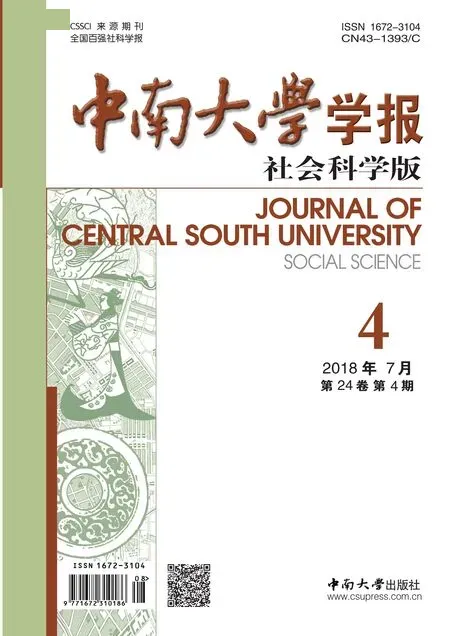民选的议会与不民主的立法:当代美国非正统立法程序考察
王怡
民选的议会与不民主的立法:当代美国非正统立法程序考察
王怡
(中山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以多级化、复杂化和专业化著称。在理论家看来,这一设计为立法过程中多元利益的充分博弈提供了重要场所。然而,精巧的理论在实践当中往往难以奏效。特别是近些年来,美国国会频繁利用程序中的灰色地带,为一揽子立法等非正统立法手段大开方便之门,使得大量议案绕过传统立法程序的关键环节,不经充分审议和辩论便获得法的身份。以至于已有不少学者宣称,教科书式的传统立法程序已名存实亡,非正统立法正主导着当今美国立法实践。理性认识美国的民主与法治,需要深度发掘和客观评价其议会民主实践。对当下美国国会立法中的非正统立法现象及其影响进行考察,或将为我国学界认识和反思西方民主制度和立法制度带来新的启发。
美国立法;立法程序;非正统立法;民主立法;法治
“依靠普选权来治理国家就像绕道合恩角时迷失了航路的海船水手一样:他们不研究风向、气候和使用六分仪,却用投票来选择道路,并宣布多数人的决定是不会错的。”[1](305)马克思不仅敏锐地指出了将普选制等同于民主这一逻辑中的天然谬误,同时也启迪后人,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认识应摆脱思维定势的禁锢,与实践和经验取得对接。如果说,选举制度是美国民主的起点,议会及其活动便是民主运行的主要场域。要对民主效果进行客观评价,就必须对议会的立法实践进行全面考察。法治一方面提供着民主实践的基本规则,一方面也是民主实践的重要输出。民主与法治的天然联结表明,衡量民主绩效,应以法治为框架和底线,法的一般性、明确性、连续性、一致性等实体价值①,法律制定的公开性、透明性、可问责性等程序价值都是民主绩效的重要衡量标准。
美国国会的立法程序向来以多级化、复杂化和专业化著称,法案到法的整个过程由无数细小的步骤和环节串联而成。尽管孤立地审视单一步骤或环节,人们很难觉察到其中蕴含的技术含量——似乎议案一经提交,就如同装运上流水线的货品,经过不同人员的质量把关和修整,最终以优胜劣汰的方式产出。但实际上,立法过程中时时处处都充斥着利益角逐和政党博弈,暗箱操作、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等腐败现象更是随处可见。经过严苛的程序筛选,绝大多数法案都会在利益拉锯中粉身碎骨,只有少数法案能侥幸逃脱、浴火重生。复杂的立法过程堪比香肠的制作过程②,美国诗人萨克斯的这个经典比喻早已为人们耳熟能详——这兴许恰好说明,利益集团也好,党派纷争也罢,这些可能的丑陋行径其实早已被制宪者们所预见,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多元主义所渴望的恰恰就是如此这般的意见市场:只要有足够多的议员代表足够广泛的选民,就不必纠结于加工过程的洁净,因为程序本身带有免疫功能,可以确保产出合格的制度产品供大众消费[2](45−46)。此外,两院之间的牵制以及总统否决权的设置又使得法案的产出无比艰辛——良法尚且不易通过,恶法更是难以立足[2](371−374)。换言之,以正当程序为基点,以分权制衡为保障,立法过程中非理性的个体私欲得以相互抵制和削减,公共理性因之得以保全。这恰好也解释了,为什么选民明知利益集团操纵立法,党派分歧影响政策,却仍然会对美国的民主法治怀有期待和信心。
然而,发生在国会当中的真实事件,是否正如教科书所言般理想?遗憾的是,即便教科书所诠释的立法过程的确存在,即便其的确曾对民主法治发挥过作用,功成名就大概也只能被归于历史[3]。如今的美国国会立法,不断上演着戏剧性反转,将其称为对传统的背叛也毫不过分。如果说,制宪者视审慎与节制为立法者之美德,特别是在面对重大决策争议之时,期待立法者对议案进行理性而充分的审议,避免因冲动立法引发不良社会效果,那么,现今国会之中上演的一幕幕立法事件,恰同上述期待背道而驰——一揽子立法、紧急法令、立法外包、非常规授权、局外人起草等立法手段正在逐渐成为主流。这些手段的广泛使用,使得大量议案绕过传统立法过程中的程序性障碍,未经充分审议而获得法的身份。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杀手锏式的立法策略作为重要的资源分配方式,又并非为普通议员或议员背后的利益集团平等享有或竞争持有,而是把持在政党领袖和白宫之主——这些拥有特定身份的少数人手中。这不仅是对民选者立法在形式上和实质上的两重背叛,也是对分权制衡的美国宪政传统提出的严峻挑战。
理性认识美国的民主与法治,需要深度发掘和客观评价其议会民主实践。对美国国会立法中的非正统立法现象及其影响进行考察,从而发现其民主理论同法治实践的自相矛盾,无疑能够为中国学界认识和反思西方民主制度和立法制度带来新的启发。顺应这一思路,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四部分:首先是对基于美国宪法和两院议事规则而形成的正统立法程序进行速写式介绍,通过诠释相关概念和制度原理,阐明其制度设计中的合理性成分。其次对美国国会立法实践中的非正统立法现象逐一列举,并结合2009年奥巴马医改法案的产出过程,剖析非正统立法的策略选择及隐藏其后的政治原因。再次,揭示非正统立法程序的普遍存在如何成为行政权与司法权正常运行的障碍,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分权制衡机制的失灵。最后在结论部分,重申本文的写作意图。公然违背法治要求的民主实践何以能够为其理论辩护?经由明显违法的立法程序如何能够产出民主科学的制度产品?此间诸多吊诡,值得人们反思。
一、美国国会立法的正统程序 ——一种教科书式的解读
谈及国会立法的品性,美国学者多乐于使用“透明”(transparency)一词。这里所谓的“透明”,显然并非是对议员们行为方式的描述,而是对国会立法功能和立法机制的修辞式总结。虽然议员们私下里谈判妥协、秘密交易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制度层面的国会立法始终都是一项以明确的、统一的、连贯的方式制定或变更法律的公共事业,其透明性体现为立法机关 制定或变更法律,必须经过公众知晓的、确定的程 序[4]。应当说,立法程序的透明同其合法性是积极相关的。根据美国立法学教科书中的常见概括,国会立法程序大致包括四个必经阶段:国会议员提出法律草案;草案送交委员会,并在委员会进行审议和投票;草案送交国会,并在国会当中进行辩论和投票;草案递交总统,由总统签署或否决。上述四个阶段,无论缺失了哪一个环节,立法的透明性与合法性都将大打 折扣。
(一) 议案提交与议员责任
美国国会活动素来强调选民至上与议员责任,国会之中从议案到法的整个过程和全部环节,均体现出较强的议员主导性。不同于其他奉行议会立法的西方国家,在美国国会立法当中,民选的议员自始至终都有机会在立法进程中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即便是一名普通议员,只要其有意愿,便总能寻到恰当时机去影响议案的命运和走向③。
向国会提交议案是议员对选民负责最主要的形式。议员提出议案的背后往往有着复杂动机的支撑,议案的灵感可能直接来源于议员的理性和经验,也可能来源于社区选民的意见和提议。议案五花八门的起源决定着议案文本也一般出自多方之手,未必都是由议员亲自起草。实践当中,无论是议案的提出还是文本的撰写,利益集团通常都是主力军。但议案不问出处,有权向国会正式提出的只能是国会议员。当然,也会有例外的存在。少数情况下议案是由总统下属的工作人员根据总统的提议起草,并通过国会当中的政党领袖代表总统提出。
国会立法中议员责任的另一个体现在于,所有的立法,从动议到最终成型,都需在同一届国会的任期内完成④。凡是在任期中间未能获得通过的议案,即便已历经数劫,所有前期工作也要一笔勾销,在新国会中重新来过。如果国会控制力量仍然把持在同一政党手中,重新提交议案可能只是走走过场。但通常而言,换届同时意味着国会在政党势力结构上的改变,这种改变可能发生在众议院,也有可能发生在参议院,或者两者同时兼有。而每一个四年,这种政党势力格局的变化也有可能因总统换届而发生。但总体而言,任期所制造的压力都是巨大的,超过90%的议案都逃脱不了夭折的宿命。从侧面来看,任期压力对于议员而言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议员完全可以将其作为自己无法履行责任的借口。种种不可预期的制度原因的存在,使得在实践当中,议员只需宣布自己提交了议案,便可宣称自己履行了议员责任⑤。
(二) 委员会审议与议案分流
议案进入国会后,首先要经过委员会的筛选,委员会的筛选是能够决定议案生死的首要环节。在很多学者看来,实质意义上的立法权把持在委员会和委员会主席手中,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4]。从技术上看,国会发言人或众议院发言人有权决定将议案委派给具体的委员会,受到委派的委员会可能是单一的,也可能是多个委员会。通常情况下,挑选委员会的工作都由议会工作人员代劳,但如果议会领导人想要对某一议案施加影响,这时他就会选择亲力亲为,将议案委派给他认为值得信赖的委员会,通过这种方式控制议案的后续走向。议案进入委员会之后,由委员会主席负责对议案作进一步处理,如果委员会主席对手中的议案立场积极或是没有立场,通常的处理方式是将议案分发给子委员会。如果委员会主席对议案持消极态度,此时他完全可以不作任何处理,以默示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一票否决⑥。除非有其他方面因素对委员会主席施加压力,主席原则上可以自主决定议案的走向,这也就意味着其能在实质意义上掌控立法进程。同理,如果议案被分派给子委员会,对议程的控制权就落到子委员会主席手中。子委员会中同样存在至关重要的否决点,对于有争议的提案而言,子委员会的挑选同委员会的挑选一样,都可以成为关键的博弈手段⑦。
议案进入子委员会后,通常会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举行听证,二是进行审议。举行听证时,子委员会将邀请多方人员参与,针对议案进行发言。参加听证的人员从政府官员、学术界人士、各领域专家或者社会名人中选取,普通公民也有机会参与讨论。由于听证往往是由多数党组织,支持多数党意见的发言人自然偏多,甚至可能占绝对多数席位⑧。审议则是争论和修改议案文本的过程。不论提案人认为自己提出的文本有多完美,都不免要被修改。修改意图是多样的,一些友好的修改用意在于澄清议案文字的含义或议案的目的与效果,以使之更加符合议员们的胃口,从而有助于其通过。相反,一些不友好的修改,用意在于削弱议案的吸引力,从而降低其通过概率。不论出于友善还是恶意,修改通常都是细微的,极少涉及实质性的修改。如果子委员会对于提案及其修改达成积极共识,议案就会重新返回到委员会手中,委员会主席重新获得议案控制权,可以选择是否将议案送交委员会讨论,也可以选择忽略议案。进入到委员会议程的议案将会经历更多的听证和审议,这意味着最初提案者将被迫接受更多的修改建议以赢得委员会成员的支持。
(三) 议会辩论中的冲突与妥协
从委员会中脱颖而出的议案得以进入两院:众议院委员会通过的议案首先进入众议院,参议院委员会通过的议案首先进入参议院。对于议案的控制权于是转移到相应议院的政党领袖手中,由其决定何时对议案进行辩论——或者直接雪藏,除非议员联名请愿迫使其议院发言人决定对议案进行辩论。
参议院和众议院奉行不同的辩论规则。在众议院中,每项议案在进行辩论时也会受一套特定的辩论机制的约束;而在参议院,辩论是无限制的,并且随时可能会有冗长辩论的发生。在众议院中,规则委员会的成员组成由众议院发言人决定。规则委员会握有为议案设定辩论规则的权力,也即议案的生杀大权为规则委员会决定。事无巨细的辩论规则会具体到辩论的时间长度。通常辩论时间会在两党之间平均分配,再由各党派内部平均分配给想要发言的议员。除非有的议员不打算发言而将自己的时间贡献出来,每位议员发言的时间不会多于2分钟。规则委员会同时会决定辩论的起止时间,通常结束辩论意味着不再提出相应的修正案。在开放式规则下,对于提案者而言,辩论时间越短,对其便越有利。众议院规则委员会还有另一项特殊的权力,其行使会对立法产生重大影响,那便是自我执行规则。自我执行规则意味着一旦决议通过,议案所使用的具体文本便是终局定稿。这一规则的目的在于回避针对争议较多的议案进行投票。特别是议案修改的最后时刻,能够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对于辩论方式的选择极大扩充了规则委员会对于议案的影响力,又由于规则委员会成员由众议院发言人任命,实质上也就扩充了众议院主导势力在立法上的影响力。
在参议院中,并没有专门的委员会来设计辩论规则,参议院奉行的传统是无限制辩论。辩论一经开始便会持续进行,直到有3/5的议员投票决定辩论终止。辩论过程中,议员的发言时间不受限制,同时也不受所在政党领袖的控制。著名的冗长辩论便由此产生。冗长辩论指的是一个参议员或者一组参议员尽可能地把持发言机会,试图将议案在投票前扼杀或者迫使议案的支持者妥协,最终达成一个折衷的方案⑨。辩论终结的时刻便是最后投票的时刻。60票可以终结辩论,也意味着41票的少数派可以有效阻止一项议案进入投票环节,但这并不同时意味着进入投票环节的议案都能至少获得60票的支持。参议员对终结辩论投赞成票,却对议案本身投反对票,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反过来说,只要有41位参议员希望辩论持续,投票程序就将遥遥无期。因此,即使一个议案可能获得足够多数的赞成票,其也未必能够进入投票程序。
根据宪法,任何一项法律议案都要同时获得两院通过才能送交总统签署。这里面临的问题是,如果两院就同一议案展开讨论,即便从相同的议案文本开始,在分别经历两院辩论修改之后,最终得出的结果也可能大不相同。因此,相互冲突的议案还要再次经历两院之间的协商与妥协。这一过程经常会如同乒乓球赛,在两院之间展开拉锯。在这一期间,两院之间的交涉往往会涉及一些非正式的协商,同商业谈判别无二致。
(四) 一锤定音的总统否决点
总统否决点是分权制衡在美国国会立法当中的重要体现。根据宪法,总统对经两院通过的议案有权进行否决,如果国会要对议案再次通过,需要获得2/3的多数支持。如果总统未能积极行使否决权,对议案置之不理,10天后议案自动发生效力。这是总统否决点同委员会否决点的最大不同,总统无法像委员会主席一样通过置之不理的消极策略阻止议案的通过⑩。总统否决点是行政权对议案进行干预的直接方式,而并非唯一方式。在实践当中,总统如果想对议案的审议进程发挥影响,自法案到法的全程,都可以进行间接干预。最为常见的是,在竞选阶段,总统候选人便开始向社会公开自己的政策计划,以赢得选民支持。此外,在议案提交阶段,总统也可以指令下属起草议案,通过议会中的政党代表提交。在议案的审议过程中,总统还可以通过暗示否决权的行使威逼国会放弃某些立法提案或争议条款。总之,总统的支持或反对是议案成为法律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述简化过程虽不能直观反映美国立法过程的复杂全貌,但也可供我们对其立法过程的本质窥知一二。由于法案的提出者和支持者们总会想方设法地推动法案在两院通过,反对者则试图穷尽一切手段对法案的通过予以阻挠,立法每一环节堪比相互厮杀的象棋游戏,其实质是党派之间、利益集团之间的非合作博弈。但无论场面上怎样刀光剑影,私下里如何暗流汹涌,国会立法总是要遵循正统的立法程序,迎合公众对于民主的价值期待,从而维护其正当性与合法性。复杂立法程序的设计使得关于立法难题的实质性争议转化为程序性博弈,特别是对于一些难以谋求价值共识的根本分歧,只有程序性博弈才能起到定分止争的关键作用。
二、从有规则到无秩序—— 离经叛道的非正统程序
宪法、法律以及国会内部议事规则共同形成了国会立法的正当程序,然而联邦法院却一再拒绝适用上述法律对国会立法进行司法审查,换言之,国会立法对正当程序的遵守,除了依靠自律并无其他约束或监督机制[5]。对此,法官及学者给出的理由是,国会立法程序本身已经容纳了许多程序性限制,这些程序性限制可被视为一种自我约束机制。立法过程各个环节中直接或间接的程序性障碍,均能够对议员及相关组织的行为发挥制衡作用。此外,总统的否决权也被视作对国会恣意妄行的有效扼制。这一论调同麦迪逊式的乐观颇为类似。为国会立法活动设置程序性障碍的目的,从正面来看是为了强化审议机制和提高辩论的质量,从侧面来讲,是为了将争议较大或尚不成熟的立法及时扼杀。然而,纸面上的立法程序终究是静态的,现实中的立法活动则掺杂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更多迹象表明,程序所能发挥的自律功能其实是有限的,在缺乏外部监督的前提下,一旦程序性限制不符合参与者的利益需求,他们便会想方设法绕过程序[6]。几乎每一项议案背后都有着强烈的推动立法通过的动机,这些动机驱使立法参与者千方百计地绕过规则,以求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小成本推动法案到法的实现。近些年来,美国国会在立法过程中越来越频繁地利用立法程序中的灰色地带,甚至明目张胆地对立法程序进行篡改。这一现象日益引起美国学界重视,不少学者为此著书立说,直言教科书中的立法程序已名存实亡,由非正统程序所主导的立法规则正在被国会以其实际行动重新书写[3,6,7]。
(一) 非正统立法的类型考察
1. 一揽子立法(omnibus legislation)的泛滥
一事一议是美国国会立法长期奉行的准则。此外,美国有41个州的宪法也都明确规定了一事一议原则,禁止同一议案涉及一个以上的主题[8]。然而,这一原则已被实践中广泛存在的一揽子立法所突破。通过一揽子法案等形式进行的议案捆绑式立法初见于20世纪末,目前正处于极速增长趋势中。据统计,在最近几届国会中,一揽子法案的数量几乎占到主要立法的12%[9](113)。对于一揽子立法,尚不存在一个周延的定义对其进行准确解释,但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所谓一揽子立法,指的是将几种制度措施打包成一个集合,或将多个不同主题合并成一个法案。omnibus一词还有公共汽车的意思,其形象地反映了一揽子法案的特点,即一项不便于通过的法案,以搭便车的形式,依附于一项易于通过的或争议较少的法案,从而跃过立法过程中的关键性步骤,以求顺利获得通过。
实践当中,一些一揽子立法是以若干小型法案的集合存在,还有一些是在同一主题立法之下囊括了许多子主题。不管是小型法案还是子主题,它们往往都是由不同的委员会起草而成的,且草案文本的形成时间也多不同步,但不论它们相互之间多么不相干,都有机会在国会立法过程中被视作同一法案进行统一表决。一揽子立法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捆绑在一起的议案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为了推动法案当中符合自己利益需求的部分成为法律,议员们往往会对法案当中其他组成部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宁愿接受自己曾经反对过的决策,只要这样做的收益大过损失。例如,美国2008年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出台之前,中产阶级选民纷纷向议员施压,要求他们抵制法案中提出的资产援助计划,任由腐败的金融巨头自生自灭从而将经济秩序引上正轨。然而,该法案的支持者们却并不死心。为了平息中产阶级的抗议,法案的提出者为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包裹上了数层糖衣,新装上市并继续向选民兜售。针对不同类型的选民,新法案许诺了不同类型的“好处”,包括特定所得税的宽减;提高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承保的银行账户存款的数额上限;扩大保险公司对于精神健康服务的覆盖;针对1989年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油轮泄漏事件受害人的税收优惠,甚至还包括针对儿童木箭生产者的税收减免。这些彼此之间毫不相干的政策措施被打包在一起,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针对性地收买选民,促成一项不受欢迎的法案顺利获得通过。
一揽子立法看似能够使得立法过程中的冲突和争议得到缓解,大幅缩短立法周期,但立法效率的提高却是以议审和法案的质量作为代价的。一个典型的例证是,美国国会在2007年底通过了一项综合预算法案,其中共打包了11项子预算和1项补充性的战争资金。这项法案全文共3 417页,规模大约是圣经篇幅的3倍或等同于一本第二版的韦氏词典。然而,面对如此之鸿篇巨著,众议院在拿到议案全本后,用了不到22个小时便表决通过,参议院用时稍长,但也不过46个小时。显然,对于一项复杂冗长的一揽子法案来说,根本不会有人真正去读它,更不用说针对其展开充分的审议和辩论。
2. 紧急立法(emergency legislation)的滥用
紧急事态的发生是法案得以绕过正统立法程序——不需要委员会讨论,也无须制作相关报告而获得通过的另一正当化理由。由紧急事态引发的立法行为,尽管在发生之时有其正当性、必要性的基础,却在民主性与科学性方面欠缺说服力。因为紧急事态中的立法并非只能紧急事态下发生效力,而是自通过之日起便获得永久的、带有普遍性的约束力。例如,“9·11”事件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白宫和国会律师共同起草了授权使用武力的决议。没有经过任何委员会讨论,也没有经过正式的辩论,仅仅是在两院协商达成一致后,决议便获得了通过,前后只用了不过3天时间。授权使用武力法尽管是在“9·11”的特殊背景下发生的,却自其生效之日起,获得了永久性的法律效力,并且成为其后美国各类反恐政策措施的重要基础[3]。由于该法授予总统以史无前例的巨大权力,对于该项权力被滥用的现实与可能,一直是政界与学界关注的焦点,该决议本身的合宪性也始终受到学者的质疑。除国家安全领域的立法外,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相关政策性措施也是紧急立法的高发地带。同样,由于立法过程的选择性简化,相关立法往往存在论证不足的先天缺陷,其科学性不免遭到诟病,脱胎于金融危机时期的劣法,无法对金融秩序进行釜底抽薪式的诊疗,极易为后续危机的爆发埋下伏笔,由此形成恶性循环[10]。
3. 立法外包(outsourcing)
国会作为代议制机构,其立法行为的合法性基础在于选民与议员之间的紧密联结。然而近年来,国会越来越多地将重要的立法决策事项授权予非民选的机构甚至非政府部门,以回避立法过程中的重大争议,加速立法进程,这种现象被称为“立法外包”。由于接受外包的机构在行使决策权的过程中往往不会遵循规范化的工作模式,也不受成型的法律原则制约,同时制度层面也缺少对其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为法院阐释制度文本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之所以说“立法外包”现象中投射出反民主本质,原因正在于此,由类政府部门或私人机构行使实质上的立法决策权,不可避免地将对立法的可问责性构成严峻挑战。法令豁免是非传统授权的另一种形式。不同于授权政府机构在法律的模糊地带通过行使裁量权制定具体规范,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法律当中写入了豁免条款,允许行政部门决定何时对国会立法中的某些具体条款的效力进行悬置。决定何时对法律条款行使豁免权,并无特别的程序性规定,豁免权的行使存在较大的暗箱操作的空间[11]。
4. 框架式立法(framework legislation)
对于框架式立法,学界尚未形成明确的定义,系统性的研究也不多见,尽管其在美国当今的立法实践中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框架式立法往往为国会立法创设新型规则,这些法律通过预设内部程序,决定着未来相关立法的审议与投票程序,从而影响相关立法的实质内容。因此,尽管从表面上看,框架式立法只关心程序性事宜,但在实质层面,其对立法内容的影响不可小觑。从理论上讲,宪法决定了三权的分配与行使,行政程序法支配着行政决策的产出途径与方式,国会当中的众议院和参议院同样也有一套成型的议事规则,它们皆可被视为一种框架。但不同于框架式立法,上述法律框架的效力与适用带有普遍性与相对永久性,而框架式立法则是针对特定领域的立法事项具体作出的程序性安排,其适用范围较为狭窄[12]。通俗地讲,框架式立法就是国会针对某些特殊立法事项设定的特殊程序,为了达到方便某项法案通过的目的,国会以决议的方式允许该法案不必经过一般的立法程序,允许在特定立法环节中存在规则的例外。
(二) 非正统立法的集大成者——奥巴马医改法案
2010年奥巴马医改法案的通过也许是美国21世纪争议最大的立法事件之一。对于政治家、经济学家或者普通公众而言,辩论主要围绕实质性问题进行,争议焦点在于医改是否能如预想般为全体美国民众创造平价医疗的福利,又或是否如反对者所言,将导致国家医疗系统的全面崩溃,乃至国家破产。然而对于从事立法学研究的学者而言,法案通过的程序性问题及其为美国民主法治带来的负面影响,才是更具讨论价值的核心问题。奥巴马医改法案的通过可以说是美国国会立法程序非正统化的一个典型例证,例如为减少分歧而将几个法案加以捆绑的一揽子立法、为确保议案审议通过而专门创设特别程序的框架立法,均在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美国医疗改革事业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至罗斯福时代,克林顿、小布什任期下的历届国会也均为此作出过努力,延续这一政治历史,推动医疗改革自然成为奥巴马任期内的头等大事。从前几任政府的失败中,奥巴马吸取了教训,他没有指令行政部门起草相关制度文本——尽管这是总统提出立法议案的传统做法,而是在明确列举了几项宽泛的原则和目标之后,将更为具体的立法细节问题指令交由国会处理。在奥巴马的总领下,国会方开始炮制医改方案的制度文本。早在最初版本的议案提交国会之前,对议案拥有管辖权的劳工委员会、能源与商务委员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便内部达成一致,要减少分歧,确保法案的通过。在众议院多数派发言人南希·佩洛西所提出的讨论稿的基础上,三个委员会经过讨论,于2009年7月14日提出美国平价医疗选择法案,即3200号众议院议案,随后该法案进入委员会审议程序。尽管三个委员会在各自的审议过程中极力压制争议以保全3200号议案,但当各个委员会将讨论好的三个版本的3200号议案提交至国会时,却惊讶地发现无法将其排入国会议程[7]。按照传统的立法程序,三个不同版本的3200号议案只能被暂时搁置,等候排期。然而,为使医改能够顺利挤进议程班车,三个版本的3200号议案被彻底废弃,而由空降的3962号议案取而代之。之所以将3962号众议院议案的诞生比喻成空降,原因就在于其并没有遵循正统的立法程序。任何一项议案要进入国会讨论,必先经过议员提案、委员会审议等程序,然而3962号议案完全省去了上述步骤,甚至没有在委员会当中进行实质性审查。更为戏剧化的是,2009年11月7日,众议院规则委员会通过903号决议,该决议为3962号议案此后在国会中的走向设置了特别程序:不仅允许3962号议案在众议院议程中插队,并且将辩论时间限定为几小时,将议案的修正范围限定为两个事项,此外还要求辩论结束后立即进行投票。这样一项决议的通过仅仅花了1小时的时间。就在当天,3962号议案也得以在众议院中进行辩论,4小时之后便获通过,3天后被提交至参议院。
民主党急切想要推动医改进入国会议程,并非是出于一时心急,而是基于重要的政治考虑。2009年8月25日,医疗改革的支持者,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泰德·肯尼迪去世,这威胁到了医改法案在参议院中的60票多数地位。2009年9月24日,民主党保罗·柯克作为临时参议员填补泰德·肯尼迪在参议院中的议席,为医疗改革暂时保住了参议院中的第60张支持票,而该议席的最终归属仍然处于未定,民主党不得不抓紧利用眼下的有利时机,确保议案顺利通过。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众议院不得不操控立法程序,使用903号决议这一工具,为3962号议案设定程序性框架——这正是前面提到的框架立法在奥巴马医改法案通过过程中的重要体现,同时也反映了程序性设置对于立法实质内容的重要影响。
尽管颇费周折,众议院提出的3692号议案并未能够进入参议院委会员审议,因为当众议院设法炮制医改方案之时,参议院也在极力推动形成自己的议案版本。这是奥巴马医改法案形成过程中另一个不同于正统立法程序之处。在正统的立法程序当中,往往是同一议案在众议院与参议院之间形成乒乓球赛式的拉锯战,然而这里却出现了两个医改议案,一个由参议院提出,一个由众议院提出。这使得医改法案的通过由判决题变为选择题——不管哪个版本能够最终胜出,本质都是医改的胜利。任何一个议案如果要想获得最终通过,都必须获得两院一致的赞成,而参议院又渴望保住自己提出的议案版本。于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里德计划从众议院提交的几项议案中选择一个议案,并将其同参议院提出的医改议案进行混合,达到“1+1=1”效果。为什么一定要从众议院提出的议案中选择一项同参议院医改议案进行捆绑?其用意是不难理解的,这是在向众议院伸出橄榄枝。如果一项在两院之间踢皮球的议案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折衷产物,两院相互妥协就会更容易。为什么参议院最后没有接受众议院3962号议案,将之同参议院的医改议案相互嫁接,原因也十分明显,因为两个版本的医改议案存在较多的冲突,不利于缩短战线。出于上述两点原因,参议院将众议院早先提出的一份已然过时了的3590号议案请入委员会进行审议,并在审议过程中,用修正案的形式实现了参议院医改方案的 渗透。
就在参议院医改方案成功实现了“借壳上市”,用3590号议案的旧瓶装了医改法案的新酒之后,新的矛盾又随之而来。2010年1月,医疗改革的反对者、共和党人斯科特·布朗当选为马萨诸塞州参议员、这意味着假如经参议院修订后的3590号议案不被众议院接受,或者在众议院讨论后被再次修改,修改后的议案返回到参议院时,恐难再获得60票的支持。一面是众议院对于3590号议案的不满,一面是参议院共和党派的威胁,一面是医改法案必须获得通过的政治野心。三面两难之间,两院不得不再次在立法程序方面做文章:第一步是由众议院通过3590号议案,并交由总统签署生效。第二步是由众议院提出一项议案,即众议院4872号议案,对生效后的3590号议案进行修正。4872号议案要想在参议院中顺利通过,那它必须不能是一项普通的议案,而必须是一项有关“预算协调”的议案(budget reconciliation),因为此类议案只要得到简单多数即51票支持就能在参议院中获得通过。就这样,3590号议案首先成为正式的法律,4872号议案由于进行了预算捆绑,也在参议院中获得通过,成为正式的法律,并对3590号进行了修正。两院民主党议员均皆大欢喜,奥巴马医改也获得了所谓的成功。
正如许多学者所说,奥巴马医改法案的胜利,是非正统立法程序的胜利,其即便不足以宣告宪法维护下的正统立法程序的彻底死亡,也已然对其长久宣称的民主法治实践造成了深远的不良影响[13]。正当程序被认为是美国宪政理论的基石,国会立法是民主法治实践的重要起点,如果立法者尚且不能尊重与维护程序的独立价值,视程序性规则为实现政治谋略的手段,人们又如何能够期待执法者与司法者能够在其后的法治接力中做到不偏不倚。
三、失向的马车——国会立法的非正统程序如何影响行政与司法
国会立法要进入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毫无疑问离不开行政权的配合,需要行政部门通过制定行政规则等手段为国会立法提供配套措施。在国会频繁借用非正统程序加速立法的大环境下,行政部门也难以不受影响。例如,一揽子立法的产物动辄几千页,并且往往要求行政部门在有限的时间内作出反应,这使得经由一般程序制定规则变得不切实际,必须通过更为灵活的方式作出行政决策以回应法律实施的需求[14]。为加快行政决策的产出,行政指导被大量使用,以绕过制定规则所需经过的公示评议程序,同时规避法院的司法审查。将发布行政指导认定为非正统的规则制定,从学理意义上讲,也许并不恰当,因为行政指导不同于行政规则,本就无须经过公示评议程序,这是由美国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的。然而在实践中,行政指导不仅在数量上已远远超过通过公示评议程序制定的行政规则,并且,大量的行政指导能够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上的影响,它们虽不是规则但已胜似规则。这就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和警惕。近些年来,已有大量学者撰文对行政部门滥用行政指导的现象进行批判,并指出其违宪本质。对于行政部门滥用行政指导的原因,也不乏深刻的分析与洞见,正如许多学者所揭示的,非正统的规则制定同非正统的国会立法密切相关。国会立法为从立法僵局中脱身,而将充满争议的政策难题留给行政权解决,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之下,行政机关不得不设法另辟蹊径,从台前转向幕后,脱离法定程序的束缚[15]。此外,美国国会立法素来被认为是党派利益集团妥协的产物,而经由非正统立法程序产生的国会立法,由于缺少实质性的审议和辩论环节,其妥协性更加明显,对于争议问题和难点问题,要么采用模糊语言加以处理,要么直接授权行政部门加以解决。面对国会转嫁而来的矛盾,行政部门除了大量使用行政指导以规避争议与审查外,另一常见做法是将执行法律的重任转嫁给各州议会、各州政府、准政府部门甚至是私人主体,以达到回避政府风险,节省规则制定成本的目的——前文提到的立法外包现象不仅存在于国会立法当中,在规则制定层面也十分普遍。
不管是发布行政指导还是将制定具体规则的任务外包给各州政权或私人机构,从规制效率上看,上述两种做法或许可以找到合理性理由,但在合法性层面,非正统的行政规制至少难以经受以下两点拷问:其一是决策结果的可问责性。其二是决策过程的公开性。由于州政府和私人主体在信息自由法和行政程序法的效力范围之外,由它们作出的行政决策或类行政决策难以受到来自联邦层面的直接监督,并且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在目前的法律架构之下,无法就上述两类主体的行为在联邦层面获得司法救济。如果说州政府的行政决策在某种程度上仍会受制于本州的行政程序规定并且可能留有相关记录供公众查阅,由私人主体作出的类决策行为则几乎处于程序规制的真空地 带,公众更是缺乏相关渠道参与决策过程,获得决策 信息[16]。
司法部门被认为是美国民主法治的最佳守护者,因为法院时常会从大局出发,对社会价值和公共利益进行通盘考量,以决定如何解释和适用法律。尽管国会立法是否遵循正当程序并非法院审查的对象[17],法院却可以通过对法律当中充满争议的模糊地带进行诠释,从而对法律文本的实质内容发挥重要影响,间接弥补和修正由于立法审议不足而造成的立法瑕疵或制度缺憾。然而,这并不等于说,非正统立法程序对于司法权的行使不会带来消极影响,这恰恰说明,经由非正统程序的大量使用,将会在无形之中加重司法部门的工作负荷,增加最高法院对法律条文进行解释的难度。正如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的经典判词:在民主国家,制定法律的权力掌握在人民选出的议员手中,而我们的作用,不过是对法律进行宣告。法官终究不是立法者,其基本功能在于宣称什么是法律。这就决定了,法院功能得以发挥的前提,是法律本身有被解读和宣告的可能。
从立法本身来看,未经充分审议同时又掺杂、糅合了形形色色政治妥协因素的制度文本,不仅在民主价值层面存在缺陷,从立法技术和文本质量上评价,多数也是充满印刷错误、表述前后矛盾或用语不统一的瑕疵产品,这些瑕疵在国会使用一揽子立法策略时暴露得更为明显。一方面,一揽子立法的文本不仅主题和内容杂乱,篇幅更是极为冗长。例如在King v. Burwell案中,最高法院遭遇到的奥巴马医改法案,篇幅就长达2 700多页[13]。另一方面,文本解释可说是近些年来最受法院欢迎的解释方法。支撑文本解释正当性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最高法院对于国会角色和职能的基本定位:尽管国会的理性被认为是有限的,但国会的立法却被推定为是全面的、精确的、简洁的和完美的[13]。正因如此,法院在解释争议条款之时,时常会从法律文本的上下文寻找线索,例如推定制度文本应是一个统一连贯的整体,同一用词或短语在全文当中具有相同含义,借以推断争议条款的准确含义。然而在King v. Burwell案中,论辩的双方均能够通过文本找到有利于自己一方的有力证据,法律文本非但未为法官裁决提供线索,反倒将司法权力推向两难。在以往的一些案件中,立法史通常能够在最高法院解释法律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论是探究立法意图还是解读文本本身,立法史都是支持法官得出结论的有力佐证,而这也正是非正统立法对法院解释法律构成挑战的又一原因。正统立法程序当中的委员会审议记录、两院审议记录等,都是法院发现立法史的重要素材,这些恰好是非正统立法所缺失的[7]。此外,在非正统立法的全过程当中,常常是有数项议案纠缠不清,正如我们在奥巴马医改法案的形成过程中看到的,在众议院已经先后存在了两项议案,尽管这两项议案都以医改为名。与此同时,参议院也提出了自己的医改议案。为了确保医疗改革这一政治任务能够顺利完成,两院在妥协之下,还借用了其他同医改毫不相干的议题。这些大大小小名称不一的制度文本,起草的人员不同、产生的时间和历史背景各异,可以说是各有各的历史。最终形成的后果便是,医改法案的通过虽有其产生的历史,却并不拥有具备法律解释价值的立法史[7]。
四、结论
正当立法程序作为立法之法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其对于政治决策的产出能够起到关键性作用,直接影响到立法审议与立法成果的质量,还因为程序本身具备独立的价值,其构成立法活动的合法性基础。正如程序主义民主理论所强调的,由于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复杂多元而又无法通约的实体价值与利益纷争,人们无以找到一个实质性的标准去评判集体选择的优劣,集体选择之所以应被人们认可,只能诉诸程序正义去构建共识。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建立在公开透明程序基础上的立法活动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可与支持,公众也更愿意服从法律。这更使得立法程序自身带有民主属性——因为设置程序的目的便在于确保立法反映多数人意志,透明、公开、审议、广泛而充分的参与是确保多数人意志得到充分表达的关键词。
效率与民主之间的价值冲突难题在法治实践中随处可见,集中体现为结果主义与程序主义之间的张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追求绩效,必以牺牲公开透明等程序价值为前提。尽管非正统立法程序的支持者们乐于从立法结果和规制效率层面为其逾矩寻求辩护,认为只有更为果敢的决策者才能满足当前风云变幻的社会诉求,以往的繁文缛节反倒成为成全公共福利的阻碍。然而,这种粗放式的结果主义是否能够真正等同于成全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这一追问直接指向了现代法治安身立命的根本。从法治的角度来说,不仅程序正当是法治的基本要义,立法程序本身也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得到实现的重要保障。正如拉兹所强调的,法律的制定应当遵循公开和稳定的规则指引。规范立法者如何立法的程序性规则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划分法治与人治的标志[18]。
如前所述,本文写作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揭示美国当前立法实践同其传统民主法治理念的背离与矛盾。本文关注对现象进行描述,立足于求真,而非得出结论或更深层面的价值评判——尽管个人立场在写作过程中不可避免。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哲学原理出发,美国非正统立法程序的普遍化或可从其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的复杂化中找到解释,相关现象的产生并非偶然。反之,基于上层建筑的争议,能否进一步激化和加深社会矛盾,尽管仍是未知,却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一种必然。当今美国法治的诸方面,均面临着民主性与合法性的危机与挑战,而本文所揭示的问题尚不及之冰山一角。
对于当下中国而言,从西方民主法治理论及实践中汲取合理养分,向法治发达国家学习借鉴制度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一定意义。但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去粗取精,笔者认为一方面应采取批判的视角,另一方面保留借鉴的可能,对于确保我国立法的民主性与科学性而言至关重要,需要立法理论家和实务者具备更为广阔的策略眼光和采取更为精准的技术考量。
注释:
① 新自然法学代表人物、美国法学家富勒提出了法律制度应该具备的八项原则:法律的一般性、法律的公布、适用于将来的而非溯及既往的法律、法律的明确性、避免法律中的矛盾、法律不应要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法律在时间之流中的连续性、官方行动和法律的一致性。英国法学家约翰·菲尼斯也提出过法治的八项要求,同样强调法律的稳定性、明确性、一致性和普遍适用性。在新分析实证主义代表人物英国法学家拉兹对法治原则的分析中,所有法律都应当可预期、公开且明确,并且法律应当相对稳定。
② 一般认为这一比喻出自美国诗人萨克斯,原文为“Laws, like sausages, cease to inspire respect in proportion as we know how they are made”,但也存在一些争议,原文可以参见:https:// quoteinvestigator.com/2010/07/08/laws-sausages/。
③ 在其他奉行议会制的国家,主要是由首相及其内阁提出议案,由专员起草法律。如果内阁对法律草案表示满意,才会向议会提交议案。议会中的普通成员仅仅是作为投票者参与到立法的最后一个环节中。
④ 美国国会通常在偶数年的11月选举,新国会在下一个奇数年1月上任,每届国会任期为2年。
⑤ 除了任期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客观因素也会导致提案的失败。例如,针对同一社会问题,往往会有多个版本的议案相互角逐,这些版本之中至多只会有一个胜出。实践中,大部分选民无暇去跟踪议案的走向,普通选民只注重开始,而不关心能否猜中结局。
⑥ 否决点是否决者能够施加影响、扼杀议案的重要时刻点,是否决者控制议程的一项重要策略。通过操控否决点,否决者不仅能够推动自己关注的事项进入议程,同时也可迫使其他事项脱离议程轨道。
⑦ 例如,1963年民权法案被引入国会后,先是被分派给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司法委员会主席将议案委派给第五子委员会——一个通常负责反垄断事务立法的委员会。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安排,原因就在于第五子委员会由民权运动倡导者所主导,并且其中没有高层南方代表。
⑧ 多数党的成员往往不会轻易决定要对一个议案进行审议,除非他们对议案的内容已经达成了共识。仅仅因为他们是多数党成员,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在同一议案上达成共识,因此立法过程中的斗争是很激烈的。例如,在奥巴马医改法案的通过过程中,能源商业委员会民主党中的保守派成员对自己政党的议案予以保留性的支持,在同委员会主席讨价还价后才最终表示支持,委员会才得以正式开启审议程序。
⑨ 冗长辩论作为参议院一项重要的议事规则,自其存在之日起便饱受争议,迄今为止已历经了多次改革。传统上,冗长辩论的形式是发起冗长辩论者持续占据议院发言位置且不间断地发言。因为参议院一次只讨论一项议案,冗长辩论将使得后面的议案得不到辩论的机会。如果议员希望能够对后面的议案进行讨论,就不得不向冗长辩论者妥协。但是要求冗长辩论者长时间站立并持续数小时地发言,如果没有其他参议员愿意一起协助的话,单独的冗长辩论者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于是,参议院在1970年修改了规则,允许双轨制立法过程。参议员可以同时讨论多项议案,如果其中一个被冗长辩论所阻隔,他们只需将相关议案放置一边转而讨论其他的议案。此外,也不再要求冗长辩论的议员长时间不间断地发言,他们所需做的只是向参议员们知会其立场,除非大多数参议员能够形成41的投票终止辩论,这些冗长辩论者会持续努力试图说服参议员对终结辩论投反对票。
⑩ 当议会任期所剩时间不超过10天时,总统可以无视议案,通过搁置否决权使法案自然死亡。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305.
[2] 汉密尔顿, 杰伊, 麦迪逊. 联邦党人文集[M]. 程逢如,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45−46.
[3] GLUCK A R, O'CONNELL A J, ROSA P. Unorthodox lawmaking, unorthodox rulemaking[J]. Columbia Law Review, 2015(115): 1789−1866.
[4] WALDRON J. Representative lawmaking[J].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09(2): 335−356.
[5] ITTAI BAR-SIMAN-TOV. Legislative suprem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Rethinking the enrolled bill doctrine[J]. Georgetown Law Journal, 2009(2): 323−390.
[6] ITTAI BAR-SIMAN-TOV. Lawmakers as lawbreakers[J]. William and Mary Law Review, 2010(3): 805−872.
[7] CANNAN J. A legislative history of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How legislative procedure shapes legislative history[J]. Law Library Journal, 2013(2): 131−174.
[8] GILBERT M D. Single subject rules and the legislative process[J].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aw Review, 2006(4): 803−870.
[9] SINCLAIR B. Unorthodox lawmaking: New legislative processes in the U.S. Congress, Washington[M].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1997: 113.
[10] ROMANO R. Regulating in the dark and a postscript assessment of the iron law of financial regulation[J]. Hofstra Law Review, 2014(1): 25−94.
[11] WATSON S D. Out of the black box into the light: Using section 1115 medicaid waivers to implement the affordable care act's medicaid expansion[J]. Yale Journal of Health Policy, Law and Ethics, 2015(1): 213−232.
[12] GARRETT E. The purposes of framework legislation[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Legal Issues, 2005(2): 717−766.
[13] GLUCK A R. Imperfect statutes, imperfect courts: Understanding congress's plan in the era of unorthodox lawmaking[J]. Harvard Law Review, 2015(1): 62−111.
[14] GREVE M S, PARRISH A C. Administrative law without congress[J]. George Mason Law Review, 2015(3): 501−548.
[15] FARBER D A, O'CONNELL A J. Lost world of administrative law[J]. Texas Law Review, 2014(5): 1137−1190.
[16] STRAUSS P L. Private standards organizations and public law[J]. William & Mary Bill of Rights Journal, 2013(2): 497−562.
[17] LINDE H A. Due process of lawmaking[J]. Nebraska Law Review, 1976(2): 197−255.
[18] WALDRON J. Legislation and the rule of law[J]. Legisprudence, 2007(1): 91−124.
Elected Congress but undemocratic legislation: An observation on the unorthodox legisl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US
WANG Yi
(School of Law,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merican Congress is famous for its multi-level, complexity and specialization. Seen from the view of the theorists, this structure provides a workplace for the interest groups to communicate and negotiate with each other. However, the dedicate theory tends to be hard to implement in practice. In the recent years, American Congress has made frequent use of the grey areas to facilitate unorthodox legislation such as omnibus legislation, due to which, a large number of bills have been approved of without adequate deliberation and debate. Just as scholars comment, the typical legislation described in textbooks is dying with the unorthodox legislation dominating the Congress. In order to learn about the democracy and rule of law in America, we need to explore and evaluate the practice of the Congress. Examining the phenomenon and the impacts of unorthodox legisl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US will shed some new light on our perception of the western democracy and its legislation institution.
legislation in the US; legislation procedure; unorthodox legislation; democratic legislation; rule of law
[编辑: 苏慧]
2018−01−21;
2018−03−30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的立法体制研究”(15JZD006);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培育项目“地方立法中的利益集团参与机制研究”(1709046)
王怡(1985—),女,山东烟台人,法学博士,中山大学法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立法学,联系邮箱:maryann77@163.com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8.04.006
D90
A
1672-3104(2018)04−004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