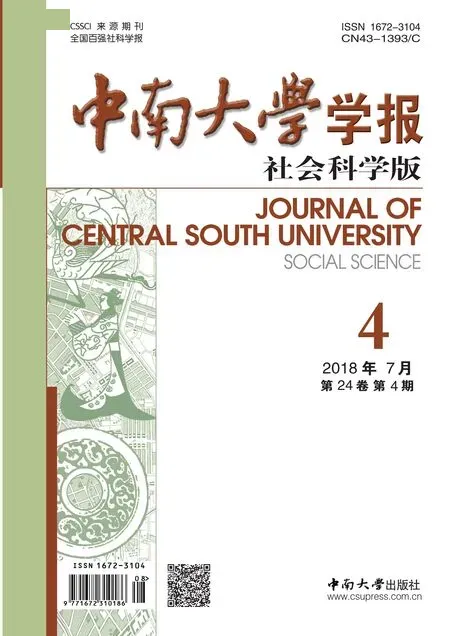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的著作权授权机制探讨
何炼红,郑宏飞
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的著作权授权机制探讨
何炼红,郑宏飞
(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公共文化机构大规模数字化建设的步伐日益加快。授权许可、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传统著作权授权机制在数字环境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导致我国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面临高昂的交易成本或潜在的侵权风险。建议完善我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引入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的一种可行路径。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对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绝版作品进行延伸性集体管理,并从程序上和实体上为绝版作品著作权人建立权利保障机制,以实现保障著作权人合法权益和促进优秀文化传承的有机统一。
公共文化机构;绝版作品;数字化利用;延伸性集体管理;权利保障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运用和数字传播技术的日益普及,公共文化机构①传统的馆藏作品保存与传播方式已无法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也难以满足普通公众文化多样性的需求,公共文化机构开展大规模数字化建设的迫切性日益凸显。与此同时,由于文化产品供给更新速度日益加快,社会生活中涌现了越来越多的绝版作品,绝版作品在公共文化机构馆藏作品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由于著作权相关立法的滞后,我国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利用②绝版作品将面临高昂的交易成本或潜在的侵权风险。如何在公共文化机构大规模数字化建设过程中,降低其所面临的高昂交易成本和潜在的侵权风险?如何在保障绝版作品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释放绝版作品的文化价值?本文在对绝版作品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拟对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的可行路径进行探讨,以期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回应公共文化机构在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二、绝版作品的界定及概念辨析
从法律实证主义的视角来看,绝版作品并非我国著作权法体系中的法律概念,而是著作权法和图书馆学等领域的学者们所创设的一个学术概念。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须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问题[1]。因此,在探究我国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的可行路径之前,首先需要对绝版作品的基本含义及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析。
(一) 绝版作品的界定
从我国当前的著作权法理论来看,绝版作品仍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话题。虽然有不少学者在学术论文中都提及过绝版作品(图书)的概念③,但鲜有学者对绝版作品的概念进行专门论证。其实,早在2001年,欧盟便已经对绝版作品进行了界定,并开始讨论如何解决数字环境下绝版作品的数字化利用问题[2],因此,考察欧盟著作权法语境下绝版作品的概念,可以为我们界定绝版作品提供有益的参考。
历经十多年的发展,绝版作品在欧盟当前的著作权立法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含义,即绝版作品指那些仍在著作权法的保护期限内,却无法通过传统的商业渠道获取的作品(例如,作品的著作权人或出版商已经停止出版或销售)[3]。不过,在我国学术界,目前对于绝版作品的理解仍莫衷一是。例如,有学者认为,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七条所规定的两类特殊作品④属于绝版作品[4]。但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该条例第七条所规定的两类特殊作品仅仅是与绝版作品存在重合之处,并非当然都是绝版作品。有学者认为,绝版作品处于著作权法保护期限内,但大多已经不再重印,不能再给出版商和作者带来经济利益[5]。还有学者认为,绝版作品是指在著作权法保护期限内且拥有巨大的文化、科学、教育和历史等价值,而公众无法从传统的商业渠道获取的作品[6]。尽管国内学者对绝版作品的具体表述未达 成共识,对其具有的以下两个重要特征却都予以 认可。
其一,绝版作品是仍处于著作权保护期限内 的作品。基于著作权法保障私人利益、促进社会进步的二元立法目的,著作权人对作品的专有权利具 有期限性,超过著作权法规定的保护期间的作品将进入公有领域,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和免费使用。因而,仍处于著作权保护期限内是构成绝版作品的前提 条件。
其二,绝版作品是难以通过传统的商业渠道自由获取的作品,这是绝版作品区别于其他作品的关键特征。当整个作品通过传统的商业渠道无法获得或不能合理预见到可以获得时,这类作品便可以被视为绝版作品[7]。例如,当某一类作品的有形复制件只保存于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或特定公众手中(包括二手书店或古文物书店),其所有版本和有形载体都不能从传统的商业渠道自由购买,则可认定该作品已 绝版[8]。
由此可知,国内学者对绝版作品的理解与欧盟著作权立法语境下的绝版作品含义基本一致⑤。本文所界定的绝版作品,也是指那些仍在著作权法的保护期限内,但无法通过传统的商业渠道获得或不能合理预见到可以获得的作品。
(二) 绝版作品的文化价值
每年,我国都会出版大量的图书、期刊、音像制品以及电子出版物,在这些出版物中必然会产生不少的绝版作品。这些绝版作品形成的原因多种多样,最为普遍的原因在于其不具有可观的商业价值,著作权人或出版商基于对经济利益的考量而不再重新出版该作品。随着已出版的作品在商业市场上销售告罄,该作品便逐渐成为绝版作品。需要指出的是,绝版作品并非“一文不值”,只是其蕴含的绝大多数商业价值已经被先前的出版行为所“消耗殆尽”,剩余的商业价值不足以激励著作权人或出版商将其再版。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并非完全同步存在,不具有可观商业价值的绝版作品并不意味着不具有文化价值。
当然,不同的绝版作品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不尽相同。在公共文化机构馆藏的海量绝版作品中,只有具有较高文化传播、科学研究、公众教育等价值的绝版作品才有数字化利用的必要性。此类作品对于许多学者、科研人员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公共文化机构对其进行数字化利用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三) 绝版作品与孤儿作品的关系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普及,绝版作品和孤儿作品已成为各国公共文化机构大规模数字化建设的主要障碍。孤儿作品是指那些经过使用人勤勉尽力寻找,仍然无法被确认或无法找到权利人且仍处于版权保护期内的作品[9]。绝版作品和孤儿作品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皆处于著作权法的保护期限内,但是,两者在使用前提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对于绝版作品的使用,关键因素是要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而对于孤儿作品的使用,其前提是要确定“孤儿作品”的状态[10]。从法律性质和特征来看,绝版作品强调该作品难以在传统的商业市场上自由购买或不能合理预见到可以获得,其著作权人可能为公众所知晓也可能无法被确认,孤儿作品则强调该作品的著作权人状态不明。正是因为绝版作品和孤儿作品存在诸多差异而理论界鲜有研究绝版作品的学术论文,因而,探讨绝版作品的利用问题具有显著的独立价值。
虽然绝版作品和孤儿作品的使用前提不尽相同,但制度设计的初衷却殊途同归,即最大限度地释放作品的文化价值,保障普通公众接触优秀文化的机会。学术界对孤儿作品的利用问题已经探讨多年,许多学者对孤儿作品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以及延伸性集体管理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学理分析和制度构建。学界针对孤儿作品利用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对于本文探讨如何采取可行路径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三、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利用绝版 作品的现实困境及法律障碍
(一) 授权许可面临高昂的交易成本或极大的侵权风险
由于绝版作品所蕴含的绝大多数商业价值已经在先前的出版行为中“消耗殆尽”,其剩余的商业价值已不足以激励著作权人或出版商将其再版,故著作权人往往对绝版作品采取置之不理或不置可否的态度。我国当前的著作权授权机制和交易规则以授权许可模式为主,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如不符合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著作权法规定的特殊情形,则需要逐个获取绝版作品著作权人的事先许可。此种情况下,公共文化机构将面临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基于保存人类文化遗产、传播人类优秀文化的社会职能,公共文化机构需要将馆藏的海量绝版作品进行数字化利用以保障普通公众平等获取知识和文化的权利,然而,这样将因其中的部分绝版作品未经过著作权人授权而面临极大的侵权风险。另一方面,如果公共文化机构通过逐个搜寻并协商的方式以获取绝版作品著作权人的授权,则将产生高昂的交易成本(包括搜寻成本、协商成本等),公共文化机构的数字化进程将因经济成本过高而进展缓慢,最终损害的仍然是普通公众获取知识和文化的权利。为规避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而可能面临的侵权风险和交易成本,公共文化机构往往会将馆藏的绝版作品“束之高阁”,从而会使大量绝版作品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被闲置和掩埋,甚至还可能使下一代丧失接触优秀文化的机会。在著作权制度诞生之初,由于传播技术的落后,作品只能物化在有形载体上传播,使用者也仅能以获取载体的方式利用作品[11],作品的市场需求量较小、利用方式较为单一,授权许可模式完全可以应对印刷时代的著作权市场交易需求。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普通公众对作品的需求方式日趋多元化,作品使用者日益要求提高作品许可效率,传统的授权许可模式已经成为普通公众数字环境下快捷、高效获取作品的障碍。综上,由于授权许可将导致公共文化机构面临高昂的交易成本或极大的侵权风险,无法同时兼顾绝版作品著作权人和公共文化机构之间的利益,难以成为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的有效路径。
(二) 合理使用制度难以保障绝版作品著作权人的经济利益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公共文化机构基于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目的,复制馆藏的作品”为合理使用情形。《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七条对该条款进行了细化规定并将其延伸至网络空间,将“公共文化机构以非营利性目的向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馆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也界定为合理使用。需要明确的是,该条例中所说的“提供”仅指为公众提供获得作品的可能性,而不实际将作品发送至公众手中[12]。从上可知,公共文化机构将以下两类作品向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属于合理使用:一是公共文化机构馆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二是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这两类作品与绝版作品具有重合之处,但并不能涵盖所有绝版作品。例如,有些绝版作品在出版之时并非数字形式,同时也并非所有馆藏的绝版作品都符合“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这一严苛条件⑥。公共文化机构对于这两类作品以外的绝版作品进行数字化复制、向公众提供则有可能面临侵权风险。此外,《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七条虽然将公共文化机构通过信息网络向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这两类作品界定为合理使用⑦,但将提供对象严格限制在“本馆馆舍内的服务对象”。而“本馆馆舍内”概念很明确,就是指图书馆物理馆舍内即实体建筑内[13]。该条款对于馆舍内服务对象获取部分绝版作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无法为馆舍外的众多作品需求者获取绝版作品提供渠道和机会,这将极大地限制公共文化机构普及知识、传播信息的社会服务功能。
最为重要的是,即使通过修改上述法律法规将公共文化机构对所有馆藏绝版作品进行数字化利用的行为界定为合理使用,也将与合理使用制度的价值理念和内在机理相违背。由于绝版作品仍具有剩余的商业价值,如将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的行为界定为合理使用,则可能导致大量的作品使用者绕过绝版作品著作权人而直接从公共文化机构获取绝版作品,从而可能使绝版作品著作权人的获得报酬权被架空,甚至还可能助长和纵容作品使用者的侵权行为。此种情况下,著作权人的经济利益将会受到实质性的损害,不仅与“三步检验法”⑧的精神相违背,更与著作权法的制度设计理念背道而驰。因此,合理使用制度不能为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提供充分的制度支撑。
(三) 法定许可制度定价效率低下且将剥夺著作权人的许可自由权
法定许可制度通过法律直接规定代替著作权人与使用者之间的协商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与合理使用制度相比,作品使用者通过法定许可制度使用绝版作品需要支付相应的报酬,从而减少了对著作权人经济利益的损害;相较于私人协商,作品使用者只要符合法定许可条件便可以在支付报酬后直接使用绝版作品而无须征得著作权人同意,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将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的行为界定为法定许可,既能保障绝版作品著作权人的经济利益,又能降低公共文化机构的交易成本和侵权风险,看似能有效地解决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的合法性问题,并能实现公共文化机构和著作权人两者利益的有机统一。事实上,考察法定许可制度的实施效果即可发现,法定许可制度不仅未像理论设计中一样发挥应有的功能,而且自其被写入著作权法之日起便因“涉嫌公权力干预著作权人私权”而备受质疑和诟病。如将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的行为界定为法定许可,将面临以下制度困境。
其一,法定许可制度自身存在定价效率低下的弊端。在实践操作中,法定许可的定价方式具有非常强的行政化色彩,由不参与市场交易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来确定付酬标准。如法定的付酬标准高于公共文化机构的预期价格,则将迫使公共文化机构放弃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最终将减少绝版作品著作权人的经济收入;如法定的付酬标准低于公共文化机构的预期价格,则可能损害绝版作品著作权人的经济利益,挫伤著作权人创作作品的积极性。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中,商品的价格应当由商品自身所蕴含的价值和市场供需关系来决定,法定许可的定价方式不仅无法真实反映绝版作品的市场价值,更会人为提高交易成本。
其二,绝版作品著作权人的许可自由权将被剥夺。根据法定许可制度的内在机理,如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的行为被界定为法定许可,则公共文化机构在符合著作权法直接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不经过绝版作品著作权人的事先许可直接使用绝版作品,即意味着绝版作品著作权在特定情形下将从支配权降格为报酬请求权⑨。在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构成法定许可的预设前提下,公共文化机构与绝版作品著作权人之间的私人协商被法律直接规定所替代,绝版作品著作权人在此种情况下无法选择许可与否以及许可的条件,明显违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基本规律。可见,法定许可制度虽然能实质性地降低交易成本,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公共权力侵入著作权人私权领域,著作权人自由许可权被剥夺,定价效率低下。因此,对于法定许可制度的扩张应持谨慎态度,故由法定许可制度来解决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问题不是最佳选择。
综上所述,我国公共文化机构在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时仍面临现实困境与制度障碍。为回应公共文化机构的现实诉求,我们不妨跳出授权许可、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的制度窠臼,探索引进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以解决绝版作品“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的矛盾,在降低公共文化机构的侵权风险、保障普通公众信息获取权的同时,维护绝版作品著作权人的获得报酬权,最大限度地减轻对绝版作品著作权所造成的限制和损害。
四、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的可行路径:延伸性集体管理
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是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深化和发展,通过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与会员著作权人之间的许可使用合同延伸至非会员绝版作品著作权人,以有效平衡社会公共利益和绝版作品著作权人私人利益。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本质上是对绝版作品著作权人自由处分和行使著作权的限制。事实上,在北欧各国的著作权法中,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也被视为是一种权利限制制度,只是相比法定许可、强制许可或合理使用等权利限制制度而言,限制力度要弱一 些[14]。通过对绝版作品著作权进行适当限制,作品使用者可以吸收、借鉴绝版作品中有益的思想、观点以创作出更高水平的作品,从而充分实现绝版作品的文化价值。
(一) 有效平衡社会公共利益和绝版作品著作权人私人利益
其一,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能有效保障普通公众平等获取知识的机会,促进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承。对绝版作品适用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正当性的讨论不应仅局限于著作权的私权属性,更应放眼促进信息自由流通、最大限度释放绝版作品的文化价值以及保障子孙后代接触文化遗产等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私有知识财产和促进社会知识进步是知识产权制度的二元价值目标[15]。著作权法通过赋予作者对作品的专有权,使其能够在特定期限内收回成本和获取利润,从而激励作者投身于作品的再创作,并鼓励潜在的作者创作作品。但专有权本质上就是一种自由权,自由当然不能是不受限制的[16]。公共文化机构作为平衡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器,应当体现其特殊性并予以适当的立法倾斜,如此方能在维护著作权人的私人利益、发挥公共文化机构的信息传播功能、保障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权利三者之间实现平衡。法律作为社会的制衡器,关注更多的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需求,而是社会整体利益的调和[17]。只有对著作权进行适当的限制以充分保障社会公共利益,著作权制度的价值功能才能得到最大化彰显。在数字环境下,绝版作品著作权人的私人利益与公共文化机构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产生了冲突,为了保障普通公众能够充分获取信息和知识,促进优秀文化传播,应当对绝版作品著作权进行适当限制,并将其纳入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的适用 范围。
其二,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能有效保障绝版作品著作权人的许可自由权和获得报酬权。从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的内在机理来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将其与会员著作权人所签订的许可协议延伸至非会员绝版作品著作权人,并代表非会员绝版作品著作权人发放许可。如非会员绝版作品著作权人不愿被延伸性集体管理,则可以通过声明退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退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之后,著作权人对绝版作品的许可自由权将恢复圆满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延伸至非会员绝版作品著作权人的许可协议只能是非独占许可协议,故即使非会员绝版作品著作权人被延伸性集体管理,其仍可以在不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发放许可相冲突的前提下自由行使作品许可权。因此,相较于法定许可制度,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能有效保障绝版作品著作权人的自由许可权。
在支付许可使用费方面,与合理使用制度的公共政策考量不同,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本质上是为降低著作权人和作品使用者之间的交易成本而创设,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著作权人和作品使用者的交易过程中充当“桥梁”的作用,故作品使用者应当在获得许可之后支付相应的许可使用费。虽然非会员绝版作品著作权人并未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授权协议,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转付许可使用费时应当对会员著作权人和非会员著作权人“一视同仁”,不得歧视非会员著作权人。同时,非会员著作权人有权在作品被发放许可之后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请求支付许可使用费。另外,延伸性集体管理过程中的许可费率由著作权人协商确定,市场化的定价机制能准确反映绝版作品的真实市场价值,有效保障著作权人的获得报酬权。
(二) 欧洲数字化领域的立法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在欧洲,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建设与绝版作品著作权保护之间的冲突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为传承人类优秀文化、保障普通公众在数字环境下能更广泛地接触到绝版作品,2016年9月14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草案)》。其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当集体管理组织代表其成员出于非商业性目的与文化遗产机构签订数字化、发行、向公众传播或提供其永久馆藏的绝版作品的非独占许可协议,该非独占许可协议可延伸或推定适用于没有被集体管理组织代表的同类型作品的权利人。其条件包括:该集体管理组织基于权利人的授权广泛代表某一类作品或受版权保护内容的权利人;许可合同中的条款对所有权利人都是平等对待的;所有权利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反对将其作品或受版权保护的内容视为绝版作品。《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草案)》引入集体管理组织就绝版作品的数字化集体协商机制,有利改变了目前的单一授权模式的弊病[18]。欧盟作为世界上版权立法实践和理论研究最先进的地区之一,其在十多年前便已经开始探讨网络环境下公共文化机构对绝版作品的数字化利用问题,至今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安排。欧盟《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草案)》中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主体资格、非会员绝版作品著作权人的平等待遇及退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规定可以为我国绝版作品数字化利用的制度设计提供启示。
2012年3月1日,为授权图书馆对绝版图书进行数字化,鼓励公众获取知识和文化,法国国务委员会根据第2012-287号法令在《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L.134-1条至L.134-9中为绝版图书创设了一种著作权强制性集体管理制度。根据该法令的规定,如果某一种图书于2001年1月1日之前在法国出版,而在当前该图书已经不再商业化发行、出版或数字化,则可认定该图书已经绝版;同时,法国国家图书馆(BNF)有义务创建一个免费的在线公共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绝版图书的清单,由BNF所持有。任何人都可以要求BNF在数据库中登记一本图书。如果一本图书在数据库中登记6个月以上,集体管理组织(SOFIA)在5年内可以非独占性地将该绝版图书数字化和向公众传播。如果绝版图书的作者有证据证明该图书在市场上可获得,则可以退出集体管理组织。虽然欧洲法院在2016年11月裁决第2012-287号法令与《欧盟信息社会版权与相关权利协调指令》的第2(a)条和第3(1)条相冲突⑩,但法国的立法实践可以为我国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的制度完善提供经验借鉴。
我国自建立著作权制度以来,深受欧洲作者权体系的影响,在保护理念和立法风格上与其存在诸多一致。在解决数字环境下绝版作品的数字化利用问题上,欧盟、法国的立法已经进行了实质性的探索,能为我国提供可行的参考和有益的借鉴。事实上,2014年6月6日,我国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六十三条⑪已经对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做出了规定。因此,探讨通过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来解决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的问题,在我国具有现实可行性。我国应把握此次著作权法修订的契机,合理引进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并进行本土化制度 构建。
五、我国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的制度设计
如何利用互联网时代的技术优势,通过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使公共文化机构能合法、高效地将绝版作品数字化利用以实现信息共享和知识普及,从而最大限度地释放绝版作品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已越来越成为各国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
我国目前正在加快推进著作权法的修订工作,我们建议,要继续完善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关于延伸性集体管理的相关条款,将延伸性集体管理的使用范围扩展到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对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绝版作品进行延伸性集体管理,公共文化机构基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授权对其馆藏的绝版作品进行非商业性质的数字化利用,同时从程序上和实体上为绝版作品著作权人建立权利保障机制,以实现保障著作权人合法权益和促进优秀文化传承的有机统一。
(一)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能广泛代表同类作品的著作权人
根据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的运行模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与公共文化机构之间达成的许可协议将延伸至非会员绝版作品著作权人,这要求该组织在对非会员著作权人进行延伸性集体管理时必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如果集体管理组织的代表性不足,说明大量权利人对该集体管理组织缺乏信任,而且使用者也无法通过与集体管理组织签订的协议取得多数作品的使用许可,此时适用延伸集体管理制度就丧失了正当 性[19]。而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代表的会员著作权人越多,则非会员著作权人越少,说明著作权集体管理能体现该类型作品大多数人的意志[20],从而有利于保障大多数著作权人的权利。此时,少数的非会员著作权人的利益也能够得到兼顾。以此为前提,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将许可协议延伸至非会员绝版作品著作权人更有利于保障非会员绝版作品著作权人的权利,从而使该制度具有实质上的正当性。我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六十三条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实施延伸性集体管理的资格限定在“取得权利人授权并能在全国范围内代表权利人利益”,虽然能够体现其广泛性,但其可操作性仍待强化。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作品的类型日趋复杂和专业化,我们不妨借鉴《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草案)》之规定,强调能广泛代表同类型作品著作权人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才可以对该类型作品实施延伸性集体管理。因此,我国在进行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时,针对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主体资格的规定,应将其表述进一步细化为“能在全国范围内代表同类型作品权利人利益”,以增强该条款的可预测性和可操作性。
(二) 公共文化机构基于非商业性目的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
与一般的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不同,为解决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问题而构建的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有其特殊性,即存在公共文化机构和普通公众等两类作品使用者。普通公众为最终作品使用者,公共文化机构从表面上看属于作品使用者,其在本质上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与普通公众之间的中介和桥梁,即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授权给公共文化机构,再由公共文化机构将绝版作品数字化复制并向公众提供。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绝版作品在市场上已难以获取,即使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直接授权普通公众行使对绝版作品的复制权,普通公众也将因无法获取绝版作品而不存在行使权利的前提。而公共文化机构基于其固有的保存文化遗产、传承人类文明的功能,往往购买公开出版的绝版作品进行馆藏并供读者借阅。目前,包括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在内的公共文化机构收藏着大量的绝版作品[21]。因此,由公共文化机构对绝版作品进行数字化复制并向公众提供更具有可操作性。其二,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因其公益性和开放性为广大普通公众所熟知,由这些公共文化机构对绝版作品进行传播,便于普通公众获取绝版作品。
当然,公共文化机构作为保存人类文化遗产、传承优秀文化、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殿堂,其在对绝版作品进行数字化利用过程中应以非商业性目的为出发点。因社会公共利益对绝版作品进行延伸性集体管理已经是对绝版作品著作权进行了相应的限制,如在实施该制度过程中,还掺杂商业性目的则是对绝版作品著作权人的“二次伤害”。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22]。立法正义本质上属于分配正义,立法过程本质上是分配利益的过程。为使对绝版作品著作权的限制符合实质正义,在保障社会公众获取信息和知识的同时,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对绝版作品著作权人利益的损害。因此,我国著作权法在进行相应的制度构建时,应坚持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的公益性目的并将实施主体严格限制为公共文化机构。具体来说,公共文化机构获得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相应授权后,应当对绝版作品进行数字化复制并将数字化复制件上传至馆舍官网,作品使用者需要在公共文化机构馆舍官网进行在线用户注册并支付相应的许可使用费⑫后便可以远程浏览、下载绝版作品数字化复制件。许可使用费与浏览、下载绝版作品数字化复制件的次数相衔接,作品使用者浏览、下载绝版作品数字化复制件次数越多,则为此所支付的许可使用费越高。同时,在确定绝版作品的许可使用费时,应当参考绝版作品的种类、性质、独创性程度以及同类作品在商业市场上的价值等因素。最后,为尽可能地保障绝版作品著作权人的剩余经济利益,公共文化机构应当针对上传至馆舍官网的绝版作品数字化复制件设置技术保护措施。
(三) 公共文化机构的权限范围应仅限于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
在确定公共文化机构对绝版作品可实施的权限范围时,应坚持保障著作权人的私人利益和满足作品使用者的文化需求并重的价值取向。一方面,为将该制度对绝版作品权利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应尽可能地将该制度实施的权限范围压缩;另一方面,赋予公共文化机构的权限范围应有利于其对绝版作品进行高效、便捷的传播,并保障作品使用者的基本文化权益。从制度设计的初衷看,公共文化机构需要将绝版作品进行数字化复制并上传至其官网供馆舍外作品需求者浏览、下载,因而,公共文化机构通过实施绝版作品的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便可实现向公众传播绝版作品的功能。从普通公众的需求角度来看,能在个人选定的时间从公共文化机构馆舍官网浏览、观赏、下载绝版作品即可满足对绝版作品的正常需求。基于此,在对绝版作品的延伸性集体管理进行制度构建时,应明确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授予公共文化机构的权利仅限于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
(四) 建立绝版作品著作权人的权利保障机制
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作为一种权利限制制度,尽管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保护非会员权利人的权利,但如何防止非会员权利人的权利不被侵害,如何保障非会员权利人的自由仍然是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必须面对的问题[23]。法国是最早尝试对绝版作品数字化利用进行立法的国家之一,但其相关立法因未能有效地保障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而受到质疑。欧盟法院也因法国的第2012-287号法令可能涉嫌侵犯著作权人的许可权而裁决其与《欧盟信息社会版权与相关权利协调指令》相违背。因此,我国在构建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的相应制度时,应汲取法国的教训,对绝版作品著作权人的权利保障机制做出明确规定。目前,尽管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在第六十三条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转付相关使用费时,应当平等对待所有著作权人,且允许著作权人通过声明排除集体管理”。我们认为,这一规定仍过于原则,应进一步从程序上和实体上为绝版作品著作权人建立权利保障机制,以实现保障著作权人合法权益和促进优秀文化传承的有机统一。
其一,规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认定绝版作品的程序,以保障非会员绝版作品著作权人的知情权。绝版作品的认定是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运行的前提,为防止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滥用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需规范绝版作品的认定方法和过程。首先,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在商业市场上勤勉调查该作品的市场流通情况,只有当该作品不能通过传统的商业渠道购买或不能合理预见到可以获得时,才可以将其认定为绝版作品;其次,应在新闻媒体、报纸以及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官网将拟延伸性集体管理的绝版作品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3个月,如公示期内绝版作品著作权人未提出反对意见,则可对其进行延伸性集体管理。
其二,允许非会员绝版作品著作权人事前反对被延伸性集体管理、事后退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以保障绝版作品著作权人的许可自由权。为充分保障绝版作品著作权人自由处分作品的权利,我国在引进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时应当规定,绝版作品的著作权人如不愿其绝版作品被延伸性集体管理,可在任何时候主张其作品不应被视为绝版作品,并排除许可合同的适用。权利人可以通过声明、公告、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主张其作品不应被视为绝版作品,自其主张之日起,权利人自动退出集体管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人退出集体管理之后,必须立即停止对该作品的管理,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已经与公共文化机构订立的许可使用合同在期限届满前继续有效。
其三,保障绝版作品著作权人的获得报酬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将绝版作品的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给公共文化机构之后,公共文化机构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作品使用费并由其转交著作权人。为保障非会员绝版作品著作权人的获得报酬权,即使非会员绝版作品著作权人并未明确表示加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但向其支付的作品使用费应与会员著作权人相同。在暂时不能联系到著作权人的情况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扣除必要的管理费用后应将作品使用费提存。
六、结语
公共文化机构的作品传播模式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数字化革命,并打破了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的传统利益平衡格局。公共文化机构在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的过程中,如何构建一种合理的著作权授权机制,面临新的挑战。面对一种全新的情势尤其是日新月异的网络社会,求助于已经形成的经验,迎头解决网络环境下的具体问题,也许是一种更直接、更真实的做法[24]。我国不妨借鉴欧盟的立法经验,积极引入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作为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的一种可行路径。
我们建议,我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六十三条新增一款关于绝版作品适用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的规定,具体表述为:“当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代表其成员与公共文化机构签订许可使用合同,公共文化机构基于非商业性目的对其馆藏的绝版作品进行数字化、信息网络传播,该许可使用合同可延伸至不被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代表的同类型作品著作权人。”与此同时,为了增强该条款的可操作性,建议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进一步界定绝版作品的概念、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主体资格、绝版作品著作权人的权利保障机制以及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通知义务等具体内容。我们希望上述立法建议对我国著作权法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修改能有所裨益,从而为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以彰显著作权法保障信息流通、促进知识共享的价值目标。
注释:
① 公共文化机构是指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档案馆等公益性机构。
② 本文中的“数字化利用”是指公共文化机构将其馆藏的绝版作品进行数字化复制并向社会公众提供数字化复制件的行为。
③ 何炼红、熊琦、陈兵、唐伶俐、管育鹰、王英、马海群、邱奉捷等学者均在学术论文中提及过绝版作品(图书),详细参见何炼红、云娇.论公共文化机构对孤儿作品的合理使用. 知识产权,2015(10):98;熊琦.大规模数字化与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创新. 法商研究,2014(2):104;陈兵、唐伶俐.欧盟图书馆馆藏作品数字化版权问题研究. 图书馆学研究,2017(17):17;管育鹰.我国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2):23;王英、马海群.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中的著作权策略研究. 图书馆情报知识,2011(1):114;邱奉捷. 国内外图书馆数字资源共建共享版权解决实践调研. 图书馆学研究,2017(11):94.
④ 这两类特殊作品是指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
⑤ 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在欧盟,绝版作品的原文表述为“out-of-commerce works”,我国有学者认为应将其翻译为“脱销作品”。(参见肖燕珠,傅文奇.欧盟《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解读. 图书馆论坛,2018. 阮开欣.《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将完善欧盟版权制度. 中国知识产权报,2016-9-30(10).) 通过分析我国的著作权法律制度和社会生活实践可以发现,将“out-of-commerce works”一词翻译为“脱销作品”会存在诸多不协调之处:首先,将“out-of-commerce works”翻译为“脱销作品”与我国著作权法律体系中原有的法律概念相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著作权人寄给图书出版者的两份订单在6个月内未能得到履行,视为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所称图书脱销。”根据该条款,“脱销作品”从字面上可以被理解为出版商在收到著作权人订单之后的特定期限内未及时出版的作品。而“out-of-commerce works”在欧盟版权立法实践中则是指那些在著作权法的保护期限内无法通过传统的商业渠道获取的作品。因而,将“out-of-commerce works”翻译为“脱销作品”可能产生语义理解上的冲突。其次,将“out-of-commerce works”翻译为“脱销作品”不符合社会日常生活中公众的认知。在社会日常生活中,“脱销”一般用以描述某类商品深受消费者喜爱而在市场上短时间内供不应求的现象。基于对商业利润的考量,著作权人或出版商往往会在作品脱销之后重新出版,而“out-of-commerce works”一词则暗含著作权人或出版商决定不再发行新版本或出售作品复制件之意。因此,将“out-of-commerce works”翻译为“脱销作品”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认知相违背。最后,将“out-of-commerce works”翻译为“绝版作品”更具有内在合理性。虽然“绝版作品”并非正式的法律概念,但在人们的日常认知中,“绝版”往往是指某一类作品不再重新出版、难以在商业市场上购买,因而,将“out-of-commerce works”翻译为“绝版作品”更符合其所指代的含义。
⑥ 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七条第二款之规定,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应当是已经损毁或者濒临损毁、丢失或者失窃,或者其存储格式已经过时,并且在市场上无法购买或者只能以明显高于标定的价格购买的作品。
⑦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符合《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七条所规定的两类特殊作品构成要件的绝版作品,公共文化机构对其进行数字化复制属于合理使用,对于这两类特殊作品之外的其他绝版作品,公共文化机构对其数字化利用(包括数字化复制、信息网络传播)则适用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也即本文所要构建的绝版作品相关制度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七条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公共文化机构数字化利用绝版作品的制度。
⑧ 以“三步检验法”来判断某一使用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即在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该使用行为不得与作品的正常使用相冲突,不会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具体规定可参见《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十三条。
⑨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之规定,著作权人可以通过“事先声明不许使用”排除他人对作品的使用,但在实践中,鲜有著作权人会做出类似声明。
⑩ 2013年2月27日,法国两位作家Marc Soupier和Sara Doke质疑该法令的合法性并请求法国国务会员会撤销第2012-287号法令。在驳回了两位作家的请求之后,法国国务会员会请求欧洲法院对该法令是否与《欧盟信息社会版权与相关权利协调指令》(以下简称InfoSoc指令)相冲突作出裁决。2016年11月16日,欧洲法院针对该问题作出裁决。法院认为,根据InfoSoc指令第二条和第三条之规定,成员国应当为作者提供独占的复制权和向公众传播权。因此,根据InfoSoc指令第五条的限制和例外规定,任何第三方未经事先许可对作品进行使用,都应该被视为侵犯作品的著作权。为保障作者的许可权不被剥夺,默示许可必须通过严格的立法才能被承认。因此,作者必须在事实上被告知他们的作品将来会被第三方使用以及拒绝作品被使用的方式。最后,法院认为该法令未能提供一种机制使得作者在事实上被通知,而且,缺乏反对意见并不能代表作者默示许可自身作品被使用。基于以上原因,欧洲法院初步裁决第2012-287号法令与InfoSoc指令的第2(a)条和第3(1)条相冲突。See Marc Soulier, Sara Doke v Premier ministre, Ministr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Communication (Case C-301/15).
[1] 博登海默. 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 邓正来,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504.
[2]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key principles on the digitisation and making available of out-of-commerce works[EB/OL]. (2011-09-20)[2017-12-08].http://ec.europa.eu/internal_market/copyright/docs/copyright-infso/20110920-mou_en.pdf..
[3]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on key principles on the digitisation and making available of out-of-commerce works-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EB/OL]. (2011-09-20)[2017-12-09]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11-619_en.htm?locale=e.
[4] 管育鹰. 我国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的反思与重构[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5(2): 18−29.
[5] 王英, 马海群. 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中的著作权策略研究[J]. 图书馆情报知识, 2011(1): 113−119.
[6] 陈兵, 唐伶俐. 欧盟图书馆馆藏作品数字化版权问题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 2017(17): 16−23.
[7]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EB/OL]. (2016-09-14)[2017-12-08].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proposal-directive-european-parliament-and-council-copyright-digital-single-market.
[8]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key principles on the digitisation and making available of out-of-commerce works[EB/OL]. (2011-09-20)[2017-12-08]. http://ec.europa.eu/internal_market/ copyright/docs copyright-infso/20110920-mou_en.pdf.
[9] 何炼红, 云姣. 论公共文化机构对孤儿作品的合理使用[J]. 知识产权, 2015(10): 97−102.
[10]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on key principles on the digitisationand making available of out-of-commerce works-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EB/OL]. (2011-09-20)[2017-12-09].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11-619_en.htm?locale=e.
[11] 熊琦. 著作权许可的私人创制与法定安排[J]. 政法论坛, 2012(6): 93−103.
[12] 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54.
[13] 马卫平, 刘净净. 对“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的理解——商榷《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七条[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1(9): 40−42.
[14] 梁志文. 著作权延伸性集体许可制度的移植与创制[J]. 法学, 2012(8): 122−131.
[15] 吴汉东, 等. 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总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94.
[16] 丁丽瑛. 知识产权法[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 105.
[17] 何炼红, 邓欣欣. 数字作品转售行为的著作权法规制[J]. 法商研究, 2014(5): 22−29.
[18] 陈兵. 欧盟《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草案)》评述[J]. 图书馆, 2017(9): 51.
[19] 王迁.著作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395
[20] 胡开忠. 构建我国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的思考[J]. 法商研究, 2013(6): 18−25.
[21] 陈兵. 欧盟公共文化机构中的绝版作品数字化版权问题研究[J]. 图书馆建设, 2018(3): 41−46.
[22] 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3.
[23] 王国柱. 著作权“选择退出”默示许可的制度解析和立法构造[J]. 当代法学, 2015(3): 106−112.
[24] 何炼红. 网络著作人身权研究[J]. 中国法学, 2006(3): 69−82.
Discussion on the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mechanism of the digital utilization of out-of-commerce works by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HE Lianhong, ZHENG Hongfei
(School of Law,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age, the pace of large-scale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is accelerating. Traditional authorization mechanism, such as authorization license, fair use, and statutory license are different degrees of limitations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which leads to the fact that digital utilization of out-of-commerce works by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 in our country confronts high transaction costs or potential infringement risks. It is therefore suggested that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63 of our copyright law (revised draft for review) be improved, that extensible collective governance of copyright be introduced as a feasible path to the digital use of out-of-commerce works by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It can achieve the organic unity of safeguard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pyright owners and promoting the transmission of excellent culture, by undertaking extensive collective governance over out-of-commerce works with cultural inheritance value by representative institutions of copyright collective management, and by establishing the rights protection mechanism for copy-right holders both procedurally and practically.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s;out-of-commerce works; digital utilization; extensive collective governance; rights protection mechanism
[编辑: 苏慧]
2017−12−27;
2018−05−2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工智能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研究”(17BFX012)
何炼红(1970—),女,湖南韶山人,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学,联系邮箱:1227374674@qq. com;郑宏飞 (1994—),男,湖南永州人,中南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学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18.04.005
D923.41
A
1672-3104(2018)04−003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