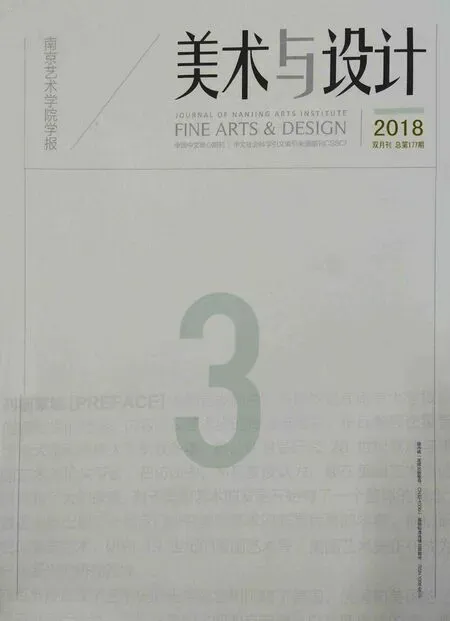由“江村体”之争论及康熙朝书画鉴藏类著述体例
刘亚刚(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北京100089)
《江村销夏录》是高士奇退居平湖期间所撰,前有康熙三十二年(1693)六月自序。此书记录其所见、所藏古书画,自称因持宁慎无滥的态度,三年余仅得三卷。此书体例以记录为主,间加评语及自作跋语,被民国学者余绍宋称作“江村体”。“江村体”被其后的书画鉴藏类著述纷纷仿效,①清代书画鉴藏类著述体例仿“江村体”的有周二学《一角编》、缪曰藻《寓意录》、陶樑《红豆馆书画记》、张大镛《自怡悦斋书画录》、胡积堂《笔啸轩书画录》、孔广陶《岳雪楼书画录》、方濬《梦园书画录》、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陈焯《湘管斋庽赏编》、吴荣光《辛丑销夏记》、李佐贤《书画鉴影》、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李葆恂《海王村所见书画录残稿》、韩泰华《玉雨堂书画记》等。著述既多,常有浮于记录而失于考证者,被讥为“钞胥”。本文将围绕记录和考证两个方面,讨论《江村销夏录》对晚明书画鉴藏类著述体例的继承和发展,并由此论及康熙朝其他五部同类著述在记录与考证上的异同。
一、有关记录与考证的“江村体”之争
道光朝顾文彬据自己所藏书画撰成《过云楼书画记》,体例极为严格,坚持绢本不录、闺阁之作不录、石刻不录、宋刻丝不录、单条及扇不录。甚至法书不录本文,名画不录题识,题跋也一概不予录入。顾文彬对当时流行的书画鉴藏类著述仿照《江村销夏录》详记藏品上印章的做法不以为然,嫌弃其为骨董家路数,以为赏鉴之道,不尽在是。对于藏品尺寸,顾文彬也声称,自己仿照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和吴荣光《辛丑销夏记》的做法不予记录,并敬告论雅道而对此斤斤计较之人,其为正法眼藏也几希。②(清)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凡例”。
究竟“江村体”是怎样的著述体例呢?简单来说就是以亲见为标准,在对书画标目、绢纸、尺寸、题跋、印章等信息客观、详细记录的基础上,附以作者自己的评语和题跋。《江村销夏录》“凡例”有八,与本文论旨极为相关者摘录如下:
一、海内名迹,收藏家甚夥,未寓目者不敢妄载。凡经评阅,随见随录,编次不以时代,亦未敢轻为甲乙。
二、前人所书古文辞,已见刻本者概不录,惟记其款识、跋语而已。其中与世本异同者,则详录以备考订。
三、是录以标目、尺度、评语为主,本文款识为第二,故下一字,题跋又下一字。至于图记不能摹入,但用楷字加圈以别之。其间文字损蚀难辨者,亦着方圈,不敢谬为增益。[1]
在考证盛行的时代,仅简单记录藏品信息的“江村体”难免为人所诟病。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即指出,“其弊也,不讲考证,不重鉴赏,而徒以钞胥为能。于是著录之书几于汗牛充栋,而芜杂遂不可问矣。”[2]448余绍宋还附录了乾隆朝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和道光朝程庭鹭《箬庵画麈》中对《江村销夏录》疏漏之处加以考订的文摘。余绍宋的这一态度与他心目中对于一个合格鉴赏家的衡量标准有关。道光朝胡积堂所著《笔啸轩书画录》,体例即仿“江村体”。对于胡积堂在此书凡例中自称不尚考据的说法,余绍宋极为诧异,反问道:“鉴别书画而曰不尚考据,其能审乎?”[2]419但对于体例也仿“江村体”的道光朝吴荣光《辛丑销夏记》,余绍宋则以为,“是书体例虽仿江村,而精审过之。所附跋语,考证至为确当。偶附题咏,亦无泛词,可谓青出于蓝矣。”[2]460可见,“考证确当”是他衡量一名鉴赏家是否合格的标准。
抛开《江村销夏录》考证方面出现的具体问题不谈,顾、余二人将记录与考证分割开来,似乎两者互不相容,但其实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并重。尽管记录并不等于考证,但客观、全面的记录为读者提供了足资考证的文献,本身就是考证的一个重要部分。
事实上,书画信息的记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书画之作传承不易,文献记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一些缺憾。康熙朝的宋荦曾用韩愈的事例来说明对书画记录的好处。韩愈曾得到一卷人物画,因为非常喜欢,在将此画送人前先以记文记明了画中人物的形状和数量,以便可以时时观之以自释。九百年后,画早已不知所踪,而记文犹存,人们依然可以据其记文而想见画的细节。因而,宋荦提出:“世有博雅之士,取凡书法、图画之流传者,诠次其源流,荟萃成书,使览者一披卷而古今之书画纷然罗吾几而悦吾目也。”[3]余绍宋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指责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严苛的体例和做法“措词不免激切”,并指出书中提到的黄公望手书《画理册》与世传的《写山水诀》不同,祝允明《正德兴宁县志》当时已无传本,而顾文彬在明知它们为“断种秘本”的情况下也坚持没有记录其内容。余绍宋不由得发出感慨:“假使录入此编,不惟可供参考而俾先哲遗文流传,天壤其功德,又当奚如?乃概从删削,等于秘传,良可堪叹惜。”[2]422-423
与顾文彬相反,与高士奇同时代的朱彝尊对《江村销夏录》重视记录的体例赞赏有加,“钱唐高詹事退居柘湖,撰《江村销夏录》,于古人书画真迹,为卷为轴为笺为绢,必谨识其尺度、广狭、断续及印记之多寡、跋尾之先后,而间以己意折衷甄综之,评书画者至此而大备焉。”[4]其认为记录可以抑制书画市场的伪造之风,“今之作伪者未尝不仿尺度为之,然或割裂跋尾印记,移真者附于伪,而以伪者杂于真。自詹事之书出,稍损益之不可,虽有大驵钜狡,伎将安施哉!”[4]
为何朱、顾等人的评价会截然相反呢?
可确知的是,高士奇在当时即以精于赏鉴被称道,康熙皇帝常令他鉴定内府所藏书画,《光绪平湖县志》说他“精赏鉴,凡法书名绘彝鼎之属,经拂拭者声价十倍。”[5]从高士奇的诗文、题跋中可以看出,与当时许多人相对主观和玄虚的赏鉴有着明显的区别,他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作品的纸绢、尺寸、印章、流传绪列等方面。这本质上是鉴定与欣赏的区别。鉴定更注重作品的真伪,而欣赏更在意作品把玩的乐趣。为何士大夫和文人们会重欣赏而轻鉴定呢?一方面,书画作品中有大量的托名、仿造、钩摹的作品被奉为经典,这使得真伪的问题并不那么凸显,加之书画真迹不易流传,多数人只能通过刻帖等方式接触和鉴赏作品,久而久之,文人士大夫们对于真伪的讨论相对缺失,形成一个重欣赏而轻鉴定的传统;另一方面,对于作品真伪的判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得出一个与之匹配的价格,而这些应当是骨董家所关注的,却是士大夫和文人们所不齿的。
由于通过记录所见而成书易于操作,使得之后的书画鉴藏类著述纷纷仿效。部分粗制滥造的模仿者是将“江村体”推入深渊的另一股力量。顾、余二人所说的“江村体”偏向一个群体性概念,包括后来大量仿“江村体”的著述。显而易见,如果没有严密的考证做支撑,一旦录入的作品鱼龙混杂,著述一事就会变得毫无技巧可言,著述者也难免被人轻视。
另外,“江村体”之争是一场发生在不同时空的争论。康熙朝处于乾嘉学派生发之初,朱彝尊对“江村体”的褒扬未必不出自真心。而提出异议的顾文彬、余绍宋等人生于以考证见长的乾嘉学派之后,考证知识的积累和能力的提高让他们指出《江村销夏录》的某些疏漏之处本不足为奇,但对这些具体问题的关注让他们难以用更宏大的视野评价“江村体”,从而得出了“不讲考证”的结论。可参考的是,乾隆朝的阮元对高士奇的鉴赏能力有所肯定。高士奇在赵雍《竹西草堂图》后有题跋两则,阮元称其“考据精詹”,因而称赏高士奇“江邨字谨饬而韶美,题跋亦多订谬处,非不读书鉴赏家题跋惟掉虚文者可比。”[6]由朝廷组织、阮元参与编写的《石渠宝笈》,体例就仿“江村体”。
在余绍宋看来,顾文彬和高士奇无疑是两个极端,而他则主张应该立酌中之法:
窃谓著录书画若“江村”之例末流,成为钞胥,固为芜杂。若此编①指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专载自题,则又类于题跋,亦乖著录题裁。谓宜立酌中之法,凡法书本文,他书未见或与他书有异文者宜全录之,名画则款识在所必录,其后跋语宜择其有关系者摘录之,印章于名迹流传有关亦应选载,纸绢、尺寸则非剧迹尽可从略。著录之人则应如此编悉加考辨之文,方足征信,今以高氏与顾氏各有所偏,为发其意于此。[2]422-423
显然,余绍宋没有顾及著述本身也有成为孤本甚至失传的事实,如果有此顾虑,唯有详细、全面地记录才最可靠。为了更好地理解《江村销夏录》体例的意义,我们还需将其放入历史的坐标加以讨论。
二、《江村销夏录》与书画鉴藏类著述体例发展的一条脉络
对于以往书画鉴藏类著述的体例,与高士奇同时代的顾复有着清晰的认识和判断:
编书难而立例尤难,前代诸书,如李嗣真《画录》,朱景玄讥其空录人名而不论其美恶,无品格高下,俾后之观者何所考信;《宣和》二谱,叙时分类,记其人之姓名爵里,又记其取法之渊源,又记其笔迹之多少,甚而记其修短妍媸嗜好,至于真伪优劣不记也;米氏二《史》,评论精确;黄氏《东观余论》,辨别差讹,皆古学之鼓吹,然少而无伦次;《云烟过眼录》,祗载收藏人家,诸迹之下,偶注一“佳”字、“平”字耳;《铁网珊瑚》、槜李《题跋》、孙氏《抄》、我家《笔记》,仅载卷轴之诗题,吾恐无诗题者不录也。若张氏铭心绝品、严氏《书画记》、韩氏《南阳书画表》,仅存人名而已。[7]
朱彝尊对此也有过简略的评论:
评书画者众矣。广川董氏病其冗长;其余又嫌太略;宣和书画仅谱其人及所藏之目;南渡馆阁之储,于金铜玉石悉识其尺寸,而于书画无之。盖昔人心思或有未及,必俟后贤而始大备也。[4]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总结道:
书评画品,肇自六朝,张彦远始汇其总,依据旧文,粗陈名目而已,不能尽见真迹也。唐、宋以来,记载日夥,或精于赏鉴而限于见闻,或长于搜罗而短于辨别,迄未能兼收众美,定著一编,为艺林之鸿宝。[8]1503
早期书画鉴藏类著述体例杂乱,重书画家而轻作品,有的仅为随笔,有的类似账目。就记录而言,记录的信息零散而随意,在作者看来是录其重点,读者看来却未必能清晰、全面、客观、易懂。就考证而言,录入的作品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录入之后定为真迹、摹本或赝品的依据也往往没有说明。尽管著述者好为评论,但评论什么,从哪些角度评论,也都很随意。杂乱的体例决定了著述水准的高低更多地要看作者的鉴赏能力是否权威,是否值得信赖。以顾复和朱彝尊同时提到的《宣和书谱》为例,此书以书家姓名排序、分大类,再以书体分小类,作品则仅录名称。如:
唐柳公权【《柳公权小传》(略)】今御府所藏十有一
度人经二,以下正书:清静经,阴符经,心经,寄药帖,宫相帖。以下行书:捡领帖,兰亭帖,紫丝鞵帖,简启草稿。①《宣和书谱》,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
相对仅录名称的作品,《宣和书谱》对书家小传着墨更多。以此条为例,柳公权“心正笔正”之谏、“碑志非公权出以子孙为不孝”等事均传写在内。这样的体例,让我们无从获知任何作品的细节。即使我们手持一件柳公权行书《兰亭帖》与此条记录两相对照,我们也无法证实它是否就是被记录的那件。
直到明代,此类著述的体例才从纪传体为主转变到题跋类型的著述上来。②耿明松认为:“这些记录和题写题跋的画史书籍不再是像以前重点关注画家,而是关注画作,或者记录作品的藏处、尺寸、画面特征、他人评价,或者记述作品的内容、笔墨技巧、印款、价值等。从关注画家为主传记体画史到关注绘画作品的题跋性画史为主,这是明代画史观念和写作体例上的发展”,《明代绘画史学在编撰体例上的发展》,《艺术百家》,2008年第2期,第94页。以《铁网珊瑚》和《清河书画舫》为代表的书画鉴藏类著述对作品题跋等信息的记录弥补了这些缺陷。
《铁网珊瑚》的作者尚有争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指出,此书旧本题明朱存理撰,但据末尾万历朝赵琦美题跋考证,应为赵琦美在两本残稿的基础上增入自己所见真迹编撰而成,因而题为《赵氏铁网珊瑚》。[8]1497朱存理另有《珊瑚木难》八卷,与《铁网珊瑚》体例不同,但内容有相似之处。就体例而言,《铁网珊瑚》以记录题跋为主,并加入作者和他人的题、赋、诗等,而《珊瑚木难》不仅记录作品的内容,而且涉及作品流传经过、历代评价等。
张丑《清河书画舫》主要记录作品正文和题跋,对少部分作品上的印章有所记录,自称:“只今闻见浸多,惧久忘佚,稍为区分,随笔笺记,造《清河书画舫》传诸雅士,不令海岳庵《书画史》独行也。”[9]2《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其书用《铁网珊瑚》之例,于所见真迹,备录其题跋、印记,有所疑似,亦多辨证。”[10]442《清河书画舫》以精于考证著称。乾隆朝严诚《清河书画舫叙》认为,“先朝书画绪论,莫夥于吴,《弇州书画跋》而外,若《金薤琳琅》《铁网珊瑚》之属,不可殚纪。青父之书最晚出,一时服其精当。”[9]1《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称,“明代赏鉴之家,考证多疏,是编独多所订正。”但同时又指出,“惟是所取书画题跋,不尽出于手迹,多从诸家文集录入,且亦有未见其物、但据传闻编入者。”[8]1500
谈及《江村销夏录》的体例,《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认为:
其体例颇与《铁网珊瑚》《清河书画舫》相似,惟间加评定之语,又以己所作题跋一概附入,稍有不同。然所录皆出于亲见,则视二家更详审矣。[8]1504
将《江村销夏录》与《铁网珊瑚》《清河书画舫》相比,高士奇本人就有这样的意识。“近代《铁网珊瑚》《清河书画舫》二编亦载世间名笔,而多未精详,恐尚有传闻之病。”[1]1在他看来,《江村销夏录》修正了这样的不足。在《铁网珊瑚》和《清河书画舫》的基础上,《江村销夏录》记录更为详尽和全面。正文未见刻本或与世本稍有不同即全部录入,款识、题跋全部录入,作品上的印章以楷书加圈的方式全部录入。在注重对作品记录的同时舍弃了对书家的传记,理由是“古来书画名家,前人已识其爵里,兹录不赘。”[1]
除了转向以作品为主的记录以外,考证的加强是晚明以来此类著述的另一个方向。很长一段时间,考证在书画鉴藏类著述中是一件并不擅长的事情。直到晚明,尽管出现很多著述,但失于考证者居多,以至于《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得出:“明代赏鉴之家,考证多疏”的结论。[8]1500《铁网珊瑚》和《清河书画舫》是其中因重视考证而被推崇的一类,却终究因其仅据传闻录入而失于严谨。高士奇以亲经品第为基本条件,对录入的作品有着自己的标准。极为少见的晋唐书画,即使已经在《铁网珊瑚》和《清河书画舫》等书被收录,仍然予以记录。明代名家赝本较多,后人难辨,遇到真迹,必为存录。[1]正文部分与世本有不同者则详录以备考订,印章文字残损难辨者以方圈代替,不敢谬为增益。另外,不轻易评定品第,“凡经评阅,随见随录,编次不以时代,亦未敢轻为甲乙。”[1]
三、《江村销夏录》与康熙朝书画鉴藏类著述体例
康熙朝有六部书画鉴藏类著述,除《江村销夏录》外,还有吴其贞《书画记》、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顾复《平生壮观》、姚际恒《好古堂家藏书画记》和吴升《大观录》。其他五部著述中,吴其贞《书画记》、顾复《平生壮观》、姚际恒《好古堂家藏书画记》和吴升《大观录》都是对其所见、所藏书画的记录,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则是汇辑前人书画录并加入本人所见、所闻者而成。尽管体例有差异,但对记录和考证的重视是它们与《江村销夏录》的共通之处。
吴其贞《书画记》是他在生意场中随见随记后整理而成。记录按所见时间先后排列,起于崇祯八年(1635),终于康熙十六年(1677),前后耗去四十三年。作品按照所见时间顺序排列,仅录重要作品,有现场所记,也有事后忆写。
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是采录前人书画鉴藏类著述并加入自己所见、所闻而成,前有康熙二十一年(1682)自序。《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先纲后目,先总后分,先本文而后题跋,先本卷题跋而后引据他书,条理秩然,且视从来著录家征引特详。惟所载书画不尽属所藏,亦非尽得之目见,大抵多从汪砢玉《珊瑚网》、张丑《清河书画舫》诸家采摭裒辑,故不能如《宝章待访录》以目见、的闻,灼然分别。”[8]1504
顾复《平生壮观》记其三十多年所见古书画,包括少量对其弟顾崧(维岳)所述书画的记录。前有康熙三十一年(1692)五月徐乾学序,以及同年春天顾复自撰《平生壮观引》。此书按时代先后排列书画家,每个书画家有简单的介绍,包括字、号、谥和官职等基本信息。在其名下详列所见作品,注明纸绢、尺寸等。自称不言虚语,不强作评价。
姚际恒《好古堂家藏书画记》是对其所藏书画的记录,书中自称:“康熙己卯(1699)记。以前散去者,甚多不录。以后散去者,亦在焉。”[11]余绍宋认为,“所记不尽录题记、印章,颇为简要,间加评论,亦多允当。”[2]413
吴升《大观录》最晚出,书前分别有康熙五十二年(1713)王掞和五十三年(1714)宋荦所作序言。据序言可知,此书为吴升汇辑其生平所见书画而成,耗尽其一生心血。此书体例仿“江村体”,凡二十卷,书画各十卷,从魏晋至明代,大体依据时代先后排列。再于大时代下列书画家,书画家名下分布其法帖名画数种,起首第一件有作者小传。每件作品题名下详记其纸绢、尺寸、法帖正文、画中内容、题跋等信息,印章以方框标出,并在正文前的记述中夹杂吴升的评语。此书体例并不统一。其一,不完全按照时代先后排列书家,如第三卷“宋君臣法书”,第四卷“北宋诸贤法书”,第五卷单列“苏文忠公法书”,附颍滨、叔党,第六、七卷又为“宋名贤法书”;其二,所记内容并不统一,如第一卷“魏晋法书”无作者传记,第十卷“元贤诗翰姓氏”仅有传记,缺法帖信息,或由于诗翰部分丢失,或由于吴升未能如愿完成书稿;其三,对于藏品信息记载不全,如对王羲之《二谢帖》的记录,评论多于记录,客观的记录仅有“纸本”二字和题跋,尺寸、印章等信息全无。此书更大的缺点在于不知别择,精审程度难以与《江村销夏录》相比。余绍宋认为:“综观全篇,凡评论书画之语颇有所见,自非寝馈其中数十年者不能道,而考证则殊非所长。”[2]451
吴升生平不详,宋荦序中提到,吴升曾与孙承泽、梁清标有交游,“子敏雅有嗜古癖,得古人真迹、断墨残楮,追其神,补其迹,因游艺苑间,遂推海内第一。游迹所至,辄倾动其公卿,若孙退谷、梁真定诸前辈更相引重,共数晨夕者有年矣。”①(清)宋荦:《大观录序》,吴升《大观录》。王掞的序中也提到吴升曾与孙承泽、曹溶有交游。《大观录》体例仿“江村体”痕迹明显,余绍宋推测:“是其书成于五十一年,江村书则成于康熙癸酉,先于此编十有九年,宜子敏必见及,知其所自昉矣。”[2]451除吴升而外,其他五人之间是否见过彼此的著述并从中获得有关体例的灵感尚不确定。《式古堂书画汇考》中详列“书考引用书”44种、“画考引用书”45种,并无《书画记》《平生壮观》和《江村销夏录》。高士奇和卞永誉最有可能见到彼此的著作,据王士禛《居易录》所载,卞永誉曾赠送《式古堂书画汇考》给他,证明书成之后在一定范围内当即流传开来。尽管卞永誉书中的自序要早于《江村销夏录》九年,引用书目中也没有提到《江村销夏录》,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江村销夏录》“录中书画,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已并载无遗,盖即从士奇此本录入。”另外,有高士奇仿吴其贞《书画记》体例之说。丁福保、周云青《四库总录艺术编》所引《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江村销夏录》“体例亦如《铁网珊瑚》,而兼详纸绢、册轴、广狭则如吴其贞《书画记》,惟以自作题跋载入,与三家小殊。”[12]135嘉庆朝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也沿袭此说,认为“其体例虽参之《铁网珊瑚》《清河书画舫》及吴其贞《书画记》,而是录则较为精密焉。”[12]136但此说并不可靠,两书体例差异较大,且“粤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就没有这样的说法。[10]445
相似的体例使得同一件作品同时出现在他们的著述中有了可能。《书画记》《式古堂书画汇考》《平生壮观》和《大观录》均记录了王羲之的《袁生帖》。似乎用一件《袁生帖》不足以说明问题,但从此帖的重要性来衡量,对它的记录是否详略、考证是否谨严有据,则足以说明四部著述在记录与考证上的异同。
顺治十三年(1656)四月十日,吴其贞在扬州钞关外的陈以谓舟中见到《袁生帖》。他的记录简单、主观、散乱:
书在冷金笺上,纸墨佳。书法之妙,已经历代帝王名贤品评,信旷代在世法书第一也。上宋徽宗题其标签,用有小玺。卷后文衡山小楷题识。[13]
在分条记下同日所见怀素小行书《千字文》、米芾《梅花诗赞》、薛绍彭二帖和宋元小画册二本计四十八幅之后,吴其贞于末尾记下从何人、何处得见,并指明这批藏品后来皆归泰兴季氏。十五天后,他在季寓庸处再次见到《袁生帖》,只记明此前曾录入。
顾复所记也很简单:
《袁生帖》,草书二十八字。宣和六玺具备,徽宗金书题签写于冷金纸,至今犹簌簌声。右军诸书,惟此非双钩也。文徵明小楷跋。真赏斋物,有华氏诸图章。卷包首是刻丝‘仙山楼阁’一方,古艳第一。[7]5
可以看出,顾复对藏品信息的记录有所拣选。其中,“右军诸书,惟此非双钩也”只是一个结论,并未给出求证过程。“真赏斋物,有华氏诸图章”则是根据印章判断其出自华氏,考证的意味更足。
与吴其贞和顾复相比,高士奇所记相对全面、客观,在记明“纸本,高八寸,阔三寸,计三行”之后录出正文,并指明释文所据为“音释本《法书要录》”。再之后是对作品信息的详细记录,最后是对文徵明题跋和印章的完整记录。对作品信息的记录如下:
右草书,计二十六字。宋宣和御府收藏。月白签,御标“晋王羲之袁生帖”七字,泥金楷书,“晋”字微有剥损。黄绢隔水右边钤印长方“双龙”玺二方,“御书”瓢印一方;本帖之右圆“双龙”玺一方,“宣和”连章一方。帖左“政和”“宣和”二玺印,长方“双龙”玺二方,“政和”连章一方,后有“内府图书之印”;末有“真赏”瓢章,华夏藏印,盖锡山华氏故物,摹入《真赏斋帖》者。以火前刻本较之,毫发不爽。外用宋刻丝装褾,织成仙山楼阁,颜色秀丽,界画精工,烟云缥缈,绝似李思训,虽笔墨追摹,恐未易到,非是帖不足以当之也。[1]1
通过高士奇的记录,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顾复所记宣和六玺、徽宗题签、文徵明跋、华氏诸图章、宋刻丝包首的具体内容、位置和大略形态。虽然高、顾二人在正文字数的计算上有出入,但大量相同的细节证明他们所记为同一作品。正文字数的不同,应是对草书释文的不同所造成的。顾复未列释文,而高士奇列出并指明了出处。值得注意的是,高士奇的记录顺序符合鉴赏一件卷轴的习惯。由绢纸、尺寸、行数、正文、题跋依次看去,仿佛缓缓打开了一个卷轴。另外,据印章判断为华氏故物以及与火前刻本比较的做法,正是考证之法。

王羲之《袁生帖》

文徵明《跋王羲之袁生帖》
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先对藏品信息作了描述,之后给出释文,再录文徵明题跋,最后以“外录”的方式录入《清河书画舫》中有关文献。对藏品信息的描述疑似从《江村销夏录》摘录,但有几处不同,一是卞永誉正文释为二十五字,较高士奇少一“尽”字(纸本此处残缺);二是卞永誉所录文徵明题跋与高士奇有四处不同,卞录“佑陵”而高录“祐陵”,卞录“沈惟则”而高录“沈为时”,卞录“尝以示余”而高录“尝以示予”,卞录“复观”而高录“复见”,卞录“俾予疏其本末云”而高录“俾予疏其本末如此”。另外,高士奇记出文徵明题跋后有“徵”“明”两印,而卞永誉未记。与文徵明题跋相校,高士奇所记一字不差,而卞永誉四处全错。(如图)
吴升《大观录》对《袁生帖》的记录与高、卞二人相似,列纸绢(指明冷金笺,较高、卞二人详细)、尺寸、书体、字数、鉴藏印、题签、宋刻丝包首等信息,再加以议论,再录正文和文徵明题跋,文徵明两印未记。其正文字数与卞永誉相似,记二十五字,较高士奇少一“尽”字,另外,正文中高、卞二人均释为“怀”字而吴升释为“惟”字。文徵明题跋中,吴升录“贉纸”,而高、卞二人录“覃纸”,另外,“复观”和“俾予疏其本末如此”两处均与卞录相同而与高录相异。
《好古堂家藏书画记》没有记录《袁生帖》。相对而言,姚际恒所记藏品的重要性难以与其他四部著述媲美。书中所记画多于书,而书法则主要集中在碑帖。体例也较为散漫,有的仅列条目,有的则详记题跋、印章等信息,少数作品有简略的考证。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对记录和考证的重视是康熙朝书画鉴藏类著述体例的共通之处,但相对而言,《江村销夏录》体例更趋完备。我们似乎可以把这一现象归为时代使然,因为在当时的题跋、笔记、诗文中随处可见对所见、所藏、所闻书画信息的记录和考证。
结 语
易于操作的“江村体”对后世影响深远,大量仿“江村体”书画鉴藏类著述的出现,被余绍宋等学者指责其不讲考证,徒为钞胥。但记录与考证并不矛盾,实可并重。客观、全面地记录作品的纸绢、尺寸、印章、题跋等信息和考证的逐渐加强,是晚明以来书画鉴藏类著述体例发展的一条脉络。高士奇《江村销夏录》沿着这条主线,在《铁网珊瑚》和《清河书画舫》的基础上有所延续和创新,使得此类著述体例渐趋完备。《江村销夏录》并非特例,对于记录与考证的重视在康熙朝的其他五部同类著述中皆有体现,但以《江村销夏录》最趋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