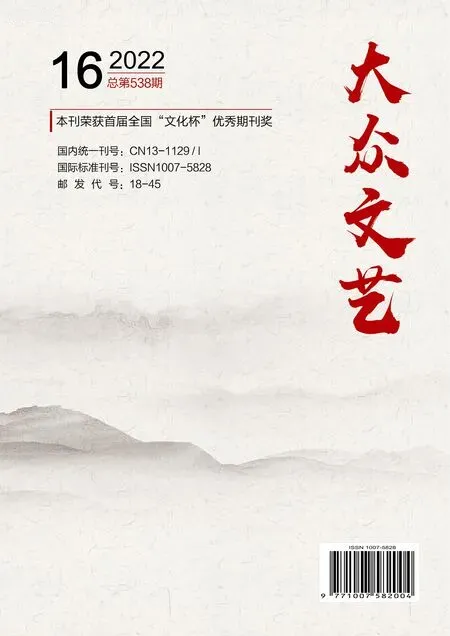以《千里江山图》为例论题跋的鉴藏功用
郝若含 (天津师范大学 300000)
题跋是观赏者对于艺术作品的一种欣赏,代表其内心的直观感受。书法题跋不仅能够体现古人的美学思想,同时也以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也为后世提供了作品鉴藏的重要依据。
一、题跋的概述
书法题跋是附于作品之上的一种篇制短小的文艺理论,一般是以题写者的感受为出发点进行记录、评论、鉴赏,而这些文字信息也为后世更全面的研究作品提供了帮助。最早之时,题跋这一艺术形式并不拘泥于纸张之上,题跋的鼻祖可以追述到青铜器物、画像石之上的题款,严格意义上来说虽在形式上与书画联系甚微,但究其实本质来说这就是一种早期的图像与文字的结合。具体意义上的题跋萌芽的出现是战国墓葬当中出土的帛书,在这些帛书之上文字与彩绘神木得以同时呈现,文字又对图像进行了解释和描述,此时真正意义上的书画结合出现了,题跋也随之有了略显具象的艺术形式。魏晋南北朝之时仍属于题跋发展的早期,这一时期的作品中题跋并不常见,人们对于题跋的观念意识也暂未形成,相对于发展的较为完备的绘画技艺题跋显的单薄,而人们认为的《洛神赋图》之上的题款也被考证是后人加上去的,并非是同时代的题跋,隋朝的展子虔的《游春图》也是同样的境况。题跋在史料上有记载是在唐代,此时的题跋在绘画作品上是以钤印的方式来表现的,虽然形式单一但是不可否定的是题跋逐渐开始以题的方式附着于作品之上。历史发展至北宋之时,题跋得以定型并趋于稳定发展,这是基于北宋当时繁荣昌盛的学术文化氛围,文人开始展示内心世界,因此也出现了黄庭坚、苏轼等题跋大家在画作之后题写诗词以表达与画作产生的共鸣,至此诗、书、画得以融合。随着文人画的兴起,书与画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开始广泛应用于画作中,题跋变为画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题写的内容也是一门艺术,它往往体现了书写者的文学素养,这就要求题跋的内容是要经过推敲考究并且联系画面得出,它要在形式和情感中找寻一种平衡,既要使得题跋不过分附庸于画作又不能让其跳脱于画面之外。这一时期名作的题跋大多由文人学士进行书写,相对于常人来说他们能够直接的面对作品进而抒发真实感受,能获取更多信息了解画作甚至还有可能与作者交好,因此题跋便具有了鉴藏价值,它为观者和后世鉴藏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不仅如此,题跋本身所具有审美价值对于画面也是有突出作用的,书写题跋时要考虑书写的位置、形式、体裁、风格等,使题跋与画面协调统一,观者在欣赏画作时能够自觉地将二者融合,这样一来精湛的绘画使题跋有了价值,题跋也与作品交相辉映,至此题跋以其灵活性获得更稳定的发展,而本文研究的《千里江山图》的题跋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引发现代学者对画作真伪的鉴别。
二、蔡京书法题跋呈现的信息
细观《千里江山图》,不难看出其题跋分为多个部分,在画作末端出现的传为蔡京所作的题跋是鉴藏的关键点也是争议点。题跋内容为:“政和三年闰四月一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通过这一题跋,我们可以得知的有效信息是这幅画作次赏赐给了蔡京,画作作者的姓名是希孟并且此人勤奋好学好画,关于身份的变动则先是画院的学生,之后被召入文书库;而画学上对这些并无记载,故而题跋的信息变得尤其关键;而据考证“谓天下士在作而已”这句话出自蔡京被满朝批判反感之时宋徽宗鼓励其坚持自我。
三、《千里江山图》书法题跋在鉴藏争论中的实际功用
1.提供具体信息对书画鉴藏起参考作用
面对一幅书画作品进行鉴藏活动之时大多数学者都会选择从作品本身开始,分析作品整体的风格、笔法的特点、墨法的应用以及构图等。但若出现这些具体信息都无法得知的情况时,而画作之上又有题跋,那么题跋所能提供的信息就变得重要,此时对题跋的内容和跋文绢幅的材质等进行分析便会得知题跋人对于作品的一些描述、观点同时也可以对题跋的真伪性作出初步判断,这关乎书画鉴藏活动如何展开。前面提到的《千里江山图》中蔡京所作题跋就是个例证。短短一段题跋交代了作者信息、作品流传过程、赏赐画作的目的,与史料记载相比虽不够全面,但在无法得知其他信息的情形下这段题跋充当着重要角色。如今,基于蔡京书法题跋提供的具体信息引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鉴藏争论:一方是以艺术史学者曹星原为代表的否定派,另一方是以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余辉先生为代表的肯定派。
艺术史学者曹星原女士所持的观点是这幅所谓的北宋山水名画实质上是一幅普通画作在清代收藏家梁清标的“精心包装”之下通过与蔡京等人的题跋作品拼接而成的伪作,她以蔡京所作题跋的绢幅的材质与画作所用绢幅材质的不同为切入点,再将题跋绢幅与画卷画芯的受损程度进行比较,最终对这幅画作鉴藏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曹星原女士的质疑有迹可循,谈起古代书画作伪,其实并不罕见,临摹、仿造、挪移等这些手段存在于被多次装裱并流经于不同朝代鉴藏者的画作中,换言之因题跋自身固有的书法形式也决定了其存在作伪的可能性。
而余辉先生则与曹星原女士所持的鉴藏观点相反,他认为这幅画作的题跋位置发生了变化,但题跋与画作本身并不假。面对这幅流传甚久甚广的画作,我们有理由怀疑其在题跋上的真伪性,题跋是否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是否就是这幅画作的题跋?题跋本来就在这一位置还是在装裱过程中被裁开挪动了?或是题跋这一部分根本就是从别的画作中裁剪下来挪移到这副画作中?而余辉先生以这幅画卷中蔡京所作跋文的字迹为切入点通过与被考证的蔡京书法作品对比,再辅以对蔡京书写特点、习惯的分析,证实题跋确为蔡京所作,在此基础之上他通过史料与题跋所述内容进行对照,最终确认了这一题跋与画作的真实性。
2.类比相关题跋为鉴藏提供重要辅证
学者曹星原对于题跋的书写位置提出了质疑。蔡京所作题跋写在了画卷后方,据史料推测,政和三年此时的蔡京已五六十岁有余,而他作为一个居高位的长者给一位晚辈题跋,题跋却书写在画卷后方,这与实际相矛盾;通过类比其它作品中蔡京所作题跋,不难发现,蔡京题跋出现在作品末端的情况只存在于其为君主宋徽宗作跋,大量的宋徽宗传世画作的真伪性是依据蔡京所作题跋的位置来鉴别。例如《听琴图》传为宋徽宗所作,但因其画中蔡京所作题跋位置居于画面上方不符合臣子为君王题跋的规律,所以据此推断这幅画作可能并非为宋徽宗所作,而有代笔之嫌;在另一幅已判定为宋徽宗真迹的绢本设色画作《雪江归棹图》中,也同样有蔡京所作的题跋,不同的是,在这幅已经被鉴真的画作中蔡京所作题跋的位置则在画作后方,种种情况表明蔡京题跋对判定画作是否为宋徽宗真迹的关键性,也向我们展示了君臣之分存在于画作之中,基于这种情况所以蔡京在作题跋之时必须谨慎,那么《千里江山图》中题跋位置是否发生变化也得到了解答。
四、结语
综上所述,题跋的鉴藏功用尤为明显,不容忽视。由于我国古代的画作保护意识略显淡薄,经过不同时代收藏家的把玩鉴藏,画作之上也附加越来越多的收藏印鉴,在原有基础上再书题跋来品评画作之事也较为常见。这就要求我们在画作鉴藏环节中重视题跋的艺术价值、文化意韵、鉴藏功用,审慎面对复杂的鉴伪情形,提高自身鉴别能力不轻易将一幅画作判入伪作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