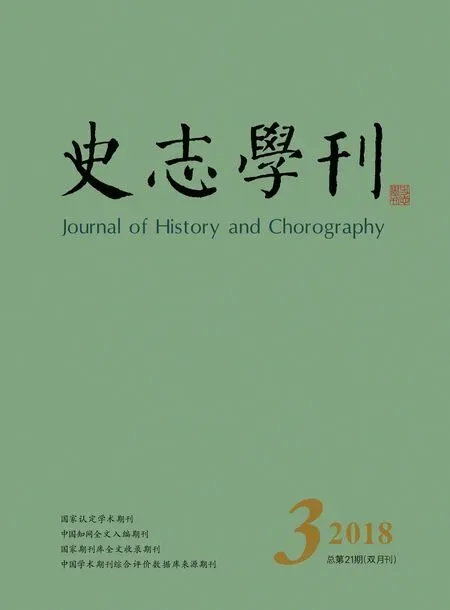清代“鸡心滩”争案的环境史
刘赫宇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2)
晋、陕两省之间的黄河小北干流段滩地纵横。胡英泽曾利用鱼鳞图册和碑刻等资料,围绕滩地的诸多问题进行过研究,从生态角度对社会区域史进行全新诠释[1]胡英泽.流动的土地——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为我们从环境史分析类似问题提供了新视角。此外,环境史学者沃斯特认为在环境史的研究之中,应聚焦在三个相互作用的变化上:其一是地球的各种系统(气候、地理、生态系统)伴随时间的变化;其二是自这些系统中谋求生计的生产模式的变化;其三是文化态度的变化及其在艺术、意识形态、科学和政治中的表现。
具体来说,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它在过去的时代中是如何组织运作的。我们把自然的有机和无机两个方面都包括在一起,特别要将一直是自然生物链一环的人类包括在内。其次则介入了社会经济学领域,因为它是与环境相关联的。内容涉及工具和劳动,涉及从劳动中产生的社会关系,涉及人们设计出的种种生产加工自然资源的商品的方式。在第三个层面中,概念、道德、法律、神话以及其他意义的各种结构,都成为个人和群体与自然之间对话的一部分。沃斯特先生认为应将这三者作为一个整体对待[2](美)沃斯特著.候文蕙译.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面[J].世界历史,2011,(4).。本文就以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面为视角,梳理其前因后果,分析双方民众态度、地方官员应对措施及事件最终的解决。
一、“鸡心滩”争案背后的社会、生态因素
清承明制,在山西、陕西均置行省,两省以黄河河道自然分界。这段具有分界线性质的黄河北起保德州河曲,南至蒲州府风陵渡,全长超过700公里,其基本流向是自北向南。
雍正六年(1728),山西蒲州升格为府,下辖永济、临晋、虞乡、荣河、猗氏、万泉六县,其中永济为附郭增置,亦是府治所在;雍正十三年,陕西同州亦升格为府,下辖一厅一州八县,自北向南分别为韩城、郃阳、澄城、白水、蒲城、大荔、朝邑、华阴、华州以及潼关(厅)。但仅过了一年,黄河岸边就“热闹”了起来。原来由于耕种黄河滩地引发纠纷,永济县沿河村庄同对岸陕西朝邑的村庄爆发了大规模械斗,双方各自出动千余人。后来清廷派工部左侍郎乌尔泰(满洲镶黄旗人)与何国宗等员前往勘查,勘查范围包括大庆关以北明代黄河改道前的旧河道和新河道东侧之滩地,他们采取两省均分的处理办法,带人在定界范围内加筑界墙,植以树木,并且绘制地图作为凭证。有清一代的这个地区,此类事情早有发生。对此我们不禁要问,这些滩涂是如何形成的呢?其后又是如何成为可资农业利用的滩地的呢?实际上,这一地区黄河滩地的形成及其争案发生的背后,有一连串复杂的自然和社会原因。
黄河的龙门——潼关一段,水利学上称之为“小北干流”。东西两岸分别是山西永济县境和陕西朝邑、华阴县境。河干在此竟急转一个近60度的大弯,朝东北方向流去。从这里沿黄河上溯,是黄河中游广大地区,这里更是黄河洪水和泥沙(特别是粗泥沙)的主要来源区,段内支流绝大部分流经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大量泥沙从这里被裹挟冲向下游。每当夏秋雨势增大,河水还会暴涨,泛滥的洪水极大威胁两岸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待洪水退去,泥沙就会在这段河道之中堆积,从而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河中泥滩。这些滩涂形成于冲击团质,地面平坦,且“地下水资源十分丰富,打井修渠,汲水灌溉,极为便利”,加之这一地区“土壤以草甸土为主,土层深厚,质地良好,宜农宜林宜牧”[1]永济县志编纂委员会.永济县志[M].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P113),气候温和,光热充裕,雨量适中,无霜期长等条件,也可以基本满足农作物一年两熟的需要。
据《史记》记载,早在汉武帝时,河东即有滩地5000余顷,时称“河堧弃地”“时作渠田,民尝争种之”[2](西汉)司马迁.史记(卷 29)·河渠书七[M].中华书局,1959.(P1410);隋文帝时,蒲州刺史在此开垦稻田,从唐代起,小北干流的滩田因数量大、壤质优,受到政府重视;到明代前期,晋王、平阳王互奏争夺连伯滩田,历时两年多,更体现出这里的滩田面积大、壤质优。很多沿河村庄的村民夹杂劳作于滩地之上,其中就包括山西永济和陕西朝邑、华阴等地的农民。根据胡英泽的统计,明初仅陕西一侧的黄河滩地面积就至少有20万亩,而山西一侧更是在60—70万亩之间[3]胡英泽.流动的土地——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M].大学出版社,2012.(P60-61)。
然而,享受大自然恩赐,必然承担相应风险。原因在于这段河道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每隔数十年必会发生较大的改道或淤涨,因此素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法(胡英泽认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河道的周期性变动,给东西两岸村庄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带来周期性的转移,所以它又是社会与自然形成的一种关系,具有文化的意义”。而沿河的环境也对当地人们精神信仰造成巨大影响[3](P125,P127-138)。自明代起,黄河中游流域的生态就开始持续性恶化:
以山西为例,晋北偏关之间的长城附近,山势高险,林木茂密,自明初就被视为北部边防的第二道屏障,可是仅仅百年左右,这道边防屏障就受到严重破坏。首先是北京的达官贵人、边境的驻军将士、本处的居民都纷纷进行采伐,每年贩运到北京的大木就不下一百多万株。很快,满山林木十去六七[4]马雪芹.历史时期黄河中游地区森林与草原的变迁[J].宁夏社会科学,1999,(6).。由屯田、畜牧造成草原的破坏也成为这一时期黄河中游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
王元林认为自明代起小北干流就开始了大规模变迁。最明显的表现是,泛溢已不是这一时期河道变迁特点,代之而起的是大规模地决徙改道,摆动不定,冲蚀崩塌。其中摆动幅度最大的河段当属蒲(州)朝(邑)之间,隆庆四年(1570)的大洪水更是遍及整个小北干流,蒲朝之间的三十里也汪洋一片;万历初,黄河又东徙;万历八年(1580),已侵至蒲州,大庆关及原西岸三牛当毁于此次东徙;万历十一年新设的大庆关西移15里,河道也西迁同样距离;到万历二十六年,河水又西徙5里左右,大庆关第二次迁移,已东距朝邑10里左右。而蒲朝以南的河道,黄河成化中西徙竟夺洛入河,与蒲朝间西徙一致。自康熙朝黄河主流东行改道后,永济县城距离朝邑县境的大庆关更是仅有5里之遥。这种河段的活动一直持续到清代[1]王元林.明代黄河小北干流河道变迁[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3).。
除了生态因素之外,当地独特的社会环境也成为滩地争案频发的重要原因。山西蒲州及临近的陕西朝邑、华阴、潼关等地,人稠地狭,耕地资源较为稀缺。因此两岸的沿河村民均十分珍视滩地资源。由于经营滩涂充满着很多风险和不利因素,还需面对风沙袭扰和不时到来的水患。由于收益保险系数较小,他们往往“有滩就种,不惜工本”,河滩上的耕作也“多采用广种薄收,掠夺式经营。不治理,也无力治理”[2]永济县志编纂委员会.永济县志[M].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P115)。
胡英泽还曾对清代至民国时期黄河的滩地作过专门研究。他认为虽然滩地除了农业收益外,还可开展制碱、制盐等生产,但农业依然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尤其对于那些原有土地被河流淹没,日常收益完全仰仗黄河滩地的村庄。但无奈“定居的村落、农业生产的偏重与出没无常的滩地形成了冲突”[3]胡英泽.黄河泛滥、河道变迁与农地制度技术策略——以清代至民国的山、陕黄河滩地历史文献为中心[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而同时政府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相应管理,因此在滩地上耕种的各方总是冲突不断。除去雍正七年(1729)那次大纷争,类似的事件早就发生过。在此前的康熙十三年(1674),在黄河滩地耕作的山西永济县鸳鸯村村民就因分地不均同对岸的陕省村民发生大规模斗殴,“动千百人,势若公战”[4](清)乔光烈,周景柱总修.蒲州府志(卷 21)·艺文[O].乾隆十九年刻本.。待冲突稍被平息,清廷开始派人在冲突发生地区筑立界墙。
然而更大规模、更为复杂的纷争还在后头。在乾隆四年(1739)、五年,几场洪水过后,黄河河道中(在蒲州城西南的洛、渭、黄汇流处)逐渐形成一个面积较大的泥滩,长约7—8公里,宽约3—4公里。因形状酷似鸡的心脏,永济县的村民形象地称之为“鸡心滩”,朝邑县的村民则称之为“夹沙滩”。鸡心滩所处的位置十分特殊,此滩“系另在河中,并非从前所筑界墙之内,秦晋之民均属有份”(关于鸡心滩形成的具体时间,有史料提出与第一历史档案馆奏折记录不同的看法,如光绪《永济县志》认为是乾隆三年(1738),乾隆《蒲州府志》则并未交代具体时间,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奏折记录的乾隆四年至五年为准)[5]准泰.奏为遵旨抄案绘图恭呈丈明鸡心滩情形平分立界等情事[B].乾隆十三年闰七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档号04-01-22-0026-156.,这也就为后来双方的争端制造了客观条件。
根据清代档案中的记载可知,两省(主要是山西永济和陕西朝邑沿河村庄)对于黄河“鸡心滩”争夺的激化始于乾隆十一年(1746)。这一年,滩涂西侧的河水流量突然减少,陕省民人因此认为鸡心滩与秦地毗连,遂思独占。正当双方争执不下之时,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原先水小的滩西侧水量突然增大,晋省一侧的滩东侧水量大减,露出大片滩涂,大有毗连之势。主动权似乎又回到了晋省手中。(本图转自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心CHGIS系统V4.1820年数据,路伟东绘制。图中粗线为原划省界,东北为晋,西为秦,东南为豫;图中亦可以清晰了解“鸡心滩”与永济、朝邑等县的位置关系。)

图1 清代“鸡心滩”附近流域示意图
有了老天爷的“壮胆”,乾隆十二年(1747)正月二十九日及二月二十九日,永济县村民纠集成伙,两次将在滩耕种的秦民驱逐出滩,并毁其草房,夺其农器。此后这类事件又发生了几次。秦民们吃了亏,到官府告状。
消息传到京城。当年三月二十四日,皇帝令军机大臣传谕时任晋抚爱必达,“务委妥协之员,详加会勘,不可因晋省民人,稍存袒护之见,秉公定界,永杜争端”[1]王欣欣.清代山西巡抚[M].山西出版传媒集团,2013.(P111)。而除了报官之外,秦民自然也不会闲着,他们没有善罢甘休。“陕省民情大概质直而任气逞刁,目无官长亦多有之”[2]清高宗实录(卷265).乾隆十一年四月乙未[M].中华书局,1985.(P445)。此后又有大批沿河村庄秦民为乡亲“报仇”,他们手持棍棒农具来到滩上,将在滩劳作的部分山西永济村民打伤。这样你来我往,双方积怨愈深。
对于河东强悍的民风,当地官府亦早有领教,自然更不敢怠慢。几乎在滩地争端出现的同时,解州府安邑县民因官府追比钱粮,数百人聚众围城,拆毁东门外牌坊,并放火焚烧北门;蒲州府万泉县更有部分农民因抗粮被捕,群情激愤冲入县城,冲击县衙,并扣押蒲州知府,威胁索要监犯。这些事件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所以在处理类似的村民纷争时,承办官员总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由上可见,同黄河其他滩地争案一样,围绕“鸡心滩”发生的争端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滩地的形成与此地地质、水文条件直接相关,明清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森林破坏,使水土流失已相当严重,进入夏季,大量的降水汇入黄河,裹挟泥沙到达这里,极易形成大面积的泥滩。另一方面,小北干流两岸均为农业地区,且人稠地狭,可耕种的土地资源十分稀缺,而滩中泥涂肥力极高,所以两省长期将滩地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源。但与此同时,黄河及滩地多变的特点又决定了利用这种资源时,原有分界起不了作用,极易发生使用权上的纷争。
二、争执不下:事件的初步解决
两地之间出现如此的争端,涉事州县各地方官自然首当其冲。永济县令费映奎提议遵照雍正七年事件的处理办法,使永济、朝邑各分其半,人们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因此最初“众以为允”[3](清)乔光烈,周景柱总修.蒲州府志(卷 21)·艺文[M].乾隆十九年刻本.。但不知为何“俄而其说中变,几再遣官,持意不能合”,双方暂时抑制的矛盾再次激化。
乾隆十二年(1747)五月,准泰到任山西。同年十二月,陈弘谋亦自鄂抚调陕。乾隆十三年七月,到任不久的准泰在查阅案卷后,认为原永济县知县费映奎在办理滩地争案时,既有畏惧永济民人之猛,亦有偏袒本省之嫌,以致“办事失准”,遂上奏将其参劾革职。同时,准泰派遣太原府通判恒庆赴蒲,陈弘谋亦派时任同州知府的乔光烈前往蒲州,蒲州知府李更在永济与其会合,众官员一并前往“鸡心滩”等地实际查勘。勘查结果显示,雍正七年乌尔泰等人所筑界墙在大庆关之西北,其大庆关西南另有康熙年间先筑者,两次所筑,总长度超过44里,直抵南首黄河湾处为止。
而考虑到此前蒲州发生多起抗官事件,乾隆帝对于革职费知县的决定,心中亦有顾虑:“山右民风,素称刁悍。倘谓该县因爱护百姓致被参革,哄然群聚纠众保留,岂不更滋事端”。他要求准泰针对民间局势预加防范,同时令准泰“当如何分界方为妥协之处,详晰绘图,于图间按地贴签进呈”[1]王欣欣.清代山西巡抚[M].山西出版传媒集团,2013.(P123)。
准泰提议遵照雍正七年(1729)之例,将此滩丈明,除去荒碱,将熟地平分,划沟立界,沟东属秦,归潼关同知管辖;沟西属晋,归蒲州永乐镇同知管辖。“俾两省小民均沾地利,自此争端可息,民业得安矣”[2]准泰.奏为遵旨抄案绘图恭呈丈明鸡心滩情形平分立界等情事[B].乾隆十三年闰七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档号04-01-22-0026-156.。显而易见,准泰这个建议充分参考了先前被参劾之费知县的方案,对处理此类事件并无太多新的认识和建树。
三、惊动朝廷:事件的最终解决
其实说起如何划分滩地的问题,首先要了解滩涂上可耕之地的数量及形态。胡英泽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滩地并非都是规则形状的,这就为分界工作增加了难度。滩地作为一种特殊的土地资源,受到河水涨盛、河道迁徙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后,滩地面积、形态和壤质都会发生巨大变化。
而要说这起争案的最终解决,首先需要了解当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因为不同沿河村庄,地形地势均不相同,滩地在村庄土地结构中所占比例及在村庄经济中的地位亦不相同。胡英泽指出,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了不同于常田的农田技术制度,从而在不稳定的滩田中建立相对稳定的生产秩序[3]胡英泽.流动的土地——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P139)。
乾隆十三年(1748)闰七月,时任鲁抚的阿里衮与准泰对调,再任山西巡抚。而到任第一件事就是处理鸡心滩一案,阿里衮派归绥道台卓尔岱和雁平道台葛尔福“前往该地覆亩确勘,秉公悉心酌议”,陈弘谋亦派榆林道台礼山、潼商道台李肖筠同往。考虑到此前黄河滩地纷争的复杂性和顽固性,乾隆帝朱批“汝两人何不面会商办?属员传言终非妥计”[4]阿里衮.奏为奉旨委员会同陕省干员前往滩地确勘秉公办理山陕民人互争鸡心滩一案事[B].乾隆十三年九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160-038.。
这样,两位抚臣的面商就提上了日程。但身为一省最高官员,辖境财政、军政、民政均需由其亲自处理。晋抚阿里衮于乾隆十四年二月初六日从太原府起程,于十五日至蒲州。巧合的是,阿里衮南下之时,正值前去平定大小金川起义的忠勇公傅恒班师回朝,他于二月初六日从军营起程回京,预计不久就会经过山西境内,阿里衮在太原安排“所有应备肩舆夫马及行馆糜给一切供应事宜,臣已委派文物大员分段预为妥协备办,并派专员沿途护送”[1]阿里衮.奏报会勘蒲州与陕西朝邑民人互争鸡心滩地事[B].乾隆十四年二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档号04-01-35-0011-044.,自己则准备在蒲州亲自迎接傅恒入境。
同时,陕省此时亦有较多军政事务需要陕抚亲力亲为。在安排好西安的事务之后,陈弘谋于二月十二日自西安府起程赴蒲,并于四日之后到达蒲州,与早已在那里等待的阿里衮一行人等会同前往鸡心滩等地。又进行了一番十分细致的实地勘查。
考虑到此前这一地区若干起滩地之争的反复性,皇帝亦在筹划一劳永逸之策。早在乾隆十四年(1749)元月十八日,朝廷以大金川乞降,命傅恒班师,并特封其“忠勇公”。由于傅恒回京必经晋陕二省,又身背如此战功,清廷对其信任有加,命其路经晋陕之际顺道勘查鸡心滩情形。
但经过仔细考虑,如果遵照这样的安排,就需要绕道前往,至少多花去四五日时间,“恐误三月初十日以前之期,不及往勘”[2]傅恒.奏为遵旨知会陕抚陈弘谋、晋抚阿里衮不再往勘山陕民人控争鸡心滩案等事[B].乾隆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档号04-01-12-0064-093.,最终乾隆帝亦认为此举并不妥当,命其直接由晋回京,傅恒最终于三月初七日返抵京城。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阿里衮心中却已有了理想的方案。念及平日在滩劳作的晋省农民居多,秦省农民相对较少,他认为前任晋抚准泰各半平分的处理意见多有不合理之处。且“老滩碱地与已种熟地错杂相间,将来均可开种,则除去荒碱之难即为定论,或如讬庸所议,以现今河身西宽东窄,将地亩会归晋省,则秦民久经分种,一朝失业,未免向隅”[3]阿里衮.奏为酌议黄河鸡心滩地秦晋均分耕种永杜争竞事[B].乾隆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171-047.。深思熟虑之后,阿里衮上奏提出自己的意见:“将滩中地亩除四围嫩滩外,其已种之熟地、并未种之老滩碱地均以六分给晋民耕种,四分给秦民耕种,照依前案筑立界墙,栽植树木以垂久远,将来地有坍涨,搃照界起除,永杜争竞”,而“两省官民俱各允服”[3]阿里衮.奏为酌议黄河鸡心滩地秦晋均分耕种永杜争竞事[B].乾隆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档号04-01-01-0171-047.。
很快,乾隆帝就应允了阿里衮的办法,两省地方官也未提出不同意见,涉事各方村民亦表示遵从。紧张的分拨工作完成后,最终山西永济县分得滩地136顷46亩有余,而陕省共得到滩地86顷52亩有余,其中朝邑县分得53顷20亩有余,而华阴县分得33顷32亩有余。与清丈分拨同时展开的还有定界工作:依照以往惯例,筑立界墙、种植树木,“以别疆域”,其中界墙“其北界对高家社,其南界对凤凰嘴”[3],分界不清的状况暂时得到解决。
乔光烈是这起争案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据《清史列传》记载,乔为上海人,乾隆二年(1737)进士,两年后实授宝鸡县知县,从此开启仕途。乾隆十一年(1746)由陕西乾州知州迁任同州府知府,见证了此次滩争,并亲自参与了清丈分拨工作,为争案顺利解决做出了贡献。之后的乾隆十六年(1752),他迁任山西河东兵备道,在乾隆十九年(1754)编纂的《蒲州府志》中,作为蒲州地方要员和那次争案的亲历者,特撰《国朝乔光烈鸡心滩记》一篇,以明后世。
根据此文描述,其实在“秦四晋六”的办法提出之后就有部分秦民表示,接受了如此的处理方案,陕省是亏了本的。乔光烈秉持公正之心,强调了一个大家都忽视掉的问题。原来,他通过对鸡心滩的实地勘察,发现“其地西厚多腴,东薄多碱,以秦之四足以当晋之六”,即使陕省仅得到滩地的四成,“于秦民固无所欠,尚欲为之争多寡哉”?[4](清)乔光烈、周景柱纂修.蒲州府志(卷 21)·艺文[O],乾隆十九年刻本.这种说法得到了大家的信服,丈量分地工作也得以顺利进行。根据胡英泽实地考察得到的资料,我们也可以对滩地清丈分拨前后若干史实细节有更多的了解。
此后,双方均认同并遵从这等分法。当地政府也开始加强对滩地的管理,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征科。《永济县志》中记载最初户部认为滩地利多税轻,以致民争不休,因此定下重赋。滩多碱瘠非膏腴比,且有无不常,每岁亩租但可五升,定为一斗[1](清)李荣和等.永济县志(卷 3)·山川[O].光绪十二年刻本.。
乾隆二十年(1756),朝邑知县高翰眼见县里案卷累积甚多,遂决定彻底清丈县内滩地。“查得朝邑县辖黄河滩地,北自郃阳县交界起,南至华阴县交界止,计长72里”,而“沿河居民因向有免粮地亩,随各认为己业,群起争种,以致讦讼纷纭”。以往丈地科租,每亩以阔1步、长240步为标准。无奈朝邑地势低洼,土性俱含碱气,沿河滩地零星荒碱甚多,这样就加大了计算的难度,应每亩加增十步,计南北阔一步,东西长250步为一亩。这次共清丈滩地1379顷45亩3分,也可见其滩地规模之大。并“饬令各村乡保立清界址,各照界内地亩绘图造册,备细勘磨,酌量分拨,凡属伍畛以上,先尽原业免粮人户,然后将余多地亩按户均分”。鉴于河水有再生变迁、界址迷失之患,“将各村交界处俱令分亩筑墩,栽植柳树,又与老崖老岸之上每村建立石杆,照所拨顷亩丈步,一一详悉刊载,以杜侵占,以息争端”。而“每亩岁科租谷一京斗,亩每年改折库平纹银五分,每年六月间开征,岁内完全解司充公”,亦成为此后两岸滩地起租标准[2]傅恒.题为会议陕省朝邑县丈量过河滩地亩数目请照乾隆十五年秦晋民人分种夹沙滩地之例征谷事[B],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题本,档号02-01-04-14945-003.。

表1 乾隆年间朝邑县滩地征科情况[2]
四、余 论
纵观清代,这场事件仅是诸多黄河滩争的一起典型。事件从乾隆四、五年(1739—1740)黄河小北干流段“鸡心滩”的形成起始,到乾隆十四年(1749)告一段落,历时近十年。时间跨度大,案情复杂,牵涉地方官员之多,甚至惊动朝廷。在这十年之中,前半段绝大多数时间山、陕双方都是保持克制、友好的,且能共同开发利用滩地,可当平衡被各自的私心打破,双方的容忍度急剧下降,甚至大打出手,伤及对方村民,事态亦急趋恶化。除此之外,河身的变化无常、地方官多变的办事方式,都对事情发展起到很大影响。而此次滩地争端的暂时解决,并未有效遏制后来此类事件的持续发生。
根据胡英泽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类似对滩、对地的争端,不仅在晋、陕两省之间,同省内各村,甚至同村内的众多农社也会发生(主要是针对土地资源)。此后的光绪年间至民国时期,黄河两岸的村庄还时常因为争夺田地而大伤和气。
笔者大量参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用以梳理分析事件处理过程中两省高层官员(抚臣)同中央(朝廷)的活动关系;而现存的涉事府县方志则为事件发展细节及中下层民间动向提供宝贵资料。结合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可以较为准确生动地展现晋、陕两省在“鸡心滩”争端过程中的完整画卷。而注意搜集整理这些文献当中的社会史资料,依旧任重道远。
简言之,争案本身涉及自然、技术和思想文化三个主题,黄河中滩地争案有其自然原因,亦有其社会原因。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就这起滩地争案,实际也涉及以上三大因素:
首先,黄河中滩地的形成得益于黄河中游流域的地形及水文因素。黄河流经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大量泥沙从这里被裹挟冲向下游,河水行至“小北干流”,河身在此急转了近60度的大弯,朝东北方向流去。大水过后,会形成大大小小的若干滩地。由于河身在这里十分不稳定,每隔数十年必会发生较大的改道及淤涨,素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法。
其次,独有的水文特征使当地沿河村民长久以来遵循特有的农业生产方式。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此地就有关于耕种滩地的记载,黄河两岸民众均十分珍视滩地资源。而处于两省多县交界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之前代划界不清等积弊,为争案的发生埋下更多伏笔。
同时,环境与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系是最为复杂的部分,胡英泽在其专著《流动的土地》中亦做出精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鸡心滩地争案的解决过程中,自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若干因素是密不可分的。这些史实,突出了环境史研究的特征。因此只有更多从自然环境的角度看待社会史中发生的事件,才能做出深入的分析,得到客观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