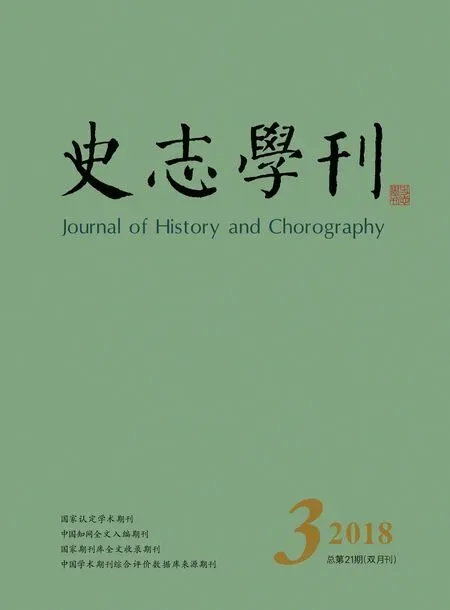1931—1945年国人对甘青藏区经济的调查研究
——以杂志报刊资料为中心
张福强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武汉430074)
甘青藏区系指今甘肃及青海的广大藏族聚集地区。该地地理位置偏僻,即使在清代西北史地学勃然兴起后,国人游历其间者依然很少。抗战爆发后,由于特殊背景驱使,赴甘青藏区的国内考察家骤增,写下了诸多游记及调查报告等,大大提高了时人对于此地的认知。其中,对甘青藏区经济情况的调查研究是考察家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目前对于该时期此项内容的研究尚多停留在资料的汇集整理阶段,对其进行学术史类的述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在前人资料基础上,对甘青藏区经济情况的调查研究做一梳理。一方面,希望对民国西北史地的研究有所裨益;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探讨抗战时期国人对甘青藏区经济的看法,能为今天的藏区开发,提供一些认识上的帮助。
一、抗战救国与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民族救亡成为主题。此种情况下,国人逐渐认识到西北地位之重要性。周宪文撰文疾呼“东北业已版图失色,西北又已岌岌可危。为免使西北为东北之续,固急议从事开发,巩固国防。”[1]周宪文.东北与西北[J].新中华(上海),1933,(11).顾执中在《到青海去》自序中说“处于严重的现时代的我们,已不暇为目前的国难,作无益的呻吟和悲叹;我们只有紧紧地把握住现在,对于已失的领土,我们当以铁血去收回,对于尚未失去而危及四伏的边疆,尤其是广大富饶的西北,当奋全力以经营它,充实它,以免重蹈覆辙。”[2]顾执中,陆诒.到青海去[M].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P2-3)更有一些爱国知识分子自发组织起来,创办报纸、杂志,从事西北边疆问题研究。一时间,“西北开发”之声高唱入云。在“西北开发”浪潮的直接推动下,到西北地区的考察家规模空前。宋子文所说“中央的人,纷纷到了西北,社会的领袖也纷纷到了西北,‘到西北’已经成为一种‘国是’了。”[1]宋子文.西北建设[M].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P98)西北研究一时蔚然成风。甘青藏区地处西北,随着西北调查研究的步步壮大,大批考察家来到甘肃的拉卜愣、卓尼等藏区,青海的玉树、果洛等藏区,对其见闻进行记述,或汇录成册,结集出版,或发表于国内各报刊杂志。以前鲜少有人踏足的甘青藏区,逐渐成为国人关注的重点对象。甘青藏区研究在危机中逐渐起步与发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正式开始。其后华北、华中、华东等大片地区沦丧。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内政治、经济中心也随之西移。大批国府要人纷纷发表言论或视察西北。尤其是蒋介石1942年8月视察西北四省后,提出“西南是抗战的大后方,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之声风起云涌,再次高涨。大批官员、记者、民间人士、考察团体等摩肩擦踵,纷沓而至,把西北边疆研究推向了高潮与鼎盛。地处西北的甘青藏区之调查研究也在此种风潮与动力的促动下,在国难中达到了研究高潮。
二、局部抗战时期甘青藏区经济的调查研究(1931—1937)
局部抗战时期是甘青藏区研究的起步阶段,对于经济内容的调查多体现出概述性特点,考察家多结合自己的见闻,汇录成文字,有些文章还节选了部分政府的统计数据,比较珍贵。另外,该时期调查研究的特点是对藏区开发的讨论,这一特点的出现与西北开发呼声的高涨有密切关系。以下就主要内容做一概述:
第一,关于甘肃藏区经济方面的调查研究。甘肃藏区焦点集中在拉卜愣地区,其中尤以1936年《方志》刊登了一系列文章为重点,其中与经济相关的文章有任承宪的《拉卜愣之农业》[2]任承宪.拉卜愣之农业[J].方志,1936,(3-4).、张元彬的《拉卜愣之畜牧》[3]张元彬.拉卜愣之畜牧[J].方志,1936,(3-4).、丁明德的《拉卜愣之商务》[4]丁明德.拉卜愣之商务[J].方志,1936,(3-4).、周映昌的《拉卜愣之森林》[5]周映昌.拉卜愣之森林[J].方志,1936,(3-4).。任文首先介绍了拉地农业概况,然后从农作物分布、作物亩数、作物产量、作物栽培、作物灾害五个方面来反映农业发展状况。张文主要探讨牧场范围、牧兽种类与数量及皮毛交易等。丁文研究的重点在于拉卜愣每年出入货物数量,此外,该文还对皮商、毛商、青盐、面粉、屠户、货资等情况作了记载。周文对该地森林之分布、木材数量之估计及种类的判断,详细准确,殊实可贵。
综合类文章最值得关注的是丁逢白的《甘肃经济概况》[6]丁逢白.甘肃经济概况[J].蒙藏月报,1936,(06).,该文虽未直接讨论藏区经济状况,对临洮、洮河、夏河、岷县、临潭、西固等藏族聚居区或散杂居地区羊毛及可耕地、荒地面积的调查分析,数据详实,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料。对藏区经济开发探讨最全面的文章当属张其昀的《洮西区域调查简报》,该文提出了发展本区的四大要点,即道路修理、农田水利、森林保存、畜牧改良、工艺促进、教育倡导,还指出“夏河有拉卜愣寺,可称为西北藏族之重心,临夏为西军故里,可称为西北回族之重心,故言开发西北,是区实居重要地位。”[1]张其昀.洮西区域调查简报[J].地理学报,1935,(01).
第二,关于青海藏区经济方面的调查研究。对畜牧业关注最多、最有深度的当属张元彬。他先后发表了《如何开展青海的畜牧事业》《青海蒙藏两族的经济政治及教育》《青海蒙藏牧民之畜牧概况》《由发展畜牧事业走向建设西北之路》等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具体阐述了他对青海畜牧事业的系统认识。他首先调查整理了青海蒙藏二族畜牧业的基本情况,在《青海蒙藏两族的经济政治及教育》和《青海蒙藏牧民之畜牧概况》二文中,对畜牧的人员、狩猎的方法及牲畜的类别,包括青海马牛羊骆驼的特色、产地、种类、优缺点、驯役、改良、疾病、繁殖、副产利用、母羊保护、皮毛产销等,驴骡猪鸭鸡犬的情况以及蒙藏两族牧地等都作了详细的交待。在对事实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青海蒙藏畜牧事业的三大措施,接着他又从更高层面上探讨发展畜牧事业和西北建设的关系,站在国家的角度上提出一些具体措施。赵慧民通过对青海蒙藏二族畜牧情况的详细调查,拟定出定牧、改良繁殖和畜种、注重卫生、改进饲养及管理方法、栽培牧草、设立防疫站、培养人才、组织畜产品制造场十条建议,《发展青海畜牧事业之方案》一文详述了他的观点。李玉润的《青海畜牧事业之一瞥》一文分为牧民之分布、牧兽之分布、牧兽之现状及改进之意见四部分,他认为“青海畜牧事业,为青海全省经济之重心。蒙藏人民之生命有所系焉。”[2]李玉润.青海畜牧事业之一瞥[J].新青海,1936,(1-2).王连三的《发展青海畜牧事业应注意之几点》就发展青海畜牧事业之重要性、青海牧区的优点等问题展开讨论,并且提出“改露宿为舍宿”“牧垦并重”“防止猛兽及盗贼之侵害”[3]王连三.发展青海畜牧事业应注意之几点[J].新青海,1936,(1-2).三条建议。其他类文章还有张建基的《青海畜牧事业之纵横剖面》、黎小苏的《青海之经济状况》、董涵荣的《改进青海农业畜牧应取之方针》、耀午的《青海的:天然牧场》《办理西北畜牧事业规划》《青海畜种分类及其分布概况》等。
抗战初期,屯垦青海的呼声日益高涨。因此,对青海藏区农业的关注也集中在开发事宜等方面。有考察家把青海应垦之区分为十个,其中大多数是藏族的游牧地,对此梦焦尖锐指出“玉树土司众部。为唐古忒族。僅十三万人尔。何致长两千余里宽千余里之土地。竟无旷土可供内地人民之移住。”[4]梦焦.辨析章嘉代表之怀疑于青海屯垦[J].蒙藏旬刊,1934,(6).然而,李自发的意见稍有不同,他认为玉树等藏区应该垦牧并重,同时又指出“蒙藏人民习性善于牧畜,而拙于耕作,如强迫其放弃牧畜,改习耕作,或根本淘汰此种人,则非特引起民族反感”[5]李自发.如何屯垦青海[J].蒙藏旬刊,1934,(07)。其他相关此内容的文章还有《青海玉树二十五族所占田地及荒地调查》《囊谦垦殖进步急速》、安汉的《青海农田水利概况》和《青海垦务沿革现状及改进意见》、李积新的《青海垦务概况》《青海农业概况》等。
青海藏民的商业贸易,皮毛出口为大宗,它直接关系着藏民的日常生产生活。该时期出现了一批专论青海羊毛事业的文章,代表作有《青海羊毛事业之现状及其将来》《一蹶不堪的青海羊毛事业》《青海羊毛事业的检讨》《青海之羊毛》等。上述文章内容主要包含了青海羊毛的产地、质量、分类、运输、改良、价格、销路及崩溃原因,解决办法等。对青海藏族商业之研究,张元彬的《对青海蒙藏人民经商之基础知识》[6]张元彬.对青海蒙藏人民经商之基础知识[J].工商半月刊,1935,(4).一文,独树一帜,该文对蒙藏二族的经商概况、商人地位、交易特性、羔皮产销、度量衡币、卖畜习俗等进行了详细记载,是研究该时期青海蒙藏商业不可不读的文章。另外对于青海经济开发最值得关注的是青海实权派人物马步芳的《建设新青海之刍议》一文,他明确指出应该将畜牧事业的建设提到很高的地位,同时认为应该广筹资金,以50万建设畜牧场,50万建设医院,100万建设工厂,40万改进蒙藏教育。
三、全面抗战时期甘青藏区经济的调查研究(1937—1945)
全面抗战时期,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进入到繁盛阶段。在经济方面表现尤为突出,除了概述性和综合性文章外,专论性文章数量增多,深度也有所提高,关于藏区开发的讨论也更为热烈。从调查情况来看,走马观花式的考察减少,专题性的深入调查增多;从作者群体来看,除政府官员、游客、记者外,专家学者群体的加入,极大提高了调查研究水平。以下为主要内容。
第一,关于甘青藏区畜牧业方面的研究,出现了诸多内容丰富的成果。以调查区域为标准划分,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既包括青海藏区,也涵盖甘肃藏区的成果,主要代表为常英瑜的《甘青两省畜牧概况》[1]常英瑜.甘青两省畜牧概况[J].新亚细亚,1944,(1).和吴信法的《甘青两省畜牧调查》[2]吴信法.甘青两省畜牧调查[J].新亚细亚,1944,(1).二文。前文内容全面,介绍详细,第一编中分设三小节,第一节介绍调查动机、范围、线路及时间,第二节着重分析骡马减少之原因,作者得出了牧草浪费、驻军拉差等七大原因,第三节主要是对西北种畜场、卫生署西北防疫处、山丹军马场三大畜牧机关的介绍,其中该节对代牧情况的描写,他类论著绝少提及,弥足珍贵。第二编是家畜种类之梗概,包含了马牛羊驴骡骆驼等,对每种家畜的种类、饲养管理、繁殖育成等都有详细交待。后文对畜牧情况的关注主要集中于探讨牲畜损失的原因,作者归结为牧民不知育种、军队溃于青海、长途跋涉、缺乏骨料、野兽侵袭、畜牧病害、寄生虫、传染病八个原因。
第二类为单论甘肃藏区畜牧的成果。李式金的《河曲—中国一极有希望之牧区》从畜牧环境、牧民分布、畜牧种类及数量、畜产及交易四方面对该地发展畜牧之优良条件展开论证,在畜牧种类数量小节中,作者列两表格,分别呈现该区畜别、数量、价格及在甘肃、全国畜牧总量中的比重,并指出“现拉卜愣所产畜牧数字已可观,然尤注意者乃该区之潜力”[3]李式金.河曲—中国一极有希望之牧区[J].边政公论,1945,(01).。顾少白的《甘肃西南边区之畜牧》[4]顾少白.甘肃西南边区之畜牧[J].西北经济通讯,1942,(7-8).涉及区域包含夏河、卓尼全境及临潭的藏民区,内容上较之李文更加全面,分畜牧现状、牲畜贸易、畜产贸易等几方面,其中表格也更加丰富多样,有对该区人口帐房的调查,有对每百户牲畜头数的估计,也有对该区所有牲畜数量、各种牲畜占牲畜总数百分比、牲畜价值、牲畜进出口及交易额,羊毛产量及出口量、价值等的统计。徐旭的《甘肃藏区畜牧社会的建设问题》[5]徐旭.甘肃藏区畜牧社会的建设问题[J].新中华,1943,(09).一文则是该时期畜牧研究之典范,该文前两部分主要描述甘肃藏区的民族分布、物产等基本情况,第三、四部分重点分析该区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含土地分配和商业资本两方面),第五部分是对该区社会性质的分析,并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进行具体论证,第六部分主要探讨建设的原则问题。张松荫的《甘肃西南部之畜牧》[6]张松荫.甘肃西南部之畜牧[J].地理学报,1942,(9).和《甘肃西南部绵羊与羊毛考察概述》[7]张松荫.甘肃西南部绵羊与羊毛考察概述[J].新西北,1942,(3).二文也是该时期畜牧研究的重要成果,前文基本涉及了该区畜牧事业的方方面面,包括牧地域分区、农牧区畜牧概况、纯牧区畜牧概况、羊毛、兽疫以及结论,作者调查细致入微,尤其在纯牧区概况一节中更表现的淋漓精致,该节分为四部分,即家畜品种、饲养、管理以及牧草情况,其中家畜管理又分为羊栏、放牧、手抛竿、配种、剪毛、去势、绵羊选种与淘汰等,牧草小节中也分别介绍了翻白草、鹅观草、牧草、天蓝、节节草、桴狐草、茅、野豌豆等十几种牧地之常见草种,该文的最后一部分就改进畜牧事业也提出了几点意见。后文仍秉承了作者调查细致之风格,虽部分内容有些相似,但在绵羊品种、羊毛出口、织维出口之种类、羊毛之硝制等方面弥补了前者的不足之处。
第三类论著单论青海藏区的畜牧情况,与甘肃藏区相比,无论在成果数量上,抑或质量上均有差距,主要的专论性文章有王化南的《青海之畜牧》《青海贵德畜牧概况》等。其他一些考察家的游记中对此项内容也有涉及,主要有吴景敖的《川青边境果洛诸部之探讨》、绳景信的《果洛及阿瓦行记》、黄举安的《进步中的果洛》等,上述文章对果洛地区畜牧种类、物产、货币、集市及土官寺庙的经济状况都有所描写,一些材料十分珍贵。
第二,关于甘青藏区农业的调查研究。甘肃藏区方面,王匡一的《甘肃西南边区之农业》[1]王匡一.甘肃西南边区之农业[J].西北经济通讯,1942,(7-8).一文对甘肃西南藏汉杂居区农业的调查,值得注意,该文介绍完面积与耕地之后,对地权和租佃制度也有所交待,接着作者对作物面积与产量、作物栽培、灾害三方面进行探讨,并用表格的形式来呈现,为后世研究留下了宝贵的数据材料。其他统计或概况类文章还有《拉卜愣农产物输出统计表》《夏河县的农业生产》《屯垦夏河荒原可解决番民生活》等。青海藏区方面,青海藏区农业情况的研究也仅零星出现几篇,都属于基本情况的概述,缺乏太深入的分析,主要文章有王生海的《青海农牧问题》《青海地政》等。
第三,关于甘青藏区商业的调查研究。论及甘肃藏区的商业,素有“小北平”之称的拉卜愣最是繁荣发达,故甘肃藏区商业贸易的介绍,基本都集中于拉卜愣。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李式金的《拉卜愣之商业》[2]李式金.拉卜愣之商业.[J],边政公论,1945,(9-12).,该文就夏河县的输出贸易、输入贸易、贸易特色等问题都有详尽交待,文中所含表格丰富,主要有夏河每年输出货物表、输入货物表、战前每年平均输出输入数量表(含50类商品)、夏河特种消费历年来进口货物调查表等,作者还指出该地贸易有以羊毛皮革换粮食、出超、商品单纯性、贸易季节性、转口货物之存在、行使硬币等六大特点,由此还提出了发展畜牧事业、改良交通、发行藏文法币三大建议。其他相关成果还有《夏河的商业》《夏河工商业统计》《夏河皮毛》等。
第四,关于甘青藏区森林物产的调查研究。该时期开发西北的呼声逐渐强烈,因此对于藏区矿产林业等资源的勘探成为政府、学界的焦点之一,有很多专家赴该地调查,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当属洮河流域国有林区管理处负责人陈景皓及技师周重光。1942年,他们随同卓尼杨司令到迭部林区进行考察,之后整理撰写《白龙江上游的森林》《岷县南部森林初步勘测》《拉子里河重要林木之树干分析》等一系列文章。其他调查报告类文章还有袁义生的《洮河上游之天然森林》[3]袁义生.洮河上游之天然森林[J].国立西北技专校刊,1942,(7-8).、郝景盛的《甘肃西南之森林》[4]郝景盛.甘肃西南之森林[J].地理学报,1942,(9).等。相比而言,郝文价值较高,该文篇幅很长,作者首先从历史之角度来探讨西北无林之害,振聋发聩,接下来又以卓尼卡车沟松油林和洮河南岸云杉林为具体案例来探讨该片区域的森林植被状况,最后提出了西北建设应走之途径。甘肃省政府为顺利施政的需要,也组织调查了各县局的资源,后整理出《甘肃各县局物产初步调查》[5]甘肃各县局物产初步调查[J].甘肃贸易,1945,(5-6).一文。该文对夏河、卓尼、岷县、临潭、永登等区域的矿产、农业、工业、畜牧业等都有诸多介绍,是了解甘肃藏区经济物产的基础性文章之一。其他综合性文章也有诸多记载,此类文章并非专论甘肃藏区的某一经济产业,而是对牧、农、商、林等综合起来进行介绍,主要有任美锷的《叠部概况》、唐莺的《拉卜愣番民的经济生活》、陈圣哲的《拉卜愣经济概况》、周南、潘荣宗的《拉卜愣剪影》等。
对青海藏区资源的调查,关注最多的是玉树藏区,其中《可贵的玉树物产》[5]和李式金的《玉树调查简报》[6]李式金.玉树调查简报.地学集刊[J].1943,(04).最为全面。前文对玉树地区物产的名称、产区、产量、用途等用表格的形式进行呈现,其中一些调查数据,很是珍贵。后文对该地农业、矿业(盐煤铜)、畜牧(马牛羊)、林业、水利、渔业、猎业、工业(毛织业、造纸业、酥油业)、商业(集会地点、币制)等都有详细调查,最后指出了玉树地区有希望发展的几类实业,并分析了青海南部藏民不用国币之原因及改进措施,该文是抗战时期玉树研究的经典之作。
结 语
以上以民国报刊资料为中心,对抗战时期甘青藏区经济的调查研究史做一梳理,从中可以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抗战时期甘青藏区经济的调查研究,有两个阶段,是一个不断进步发展的过程。局部抗战阶段是甘青藏区经济研究的起步发展阶段,全面抗战时期是繁荣鼎盛阶段。因此,从成果数量看,呈现出递增的趋势;从成果内容看,由综合性的论述逐渐走向专论性调查;从成果体裁上看,由以游记为主走向以游记、调查报告、开发规划书等多样性成果并存;从作者群体上看,全面抗战时期中专家群体成果的大量发表,为该时期经济的调查研究增色不少;从调查区域看,第一阶段主要集中在甘肃拉卜楞地区、青海玉树等重点地区,第二阶段中考察家对藏汉杂居地的关注为其后相关研究留下了珍贵材料。
第二,该时期甘青藏区经济调查研究的发展繁荣,最大推动力为抗战救国大背景。无论在成果内容上,抑或研究走势上,均受到该背景的影响。在内容上,国难当头,危机加重,救国自然成为考察家们最为关心的主题,这一主题在文本中有着深刻反映,其中对于藏区开发的关注最具代表性。部分开发细则,如提高牧区的生产效率等,现在看来价值很大。然而,如大面积屯垦青海、改牧区为农区、大力发展工业等意见,与当时甘青藏区的实际情况有所背离,操作可能性并不大。在研究走势上,抗战的爆发,迫使大批政府机构及国人内迁,甘青藏区经济调查研究的主要作者群体来自内地,本地作者所占比率极小。抗战结束后,国内重心再度回到东部,各种机构回迁,研究热度也骤然下降。
第三,上述各类成果不仅大量见于专事边疆研究或综合性的期刊,如《边政公论》《新西北》《新青海》等,而且也刊于如《西北日报》《甘肃民国日报》《兰州日报》《青海民国日报》等地方性的报纸和《大公报》《申报》等发行量极大的全国性报纸。这些文章一方面提高了各阶层国人对边疆社会的关注,增强了他们对藏边社会的认识程度。另一方面,部分论著对藏区基本情况的系统描述为开发该区提供了参考。
——以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创办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