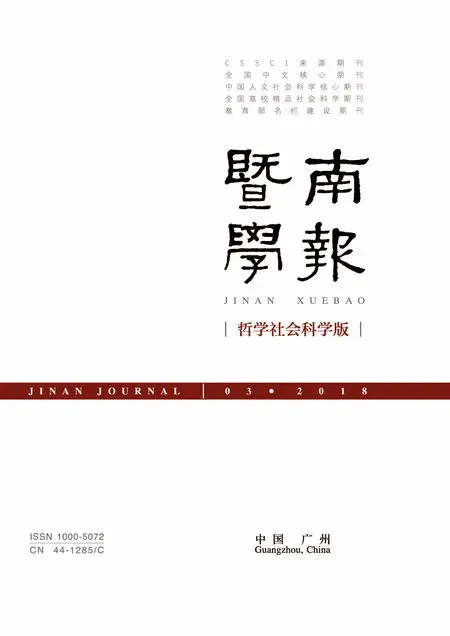论《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批评
高华平
《吕氏春秋》一书,自《汉书·艺文志》以来,在历代目录书中皆被隶之杂家,且被视为先秦杂家著作的一个标本。《汉书·艺文志》“序”杂家曰: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先秦杂家著作,共八家二○三篇。但这些先秦杂家著作,除“《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班固自注:‘秦相吕不韦辑智略之士作。’)”流传至今之外,其余皆已亡佚。故今人论先秦杂家之思想,实多有赖于是书。
只是《汉书·艺文志》既未对《吕氏春秋》的思想特点作任何说明,其“序”杂家学说之言,似乎也存在着某种模糊不清之处。如它虽然指出了杂家有“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的“所长”,但却并未指出其相应的“所短”之所在,而是转而批评杂家中有一部分“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仿佛杂家的“所短”并不是所有杂家本身所具有的,而只是在其中的一部分“荡者”那里才存在。这就无形中将杂家分成了所谓“荡者”和“中正者”两派,给人的印象是只有杂家中部分“荡者”的著作才存在“漫羡而无所归心”的问题,其他的杂家著作皆是“中正者”之“所为”,自然就都是“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的“所长”了。
具体到《吕氏春秋》一书,《汉书·艺文志》也只是说它是“秦相吕不韦辑智略之士作”,同样并未对其思想特点作出任何说明。但是,由于班固在《汉书·艺文志》的自注中已将帮吕不韦辑《吕氏春秋》那些人称为“智略士”,故这些人即使不能算是杂家中的“中正者”,显然也是不能划入“荡者”之列的。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研究《吕氏春秋》一书时,首先应该给《吕氏春秋》定下一个总的基调,即《吕氏春秋》一书并不是一部“漫羡而无所归心”之书,而是一部“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的杂家著作。
一、《吕氏春秋》的主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吕氏春秋》既然是一部“兼儒墨,合名法”而有所“体”、有所“贯”的杂家著作,那接下来的问题,就应该是探究其所“体”和所“贯”之所在了。对于这一点,历代论者除了一部分以之为“荡者为之”的“漫羡而无所归心”之作,故对它置之不理之外,大部分研究者都曾进行过认真的探讨,并得出了各不相同的结论。有人认为《吕氏春秋》的思想“较诸子为醇正,大抵以儒家为主”(《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七);有人认为此书“以道德为标的”,因而属于道家思想;又有人认为此书“大约宗墨氏之学,而缘饰以儒书”(卢文弨 :《抱经堂文集》卷十《书吕氏春秋后》);还有人认为此书之义例“因四时之序以配人事”,属于“古者天人之学”,即阴阳家言。要之,《吕氏春秋》在历代虽隶之杂家,具有“兼”“合”百家之学的特点,但它实则是有其一贯之“体”——即有其“中心思想”或指导原则的。当然,在以上诸说中,影响最大的是《吕氏春秋》的主导思想属道家和阴阳家二说。东汉高诱《吕氏春秋序》曰:
……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荀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是以著在《录》《略》。
对于高诱《吕氏春秋序》中的这段话,人们存在不同的解读。高氏曰“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公方为检格”云云,“道德”“无为”固然属于道家思想,但“忠义”“公方”则似更接近于儒家观点。故高氏接着又说,《吕氏春秋》“与孟轲、荀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孟轲、荀卿属儒家,世所周知;《汉书·艺文志》虽将《淮南子》隶之杂家、扬雄隶之儒家,然后世多以道家视之。可见,高诱之言实际仍应该是说《吕氏春秋》思想乃“兼儒、道”的意思。现代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曾批判吕不韦说,《吕氏春秋》对于先秦诸子有一个基本原则,即“对各家虽然兼收并蓄,但却有一定的标准,主要的是对于儒家、道家采取尽量摄取的态度”。这显然也是由高诱之说而来。但当代有些学者对高诱之说又有不同理解。他们认为高诱概括的道德、无为、忠义、公方等几个方面,实际只是“吕不韦(在)要求编写者们以天、地、人统一的思想来‘纪治乱存亡’”而已。这和整个《吕氏春秋·八览》的内容一样,“主要(是)讲君主应该做什么……是从君道的角度供君主治国平天下以参考”。所以,他们得出结论说:“《吕氏春秋》是新道家,是以‘黄老’为名号的新道家。”
《吕氏春秋》的主导思想属阴阳家之说,则以近人余嘉锡、陈奇猷为代表。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一书中,力辨《四库总目提要》所谓《吕氏春秋·十二纪》夏言乐、秋言兵之外,“其余绝不晓”之说为误,认为其“十二纪以第一篇言天地之道,而以四篇言人事(其实皆言天人相应),以春为喜气而言生,夏为乐气而言养,秋为怒气而言杀,冬为哀气而言死,所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也。”此乃“古者天人之学也”,正合阴阳家思想。随后,陈奇猷进一步发扬此说,更明确地指出:
吕不韦之指导思想为阴阳家,其书之重点亦是阴阳家说……今观《吕氏》书,《十二纪》每纪之首篇,《八览》首览首篇,《六论》首论首篇,以及《明理》《精通》《至忠》《见长》《应同》《首时》《召类》等篇,皆是阴阳家说,与《史》《汉》所指阴阳家之特点正合。其《十二纪》,每纪间以他文四篇,大抵春令言生,夏令言长,秋令言杀,冬令言死,盖配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义,正是司马谈所指阴阳家重四时大顺、天道大经之旨。
那么,《吕氏春秋》一书的主导思想究竟是先秦的杂家、道家,还是阴阳家呢?又该如何理解先秦道家与杂家及其代表作《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百家之学的“兼”“采”“撮”“合”呢?它们之间的异同,特别是其差异又何在呢?我认为,这恐怕不能离开《吕氏春秋》的文本来寻找答案。
在《吕氏春秋》一书中,最能表明其编撰者本人的学术思想及其对先秦诸子百家取舍态度的,莫过于该书中的《序意》和《不二》两篇。《序意》篇开头曰:“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云云,表明该书成书于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接着,吕氏自叙其著书的宗旨及思想原则曰:
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对吕不韦的这段“自序”,以前的学者也存在不同的理解。主张《吕氏春秋》属阴阳家观点的论者认为,吕不韦说自己“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当出于《汉志》阴阳家著录的《黄帝泰素》二十一篇”,“本是阴阳家学说之一部分”,所谓“上法大圜,下法大矩”和“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亦正是阴阳家言四时大顺之学也。主张《吕氏春秋》的主导思想属道家者认为,吕不韦《序意》中既言“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又提出所谓“法天地”之说,此实即老子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意,说明“吕不韦自己表述的主导思想,简言之就是‘法天地’三字”,也就“是以‘黄老’为名号的新道家”。
但在我看来,以上两种理解,虽然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是各有偏颇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吕氏春秋》一书中念兹在兹的“道”字,它与先秦诸子各家各派之所谓“道”有何联系与区别。《吕氏春秋·不二》篇曾举“天下之豪士十人”,以见各人所持之“道”的不同,曰:“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孙诒让曰:“《尔雅·释诂》邢疏引《尸子·广泽篇》‘墨子贵兼’,‘廉’疑即‘兼’之借字。”),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指出了各家学术思想的差异。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先秦诸子之学本是在当时“百家争鸣”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他们的学术宗旨又都是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所说的“皆所以为治也”,故各家的思想主张又不能不有异中之同。如阴阳家本是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以授民时”的产物,属于依“天道”而行人事之学,但如果依《汉书·艺文志》而言,“实际上阴阳家与儒、道、墨、法、农等诸子学派也都具有学术思想上的许多共同点。如《汉志》称儒家为‘顺阴阳,助教化者也’。道家的老庄以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庄子·则阳》)。墨家‘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汉书·艺文志》);而《管子·四时》则说:‘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而农家‘播五谷,劝农桑’,法家的‘举事慎阴阳之和,种树节四时之适,无早晚之失,寒温之灾’,皆与阴阳家学说有其相通之处”。
只是我们若从先秦诸子之学各自的差异来看,尽管诸子百家可谓皆是“以道自任者”,但他们各自理解和秉持的“所以为治也”的“道”,彼此却又是似是而非和各有畛域的。《吕氏春秋》所主张和作为其思想原则的那个“道”,与阴阳家“因阴阳之大顺”以配人事的“天道”,或老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无为之道”,其实皆是并不完全相同的。
与阴阳家学说相比较来看,《吕氏春秋》不仅其“四时寄政”“五行生克”等说全与阴阳家学说相同,而且其对邹衍“五德终始”之说更是深信不疑,甚至可能超出了一般阴阳家,故其中急切地告诫秦王政以水德代周的必然性和紧迫感。《应同篇》曰:“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及文王,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胜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但《吕氏春秋》又并不完全盲从或照搬阴阳家的“天道”,不把天地之道当成为决定一切的绝对力量,而是在主张“适时”或“治身与治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召类》)的同时,强调人的能动性,强调人应修德行和“知义理”,从而达到消灾化祸、变祸为福的目的。故其《尽数》篇曰:“今世上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来”;而《制乐》篇则举成汤、文王和宋景公三人修德化灾之事,力证“人德”可以影响,甚至改变“天道”之“自然”。
由此来看,《吕氏春秋》实际上并不认为自然“天道”对人事有绝对的决定作用。“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本身是客观的存在,“不长一类”,“不私一物”,“不阿一人”,可谓“至公”,“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尽数》《贵公》),人之“治身”必须无条件地遵从“天道”,“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尽数》)。但在人的社会活动方面,特别是“治世”方面,则又不然。在社会活动领域,自然“天道”虽然仍然发挥着某种感应或警示功能,却并不能对人产生“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决定作用。只要人们如成汤、周文王、宋景公那样“明理”、“修德”,照样可以逢凶化吉、转祸为福。从这个意义上讲,《吕氏春秋》对阴阳家“牵于禁忌,拘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的偏颇,甚至“五行相生相克”和“五德终始”之说,实际上都进行了理性的批判和修正,从而使自己与阴阳家的思想和学说划清了界线。
与道家学说比较来看,尽管如郭沫若所云,在《吕氏春秋》书中“道家颇占势力”,“书中每称引《庄子》,有好些辞句与《庄子》书完全相同”,可以说《吕氏春秋》对道家学说吸取最多。但实际上,《吕氏春秋》思想中的所谓“道”,与道家之所谓“道”,却是并不完全相同的。《吕氏春秋·不二》篇,是该书中对先秦诸子作出全面批评之作,在该篇所举出的先秦诸子之“天下之豪士”中,可以明确归为道家学派的,即有老聃、关尹、子列子、田骈(《汉书·艺文志》入“道家”)、阳生(杨朱)等五人,占到了整整一半之多。这还不包括《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作为稷下黄老道家人物而叙述的尸子等人。《吕氏春秋·重言》曰:“故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詹何、田子方、老聃是也。”所标举以为“圣人”者,与其他学派的“圣人”没有任何交叉,皆道家中人。故《吕氏春秋》书中屡引老子、庄子、列子、子华子等先秦道家学者之言,可见其对道家态度之一斑。
先秦道家学派,《汉书·艺文志》共著录有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首列“《伊尹》五十一篇”,其次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鬻子》二十二篇”、“《筦子》(颜师古曰:‘筦,读与管同。’)八十六篇”等。近代学者蒙文通等人,以为先秦道家其实可分为南北两派。陈奇猷则据《吕氏春秋》诸篇引伊尹学说及其行事,认为先秦道家存在所谓伊尹学派。我在经过细致梳理先秦道家发展历史后,发现先秦道家殆可分为三派,即以老庄为代表的南方道家,以杨朱为代表的北方道家和以稷下学派为代表的“黄老道家”。杨朱道家一派,蒙文通又曾以为:“杨氏之学,源于列衘寇,而下开黄老。”我也曾认同此说。但从《吕氏春秋》所引述的道家学说来看,杨朱之学应该是以“为身与治国”、“治身”与“治世”为一致的道家学说,而当源于上古伊尹之学。
伊尹之书,《汉书·艺文志》除道家著录的“《伊尹》二十二篇”外,“小说家”又著录有“《伊尹说》二十七篇”。但二书皆已亡佚,后人辑佚,不过采先秦两汉古籍有关伊尹言行事迹,裒为一帙。伊尹学说虽佚,然赖《吕氏春秋》之《先己》《本味》诸篇而得以存其真。《吕氏春秋·先己》篇载:
汤问于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对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将先取。”
同书《本味》篇又载:
汤得伊尹,祓之于庙,爝以爟火,衅以牺猳。明日,设朝而见之,说汤以至味。汤曰:“可对而为乎?”对曰:“君之国小,不足以具之,为天子然后可具。……凡味之本,水最为始。……天子不可彊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则至味具。故审近所以知远也,成己所以成人也,圣人之道要矣,岂越越多业哉!”
以往的学者多因《本味》篇所记与《孟子》中所谓“伊尹以割烹要汤”近似,故疑其乃《汉志》小说家“《伊尹说》二十七篇(班固自注:‘其语浅薄,似依托也’)”中之一篇,陈奇猷更因而进一步分析所谓“伊尹学派”为二 :《先己》所载为道家伊尹学派,《本味》所记则为小说家之伊尹学派。我认为,先秦诸子中的“小说家”,主要是一个从著作文本形式,而非从其思想内容上的分类。故认为传承伊尹学说的所谓“伊尹学派”,可分为“道家之伊尹学派”和“小说家之伊尹学派”,这一说法是不可取的。先秦实际只有一个伊尹学派,即道家之伊尹学派。如果这一学派中的某些学说,不是以书面的形式(“镂之金石”、“琢之盘盂”或“著于竹帛”)而是以“口说流传”的形式(“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传承,则被归入到了所谓“小说家之伊尹学派”。《孟子·万章上》之“伊尹以割烹要汤”,《吕氏春秋·本味》之“有侁氏以伊尹媵女”,等等,皆是其例。如果从思想内容来看,则这两个所谓“伊尹学派”实际并无区别:不论“道家之伊尹学派”中,还是“小说家之伊尹学派”,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思想特点,即它们都不一般地谈论“治国”,而是以为“治国必先治身”,由“治身”而通向“治国”——具体来说,是由“具至味”以“治身”(养生),然后由己及人、由近及远,推论治国平天下之道。《吕氏春秋·情欲》曰:“古之治身与治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可见,“治身”与“治国家天下”是相通的,都必须以天地之道为准的。故《吕氏春秋·先己》曰:“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响者不于响于声,善影者不于影于形,为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此后,杨朱学派中的詹何、子华子等人由“治身”(“贵己”、“尊生”和养生)而“治国”的思路,与所谓“伊尹学派”学说正是一脉相承的,而儒家思、孟学派的推己及人之说,亦应多少受其影响。《吕氏春秋》书中既对道家老子、关尹、列子、阳朱、田骈等人的学说有精到的概括,全书又多引道家老子、子华子、庄子、列子、詹何等人之言,足见其对道家之学的重视。但这些地方,虽也涉及“道”的无言无形,但却不是为了论证“道”的虚无恍惚;虽也涉及“德”的无为,但却并不是为了否定仁义礼智。故《吕氏春秋》言“道”之“无形”和“无象”,只是为了阐明君道之“无得”、“无识”与“无事”(《君守》),只是为了论证“至智去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的“君人南面之术”(《任数》)。可以说,《吕氏春秋》对先秦道家的各个学派的学术思想都有接受、扬弃和发展:它对老庄道家的“道德”本体论学说、事物相互对立转化和“达于性命之情”的观点,都有继承和吸收,但扬弃了其中过于虚无和消极的成分,而朝黄老道家或“道法家”(“法道家”)的方向发展了,故与杨朱学派的观点更为接近。故近人顾实等将《吕氏春秋》之《本生》《重己》《贵生》《情欲》《尽数》《先己》诸篇,皆视为杨朱遗说。而在现存先秦诸子著作中,《吕氏春秋》一书中引杨朱学派中詹何、子华子之说,亦为最多。
由此可见,《吕氏春秋》一书所持之“道”,既非阴阳家的天地之道,也非先秦道家各派的“治身”和“治国”之道,而是属于其自身所特有的“兼”采百家而不专主或不滞留于某一家的杂家之“道”——《吕氏春秋》称之为“圜道”。以往学者皆只注意到《吕氏春秋·序意》所谓“法天地”之说,并以之为源于《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以之属黄老道家。实际上,《吕氏春秋》的“圜道”,并不等于道家的“天地自然之道”,二者乃似是而非。《圜道》开篇曰:
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圜也?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
接着,《圜道》又历数了“圜道”的各种表现:“日夜一周”,生物的“萌”、“生”、“长”、“成”、“衰”、“杀”、“藏”,“云气西行”,“水泉东流”,“帝无常处,”人之九竅“一不留处”,圣之法令“瀸于民还周复归”,等等。并且说,以此“圜道”治五音,“音皆调均”;以此治事,“主无不安”;“以此治国,国无不利”。初看起来,《吕氏春秋》的“圜道”似乎只是指“天道”或“自然之道”,即所谓“天道圜”。但进一步考察则会发现,《吕氏春秋》的“圜道”,实际上包含“天、地、人”而言的。它既是《吕氏春秋》所认定的世界运动的总规律,也是其评判世界一切事物的总原则,毫无疑问亦即该书的主导思想。所谓“地道方”,其实是说,若静止地看,地上的方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而如果从“还周复杂”或“还周复归”的角度来看,则万事万物无一不是处于“无所稽留”、循环往复的运动之中。那么,是否世上的事物,特别是人事也表现出“圜道”呢?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引俞樾解“以言不刑蹇,圜道也”曰:“然则‘不刑蹇’者,不踬碍也。盖引黄帝之言而释之曰:‘帝无常处者,以言不踬碍也,是圜道也’。《应同篇》引《商箴》而释之曰:‘以言祸福人或召之也。’文法并同。”可见,在《吕氏春秋》中,世上的方物人事也遵循“圜道”,主要是指其“不踬碍”,“不留处”,用《老子》中的话说,这叫事物的“伏”、“倚”或“复”;用《应同》篇的话说,即是“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简言之,则是事物永不停留的、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存在法则。《老子》曾言“反者,道之动”(第四十章)。又云:“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第十六章)。”所言似乎也是一种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圜道”。但《老子》的这种循环往复的“自然之道”,实际更接近于阴阳家的“阴阳之道”,而《吕氏春秋》的“圜道”,则是与之有别的。其一,《老子》的“反复”之道为纯粹的“自然之道”,人于此地“道”只能俯首听命、一味顺应;而《吕氏春秋》的“圜道”则同时强调了人的主动性,认为人如能积极“为善”“积德”,也可以影响,甚至改变“天道”的运行轨迹。如上文引《制乐》篇中的成汤、周文王、宋景公之例,即是如此。其二,《老子》的自然“反”“复”之道,虽强调一任“自然”,但其实仍是有所“滞留”的——“滞留”于其本身的“柔道”(即所谓“老聃贵柔”),它对儒家的仁义之道就予以了明确的批判与否定;而《吕氏春秋》的“圜道”,则对先秦的诸子百家一视同仁,皆既有吸引、肯定,也有批判与扬弃——用它自己的话说,叫“无所稽留”或“一无留处”。所以,我认为,《吕氏春秋》一书的主导思想和指导原则,既不可能是阴阳家思想,也不可能是道家或黄老道家学说,而只能是坚持“圜道”的杂家思想。
二、“兼儒、墨”——《吕氏春秋》对儒、墨的学术批评
作为杂家的《吕氏春秋》对儒、墨的基本态度,是《汉书·艺文志》所谓“兼儒、墨”。而这里所谓“兼”,在我看来,不仅是如《荀子》所说的“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荣辱》)的兼容并包之术,而且至少包含对儒、墨两个学派同时都既有肯定、吸收,也有批判扬弃,以及对儒、墨进行重新整合,以形成既与原有儒、墨思想密切相关,又与其并不完全相同的新的思想形态两个方面。
就对儒家思想的肯定、吸收和否定、扬弃而言,《吕氏春秋》吸收儒家思想的显例,当属《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诸篇对儒家《乐论》思想的继承。此外,《吕氏春秋》对儒家源于孔子的仁义忠信等观念和思孟学派的“五行”学说及荀子“明分使群”、隆礼重法的思想,也都有明显的继承和发展。《吕氏春秋·去私》以孔子之言称赞祁黄羊为“至公”、《先己》篇由孔子之言发挥出“修身”然后“治天下”之理,《尊师》篇以孔子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而见师道之可尊、《高义》篇以孔子见齐景公不受廪丘之养而称颂孔子“取舍不苟”、“动必缘义,行必诚义”,等等,皆可见其对儒家价值观的肯定与吸收。《劝学》篇又曰:“先王之教,莫荣于孝,莫显于忠。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也。”《孝行览》曰:“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务本莫贵于孝。”这些显然又是对孔子“文、行、忠、信”和孔门弟子“孝弟(悌)也者,其为道之本与”(《论语·学而》)、以及《孝经》所谓“以孝事君则忠”思想的继承。此外,《吕氏春秋·顺民》曰:“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这与孟子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之说,应该具有某种继承关系。《荀子·王制》和《非相》等篇曾说:人之“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因为“人能群,彼不能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则在于人之有“礼义”,“明分”、“能辨”,即所谓“明分使群”。无独有偶,《吕氏春秋·恃君览》亦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汪中《补遗吕氏春秋序》疑《吕氏春秋》一书中《劝学》《尊师》《诬徒》(一作《诋役》)《善学》(一作《用众》)四篇、《大乐》《侈乐》《适音》(一作《和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诸篇,在刘向所得之书中,“亦有诸子同于河者献王者”,为“六艺之遗文也”。
《吕氏春秋》虽然对儒家思想肯定、吸收和赞扬最多,以至于学者多以为该书“大抵以儒家为主”,但实际上它对儒家也是有批评和否定的。如《至公篇》在比较孔子和老子二人评论楚人“遗弓”一事后说:“故老聃则至公矣”。这种“在孔子之外另增加老聃之举,实则是“把老聃置于孔子之上”,是在“以老子来贬抑孔子”;同时也等于批评了孔子的心胸还不够广大,尚未达到真正的“至公”。《吕氏春秋·有度》曾说:“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然无所行,教者术犹不能行,又况于所教?”这里虽是合孔、墨而言,但实际上和《韩非子·五蠹》一样,也主要是针对天下之圣人孔子的,即所谓“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明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韩非子·五蠹》)。不同的是,《韩非子》是在以其“势”论批评孔子“仁义”之说难以实行;而《吕氏春秋》则沿孟子批评告子“仁内义外”的思路,认为“仁义”皆属内在道德实践的德目,而批评孔门后学的以外胜内为“不通性命之情矣”。

当然,正如汪中所指出的,《吕氏春秋》对墨家思想也有批评和扬弃。这主要集中于《振乱》《禁塞》《大乐》等篇对墨家“非攻”“偃兵”“非乐”等观点的批判上。在《墨子》中,《非攻》上、中、下三篇及《公输》《鲁问》《耕柱》诸篇,都有明确的“非攻”思想,从道德的“不义”,给国家和人民生产生活造成的巨大损失,以及对鬼神宗庙造成的破坏等多方面论证了侵略和兼并战争的危害,表达了强烈的“非攻”或反战倾向。《吕氏春秋》则与之针锋相对,其中《荡兵》《振乱》《禁塞》《怀宠》四篇,可以说完全是站在《墨子·非攻》诸篇中“饰战者”的立场上对墨家“非攻”思想的批驳。《吕氏春秋》以上诸篇首先认为,兵战自古即有,“攻战”只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功用,关键在于如何使用,绝不可因噎废食。如果攻战者是“攻无道而伐不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振乱》)相反,倒是墨者所持的“救守”之术,则完全是不辨是非的:“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无道而救不义也”。“救守者”开始也许只是“以说”——欲以言说打动统治者,但在言说不行的情况下,则“必反之兵矣”,走向“非攻”和“偃兵”的反面,同样要借助于兵战。(《禁塞》)所以,《吕氏春秋》说墨家“非攻”“偃兵”的思想,如果以“义”和“理”来进行评判,就会发现它并不合“义理”;而如果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来看,更可以说对它应给予无情的否定:“故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怀宠》)
应该说,《吕氏春秋》和《墨子》对兵战的态度,虽都标榜从“义理”出发,但结论却是完全相反的。其主要原因,乃是因为二者所处的时代和立场不同。墨子既站在小生产者立场上,所处的又是春秋战国之际——周朝虽然已是礼崩乐坏,但周天子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而吕不韦所处的战国末期,时代已提出通过战争实现国家统一的必然要求,吕不韦又以相国之重,“号称仲父”,故他必然会为当时秦国发动的兼并战争进行辩护,而斥山东诸国的“救守”之举为“与义理反”。同样,墨子站在小生产的立场上主张“节用”、“节葬”和“非乐”,吕不韦却完全是从“南面君人”的角度来看待墨家的这些思想主张的。如《墨子》论“厚葬久丧”之弊,有“以厚葬久丧者为政”,此不可求“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和不可“以干上帝鬼神之福”两项,而《吕氏春秋》之《节丧》《安死》等篇则仅言及其奢侈浪费和炫富而使死者不得安身。可见,《吕氏春秋》即使在采用墨家的观点时,对它也作了某些修正。而《吕氏春秋·大乐》《侈乐》《适音》《古乐》“不仅接受了公孙尼子的《乐论》的音乐理论,有时还把它扩张了,在这儿同时还尽了反对墨家的能事”。
当然,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吕氏春秋》对儒、墨两家的批判和继承,更主要的还表现在所谓“兼儒、墨”的一个“兼”字上。这个“兼”字,一是表层的综合,将儒、墨两家合并而论;二是深层的整合,将儒、墨两家的某些核心观点加以融会贯通,创造出一些《吕氏春秋》所独有的、与儒墨二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思想观念。表层的综合,如《吕氏春秋》之《当染》《顺说》《高义》《尊师》《博志》《有度》《下贤》等,或将儒、墨并列,或将孔丘、墨翟并提而称“孔、墨”,即是如此。此时的儒、墨或孔、墨,正如《韩非子·显学》篇中的“世之显学,儒、墨也”,不过是以“儒、墨”并称而指代当时社会的学者或“文学之士”。深层的整合,则可以说是对儒、墨二家思想的批判、继承与发展。如儒、墨都谈“仁”、“义”和“仁义”,《吕氏春秋》则在此基础上有其新的发展。儒家孔子的思想以“仁”著称,即《吕氏春秋·不二》所谓“孔子贵仁”。孔子又曾以“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刚毅木讷近仁”、恭、宽、信、敏、惠等多种品德为“仁”,可见,孔子是把“仁”分成了若干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把人当人看,把人的生命视为万物中最可宝贵者”;第二层次,“是‘克己复礼为仁’”;第三层次,也是“最高的层次,是以上众多品德的集合”——“已超凡脱俗,转识成智,达到了‘圣人’的境界”。孔子也讲“义”,所谓“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同上,《卫灵公》)。“见义不为,无勇也”(同上,《为政》)。“见得思义”(同上,《季氏》)。但孔子并未对“义”有更多的说明,故后人谓“孔子所谓‘义’即道德原则之义……泛指道德的原则”。孔子之后,儒家的孔门七十子及其弟子已开始“仁”“义”对举。相传为子思所作的《中庸》和《表记》《礼运》等篇,即有其例。《中庸》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表记》曰:“仁者天下之表也,义者天下之制也。”《礼运》曰:“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仁者,义之本也。”此后,《孟子》一书遂如朱熹《孟子序说》所云:“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似乎“仁义”已“是当时人的常用辞语”。故有学者推测“以‘仁义’并举,可能始于孔门再传弟子”。
《墨子》是现有文献中最早“将仁义相连并举的”,且《墨子》一书有对“仁”“义”的严密界定。《墨子·经上》:“仁,体爱也”;“义,利也。”《墨子·经说上》曰:“仁,爱己者,非为己用也,不若爱马者,若明”;“义,志以天下为芬(分),而能能利之,不必用。”这里墨家所谓的“仁,体爱也”,主要是指“墨家爱人纯由情出,豪无所为,不若爱马者为其驰也”;所谓的“义,利也”或“义,志以天下为芬(分),而能能利之,不必用”,是说“义”者,有志于天下之内而“能善利之也”。可见,墨家所谓的“仁”,虽与儒家的“仁者爱人”或“仁者人也”有共同之处,但墨家之所谓“仁义”则与儒家明显有别。这种区别主要有二:一是儒家的“仁”,在孔子那里已是区分为若干层次的(见前述),到孟子那里更有“仁与亲与爱的层次”;即使就“仁”皆为“仁爱”之义而言,儒、墨之“仁爱”也是有别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儒家的“仁爱”为等差之爱;而墨者的仁爱乃为“兼爱”。《吕氏春秋·不二》篇所谓“孔子贵仁,墨子贵廉(兼)”,实际是指出了二者在“仁爱”上的不同。二是儒家“仁”“义”(“仁义”)观虽也划分“仁”“义”为二种德目,将二者视为人之内心的固有性情,而其实更重视“仁”。与之不同,墨家的“仁义”既明确主张“仁”为人之内心所自出,而“义”为人所做出的“利他”之举,故有明确的“仁内义外”之意;另一方面,由于墨子学说重实用功利的出发点,故不论墨子所主张的“仁”还是“义”,都是以“利”为宗旨的。《墨子·非命》上、中、下三篇皆提出了对事物的价值评判的所谓“三表法”——“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人民之利”。(《非命》上,《非命》中、下“三表”顺序有时倒置)即凸显了一个“利”字。《墨子》中论“兼爱”“非攻”“非乐”“节用”“节葬”,其出发点和归宿也无不在这个“利”字上。《兼爱》中曰:“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可见,一切行为主张的出发点,确在一个“利”字,所谓“兼相爱”,其实也就是“交相利”。故墨家之“仁义”,实际也就是所谓的“爱”和“利”,而其落脚点既在一个“义”字上,亦在一个“利”字上。
《吕氏春秋》既以孔、墨或儒、墨对举,对儒、墨两家进行了外在形式上的初步整合,接下来必然要从思想观念上对二者做出更深层的整合,提出一种与儒、墨原有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新思想。《吕氏春秋》中的“仁”“义”或“仁义”观,可以说就是对先秦儒、墨两家既有思想观念批评、继承和扬弃的产物。《吕氏春秋·论威》曰:“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即以“仁义”为治国之首术,与儒、墨的“仁治”观点已十分相近。同书《爱类》论“仁”曰:“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吕氏春秋·爱士》记赵简子杀爱骡而救阳城胥渠之事曰:“夫杀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杀畜以活人,不亦仁乎?”其所赞扬的赵简子之“仁”,显然即是其“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仁爱观的具体化,与儒家“仁者爱人”或“仁者人也”同调,而源于孔子的“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的思路,合于孟子所谓“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之义。(《孟子·尽心上》)《吕氏春秋·论威》又论“义”曰:
义也者,万事之纪也,君臣上下之所由起也,治乱安危过胜之所在也。
《吕氏春秋·论威》此处论“义”,将义与君臣上下亲疏联系起来,显然与上引儒家思孟所谓“义者宜也”、“敬长义也”之说相近,“都肯定了人与人的差别”。但这并非《吕氏春秋》“仁”“义”或“仁义”之说的全部,故《爱类》篇接着又说:“故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所为皆“所以见致民利也”,“其于利民一也”。这也就是说,在《吕氏春秋》中,所谓“仁”“义”或“仁义”,其实都是“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的“爱利”。“仁”是这样,“义”是这样,“仁义”亦是这样。故《爱类》篇记赵简子“夫杀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杀畜以活人,不亦仁乎”之言后,同时又说:“救之义也”。即把“仁爱”当作利民的“义举”。而《无义》篇则修正《论威》篇对“义”的定义说:“故义者,百事之始也,万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也把“义”由儒家的肯定“人与人的差别”向墨家的“义,利也”的方向进行了反拨。故《高义》篇曰:“君子之自行也,动必缘义,行必诚义”。《用民》篇曰:“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应同》《召类》二篇皆曰:“凡兵之用也,用于利,用于义。”实际上,可以说《吕氏春秋》的“仁”“义”或“仁义”观念,既是儒家和墨家的,又不是儒家或墨家的,而是属于自己所独有的。它对儒、墨两家的“仁”、“义”或“仁义”观都有所吸收和继承,又作了双向的扬弃,进行了深层的整合。它在儒家“由然而至”的“仁爱”本心中加进了功利的内容,又在墨家纯功利的“义”中注入了“尊贤”、“敬长”等肯定人与人的差别的内涵。这就使《吕氏春秋》的“仁义”观,变成了一种以“利”为基础,而又是本之于本然之爱的、可以量化评价的范畴。
三、“合名、法”——《吕氏春秋》对名家和法家的批评
《吕氏春秋》的“合名、法”,就是对先秦名家学说和法家学说进行的批判性整合。
名家,即名辩家,先秦诸子著作多称“辩者”,亦称“察士”。《汉书·艺文志》曰:“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謷者为之,则苟钩鈲析乱而已。”《汉书·艺文志》的这段话,既说明了名家的源流,也说明了名家的特点。——用孔子的话说,叫做“正名”,但在“謷者”那里,则是“苟钩鈲析乱而已”。此亦即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所说的:“名家苛察缴绕”。因为孔子的“正名”,是“有政治意义”的,而孔子又是主张“为邦以礼”(《论语·子路》)的,所以《汉书·艺文志》就把“礼官”当作名家的源头,并且说,“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似乎名家是专门考究“名位”与“礼数”关系的,而那些“苛察缴绕”或“苟钩鈲析乱而已”的所谓“謷者”,倒似乎应该被赶出“名家”之列。但这只是班固的一面之词。实际上,先秦时期的那些著名的名家人物,如公孙龙、兒说、田巴、桓团,乃至惠施之类,个个都是在抽象的名实关系上“苛察缴绕”的,如果将这一帮人赶出名家之列,也就可能真如有些学者所论,先秦的确是没有所谓名家了。
法家,先秦时多称为“法术之士”,汉代始有法家之名。《汉书·艺文志》曰:“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这段话,一是说明了法家出于“理官”,二是说法家“信赏必罚”,严格执法,亦即有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所谓“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之义。
《吕氏春秋》对名家学说肯定和继承的,主要是名家对“名辩”的重视及由此而形成的名实相符、形名耦合的“正名”思想。先秦名家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邓析》二篇”、“《惠子》一篇”、“《尹文子》一篇”、“《公孙龙子》十四篇”等多种,但由于邓析其人之时代既早于孔、老诸子,其时诸子“九流十家”尚未形成,故前人皆曰:“邓析只以教人讼为事,盖古代一有名讼师也”,并不是真正的“辩者”,更非所谓“名家”。而传世《邓析》竟“误以‘无厚’为无恩泽也,”其“伪迹故显然易见”。《尹文子》一书,今存本分为《大道上》《大道下》二篇,其《大道上》云:“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故名以检(或作“验”)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或作“验”)名。”诚为名家之说。但因其中所论“多法家口吻”,故学者仅以今本《公孙龙子》六篇为先秦残存,而认为《尹文子》同《邓析》一样,“是伪书”。所以,今天考察名家的思想特点,最可信据的,自然是《公孙龙子》残存六篇了。
在《公孙龙子》残存六篇中,尽管涉及“白马非马”“指不至,至不绝”“坚白离”“二无一”等众多命题,但其探讨的中心问题,实不出“名实论”之囿,而其目的仍在“正其名也”。《公孙龙子·名实论》曰:“天地与其所产者,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不旷焉,位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原无“此”字,依俞樾说补)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吕氏春秋》曰:“正名审分,是治之辔也。”(《审分览》)又曰:“凡君子之说也,足以言贤者之实,不肖者之充而已矣,足以喻治之所悖、乱之所由起而已,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获以生而已矣。”(《正名》)“名正则治,名丧则乱”,“凡乱者,刑名不当也”。治国“能以其出为之入,以其言为之名,取其实以责其名,则说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执其要矣。”(《审应览》)而《应言篇》称惠子之“言无所用者为美也”,则显然有为名家辩护之意。这些都与名家一样,强调了“名言”或“名辩”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既是对名家思想的肯定,也是对名家思想的继承。不仅如此,当时学术界对有关名言与形物复杂关系的思维活动也已有相当深入的认识,如《易·系辞上》曰“言不尽意”、《庄子》说“语所贵者,意也”(《天道》);“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墨子》讲“循致闻而得其意,心之察也”;“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辨也。”(《经上》)“以名举实,以辞抒意。”(《小取》)《荀子》更进一步说:“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确定了名实与辞意的关系。故《吕氏春秋》讨论名实关系,并不如惠施、公孙龙等人那样只是局限于形名的耦合,而是注意到在事物概念(名)的形成过程中,有人的主观活动参与其间,即有一个“辞(词)与意的关系问题”。故曰:“言者,谓之属也”;(《精谕》)“言者,以谕意也”;“夫辞者,意之表也,鉴其表而弃其意,悖。”(《离谓》)而竟有道家“至言去言”、“得其意则舍其言矣”(《精谕》)《离谓》)之趣。
当然,尽管《吕氏春秋》对惠施、公孙龙“正名”的思想观点,持肯定和继承的态度,但其“正名”思想的直接来源却并非惠施和公孙龙等人,而应该是稷下学派中的宋钘、尹文等人。《庄子·天下篇》叙宋钘、尹文之学曰:“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又说:“接万物以别宥为始”云云。《汉书·艺文志》以“《尹文子》一篇”入名家,以“《宋子》十八篇”入小说家。可见,二人学术之“杂”。《尹文子·大道上》曰:“名者,正形者也。形由名正,则名不可差。……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这说明宋、尹的名家思想重在“由名正形”的“正名”,而其起点则在“别宥”。故《吕氏春秋》在《正名》之前则有《去宥》一篇,曰:“凡人必别宥然后知,别宥则能全其天矣”。《吕氏春秋·正名》虽与《荀子》中之《正名》篇名相同,却并不如《荀子·正名》那样热衷于讨论“制名”的原由、方法和意义,也并不如《荀子·正名》那样对宋钘等人的“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等名辩论题予以严正的批驳,而是在批评“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等“淫说”的同时,为“东方之辩士”尹文等辩护,称其与齐湣王之论为“见刑名异充而声实异谓也”,以至于后世学者认为此篇与《去宥》“正是一组”,两篇“盖即料子、宋钘、尹文等流派之说也”,或“即尹文后学之作也”。
《吕氏春秋》对名家的批评,主要针对其“妄言”和诡辩。如田诎对魏昭王的所谓“为圣易”(《审应》)、赵惠王问公孙龙的所谓“兵不可偃乎”之说(同上)的批评等。故《吕氏春秋》之《离谓》《淫辞》诸篇,明确地将“辩者”的所谓辩说斥为“淫辞”或“桥言”。而《吕氏春秋》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名家学者(辩者)过于注重于名实之辨或辨名析理,恰恰因为所谓“坚白之察,无厚之辩外矣”(《君守》),亦即《吕氏春秋·正名》所说的“形名不当”,或《离谓》《淫辞》等篇所说的“言意相离”或“言心相离”。因为名言、论辩、辩说的目的,都不是为名辩而名辩,做某种无意义的概念游戏,而是为了“明理”,为了“谕意”,或“谕心”也。故《吕氏春秋》诸篇又正面论“名”“辩”“议”“说”曰:“名固不可不相分,必由其理”(《功名》);“凡君子之说也,非苟辩也,士之议也,非苟语也,必中理然后说,必当义然后议”《尊师》);“所贵于辩者,为其由所论也”(《当务》);并从反面阐明了名、言、辩、论“不当”的危害:“辩而不当论,大乱天下者也”(《当务》);“凡乱者,刑名不当也”(《正名》);“言意相离,凶也。乱国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顾其实,务以相毁,务以相誉,毁誉成党,众口熏天,贤不肖不分,以此治国,贤主犹惑之也,又况乎不肖者乎……此所以欲治而愈乱也”(《离谓》);“言心相离,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淫辞》)。正是基于这些理由,《吕氏春秋》一书对“形名不当”“言意相离”或“言心相离”的“淫辞”诡辩,是予以坚决的批评和反对的。
对于先秦的法家思想,《吕氏春秋》肯定和继承的主要是其与黄老道家或“道法家”(“法道家”)相关的思想。
《汉书·艺文志》把法家的源头上溯于“理官”,其著录的法家著作,则以“《李子》三十二篇”(班固自注:“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为始。但根据我的研究,先秦法家实应以吴起为开祖,只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的“法家类”并未著录吴起的著作,吴起的著作《汉志·兵书略》中的“兵权谋”类有“《吴起》四十八篇”,可惜已经亡佚了。自《宋史·艺文志》起,则有“《吴子》三卷”。学者认为此书“辞意淫浅,殆非原书”。先秦法家著作保存基本完整的,是《汉书·艺文志》中的《商君书》和《韩非子》,其次则是《慎子》和《申子》,各有部分遗存。近代学者蒙文通曾合有关文献而考察先秦法家之流变,认为先秦法家之义尽于法、术、势三者,“(知)法者商子之所立,而慎子承之,又益之以言势;势者慎子之所立,而申子承之,又益之以言术;韩非则直承之而已。其《韩非子》书言术者大半,于法与势亦略言之。”先秦法家思想的演变,自慎到、申不害为之一变,大略为“商君言法”,而慎到、申不害“遂合于黄老之义”而言势、言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到,赵人……学黄老道德之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又说:“申子(不害)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本归于黄老”。这正指出了诸人法家思想“因道全法”,偏于术、势的历史特点。在《吕氏春秋》中对法家的法、术、势思想的态度基本与《韩非子》相近,最重论“术”,其次是论“势”,于“法”则偶一论及而已。从《吕氏春秋》论“法”的言论来看,它对法的重要性和严格执法的行为是基本肯定的。所谓“家无怒笞,则竖子婴儿之有过也立见;国无刑罚,则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见……故怒笞不可偃于家,刑罚不可偃于国。”(《荡兵》)“先王之法曰:‘为善者赏,为不善者罚,古之道也,不可易。’”(《禁塞》)即可为例。而且,《吕氏春秋》对法家“信赏必罚”,“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思想观点也是认同的。《吕氏春秋·贵信》说:“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同书《直谏》载葆申以楚文王荒淫废政而坚决对其执行笞刑,则是肯认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之例;而《贵卒》又赞扬吴起遇害前“伏王尸”而使加害者“尽加重罪,逮三族”,以为其反应敏捷,实际也是对吴起废绝“礼治”、推行法治之“变法”内容的肯定。但《吕氏春秋》并不是无条件地赞成使用刑罚等法制手段治国,也不把赏罚当成圣人治国的最高境界,而是明确反对严刑峻法。《用民》篇说:“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又说:“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威太甚则爱利之心息,爱利之心息而徒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绝也。”明确赞成儒、墨的“爱利”而反对法家的严威。《吕氏春秋》对包括吴起、申不害等法家人物的言行多有记载,且多以正面和肯定之笔出之,但对以“言法”著称的商鞅之言行的记述则仅有两例,且一例以“无义”斥之(《无义》)。由此可见,《吕氏春秋》对完全与儒、墨之“仁义”、“爱利”绝缘的“徒法”,是何其的厌恶和反感啊!
对于先秦法家的“势论”和“术论”,《吕氏春秋》则有更多的肯定与继承。《吕氏春秋》对先秦法家“术”论和“势”论的肯定和继承,主要是通过对此前慎到、申不害观点的吸收和转述来实现的。《韩非子·定法》篇曾说:“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又著《难势》一篇以申述慎到的“势”论。然《荀子·解蔽》则曰:“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智)”班固《汉书·艺文志》将申不害、慎到皆著于法家,且于“《慎子》四十二篇”之后自注:“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可知,申不害既言“术”,亦言“势”,而此二者“均取则于慎子也”。根据蒙文通的研究,慎到之学既重“术”,又重“势”,但从哲学思想的层面来讲,实可以“因循”二字概括之——“因循固慎子思想之核心”。《庄子·天下篇》言慎到之学,“皆因物循理之说也”;“《管子·心术》《内业》,义合于慎到,实……有取于慎子”,遂“合因循、虚无为一说”,而成其“静因之道”也。在《吕氏春秋》中有《贵因》一篇,其辞有曰:“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又曰:“夫审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时,因也。……故因则有功,专则拙。因者无敌。”蒙文通以《御览》七百六十八引《慎子》“行海者坐而至越”云云,与《吕氏春秋·贵因》中“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一段文辞相类似,故而认为“即此《贵因》之文,即本之慎到。”并进而认为,《吕氏春秋·贵因》之次篇《察今》及之前二篇《顺说》《不广》,“并皆论因”,“似亦取之《慎子》”,或“似亦慎子一派之说”。故包括《吕氏春秋·审分览》之《任数》《知度》《慎势》诸篇,“皆依慎子之义,合因循、虚无为一说,固精于《贵因》者也。”
但如果从政治学说的角度来看,《吕氏春秋》所继承和肯定的,似主要是慎到的重“势”思想和申不害将法家与名家结合而提出的“督名审实”、“循名责实”的观点。《吕氏春秋》的《慎势》一篇,上文说蒙文通从“因循”的角度,说明该篇乃“依慎子之义”的作品;而郭沫若则因为《慎势》“开首就说:‘失之乎数,求之乎信,则疑矣。失之乎势,求之乎国,危。’前一句与《韩非子·难二》引申子的话相同”,故推断“下一句也应该是申子的话”,并“疑心这《慎势》一篇,整个是申子的文章”;即以此篇同《任数》一样,都是要让君主任术数而“不讲信义”的。但我认为,《吕氏春秋》中这篇《慎势》论述的中心,仍是在一“势”字上,其开首前一句“失之乎数,求之乎信,疑”和后一句“失之乎势,求之乎国,危”,从文法学上讲是“对文”,应该是互文见义的,重点都在说明“势”之不可“失”。故其下文接着说:“吞舟之鱼,陆处则不胜蝼蚁。权钧则不能相使,势等则不能相并,治乱齐则不能相正”云云。这与《韩非子·难势》引“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蛇同矣,失去乘也”同义。故《慎势》全文的核心观点和结论是:“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奸止,此畜人之道也。”强调的正是“势”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上文所讲的慎到的“因循”、《吕氏春秋》此处所讲的“威势”,实际上都属于法家“术”论的范围,都是法家所讲的君主驭臣的“治国之术”。“因循”是一种“术”,“乘势”是一种术,“循名责实”或“督名审实”也是一种“术”。故《吕氏春秋》的同一篇《慎势》,蒙文通以之为“本之慎到”,所述为“因循之义”;而郭沫若则认为这一篇“整个是申子的文章”,是在“言术”;而申不害则以黄老道家的“清静无为”之说为理论根据,将慎到的“因循”、“乘势”的“势”论和名家“循名责实”的“正名”理论结合起来,形成其“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的“君人南面之术”。但《吕氏春秋》继承申子此论时,却对之有所发展,即它将申子的“正名”或“督名审实”,当成了人主治天下的第一要务。如《吕氏春秋·审分览》曰:“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辔。其辔何如?正名审分,是治之辔已。故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美,无使放悖。夫名多不当其实,而事多不当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审名分也。”《审应览》曰:“凡主有识,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随,以其出为之入,以其言为之名。取其实以责名,则说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执其要矣。”《知度篇》曰:“故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官使自司,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实。”《分职》篇曰:“夫君也者,处虚素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等等。
由此可见,《吕氏春秋》比申子之“言术”更多,也更注重“术”。这既是一种言“术”、言“法”与“势”,也是一种“合名、法”。从此,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名、法两家几乎不可分离了。说到法家,你必须联系到其使用的名家的“审核名实”或“循名责实”之“术”;说到名家,你也不能不提到“循名责实”在君主治国驭臣时的运用,而“刑名家”或“名法家”之称亦由此而生也。
四、《吕氏春秋》对从农家、纵横家、小说家的学术批评
先看农家。
《汉书·艺文志》叙农家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章太炎已指出,“农家诸书”,并不如贾思勰之《齐民要术》或王桢之《农书》,仅叙农业生产技术,几如方技,“与医经经方同列”。因为诸子百家皆“务为治者也”,故农家之学当同时兼后来之所谓农业技术和由“上(尚)农”而发生出的治国之道二者。《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学者向来皆以为是先秦农家的作品。但比较《汉书·艺文志》所载农家著作就会发现,先秦农家原本是分为“神农之教”和“后稷之教”两派的。二者虽都“重农”,但“神农之教”侧重于从理论上说明“上农”的必要性,极端者竟如“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之类,“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而食”;而“后稷之教”则更多地侧重于农业技术方面,而形成如《汉志》中的《汜胜之书》这类“农书”。《吕氏春秋》对先秦农家的批评继承,一是表现为对先秦农家侧于“神农之教”和侧重于“后稷之教”两派的综合;二是表现为它似乎对农家思想中“后稷之教”更为偏重,为我国大量保存了先秦有关农业生产技术的内容——这与《墨子》一书大量保存先秦自然科学的成果意义同样重大;三是它虽然也赞同农家的“上农”,但其出发点和指导思想却不是农家的“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而是法家的“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议,少私议则公法立,力专一”(《上农》)。因此,它虽不如孟子和韩非子那样强烈地反对“君臣并耕而食”,但却认为“同异之分”,“贵贱之别,长少之义,此先王所慎,而治乱之纪也。”(《处方》)故所谓“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上农》),亦只能被理解在礼仪的范围之内。从《汉书·艺文志》来看,《汉志》著录的先秦农家著作,确定无疑的实只有两种:“《神农》二十九篇”(班固自注:“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农耕事,托之神农。”)、“《野老》十七篇”(班固自注:“六国时,在齐楚间”。)另有“《宰氏》十七篇”,尽管后人(如叶德辉等),以宰氏为陶朱公范蠡之师计然,但并无确证。而从《汉志》所录之寥寥数种可确定的先秦农家著作来看,其内容也只是“托之神农,道农耕事”而已,很难说有什么具体的耕种技术和方法。直到汉代的“《汜胜之书》十八篇”之类,才真正是“著书言播种树艺之法”。因此可以说,《吕氏春秋》一方面继承了“神农之教”之“上农”的思想,认为“古先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更多的则是《汉志》中所没有的先秦农家“后稷之教”——即有关具体农业耕作技术的内容。《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既反复引“后稷曰”,篇中又详述各种依据土地、季节进行耕作的技术,故后代学者研究认为:“《吕氏春秋》的《上农》四篇,大致取材于后稷农书。《任地》一开始,就用‘后稷曰’的口气提出十项问题,以下则是解答。但是《任地》一篇并没有解答明白,而是在《辨土》《审时》两篇中作了补充和申论,才算解答完成。由此可见,《任地》《辨土》《审时》三篇,都是后稷农书上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吕氏春秋》的《上农》等四篇大致都是取材于后稷农书的。不过,在《吕》书的编辑中有所割裂和增减而已。”
《吕氏春秋》这种对先秦农家思想内容的取舍,一方面固然是当时的思想时代背景所致——秦王朝政治和思想文化的专制和独尊已基本形成,不可能再允许大肆鼓吹那种“君臣并耕而食”的思想主张(看看《韩非子》中的相关内容即可推知);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由于《吕氏春秋》的编撰者们对先秦农家中夸夸其谈所谓因“上农”而“君臣并耕而食”的主张失去了兴趣,故而基本不摄取这方面的内容,而只叙述其中关于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后稷之教”。从此以后,中国目录中所著录的农家著作,亦基本只是前朝的“农书”,而不见先秦农家宣扬自己政治哲学的著作。
其次,再看纵横家。
纵横之义,《韩非子·五蠹》曰:“从(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因为战国中后期秦国最为强大,已有吞并六国、统一天下之势,故此时所谓的“纵横”,已变得非常具体:六国南北联合以西向抗秦,谓之“合纵”(即“纵”);秦国联合六国中之一部分而对六国各个击破,则谓之“连横”(即“横”)。应该说,纵横家都是当时的一些外交家或政客,本没有多少学术思想,而只有一些政治主张或策略。
《吕氏春秋》的编撰者们所处的位置与时代,是强秦统一中国的前夜,吕不韦更是秦国攻伐六国、统一天下政策的参与制定者,故他们对纵横家思想的取舍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吕氏春秋》一书中并未见直接对纵横家的评论,而且其中有关纵横家的事迹也十分稀少。但就是在这些极为稀少的材料中,仍可见其对纵横家态度的蛛丝马迹。在上文论《吕氏春秋》对墨家“非攻”之说的批评时我们曾说,《吕氏春秋·孟秋纪》之《荡兵》《振乱》《禁塞》《怀宠》诸篇,对墨家所谓“非攻”“偃兵”之说及救助弱小国家的“救守之心”,实际上都是否定的。《吕氏春秋》说:“古圣王有义兵而无偃兵”(《荡兵》),“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无道而救不义也。”(《禁塞》)即是其例。而如果从总是强大的一方取“攻伐”态势,而弱小的一方取“救守”态势的角度来看,《吕氏春秋》对“攻伐”和“救守”的态度,实际也可以看成是其对“纵横家”的态度。它对秦国“攻伐”弱小诸侯国的行为是极力辩护、强调其合理性的;而对众弱小国互相救助而反击秦国的行为,则完全取一种反对和批判的态度。但这种评价又不是一种“同情弱者”的态度,而是以“道”、“义”和“利”、“害”为价值尺度进行评判的。故《振乱》曰:“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不义也。攻无道伐不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禁塞》曰:“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亦不可。……故大乱天下者,在于不取义而疾取救守。”
在《吕氏春秋》一书中,偶尔也有关于纵横家言行的记录。如《吕氏春秋·不侵》记“孟尝君为(纵)”,但遭到公孙弘的劝阻,曰:“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为臣,何暇从(纵)而难之。”《报更》篇更明称赞主张“连横”的纵横家张仪对东周小国以德相报,使其名誉大盛,曰:“逢泽之会,魏王尝为(东周昭文君)御,韩王为(东周昭文君)右,名号至今不忘,此张仪之力也。”所显示出的张仪有情有义,与《战国策》及《史记·张仪列传》等书中欺诈无信的形象,几有天壤之别。而这无疑也显示出了《吕氏春秋》编撰者们对纵横家的评判,与当时哪怕属于秦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法家,都是并不相同的。《吕氏春秋》明显有偏向于“连横”一派的倾向,而法家则是对“合纵”、“连横”二派一概予以反对和否定的。《韩非子·五蠹》曰:“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国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国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又说:“人臣之言从(纵)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而亡地败军矣。”可见,法家对纵横家的态度与《吕氏春秋》是完全不同的。
再次,来看看小说家。
即使对于先秦诸子“九流”之外的“小说家”,《吕氏春秋》也是有所批评和继承的。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先秦“小说家”著作,有“《伊尹说》二十七篇”、“《鬻子说》十九篇”、“《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务成子》十一篇”、“《宋子》十八篇”、“《天乙》三篇”、“《黄帝说》四十篇”等。但因诸书皆早亡佚,后人因无以论《吕氏春秋》吸收、改造及评判先秦“小说家”的情况。但《吕氏春秋·孝行览·本味》一篇记汤与伊尹甚详,历代学者多以为此篇当即《汉书·艺文志》所载“《伊尹说》二十七篇”中之一篇,《孟子》书中所谓“伊尹以割烹要汤”亦属此篇。在上文我们讨论《吕氏春秋》与先秦道家的关系时曾经指出,《吕氏春秋》之所以引述“小说家”《伊尹说》的内容,乃是因为伊尹学说与《吕氏春秋》所推崇的杨朱学派以“为身”与“为国”、“治身”与“治世”一致的学说相契合,杨朱之学当源于上古伊尹之学的缘故。而如果从《吕氏春秋》对“小说家”思想的批判继承关系来看,则《吕氏春秋·本味》对“小说家”著作《伊尹说》的大篇幅详细的转述和编入,也正反映了《吕氏春秋》对作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的“小说家”的重视,即它并不以之为“刍荛狂夫之说”而视为“德之弃也”,而是以为“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汉书·艺文志》)。可见,它对“小说”这一民间的“文学”形式也是十分欣赏,并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和吸收的。《吕氏春秋》一书各篇中,差不多都记载有一些为史书或其他传世文献所没有(或传闻异辞)的传说故事,这些也说明《吕氏春秋》对“小说家”的态度是一贯的,即采取一种尽量继承和摄取的态度。当然,《吕氏春秋》对“小说家”之“小说”的这种继承和摄取,也是有自己的原则和选择的,即《察传》篇所谓“凡闻言必熟论,其于人必验之以理”。也就是说,它认为“小说”不必求事实的“真实”,但必须要求“合理”,必须合乎事物发展的逻辑,合乎人类思维的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关于“小说”真实观的最早论述。
以上是我们就《吕氏春秋》一书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批评所作的梳理。由此不难看出,《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九流十家”的思想,实际上都是既有继承和吸收,也有批评和扬弃的。《吕氏春秋》虽“循阴阳之大顺”,但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以阴阳家思想为指导;《吕氏春秋》虽要“法天地”,主张“无为而治”的君人南面之术,但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可归入道家或黄老道家。它实际上是主张“天圆地方”——包括先秦诸子百家在内的万事万物,既是“皆有分职,不能相为”,又是“还周复始”、“一不欲留”(《圜道》)的。此之谓“圜道”。它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也是此“圜道”。故《吕氏春秋》对诸子百家的思想,虽也主张“假人之长以补其短”的“用众”,但并不主张人为地“取长补短”,而是更重视“时”、“遇”(《首时》《遇合》)。因此,它不属于儒、墨、道、法、阴阳中的任何一家,而只属于“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