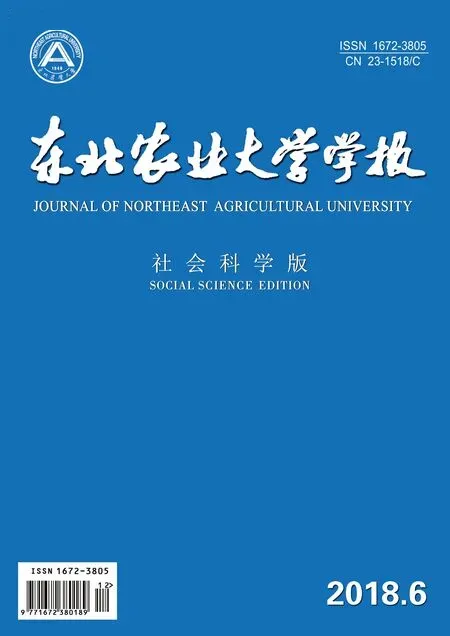严歌苓新移民小说的跨域书写
杨 帆杨亚丽
(1.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2.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作为“新移民文学”的代表,当严歌苓在20世纪90年代辞别故国,踏上大洋彼岸。她并未沉溺于思乡和寻根情愁的书写,而是以平和心态和敏感笔触,在坚守民族尊严同时,刻画了无数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以独特叙事方式,传达对东西文化差异的感叹。新奇而异质的文化,使其感受到自己被连根拔起后栽种到一片完全陌生又新鲜的土壤。“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是裸露着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地敏感。”[1]严歌苓自称“游牧民族”,因无论从地域空间还是心灵归属感,其既游离于故国家园,也有别于寄居国文化。正是这种边缘处境,使其在异域风情中不断地更新和演化,从东西迥异文化中汲取营养,从人性广阔的空间审视不同族群文化。经历文化跨越的严歌苓,从“留学”到“学留”,再到跨国婚姻,更加关注移民这一特殊群体,“移民,这是个最脆弱,敏感的生命形式,它能对残酷的环境做出最逼真的反应。”[2]为在异域他乡留下来、活下去,有些移民放弃对故国文化的坚守,选择退让和改变。严歌苓对此并未苛责,而是给予宽容和理解。赴美前,严歌苓已发表多部文学作品。1989年,初到美国的严歌苓不仅遭遇生活困境,更受到文化差异的巨大冲击,经历了抽丝剥茧般阵痛,使其能跨越东西文化差异,冷静平和地审视移民的生活和跨越,其移民书写跨越了艰难生活的物质层面,将敏感笔触延伸到人的心灵世界。
西方文明起源于海洋文化,海洋赋予了西方人自由豪放、探险好胜的性格;东方文明起源于农业文化,土地造就了东方人谦逊温和、固守家园的寻根情怀。跨越东西文化差异的严歌苓,在全球化视域下用自我真实生命感触书写文化差异与融合。她极力寻求多元文化的平等沟通,无种族、政治和文化因素掺杂其中,因“文化只有在多元的状态下才能显示出它的魅力和意义。”
同许多移民作家一样,严歌苓“在漂泊过程中变得更加优秀”,“这是移民生活给他们视角和思考的决定性的拓展与深化。”[3]移民面对中西文化的巨大反差,固有文化体验和思维定式在严歌苓笔端被无情解构,她以多元思维方式,让作品中移民选择面对异域文化不同应答方式,通过多元选择,传达自身面对两种价值观念和文化思想的独立态度。
一、对屈从强势文化、原乡情怀失守者的理解和宽容
1882年,美国颁布《排华法案》,是美国第一步针对特定族群的移民法,在种族歧视背景下,华裔移民境况可想而知,他们不仅要应对生活困难,还要遭受文化歧视,不得不屈从于“西方文化中心”的强势文化,原有故乡情怀被无情击垮和解构。
远离故土、飘洋过海寄居他乡的移民,“像任何一个白手起家的移民一样,他们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但不是抽象的,精英式的忧患意识。普通移民的忧患意识是难民式的,那就是:呆下来,活下去。虽然不免有些原始,但它在最大程度上激活了人的生命力。”[4]他们深切感受着与另一种文化、另一个种族磨合的痛苦。
小说《方月饼》中主人公是华裔留学生,只因随手翻阅美国室友的报纸,就被要求分担订报费用,抱了室友的猫,就被要求支付体检费,欣赏室友的鲜花,又被要求分担买花的钱。西方文化强调平等自由,东方文化强调亲情友爱,在两种文化冲撞下,“我”不得不屈从和接受西方强势文化,如在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我”想买象征团圆的月饼与同乡聚会赏月,共寄乡愁,而同乡却因各种理由无法与“我”共度中秋,“我”买不到象征团圆的圆月饼,只能以方月饼替代,邀美国室友一起过节。而室友对“我”讲的月亮、月饼故事和传说毫无兴趣,只顾吃月饼并担心月饼的卡路里,吃完即离开,留下“我”一人孤独地对着月亮。面对强势文化,“我”无法固守原乡情怀,只能像被改变了形状的月饼一样,接受故国情怀被无情地解构。
《大陆妹》中,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大陆妹”,寄居在从中国台湾移居美国的亲戚家中,负责照顾一家人生活起居,亲戚虽接纳她,但始终与其保持一定距离,在亲戚眼中,大陆肮脏、落后、土气,他们怀疑大陆妹把虱子传染给孩子,排斥她的生活习惯,她吃饭的碗筷与他人不同。尽管文化情怀难以割舍,但为融入美国社会环境,或融入其寄居家庭,大陆妹努力改变生活和处事方式,不得不模仿台湾亲属的口音,把“吃饭”说成“呲饭”,把“垃圾”说成“勒色”,把辫子披散开,不再哼唱带有“土腥味”的大陆歌曲。唐太太说干烧鱼是大陆做法,大陆妹尽管心里不认可,却点头表示赞同。当小娜拉把故乡说成香菇,大陆妹也凑趣地跟着其他人一起笑。在异质土地上,为融入环境,无奈屈从、主动放弃原乡文化,大陆妹在此过程中迷失了自我。
在小说《红罗裙》中,海云在丈夫去世后,为让儿子有好的学习环境和前途,奔赴美国。而她却因身无长技,不得已嫁给七十多岁的周先生。周先生年老多病,海云照顾其生活起居,在和丈夫的有限交流中,丈夫还可选择摘或戴上助听器听或不听她讲话。这是华人女性在异域土地上为求生存,以个人婚姻为代价,向强势文化的妥协和屈从。
小说《约会》中的五娟,在美国的家中不仅无地位,甚至无自由,她和儿子生活在美国丈夫的密切监视之下,丈夫甚至阻止她与儿子见面。在这种畸形生活境遇中,五娟难以割舍对儿子的依恋,她对儿子的痴迷和爱恋仿佛女人对理想男性的爱恋,她甚至希望儿子可以取代丈夫,她对儿子撒娇,让儿子帮忙试衣服,倍加珍惜每一次与儿子见面的机会。虽然“他们从没做过任何亵渎母子之情的事。他们只是将母子最初期的关系——相依为命的关系延长了,或许是不恰当、无限期地延长了,或许是异域的陌生和异族的冷漠延长了它。因此他们总是在对于陌生和冷漠的轻微恐慌中贪恋彼此身上由血缘而生出的亲切。”[5]生活在美国边缘文化中的五娟,为在美国立足,不得不屈辱地过着寄生生活,在婚姻关系中完全失去自我,对儿子的依恋亦似乎有悖于伦理,委曲求全的屈辱生活扭曲了这些移民的正常心理。
处在文化和性别双重边缘的女性新移民,在强势文化面前选择隐忍妥协,而在异质土地生存的华裔男性,一样充满艰辛和痛苦。
《阿曼达》中的杨志斌出国后产生巨大心理落差,他在国内是学校的风云人物,是女性心目中的理想伴侣。但当以陪读身份随妻子赴美后,不仅在生活上依赖妻子,也无法融入主流社会,只能沦为夜间保安,巨大落差使其孤独苦闷,认为自身失去存在意义,而少女阿曼达带给他被需要的慰籍。当杨志斌以诱奸罪被送上法庭,为在美国留下来、活下去,他只能以“非正式存在”方式,在一家华人超市打工,抹去以往的生存痕迹。在移居国度,杨志斌不仅失去原乡文化,连性别身份也被隐匿。
《魔旦》中阿玫是粤剧中花旦角色,他杨柳细腰、柳叶眉、樱桃口,作为“金山第一旦”,吸引了无数西方戏迷,他们痴迷的并非中国戏剧中男扮女装的艺术,而是阿玫在舞台上妩媚动人的形象满足了他们对古老东方世界的猎奇心,并激发其强势民族的优越感。同性恋者奥古斯曼对阿玫展开强烈追求,阿玫虽无同性恋倾向,却接受并迎合奥古斯曼以摆脱戏子命运,借助奥古斯曼资助,阿玫在会计学校毕业,之后他杀死了奥古斯曼,混入穿西装打领带的人群中。阿玫似乎融入了强势文化,但以屈从妥协为代价,这是男性移民在强势文化中的无奈选择。
为在异域他乡留下来、活下去,有些移民放弃坚守故国文化,选择退让和改变,同样经历文化跨越的严歌苓并未加以苛责而是给予理解。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严歌苓笔下这些移民形象依然鲜活生动,他们的生活依然充满生机。
二、对追求人格和尊严、拒绝强势文化救赎、期待平等对话者的同情
“人类世界是由多种文化组成的巨大社会系统。多种文化存在构成我们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6]在多元世界里,任何民族文化均是“这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渗透着这个民族的基本特征;它是维系民族共同的生活秩序和思想感情的坚不可摧的。”[7]因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东西方发展存在很大差异,但文化可有差异,却不该有强弱,承认文化差异,有可能实现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而各民族与文化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和沟通,需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在小说《扶桑》中,妓女扶桑的东方魅力深深吸引了白人青年克里斯,他梦想自己是勇敢的骑士,要救助被关在囚笼中的东方少女。当扶桑在克里斯救助下住进拯救会的房子,穿上拯救会的白色袍子,克里斯对她的爱慕突然消失,在他眼里,只有穿上象征东方的红色绫罗的扶桑,才是他要拯救的弱势文化中的少女。即使向扶桑求婚时,克里斯的眼神也透着悲怆,种族优越感使他把救赎扶桑当作高尚的责任,在他看来,这种爱恋是伟大的自我牺牲,“他拿你成全他对于爱情理想的牺牲。他还想让他的民族和你的民族都看看,他的自我牺牲将成为一座桥,跨于种族的鸿沟之上,也是通过你,他牺牲自己而赎他民族对你犯下的罪恶……”[8]然而扶桑拒绝了克里斯的救赎,“你不要拯救我,爱我就可以了”[8]。扶桑“跪着的姿态使得她美得惊人,使她的宽容和柔顺被这姿势铸在那里。她跪着,却以弱者的姿态宽恕了站着的人们,宽恕了所有的居高临下者。”[8]
在《栗色头发》中,“我”与生俱来的东方美吸引了“栗色头发”,“你长得非常……特别,非常好看,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理想的古典类型的东方女子。”[9]“我”被一群西方人包围,无法摆脱陌生与无奈的感觉,“这陌生是实质性的,它来自不同的人种、国籍、语言,当然还有观念。我又唤一声李豪,我听出这叫声中的委屈和哀痛,像只失群的雁。”[9]而高傲的“栗色头发”却“引长颈子先大声清理喉咙,然后响亮地往地上一啐。”[10]他骄傲地模仿中国人吐痰的样子,使在场所有人放声大笑。“我”无法忍受“栗色头发”用“那个”腔调讲中国人,在他兴致勃勃地讲述他的伟大理想:他会怎样帮助“我”克服中国人不礼貌、不文明、不整洁的习惯时,在他提到“中国人”使用特殊口吻时,“我”就下定决心再不见他。自尊使“我”不能接受“栗色头发”的所谓救赎。
严歌苓在其作品中极力呼唤不同文化、种族、性别间的平等关系:一个国家,一种文化,总是觉得自己高高在上是不行的,两颗心应该平等,如果你真的爱我,就不要试图拯救我。严歌苓极力寻求不同文化之间平等相处、沟通交流,但却极度艰难,在其作品中,西方文化以救赎方式占据和改造东方文化,多以失败而告终。
《无出路的咖啡馆》中的“我”是一个在美国的华人留学生,因与美国外交官安德烈恋爱而受到FBI调查和审讯。“我”生活拮据,在餐馆打工赚钱难以支付生活费。安德烈对我一见钟情,他是一个无可挑剔的未婚夫,不仅经济富裕,而且性情温柔,对“我”体贴入微,记得“我”爱吃的和不爱吃的东西,甚至为了“我”放弃外交官工作。爱情对于面临生存和文化多重困境的“我”无疑是难得机遇,接受安德烈的爱情,“我”便可过上安逸生活。而“我”为追求人格尊严和独立,宁愿放弃爱情,继续窘迫孤独地生活。此题材来自严歌苓个人经历,她曾因与美国外交官劳伦斯恋爱而受到联邦政府调查,丈夫也因此被取消外交官资格,现实生活中严歌苓和外交官的爱情冲破了文化和种族偏见,此事让严歌苓对西方文化一贯宣称的自由有了颠覆性认识。
移民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接受西方文化熏陶,逐渐接受其价值观念,但在内心深处,故国文化根茎还在,仍会影响其思维和判断,他们在异域土地渴望人格和尊严,期待与寄居国人平等交流和对话,而非救赎与被救赎,因各民族文化均是色拉碗中的重要一味,共同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多元美味。
三、对边缘语境中坚守故国文化者的敬意
严歌苓在作品中成功塑造一系列移民形象:生活在异域文化边缘,在艰难中始终坚守故土文化。传统中国文化推崇“性善”,强调回归生命本身,追寻真善美。严歌苓通过人物塑造,尤其是女性主人公塑造,诠释中华文化对善与美的执着追求。扶桑、少女小渔善良和宽容,微笑面对外界的残忍和不公,扶桑是“微笑得那么无意义,带一丝蠢气”,而小渔则是“人说小渔笑得特别好,就因为笑得毫无想法。”[10]面对复杂万变的社会,善良的小渔“低头一笑”。默默承受一切,男友因工作压力脾气暴躁,不理解她如何能与邋遢的意大利老头和谐相处,甚至帮助猥琐的老头收拾房间。对于房租提高:“她宁可拿钱买清净。她瞒着所有人吃苦,人总该不来烦她了吧。”[1]扶桑和小渔无原则的忍让,无条件的宽容是她们内心深处善良本性的流露。在包容、善良的母性中,外表强悍的大勇被扶桑怜悯和救赎,猥琐的意大利老头受到小渔的感召,对生活有了积极态度。她们的爱心超越人世间利害之争,她们的善良包容一切,是一种自我完善的力量,在异质土地上,坚守故国文化。如严歌苓在《弱者的宣言》中所言:“她的善良可以被人践踏,她对践踏者不是愤怒的,而是怜悯的,带一点无奈和嫌弃。以我们现实的尺度,输了,一个无救的输者。但她没有背叛自己,她达到了人格的完善。她对处处想占她上风,占她便宜的人怀有的那份怜悯使她比他们优越、强大。我在这篇小说写成后才发现自己对于善良的弱者的敬意。”[3]正因弱者的善良,华裔移民才能够在异域土地、强势文化中绽放人性光辉。
严歌苓在国内创作的作品多以部队生活和“文革”时期题材为主,赴美后,移民小说成为其创作主流,读者可从中感受到作家身份和思想的演变。严歌苓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异域漂泊并未淡漠其内心深处对传统的坚守,留美后,她不仅关注移民生活,且从更高层次跨越文化差异,探寻人性真谛。其移民题材小说“一方面拓展了固有民族文学的疆界,另一方面又加速了该民族文学的世界性和全球化进程。”[10]严歌苓笔下移民面对异域文化与本民族文化差异的选择,传达其对多元文化的态度:文化可有差异,但绝无好坏,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文化魅力无与伦比,美国能在短时间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文化也必有可取处。华裔移民只有跨越东西文化差异,才能在多元文化中发现自我,实现自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