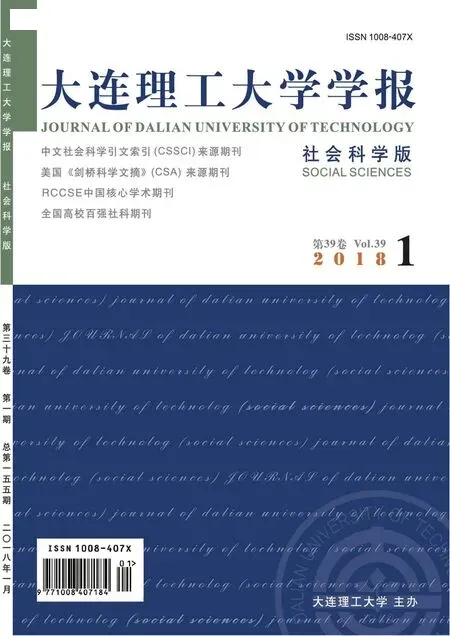“自媒体”时代的审美现状与思考
侯 李 游 美
(成都大学 美术与影视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自媒体”时代的审美现状与思考
侯 李 游 美
(成都大学 美术与影视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近年来,“自媒体”一词渗透到大众文化各领域,从人文学科给予其所承载的相关内容以新的介入与思考,愈发得到学界关注。将自媒体与审美相结合,运用美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为由现代技术所颠覆的传统审美取向进行把脉,在当前背景下对“审美”的边界进行新的探索,有益于准确把握“审美”的嬗变轨迹,更能通过解读“自媒体”为“审美”带来的新冲击,从学理层面给予一定的思考。
“自媒体”;文化征象;审美;思考
当今时代正被冠以“自媒体”“微时代”“互联网+”等极具个性化的称谓,同时也深刻改变有关“意义生成”的方式。我们的身心认知领域,通过技术革新与文化环境互动,被极大程度地拓宽,虚拟网络与现实社会的边界正日益模糊。特别当自媒体颠覆传播主客体、无限降低传播门槛时,不仅因传播行为易操作而实现快速传播的效果,更因营造了“生活审美”、关注人之“当下期待”,为我们在日常生存中绕开精神超越的美学取向提供了另一种“便宜”通道。从审美维度本身看,当人日常“感觉场”被极大规模扩张,审美系统所确立的精神准则也正逐渐被消解,置身业已去除知识界线的审美国度,美学自身亟须重新思考其话语存在方式与新的阐释形式。
一、“自媒体”时代的文化征象
自媒体(We Media),即个人或公民用现代电子技术手段,通过普泛性的方式向大众或特定个体自主传播信息的媒体总称,如微信、微博、网络论坛(BBS)、贴吧,以及国外的Facebook、Twitter等传播媒介。通过这些平台,个人可对外发布亲历亲见亲闻之事,甚至极具个人风格的所感所想,如新浪微博的口号——随时随地分享身边事儿,腾讯微博的口号——不一样的精彩。传播媒介作为社交发布平台,不仅以一种新型文化身份介入传统审美方式,同时也极大程度改变着审美文化的固有形态。当微博把博客内容微缩为人人可发布的140个字符,通过简短内容发送提高了传播率,后增加长微博(一般不超过2000字)类型,希望用户信息传递更符合自然语言的表达。当微信朋友圈中一个个“点赞”符号象征人际交流的情感认同时,我们沉浸于感性、直接的话语表达与人际共享意义生成之中。当以视频APP为代表的流媒体冲破纯文字表达,视频直播这种新的传播形式,模糊了生活本身和审美意义、日常感受和审美经验的差异,对日常感受的撷取演变成娱乐性、消遣性的视听消费,对生存生命的哲学反思,被当下“多重参与”活动的生活功能强大话语所稀释。
“自媒体”时代,文化中的一切现象也与媒体嬗变息息相关,随着移动技术充分运用与互联网信息的海量化、全球化,由技术主导的媒体直接改变了我们的感受方式,人工智能、VR(Virtual Reality)、无人机、车联网,甚至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全球联网计划,最大限度地炮制出有关生活的审美普泛化征象。“美”本身已经由象征着理想升华之境,作为引领人走向永恒追求的意义而存在,泛化为我们在生活现实中的当下体验与感受,消费着一种日常生活形象与投射,呈现为个体审美的当下性与瞬时性。商业本身跳脱固有功能,转单向“兜售”为价值认同构造,今天的很多产品都旨在向客户传达某种生活态度,倡导某种美学精神(如极简美学、生活美学)和价值取向的同时,为产品本身打上艺术与美的光环,通过对客户传递有关“品位”、“阶层”的价值认同,实现最终的商业目的。于是,凡是带有精神烙印的商品,更易让客户买单。文化上则倾向于某种前所未有的“生产性”:数量庞大、直接感性且微化的“审美内容”,为我们快速捕获生活表象打开无数方便之门,移动技术带来的信息生产和获得的便捷性与自由性,彻底消解审美本身的精神特质与小众性,分享无门槛式的草根化生活内容。这样的美学现实,让人的生活反思能力和生命体验进程无需进入形而上的思索,而堕入信息生产和消费的平面化强大网络,直接性、消费性的日常感受成为满足我们当下生活情绪的审美体验。于是,美和审美传统的边界在不断被突破,美学意义的建构模式也在频繁遭到挑战。既往关于审美的深度性与恒久性追求,正在被低密度、平面化、即时性的生活实景所置换。
如果说传统媒体是自上而下的,那么自媒体就是自下而上的。塔勒布在《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一书中说道:“一切自上而下的东西都会使我们变得脆弱,并且阻碍反脆弱性和成长,一切自下而上的事物在适量的压力和混乱下反而能够蓬勃发展。”[1]的确如此,当下“自媒体”形势下的网络传播世界已颠覆传统传播的载体与内容,其效力也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我们的生活方式与审美理念之中。如由内容表演建构的“网红”模式,必将以吸引眼球为爆发点形成无所不在的“吸引力”经济,由此诞生的新光“造星”运动,让电视选秀模式的影响力日渐式微。当前,“互联网+向心力”是一种趋势,“互联网+”本身是一种融合,眼下炙手可热的“网红”是一种吸引,商业价值最大化必然是产业者们的追求,但由此表现的文化征象,不只是属于大众文化现象,更值得学术界关注。新技术与新文化内涵双重夹击下,经典或传统视域中的“审美”概念与“审美行为”已然发生异变。由“互联网+”风暴而来的即时性、碎片性文化内涵的表达,固然充实了传播内容与选择途径,实现了信息自主化与互联网人本化,但随即而来的审美过程的真实化、在场性的即时效果,更让审美对象超越了传统美学意义属性,在审美泛化中将审美价值击溃,使持久、严肃的美学意蕴架构轰然崩塌。当前的审美趋势越来越“从众化”、“吐槽化”。前者较易理解,处于信息量无限增长的社会群体中,我们不得不受外在信息的影响,生怕转发、分享慢了,被他人谈论的“话题”所抛弃;后者所谓“吐槽”,带有一定的调侃、戏谑意义和扁平取向,在气氛自由且选择无限的虚拟空间中,真实生活场景下的规则、束缚被逐渐解除,对现实的不满与批判,在调侃和戏谑的虚拟环境下,转化为类似于审美行为发生后的心理安慰与愉悦。
二、“自媒体”时代的美学取向
1.审美具身化视域下的情绪体验
“自媒体”时代,信息受众同时亦是信息生产者,每一个人都可成为传播者,每个人都不再局限于做“单一传声筒”的传播对象,相反,具备了自主言说、交流的深度自由。其间审美具身化的特殊表现及其连锁反应,亦值得我们关注。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互动仪式》一书提出,“生活犹如剧场,我们需要装扮的空间”[2],“在面对面的符号互动后面有一个更大的背景社会机构,好比一个舞台”[3]。自媒体是多文本(服务)、多场景(7x24小时)、多终端(屏读)的世界空间,如朋友圈中对名人的哀悼呈现为大众化的仪式,个人感情和情绪已不重要,个人的参与仅需“身体”参与其中。几十年前的纸媒时代,我们通过直接的人际交往或者间接的口口相传,实现信息传播。与戈夫曼时代不同的是,自媒体如此发达的当下,一场场“自我表演”转换到了社交媒体之上。
媒介文化越来越重视审美,甚至设法张扬美。“自媒体”以内容、观点、兴趣、吸引力等为核心聚集,形成自发、个体、拟态化的“世界图式”,始于人际传播,过渡到由眼球、人气、点击、转发、吐槽等由“身体”的具身化切身参与形成的“围观世界”,正逐渐改变传统审美习惯与审美范式。审美具身化(embodiment)是一种情境性(situatedness)过程,身体在知行中处于核心地位。“embodied”意味着审美行为发生和具体身体密切相关——基于身体并涉及身体。其间的审美发生,一切都涉及的是自主选择。从印刷时代的“阐释”,到电视时代的“现场”,再到当下自媒体时代的“身体”。有人说,这个时代分为两类人:“网红”与“非网红”。两者之间是消费与被消费的关系,“内容+网红”作为一种孵化模式,正在无限消弥场景式消费与审美活动的边界。“身体”作为人在世体验和生存意义的接受与给予者,是我们“鲜活存在”的母液,梅洛·庞蒂所提出的能意识、能感知的身体,让其体验性成为感知、体知的源头。目前来看,直播与视频,从某种程度来说,全面优先于文字和图片传播。前者由感知重要器官——视听带来了更进一步的沉浸感与刺激感,并在某种情境状态下得到进一步强化。自媒体时代,注意力是稀缺资源。小到商品,再到消费,甚至宣传,都打上了审美的烙印,“审美”已通过媒介遍及生活的各个角落。只有通过审美创造与公众之间的良性循环,才能逐渐累积成为社会的“审美财富”。当下,审美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审美民主化时代,拥有着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和丰富性。“网红”形成的“直播间文化”尤其体现上述所说的审美具身化和情境性。目前很多直播充斥的是“猎奇”、“偷窥”,甚至“刺激”等一系列只见“身体”的伪文化产品,而未让我们看到健康、正能量的精神文化产品。一系列围绕具身化展开的情境活动,让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审美活动、消费行为、信息传播中秉有能感与可感互反性,产生精神富足的幻觉。
在自媒体平台,逻辑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参与者能否在其间找到情绪(体验)刺激点。笔者将这一系列体验称为“极乐体验”:美食、美人、影像、奇货、音乐等众多事件林立,视听触嗅味等直接感官受到强烈冲击,一切看似堂而皇之且皆成奇观,感官体验上难以命名的所有感觉爆量、充盈,深含惊奇。从内容制造看,不管是常见的群体称呼(如“X二代”、“宅男”等),抑或由集体情绪(怀旧、不安全感等)炮制的话题营销,都利用某个群体或大多数公众最易被调动的情绪点,它们可以是一代人的痛点或对社会尖锐矛盾的共鸣,再用或戏谑、或自嘲、或吐槽、或反讽等方式打动受众。“自媒体”在不断“刷存在感”时,通过对公共话语权的抢位,让主流话语权全面下放,所形成的对传统话语形态的解构与重塑,特别是其间社会心理、文化操守的失衡,值得学者们关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Sherry Turkle曾指出,“社交中表演性文化已经成型,叙述性和分析性的自我思考越来越少见。”[4]诚然,自媒体境域下,原本对“文本”(叙事文本、世界文本等)更深层次的思考,正被连续性缺失、不确定性增加、娱乐性泛化等表达给轻易冲淡,传统审美活动中正统、严肃的东西在此境域下或多或少都被消解了。今天我们须正视的东西,类似于波兹曼当年面对的电视节目,如果说前一个阶段的电视辩论让严肃的问题娱乐化,那么现在“自媒体”空间中的一切话题参与已延伸到所有社会公众。
2.空间碎片化场域中的交互表达
有人认为“We Media”翻译为“众媒体”更合适,本文提出可将其理解为“场域”,如微信既是一个“We Media”,也是一种场域。但不能说任何一个场域就是自媒体。此类场域特性在于:有不同(甚至大量)的人共同参与,进退自由。个体之人会“网络死亡”,但场域寿命与活性则较长,其生长周期很可能跟端点数量成正比。互联网出现后,曾产生了这个词:Blogosphere(注意并非blogsphere),它包括3个词:Blog、Logos、Sphere。第一个词是“博客”,最后一个词是“空间”,中间的词则是“逻各斯”,后两个词接近哲学、美学方面的意蕴。当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场域理论,他认为社会行动者一旦进入场域,习性就会引导行动者将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一个被赋予了感觉和价值的世界”[5],“场域”本身就是一个关系网络。随着人社会化进程的加快,时空存在的与人之关系也在发生改变,曾经“点对点”的信息传播模式已被“点对面”的“沉入性”信息参与模式全面取代,“永远在线”突破了时空客观局限,历时性的“全天候”网络“在场”、个体“在场”与共时性的“全方位”网络“世界图景”,在审美时空场景上呈现出别样的色彩和意义。
把这里的“场域”与Logos联系来看,Logos音译成“逻各斯”,即“智慧”。也就是说博客场域并非简单的文字集合,它更代表一种思想的聚合。在西方,基督教语境下的“逻各斯”具有神学意义,成为上帝话语,作为一切真理的源泉而存在。“逻各斯”本身作为一种“意义”或“话语”,它具有“场所”的一切属性,处于其间的人,正由于此“场所”而“言说”,才成其为存在之“人”。“意义从来就不是不可更改的,而始终是暂时性的,始终依赖语境。”[6]作为构建社会话语的语言,始终在我们思想所及或未及的边界,其间充斥着关于话语权力、审美内容的生产、谈判和争夺。
我们已深刻领略了互联网使人人皆成发言人(甚至某一类代言人)的魅力。从贴吧吧主到微博意见领袖,从微信公众号到直播间网红,不同现实时空的个体以不同姿态和视角进入、参与到众声喧哗的网络空间。当“真实社交”与“虚拟交往”融合,“主体自觉”和“个性突显”并存,一场网络世界中的审美狂欢愈发让审美对象(一切影像生产成品)的审美意义日渐被消解、话语中心权日益被放逐。审美者在多元并包的影像观赏需求下单向度话语权进一步削弱,信息接收在“微关注”与“宏视野”混合下不断“碎片化”。在时空表现方面,其中最突出的是人在空间碎片化场域中,突出参与和沉浸的交互体验与表达。当我们进入移动媒体时代,由此而来的网络性、定位性、移动性迅速催生了“定位叙事”这种新的叙事方式,它与空间具有根深蒂固的联系。人在虚拟现实下重回特定空间,无论哪种自媒体之下的“参与”(包括“接受”、“阅读”或“欣赏”),我们关注的都是当中的具体情节——时空在此分离,空间性的内容突显,甚至成为“独立事件”,时间变成空间化的。连空间自身最后也碎片化了,充斥其中的信息制造与信息接收方式也是“碎片化”的。我们眼前堆满的是各种各样的空间性存在,即时吸引、耀眼炫目,人于其中进一步体验了现实感的加强。通过定位叙事的“陌生化”与“场景化”,空间成为地方,在开拓话语空间的同时,也开拓了话语本身的各种视野,比如底层发声有了新的渠道,比如文艺的快速阅读和同质化内容,让创作不止有了原创这一条路径,还可以对无数文化成品进行解构,幻变成一副全新的面目。互联网空间碎片化的交互式存在,固然能让当世之人仿佛可在一生中经历无数事情,这是过去人所无法想象的。我们更应该看到,合理利用它能更好地感知社会态势,畅通社会不同阶级、人群的沟通渠道,在互动、体验、分享中积极营造国家的网络空间主权话语。
3.情境视像化世界中的感性激发
自媒体所具有的“互动性”与“参与性”,使人在电视前被闲置的双手和大脑最大限度地参与其中,每个人在里面都能参与到“可说”、“能说”的“话语空间”,人在不断“激活”文本时,文本也自然而然地“激活”人的感觉。所谓“情境”(situatedness),包括社会的、具身的、场域的、参与的一系列相关内容,审美者和其实践的审美世界彼此相互依存、共同生成。具身化的身体也不再是物理学上的躯体,它指与“环境”进行接触并相互作用的身体。“自媒体”所具备的情境性正重塑人的审美新感性,改变人知觉方式,传统美学中的一系列套路或范式,如审美距离、崇高、悲剧、意蕴……皆面临被重置、替换的命运。频繁切换的画面,让凝神静观的审美距离发生改变,点击鼠标的机械运动,使对审美对象的回味让位给新奇惊颤的效果,这种心理体验有刺激无升华、有震颤无净化。当图像取代文字,人们似乎可以在“虚拟现实”中无须心游而身历,一切“不在场”都可被调动为“在场”,不通过想象就能实现身临其境和物我合一。“自媒体”上的即兴制作(而非创作)替代了个性,数码复制剥离了原创,具身化的情境消弥了距离,图像切换的空间性并置方式消解了时间线性阅读带来的回味感。
如果说审美的重要功能是给人们带来精神愉悦,那么“自媒体”以满足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欲望、人在日常生活的细微欢愉体验的双向特征,区别于传统的艺术审美。比如以对衣食住行为载体的日常生活各类瞬间捕捉,以感性图像渲染某种境遇,通过触动人的感官带来审美者或接受者的亲临感,而无需文字背后更深层次的理性思考。由于审美对象样式和内容的多元化,特别是在“自媒体”环境下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表现内容,审美者或接受者的主体参与意识空前强烈,能根据自身当下情境自由选择更具有“美感”的事物。审美世界中那些极具诱惑或刺激的内容,朱光潜曾举例加以说明:“看见血色鲜丽的姑娘而能‘心如古井’地不动,只一味欣赏曲线美,是一般人所难能的。就美感来说,罗斯金所称赞的血色鲜丽的英国姑娘对于实际人生距离太近,不一定比希腊女神雕像的价值高。”[7]传统审美往往触及审美者的心灵,达到精神共鸣。“自媒体”环境下的审美,却表现为人因为对媒介的过度依赖而产生对即时性的过于迷恋,传统意义上的“静观”、“涤除玄鉴”等审美主张统统失效,取而代之的是对近乎于快感的新感性的迷恋。无数以个人为中心看似又无中心的媒介,无限“延伸”了参与者的主体性,让其体验到“审美”不再专属于专家学者们,而变成了人人时时都可参与的普遍现象,更让“自媒体”世界里的“审美”,呈现了一种新的感性特征。
三、“自媒体”时代的审美思考
身处“自媒体”时代,我们似乎越来越接近审美的目标——实现大众化的“审美”,我们麻木疲惫的灵魂得到了感官上的即时刺激,或被触动或被激扬。其间的审美过程,接近于黑格尔所谓的“审美具有令人解放的性质”[8],黑格尔认为审美感的发生为我们的自由带来了契机,人可通过自己的撷取营造符合自己审美意愿的产品。当“自媒体”不断缩小时空距离,不断改变人际交往方式,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虚拟世界里寄托人的心灵和情感。当人人都可被塑造成生活的艺术家,在虚拟和现实的双重挤压之下,随着审美载体的不断更替,审美文化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进大众的世界,每个个体都可在其间发出自己的声音,任何审美的东西都是自己抓取的,在自己选择中不自觉地陷入迷狂状态,甚至成为一个个片刻不能停止的信息收放端口。曾经当康德叩问人类的审美体验是什么样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回答是审美能引发人的愉悦。今天当现代技术颠覆传统审美规范时,固然涉及到如何释放话语空间与权力尺度,但其中所呈现的审美空间,虽然不断碎片化,依然类似于康德所认知的——属于感性的主观形式。对他来说,“审美空间”属性来自于我们的“mind”,具有观念实在性。对我们而言,“审美碎片化空间”属性更多地来自于我们的“the flesh”,具有体知交互性。前者寄寓于想象力,因为在康德看来,通过想象力提供的场域,有限人类才能逼近无限的理念[9]。后者则承载的是身心快感,因为在我们看来,交互着深切感官体验的场域,通过狂欢杂耍般的游戏,才能满足当下瞬时的欢愉。
赫胥黎忧虑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波兹曼担心我们在汪洋大海的信息中变得被动和自私,思考被淹没在无聊繁琐、充满感官刺激、欲望的庸俗文化中,痛苦的不是人们发笑或不思考,而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和为什么不思考[10]。从目前看,我们面对的媒介改变程度或许比两位前辈面对的更深切。直观性、甚至消费性的日常体验上升为审美感受而成为满足人们各种生活情绪的审美产品时,人本身的想象和反思能力不断被“自媒体”无所不在的信息生产和消费所屏蔽。“自媒体”对审美的影响与渗透,始终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前者为审美文化内容带来新的手段与空间,另一方面又对审美内涵固有的传统规则形成威胁,特别是在工具技术理性对表现理性的超越上。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以“自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传播载体,正在暗暗引导我国当代审美内容和审美形态发生变迁。有关“自媒体”对审美内涵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我们须保持一种开放的审视态度。当现代技术颠覆传统审美规范时,我们须保持一定的张力与觉醒。缺乏审美素养的大众,会让充斥其中所谓的审美产品的生产与接受愈发反常甚至反智;而培育大众审美文明的重要素养,又依赖于新技术潜移默化地推动“生活美学”这类审美叙事深入展开。从传播学、美学,抑或社会学来看,都印证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个体意识的全面崛起与无限放大,但审美本身是在进化还是退化,如何在技术突围的时代,保有或重建人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保持二者的平衡,不仅是大众的问题也是学界的重要议题。
[1]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M]. 雨珂,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67.
[2] 梅洛·庞蒂.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M]. 罗国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342.
[3] 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姜志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1-24.
[4] 雪莉·特克尔. 群体性孤独[M]. 周逵,刘菁荆,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216.
[5] BOURDIEU P. The Social space and the genesis of groups [J]. Theory and Society,1985(14):127.
[6] 约翰·斯道雷. 记忆与欲望的耦合——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与权力[M]. 徐德林,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10.
[7] 朱光潜. 谈美[M]. 北京:中华书局,2010:28.
[8] 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M]. 朱光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47.
[9] KANT I. The Critique of Judgement [M]. Oxford:Trans. J. C. Meredith,1955:108-110.
[10] 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M]. 章艳,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85.
TheAestheticStatusof“WeMedia”Era
HOULiyoumei
(CollegeofArtsandFilms,ChengduUniversity,Chengdu610106,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word “We Media” has penetrated into every area of popular culture. “We Media” has drawn from humanities and gained much public atten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s, this paper draws upon aesthetics, communication and psychology to assess traditional aesthetics subverted by modern technology and investigates the boundary of “aesthetic thinking” in the present context. It is an enlightening approach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aesthetic thinking” and 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the impact of “We Media” upon “aesthetic thinking”.
“We Media” era; cultural signs; aesthetic thinking; reflection
10.19525/j.issn1008-407x.2018.01.017
B832.1
A
1008-407X(2018)01-0124-05
2016-01-09;
2017-03-06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传统乐器陶埙的文化传承与创新设计研究”(16YJC760015)
侯李游美(1985-),女,四川成都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西方美学研究,E-mail:houli-00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