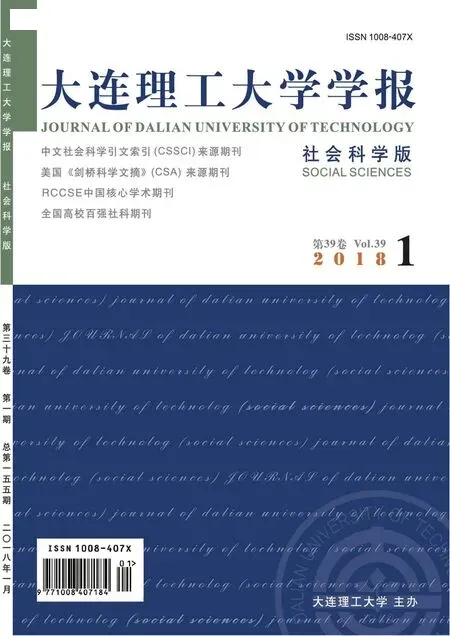寻找语图关系中的缺失之环
——以画学对苏诗的贡献为中心
关 鹏 飞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210023)
寻找语图关系中的缺失之环
——以画学对苏诗的贡献为中心
关 鹏 飞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210023)
在文学影响图像的顺势下,图像对文学表现出不易觉察的反哺作用。以提倡“诗画一律”的苏轼为例,画学对其诗学的反哺作用表现在3个层面:首先,画中物象能够唤醒诗中汉字的图像意味;其次,画面不仅推动苏轼诗歌空间的二维平面化,也促使诗句与画中物象呼应、诗篇借鉴画轴的分合形态、诗中写景视角继承画卷的两种展读方式。最后,诗学中更存在画论渗透现象,主要表现在画论对诗学眼光的磨砺、对诗歌理论的强化、对诗歌现象如以文为诗的补充等。图像对文学的反哺作用有助于重新审视语图关系。
语图;诗画;反哺;苏轼
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图文、语图关系逐渐引起学界关注。赵宪章认为语图互访存在顺势和逆势的差别[1],赵炎秋认为语图之间的虚实“更纯粹是一个角度的问题”[2]。顺势与逆势之称,主要取决双方影响力的大小。相对而言,实指比虚指更有灵活度,但都没较好地揭示出图像对文学的具体影响。这种忽略与学界对诗画关系的研究一致,多注重诗对画(或语图互文理论)的影响,如邓乔彬《有声画与无声诗》[3]、李明彦的《从语图互文理论中寻究中国诗学因素》[4]、史宏云《花鸟画和题画诗的意象研究》[5]等,而忽略画学对诗学的影响。
出现这类现象的原因,与诗的艺术高于画的艺术的传统思维有关。其实,学界已对“诗的艺术高于画的艺术的传统思维”展开反思,刘石就认为“诗画的关系是平等的”[6]128,邹广胜则通过比较莱辛与苏轼的诗画观,认为不管是强调差异还是一律,都是对诗、画两门艺术的平等对待,而非黑格尔、康德等人本主义者所谓的诗的艺术高于画的艺术,这种观点是忽视中西方文化背景造成的[7]。在艺术史研究领域也有此类反思,如王新在《诗、画、乐的融通》中就特别强调技艺层面的研究。其中也不乏用西方的艺术史理论来阐释中国古典诗词的尝试,如以诺曼·布列逊凝视(gaze)与瞥视(glance)视角对李煜词风转变进行视觉性研究[8]。
以上反思启示我们,即便在古代艺术发展的长河中存在着诗高于画的偏见,诗确实也深入地影响着画,但不意味着画对诗没有影响或影响甚微。本文以诗画一律论提出者苏轼为分析对象,着重探讨画学对其诗学的逆势影响,从而揭示图像对文学的反哺作用。
一、画中物象对汉字图像意味的唤醒
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尤其是汉字组成的诗歌,跟图像有天然联系。汉字原是象形文字,抽象化的历程中多少还保有图画意味,何九盈云:“甲骨文时代汉字已是相当成熟的系统,但图画的意味还比较明显,当然跟图画已有性质上的不同。”[9]152“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等字不必说,就是形声字,其形旁也有浓郁的图画意味。这4类字在汉字中占据绝大多数。因此可以说,汉字所写的诗歌与图像之间本来就是血脉相连。这从埃兹拉·庞德等人发动的意象派诗歌中可以看得更清楚。庞德从汉语文学的描写中看到一种语言与意象的魔力,主张寻找出汉语中的意象,其长诗《诗章》中便多处夹着汉字,使汉字本身的图像意味成为诗歌意象的组成部分。
但不容否认的是,文字跟图像虽然同源,却在并存的道路上扬长补短,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说:“自从文字出现,将大部分的功用性沟通承担起来之后,减轻了图像的负担,使之得以发挥表现和抒发的功能,大大展示相似性……图像是符号之母,但书写符号的诞生使图像可以完全发展成熟,独立存在,与话语分开,减去了沟通方面的普通职责。”[10]193图像符号在“大大展示相似性”的时候,书写符号也日渐变得更加抽象,远离原始图像,从而更直接、更准确、更简练地描述和表达客观世界,成为人与人之间进行沟通的主要工具和途径。
针对以上特点,汉字也不例外。但是汉字在变化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形”“音”“义”的三要素,因此,其图像意味虽越来越不明显,却始终包含在字形之中(假借和转注字除外,但比例很小)。而古典诗歌少用词组、多用单字的特点,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最大限度地发挥汉字的图像意味,只是此时的汉字图像与原初的物象之间已经存在较大距离。而画中的物象对缩短此中距离、唤醒汉字原有的物象很有帮助。如苏轼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题雍秀才画草虫八物》,其中有3首很值得注意,现录如下:
《天水牛》:“两角徒自长,空飞不服箱。为牛竟何事,利吻穴枯桑。”[11]2735
《蝎虎》:“跂跂有足蛇,脉脉无角龙。为虎君勿笑,食尽虿尾虫。”[11]2736
《鬼蝶》:“双眉卷铁丝,两翅晕金碧。初来花争妍,忽去鬼无迹。”[11]2737
天水牛,即天牛,据《本草纲目·虫部》说,“有黑角如八字,似水牛角,故名”[12]1543。但苏诗中的“两角徒自长”却不是此意,乃是指天牛头上的触须。服箱即负车箱,指拉车。天牛是昆虫,自然只会用利嘴在枯树上打洞,不会像牛那样拉车劳作,苏轼为什么会在画中的昆虫身上联想到牛?因为按照《本草纲目》的解释,天牛与牛的相似度极小。
再看《蝎虎》。蝎虎指蜥蜴。诗的开头两句先说蝎虎跟蛇一样是爬行动物,但跟蛇不同的是它有脚;跟龙一样昂头凝视,细看却又没有龙一样的角。这是通过跟龙、蛇比较异同来揭示出蝎虎的特征:它尽管跟龙、蛇不太一样,但大体上还是相似的地方多。既然跟龙、蛇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为什么却又突然说到“为虎君勿笑,食尽虿尾虫”。“君不要笑它被称作虎(却没有一点虎的威严凶猛),毕竟它还是能够捕食蝎子吃的。”这样调侃的奇思妙想从何而来?
最后一首《鬼蝶》也是一样。鬼蝶又叫鬼蛱蝶,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虫鱼志》云:“鬼蛱蝶,大如扇,四翅,好飞荔枝上。”[13]67鬼蛱蝶的双须像卷起来的长铁丝,其翅膀(范成大说是四翅,苏轼写为双翅,盖画面如此)则色彩斑斓,金碧辉煌。这样的形象,跟“鬼”相去太远,苏轼为什么却联想到“鬼”,还用“鬼”的来去无踪形容它飞翔之迅捷?
从这3首诗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它们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画面所画之物象与诗中后两句所写的形象之间存在着相反关系。前两句所写物象尽管与图画一致,后两句所写却与图画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3首诗中都出现,不能算巧合。仔细分析后两句引起矛盾的物象,都跟这3个物象的命名有关。其中天水牛、蝎虎与后一个字有关,鬼蝶与前一个字有关。在诗句的转换中,“天水牛”的“牛”、“蝎虎”的“虎”和“鬼蝶”的“鬼”,都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汉字,它们被形象化为真牛、真虎和真鬼,从而与画面上的物象进行对比,产生反差,突出诗意。
作为汉字的“牛”“虎”“鬼”都是象形字,原本富有图画意味,因此,在苏轼的诗歌创作中,不乏通过诗性思维将其化为诗歌形象者。如“牛”,《黄牛庙》云:“江边石壁高无路,上有黄牛不服箱……山下耕牛苦硗确,两角磨崖四蹄湿。青刍半束长苦饥,仰看黄牛安可及。”[11]94-95如“虎”,《虎跑泉》云:“亭亭石塔东峰上,此老初来百神仰。虎移泉眼趁行脚,龙作浪花供抚掌。”(“鬼”字由于苏轼诗歌中不多,虽有《水陆法像赞·一切饿鬼众》赞,但跟诗歌不一样,故略)通过诗性思维将其化为诗歌形象,跟“牛”“虎”在《天水牛》、《蝎虎》和《鬼蝶》中扮演的角色一致。
但《题雍秀才画草虫八物》这3首诗跟前面的《黄牛庙》《虎跑泉》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后二者竭力通过青牛与黄牛、龙与虎的对比、并置,以突出其形象性,把“牛”“虎”写真,从而增强感染力,这说明它们本身的形象性是不行的,需要诗性思维渲染画面感才能达到;而在前3首诗中,作者竭力描写的却是每首诗前两句的画中物象,在画中物象得到充分表达之后,才来与“牛”“虎”“鬼”对比或比拟,这说明“牛”“虎”“鬼”的形象性太强,以至于诗人不得不减省笔墨,从而避免对诗中所写的画象造成喧宾夺主的效果。这说明画面容易唤醒诗人脑海中被抑制的汉字图像意味,并不断干扰画面本身。
画中图像对汉字图像意味的唤醒,在苏轼诗歌中显著表现出来的并不多。这跟他的画学理论有关,他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所以在题画诗中以追求画理、画神为主,脱落画中的物象,而代之以诗中的画面感。同样在《题雍秀才画草虫八物》中的另外5首诗便是如此。在《蜗牛》诗中,蜗牛画面与汉字“牛”所唤醒的图像意味的融合已在《天水牛》中使用过,因此,只能摆脱画面,费力营造诗中画面。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八引《王直方诗话》云:“东坡作《蜗牛》诗云:‘中弱不胜触,外坚聊自郛。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后改云:‘腥涎不满壳,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粘壁枯。’余亦以为改者胜。”[14]1524这两版诗的不同之处主要在前两句。“中弱”两句还是对画中物象的描绘,与《天水牛》相同,但不同的是诗人要避免被画面唤醒的“牛”字所指的实体形象(此形象在《天水牛》中使用过),不得不抛弃画面的形似描写,换作“腥涎”二句。“腥涎不满壳”在画面上无法表现出来,因为“壳”与“壳中涎”处在两个平面中,可以在画面上展露一角,却无法全部(即“满壳”)描绘。“腥涎不满壳”虽不是原有画面,却跟后两句形成完整的诗中画面,使蜗牛形象饱满起来。
画中物象对汉字图像意味的唤醒,使诗人较容易结合二者,身临其境,但对提倡“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苏轼来说,只是偶一为之,更多时候是想达到更深一层,即“诗中有画”——诗本身是一个自足自洽的弹丸,它内部已含有画面感,不需要外在的形象来补充。但这“偶一为之”本身,已足证明画中物象对汉字图像意味确实存在唤醒的功能。
苏轼在诗歌创作中,尤其是在题画诗的创作中尽量避免这类唤醒对其诗歌“深度”的制约,从而努力超越。另外,画中物象唤醒汉字图像意味时,会使汉字的色彩感突显。苏轼《书退之诗》云:“韩退之《游青龙寺》诗,终篇言赤色,莫晓其故。尝见小说,郑虔寓青龙寺,贫无纸,取柿叶学书。九月柿叶赤而实红,退之诗乃寓此也。”[11]7519韩愈此诗指《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苏轼指出,韩愈之诗是暗用郑虔典故,而郑虔“善图山水”的画家身份使韩愈在暗用其典故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关注到色彩。苏轼不仅注意到这一点,且在创作中也表现得青出于蓝。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所作《寿星院寒碧轩》云:“清风肃肃摇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围。纷纷苍雪落夏簟,冉冉绿雾霑人衣。日髙山蝉抱叶响,人静翠羽穿林飞。道人绝粒对寒碧,为问鹤骨何缘肥。”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东坡寒碧轩诗”云:“苏文忠公诗,初若豪迈天成,其实关键甚密。再来杭州,《寿星院寒碧轩》诗句句切题,而未尝拘。其云:‘清风肃肃摇窗扉,窗里修竹一尺围。纷纷苍雪落夏簟,冉冉緑雾沾人衣。’寒碧各在其中。第五句‘日高山蝉抱叶响’,颇似无意,而杜诗云‘抱叶寒蝉静’,并叶言之,寒亦在中矣。‘人静翠羽穿林飞’,固不待言。末句却说破:‘道人绝粒对寒碧,为问鹤骨何缘肥。’其妙如此。”[14]5912全诗每句都紧扣“寒碧”二字,故而能够达到身临其境的艺术效果。以诗中汉字所包含的色彩意味暗示画面,在读者脑中形成主色图,使其身临其境。苏轼的处理方法,对读图时代的文学创作无疑具有启发性。
需要说明的是,图画对汉字的这种唤醒功能,是通过画中物象与汉字图像意味的共振引起的,它听起来似乎类似于西方的“文本间性”或“互文间性”,但实际上却并不相同。文本间性或互文间性是从读者的阐释角度出发,面对的是已经成型的多个文本或图画,而本文所处理的问题却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诗、画、实体形象3个方面的平衡。
二、画面:诗篇空间布局的二维展开
丰子恺将绘画分为两种:“一切绘画之中,有一种专求形状色彩的感觉美,而不注重题材的意义,则与文学没交涉,现在可暂称之为‘纯粹的绘画’。又有一种,求形色的美之外,又兼重题材的意义与思想,则涉及文学的领域,可暂称之为‘文学的绘画’。”[15]35可见无论是“纯粹的绘画”还是“文学的绘画”,“形状色彩”是共同的要素。色彩是指“绘事后素”的“绘”,是绘画的本义所在;而“形状”则是画中物象的展开,是构成物象的另一个重要部分。然而,无论是色彩还是形状,都需要有表现的载体,这个载体呈现在纸帛上就是画面。尽管画面是平面的,其效果却不止于此。丰子恺又说:“图画能在平面上作立体的表现,故兼有平面与立体的效果。”[16]4这种平面的画面,在诗歌中也有表现。
画学对苏诗的平面化影响,可以概括为苏诗空间布局的二维展开。二维指平面,展开则意味着诗篇在作为空间艺术的画学影响下依然保持着其时间艺术的特质。这种二维展开,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1.诗句与画中物象的呼应
闻一多提倡诗歌创作中的建筑美,已经注意到诗篇本身由文字形成的造型会影响其内容、思想和情绪的模拟与表达。当然,闻先生走的路子还比较传统,像美国诗人E·E·肯明斯(E·E·Cummings)的《l(a)》等诗歌,则把诗的形状与诗歌内容的结合表现得更极端,同时也更鲜明[17]14-15。苏轼诗歌创作中也有此类现象。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九月《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何人遗公石屏风,上有水墨希微踪。不画长林与巨植,独画峨眉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于诗人同。”[11]566诗中明说“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于诗人同”,即画师与诗人在“摹写物象”这一点上有相同之处。这一“物象”具体是指孤松。诗句竭力摹写这棵孤松的形状,在与长林、巨植的对比和孤烟落日、含风偃蹇的衬托中,孤松形象也就具体化了。然而最使读者形象化地感受到孤松,却是诗中的长句,即“独画峨眉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这句长达16个字的诗句屹立在全诗之中,跟其他的七言、九言句相比(总和加在一起才16字),差别巨大,直接展现出孤松在群山崖涧孤标独出的画面感,诚如汪师韩所云:“长句磊砢,笔力具有虬松屈盘之势。”[11]568
有时候诗句对画中的题字也会呼应,并使画中题字产生审美效果。如《郭熙画秋山平远》一诗,苏轼自注:“文潞公为跋尾。”文潞公指文彦博。诗云:“玉堂昼掩春日闲,中有郭熙画春山……伊川佚老鬓如霜,卧看秋山思洛阳。为君纸尾作行草,烱如嵩洛浮秋光。”[18]1509-1510诗题为“秋山平远”,画中先写“春山”,后写“秋山”。诗中提到文彦博为画所题之跋尾,字体是行草,波动连绵,恰如洛水上浮起的秋光。则苏轼在题画的过程中,把书法也一并绘画化了。这种把题字也绘画化的做法,在徐渭等野逸派写意画家中得到呼应:“野逸派写意画家的作品就不同了,如果删去所题诗(文),作品就残缺了、不完整了,画面的所指就变得很不确定。”[1]但在苏轼那里,还没有如此极端,即便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诗中说:“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11]2593也只是在做完画、郭祥正题诗后,自己又写一首,而非一开始就把诗画合在一起。故周亮工《画影》卷十说:“不必见其画,觉十指酒气,沸沸满壁。”[19]1030这显出此诗本身的自足性。
2.诗篇对画轴形态的借鉴
不仅诗句形态会对画中物象有所模仿,就是画轴分合的物质形态,也会直接影响诗人的艺术构思。学界已有对画框的知觉转换与再现的研究[20],这里主要从构思的角度展开。如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苏轼创作《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其一云:“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11]3167其二云:“人间斤斧日创夷,谁见龙蛇百尺姿?不是溪山成独往,何人解作挂猿枝。”[11]3169就诗本身来看,所写似乎是两幅画,一幅画可称作野水疏林图,另一幅可称作溪山疏林图。尽管都是画疏林,却有地点之别,一在水边,一在山上;一幅勾起诗人归隐之意,一幅使诗人羡慕画家深入溪山采风、绘画生涯恍如隐居一般的生活和由此带来的高超画艺。
据邓椿《画继》卷四云:“予尝见其孙皓云:‘此图本寒林障,分作两轴。前3幅尽寒林坡,所以有‘龙蛇姿’之句。后3幅尽平远,所以有‘黄叶村’之句。其实一景,而坡作两意。”[21]24原来此画本是一幅,被分成两轴,而每轴分别引出苏轼诗思。跟这幅画虽分成两轴而终究是一幅同样的是,这两首诗虽然各有立意,却在“隐居生活”的层面达成一致。两首诗看起来分开独立,实际上也有共同的主题衔接。这或许与组诗的性质有关,但一幅画分成两轴的实物形态无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3.诗中写景与画卷的两种展读样式
以上论述画学对诗句、诗篇的影响,按照苏轼的画学,更多的应该是“诗中有画”,这就体现在诗歌写景对绘画构图的学习和改进上。但是关于山水诗和山水画,很难证实究竟谁影响谁,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观看、游览等方面,实在太过于相似,何况它们还有着极为相似的产生背景。王淑娟从时代的角度,对山水画与山水诗的关系作出界定与论述[22],这种论述也许对一个时代是有效的,但对苏轼个人来说,情况远为复杂。因为苏轼诗中对画的接受,有可能是来自画,也有可能是继承前人诗作中对画的吸收。然而,就算是继承前人对画的吸收,其实也是受画学影响。故而最难的地方不在这里,而在于诗、画共同的来源,即观察大自然上。
丰子恺似乎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方法:“中国的艺术真有些儿奇妙:用言语来作诗文时,很会应用绘画的远近法,而把眼前的景物平面化;但真当到了平面的纸上去作画时,反而不肯把景物看作平面形,而描出远近法错误的绘画来。”[15]40对此现象,丰先生得出的结论是“诗画交流”所引起的。这里面的问题是,中国绘画从来就没有遵守过远近法,丰先生的立论很难站住脚。
所幸,作为绘画古今也有不变者在,就是其构图只能呈现出某个面向的二维结构。本文结合此一特点,并在古人评论的基础上加以论述。毕竟古人所接触的绘画与原貌更为接近。比较有代表性的资料如下:
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五月《司马君实独乐园》:“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11]1497-1498比苏轼略晚而与黄庭坚同时的王直方评论说:“只从头四句便已都说尽……此便可以图画。”[14]1525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城南县尉水亭得长字》:“两尉郁相望,东南百步场……泽国山围里,孤城水影傍。欲知归路处,苇外记风樯。”[11]2068-2069査慎行评末四句“入画”[11]2070。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与客游道场何山,得鸟字》:“清溪到山尽,飞路盘空小。红亭与白塔,隐见乔木杪。中休得小庵,孤绝寄云表。洞庭在北戸,云水天渺渺……”[11]2022纪昀:“起四句如画。”[11]2025
第1条资料中,可以绘图的诗句呈现出的画面是青山在上,流水在下,园屋在中间,形成一个上下拓展的二维平面。第2条资料中,可以入画的诗句呈现出的画面是水在山中,水旁有孤城,芦苇外有舟船,形成一个左右拓展的二维平面。前者对应着挂壁式的绘画,后者对应着横轴式的绘画。这正是古代绘画的两种平面款式。第3条资料,需要注意的是,纪昀是将诗歌中的文脉切断,因为“清溪到山尽,飞路盘空小。红亭与白塔,隐见乔木杪”之后紧接着“中休得小庵,孤绝寄云表。洞庭在北戸,云水天渺渺”。他为什么要切断?因为这8句诗中包含着上下、左右两个方向的平面。前4句由下而上,分别有溪山路树、红亭白塔,这是典型的挂壁式。后4句中的前两句依然可以嵌进挂壁式画面,但由“小庵”引出来的“洞庭在北户”,则窜入横轴式画面。这两种画面是没法统一在一个二维画面中的,因此,纪昀只取开头4句。
这在苏轼前的诗歌创作中还不太自觉。如岑参《酬崔十三侍御登玉垒山思故园见寄》:“玉垒天晴望,诸峰尽觉低。故园江树北,斜日岭云西。旷野看人小,长空共鸟齐。山髙徒仰止,不得日攀跻。”[23]464尽管“旷野看人小,长空共鸟齐”两句,如丰子恺所分析“仿佛是远近法理论中的说明文句”[15]5,但查看全诗,一会儿“北”“西”,一会儿“上”“下”,在短暂的诗句中,画面感并不强烈。而苏轼已经从4句(4句相当于一首绝句,可以独立成诗)中把握一个整体的画面,这个画面有一个主要的拓展方向。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宋代绘画的两种样式,即挂壁式和横轴式,对苏轼的诗歌创作是有影响的。有时如第1、2条资料那样,单独地影响到苏轼观看景物的视角,有时又如第3条资料那样,综合地运用到对景物的观察中去。但无论是哪一种,都是富有画面感的组合,而非唐代诗人那样随性、破碎、不成一体。
三、诗学中的画论渗透
画学对诗歌的影响,如前所述,已经不可忽视,但更重要的是对诗学的影响。这种影响虽然没有前面显著,却是诗学中更为本质的方面。它较为重要地体现在诗学眼光、功能和风格3个层面。
1.对诗学眼光的磨砺
苏轼诗画论的形成,有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画学理论和习画实践[24]。绘画尽管师法造化和心源,本身含有形象性的渴求,但由于工具媒介如线条、颜色、形状等本身的含混性,对画面进行深入解读和剖析需要比鉴赏诗歌更为敏锐的眼力。苏轼在这方面就得到画学较为全面的锻炼,以至于著名画家文与可视苏轼为唯一知音,《书文与可墨竹》叙曰:“与可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与可尝云:世无知我者,惟子瞻一见,识吾妙处。”[18]1392甚至文与可作画也只等苏轼品题,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题文与可墨竹》,其叙:“故人文与可为道师王执中作墨竹,且谓执中勿使他人书字,待苏子瞻来,令作诗其侧。”[18]1439而苏轼本人也对自己的鉴画能力颇为自得,他能一眼看出吴道子画是不是真迹,元祐九年(公元1094年)《次韵李端叔谢送牛戬〈鸳鸯竹石图〉》也说:“知君论将口,似我识画眼。”[11]4301
这种鉴画眼光对他欣赏万物之美从而入诗很有帮助。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次韵滕大夫三首·雪浪石》云:“画师争摹雪浪势,天工不见雷斧痕。离堆四面绕江水,坐无蜀士谁与论。老翁儿戏作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此身自幻孰非梦,故国山水聊心存。”[11]4242-4243《雪浪斋铭》引云:“予于中山后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孙位、孙知微所画石间奔流,尽水之变。”[25]574无论是诗还是文,两者都讲明对雪浪石的欣赏得益于孙位等人的绘画。诗中所写的雪浪石,虽寥寥几笔,而其天生丽质便乍现眼前,非常生动。可是雪浪石的尊容究竟如何,杜绾《云林石谱》卷下《雪浪石》记载道:“中山府土中出石,色灰黑,燥而无声,泯然成质,其纹多白脉,笼络如披麻旋绕委曲之势。”[26]31披麻之喻,已经不美。王士祯《秦蜀驿程后记》卷上说得更明白:“予审视,盆四面刻纹作芙蕖……然石实无他奇,徒以见赏坡公,侈美千载,物亦有天幸焉。”[27]1151无论是比苏轼略早的“岩石矿物学家”杜绾,还是较后的诗人王士祯,在他们看来,雪浪石并无奇特,遑论丽质。而苏轼却能从中激发出审美的气质,并写入诗中,流传千载,无疑跟他从石头文理上参透“孙位、孙知微所画石间奔流”“画师争摹雪浪石”有关,即苏轼本人的画学修养使他易于联想,敏于观察。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壶中九华诗中,诗题为《湖口人李正臣蓄石九峰,玲珑宛转,若窗棂然。予欲以百金买之,与仇池石为偶,方南迁未暇也。名之曰壶中九华,且以诗纪之》,其诗云:“清溪电转失云峰,梦里犹惊翠扫空。五岭莫愁千嶂外,九华今在一壶中。天池水落层层见,玉女窗明处处通。念我仇池太孤绝,百金归买碧玲珑。”[18]2048诗中描写九华峰上天池落水,缝隙间仙女飘飘,可谓绝品,于是不惜以重金购买。但据知情人士透露,此又是苏轼的一次艺术审视,而非实录。方勺《泊宅编》卷中云:“湖口李正臣所蓄石,东坡名以壶中九华者,予不及见之,但尝询正臣所刻碑本。虽九峰排列如鹰齿,不甚崷崪,而石腰有白脉若束以丝带。此石之病,不知坡何酷爱之如此,欲买之百金。岂好事之过乎?予恐词人笔力有余,多借假象物以发其思,为后人诡异之观尔。”[28]81田晓菲分析说:“方勺明白石头的价值,与其说在于石头自身,还不如说在于诗人对它的鉴赏。在方勺的叙述中,苏轼被还原为‘有力者’,是他的‘笔力’赋予了自然之物魅力和价值。”[29]42而这种“鉴赏”的“笔力”,固然与诗人的诗性思维关系密切,也与诗人本身深厚的艺术鉴赏密不可分。
2.绘画理论对诗歌理论的强化
在《艺术和人文——艺术导论》一书中,绘画和文学都归属于艺术,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无论是绘画还是文学,都在创造一种跟价值有关的表现形式,尽管它们的表现工具有所不同。这就带来一个难点,即探讨艺术跟哲学、史学等人文学科的关系较为容易,而在艺术内部进行明确区分则比较难。在苏轼的画学和诗学之间进行理论探讨则更难,因为理论本身是需要抽象的,而一旦抽象起来,就会成为比诗、画范畴更高的艺术的理论,就很难再去区分谁影响谁。即便按照资料的年代进行先后排序,那也只是反映出资料撰写的先后,不一定代表理论思考的早晚。因此,本部分探讨的重点是画学对诗学理论的加强倾向,而不敢断然说没有画学这样的诗学理论就不会产生。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撰有《画水记》,其文云:“古今画水,多作平远细皱,其善者不过能为波头起伏,使人至以手扪之,谓有窪隆,以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与印板水纸争工拙于毫厘间耳。唐广明中,处士孙位始出新意,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号称神逸。其后蜀人黄筌、孙知微,皆得其笔法。始,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笔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轮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11]1302仔细分析文中所说的“与山石曲折”和“作湖滩水石四堵”可知,所谓“山石”和“水石”,都是指作为画中物象的山水石头。
苏轼晚年所作《自评文》又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岀,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11]7422其中“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的理论,跟《画水记》有相通之处。在此文的表述中,已经将画中之水看作不择地而出的万斛泉源,是自然界中的真水。而苏轼对孙位画水的体味,也是“尽水之变”,评孙知微画也是“轮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都认为画中水是“活水”,即真水。
从艺术反映现实的角度来看,它们是一致的,都是苏轼在模仿自然的过程中对艺术原理的深刻洞察。但具体考证苏轼对孙位的接触,似乎又不能如此笼统地看待。苏辙《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回忆云:“予先君宫师平生好画,家居甚贫,而购画常若不及。予兄子瞻少而知画,不学而得用笔之理……予昔游成都,唐人遗迹遍于老佛之居。先蜀之老有能评之者,曰:‘画格有四,曰能、妙、神、逸。’盖能不及妙,妙不及神,神不及逸。称神者二人,曰范琼、赵公佑,而称逸者一人,孙遇而已。”[30]1106昔游成都指苏洵带二苏兄弟去成都拜访张方平。先蜀能评画者,指黄休复及其《益州名画录》。孙遇即孙位的别名。尽管苏轼、苏辙对画的看法都有变化,但苏轼赞美孙位画水的神妙却一以贯之,在诗文中也多次提到孙位。苏轼对孙位的理解自然需要他自身的艺术实践融入才能完全达到,这种艺术实践或许也少不了其诗学实践的加入,但仅就苏轼对孙位画水“随物赋形”的理解而言,无疑会对他诗文创作中“随物赋形”之类观念的产生,起到一定的强化作用。
这里还有一个小证据。“随物赋形”,张志烈等指出:“晋人谢赫《古画品录》提出绘画六法,第四为‘随物赋彩’,此处发展其意。”[31]360谢赫绘画六法中的第三法是“应物象形”,与“随物赋彩”结合起来,便是“随物赋形”。苏轼把“彩”去掉而保留“形”,与中国绘画由重视傅彩上色到水墨线条的演变一致,这里要探讨的是,万物有颜色,是很显然的,但是万物在画面上表现出来的线条轮廓,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而“随物赋形”的“形”,指的就是物体的线条轮廓。也就是说,从“彩”与“形”的不同取舍可以看出,苏轼“随物赋形”理论更多的是直接从绘画中来,而非对自然世界的审美观察,因为在大自然中并不存在抽象线条,它只是画家用来表现物象的基本工具。
3.画学对以文为诗的补充
相比唐诗的兴象玲珑,多数人把宋诗的特点概括为“以文为诗”。以文为诗的内涵,在今天存有争议。程千帆《读宋诗随笔·前言》中说:“严羽指出宋人以文字为诗。文字这个词在宋代有广狭二义:广义指书面语言,狭义则指散文。这里显然是指曾经引起非议的以散文为诗;而以散文为诗,又往往和以议论为诗是紧密地联系着的。”[32]383周裕锴则认为“以文字为诗”并非以散文为诗,而是作为禅家“不立文字”的对立面提出来的[33]。这里不做精微的区别,而取其广义。以文为诗导致的后果,是才学、议论的强化,而诗歌的形象性则受到一定的损害。而画学的融入,却是对以文为诗风格的一种有益补充,使诗歌更多一些形象画面,这在苏诗中尤其明显。
画学对以文为诗的补充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画面描写的直接介入,使全诗形象生动。如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江上愁心千叠山,浮空积翠如云烟……使君何从得此本,点缀毫末分清妍。”[18]1608汪师韩评前半部分便说:“竟是为画作记。然摹写之神妙,恐作记反不能如韵语之曲尽而有情也。”[34]444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影响风景描写而渲染诗情。通读苏诗可以发现,此类现象并不少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九东坡四已经发现此类现象:“苕溪渔隐曰:李太白《浔阳紫极宫感秋》云:‘何处闻秋声,翛翛北窗竹。回薄万古心,揽之不盈掬。’东坡和韵云:‘寄卧虚寂堂,月明浸疎竹。泠然洗我心,欲饮不可掬。’予谓东坡此语似优于太白矣。大率东坡每题咏景物于长篇中,只篇首四句便能写尽,语仍快健。”[34]212后面又举出一些例子,如《庐山开元漱玉亭》首四句云:“高岩下赤日,深谷来悲风。劈开青玉峡,飞出两白龙。”[18]1216《行琼儋间》(原题为《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首四句云:“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18]2246其他还有《谷林堂》《藤州江上夜起对月》等。
胡仔颇有眼光,但所论过于狭窄(这可能跟当时摘句风气有关,比较喜欢摘录画面感较强的诗句[35]),其实何止首四句,如《开先漱玉亭》四句之后的描写也极为精彩:“乱沫散霜雪,古潭摇清空。余流滑无声,快写双石谼。”不一而足。这些诗句中,有一些明显是受到画卷展开形式的影响,如“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疎。美哉斯堂成,及此秋风初”;而“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则倾向于是横轴式。更多的则是融合二者。画学通过景物描写,使其更有画面感,更有层次感,同时也更为形象化。
四、结 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同为艺术中的两大门类的绘画与文学,在苏轼的画学与诗学中表现出复杂的关系。画学对苏诗的影响,也呈现出较为立体、综合和深入的特征,并在诗歌字词、诗篇布局与构图、诗学等层面展现出积极的作用。总之,在苏轼的诗学影响画学的主流之下,还暗含着画学对诗学的反哺,这种反哺虽然不易察觉和论述,但却是真实存在并强劲有力地推动苏诗前进,对苏轼诗歌艺术成就有所贡献。而这种反哺作用,对于我们重新审视语图关系,是极有助益的。
在宋代,绘画与诗歌皆在传统的基础上发生巨变,为身处其中的苏轼画学反哺诗学营造绝佳的酝酿条件和接受环境。这绝非偶然,而是中国绘画反哺诗歌历程的典型代表。至于中国绘画反哺诗歌历程,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首先,中国画与西洋画差别极大,主要区别在追求形似还是神似,从而在用笔、上色、构图等方面均有不同。但从美术史角度看,中国画中也分画师画与文人画,它们在相辅相成的融合中呈现此消彼长之势。画师画与文人画的发展、成熟与新变,与中国绘画反哺诗歌的历程、特征密切相关。其次,中国绘画反哺诗歌的历程、特征,也与诗歌本身发展息息相连。中国诗歌自身有漫长演变史,如果从广义诗歌的角度观照,从诗骚发轫,其复杂情况需要专门诗歌史探究。但就诗歌特性而言,“诗分唐宋”是对其不同特质较为准确的宏观把握。唐音宋调不仅是对唐宋诗歌的风格概括,更成为后宋诗歌的评判标准,在中国绘画反哺诗歌历程中成为重要变量。至于二者究竟如何在历史长河中演变,笔者拟撰专文讨论。
[1] 赵宪章. 语图互仿的顺势与逆势——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J]. 中国社会科学,2011(3):170-184.
[2] 赵炎秋. 实指与虚指: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再探[J]. 文学评论,2012(6):171-179.
[3] 邓乔彬. 有声画与无声诗[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4] 李明彦. 语图互文理论中的中国诗学因素[J]. 文艺争鸣,2014(12):80-85.
[5] 史宏云. 花鸟画和题画诗的意象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6] 刘石. 诗画一律内涵[J]. 文学遗产,2008(6):117-128.
[7] 邹广胜. 谈文学与图像关系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J]. 文艺理论研究,2011(1):20-25.
[8] 王新. 诗、画、乐的融通[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9] 何九盈. 汉字文化学:第2版[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0] 雷吉斯·德布雷. 图像的生与死——西方观图史[M]. 黄讯余,黄建华,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1]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 苏轼全集校注[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12] 李时珍. 本草纲目[M]. 刘衡如,刘山水,校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13] 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校注[M]. 严沛,校注.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14] 吴文治. 宋诗话全编[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5] 丰子恺. 绘画与文学[M]. 长沙:岳麓书社,2012.
[16] 丰子恺. 艺术漫谈[M]. 长沙:岳麓书社,2010.
[17] F·大卫·马丁,李·A·雅各布斯. 艺术和人文——艺术导论:第6版[M]. 包慧怡,黄少婷,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18] 王文诰. 苏轼诗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19] 曾枣庄. 苏诗汇评[M].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
[20] 汤克兵. 知觉性画框与绘画的视觉再现[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5):131-138.
[21] 邓椿. 画继[M].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
[22] 王淑娟. 从中国古代山水画看山水诗创作[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47-53.
[23] 岑参. 岑嘉州诗笺注[M]. 廖立,笺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4.
[24] 关鹏飞.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苏轼诗画论流变研究[J]. 社会科学论坛,2017(5):62-81.
[25] 苏轼. 苏轼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26] 杜绾. 云林石谱[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27] 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 苏轼资料汇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94.
[28] 方勺. 泊宅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29] 田晓菲. 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30] 苏辙. 苏辙集[M]. 陈宏天,高秀芳,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1990.
[31] 张志烈,张晓蕾. 苏轼选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32] 程千帆. 程千帆全集·读宋诗随笔[M]. 莫砺锋,编.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33] 周裕锴. 《沧浪诗话》的隐喻系统和诗学旨趣新论[J]. 文学遗产,2010(2):28-37.
[34] 曾枣庄,舒大刚. 三苏全书[M]. 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
[35] 于广杰. 北宋句图对“诗意画”发展之作用[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32-136.
Back-Feeding:TheMissingPartintheRelationshipBetweenLanguageandImage——OntheContributionofPaintingtoSuShi’sPoems
GUANPengfei
(CollegeofLiberalArts,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23,China)
In addition to literary influence on images, images also have a back-feeding effect on literature. TakeSuShifor example, he believes that paintings and poetry go together. His paintings have played three roles in his poetry. First of all, the picture in the painting can awaken the pictorial meaning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poetry. Secondly, the picture not only promotes the two-dimensional planarization ofSuShi’s poetic space, but also makes the poem and the picture echo each other in the picture. The poem draws from the division of the axis and the landscape perspective to present two ways of reading. Finally, poetry is influenced by the theory of painting. To be specific, the theory of painting hones the poet’s vision, strengthens the importance of poetry theories and illustrates the poetic phenomenon of poems supplemented with paintings. The feedback effect of images on literature is helpful for reexamining the Language-Image relationship .
language-image; poetry and painting; back-feeding;SuShi
10.19525/j.issn1008-407x.2018.01.016
I207
A
1008-407X(2018)01-0116-08
2016-11-02;
2017-03-06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后山诗注续补”(1540)
关鹏飞(1988-),男,浙江安吉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与文献研究,E-mail:bookgpf@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