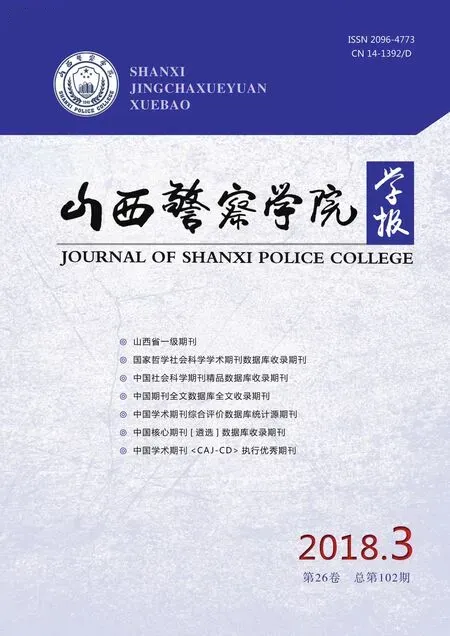韩非的犯罪预防思想研究
□郑 好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8)
犯罪是各种社会矛盾与弊病的综合症,由于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人口分布、人口素质、物质资料生产等方面的原因,犯罪现象还会在较长时期内存在。治理犯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即是以预防犯罪为主,以防患于未然,达到抑制犯罪、减少犯罪的目的。
我国古代文化传统灿若瑰宝,先秦诸子百家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其中不乏前人对犯罪预防所进行的探索、思考以及实践。韩非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家,吸收了儒、 墨 、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对于古代社会治理以及预防犯罪,《韩非子》一书以其独特的魅力提供了极为宝贵而又丰富的遗产。
一、“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韩非的整个犯罪预防体系建立在“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基础上,以他的方式做了一番严密的推理,“好利恶害”的人性不仅在一般人之间存在,即使具有骨肉亲情的父母与子女之间、夫妇之间、君臣之间也存在,甚至连古代圣人也概莫能外。
这就为其法治理论和犯罪预防找到了人性的根据。韩非认为人自私自利的本性是不可改变的,也无须改变,这本是人的一种“趋利避害”的自然属性,并无好坏对错之分。这种利害关系基于人的自然属性,与道德无关,在韩非看来,人的这种“趋利避害”的自然属性,并不需要作价值评判,“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1]人都会趋利避害,这是本能反应,所以去谴责一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既没有作用也没有必要。既然人都有好逸恶劳的心理,就应当因循人的本性,因势利导,用赏赐来引导人们的求利行为,用刑罚来禁止人们的犯罪行为。
在对当时社会现象和人性有着深刻认识的基础上,韩非对于预防犯罪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仅讨论其犯罪的社会预防、刑罚预防和犯罪控制。
二、社会预防
犯罪的社会预防理念贯穿着社会框架、治国理政的整体设计,是有关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各方面各领域的综合发展。韩非的社会预防理论,从宏观上对治国进行整体设计,涉及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多方面以建立一个犯罪消弭、秩序良好的社会。在韩非设计的社会预防框架中,经济上富国强兵,政治上君主高度集权,文化上实行思想控制,并用法律对社会资源力量进行有效整合,以社会的整体进步而带动犯罪率的降低。
(一)国家的富强与民众的贫困
韩非虽然在经济方面的目标是富国强兵,但这只是针对国家的富强;对于家庭及个人,韩非则主张保持民众适度的贫困,以遏止人的惰性,从而使人加倍努力,这样更有助于君主对下的控制。
韩非认为,人口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因而必然造成社会财富分配的危机,从而产生“人民众”与“货财寡”的矛盾以及“事力劳”与“供养薄”的矛盾。这两对矛盾发展的结果是“民争”,无疑给社会增添了潜在的不安因素。人多财少,资源有限,民众容易起争心,这是犯意萌生的原因之一,即“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2]700。所以犯罪预防一方面应从控制人口着手,另一方面应该增加社会财富,归根结底,应该使人口的增长与财富的增加相匹配。
韩非认识到了人口增长速度快于物质生产资料增长速度容易产生社会动乱,但是却坚决反对济贫政策。韩非以秦昭襄王不赈济灾民为例,而对此行为表示了肯定。秦昭襄王时发生了严重饥荒,应侯范雎向秦王请求发蔬果以赈灾活民,但秦王却认为救济灾民是“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3]508,坚持恪守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3]508。“夫生而乱,不如死而治”[3]508,在社稷的治理与国家的安定面前,与其让受救济的灾民活着使国家混乱,不如让他们死掉反而能使国家安定。
在韩非看来,除了极少数的圣贤外,普通民众的本性都是在财用充足后,容易奢侈懒惰。韩非严厉指出了这种“财用足而爱厚”所引起的恶果,但是却并不主张通过人人货财足用以缓解社会危机,反而认为民众所掌握的物质资料不尽然充沛,更有利于统治者的管控,“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4]663,最终为其重刑理论和赏罚手段服务。
(二)明主治吏不治民
“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3]516对于君主来说,对民众的统治必须通过官吏来进行,官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君主的利益,因而治吏比治民显得更加迫切、更加重要。而对于预防犯罪而言,通过治好官吏,君臣共同统治民众,使人民安居乐业,安于现状,不致于滋事犯罪。
关于治吏,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体。韩非认为,法、势、术都是人主治国的工具,法指法令,势指权势,术指统治策略和手段。韩非看到了三种政治现象之间的关系,同时对于处理三者关系提出自己的见解。韩非认为法、势、术都是君主不可缺少的工具,三者中法令最为重要,必须以法为本而兼顾势和术,将法置于势和术之上。
法、势、术的结合,突出显示了韩非“治吏”思想的特点,用严刑峻法和阴谋权术来维持君主的统治,无需君主亲自管控,通过治吏而治民,统治者按照一定标准选拔好官吏,管理好官吏,各级官吏逐级向下运作、管理较自己位阶更低一层次的人和物,以获得自己向更高位阶迈进的可能性。在这样一套完备的管理体系和管控的链条中,官吏为了向上的可能性,竭尽全力治理民众,而民众则各安其位,在被辖区内安居乐业,以达到官民共治,社会安定团结。
(三)“治民无常,唯法为治”
韩非认为法治胜于礼治、胜于任贤任智,法令的明确规定,使民众明白易知,民众畏惧法令,不敢以身试法,不致于为恶犯罪。
韩非认为,用法治预防犯罪有其必要性。法治胜于礼治德治、胜于任贤任智,更是国富兵强、国治民安的根本保障,且易于操作,行之有效,故需要实行法治以预防犯罪。韩非所说的“法”,应该是“编著之图籍”的成文法,由官府制定和颁布,并且需要广泛公布,使百姓明白易知,在民众心中产生震慑,具有公开性和强制性。
韩非认为法律是治国的工具,这种将以法治国作为君主治国的工具和手段,而非终极目标,是可以不断变化和调整的,因而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秦国厉行法治,发展强大,统一六国;秦始皇肆行专制,导致二世而亡。韩非的法律主义工具论历来受到诟病,古代的法律是皇帝的一家之法,是皇帝统治臣民的工具,目的在于防止民众犯上作乱,以达到维护统治的目标。
(四)思想文化控制
韩非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文化专制思想,主张毁弃一切文化典籍,取缔一切学术派别。“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2]714
民众学习知识的内容只限于朝廷的法令,看到的文字也只能是朝廷的法令。整个社会除文吏外,没有具备文字能力的人,人们要学习文字,只能向政府官员学习。政府官吏承担了教育行政官员和教师的职责。用法律教育和官吏控制将民众的思想高度统一起来。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秦代施行愚民政策,加强思想控制,巩固中央集权的标志之一。“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5]通过禁锢思想,加强专制统治,达到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目的。另一方面,民众通过知晓法律,知道什么是合法行为,什么是违法行为,也就有所趋避,民众不敢轻易犯法,官吏也不敢轻易违法。
从商鞅的“燔诗书而明法令”[6],到韩非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至秦焚书坑儒,极端的文化专制与统一思想,为秦朝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三、刑罚预防
刑罚预防的目的分为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一般预防是通过刑法的预告和执行,一般性地告诫人们不要去违法犯罪,否则会受到惩罚,从而预防一般人犯罪;特殊预防是对犯了罪的人适用刑罚,让其亲身感受到犯罪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并对其进行教育改造,防止再犯罪。[7]321
韩非思想中有关刑罚预防的理论,是建立在好利恶害的人性基础上,更偏重使用重刑进行一般预防。在法家看来,性恶虽是犯罪的根源,但同时也是防止犯罪的枢纽,既然人们事事都计较利害,那么法令刑罚就大有作为,尤其强调严刑重罚对于预防犯罪的功效,一是使人畏惧刑罚,二是使人们不愿意因小利而蒙大罪,三是使重罚可以起到儆戒作用。[8]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治道具矣。”[9]681在韩非看来,治理天下、预防犯罪需根据人性因势利导,在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基础上,提出了赏罚二柄作为预防犯罪的重要手段。
正是由于人性的趋利避害,故赏罚二柄可用,君主更需要牢牢掌握赏罚二柄。“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10]但此处的刑更多地偏重于罚,德也并非儒家所说的德治,而是以利为诱饵的奖赏。赏和罚是韩非赋予法最重要的内涵,也是韩非法治思想最基本的要点。
在韩非看来,无论尊卑贵贱,当信赏必罚,有功则赏,有过则罚。赏不可以不厚,罚不可以不重。“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2]707,与厚赏重罚相匹配的,还有“赏誉同轨,非诛俱行”[9]693。“有重罚者必有恶名,故民畏。罚,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则国治矣”[9]693,赏罚是社会行为的风向标,对民众的行为具有指引和规范作用。舆论的评价标准应当和法律的评价标准相一致,否则法律的权威性大打折扣,而且也不利于发挥赏罚的劝禁功效,即所谓“赏誉不当则民疑”[9]693,“赏者有诽焉,不足以劝;罚者有誉焉,不足以禁”[9]693。在用法律对犯罪行为进行赏罚规制的同时,韩非还注意到了社会舆论对于精神惩罚的作用,并指出了舆论的指向应当与法律的评价标准一致。
“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4]660-661韩非以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作为重刑的依据,轻罪重罚,民众获取的利益远不如惩罚所带来的损失,故计算利害得失,人民就不愿意以谋取小利而触犯律法。
他还批评了当时流行的轻刑止奸说,认为重刑才符合人们好利恶害的心理状态。“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4]660在他看来,人们对待周围的事物总是以利害相权衡的。如果犯罪行为所获得的利大,而因犯罪所受到的刑罚轻,那就无异于鼓励人们冒险犯罪违法;相反,如果犯罪行为所受到的刑罚大大超过所获得的利益,那么人们就不敢轻易违法犯罪了。
“且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贼,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韩非的重刑主义为一般预防,希望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通过刑罚威慑力的必然性,震慑普通民众,即所谓“以刑去刑”[11]。
韩非的重刑主义不能不使人警惕。秦国采商鞅之法而富国强兵,统一东方六国。而秦朝统治者采用韩非之思想,将重刑政策发展到摒弃礼义教化,单纯依靠苛法严刑“经纬天下”。秦朝灭亡的原因很多,不能一概认为只是专任刑罚的后果,但秦帝国顷刻覆灭确实和极端重刑主义有莫大的关联。为何采商鞅之法而胜,采韩非之法而败,这可能跟贾谊所说的“攻守之势异也”有关,秦国所辖区域毕竟有限,而统一六国以后的秦朝辖区已变为幅员辽阔的全国疆域,在较小范围内推行重刑主义和全国范围内推行重刑自然效果不同。极端的重刑不仅不能预防犯罪,反而会助长更严重的犯罪行为。所以,犯罪的刑罚预防不应一概而论,不同的犯罪当有不同的惩处,“刑罚对犯罪的预防作用是受一定条件、一定范围、一定对象限制的”[7]323。
四、犯罪控制
犯罪控制,又叫犯罪的治安预防,需要依赖专门的社会控制力量来进行,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是对特定的人、特定的行为、特定的场所或特定的行业实施的预防性措施”[7]294。
韩非以维护统治为出发点,特别指出了君主需要重点防控和清除的对象,如五蠹和八奸。
韩非认为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刺客)、患御者(逃避兵役的人)是五种危害国家的蛀虫,“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侔农夫之利”。[2]722韩非认为这五种人都是破坏法治、妨碍耕战,对君主有害的人,必须作为重点防控对象,坚决予以铲除。
君主需要重点控制的犯罪对象除了五蠹以外,还有八奸。八奸主要是指在君主身边容易对君主的统治造成威胁的人,也指篡夺君权的八种手段,“凡人臣之所道成奸者有八术:一曰同床,二曰在旁,三曰父兄,四曰养殃,五曰民萌,六曰流行,七曰威强,八曰四方。”[12]70-80“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奸,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12]71-72因此在预防犯罪方面,君主尤其要把这八种人作为重点的控制和预防对象,避免被他们所利用,以致位失身死。[13]
围绕防奸的中心议题,韩非进一步强调了“进贤材劝有功”[12]75的必要性。用人标准不统一很容易引起犯罪,依法统一用人标准,避免了人性的缺点在选任过程中的负面影响,在全社会树立起规则意识,犯罪现象必然也会减少,形成良性循环,以此消除五蠹和八奸成长的环境。
五、对韩非犯罪预防思想的反思
趋利避害的人性论是韩非预防犯罪理论的基点,正因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因此预防犯罪,也应根据人的秉性,因势利导,最先是能禁止其作恶的心,变自利心为互利心,争取双赢。韩非认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未免有失偏颇,古往今来,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涌现出了很多舍生取义、公而忘私的英雄人物,他们不计名利、不计报酬,为人民的幸福抛头颅、洒热血。
韩非关于社会治理、犯罪预防的措施具有他那个时代所独有的特色,确实在一定时期对社会稳定内取得了显著成效,很多措施为后世所沿用。
韩非认识到了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会产生社会危机,但是仍然主张保持民众适度的贫困。因为在他看来,这样反而更有利于统治者的管控。为了使赏罚得当,反对济贫赈灾,即使灾民因为得不到救济而死去也不为所动。为了坚持信赏必罚,竟然罔顾生命,这可能也是秦失民心的原因之一。
韩非的法治理念,是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最终目的的,而最高统治者并不受所谓“刑无等级”的约束,这既是韩非受立场所限制,也是向帝王兜售自己思想的保障和前提。对于古代社会治理犯罪,有法可依,如何使法适应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状况,在法的稳固性和灵活性之间如何寻求平衡,韩非的法治理论应当说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韩非看来,无论尊卑贵贱,信赏必罚,有功则赏,有过则罚,不可滥赏滥罚,更不可偷赏赦罚,这些理念直至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
韩非的犯罪预防思想既着眼于社会的整体设计、综合为治,又结合了战国所处的时代特色、个体差异,其关于犯罪的社会预防、刑罚预防和犯罪控制,在前人的基础上,可视为“既有心理层次的威慑、防范、诱导、亲和等等,也有理性层次的认知,行为层次的自律、自治”[14]。在韩非所处的战国时代,对于某一个国家而言,这些措施确实有短期见效的成果,但是当秦王朝统一全国以后,各方面的形势、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仍然固守不知变通,便犹如韩非所说的“守株待兔”了。
根据现代犯罪学理论,按照犯罪预防措施的作用水平,犯罪预防可以划分为社会预防、心理预防、治安预防(又叫犯罪控制)和刑罚预防四个层次和环节。[7]266在韩非所处的时代,虽无现代犯罪学的理论,但其关于犯罪预防的理论已初具规模。在韩非的犯罪预防体系中,唯独缺少了心理预防。需要指出的是,犯罪的心理预防主要是指“对健全人格的社会培养和个体的修养过程”[7]266,在古代社会很难有健全人格的培养,即使是儒家也只是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其与现代意义上的健全人格并不相同。儒家对秦朝短暂而亡的探讨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韩非犯罪预防理论中心理预防的缺失。秦朝灭亡的教训让后世儒家注意到了专任刑罚而忽视德治的危害,劝善是预防犯罪于先,刑罚是惩治犯罪于已然之后。法律不可能调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依法治国的同时,以德治国是不可或缺的,很多法律触及不到的层面,则需要用道德或者社会舆论的力量,只是法治与德治应有所侧重,而不应一概而论孰轻孰重。所以,在犯罪预防方面,法治与德治应当结合起来,既充分发挥儒家德治的作用,也采用法家法治的思路。
《韩非子》一书,虽是两千多年前的作品,但是现在读来,仍有很多可资借鉴之处,特别是在预防犯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方法和思路,仍然有很多积极的因素,扬长避短,方能从传统法律文化中吸取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