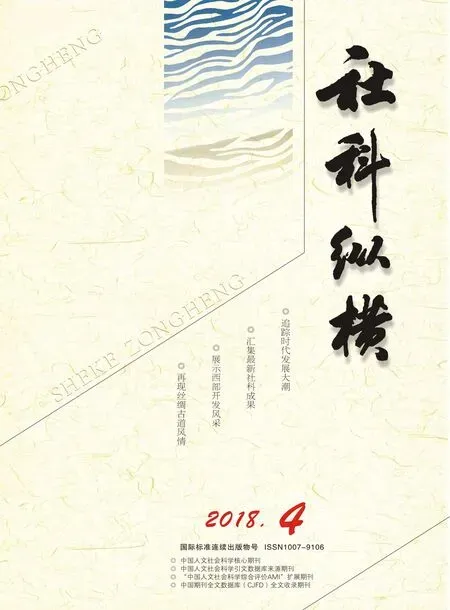试论葛兰西实践哲学的当代意义
吕连凤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早年较早离家求学,又因生活困顿而饱受饥饿与寒冷之苦,但这却磨砺出他坚忍的性格和不屈的意志,使得他日后从事性命不保的革命工作和历经十年监狱之苦并写下不朽名著《狱中札记》成为可能。“实践哲学”是葛兰西在狱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特殊称谓,以此来逃避监狱检查。我们认为,他的“实践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无异,是对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的进一步阐发与深化。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旨在“改变世界”,实现人类的最终解放,葛兰西遵循马克思所开辟的方向与道路,将理论付诸实践,他指出,“实际上,对实践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1](P75)因此,实践哲学就是“行动的哲学”[2](P58)。
一、实践哲学:政治行动的纲领与前提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实践哲学与现代文化”中高屋建瓴地指出了实践哲学的两项任务:一是战胜最精微的现代意识形态,以便能够组成自己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二是教育在文化上还处于“中世纪”的人民大众[2](P74)。这是基于理论与实践、哲学与政治相统一的原则所作出的理论阐发,是他的“实践哲学”的理论宗旨。两项任务相比,葛兰西认为第二项更基本、更重要,“新哲学”的性质恰恰在于不仅从数量上,而且也从质量上吸收全部力量,毕竟“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P9)。
其实葛兰西在《狱中札记》“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开篇首先就提到了这“两项任务”的实现前提,他说:“批判自己的世界观就是要使它具有一致和一贯性,把它提到世界最先进的思想界已经达到的那个高度。因而,这也是批判所有以前的哲学,因为所有以前的哲学在民间哲学里留下了坚固的冲击层。”[2](P7)这段话有两层含义,是对“两项任务”的具体阐释。含义一,葛兰西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评”的原则基础和本质精神,力图将实践哲学提高到“最先进的思想界”所达到的高度。“如果实践哲学在理论上断言任何认作永恒和绝对的真理都具有实践的来源,并代表着暂时的价值(任何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历史性),那么,在实践上很难理解这种观点不适用于实践哲学本身。”[3]这契合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的”、“革命的”本性,这也是“战胜最精微的现代意识形态”,从而“能够组成自己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的前提和基础。含义二,葛兰西指出了“批判”的具体途径,即对以往的哲学进行“清算”,以剔除其在民间哲学里留下的“坚固冲击层”,除去人民大众头脑中的顽固的、腐朽的意识形态残渣,这样才能使新哲学“社会化”成为可能,也才能够“教育在文化上还处于中世纪的人民大众”。如同他在1927年3月19日写给塔吉娅娜的信中所说的,在他所要研究的、杂多的哲学题目中贯穿着一条红线,即人民的创造精神,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样是这些题目的基础[4](P55)。我们认为,“实践哲学”最终关注的也是马克思所关注的,那就是“人”的问题、人类解放问题。
那么,什么是实践哲学呢?“实践哲学”这一概念是葛兰西从意大利共产主义先驱拉布里奥拉那里直接拿过来的,在那里,“实践哲学”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称呼;而且,葛兰西给实践哲学所下的定义,也是借用了拉布里奥拉的思想,即把实践哲学看作是一种创造性的、独创性的理论,看作是一种“新世界观”,它是一种自足的理论,本身具有继续发展的因素。
这种“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葛兰西称之为“绝对的历史主义”或“绝对的人道主义”,是“整体的世界观”。在《实践哲学》中,葛兰西提醒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应该强调的是第一个术语“历史”,而不是第二个词。实践哲学是绝对的历史主义,是绝对的思想世俗化和尘世化,是绝对的历史人道主义[5](P161)。在1930年2月10日写给妻子朱丽娅的信中又指出,萨尔韦奥利接受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以经过克罗齐修正的在意大利所具有的形式来接受的,即作为历史研究的实际标准,而不是作为整体的世界观。(这与孙正聿教授的观点惊人的相似,他在相关文章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是新世界观。)在1930年12月1日写给塔吉娅娜的信中,葛兰西针对克罗齐所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类似中世纪神学哲学的哲学立场、“经济结构”是“无名的上帝”的隐喻的观点时指出,克罗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如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路德的宗教改革立场:“路德进入哪儿,哪儿文明即失”(伊拉斯谟语)[4](P284)。葛兰西一针见血地指出,克罗齐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路德和宗教改革是包括他本人的哲学在内的全部近代哲学和文明的开端。如果说中世纪的人们没能理解,像路德宗教改革那样一场伟大的思想和道德革新运动因深入人民群众而具有粗俗、甚至迷信的形式不可避免能够被人接受,则像克罗齐这样当代最大的知识分子居然无法认清历史唯物主义的真面目,则让人惊奇并产生疑问了。在《克罗齐是文艺复兴的最后一个代表》中,葛兰西深刻地指出,克罗齐哲学“过分知识分子化,过分属于文艺复兴的典型,因此无法被人民大众所接受”。葛兰西看到,克罗齐的哲学仍旧是思辨的唯心主义哲学,是“现代空想的哲学”[2](P40),对现实的改造丝毫不起作用,“克罗齐与之更为一致的是黑格尔而不是马克思。”[6](P19)
沃尔什说过,马克思的目的不在于建立一种思想上严密无瑕的理论,而在于为政治行动提供一种有效的基础[7](P165)。这话同样适用于葛兰西。《狱中札记》庞杂而隐晦,但其宗旨却是一以贯之的,即通过对克罗齐等以往思想的批判与“清算”,通过对“实践哲学”“两项任务”的研究与阐发,为夺取领导权、实现人类最终解放的政治行动准备纲领和前提。
二、人类解放:实践哲学的目标
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使“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8](P335)。与德国古典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P72),是“现实中的个人”,这种“现实的人”既不是通过“理性思维”,也不是通过“感性直观”得到的,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P73)葛兰西遵循马克思的思想,认为马克思给“人”下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定义是最为精确的定义,他说:“不能把人设想为别的,而只能设想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2](P37),葛兰西反对天主教把“人”看作是对先天本性的实现及受限制的个体,认为必须把人作为许多积极的关系(作为一个过程)来考察,指出“人”的概念包含着形成的观念:人在形成。人在不断地改造外部世界,改造社会关系,从而改变着自身,加强着自身,发展着自身,从而使“人类解放”成为可能。
与把“人”从词句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聪明的哲学家”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只有在现实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1](P74),“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1](P87)在资产阶级社会这个“现实世界”里,葛兰西认为,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横暴掠夺,而生活于社会中的活动着的个人却受到严重的异化而失去了独立性和个性,因而要想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类的“独立性”和“个性”,实现人类解放,那么,“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就是,必须对资本加以限制,消灭雇佣劳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用新的历史形式再次将因异化而遭破坏的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原始统一恢复过来,使人类回归以实践为基础,以全面的人为指向的现实生活,从而实现“对人的本身的真正占有”。
诚然,人类解放不是一件易事,但它绝不是乌托邦!“社会主义不是在某一特定的日子建立起来的——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是一个向着由大多数公民(即无产阶级)组织和控制的自由王国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9](P33)马克思指出,“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1](P12)因为“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10](P105)德国工人阶级有能力接受新哲学、新世界观,并最终实现自身的解放。葛兰西通过“对意大利复兴时期历史的解释”断言,“辩证地继续意大利传统的是劳动者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传统的公民和传统的知识分子。”[2](P312)这是对恩格斯的“德国工人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的发扬。
总之,葛兰西认为,“我们的活动始终是政治的活动”[2](P9),哲学与政治是无法分开的,哲学也就是政治;他“厌恶克罗齐拒绝像他那样承认哲学必须也必然导致政治行动的看法”[6](P20),这契合了马克思的思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哲学既是“政治的哲学”,也是“哲学的政治”,是哲学与政治的完美联姻,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和发展。葛兰西指出,世界历史就是由人们为把自己从特权、偏见和偶像崇拜中解放出来所作的一系列努力,并且,“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1](P89)。在这种“现实的运动”中,人们要想真实地面对生活,就必须“忠实于生活,所有的行动都面向生活,将全部精力都真诚无私地献给生活”,“去确实地体验历史的真实”[11](P13)。
三、葛兰西实践哲学的当代意义
葛兰西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卓越继承者,他的思想直到今天仍然闪烁着夺目的光芒,让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刮目相看。路易·阿尔都塞认为,真正试图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能让他想起来的只能是葛兰西。纵观葛兰西哲学思想,我们认为,他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思想宝藏,并为我们指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所应遵循的视轨和方向。
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在于它超越了先前的哲学,并且首先在于它开辟了一条“从头到脚地更新了整个设想哲学本身的方式”的“新路”[5](P161)。葛兰西看到了思想本有的不同的视轨和方向,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所在,为我们坚持和体认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变革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葛兰西走近马克思,但又不拘泥于此,而是基于意大利的现实国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知识分子等理论,不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的理解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马克思本人在写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就俄国革命道路问题时曾告诫人们,绝不要妄想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的钥匙”去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说:“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8](P342)我国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的“攻坚”阶段,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我们不断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营养,“实事求是”地处理好各种矛盾,在此,葛兰西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
有人把葛兰西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就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相应影响来看,确实如此;但他毕竟不同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连英国“新左派”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都认为,葛兰西与那些闭口不谈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传统最核心问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他是属于对经典遗产作出解释的那一类人,是“唯一的例外”[12](P61)。也许是葛兰西的这种“例外”吸引了阿尔都塞,在“列宁和哲学”一文中,阿尔都塞便把哲学定义为“理论中的政治”;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他认为,“经过同旧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了激烈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之后,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教育的国家机器”[13](P343),这是可看作是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深化和发展。我们认为,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受益于葛兰西,在此意义上,他无愧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称号。
葛兰西正确地指出:“马克思是一个历史时代的精神的创始人,这个时代大概要延长几个世纪,也就是一直到政治社会消灭和调整了的社会建立为止。只有到那时候他的世界观才会被超越(必然性观念被自由观念超越)。”[2](P66)这反驳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增强了我们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和力量。对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葛兰西哲学,我们认为,借用他在《历史》一文中的一句话来评价再恰切不过:“它照亮我们,而不是遮蔽我们。”[11](P14)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意]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转引自田时纲.简论葛兰西领导权理论[J].哲学研究,2001(5).
[4][意]葛兰西.狱中书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意]葛兰西.实践哲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6][英]詹·约尔.郝其睿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7][英]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意]葛兰西.葛兰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意]葛兰西.葛兰西狱前著作选[M].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影印本).北京: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2003.
[12][英]佩里·安德森.高銛等译.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3][法]阿尔都塞.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2003.
[14][英]戴维·麦克莱伦.李智译.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