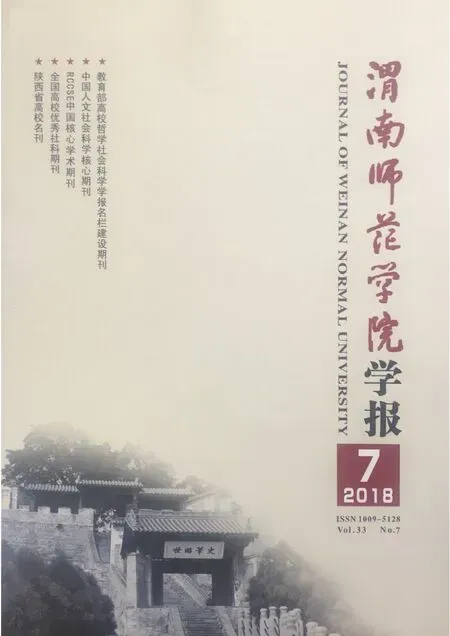堕落的乡村知识群体
——论鲁迅对传统乡土社会文化生态恶化的精神焦虑
晏 洁
(海南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 海口 571158)
从鲁迅的文学创作来看,他的小说在整体作品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呐喊》和《彷徨》一共收录了20篇,但是其中涉及乡村知识者的就有13篇,如《孔乙己》《阿Q正传》《肥皂》等。在这13篇作品中的乡村知识者形象呈现一种绝对的两极对立现象——非恶即疯或死,或出走,也可以说,能够留存并立足于传统乡村的知识者都非真正或正常意义上的知识者,他们依靠的是知识以外的恶名与权势。反之,知识者就无法在乡村社会生存下去,其结果都以悲剧告终。
那么这些两极反差的知识者形象承载了鲁迅对于中国文化和传统的现状以及前景怎样的看法,另外鲁迅究竟出于怎样的心态会如此选择性书写乡村知识群体呢?我们将从两个方面,即小说中知识者的表层形象的书写和各知识者文化内涵的潜在对话来探究其中蕴含的深刻思想。
一、对乡村知识者言行举止的表层书写
首先对“乡村知识者”范围进行概念界定。乡村知识者,顾名思义是乡村中接受过文化教育的人,就中国传统乡土社会而言,所能接受的文化教育就是儒学教育,从这一角度来说,乡村知识者也可以称之为儒生。在中国古代,他们是处于四民之首的“士”这一阶层,也是社会的精英阶层,科举制度也使他们成了一个流动的阶层。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傅斯年与傅衣凌有着类似的表达,前者认为是“上级的社会和下级的社会,差不多可以说是不接触,上级社会的政治法律礼俗等,影响不到下级社会;下级社会有他们自治的办法”[1]351,后者认为是有“公”与“私”对立的两个系统,在上和下、公与私之间,要实现控制与被控制、统治与被统治的目的,必须且也“只能由一个双重社会身份的阶层来完成”[2]。因此,儒生这个可上可下的知识群体便成了重要的中间阶层。学者艾尔曼认为在中国的1400—1900年间,真正通过科举入仕的儒生“只占5%”,“剩下的95%的儒生回到了基层社会中”,“传统的知识体系,出产的不仅是几千名熟读经籍的官员,还有数百万计的识文断字的人”[3],而这其中的一部分便成为掌控地方的文化阶层——乡绅。本质上为儒生的乡绅,“在乡村社会中,作为唯一的知识分子阶层”,“是社会规范的解释者和文字的传播者,教化和教育是赋予他们的最基本任务”[4]。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鲁迅小说中的乡村正在经历新旧思想冲突、处于社会转型与裂变时期的乡村,乡村权力虽然仍由名义上的乡绅把持,但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儒生已经不再是乡绅群体的唯一来源,不过他们仍然算是乡村中的知识阶层。另外,由于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使接受文化教育的方式和内容发生了部分改变,乡村中的知识阶层不再仅限于以儒学为唯一知识来源的儒生,新学与留学成为其知识结构的组成部分。社会转型和文化多元化为乡村知识者带来的知识来源与身份的变化,也反映在鲁迅的作品中,因此鲁迅小说中的知识者形象除了儒生,还有以儒学为底蕴的新式知识分子。从具备文化知识这一角度,我们将他们个体概括为“乡村知识者”,如果从整体上来说,即是乡村知识群体。
鲁迅小说里的乡村知识群体书写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这个群体呈两极绝对的对立状况,一极是掌握乡村权势的乡绅阶层与进城的儒生,另一极则是未能成为乡绅的旧儒生和介入新旧之间的知识者。在13篇关于乡村知识者的小说中,涉及前者形象的共计有9篇,这反映出鲁迅对于乡村文化生态中乡绅影响力的重视,那么鲁迅对于后者的书写,除了是对乡村知识者形象的补充,也是对前者在乡村社会与文化威权影响的一个反衬,更加全面地表达了鲁迅对于新旧之变中乡村文化环境恶化的焦虑。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将乡绅作为考察的主要对象,从而了解鲁迅是如何通过乡绅形象,阐释自己对于传统乡土社会转型时期文化衰落的忧虑意识。
在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明清以后,在“权力的毛细管”系统中,乡绅是控制与维持地方的重要力量。“乡绅”的来源在于科举,而科举的根本是儒学,因此从理论上来说,乡绅都是儒生,是那部分通过科举入仕后退隐,或者获得某一级别的功名,以此留在地方获取相应的社会权力地位的。所以,乡绅不仅是儒生,还必须是儒生中的精英,因为儒学这种“高尚的文化注定要由谦恭俭让的儒者来宣扬”[5]5可以说,乡绅的社会权力地位是与其儒学的学识修养成正比的,也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但是鲁迅小说中的乡绅所必备的这两种因素却发生了距离极大的分离。
首先来看乡绅与其儒学背景不相符合的言行举止。在《论语·为政篇第二》中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6]11,讲的就是须以德治民,尽管这个“德”包含了很多内容,但是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应当就是仁与善。在《孔乙己》中,有一个未出场的乡绅——丁举人。根据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制度,举人是考中乡试的生员,“各省乡试中额的规定,录科人数则依一定的比倍加倍,大抵三十比一”[7]22,也就是中举的比例差不多是3%,因此能够中得举人,已是儒生中的佼佼者。但是这个丁举人使乡民们甘愿俯首帖耳的原因,从小说中透露出来的信息看,并非因为其深得儒学精神而“德高望重”。乡民确实都“服”他,但是这个“服”却是从“怕”而来的,因此这样以绝对的权势造成的“服”实际上是“压”,乡民只能是不得不服、不敢不服。鲁迅对他没有正面描写,只有寥寥几语,用乡民的一句经验之谈,“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其潜台词便是,丁家的权势高高在上,不能惹更加不敢惹,一旦触怒丁家,后果不堪设想。可见这位丁举人闻名鲁镇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平常待人的刻薄凶狠,而不是儒生应有的“仁”。被打断双腿的孔乙己最终在穷途末路中死去,为丁举人的残暴纪录又添上了新的一笔。以儒学取得的社会地位、与儒学背道而驰的凶残行为,两种根本对立的事物却并不矛盾地存在于丁举人身上,让人深思:教人向善的儒学除了成为获取功名的工具之外,已无其他作用。丁举人以儒生之名做着实质上反儒学的行为,不能不说是儒学的悲哀。
《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一位秀才之父,只是因为被“喝了两碗黄酒”就胡说八道的阿Q说与自己同姓,还比秀才长三辈的话激怒之后,瞬间忘记了文人“动口不动手”的规则,而是“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还禁止阿Q姓赵,“你哪里配姓赵”[8]513。阿Q的话确实冒犯在先,但是赵太爷打骂之后,地保和其他乡民对此的反应却都是责怪阿Q自己招打,充分显示了赵太爷在未庄一贯的横行霸道,已经让未庄居民有了经验,知道说什么或者做什么可能会激怒赵太爷。在阿Q与吴妈发生“恋爱悲剧”之后,赵秀才不问青红皂白便拿着一支大竹杠打阿Q,嘴里还骂着“忘八蛋”。赵秀才的“竹杠”不仅打了阿Q的身体,还将阿Q所有的财物敲诈得空无一物,连阿Q的一件破布衫也不放过,“大半做了少奶奶八月间生下来的孩子的衬尿布,那小半破烂的便都做了吴妈的鞋底”[8]528。可见赵秀才家的威信与丁举人一样,是靠“打”威吓出来的。
《肥皂》里的四铭并不处于乡村,但是却和乡绅有着同样的儒学背景,他口头上对新文化进行诋毁,看不惯旧道德的沦丧,但是私底下却对年轻乞丐女被污垢覆盖的身体产生了某种想象,他千方百计遮掩的心思结果被太太一眼看穿,无地自容。在《论语·季氏》中,孔子于庭中训诫儿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但是口头上大骂新学堂和新文化、一心呼唤旧道德的四铭对儿子的庭训是每天昼夜之交“在墙角落上练习八卦拳”[9]53。在《肥皂》里除了四铭,还有一个旧文人何道统,其名也是相当有深意。“道统”一般指儒家之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10]172。余英时认为,作为概括儒家精神的“道”,“是没有组织的,‘道’的尊严完全要靠它的承担者——士——本身来彰显”[11]91。何道统一开始确如其名,拟了一个尽可能长、但又不必多广告费的字数范围内的“专重圣经崇祀孟母以挽颓风而存国粹文”的题目,剩下的两句话便是“哈哈哈!两块肥皂!”“你买”“洗一洗,咯支……唏唏……”,言语之间无比轻佻,与他所拟的那个严肃题目之间形成了绝佳的对比。四铭和卜薇园两个人的对话也全部围绕着那个年轻的乞讨女、肥皂和身体。这三个人的表现,正是鲁迅将“道统”的名字上加上“何”姓——“何有道统”之意。一个街边的乞丐女引发了三个儒生无尽的遐想,在这个以肥皂为线索的故事中,“有一个精妙的象征,女乞丐的肮脏破烂衣裳,和四铭想象中她洗净了赤裸身体,一方面代表四铭表面上的破旧的道学正统,另一方面代表四铭受不住而做的贪淫的白日梦”[12]39。
《离婚》里的慰老爷和七大人,应该是爱姑口中所说的“知书识礼”“什么都知道”、可以主持公道的乡绅。但事实恰恰相反,连爱姑都知道,这桩离婚案自己丈夫理亏,所以打官司也不怕,一定要告到底。可一脸庄严、看似博古通今的七大人,奉行的却是根本没有是非观念的“和气生财”,添了十块钱的“天外道理”,便糊里糊涂地结束了这场离婚。《高老夫子》里的高尔础,发表了一篇《论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史之义务》的文章,便做了贤良女学校的历史教员,但实际上“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根本没有真才实学,以至于在讲台上惶恐不安、语无伦次,在学生的嘲笑声中狼狈逃出了教室。
上述鲁迅小说中的乡绅或进城的儒生,无论在乡或者离乡的,其言行与一个儒学精英本应体现的相去甚远,背离了作为一个儒学精神继承者的身份以及这个身份所应背负的思想与责任。乡绅在权力上掌控着乡村,但是已失去传统意义上“绅”的合法性,无法再继续维持乡村的儒家道德和伦理传统;另外将儒学作为谋生手段的进城儒生,如四铭或高尔础之流,与留守乡间的乡绅不同,他们处于新旧之间,但并无儒学的文化包袱,旧文化也只在放在嘴边说说而已,以“混”的姿态展现了儒生的另一种面貌。
二、与乡村知识者文化内涵的潜在对话
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来说,言行是人物形象的外在表现,应该符合一定的规则和逻辑,即言行必定受内在思维、身份等因素的控制或影响,就像鲁迅自己所言,“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波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13]208,但是这种煤油大王捡煤渣、灾民种兰花的反差却在鲁迅小说里对乡绅和儒生的形象书写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传统乡土社会里,可以称得上是社会精英的儒生群体,在鲁迅的笔下却表现出与其本应具备的知识背景与身份极不相符的言行举止——残暴、油滑、卑劣。我们不禁要追问,这种形象书写的逻辑与合理性何在呢?从小说表层叙事来看,似乎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当我们绕行到文本中那些看似平常的细节背后,发现作者与乡村儒生群体的文化内涵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知识结构对话的潜在叙事,这种对话关系的存在揭示了儒生群体行为呈现的内在逻辑性——知识背景决定言行,鲁迅更通过这种潜在的对话方式隐约表达了传统乡土社会文化精神的劣化趋势、面临断裂现状的担忧。
在鲁迅关于乡村知识群体的小说中,除了《狂人日记》《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和《祝福》中,有作为新式知识者身份出现的第一人称“我”的叙事参与外,其他有8篇都是以全知视角进行叙述的。在这8篇里,作者以一种隐身的方式,对乡绅或进城的儒生进行了知识对话。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是一面启蒙的旗帜,以至于后世“无论如何穿透历史,还原现场,‘启蒙’是大家都能接受的鲁迅研究的逻辑起点”[14]。但同时,我们不能忽略的是鲁迅对于传统文化实际上用力颇深,学养深厚。例如在《这个与那个》中,鲁迅说起让“现在中西的学者们”一听名字就“魂不附体,膝盖总要软下来似的”《钦定四库全书》,可是在鲁迅看来并不以为然,不过就是“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添加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15]148,能够看出错字的更正、文章的删改,可见鲁迅对让中西学者顶礼膜拜的《钦定四库全书》有多么熟悉。在鲁迅的作品中,古代的各种典籍、典故,有些还不乏生僻,也是随手拈来,因此看似鲁迅在字里行间都是反传统,但是事实上在他那里,传统与启蒙是不相排斥的,正如夏济安说:“他虽极力反对旧书、旧中国,但不时也能全心全意地沉浸在中国旧诗的晦涩与传统里,因袭古代士大夫的文化,在社会巨变和政治革命的时代里求得一点心灵的慰藉。”[16]132在鲁迅如此强大的旧学背景下,那些留守乡村的乡绅与进城投机的儒生在儒学知识上的伪装就被彻底撕开。
《风波》里的赵七爷用类似于精神暴力的方式让七斤一家乃至整个村庄提心吊胆,天天猜度会不会祸从天降。赵七爷之所以具备对乡民实施精神暴力的资格,原因在于他“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表面上看,赵七爷的“财”与“才”让乡民心悦诚服,他以“学问家”的身份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与意见,也足以令乡民奉为行动指南。可是再一细看,赵七爷成为村庄文化权威所凭借的“学问”是相当可疑的,“他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他不但能说出五虎将姓名,甚而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和马超表字孟起”[8]494,而代表读书人身份的长衫,赵七爷也只是在仇家遭殃时才穿来表示自己的胜利。从此处可以推断,赵七爷这个乡绅根本不是真正的儒生,尽管他的识字发蒙绝对是以儒家经典开始的,但是他如数家珍的只是一部《三国志》,用来吓唬乡民的也是“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谁能抵挡他”[8]497,可见赵七爷对时局的无知程度与乡民一般。
与赵七爷的言谈间不离《三国志》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小说一开始,高尔础正在为上课而烦恼,因为新式历史教科书与他所熟知的《袁了凡纲鉴》有诸多不相符的地方,这让他既无从理解,也无所适从。那么让高老夫子奉为圭臬的《袁了凡纲鉴》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纲鉴”类史书在明代隆万年间兴起盛行,是将《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合在一起,便于“最为快捷有效地阅读这两部史书”,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适应科举考试”[17]的需要。而此本纲鉴的编纂者袁了凡,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准备科举或者进行科举上,他从“考中秀才是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18]至“万历十四年(丙戌)及第,被任命为宝坻知县”[19],这个从秀才到进士的过程整整36年,科举经验的丰富与科举之途的坎坷,使袁了凡中举后致力于科举参考书的编纂,这本《袁了凡纲鉴》就是其中之一。这也说明,这本高老夫子引为标准的历史书,实际上只是一本简明扼要、普及常识的考试用书,并且在已经废除了科举制度的时代里,这本书的价值也不复存在。但是高老夫子只接受《袁了凡纲鉴》里的历史,埋怨新版教科书与之“若即若离,令人不知道讲起来应该怎样拉在一处”,除此之外,高老夫子还对前任教员相当不满,原因在于那个人先于他讲完了三国,让他感到十分遗憾,“他最熟悉的就是三国,例如桃园三结义,孔明借箭,三气周瑜……”,那些故事,“满肚子都是,一学期也许讲不完”[9]76-77。可见高老夫子对于三国的历史也仅止于那些似是而非的故事,因此对于贤良女校的历史课,他感到十分吃力,或者是没有知识能力,或者出于内心排斥新知识。鲁迅在小说中反复提到高老夫子对《袁了凡纲鉴》念念不忘,以此表现高老夫子知识结构的陈旧狭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对“旧人”,竟然追逐时髦,将名字特意改为与俄国作家高尔基相似的“高尔础”,而这个新名字又显示出高老夫子对于新文化的一窍不通。
《祝福》里的鲁四老爷,他是一位老监生,如不深究,我们从这一身份可以推导出鲁四老爷应该具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因为在清代,官员培养与选择体系中,监生是其来源之一,与贡生一样是进入到北京国子监子里读书的学生,学习期满肄业可以“直接入仕”[20]。但是在清代除了科举、国子监这样正途入仕的方式之外,还存在捐纳制度,特别是在清后期,捐纳越发泛滥,就成了不过是花钱买一种身份,根本没有真正入仕的机会。从鲁四老爷久居乡里,已是一位老监生的情况来看,他的监生身份应是捐纳而来。这一点在鲁迅杂文里可以得到证实,“先前的‘士人’‘上等人’自居的”,“清朝时该去考秀才,捐监生”[15]109,捐纳制度使儒生身份获取容易,进而泛滥,鲁迅显然看不起这种用钱买功名、名不副实的伪儒生。在身份说明之后对鲁四老爷书房的细微描写,更是直接揭示了其知识构成的浅薄。书房的案头上有三种书,“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9]6。根据《辞海》中《康熙字典》的释义可知:“字书。四十二卷。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印行”,但是“此书音切、释义,杂糅罗列,漫无标准;疏漏和错误甚多”,因此“道光年间王引之订正重刊,改正引用书籍字句讹误者2588条”,“王力《康熙字典音读订误》订正5200余字音读注释之误”[21]1220。一般说来,认字是知识积累的开始,鲁四老爷使用这本谬误多不胜数的《康熙字典》作为标准去获取知识、理解文化,必定也不是准确的,而是以讹传讹,离真义越来越远。小说中还特别提到了鲁四老爷的这本字典已经缺页少字、残缺不全,就更加的不可靠了。其他两部《近思录集注》和《四书衬》,也并非儒学原典。《近思录集注》是指清代江永对《近思录》所进行的集解笺注,而《近思录》一书则是由朱熹、吕祖谦所编,是“北宋新儒学的入门之作”[22]“理学入门基础读物”[23]。《近思录》是理学基础性读物,这一特点决定了《近思录集注》的内容深浅程度以及编纂的目的,作者江永在《自序》中也说:“此录既为四子之阶梯,则此注又当为此录之牡钥,开扃发鐍,袪疑释蔽,于读者不无小补。”[24]2因此这只是一本普及性的理学知识读本。鲁四老爷书桌上的另一本《四书衬》,是清代骆培所撰,此书“言本于《朱子章句集注》以及《朱子或问》、《朱子语类》,佐之于先儒之粹言,以成此编。对四声句读,尤详加校正。其书融合经注,成为一片,着语无多,条理分晰,对课举业者,不无裨益”[25]606,可见《四书衬》和《近思录集注》一样,也是一本主要用于科举考试的参考书。这两本理学基础读物与那本谬误百出、残缺不全的《康熙字典》堆在一起,基本就反映出了鲁四老爷的监生确实只是捐来的一个身份而已。而“我”发现了书桌上的《康熙字典》缺页不全,显然只有阅读并且熟悉《康熙字典》才能一眼看出其不全,而在看到另外两本《近思录集注》与《四书衬》后,“我”下了决心,“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9]6。小说中并未说明这两本究竟是什么书,但是“我”一看书名,已然明白这只是浅近的儒学入门读物和科举参考书,实在不愿意、也不屑与装腔作势的鲁四老爷继续尴尬的对话,因为后者的儒学水平与“我”显然不在一个层次。“我”的儒学知识是作者所赋予的,有理由相信“我”对鲁四老爷的态度,实际上就是鲁迅对于此类有身份无实学的乡绅的态度。
从鲁迅与文本中的乡绅或儒生之间进行的这种潜在知识对话中,可以看到,鲁迅通过反映出这样的一种现象,即在清末民初的乡村社会中,儒学已经沦为一种身份的装饰,无论是留守乡绅,还是进城儒生,他们都不具备可以支撑起他们“儒生”身份的儒学知识与修养,这一部分人就是乡村知识群体中的“伪儒”。但正是这些伪儒以正统儒学继承者的身份掌控着乡村实际的社会与文化权力,或者由于废除科举而不得不主动进城、以儒学背景迎合对新文化有抵触而怀旧的心理,以此在新式语境中继续维持其儒生的文化身份与地位,然而以这种折中和功利的心态,游走于新旧文化之间的儒生能够如此轻易地改弦更张去适应新文化,就足以说明儒学对他们、他们对儒学的双向疏离。这些伪儒成为掌握社会文化的主流,挤压的是真儒学的生存空间,其后果是正统儒学的没落,而新文化也因为掺入了这些投机的伪儒而不伦不类。
三、对乡村文化生态恶化的焦虑心态
在鲁迅小说中,由伪儒所控制的乡村社会除了经济上出现的萧条之外,与之相连的还有文化精神的散漫,同时传统乡土社会赖以维持的伦理价值被抛弃,而人性中的恶由却因失去管束而被释放和放大。同时,鲁迅所书写的在乡村知识群体中,与伪儒的权势与功利相参照的是这个群体中的反抗和失败的知识者,而反抗与失败往往是互为因果。从这些失败知识者的角度,鲁迅从另一个层次表达了乡村文化环境的恶化,以及对于乡村前景的绝望。
孔乙己是一个旧儒生,未能进学成为秀才,失去了成为乡绅的机会,更由于个人的“不会营生”和“好吃懒做”,为了谋生不得已偷窃,口头上坚守着“君子固穷”的道理,“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8]458,最后是被丁举人打断腿,终于死去。丁举人与孔乙己两个同为儒生、但处于社会地位高低两端的经历,显示了此时的功名除了带给儒生社会地位之外,已经不能说明功名的获得者是否能够真正地按照正统的儒学标准行事做人,伪儒成为乡村的主宰,影响的是整个乡村文化。与孔乙己有着相同结局的还有《白光》里的陈士成,将一生的时间与希望都寄托在科举上,结果是考了十六回的科举不中,最后一次落榜后,在反复念叨着“这回又完了”中,绝望而死。从孔乙己与陈士成的悲惨遭遇来看,旧儒生如果不能成为乡绅,其儒学知识就毫无用处,而在那些伪儒那里,儒学只是一个获得身份的名目,对乡村已经失去了维持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的作用。儒学从文化根本变为“无用”,还有《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其身份是“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可知狂人应该上过新学,同时从他病愈后“赴某地候补”也可以得知,他也是一个儒生。新学让狂人得以从他者的角度重新审视早已习以为常的文化传统,开始反抗,并试图影响身边的其他人,但是狂人注定只能是一个孤独的反抗者,他的反抗不仅不被人理解,同时还得不到回应和帮助,狂人和周围环境处于一种不可调和的对立状态。如果继续疯狂的反抗状态,后果只有死亡,因此狂人以病愈为借口,放弃反抗,终于回到他极力想逃出的“吃人”的行列,成为乡绅中的一员。正如鲁迅所说的,中国就“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26]20,狂人清醒反抗的“狂”改变不了染缸的颜色,而自己也变成了黑色的一部分。
《孤独者》里的魏连殳上的是新学,“所学的是动物学”,然而在乡村中却无法用新学来谋生,他只能靠以往的旧学在“中学堂去做历史教员”,但由于魏连殳“是‘吃洋教’的‘新党’”[9]88-89,使他在乡村中成为受到排斥的异类,最终被辞退,只能靠卖旧书来度日。当“我”在旧书摊上看到对于魏连殳来说非常珍贵的藏书——“汲古阁初印本《史记索隐》”后,“我”出于关心去了他家,只见家里只剩了“在S城决没有人会要的几本洋装书”[9]96-97。这个细节显示了魏连殳在新旧交替文化语境中的尴尬地位,虽有新学但只能以教旧学谋生,同时还受到旧学的攻击,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之下,魏连殳确实是一个无法言语的“孤独者”,应该说,他的死是必然的结局。《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曾经也是激进的青年,去“城隍庙里拔去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式以至于打起来”[9]29,但是十年过去,吕纬甫麻木、颓唐,以教授当年他激烈批判的《诗经》《孟子》和《女儿经》谋生。可以预想的是,吕纬甫如果像魏连殳那样“孤独”下去,其结果和后者没有不同,因此吕纬甫和狂人一样,回到原来的文化母体中,“敷敷衍衍,模模糊糊”[9]29地苟且活着。
那么新式知识者是否只有这样的出路,《阿Q正传》里的假洋鬼子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相较于魏连殳与吕纬甫,假洋鬼子留学国外,其在知识上“新”的程度应该远高于后两者,可是这种“新”并未给未庄带来任何新的影响。小说里有这样的情节,赵秀才得知革命党进城了之后,“便将辫子盘在顶上,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钱洋鬼子”[8]542,秀才与留学生的“不相能”表面上看似乎是新旧文化之间的抵触,但实质上他们的“不相能”是在社会权力地位上的争夺,而“革命”让他们有了一个可以相互谅解的机会:伪儒乡绅依靠投机革命获得继续保持权力地位机会,留学生依靠新式知识者的身份理所当然地成为“革命者”,进入到乡村权力阶层,与旧式乡绅分享权力地位,所以,假洋鬼子之所以是“假”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魏连殳、吕纬甫和假洋鬼子三个新式知识者不同的遭遇,似乎是在表明,在传统乡土社会里,如果新式知识者不能主动地与旧乡绅合流,其下场就是魏连殳的死亡和吕纬甫的困顿,而假洋鬼子与赵秀才之间建立起来的“情投意合的同志”关系,使“新”旧顺利合流,或者说“新”终于有机会成为“旧”中的一员,从而得到旧式乡村权力阶层的认同与接纳,这与狂人的“清醒”有着同质性。同时这也说明了在传统乡土社会,新式知识者不是自我消亡,就是主动地将自我消解在旧文化中,鲁迅用文学生动演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染缸效应”。
从孔乙己到吕纬甫,有未能进学的旧儒生,也有半新半旧的知识者,他们的际遇不是走投无路、穷困至死,就是向社会妥协、颓废庸碌,无论哪一种结局,这都是属于向下的流动,由乡村知识阶层堕落到社会底层。与伪儒乡绅与进城儒生的主动的精神堕落相比,向下流动的乡村知识阶层则是被迫的物质与精神双重堕落,且不可自救。实际上,乡村社会里的知识群体并非全是如小说里那样,鲁迅选择性的书写了处于社会与文化地位两端的知识者,身份虽有不同,但却是殊途同归——不同方式与不同形式的堕落。在鲁迅小说里,乡村知识群体集体性的堕落,揭示了传统乡土社会失去了儒学文化的支撑,从乡景上看到的经济性的破产只是表层的,更为严重的是内在精神的崩塌。鲁迅为什么要如此地书写乡村知识群体,其原因可能仍要回溯到他早年的精英主义启蒙主张。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要“立人”,要“尊个性而张精神”[8]58,在《摩罗诗力说》中呼唤“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安在?”[8]102,“立人”也好,“精神界之战士”也好,这样的人绝非平庸之辈,是可以“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8]135、有着非同一般精神力量的精英。如果将其解释为鲁迅呼唤现代知识精英,是对的,但是却并不完全。因为旧文化并不能与传统瞬间断裂,也就不可能出现与旧文化彻底决裂的现代知识精英。正如鲁迅自己说的“背着因袭的重担”,因袭的正是无法摆脱的旧文化传统。这样的人对于传统乡村社会来说,就是能够继承正统儒学的儒生,虽然他们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通过科举进入国家统治阶层,绝大多数只能留守社会基层,因此,也许科举最为重要的作用并不在于选官,而是为社会教育与培养了精通儒学、坚守儒家意识形态的科举失败者——儒生,这些基层精英是乡村社会文化的中流砥柱,学者王汎森称他们为“道德镇守使”*王汎森认为:“在中国,‘道德镇守使’包括乡宦、有科举功名者、绅董、局董,地方上的读书人,甚至作一手好诗、写一手好字的人。”参见罗志田等《地方的近代史:州县士庶的思想与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他们掌握着整个社会文化的方向。因此,如果儒生失去文化担当的责任和能力,也就意味着整体文化精神的失落。
在鲁迅的小说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传统乡土社会无疑是衰落了,这种衰落的迹象不仅表现在“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9]501这样的乡景上,还表现在乡村社会儒家文化精神的整体缺失。可以说,文化之根的腐败溃烂导致了文化之果——乡村社会的凋落与死气沉沉。作为维系文化根系生存、发展的儒生则难辞其咎,他们的集体劣化是导致乡村衰落的重要因素。同时,这种劣化的态势相当严重,以至于阻断了新式知识者改造乡村文化生态的可能性,使新式知识者或出走,或死亡,或沦为庸碌,无一不是现实的失败者、理想的逃跑者,与伪儒乡绅相比,是另一种形式的堕落者。鲁迅将书写视角对准乡村知识群体呈两极,一方面揭示了传统乡土社会衰落的深层原因,更为重要的是表达了鲁迅对于乡村社会日渐恶化的文化生态的精神焦虑:当基层知识精英群体都集体堕落了,“精神界战士”又从何而来,中国社会的未来又何在?鲁迅通过劣化的乡村知识群体表达这种精神焦虑的同时,也意识到此焦虑无法消解的绝望,这实际上宣告了鲁迅早期精英主义启蒙思想的挫败,也为他后期思想的转向埋下了伏笔。
参考文献:
[1] 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M]//欧阳哲生.傅斯年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2] 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3):1-7.
[3] 艾尔曼.变动中的晚近中国传统文化(1400—1900)[J].曹新宇,张安琪,译.清史研究,2015(1):1-13.
[4] 徐祖澜.乡绅之治与国家权力——以明清时期中国乡村社会为背景[J].法学家,2010(6):111-127.
[5] 戴梅可,魏伟森.幻化之龙:两千年中国历史变迁中的孔子[M].何剑叶,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
[6]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4.
[8]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 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 韩愈.原道[M]//韩昌黎全集.上海:世界书局,1935.
[11]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2]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13] 鲁迅. 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4] 张冀.论鲁迅之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反讽意义[J].文艺争鸣,2015(11):89-101.
[15] 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6] 夏济安.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
[17] 左桂秋.科举考试功能下的史学普及:析明代纲鉴史书[J].山东社会科学,2012(7):42-45.
[18] 张献忠.袁黄与科举考试用书的编纂——兼谈明代科举考试的两个问题[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193-199.
[19] 酒井忠夫.袁了凡的生平及著作[J].尹建华,译.宗教学研究,1998(2):78-82.
[20] 杜家骥.清代的官员选任制度述论[J].清史研究,1995(2):9-19.
[21] 夏征农.辞海[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22] 李祥俊,贾桠钊.《近思录》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系结构[J].哲学研究,2014(9):40-46.
[23] 程水龙.江永《近思录集注》版本源流考[J].文献,2007(1):113-123.
[24] 江永.近思录集注·自序[M].上海:上海书店,1987.
[25] 李学勤.四库大辞典:上[K].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
[26] 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