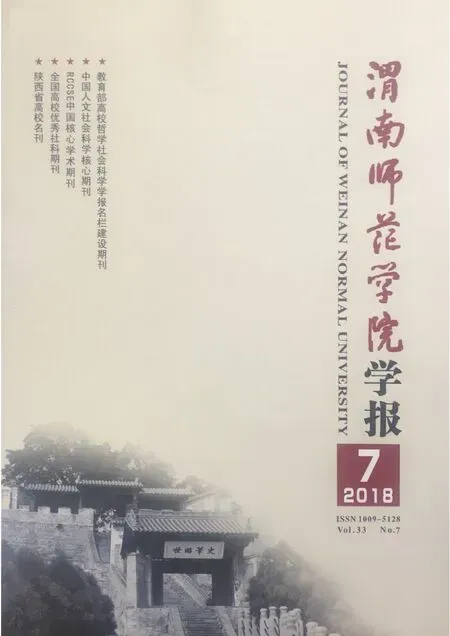论先锋小说对叙事成规的反叛
杨 雷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1)
先锋小说以形式革新为鲜明的标志在文学史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其影响不可忽视。新的审美原则的崛起必然对传统审美规范形成冲击。正是新的审美原则形成了对传统审美规范反叛的阅读效果。先锋作家通过一系列的小说实践证实了“真实观”与“历史观”可能存在的遮蔽性,于是重新设计文学精神的外衣,强调形式与内容的主体间性,突出形式的表达效果。从叙事视角的多变、叙事结构的戏仿拼贴到情感基调的零度和狂欢,先锋小说建构起自主的审美特征。
一、多元变换的叙事视角
对叙事视角的研究,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概括了“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三种类型:零聚焦即所谓的全知视角,叙述者说出的内容比任何一个故事里的人物都多;内聚焦把作者限定在一个故事人物的认知当中,叙述者只能表达符合故事人物身份的话语内容;外聚焦则压抑作者的表述内容,他只能当一个旁观者,他所表达的都是纯客观的。视角一半联系着文本,一半联系着读者,它是一个中介点,透过这个视角既可以发现文本所反映的现象,又可以让读者从不同侧面感受文本的审美价值。先锋小说秉承文学“向内转”的思想,认为全知视角只代表作者个人的思想,不能体现事物的全貌。从零聚焦到外聚焦的视角转变,先锋作家制定了两条叙事策略:一是用元叙事的方法反讽全知视角;二是不停转换叙事视角来多元立体展示文本中真实的世界。
(一)元叙事的运用
元叙事,就是作者在构思自己的故事的时候,故意揭穿故事的虚构性,向读者暴露自己叙事行为,表明故事的线索脉络,探讨作品的一系列问题。先锋作家反主流的姿态驱使他们要暴露叙事的虚构性,暴露历史的言说性,暴露真实的不可靠性,因此元叙事被当作最好的叙事手段而被他们大力实践。先锋作家用元叙事方法介入到小说创作中,就必然用到第一人称,给读者营造一种全知全能的假象:这个故事是本人杜撰的,本人对故事情节、人物心态无所不知。但具体到故事的展开,作者又陷入内聚焦的视点,用感官感知自己的可视视域。正是这种内在的矛盾使读者在真与假之间上下起伏,徘徊不定,体验“辩证的否定”式的反讽效果。
马原是先锋作家里最早用元叙事来暴露虚构行为的作家,他的那句“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曾一时风靡,广为流传。他不仅在叙事层面为中国作家开启了一扇写作方法的大门,还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扇年久封闭的认知的窗户。《冈底斯的诱惑》中第十五章作者突然跳出来跟读者讨论故事的一些问题,并给予解答,这就明显暴露了作者的虚构行为,使得读者不再相信故事的真实性。在《虚构》里,他开始第一句就交代了自己的姓名职业,还表明自己编造的故事多少有点耸人听闻,这为后来作者进入麻风村做了铺垫。作者在麻风村见闻结束后,在第十九章宣告自己的这个故事是杜撰的,他为这个故事的形成寻找了很多的偶然素材,如他老婆认识麻风医院医生,他读过的两本关于麻风病的书,他的司机载过麻风病人。“我还得说下面的结尾是我为了洗刷自己杜撰的,我没别的办法”,正说明了关于麻风村故事的虚构性。
洪峰是继马原之后,在元叙事上实践得比较多的先锋作家。在他的《小说》一文中,开始本来是讲关于照片的故事以及后来与路人互吐口水的事情,作者却在文中插入这么一些话“比如说这篇东西,没写的时候我就已经后悔了。然而我还是一边后悔一边挖空心思写它里边的因素非常复杂,说清了也没用处”[1]150,这种直接把写作行为暴露在小说中的方法,旨在拉开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使小说的现实与客观的现实模棱两可,无法界定。在小说最后,作者还勇于暴露自己的写作目的,告诉读者他写这篇小说就是为了上《作家》九月号。他的《讲几个关于生命创造者的故事》更是把元叙事变成一种魔咒。小说的题目就暴露了“故事”的虚构性,作者在第一段直接跳出来告诉大家“没必要太看重这个题目……大家只需记住这个事实:我的小说之所以有题目,只是出于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尊重,没别的意思”[1]223。
作者们不停地在小说中玩弄元叙事的技法,表达了对现实主义小说隐退作者的方法强烈不满。他们就是要进入到小说中,让作家与叙述者并行存在。元叙事手法是作者与叙述者之间视角的转变,于故事而言,这是一种宏观视角的转换。作者发表对小说的构思评论等问题时,他的视点是落在整部小说的基础上;叙述者对小说故事内部的叙述,是基于故事内在的生成系统,其视点落在故事内容中的场景、人物行动等方面。读者在虚构与现实中穿梭徘徊,真真假假已经不再是重点,重点是对小说直观感觉上的认同。传统小说中,作家一直是幕后的推手,所有的一切都是暗箱操作。先锋作家则把作者暴露在小说中,并把作者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让读者与之交流而形成认同,从而达到新的审美效果。
(二)视角的不停转变
先锋作家在视角方面的转化主要体现在叙述者外视角与人物内视角转换和人物内视角之间的相互转换上。外视角下的所见之物都是比较客观存在的事物,诸如环境描写、人物肖像和动作描写等,而这并不是说人物内视角不关注这些描写,只不过内视角更偏重心理层面的渗透,即使有这些描写,也都投射了主观的情绪在里面。
余华在写《鲜血梅花》的时候,作者在开始部分对阮进武之妻及其现状的描绘就是一种外视角:“阮进武之妻已经丧失了昔日的俏丽,白发像杂草一样在她的头颅上茁壮成长。经过十五年的风吹雨打,手持一把天下无敌梅花剑的阮进武,飘荡在武林中的威风如其妻子的俏丽一样荡然无存了。”作者客观地对妻子进行了外貌描写,写出了阮进武死后十五年里妻子的憔悴与衰老。可以想象她一人带着儿子阮海阔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妻子昔日的俏丽与今日的衰老形成鲜明的对比,阮进武当年的威风也一并消失,这是外视角才能达到的客观效果。再如描写阮进武死时的画面,就是借用妻子的眼睛这种内视角表现出来:“阮进武仰躺在那堆枯黄的野草丛里,舒展的四肢暗示着某种无可奈何。他的双眼生长出两把黑柄的匕首。近旁一棵萧条的树木飘下的几张树叶,在他头颅的两侧随风波动,树叶沾满鲜血。”再如阮海阔离开房子远去时母亲自焚的画面,“红色的火焰贴着茅屋在晨风里翩翩起舞。在茅屋背后的天空中,一堆早霞也在熊熊燃烧。阮海阔那么看着,恍恍惚惚觉得茅屋的燃烧是天空里掉落的一片早霞”,更是把阮海阔眼中的自焚与其内在的心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小说中,外视角占了很大的比重,内外视角总是在不停的转换,外视角为小说提供了背景和故事的连续性,使得读者能把握故事的整个脉络,从而体会其现实的荒诞不经;内视角让读者体会到阮进武妻子的痛苦与怨恨,体会到阮海阔把杀父之仇看得风轻云淡以及为后面他所扮演的传信者而不是杀人者奠定了的情感基调。
二、戏仿拼贴的叙事结构
先锋小说的反讽性,在戏仿和拼贴上最具有表现力度,它们把常态视作主流意识形态的附庸,认为那是对历史的欺骗与遮蔽。他们认为戏仿是对常态事物的辩证否定,拼贴则是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注重的因果联系的反讽。在叙事结构上,戏仿主要是对先前具有的小说母本进行加工戏拟,改变母本所表现的主题意蕴,使之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展现多元化的精神内涵。而拼贴则强行把毫不关联的多个文本并入到一个文本当中,表现小说叙事的多元并存功能,揭露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因果逻辑的逻各斯中心。
(一)戏仿
戏仿并非先锋小说所独创,《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和鲁迅的《故事新编》等等都是对已有原型的戏仿。戏仿主要通过对主题的反叛,对形式的创新,对语言的革新等改变原型的常态写法,正如刘恪说:“戏仿更多注入了性质上的内省(荒诞),词语句法上的调式变化(冷嘲),故事与生活不协调编排(嘲弄),对传统形式与内容的普遍怀疑(非确定性)。”[2]213本文讨论的戏仿,主要从内容上来分类梳理,诸如孝悌伦理、文革、战争、探案、民间故事、武侠和爱情等类别。
在以孝悌伦理为主题的戏仿中,余华的《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鲜血梅花》、洪峰的《奔丧》等可谓淋漓尽致地颠覆了古往圣贤崇尚的“父父子子”之纲,孝悌伦理在这些小说中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在《现实一种》中,山岗、山峰兄弟的互相厮杀,叔侄之间的武力迫害,祖孙之间的冷漠无情,山峰夫妻间的简单粗暴,叔嫂间的苦大仇深,妯娌间的麻木无情,以高度集中的残酷画面感呈现在读者眼前。在这部小说里,没有任何的亲情可言,没有任何的温暖烛照,唯有死与恨成为人物的最终归宿。山峰一脚踢死侄子皮皮毫不愧疚,山岗把山峰绑在树下百般折磨,山峰妻子想办法把山岗遗体肢解而死无全尸,祖母絮絮叨叨孤独终老,人物关系高度紧张,人间伦理毫无体现。这部小说是对以往歌颂孝悌伦理的戏仿,它反讽了当今社会物化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无情。在《鲜血梅花》中,阮海阔对于母亲的死,对于杀父之仇,都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反而他很享受漫游与带口信这样的事情。在《世事如烟》里,祖母与孙子发生乱伦关系,父女亲情被金钱关系所玷污,算命先生奸污少女并牺牲儿子性命来延长寿命,都暴露了传统伦理的分崩离析。
格非的《半夜鸡叫》就是戏仿了民间的“三女婿拜寿”的故事,改写成“三媳妇拜寿讲故事”。《三个姑爷拜寿》以及湖北民间地区的各类版本的“三女婿拜寿”都体现了怀抱不同价值观的姑爷们的针锋相对。在格非的这篇《半夜鸡叫》里,作者套用这种拜寿模式,却换成三个媳妇讲述不同的关于鸡的故事,三个故事交相呼应,互为文本。《古典爱情》就是对《莺莺传》这类古典才子佳人小说的戏仿。“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成婚大团圆”是才子佳人小说的模式,但作者却颠覆了这个模式,落魄公子没有中状元,朱门小姐香消玉殒,公子见卿心切,反而断了爱人的重生之路。《鲜血梅花》则是对中国武侠小说的戏仿,同样是替父报仇,小说却反其道而行之,把主人公阮海阔描绘成不会武功的少年,内心只有漫游,报仇已经无所谓,最后仇人被别人所杀,而他只充当了一个通讯员。《河边的错误》戏仿侦探故事,罪大恶极的杀人者却是一个不明就里的疯子,警察对其无可奈何,法律对其无计可施。作为警察的马哲,枪杀疯子,为民除害,最后反而要接受法律的制裁,为了保全,他被动成为疯子,被关进精神病院。
戏仿是对母本的反讽,戏仿就是要用不一样的视角去重新构造一个事物,这个新事物与原事物形成强烈的反讽效果。先锋小说正是通过戏仿的手法,表达了他们对现成文学秩序的不满,他们要打破传统一元中心论的写作模式,展现别具一格的写作风格,开辟更多小说写作的可能性。
(二)拼贴
威廉·哈蒙在他的《文学手册》中对拼贴解释为:“‘拼贴’(pastiche)源于绘画,原指新潮画家的一种绘画方法,即将毫不相干的事物,譬如报纸、木头、布片、塑料或瓶盖等拼接粘连在某个平面上;文学借用它来指作家将引语、典故和其他怪异表达结合在一起的作法。”[3]传统小说也引经据典,但那都是与所在语境一一暗合,旨在突出主题,从而表现意识形态背后的教化功能。传统小说严格要求因果逻辑,顺序发展,但先锋作家手里的小说却被大洗牌,很多既定的规则被打破,很多新的美学法则被建构,拼贴就是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潮流中涌现出来的。在传统小说的诗学建构中,因果关系是小说的逻辑起点,人文关怀是小说的终极追求,缺少这两个基本点,小说意义和价值将不复存在。没有严格的逻辑关系,小说细节经不起推敲,人物转变的太过突兀,小说就失去了光环。
先锋小说对因果逻辑的观点是否定的,他们认为那是刻意雕刻出来遮蔽历史偶然性的。现实本来就是碎片化的,用线性的关系论写小说是对文学的亵渎。据此,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成为先锋小说的拼贴实践的开篇之作。作者强行把三个互不关联的故事放在一个文本当中。穷布猎熊,陆高、姚亮看天葬,顿珠、顿月兄弟的生活,三者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要强行阐释其互文性,那也就是表达了西藏文化的三个维度,即勇猛、神秘和细腻。这种拼贴结构是对传统小说的一个中心线索的反讽,是对单一情节组织全文的反叛。他的《拉萨河女神》同样是用拼贴这种陌生化的手法组织小说,从而形成新的阅读期待。“为了把故事讲得活脱,我想玩一点儿小花样儿,不依照时序流水式叙述”[4]294,马原把人物设置成数字符号,这些数字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只是偶然相遇,并在河边随机组合。洪峰在《瀚海》中,也继续玩弄这种碎片化的拼贴,疯姑娘与我妹妹,奶奶和爷爷,姥姥和姥爷,二哥和琳琳,姐姐和大哥,我和雪雪,多个组合项并列发展,项与项没有必然关系,宛若一幅家庭百态图。各个子项同时在文本里变化发展,互不关联,如同清明上河图一样,从各个角度都能发现故事,但又各取所需,各有所想,只不过同享一个文本框。
以上小说的拼贴是多个故事的拼贴,完全断绝故事之间的联系,这是先锋实验的标志。但小说不能完全套用这种模式,于是先锋作家们又实验了一种场景大挪移的写法。在格非的《半夜鸡叫》里,故事的主线是三媳妇给老太讲故事拜寿,但小说并不是写拜寿的场景,而是主要讲述每个媳妇所编撰的关于鸡叫的故事。天佐媳妇讲周扒皮学鸡叫督促长工们夜以继日的劳作,天佑媳妇讲周扒皮学鸡叫与弟媳小倩通奸偷情,天宝媳妇则讲述小毛刺绣寻母亲,最终得知母亲始嫁周小皮。三个故事虽有人物伦理关系,但都是独立成文。作者在一个大的情境里拼贴出这三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有自己完整的生长系统,这让读者对文本产生新的阅读体验。在如《往事与刑罚》中,余华把1958年到1971年的几个血腥场面拼贴在一起,从车刑、宫刑、腰斩到点天灯,每个场景都骇人听闻。作者对四个日期的空间化血腥描述,把碎片一片片组合,把毫无联系的四个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刑罚场面写得惊心动魄,余悸难了。
三、零度狂欢的叙事语言
要厘清先锋小说的形式反叛,还得回到语言本体来讨论,因为先锋作家首先是对语言的变革再到形式的创新,语言是彰显反讽精神的重镇。语言的解压与思想的解放互为表里、互为因果。先锋小说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进行反讽时所裹挟的冷峻与狂欢质素成为显性特征。但语言的冷峻与狂欢又不能截然分开:冷峻背后默认了无止境的情感宣泄,故血腥、暴力、性等欲望的滋生是冷眼旁观的结果;狂欢的语言表述把禁区的事物放大到极致,看似疯癫却又能在现实中寻找到蓝本,引人沉思。语言的反讽正是基于这两者而产生强烈的先锋效果。
(一)冷峻陈述
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打磨语言、刻画人物、构思情节,其目的就是要把文本的中心主题展示出来,把潜在的意识形态表现出来,从而达到文学审美化的高度。先锋作家首先批驳的就是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对语言的塑造造成了语言本体的异化。先锋作家认为传统现实主义的语言是“带着镣铐在跳舞”,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开镣铐,把语言从规约中解放出来,重新组合秩序,重新感知语境,重新描述世界。冷峻的陈述是相对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部分触及心灵禁区而言的。这种冷峻陈述即所谓的零度情感,用旁观者的姿态关注一切,不再强调个体情感的带入,叙述者完全隐退为一个冷冰冰的记录者。叙述的语言不再顾及主体情感、人物形象塑造、结构逻辑等,从而提供给读者一种更加真实的印象。
借着零度情感的语言手段,先锋作家们对暴力和死亡展开了血腥的暴露。余华在暴力书写方面声名卓著,成果累累,他的《现实一种》《古典爱情》《难逃劫数》等淋漓尽致地向读者展示了嗜血的江湖风云。在《现实一种》里,写到皮皮虐打堂弟时的句子是“他就这样不断去卡堂弟的喉管又不断地松开,他一次次地享受着那爆破似的哭声”,童年时光就被暴力侵浸,模仿父亲虐打母亲,并在这种施暴当中寻找快感,这让善良的读者难以接受。在写到皮皮趴在地上舔血的情节中,皮皮“望着这摊在阳光下亮晶晶的血,使他想起某一种鲜艳的果酱。他伸出舌头试探地舔了一下,于是一种崭新的滋味油然而生”。作者完全摒弃了作为一个被道德伦理豢养的成年人应有的人文关怀,他把儿童的那种充满好奇与童真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面对暴力和死亡,作者没有丝毫的同情和规避,反而十分迷恋这种冷峻的描述。山岗被枪决之后,山峰的妻子冒名为其妻而捐献了山岗的遗体,于是山岗的身体被大卸八块,死无全尸。三十来岁女医生一刀刀剥掉了山岗的皮;胸外科医生切断软骨,打开胸膛,取出肺叶;眼科医生取眼时还开玩笑说那执刑的武警或许就是某一个眼科医生的儿子。读者读到这些分解尸体的画面不免心有余悸,难以接受。作者就那样冷冰冰地把解剖过程一一展开,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在《难逃劫数》中,结婚当晚露珠在东山脸上泼了一瓶硝酸,从此东山毁容了。作者在描写这个过程时,沉着冷静。露珠摸东山的脸,就感觉如同水果皮一样光滑,然后撒了一滴硝酸,“她听到了嗤的一声,那是将一张白纸撕断时的美妙声音”,接着她把一小瓶硝酸全泼在东山脸上,“于是她听到了一盆水泼向一堆火苗时的那种一片嗤嗤声”。东山哇哇大叫,手忙脚乱,最后“那些焦灼的皮肉像泥土一样被东山从脸上搓去”。画面感鲜明生动又没有作者情绪诱导,作者冷静的笔法让读者饱尝了“犯罪的快感”。在写到东山杀妻的时候,作者用烟灰缸、凳子、衣架、台扇等工具作案,硬是把露珠活生生给打死,最后“脑袋像是一个被切开的西瓜一样裂开了”。面对暴力和死亡,用异常的冷静态度去观照并描摹,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也有体现。陈宝年为了十亩水田断送亲妹妹的一生,蒋氏为了生存在死人塘边砍杀乡亲,陈玉金上城做竹篾匠被阻就砍杀妻子,这些情节都把人性的恶毫不留情地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苏童的零度情感叙事还有《罂粟之家》《十九间房》《游泳池》《刺青时代》等,都是站在一种十分客观冷静的高度去叙述暴力和死亡的场面,把读者带入到“血迹斑斑的现场”,让读者在残酷的情境里释放内心对丑恶的臆想,从而达到一定程度的真实。
(二)狂欢戏谑
王一川在《当代自我的末路狂欢节》里对先锋小说的人物进行四类(类象、寓言、能指和类型)描述,认为人物已经偏离了卡里斯玛式的原创性和神圣性,走上了移心化的道路,“显示其末路狂欢迹象,从而成为当代自我聊以自娱的末路狂欢节”[5]。人物的刻画离不开语言的表述,先锋小说的狂欢戏谑主要体现在语词的恣肆和陌生化的变形上。
莫言的语言可谓是油滑恣肆的代表,他充分利用东北高密民间的精神资源,把民间的语言写进小说,展示出接地气式的精神状态与人物野性的生命力。莫言语言的恣肆首先体现在粗鄙话语上,在他这里,丑恶的低俗的描写已经百无禁忌,粗鄙反而获得美感,庸俗反而生成诗意。如《透明的红萝卜》里开篇就有队长的骂骂咧咧:“他娘的腿!公社里这些狗娘养的,今日抽两个瓦工,明日调两个木工,几个劳力全被他们给零打碎敲了”。[6]队长看到十岁左右的黑孩儿,其语言粗鄙,反而体现出了队长的性格特征。队长说:“黑孩儿,你这个小狗日的还活着?我寻思着你该去见阎王了。打摆子好了吗?”这种叫骂式的对话,体现出黑孩在村里的地位以及他悲苦的命运。这种人物粗鄙的语言在莫言小说中不胜枚举,从一定程度体现了狂欢语言背后的叙事风格。在《欢乐》《酒国》《红蝗》等小说中莫言不拘规则纵情挥洒狂欢,语言极度夸张、铺陈。在《欢乐》中,莫言把屁、屎、汗等一起写进小说里,把顺口溜、民间歌谣等杂糅在一起。农民出臭汗,小姐出香汗,低等人放臭屁,高等人放香屁,这些拿粗鄙事物揭露事实,披露丑恶,戏谑秩序,成为莫言小说语言洒脱恣肆的一个鲜明的标志。《红蝗》对四老爷拉屎极尽揶揄,语言十分具有反讽性:“四老爷蹲在春天的麦田里拉屎仅仅好像是拉屎,其实并不是拉屎了,他拉出的是一些高尚的思想。混元真气在四老爷体内循环贯通,四老爷双目迷茫,见物而不见物,他抛弃了一切物的形体,看到一种像淤泥般的、暗红色的精神在天地间融会贯通着。”如此对大便描写,还上升到形而上的思索上,审丑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戏谑了严肃文学的愉悦教育作用,在这里只看到作者对语言的玩弄和嬉戏,在一定程度上是狂欢化的表征。
对语言的陌生化变形,是先锋小说对传统小说语言最具反讽性的实践,这种实践摒弃传统的语言经验,把语言规范带入到无尽的深渊,把语言规则撕碎之后,重新排列组合语项,创造新的审美感受。作者初尝变形的欢乐便一发不可收拾,从怪异的词语搭配到异常的比喻比拟再到能指的失效,先锋小说的语言千奇百怪,既是一种戏谑狂欢的现象,又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多元的美学效果。
怪异的搭配冲击着读者的既定语言习惯,给予读者无尽的新奇与梦幻。格非在《青黄》里说:“枯黄的树叶和草尖上覆盖了一层薄霜,鸟儿迟暮地飞走了。”孙甘露在《我是少年酒坛子》里说:“世界艺术地远去,我和我的诗句独自伫立。”格非在《没有人看见草木生长》里说:“我想用一种我自认为是新的方法来结构我的小说。”,都是在词性上大做文章,疏离常规,变成奇异。“迟暮地”与“鸟儿”搭配,是把形容词化用副词;“艺术地”与“世界”搭配,是把名词化用副词;“结构”和“小说”搭配,是把“结构”动词化。这种用法在古代汉语用得比较多,但现代汉语语汇丰富,发展成熟,对词的活用不甚明显。通感的用法在先锋小说中也十分明显,但先锋作家在运用的时候也力图新奇,反常搭配。《世事如烟》的“他们的声音在这雨天里显得无比鲜艳”,《现实一种》的“堂弟‘哇’的一声灿烂地哭了起来”,《灼热的天空》的“只有滚烫的阳光大片大片地落下”等,让读者的感觉发生错觉,仿佛遇到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事物时所表现出的手足无措,胡言乱语,可又能感知一二,妙不可言。
先锋小说对个体的内在感知比较关注,个体情感的表露又不能直抒胸臆而丧失陌生化的效果,于是小说中很多怪异的比喻便纷至沓来。如余华《现实一种》里的几条比喻:
例(1)他一直飘到他对面,然后又飘下去坐在了凳子上。接着用一种像身体一样飘动着的目光看着他。[7]26
例(2)“你为什么不打他一拳?”他听到妻子这样说。妻子的声音像树叶一样在他近旁摇晃。[7]30
例(3)失去了皮肤的包围,那些金黄色的脂肪便松散开来。首先是像棉花一样微微鼓起,接着开始流动了,像是泥浆一样四散开去。于是医生们仿佛看到了刚才在门口所见的阳光下的菜花地。[7]55
例(1)和(2)中,目光像身体一样飘动,声音如树叶摇晃,这都是“他”那难以言表的感觉。面对亲兄弟的残暴,他的内心五味杂陈;面对老婆的埋怨,他欲说还休。“飘着”的身体和目光,“摇晃”的树叶和声音,使他的内心细腻的感情跃然纸上:他的内心是激动的,焦灼的,可作为男人,他不能表达出他的恐惧、悲愤和不安。例(3)写出了外科医生割开皮肤后的那一瞬间的动态,脂肪如棉花鼓起,如泥浆流动,如菜花金黄,既有历史性的解剖行为变化过程,又有情感的微妙变化的文本互文性。还有一些比拟手法怪诞出奇,却能反映叙述者抑或人物的内在心理。如格非《夜郎之行》中“我看着朋友们相继离去。孤独的阴影又一次攥紧了我”,吕新《发现》中“一棵苍老的桂树用叹息删节着时光”,《古典爱情》里“一旦认出小姐的坟冢,小姐的音容笑貌也就逃脱遥远的记忆,来到柳生近旁”。“孤独的阴影”变成主体,“我”变成被动的一方,突显了个体的无奈与孤独感的浓厚;桂树用叹息删节时光,把桂树的衰老表现得生动自然,如人一般感叹岁月的无痕;关于小姐面容的记忆被唤醒,坟冢不经意间成为记忆之门的钥匙,模糊的记忆总在坟冢出现时被重新找回。
先锋小说在语言上更大的反讽就是消解了语言的所指功能,语言从常规符号中解放出来,变成一种感觉的空灵之物。孙甘露在小说的语言观念和写作观念上颇有研究,他笔下的小说具有鲜明的后现代性,那就是“不谈世界、对象、真理、历史、社会、人物,而只是谈语言、符号、文本、语境、关系、结构、生成、转换、消解”[8]。
他的《访问梦境》就是各种文体的杂糅之物,无中心无所指,全然一篇语言的旅行散文。小说错综复杂,没有线索脉络,几十个段落独立存在,内容飘忽不定。所谓梦境,就是要呈现意识流的东西,关注瞬时的情感思绪。小说洋洋洒洒,却没有任何可以阐释的对象,没有任何意义的解读,语言自立自足,全然演绎成为语言而语言的叙述游戏。他的《信使之函》更是体现了语言能指的时效性。全篇运用54个“信是……”的判定句式,看似能指很多事物,然而信作为一个能指符码 ,被加载了54种所指的含义,就改变了信的定义的唯一性和准确性,使其陷入了某种不可知论。
先锋小说的形式变革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它还是理论内涵上的转变,其背后有强大的西方话语资源影响和当时社会思想文化革新的需要。形式的反叛表达了新的审美意识的觉醒,显示了现代主义话语与中国思想更新的合谋关系。小说技术层面的发展昭示了文学的多元性与反抗性,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有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洪峰.重返家园[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
[2] 刘恪.先锋小说技巧讲堂[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3] 何林军,肖建英.拼贴与戏仿:《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J].中国文学研究,2007(3):13-15.
[4] 马原.1980年代的舞蹈[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
[5] 王一川.当代自我的末路狂欢节——先锋小说人物与典型的移心化[J].大家,1994(3):161-163.
[6]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J].中国作家,1985(2):179-203.
[7] 余华.现实一种[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8] 王岳川.九十年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批评”[J].作家,1995(8):70-73.